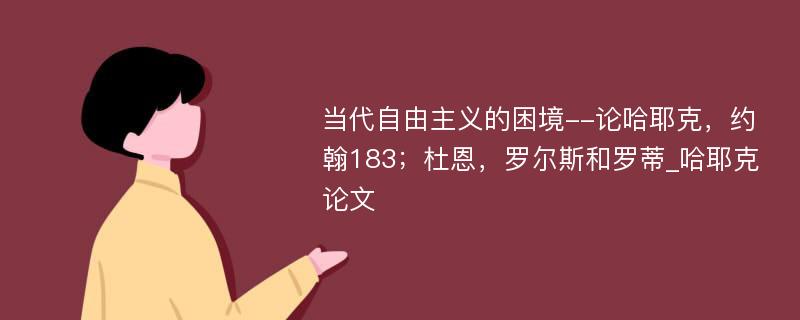
当代自由主义的困境——论哈耶克、约翰#183;顿、罗尔斯和罗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困境论文,当代论文,哈耶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常感谢高瑞泉教授的邀请,使我十分荣幸能有机会来华东师范大学主持第九期大夏讲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当代自由主义的困境——论哈耶克、约翰·顿、罗尔斯和罗蒂”。正如在座诸位知道的那样,这个演讲其实是我这次在华东师范大学系列演讲的第三讲。前两讲的题目分别是“人类学文化观念中的知识论意蕴”和“文化观念中的知识论意蕴:中西哲学的讨论”,其出发点就是去探讨如何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会通中西。
一
我们知道,20世纪许多中国思想家都主张会通中西,为此他们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很多人并不重视哲学在会通中西方面的重要性。如罗蒂(Richard Rorty)出于其反基础主义的立场,认为哲学在文化中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不过是跟物理、文学等一样是众多地位平等的学科中的一门。会通中西完全可以通过贸易等方式来实现,不一定非借助哲学不可。而港台地区的新儒家虽然长期致力于从哲学上会通中西,但近来在杜维明等人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历史学的转向,即避免把儒家思想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上,而是强调通过历史研究从具体的存在中发现普世价值,从具体的历史挖掘中觅得洞见,进而创造性地阐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对此,我都不敢苟同。第一,尽管罗蒂认为整个社会就应该关注比较具体的问题,不要高谈什么哲学性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观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哲学性的主张。第二,杜维明认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如平等、自由、经济发展等已经越来越被所有人接受,而且崇尚男女平等、保护自然、宗教、多元主义等价值也是世界潮流,所以,以此为基础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将有助于克服世界的分歧和冲突。而在我看来,尽管很多人肯定上述理想和价值,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很深的分歧,尤其是一些哲学性的分歧并不那么容易克服。因此,如果要建立并推行全球伦理,如果要会通中西,仍然需要哲学。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哲学分歧或者观念冲突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首先是有关知识论(epistemology)的分歧。经典看法认为,知识是经过辩明的真信念,这样的信念具有客观性。但17世纪以来由笛卡尔、休谟、康德、尼采、韦伯(Max Weber)、波普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引发或推动的近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以下简称GMWER)对知识的本性展开了更为深入而复杂的讨论:什么是知识?知识有效吗?如果有效,知识的边界是什么?如在知识范围的界限问题上,休谟坚持认为不存在关于道德实践的知识,康德认为没有关于本体之终极本性的知识。这些在认识论上的悲观看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相信知识只有以经验现象为依据时才是可能的,“刨根问底”和构建一个“体系”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场革命又可称作认识论上的悲观主义革命(epistemologically pessimistic revolution)。当然,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有许多人在认识论上仍然持有乐观的态度(epistemologically optimistic attitude),如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所展示的那样,更不用提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之后的罗马天主教哲学,以及众多通俗的、政治的和学术的讨论。再者,即使休谟和康德对人类理性的可错性(fallibility)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们依然允许人们继续信任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理性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德性的结合,运用归纳和常识去做出有关生活世界包括人类历史的客观真实的描述性和因果性的陈述。换句话说,不论知识范围的界限是什么,人们还是可以获得由“理性”、“德性”等普遍观念所构成的平台(platform),并以此为基础去自信而客观地对这个世界给予描述,评价人们的各种不同行为。
其次是在有关历史的因果模式(patterns of historical causation)及其对目前政策制定的潜在影响方面的分歧。历史应该被视为一个目的论的过程吗?它遵循从某种黑格尔式的宇宙论法则演绎而来的发展规律,适用于全球的所有的社会,而无需考虑他们的文化差异吗?难道远古时代某些核心知识的发展就能决定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吗?与多数的中国和西方编年史都有黑格尔式哲学倾向即喜欢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做宏大叙事的概括不同,韦伯所代表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谈论历史发展的逻辑、人类历史的总体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因果模式只能按照经验主义去决定,即将历史分解为文化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变量,对这些变量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并探究它们如何不断地互相影响。
最后是一个牵涉普遍的人性本质(the nature of universal human nature)的分歧,更为确切地说,是存在于普遍的人性冲动和利他主义之间,或者说,乌托邦主义者跟那些持所谓“幽暗意识”(对历史中永恒的道德黑暗的意识)者之间的争论。究竟是“对财富和政治权力的贪婪追逐”还是叔本华(Schopenhauer)所看到的“人们更复杂的、局部无意识的自私冲动机制”才是抗衡利他主义的主要冲动?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能实用地以纯粹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还是应该以中庸之道的“礼”为基础?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无视国家民族利益,促使政治生活转向利他主义时代的“世界潮流”,还是应该追随波普的思路,在神魔混杂的历史中一点一滴地寻求本土和世界的进步?
二
要解决上述哲学分歧或观念冲突,不仅需要来自历史知识方面的资源,更需要唐君毅所谓的“会通”,即一种系统的哲学分析(systematic philosophical analysis)。在当今时代,对于系统之哲学理解的追求应该旨在提出一种可以说明如何能够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道德—政治进步(moralpolitical progress based on knowledge)的哲学。与此同时,这种哲学应当处理:a)文化观念的认识论意蕴,b)韦伯所揭示的在历史因果性方面的诸多复杂问题,c)有关永恒的神魔混杂的历史,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妨碍人类理想之完全实现的问题。这就是说,这种哲学必须应对上面提及的那三个重要的哲学分歧或观念冲突。
由此观之,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最后都是一种政治哲学,都牵扯到政治。正如斯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学派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从修昔底德、柏拉图到洛克、卢梭、穆勒甚至包括海德格尔的众多西方名家的名著之中。同样的,在萧公权、陶希圣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政治思想”也已被广泛运用来描述从孔子、荀子到董仲舒、柳宗元、王安石、司马光、黄宗羲、康有为,以及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的著名学者的各种不同思想。这里使用的“政治”一词,在本质上是指国内和国际的政府行为及其直接背景。相异于政治学对描述政治时事的兴趣,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则致力于对政治活动的理想形式或准则进行定义和辩明。
在我看来,改善人类生活的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不可能总是果断的(resolute)——除非它们在逻辑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就此而言,当主流的悲观主义认识论或对或错地否定了政治目标和社会规范能以知识为基础的时候,果断的政治行动要么就被预先排除了,要么不管怎样都被禁止了——这就是被施密特(Carl Schmitt)归因于自由主义政治的无力困境(dilemma of impotence)。可事实却相反。最近的百年所见证的东西方许多的政治运动倒是过度的果断,而且还追随饱受诟病的乐观主义认识论。因此,旨在追求政治进步的那些果断的却又负责任的政治行动是否可能,似乎就取决于政治目标在何种程度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能否避免“跷跷板效应”,即从果断的行动倒向认识论上的谨慎,还是从认识论上的谨慎倒向果断的行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与上面谈到的三个哲学分歧或观念冲突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认为,一种好的或合理的政治哲学应该对这三个分歧或冲突给予合理的处理,或者说,一种好的或合理的政治哲学应该充分回答关于文化和知识的问题,以及有关历史因果性和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的问题。
限于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先着重讨论一下文化和知识的问题,然后再着眼于合理的政治哲学应该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合理处理,来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若干代表略作评述。前面已经提到,在近代西方发生认识论大革命的同时,许多人仍然在认识论上抱有乐观的态度。事实上,这种有限的乐观主义认识论直到这场大革命遭遇文化的观念时才真正遇到了严肃的挑战。作为文化观念的来源之一,以赫尔德(Herder)为代表的德国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变化不居的历史、语言和其他情况不仅形成了风俗习惯,而且形成了世界观。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风俗习惯这一旧观念被认为构成了文化概念的核心,正是业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原本看来难以理解或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意义的言与事变得有意义。随着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阐释》一书在1973年的出版,文化越来越被当作是“真实生活的非形式逻辑”和“社会行动的象征维度”。不过,文化理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格尔兹的理路。以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为核心的习俗观念,不仅与维特根斯坦、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罗蒂等哲学家所推动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互相配合,而且与博克(Kenneth Burke)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学者有关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彼此激荡,促使人们认识到对文化模式的理解,只研究可观察的当地人的行为和对他们的访谈是不够的,还必须补充以对那些篇幅长得足以表达世界观之多重复杂性的书面文本的广泛研究。
换句话说,最好能用话语(discourse)的观念来描述文化生活。话语是一个动态变化着的语言现象,人们通过提出竞争性的存在争议的主张相互辩驳。不过,基于在定义生活目标方面的共享前提、在世界中实现这些目标的既定手段,以及其他既定的条件,包括阻碍这些目标实现的条件和用以区别有意义与否的基本的认识论标准,这些主张至少提出了一个暂时性的无争议的共享议程。这些前提被共享它们的文化群体认为是无可争辩的,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就指出,“抽象的观念……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自明的真理,就象默会的预设一样起作用。”我更愿意将这些抽象的观念、默会的预设称为“成功思维的规则”,对于使用它们的群体来说,这些规则看上去就是些陈词滥调,譬如我所属的群体所认为的“种族主义是坏东西,自我意识是最重要的目标,论证应该由恰当使用一种历史的语言所构成,清晰性要求对描述性的、因果性的、预言性的、评估性的、建议性的以及认识论的观念予以区别”,等等。
叔本华的两个洞见使这种把文化研究归约为话语描述的做法更趋于复杂。他认为,一方面,鉴于自我意识的限度和无意识的作用,话语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晰;另一方面,构成话语之不变基础的利他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动机和行动之间通常存在着矛盾。基于这种矛盾,话语从语言互动历史形式转变成为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对其加以分析的人们的批判对象。换句话说,在有关话语模式的“符号学进路”(semiotic approach)之外,必须补充一个规范性的、哲学的进路,即去追问一种话语如何以及为什么应当被修正。正如贝拉(Robert N.Bellah)所指出的,应该把文化看作是一个进化的、可修订的、有些未定形的“论证”或“问题群”(problematique),而不是一套恒常不变的趋向(orientations)或“系统”。
当我们用话语这一复杂的观念去完善文化的概念时,穆勒哲学所代表的有限的乐观主义认识论开始解体了。这就是说,人们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有关理性和道德的普遍主义的、算法式的、超文化的平台(universalistic,algorismic,transcultural platform),基于这一平台人们可以客观地来描述和评价由历史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和话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分析话语时,被认为仅仅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重新描述一种别的话语,他们并不拥有可以把任何一种话语评价为较之另一种话语更接近真理的那些普遍主义的、算法式的标准。在库恩(Thomas Kuhn)思想的影响下,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认为即便是在自然科学中,相信这些“客观主义的”标准的可得性(availability)也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戴维森提出了他那个广受赞誉的、排除了任何对知识之完全掌握的可能性的论题,即“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的观念。在他看来,任何对知识的追求都将使有关世界的本真知觉、一个人对世界的言说以及别人解释这个人的言说的方式这三者变得模糊起来。当然,从话语的观点来看,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任何关于生活世界的描述性的、因果性的、预言性的、评估性的、建议性的和认识论的命题之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里所论及的由文化所形成的话语。这一观点,特别是当其被运用到在逻辑上至关重要的有关历史之因果模式和当下的政策建议之间的关系上时,坚决反对目前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的如下观念:所有文化中的经济和政治决策都遵循一个超文化的、算法式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标准。
总之,GMWER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证据支持着一个有关文化的重要论题,即由文化所形成的各种取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而且对用以刻画人类生活和世界之剩余部分的范畴,包括学者们所使用的范畴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这一论题不仅在经验基础的问题上引发了争议,而且招致了对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relativistic historicism)的恐惧,但是,如果这一论题如我相信的那样是合理的,那么它是否威胁到了知识的可能性?或者是否使得一种对于知识范围之新的、更为清晰的把握,并因此使得一种走出相对主义困境的途径成为可能呢?在我看来,除非我们首先理解了GMWER所发现的这一重要的经验事实:文化取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有关什么是真的观念,并因此而妨碍了对知识的追求,否则理解知识的范围、把握知识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去增加知识,以及由此增加个人基于知识而选择生活的自由,都将是不可能的。
三
正如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当今时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一种可以说明如何能够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道德—政治进步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必须充分回答关于文化和知识的问题,以及有关历史的因果性和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当代西方社会有一个几乎是常识性的观点,即西方的现代性(Western modernity)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哲学蓝图的基础之上,这个蓝图可能就是自由主义哲学(liberal philosophy) 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的某种结合。着眼于合理的政治哲学应该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合理的处理,接下来我就对哈耶克、约翰·顿(John Dunn)、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蒂所代表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略作评论。
在有关文化和知识的问题上,哈耶克对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予以了充分的阐明。在他看来,科学构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平台,这一平台超越了由不同的文化视角所构成的历史变迁,置身其上将有助于人们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当然,他也非常重视来自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而且他强调人类生活表现为以“思维图式”(schemata of thought)为基础的“自发地”发展着的文化结构,而这些图式也就是一些“往往是无意识拥有的有关何为正确与正当的观念”。此外,在这些文化样式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哈耶克强调“文化”和“理性”的彼此依赖。不过,他完全相信可以非常精确地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来区分知识与纯粹的文化格式塔(mere cultural gestals),因此他毫不怀疑他可以站在由普遍真实的原则所构成的平台上来审视人类的存在。
哈耶克强调他正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科学地”处理所有问题,并对其朋友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最终的认识论立场。不过,他实际上将波普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所作的那些基本区分弃之不顾,认为科学可以揭示所有人都应当遵从的规范性原则,而无论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如何的不同。
哈耶克相信,有关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科学研究所揭示的,是由“内在欲望”、“理性”和创造“复杂的文化结构”的能力所构成的普遍人性。此外,尽管个人目标和文化模式极为多样,但人类通常都拥有相同的基本目标:“生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平”、“正义”、“道德”和“自由”,而这些目标都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
根据这些普遍的规范,哈耶克就可以“科学地”描述和评价从“部落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变迁;也可以证明最能实现普遍的人类目标的文明社会将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企业,它不仅拥有重要的政府功能,而且拥有一种将西方核心的德性传统的本质与谋利动机之正当化结合在一起的“精神气质”(ethos),还可以公开指责各种非理性的知识和政治模式,如弗洛伊德主义以及那些相信政府能够集中而有效地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者的“致命的自负”。
总之,哈耶克在认识论上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学者们能够站在一个由普遍主义的理性和道德原则构成的平台上来对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做出经过客观辩明的描述性的、因果性的、预言性的、评估性的、建议性的和认识论的陈述。由此,他提出了一种颇有影响的基于知识的进步予以概念化的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主义未能就有关文化、历史因果性和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四
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约翰·顿所提出的自由主义与众不同。他尊重但并不强调GMWER有关文化如何限制了知识之范围的论证,高度重视韦伯所指出的有关历史因果性的那些复杂问题,同时又回避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不过,他未能提出一个以追求基于知识的进步为目的的果断行动的概念。约翰·顿相信近代政治学家洛克所代表的主流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古典理想,但是,他一方面承认他能够反驳文化相对主义并证成那些理想的唯一方式就是以一种纯粹强制的方式将它们等同于“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分享了韦伯对于历史的沮丧,认为在其中看不到有效的实现那些理想的可能性。
五
罗尔斯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因其精巧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和“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概念而声名显赫。凭借这两个概念,他致力于澄清民主的规范性原则。不过,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一个他所提出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认识论观念,即“合理性”(reasonableness)。
一方面,像约翰·顿一样,罗尔斯尊重GMWER针对理性完全从某种说明作为总体之人类存在的本质的可证实的“整全论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出发来推衍道德规范的能力所提出的质疑,他认为任何“理性的”(rational)个体都将发现任何这种“整全论说”都无从被判定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换言之,罗尔斯基本上接受了波普关于知识的定义,即知识是尚未被经验实验所否证的猜想。
另一方面,罗尔斯坚持认为,除了认识到他们的“整全论说”是不可证实的以外,通过阐明将“常识”、科学知识、“经过充分反思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以及赋予“有关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传统”(如“民主社会的公共的政治文化”)以特权的决定这四者整合在一起的“合理性”这一概念,所有“理性的”人们还能解决如何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问题。
由于来源于这四种观念,合理性的概念呼唤一个由“理性的”、“自由的”、“平等的”和“道德的”公民所构成的公正社会。于是,在自由社会中展开于拥有彼此矛盾的“整全论说”的人们之间的竞争就将是和平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将被限制在那些所有公民认为是“合理的”(reasonable)范围之内。通过想象具有合理性的人们在合理的条件下将如何为他们所不认识的合理公民设计一个公正的社会,剩下的问题不过是去规划财富的公正分配罢了。
因此,与约翰·顿的自由主义不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基于知识的进步概念。不过,相异于约翰·顿,他对文化观念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尽管一再地提起康德,他却忽略了有关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常识”和“反思”(如果不是“科学”的话)这一康德之后的思想。罗尔斯也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始终坚持其有关创造一个由“理性的、自由的、平等的和道德的公民”所管理之社会的提议的可行性。如果历史可以充当指南,那么进步的问题就不是去想像这样一些理想的存在者将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去改进一个在历史中是具体的公民群体的政治生活,这些公民最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自由的、平等的和道德的。至于历史因果性分析中那些韦伯式的复杂情况,在罗尔斯的思想中却被排除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果性的命题已是公认的事实。
六
至于罗蒂,他的观点即使没有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之一,至少已引起了整个西方哲学界的极大关注。凭借“好战的反权威主义”(militaint antiauthoritarianism),罗蒂的确对进步展开了深入的概念分析,他完全承认一个人从文化上继承而来的词汇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其有关世界的描述产生了影响。但是,老实说来,他在政治上的建议是乌托邦主义的,而且他对历史因果性问题上的韦伯式思考也多有忽视,甚至否认进步应当或能够建立在对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
罗蒂充分利用了GMWER所主张的知识的有限性来拒绝所谓客观的实在和原则。由此,他接受了康德之后学术界所强调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是如何地塑造了有关何为真理(what is true)的信念,也就是说,历史、文化和语言是如何地取消了置身其上就对所有形式的存在予以客观描述与评价的有关理性和道德的跨文化平台。罗蒂思想的惹人瞩目之处就在于他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使得GMWER的这一立场更为激进,然后再暴风骤雨般地为之高唱赞歌。
妨碍罗蒂将其理想与理论统一起来的主要自相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重视自由和“自我创造”(self-creation)这些浪漫主义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否认个体能够自主地运用其批判的反思能力来尝试获得作为有关客观如此之物的真观念的知识,也不提及有关规范的知识。在作出上述否定的同时,罗蒂坚持避免把任何一种对于人类生活的理想归结为客观所与(the objectively given)同对它的自我回应(a self responding to it)之间的一种联系。正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所宣称的,所与的观念是一个“神话”。任何的客观所予都是和有关个人之特定历史背景的变动不居的词汇表交织在一起的。不应当把个人视作自我或“认识主体”,而应看作在科学上可观察的一连串行为。就像赖尔(Gilbert Ryle)所指出的,“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是不存在的。由于缺乏思维的自我,如同蒯因(W.V.Quine)所认为的,意义无论如何就不会独立于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词汇表之语义和句法形式而存在的,也不存在独立于基于这个词汇表而形成的“单词游戏”的“心智主义的”(mentalistic)思维过程。
由此,对罗蒂来说,由共享的词汇表所形成的真理和道德的定义,就不可能受到在理智上自主的、具有创造性的、效仿苏格拉底的个体的挑战,而这些个体效仿苏格拉底的地方就是去思考自身所处时代的那些在俗成意义上(conventionally)是循环的观念是否与超越它们的任何一种对于真理和道德的理想相一致。没有任何一种批判性视角可以超越那些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俗成的观点模式。这样,尽管人们在其写作中所充分展现出来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是不容否认的,罗蒂仍然试图把这种能力转变成所承继的文化与历史的偶然性的附属品,而不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把它看成是一种跟所承继的文化理念前提密不可分的却又存在张力的自由的心智过程。
于是,对罗蒂来说,“自我创造”是最为重要的,但他仍然强烈否认有人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创造性地、有效地去寻求一种与“当下的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思想。换句话说,罗蒂没有看到历史中俗成的观点与那些对其发起挑战并进而形成新的传统的具有创造性的不和谐声音之间那种复杂但显然又确是辩证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他尝试把“当下的理论和实践”看做是一组为在社会中所表述出来的任何观点提供唯一辩护的俗成信念。由于坚决否认一个观念的证成可以从客观实在这一概念得到,罗蒂在逻辑上最终倒向了有争议的社会学主义的(sociologistical)立场。他之所以坚决否认这一点,是因为他推崇个体的自由和“自我创造”并由此反对任何对于它们的毫无道理的限制。
换句话说,源于“当下的理论和实践”的那些限制不过是寻常的认知情境的一部分,但是,试图通过援引某种客观实在的概念来加以限制,甚至谈不上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它不过是一种祈求幻想并借此支持权威主义的鲁莽尝试。
当罗蒂反对针对世界之客观真实的陈述的可能性时,人们可以反对说,他在逻辑上已经预设了准确刻画客观实在(语言与世界之其余部分之关系)的命题。但是,罗蒂试图通过说从逻辑上推出预设在他看来并非一种有用的活动来摆脱这种矛盾。这样,在罗蒂这里,GMWER对于知识范围的探究最终得出了结论,即不存在人们必须接受的逻辑原则,而这一结论可以追到蒯因针对“分析性”的那些挑衅性看法。
七
当我们开始审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光谱时,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现不仅存在着一个需要平等与“消极自由”(例如,或许可以称其为有关经济的、政治的和智识的“三大市场”之自由的东西)的共识,而且还存在着如下一个重要的共识,即这三大市场都要求重视科学、法律,以及包含伦理规范的某种“精神气质”,并且由所有的机构来加以宣传并达到教育的效果即“教养”(paideia)。
不过,这样的共识看起来是相当脆弱的,其原因主要就是在如何定义这种精神气质方面存在着争议。事实上,美国当前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y)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些争议。在我看来,定义这种精神气质的不同努力在如下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未能取得成功:未能在概念上阐明如何能够去追求以知识为基础的进步;未能认识到GMWER及其文化概念如何使得任何一种搭建由普遍有效的原则所构成的、置身其上就能对所有形式的人类生活予以客观描述的平台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在承认文化和语言对描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同时,未能抓住对修正人们的文化遗产、增加其自由来说是必要的那些活动的本质,也未能就以承继下来之核心的德性传统为目标的偶像破坏论(iconoclasm)予以仔细的权衡;在制定政策时未能考虑在历史因果性方面的韦伯式的复杂情况;在乌托邦主义和历史悲观论调之间摇摆不定,而不是在神魔混杂的历史中稳定地寻求一点一滴的进步。
无论是哈耶克对于以核心的德性传统为基础的、未被既得利益权力所污染之自由市场体系和政治架构的乌托邦式的呼唤,罗尔斯关于由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和道德的公民所管理之公正政府的同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还是约翰·顿对于政治的普遍本质排除了向着这一理想进步之可能性的坚持,抑或罗蒂对于权威主义之斩钉截铁式的公开抨击,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不仅把有关可行之政治进步的分析都留给了记者、政客和政治学家,而且也没有去提及在非西方社会、非民主社会中对于可行之进步的讨论。显然,美国之所以在其应付非西方社会的努力中遭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就是因为西方有关政治可行性(practicability)的讨论与旨在澄清文化差异与知识概念之关系的适当的哲学努力之间存在着脱节。
通过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若干代表的分析,我们不能看出,伴随着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西方社会的问题而来的全部混乱,并非仅仅是健康的多元主义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是这样一个危机,它不仅侵蚀着教养,而且加剧了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无论这种认识论上的混乱是否使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雪上加霜,它的的确确已经妨碍了以共享的哲学洞见(会通)为基础的“全球伦理”去获得其确定的形态。
标签:哈耶克论文; 政治论文; 认识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