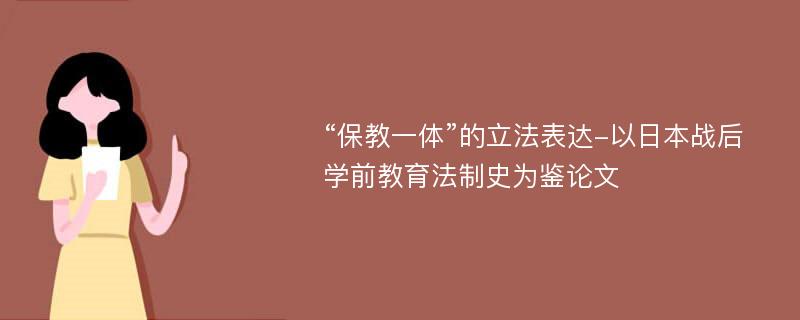
“保教一体”的立法表达
——以日本战后学前教育法制史为鉴*
张 挺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保教一体是国际学前教育发展趋势,是当前国际学前教育立法的关注点。日本战后学前教育的二元体制造成了保育所和幼儿园的分割,虽然通过“认定儿童园”等方式试图向保教一体靠近,但是改革困难重重,见效不大。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在学前教育法总则部分确立保教一体原则,继而在适用范围、管理体制、学前教育机构的具体制度中贯彻该原则。同时,应当考虑到地区差异、不同学前教育机构的差异等因素,在办园体制、投入体制等方面允许存在差异,体现幼儿园和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为地方立法和法律解释留下空间。
关键词: 学前教育法;保教一体;二元制;管理体制;认定儿童园
一、问题的提出:学前教育立法中的“保教一体”
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学前教育法》列为一类立法项目,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教育部也将研究起草学前教育法草案作为2019年工作要点之一。当前学前教育立法具有现实紧迫性。针对学前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社会各界呼吁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学前教育的法律,在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管理规范等方面予以保障。学前教育立法首先碰到的难点和重点之一便是立法中是否确立及如何明确保教一体原则的问题。
所谓“保教一体”,从纵向来说,就是把0—3岁与3—6 岁的学龄前儿童的教育进行整合,把0—6岁的学龄前儿童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使托幼机构在目标和内容上具有连贯性,管理、办园机制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一体化,进而能够根据0—6岁的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保育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从横向来说,就是把早期教育阶段和幼儿园阶段统称为学前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不仅仅关注婴幼儿的教育情况,也关注其保育情况,促使学前教育机构能与社会、家庭、社区横向有机联系[1]①。保教一体在外部表现为保育所和幼儿所一体化设置、管理,内部表现为婴幼儿保育和教育相互融合。当然,保教一体并不意味着否认托儿所和幼儿园、保育和教育在学前教育中的区别,或者说保教一体并不意味着保教合一。
喷油器喷油压力低:喷油器喷油压力偏低,出现早喷早燃现象,导致柴油机反转。这种情况应检查调整喷油器喷油压力,使之达到规定值。
为提高保教质量,减少教育保育资源的浪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在促进“幼儿园”与“托儿所”机构整合、教育功能与保育功能相互浸透的“保教一体化”理念应运而生,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前教育立法逐渐受到保教一体社会思潮的影响,并逐渐成为国际趋势和潮流。如英国、瑞典、挪威、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进 “保教一体化”的学前教育改革;OECD在其学前教育报告《强势开端Ⅱ: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中指出,学前保育制度应与教育制度结合;亚洲的日本、韩国也一直努力实现“保教一体化”[2]。
与保教一体的学前教育体系不同,目前我国学前教育采取的是二元制体系,即学前教育分为针对3—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和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保育(早期教育)。前者以教育为主,而后者以保育为主。与此相对应,前者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单位,后者则以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单位,从而形成了教育和保育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这两套系统越行越远,逐渐与社会需求相背离,产生了不少问题。另一方面,目前两套系统的分离也造成保育和教育的分离,缺乏两者之间的融合,不符合学龄前儿童教育保育的规律。
我国地方层面上已经出台了十数个学前教育条例,大多数回避了0—3岁学龄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法律规范问题,而仅仅规定了幼儿园教育的相关内容,这与国际上的立法潮流和趋势并不相符[3]。另一方面,有学者虽然认为0—6岁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保育统一纳入学前教育法的立法调整范围,但是应当对0—3岁和3—6岁的学龄前儿童采取不同的模式,即划分为0—3岁学龄前儿童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模式,3—6岁学龄前儿童的学校教育模式,这只不过是传统二元制的另一种变形罢了[4]。
如果学前教育立法的法律调整范围明确为0—6岁婴幼儿保育教育,那么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学前教育法如何在法律构成上安排保育和教育的相关内容?现实可以考虑的模式存在以下三种:第一种模式是拼搭模式,即基本上就是托儿所法和幼儿园法的集合,分几章分别规定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相关内容,总则部分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但是,这种立法模式流于形式,缺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并脱离了保教一体的立法本意,实际上意义不大。第二种模式是兜底模式,即学前教育法主要规定幼儿保育教育的相关内容,利用兜底条款或者兜底章节规定0—3岁婴幼儿保育教育的相关内容。比如,有学者认为,考虑到0—3岁婴幼儿与3—6岁儿童在年龄阶段特点、保育教育机构等方面的差异,学前教育立法可以设专章规定早期教育指导,同时规定不满3周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早期教育指导“参照”学前教育法有关规定执行[10]。不少地方立法也遵循这种折中模式④。这种模式考虑到了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学前教育存在经验不足以及教育、保育的差异等因素,是一种相对妥协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对0—3和3—6两者之间厚此薄彼,尤其是对0—3岁婴幼儿保育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真正有效的规范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从保教融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也并非真正的保教一体。第三种模式是融合模式,即在学前教育法整部法律从总则到附则贯穿保教一体的精神,按照学前教育的规律,体现保教一体的要求。这种模式从法律形式上,法律各章(至少是大部分章节)同样适用于幼儿园和保育所。总则中就应当规定保教一体原则,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置、监管体制等各章内容都应当体现保教一体的原则。从法律内容上来看,将0—3岁和3—6岁儿童视为一个整体,既不能简单以年龄作为保育和教育的区分,也不仅仅以年龄作为入学的条件,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整体施以保育教育,才能满足两者不同的发展需求[11]。
二、日本战后学前教育法制史的经验与教训
1.从二元制到三元制:日本学前教育保教一体的尝试
与我国的情况相似,二战后日本的学前教育分别依据《学校教育法》和《儿童福祉法》,形成了幼儿园教育和保育所(相当于我国的托儿所,下同)保育的二元化体制,即依据《学校教育法》建立的、作为学校教育制度之一的幼儿园的教育系统,和依据《儿童福祉法》建立的、以儿童福利为目的的保育所的保育系统[5]。两条线渐行渐远,渐成平行线,弊端显现。战后日本学前教育法制史的发展过程中,“保教一体”成为学前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词。反反复复进行尝试,大体来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二元制形成阶段
1946年8月,日本教育改革委员会审议战后教育改革方针的过程中,虽然也讨论了保教一体的问题,但是1947年3月制定的《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是学校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同一时期,1947年12月,日本制定的《儿童福祉法》规定了保育所制度。日本学前教育由此开始了两大制度并行的二元体制时代。但是,1948年日本教育行政部门文部省制定的《幼儿园教育基准》中也出现了保育的内容,而且作为社会福利主管部门的厚生省也参加了该基准的制定,并考虑保育所同样适用该基准。另外,当时保育所被认为是“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对婴幼儿实施保育的机构”。但是1951年修改《儿童福祉法》之后,缺乏保育条件的家庭才能申请入保育所,同时修改后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将幼儿园的保育时间限定为四个小时。
1963年,在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局局长和厚生省儿童局局长发出的《关于幼儿园与保育所关系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幼儿园是以学校教育为目的的机构,而保育所是对“欠缺保育条件的儿童进行保育”的机构, “两者发挥的机能是不同的”。同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欠缺保育”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明确了两者的设置目的和机能的差异,显然是为了促进两者的二元化发展。但是,通知同时提出,在教育方面,保育所可以参考《幼儿园教育要领》,表明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为此,1965年,对于保育所的“教育”部分,日本厚生省参照幼儿园教育方针制定了《保育所保育方针》。此后,为了整合保育内容和教育内容,在修改《幼儿园教育要领》《保育所保育方针》之时,文部省和厚生省参加了彼此的修订工作。尽管如此,上述通知还是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制度差异,二元化方向改革的意图非常明显。自60年代起,地方上虽然也有幼儿园和保育所尝试一体化运营,但是并没有形成全国风潮[6]。至此,日本学前教育的保教二元制正式形成。
(2)一元制改革尝试阶段
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保教一体化改革的动向,自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摸索。70年代初,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学制改革的审议过程中,对幼儿园和保育所的关系提出了“具备幼儿园必要条件的保育所,可以给予其幼儿园的地位”。中央教育审议会强调幼儿园优势地位的观点受到了保育所团体的猛烈批判。1977年,文部省和厚生省联合成立了“关于幼儿园及保育所的恳谈会”,恳谈会在1981年提交的最终报告书中得出结论:“目前难以实现保教一元化。”虽然二元体制得以保留,但是这段时期还是有地方层面探索对幼儿成长更为有利的保教关系[7]。
农业创新主体是否愿意对于创新项目加大投入、是否愿意协同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与相关的支持政策和政府引导密不可分。各涉农部门将对相关政策进行梳理、优化、会商,让敢创新、能创新的企业得到更大的支持。
红色代办员是企业与政府的“中间人”,每个代办项目均由专人负责材料准备、流程图制定、组织协调、全程指导、跟踪督促、疑难会商,实行“一对一”审批跟踪服务,建立全程代办工作台账和日志。实现项目审批由“企业跑”向“政府跑”转变。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出生人口不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便是“少子化”,学前教育服务自然成为促进生育的手段之一而受到重视,从而加快了保教一体改革的步伐。此时,日本社会意识到,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保育所政策应当从相对抑制转向积极鼓励。另一方面,1991年文部科学省在《关于幼儿教育的振兴(第三次)》的文件中,承认了幼儿园的保育活动。1997年,文部省将“托管保育促进事业”作为预算事项,对延长幼儿园保育进行奖励。由此,在政策方向上,幼儿园逐渐发挥了准保育所的作用,即所谓的“幼儿园的保育所化”。
1996年12月,日本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在一份建议书中提出:“在少子化时代来临之际,为满足儿童及家庭的多样需求,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应当强化幼儿园和保育所之间的协作以及两者相关设施的综合化,采取设施共有化等强有力的措施。”1997年4月,文部省和厚生省发起成立了一个联合审议会,并于次年3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幼儿园和保育所的设施共用化等相关指南》。但是,该指南并不以一元化为目标,而是推进两者设施及运营的共有化,以及明确设施面积、职员数目等保育所最低标准以及幼儿园设置标准。虽然有地方采纳了共有化建议,但是截止 “认定儿童园”出现之前的2006年,实现共有化的幼儿园、保育所只占全国的2%至3%[7]。这一阶段的改革体现了日本保教一体改革的迫切性,并对接下来的改革奠定了方向。
叶晓晓有气无力地回到宿舍里,刚躺下,爸爸的电话就来了,叶之容在电话那头焦虑地说:“快回来快回来!快叫辆车回来!从小带你的夏太走了!”
2002年10月,在日本分权改革推进会议的最终报告《关于事业、业务的应有之意的意见》中,对于学前教育,再次提出了“根据各地的经验,向着一元化方向努力”。为了实现一元化目标,意见提出:“国家对保育所运营的干预过多,尽管地方希望实现保教一元化,却难以实现,故而应当修订《儿童福祉法》等法律。”2003年2月,日本综合规制改革会议在其重点任务中也提出了“保教一元化”的任务建议。上述两个报告中都提出,应当将国家辅助金财政化,降低保育所入所条件,统一保幼设施设备的基准等等。但是,上述地方分权改革推进会议与综合规制改革会议的“一元化”的建议遭到了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反对。
2003年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国库辅助负担金合理化方针》中提出了设置“综合机构”的建议。2005年该机构进一步演化为“学前保育教育一体化的一贯制综合机构”(示范园)。该示范园2005年在全国35个试点施行,2006年3月通过综合机构示范事业评价委员会的评价后,进一步制度化。综合机构是“在社会构造和就业构造显著变化的基础上,从综合性地养育儿童的视角出发,全新的儿童养育体制。根据地方的需求,设立学前教育保育一体化的机构”。在中央教育审议会幼儿教育分会和社会保障审议会儿童分会的联合审议结论中,明确提出了制度框架的构建,即综合机构应当提供如下服务:“在规制缓和、地方分权的潮流中,由各地根据地区实际情况以及父母对幼儿教育保育的需求,恰当灵活地应对。”作为具体方案,应当考虑“既有机构的转换,既有机构相互协作等,尽可能采取灵活的制度”。这种综合机构还是以过去的二元体制为前提,也就意味着除了传统的幼儿园和保育所,还出现了兼具两者功能的第三种机构。该机构就是2006年立法的《推进向学前儿童综合提供教育保育法》规定的“认定儿童园”。由此,日本的学前教育不但没有实现一元化,反而形成了三元化的状态。
关于“认定儿童园”的现状,截止2018年,日本共有“认定儿童园”4 521所,在园儿童603 954个;同期幼儿园10 474所,在园儿童1 207 884个[8]。两者比例大致为1∶2,应当说一元化改革还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认定儿童园”不问父母是否是双职工,向所有家庭开放,同时具备学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服务的机能。具体来说,认定儿童园又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幼儿园型(认定的幼儿园兼具保育所的功能);二是保育所型(认定的保育所同时接收欠缺保育的儿童之外的幼儿);三是幼保合作型(认定幼儿园和认定保育所合作一体运营);四是地方裁量型(既没有认定幼儿园又没有认定保育所的地方教育保育机构发挥认定儿童园的机能)。认定儿童园的出现,满足了部分家长自由选择保育时间的需求,也给了部分不上班也需要学前教育服务的家长一个选择,受到社会的欢迎。但另一方面,认定儿童园只是降低了幼儿园设置的最低标准。这些标准本来国家只是提供一个指南,最终还是需要地方政府决定并认定,因此可能进一步扩大地方教育差距。同时,入园之际家长和园方需要直接签订合同,由机构设定学费,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可能难以被筛选入园,从而存在儿童福利倒退的风险。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求,但是认定儿童园的出现不过是日本社会规制缓和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可能导致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的倒退,对学龄前儿童教育未必有利[7]。因此,也有中国学者如此评价“认定儿童园”:“日本的幼保一元化本身是一个涉及多方面问题的过程……实行认定儿童园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权宜之计,只是日本政府主导的保教一元化的一种制度设计。虽然实行认定儿童园制度希望促进儿童教育权平等,但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观察。”[5]
2. 日本学前教育的教训
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的时候起,日本学前教育的政策及立法便开始反思保教二元体制。保教一体的尝试几度沉浮,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最终也没有完成保教一体改革目标。可以说,在日本学前教育法制史上,对于保教一体的问题,教训多过成功经验。
在明确了保教一体的理念之后,应当保证该理念在相应法条中落地,否则可能造成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立法理念和法条内容两张皮的问题。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差异大,许多政策和做法尚有待时间的检验,因此学前教育法应当注意保育和教育存在的差异。在体现保教一体理念的同时,也应当考虑立法相对于政策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同时应当保证学前教育立法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学前教育立法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贯彻保教一体理念:
三、我国学前教育法关于保教一体的整体思路
1. 我国保教一体的立法模式选择
教学良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较高教学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提高教学艺术和教学能力,打造有效课堂。注重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为人师表。
那么,已经启动的学前教育立法应当如何看待托儿所保育和幼儿园教育的关系?是按照传统二元模式分别规定,还是遵循国际潮流,在保教一体新理念下有所创新?下文将以日本战后学前教育法治中保教一体改革的历史轨迹为视点,结合我国学前教育的现实,回答上述问题。之所以选取日本为比较对象,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学前教育二元体制和我国非常相似。日本学前教育保教一体化尝试所碰到的困难,也可能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日本对学前教育非常重视,也是公认的学前教育强国之一。但是即便是日本,如下文所述,试图从二元模式向一元化转向,也是极其困难的。日本学前教育立法和政策的发展过程可以为我国的学前教育立法提供若干思考。
综上,我国保教一体的立法模式应当采取融合模式,改变行政管理的“分离模式”,不断扩大教育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使行政管理走向“统一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保育和教育相互融合、互为渗透、共同提高,实现真正的保教一体。
脂肪酸酯也可发生此类反应生成a-单磺酸化脂肪酸酯[18],此反应常被用来制备类似结构的表面活性剂,产品易降解且对环境近无危害。
2. 我国保教一体的立法建议
立法上的分割造成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人为分割,给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与福利部门)的利益纷争提供了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日本由《学校教育法》和《儿童福祉法》分别规定了幼儿园和保育所的设置、管理乃至教学内容等事项。此后,社会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法律仍未作出调整。有更多的家庭需要保育服务,保育所不应仅仅针对有保育困难的人;大量的幼儿园也开展了保育服务,如根据日本第2次教育再生恳谈会的统计,日本有大约四成的3—6岁儿童在保育所接受保教服务,因此并不能仅以年龄作为区分保育所和幼儿园的入学条件。立法分割还有一个弊端便是造成了部门利益的分割,不利于幼儿的成长。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厚生劳动省作为福利主管部门虽然也认识到了保教一体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到了保教一体改革之时,便呈现出典型的部门立法的特点,守着各自一亩三分地,既不想对方染指本部门的领域,更不愿去做两者统合的工作,最终采取了“认定儿童园”的妥协模式。如前所述,认定儿童园既不是保教一体的一元制,也不是传统的保育所幼儿园区分的二元制,而是形成了一种更加复杂的三元制的状态。目前,日本对于认定儿童园的模式还存在巨大的争论,其前景并不明朗。归根结底,日本保教一体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以学龄前儿童的保育教育规律为支撑,在立法上统合《学校教育法》中幼儿园教育和《儿童福利法》中保育所保育的相关规定。换言之,立法上如果还是继续保持分割状态,很难在政策上获得真正的突破。也就是说,在法律作出重大调整之前,这一现状恐怕难以改变。
首先,在学前教育法总则部分,应当将保教一体作为法律原则之一确定下来。具体来说,保教一体原则在总则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包括学前教育法的适用范围以及管理体制。关于学前教育法的适用范围,应当专设一条规定:“本法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对0—6岁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包括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等形式。”[12]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像地方条例一样,明确0—3岁为早期教育,3—6岁为幼儿园教育。笔者认为,立法上不必明确。如前文所述日本的情况,0—6岁是一个整体的学前教育,并不是截然以年龄为标准分为托儿所和幼儿园,现实中还需要给幼儿园接收0—3岁儿童以及托儿所内3—6岁儿童继续接受幼儿园教育留下法律上的空间。
如前文所述,世界学前教育法发展趋势是从保教分离、保教并重到保教逐渐结合,最终融合为相互影响、不可割离的有机整体。保教一体既是幼儿园保教发展趋势的“顺势而为”,也是处理保育所和幼儿园法律关系的“应有之义”[9]。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地方立法事实上是幼儿园法,基本上都不含0—3岁婴幼儿保育教育的情况②。吸取日本学前教育法制史的教训,我们首先应当制定的是“统一”的学前教育法,而不仅仅是幼儿园教育法③。现实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目前我国除了上海,地方立法上基本都没有关于0—3岁婴幼儿保育教育的相关内容,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监管是存在缺失的。但是,这一方面的社会需求是显性的,监管的紧迫性甚至超过幼儿园的监管。第二,从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资源是极其稀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将学前教育法列为一类项目,机会难得,一旦错过,等到下次修法或者重新启动立法将不知何时。因此,应当抓住机会,同时解决0—3岁和3—6岁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保育问题。
其次,为了确保保教一体的落地,学前教育立法应当明确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如前文所述,日本学前教育法制史的教训之一便是托儿所和幼儿园在管理体制上的人为割裂,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且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因此,我国在学前教育法中应当明确学前教育工作的“总负责”部门,打破过去的各自为政的局面。笔者建议,在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提供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中的主导责任的基础上[13],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学前教育实施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学前教育工作”。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过去一般认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托儿所的工作,或者妇联为儿童照顾体系的主管部门[14]。有学者还指出,让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可能还面临着部门利益调整、教育部门监管力量不足等重大难题[15]。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0—3岁婴幼儿并不仅仅是养育看护的问题,同样伴随着教育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教育虽然不是学校教育,但将深刻影响儿童将来的发展。专业的事情还是让专业的部门来做,教育部门显然是最合适的。这方面我们应当改变过去教育部门不该介入托儿所管理的刻板印象,在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学前教育立法应当明确除了婴幼儿健康以及保育行为之外,由教育行政部门对学前教育工作负主要责任。这是保教一体原则往前走一步的重要标志。
再次,在学前教育法中关于学前教育机构的相关章节,应当关注以下方面:第一,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各种托幼机构的差异,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并不利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前教育法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条件不应规定得过于具体,学前教育法应当规定一些基本的框架即可,比如符合规定的机构、必备的资金、符合标准的场地等,这些托幼机构和幼儿园可以同时适用。学前教育法可以规定幼儿园、托幼机构等设置的具体办法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第二,在学前教育机构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不应区分机构种类,坚持统一适用,可以由相应的条款规定学前教育机构的权利、义务,对学前教育机构在卫生健康、安全等方面作出一致的规定。第三,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身份显然是不同的,相应的资质也可以作不同要求,但是在其准入禁止、教师职称等方面可以考虑统一规定。
必须要让基层民警了解并分清他们的服务职能,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基层警务工作者服务也不能事事都管,不属于基层警务工作者管辖范围不应该越权,这样会导致群众对于基层警务工作者工作的不满。加强对于基层警务工作者的岗位培训,让基层警务工作者了解目前的法律政策、自己的职能范围和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技巧等,让基层警务工作者在履行自身职责时更有底气和依据,并且在与群众交流过程中更容易得到群众的肯定。
最后,在学前教育的投入机制、办园体制、督导问责机制、教育扶助制度等方面,应当承认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教育之间、不同机构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有些条款仅仅是针对幼儿园而提出的,所以应当注意相应条款的适用范围。但是,考虑到保教一体的发展趋势,学前教育法也应当为早期教育的法律监管留下空间,可以授权地方制定地方条例开展试点工作。
(3)保教融合新阶段
四、结 语
保教一体是学前教育国际立法趋势,是保障学龄前儿童保育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必须作出回应。对此,学前教育立法明确为学前教育法而非幼儿园法,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学前教育法应当在总则中确立保教一体的原则,通过管理体制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避免学前教育事业人为分割的情况。同时,应当考虑学前教育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不可盲目追求统一性,同时为地方立法以及法律解释留下空间。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保教一体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立法是有其局限性的。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和急剧变化期,许多问题不断发生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如何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如何营造最适合婴幼儿时期的生活场所,如何提高保育教育质量,如何强化家庭、社会等支援学前教育的制度等等。如果说立法表达是保教一体的外在形式,那么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才是保教一体的核心。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得到解答。
注 释:
① 比如《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不满三周岁婴幼儿开展早期教育,以及对幼儿园以外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再比如《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对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不满三周岁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教育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② 也有极少部分的地方条例中明确规定学前教育条例涵盖0—6岁的所有学龄前儿童,比如《福州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对0—6岁儿童实施的教育。本办法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对0—6岁儿童实施教育的机构,包括幼儿园和0—3岁儿童早期教育机构。”
高中化学实验有很多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充分的反应,由于学时紧,教学内容量大的因素不能在课堂教学中展现这些反应过程.但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视频技术可以将长时间过程的化学反应快速展示在学生眼前,让其体会到化学反应有时候会发生的非常缓慢的事实,从而更深入了了解化学反应的原理.
③ 至于有人提议立法名称改成《学前保育教育法》,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如此。一来学前教育法的名称并不会混淆视听,给人印象这部法律只管教育不管保育;二来教育广义上本来就含有养育的意思,只是在先前的教育类立法中采用了学校教育这个相对比较狭窄的范围罢了。
④ 比如《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对不满三周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早期教育指导,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同时,该条例专设第五章“早期教育指导”,对0—3周岁婴幼儿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
向西、向北,要联合云、贵、渝、川及西北、中原各省区,积极对接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沿线城市合作。通畅地连通"渝新欧"旅游线路。竭力推进品牌形象共塑、精品线路互推、客源市场共拓、产业发展共促,共同推动南向通道旅游发展;还要以云南为连接点,深度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旅游合作;以桂林为连接点,打开广西北大门,深度对接湖南、湖北、河南等中原各省,互辟旅游目的地,共同开托客源市场。
参考文献:
[1]李 静,方 红.我国学前教育保教一体化的初步构建[J].幼儿教育研究,2016(3):56-58.
[2]但 菲,索长清.“保教一体”国际趋势与我国学前师资培育改革[J].教育研究,2017(8):96-102.
[3]易凌云.英国早期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6):76-84.
[4]倪洪涛.助推学前立法,守护国族未来[N].法治周末,2019-01-19(3).
[5]张德伟.日本幼保一元化改革与“认定儿童园”制度的确立和实施[J].外国教育研究,2012(2):4-11.
[6]楠山三香男.講座幼児と教育5[M].東京:岩波書店,1994:86-95.
[7]村野敬一郎.就学前教育·保育制度のあり方を考える視点——「幼保一元化」、「認定子ども園」の検討をふまえて[J].宮城学院女子大学発達科学研究,2011(1):25-29.
[8]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調査——平成30年度結果の概要.[EB/OL].[2019-02-28].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chousa01/kihon/kekka/k_detail/1407849.htm.
[9]邓诚恩.幼儿园保教关系新论[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4):7-12.
[10]湛中乐,李 烁.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研究——以政策法律化为视角[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45-53.
[11]赵 琼.托幼一体化是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1):122-123.
[12]梁慧娟.我国地方学前教育立法的内容分析及其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3(4):38-47.
[13]庞丽娟.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法》立法进程[N].中国教育报,2018-03-11(8).
[14]岳经纶,范 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9):92-111.
[15]管 华.学前教育立法应处理好十大关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6-12.
The Legislative Express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and Childcare Centre ”——Taking the Legal History of Post-war Preschool Education in Japan as a Lesson
ZHANG Ting
(School of Law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China )
Abstract : The un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and childcare centre i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focu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legislation. The dual system of post-war preschool education in Japan caused the separation of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Although the attempt to protect education through “Authorized Child Garden” has been tried, the reforms have been difficult and ineffective. China’s legisl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Japan, and establish principles of “the un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and childcare centre” in the general par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The principl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scope of the law,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factors such a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ifferences are allowed in the system of running kindergartens and investment systems so as to reflect the diversity and flexibility of kindergartens and other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eaving room for local legislation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the un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and childcare centre; dual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authorized child garden
DOI: 10.19503/j.cnki.1671-6124.2019.03.009
*收稿日期: 2019-03-13
基金项目: 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学前教育立法研究”[CLS〔2017〕C41]
作者简介: 张 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讲师,浙江省法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G40- 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6124( 2019) 03- 0063-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