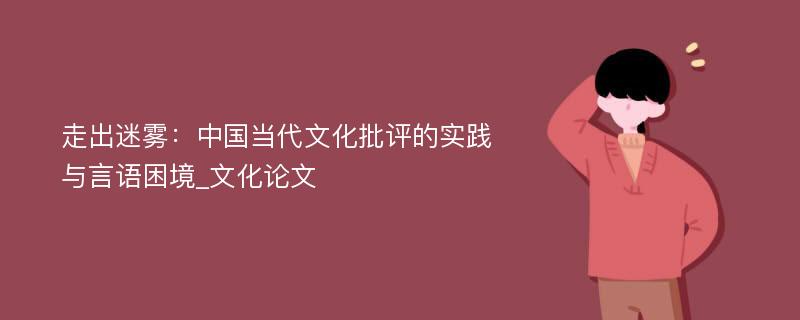
游离在雾蔼中——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践履迷误及言说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雾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在一片唏嘘声中,文化批评走到了学术舞台的前场。当一些执着的跋涉者还寂寞地守候在传统文学文本所构筑的纯文学营地之时,它早已作为一种新兴的元素植入了文学的肌体。于是乎,当那些默默坚守纯文学阵地的批评家领略了它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之后,不但感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奚落与冲击,而且深深为文化批评——这个经过悉心装扮的批评斗士向文学的话语空间野蛮施暴而痛心疾首。当代文化批评正方兴未艾。
这是否意味着文化批评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批评的霸权,或者说,文学批评已经自觉地认识到了在参与意识越来越浓的中国当代文化现实中已无法再以那种凌厉的姿态抵挡当代文化全面渗透的强势攻击而主动向文化批评交出了“令牌”?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没有主动“缴械”,文化批评也没有成功“夺权”,时下的局面倒是我们不得不凄婉地看着文化批评在“文化”与“文学”之间貌似庄重地“游”来“游”去。
文化游离状态中的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其表征之一就是批评的泛化。人们不假思索地将各种各样的文化分析都纳入了“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下,文化成了谁都可以拿来一试身手的武器和工具。在文化批评中,所有的问题都被放大,放大到除了用“文化”加以囊括之外,任何描述分析都显得无能为力的地步。以前人们曾苦心孤诣地探索文本“说什么”、“怎么说”,而当文化成为一次性消费品之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谈阔论之中,这些问题由于被无限放大而自动消解了。文化批评正不屑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因而以一种貌似庄严的方式解构了这些问题的逻辑存在。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游离色彩的又一表征是批评的浮躁。批评的浮躁表现为批评姿态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当代文化批评在“文化”的雾蔼中漫无目的地游走,在不同的学科边缘自由飘荡,但就是抓不住批评的对象,即使是把它的锋刃对准某一对象,寻个破绽下手,也总是满足于浮光掠影般的描述和语焉不详的搪塞。批评的浮躁还表现在对于热门话题各自心怀打算的“集体攻关”,一位学者在谈到中国当代批评现状时说:“当代文学批评到90年代愈加变成一种表演。昔日那种沉入生命、沉入文化深处的理念已成为过眼烟云。批评在合谋、无聊、调侃之后仅剩下肉麻,而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批评不但善于跟踪热点,而且善于制造热点,炒作热点。浮躁在威慑和褒贬中愈演愈烈。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泛化,一方面在于它罢黜了文学经典、精英文本的核心位置之后造成的批评指涉范围的扩大。罢黜了文学经典之后的文学批评,得以向“文化”的广阔地盘伸展手脚,但同时也造成了漫无边际四处撒网的混乱局面。而另一方面,当文化批评在貌似丰裕的批评资源之中沉浸在如鱼得水般的欣慰之时,却没有意识到由于缺乏应有的厚重而使自身的话语空间变得平面化。
与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泛化和浮躁相纠缠的还有批评规则的匮乏。在此,有些批评家道德感的淡漠和理性自觉的缺失难辞其咎。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已在多重践履迷误中,陷入了一种即将丧失本体功能和精神使命的既痛快淋漓高潮迭起又空泛浮躁积重难返的困境之中。它不屑于在文本间自娱自乐,但又缺乏走向历史的深度和融入文化理念的品格,在背弃了文学生命特质和皈依时尚的过程中徒增了参与文化现实的勇气却无力实现它内在的精神祈向和人文关怀。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自身学科规范、学科限制以及内在理路仍有许多有待完善和建设的环节,因此随着它突现于世界范围的学术视野,它的内在缺陷也不断暴露出来,而另一方面又与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批评观念过程中的迷误有关,同时又是中国当代特有文化语境造成的批评失重的结果。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既缺乏对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合理剖析和有效消化,又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入考察,在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缺乏理性自觉和批评规范的语体氛围中以一种思维的滞后性想当然地认同西方的理论先导,忽视了与中国本土现实语境的龋合,用徒然眩人眼目的批评风景代替了批评观念的有利同化。
文化批评,像许多在中国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促使中国批评家蜂拥而上的其他批评观念和方法一样,同样是一个西方文化语境中出现的批评观念。中国批评界和学术界接受的文化批评观念是与两个文化研究流派分不开的,一个是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另一个则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就文化批评来说,英国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前者基本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文化分析,是从文学研究领域孕育的文化视野中的批评观念;后者则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主要是以大众文化为靶心,结合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反人性的文化主题。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并不是他们进行文化批判的唯一对象。除了大众文化之外,现代艺术、现代科技、意识形态本身、语言问题都是他们的批判对象。英国文化研究在二战后进入了美国的知识界,并得到了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理论家的关注,如詹姆逊、赛义德、斯皮瓦克、米勒等等。他们把文化研究扩展到了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使文化研究完全脱离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文化分析的模式,而走向了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模式。这种文化研究模式的实践方式就是文化批评。但是,经过了美国知识界的扩展和深化之后,此时的文化批评已经有了不同于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义。
文化批评在中国批评界出场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在90年代,它迅速占领了批评的主流位置。中国当代文化批评接受的基本是经过美国知识界深化了的英国文化批评观念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观念。因此,当代文化批评在践履形式上也相应体现出了英—美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两种倾向。前者,主要是在文学研究中践行着一种基于中国文本并融合当代世界文化思潮的批评方式。如中国当代后现代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后者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传人则在中国的具体文化语境中对大众文化、流行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冲突中的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商品性,以及各种流行艺术中文化符号的意义解读。就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在接受这两种文化批评观念时,缺乏对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历史语境的症候分析和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入详细考察,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置于一种左右支黜的游离状态。
90年代,我们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批评观念时,忽视或轻视了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过程,那就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带给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遗产,并非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语言学的方法和观念早已作为一种要能植入了西方文学批判的观念之中。因为它“把一个生成的模式给予文学”。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叶之后,随着全球化文化思潮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崛起,文学批评冲出语言牢笼的呼声日趋强烈,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我们无法否认“语言论转向”在西方文学批评史的潜在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多以直观感悟为基点,并长期以来受实用主义品格的限制,难以切入文本形式的深层结构去分析判断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当文化批评冲击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我们在仓促上阵之时,由于缺少像“新批评”那样的文本细读分析对批评的归约和深化,面对“文化”这个庞然大物,才会依葫芦画瓢,大而化之,在文化和文学的道路上都走得偏离了方向。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化批评既盲目拒弃传统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又缺乏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学理分析和人文关怀,只是在一个虚假浅薄的文化景观中将批评装点成泛文化的集合。
许多学者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出场语境之时,都涉及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迎接“全球化”文化观念的挑战,二是与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遥相呼应,三是受中国当代一些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革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实践中并没有明显的反映,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仍然是在自说自话中咀嚼着罢黜文学的快感,把“全球化”仅仅当成了一次不出国门的批评旅行的尝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8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百年以来文化争论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但80年代文化论争所讨论的问题——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改造中国文化,却被90年代以来的“文化全球化”大潮冲淡了。人们不再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劣,也不再为继承和改造传统文化而呼告,而谈对话、交融。岂知若不是在同一个接受平台上,这种对话交融仍然是以西方文化界和知识界的价值评判和认知模式为标准的。
文学批评的退隐,文化批评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批评角色的置换。如果说在传统的文本批评中,批评扮演的探究深藏在文字隐喻之后的本质意义的解码者角色能够使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观照行为立足于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的话,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对精英文学研究的冲击下,传统的文本形式批评的根基正在发生着动摇,同时文学批评固有的关怀意识和参与精神也迫使文学批评的角色发生置换。它要求批评在一个高度综合的文化视野中去理解和阐释意义的生成和表现,以一种介入者的角色“精确地揭示‘现实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暴露事物的突然存在和应然存在之间两相对立的隔阂”。当我们以文化批评出场的种种端由来审视和追问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之时,才发现正是在这些本来该是文化批评最能体现超越精神和关怀意识的层面上,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在多重践履迷误中陷入难于自拔的言说困境之中。
因此,就中国当代文化批评而言,对它自身的反思远比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反思更为重要。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由于自身空泛浮躁的批评姿态和缺乏理性自觉和道德意识的弱势品格正面临着丧失本体功能和神圣使命的危险。文化批评作为批评话语实践方式,需要具有具体扎实的探索精神;文化批评作为人文精神的赓续弘扬途径,则需要有清醒的理性操守。文化批评的话语实践要求它对具体的文本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文化批评的人文指向则要求它对人类的文化行为方式进行精神提升和投以人文关怀。二者促使文化批评走向超越之维。这种超越意识要求文化批评的建构和实践既不应武断地拒斥批评的审美之维,同时又能够采取一种综合的文化神野“打通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理解并创造文学”,分析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