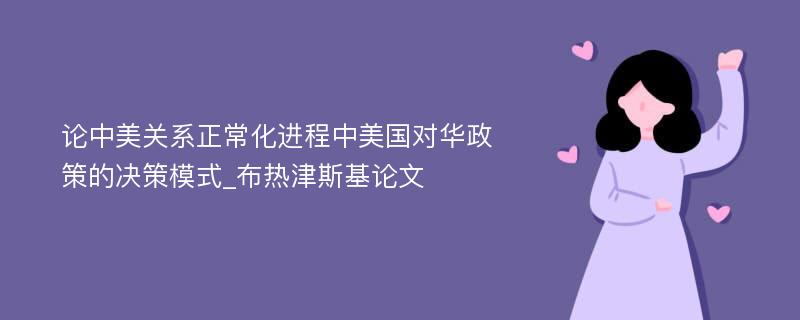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美国论文,过程中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3—0022—04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3次辩论。第一次辩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70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
从1949年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40年代末的覆辙。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 (P225)。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1967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他暗示美国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总统后,向中国政府做出友好姿态,做了一系列事情,力图改善中美关系。
1969年11月,美国驻华沙大使主动向中国外交官传递信息表达了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愿望。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肯定的回应。1970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通过一系列信息的传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得以在1971年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本人访华奠定了基础。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外交行动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这一行动主要是由国际因素所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对付苏联,美国决策者都是通过美苏关系来确定中美之间的对立与缓和。正是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使美国决策者将中苏视为铁板一块加以遏制。也正是由于苏联的扩张和中苏的分裂使美国决策者觉得有机可乘,因而推动他们努力谋求美中和解。第二,这一行动的决策是非常规的。尼克松总统是通过一种非常态的决策机制来完成美中初步和解的,参与决策的人数非常有限,在很多决定上,甚至作为总统外交政策首席顾问的国务卿罗杰斯都被蒙在鼓里。第三,这一行动是以高效率完成的。正是因为关键决策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阻力。第四,这一行动的成果终因美国国内因素的强烈影响而受到破坏。尽管美中缓和主要是由国际因素推动的,但1972年以后却受到国内因素的强烈影响。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曾承诺在他第二任期的前两年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水门事件”东窗事发,美中关系只能在原地踏步。
二、福特:小步移动
“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尽管换了总统,但幸运的是,推动美中缓和的一个关键人物——基辛格仍然执掌美国外交大权。福特上台之后,也重视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但很多不利因素渐渐浮出水面。首先,福特不是通过竞选上台的,在美国那样的民主政体里,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福特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创举,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大事他是很难完成的。其次,美中关系正常化毕竟不同于打开中国的大门那么简单,两国的分歧太大,很多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其中最为突出的自然是台湾问题。而实现关系正常化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再次,国内政治发生了不利于福特的转变,民众对美国政治的阴暗面感到厌恶。来自左的和右的势力开始向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发难,这种状况决定了福特政府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得罪了民众。最后,总统大选迫在眉睫,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福特必须敏感地对待和处理国内政治、尊重民意。
1974年8月,福特就任总统后,就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声称对他的政府而言,没有比“加快”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更为重要的事了[2] (P101)。基辛格也于当年10月访华。这次访问基辛格遭到冷遇,没有见到毛泽东,双方的矛盾非常明显,中方只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感兴趣,而美方只要求向苏联表现出中美和好的姿态,因为这样既可以在国内政治中得分,又可以作为对付苏联的筹码。美方要求无论如何谈出一个联合公报,但中方认为既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那就没有签署联合公报的必要。美国的这些要求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连的,从国际角度看,美苏缓和的高潮已经过去,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重新归于紧张。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共和党右翼对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抨击越来越强烈。福特非常清楚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必然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美中双方还是就1975年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一些基本共识。
福特于1975年如期访问了中国,也会见到了毛泽东,但这次访问并没有为福特赢得多少分,几乎是空手而归的。在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联华抗苏派的推动下,福特政府也做了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事情,例如,美国持续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政府放宽了对华出口的限制。
总之,尽管福特也重视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利益对他而言太重要了,他不得不使前者从属于后者,这就决定了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不可能有美中关系的新突破,只能是在一些小问题上“修修补补”。
三、卡特:从小步到大步
随着福特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败北,其访华期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承诺自然无法兑现。卡特是作为一位华盛顿政治的“局外人”当选的,因为水门事件以后,美国民众很厌恶华盛顿的政治。
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在外交问题上,卡特也将对苏关系放在核心位置。尽管国际局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但卡特和他的国务卿万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与尼克松、福特的判断大相径庭[2] (P121~122)。卡特认为,苏联的威胁被夸大了,美国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谈判方式来解决同苏联的分歧,没有必要通过扩充军备、谋求实力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相应地,他们并没有像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那样看重中国的作用。事实上,在卡特政府内阁成员的碰头会上,他们并没有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当作是个亟须处理的问题[3] (P229)。
1977年8月,国务卿万斯访华,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美两国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无法弥合,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不能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核心决策者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他们的目标是促进和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万斯更强调直接与苏联打交道,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却主张通过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牵制苏联。
他们两人的矛盾首先围绕着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而展开,万斯认为派布热津斯基这样与总统接近的人访华必然会影响美苏关系,所以他建议派副总统访华。而布热津斯基却认为只有推动美中关系才能迫使苏联方面作让步,所以他坚持要亲自出马访问中国。在百般犹豫之后,卡特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华,并授权他告诉中国人“总统已经下决心了”。美国政府的这种决心出乎中国高层的意料之外,使中国领导人临时改变接待规格和议事日程。布热津斯基果然不负众望,和中国领导人就建交谈判、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为期待已久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四、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有关外交政策、外交行为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各种理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均从不同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最为著名的有华尔兹的三层次理论,华尔兹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由三个层次的原因引起的:一是个人层次,华尔兹认为一国的国际行为与该国的领导人的个性因素有关系。二是国家层次,即国家的性质,它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机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打仗,这种战争只有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才会被消灭。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这些都是从国家层次上分析问题。三是国际层次,即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权力分布格局决定了一国的外交政策。尽管他是在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对外行为,但也为我们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从三个视角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是国际视角,这和华尔兹的国际层次理论基本上是一回事,国际角度强调整个国际体系中美国相对他国的实力和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全球均势所制约的结果。二是国家视角,该视角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美国国内制度运作的结果,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决策者将国际和国内的限制转变成政策。该视角主要考察的是政府内部的制度性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黑箱”(black box)。三是社会的视角,即将国内政治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多元视角将美国外交政策看成是国内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媒体、政党等非政府行为体之间你争我夺的结果[4] (P9~10)。
在美国,艾利森是研究对外决策模式的权威人士。他在197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 Crisis[5] 的书,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该书成为美国政治学界70年代的主要成果之一,他本人的学术地位也空前高涨[6] (P134)。Allison在他的书中归纳了三种对外政策的决策模式:一是理性行为体模式。假定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理性行为体,决策者都是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他们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及他们所代表的机构的利益。该模式要求决策者首先确定国家追寻的若干目标,并且明确这些目标的轻重缓急,再找出实现这些目标的诸多手段,然后算出每一手段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根据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确定国家应该执行的政策[7] (P140)。二是组织过程模式。艾利森认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有一套处理对外关系的程序和固定模式。例如,美国的国务院每天收到数以千计的电报,也同样需要发送数目巨大的电报,而这主要是根据固有程式来完成的[7] (P140)。三是官僚政治模式。他认为,前两种模式无法解释很多的外交政策问题,因为很多政策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争斗和博弈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艾利森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之间的界限不太明确[8]。
综合以上几位学术权威的观点,特别是伊肯伯里和艾利森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首先,因为美中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无法通过政府多年以来形成的经验和固有程式来处理,所以艾利森的第二种模式也并不适合于我们所要探讨的70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其次,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国家,除了有强大的政府之外,市民社会历来就很不甘示弱,有力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所以将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完全排斥在外交决策圈之外是欠妥的。约翰·伊肯伯里就曾对艾利森的这种看法提出质疑[9] (P132)。所以,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笔者认为存在一个新的决策模式,叫做多元社会模式。
约翰·伊肯伯里的三视角刚好对应着外交决策三模式,国际视角对应的是理性行为体模式,该模式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寻求利益最大化,在美国内部没有不同意见,至少在对外政策上全国上下是一致的。在对华政策上,该模式假设美国首要的是根据全球战略均势的变化来确定其对华政策目标和行为。国家视角对应的是官僚政治模式,该模式假设美国外交政策是由不同的政府机构、不同的决策者从本机构、本人的政治前途出发,进而相互博弈的结果。社会视角对应的是多元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凸显各种社会力量对政策的决定作用。
很显然,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他和基辛格对国际格局理性评估的结果。尼克松在1969年上任后,对美国当时在全球均势中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吃惊,因为当时的美国已经不是50年代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了。他的首要目标是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占据主动。正是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他和基辛格想到了中国。当然,当时也受到官僚体制和国内政治的制约,比如,尼克松非常担心民主党的议员会在他之前访问中国,所以他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递信息,希望中国阻止他们成行[10] (P220)。由于当时美国国内对苏联的威胁有着较强烈的共识,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成功地回避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尽管当时有一些零星的反对声音,但没有对尼克松政府造成多少麻烦,1972年2月访问中国前的尼克松政府在中国政策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国务院是由懦弱的罗杰斯把持,他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满。因此,这一决策模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理性行为体模式。随着水门丑闻调查的深入,尼克松日益陷于被动局面,完全没有能力兑现其访问中国时承诺的“在第二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尽管福特也很看重对华关系,但他的基本判断是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会使他在政治上失分,而不是得分。他不愿付出由此而带来的政治代价,因为他面临着1976年底的总统大选。其实,在对华政策上,福特受到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他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制约,任何内政外交的失败都可能使民主党抓住把柄,进而不利于他的竞选;第二,他也受到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的制约,给福特造成很大压力;第三,福特还受到了一些亲台派议员的制约;第四,福特担心大踏步地发展美中关系会疏远某些选民,特别是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选民。所以尽管基辛格仍然身居要职,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动对华关系,但福特在中美关系上没有走出任何决定性的步伐。福特政府的对华决策遵循的是多元社会模式。
正如前文所言,尽管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卡特和万斯的判断却比前几届政府要乐观得多。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的威胁,所以他们没有像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那样重视美中关系。卡特政府的中国政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布热津斯基——一位现实主义学派的欧洲裔学者,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熟悉欧洲历史。和卡特与万斯不同,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的威胁很大,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上的协调是美国制约苏联扩张的可行办法。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两个人及他们各自代表的机构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2] (P123)。比如,布热津斯基绕过国务院的正常渠道向中国政府表达访问中国的意向,在万斯不赞同的情况下,他利用每天早晨向总统做汇报的机会游说总统,并利用布朗等其他官员劝说总统。万斯却认为美中关系应该从属于美苏缓和的大局。在北京访问期间,布热津斯基又有意将代表国务院的霍尔布鲁克排斥在某些重要会谈之外。所以卡特总统的对华决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政治模式。国际(苏联)因素肯定存在,但不是当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像尼克松和福特那样悲观地看待国际体系和美苏关系。国内政治的因素也在—定程度上存在,但当时卡特当选不久,距离下一次大选的时间还很长,卡特政府有能力承受一些国内政治的代价。
标签:布热津斯基论文; 尼克松论文; 中美关系正常化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基辛格秘密访华论文; 苏联总统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福特总统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