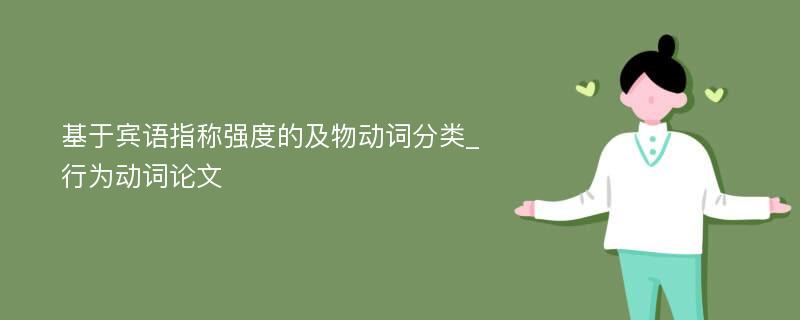
基于宾语指称性强弱的及物动词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宾语论文,强弱论文,动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词例的“词性”和词项的“词类”
由于缺乏形态标志,汉语的词类划分和词性鉴定一直是有重大争议的。朱德熙[16∶217]首先提出“概括词”和“个体词”这一对概念,对于这方面讨论的深入,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指出:“概括词是个体词的抽象和综合”,“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不是个体词的直接分类。个体词和词类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朱德熙的意思,说个体词只跟成分范畴(主语、宾语等)有直接关系。
吕叔湘[10∶28]也提出“备用单位”和“使用单位”这对重要概念。我们可以说,“概括词”是备用单位而“个体词”是使用单位。为方便和简洁起见,本文把“概括词”和“个体词”分别称作“词项”和“词例”①。
为了进一步明确区分“词例”和“词项”,以及两者跟“词类”的不同关系,我们不妨把词例所落实的词类性质称为“词性”。兼为动词和名词的“名动词”如“劳动、学习、研究”等等,作为词项,可以看作一类(名动词),但是作为词例,通常情况下,不是落实为“动词性”就是落实为“名词性”,如“讨论”在“我们讨论(法制问题)”和“进行(法制)讨论”中就分别落实为动词性和名词性[5]。也就是说,兼类的主要是“词项”,而“词例”的词性不明确的场合要少得多。兼类的只是“词项”而不是“词例”②。
既然“词项”是“词例”的概括,那么,“词项”的明确分类应该建立在“词例”词性的明确落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流程:成分范畴>词例的词性>词项的词类。
但词例的词性也并非永远都是明确的。如“开始认真de讨论”,其中的de似乎写作“的”和“地”都可以,就反映了其中“讨论”的词性的不明确。这种不明确性通常能随着结构的复杂化而降低。若把语境扩大为“开始第三次认真de讨论”,则de宜写作“的”;若把语境扩展为“开始认真de讨论政府官员收入阳光化问题”,则其中de就宜写作“地”。“开始”再进一步带“了”,其中de又倾向于写作“的”,即“开始了认真的/*地讨论”。这表明“开始了”比起“开始”,其宾语的名词性更强。这一点还表现在其“谓宾”(由谓词充当的宾语)本身不能再带宾语,如“*开始了认真de讨论政府官员收入阳光化问题”③。
按照一般的分析程序,我们可以拿明确的情况为两端,由此建立一个连续统,从而发现名动词作宾语时词性落实的渐变规律性,寻找影响名动词词性落实的因素,同时对所谓“名物化”现象的本质的探讨提供一些参考。
有关名动词的讨论总是牵涉到“准谓宾动词”,主要问题是它们作“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时所落实的词性到底是什么。
朱德熙[17∶122-124]把宾语两分为“指称性宾语”和“陈述性宾语”,所用的鉴别标准是:回答“什么”的是指称性宾语,而回答“怎么样”的是“陈述性宾语”。
“陈述性”、“指称性”这对概念,是语用概念,反映了成分在句子中的具体用法。说一个动词“名词化”或“名物化”,曾引起很多争论。但是批评“名词化”、“名物化”最坚决的朱德熙,自己也使用“指称化”一词。所以,本文采用“指称化”作为首选术语,在某些场合,为了引用文献等等的方便,也不排斥“名物化”这一说法。
朱氏的两分只是最基本的划分,从连续统的角度看,有不同程度的指称化。从下面一节开始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说名动词的“陈述化”而说名动词的“指称化”。名动词的指称化,本质上是一种“动词名用”,而其“陈述化”可看作“名词动用”。沈家煊”[11]分析了两者的不平衡:“动词名用”是一种本体隐喻,很普遍很自然,而“名词动用”比较特殊,因此才称为“活用”。但我们若从复杂性看,却是“动词名用”比较复杂,如同后面的分析将显示的那样,有不同程度的“名用”(指称化),而“名词动用”则单纯得多:一个名词一旦“活用”为动词,就完全是陈述性的。
科学研究中,常常是习焉不察的平凡事物、现象中蕴藏着更普遍、重要的原理,值得人们去深究。因此,“指称化”因其普遍性、平凡性而比“陈述化”具有更大研究价值。
2.指称性和陈述性的三个基本测试
我们可以以上一节所提到的三种方法去测试“谓宾”究竟是指称性的还是陈述性的:
一、朱氏所说的“什么/怎么样”提问测试(“做什么”可以作为“怎么样”的一个变体形式)。
二、添加定语或状语的测试。如果原来已经是偏正词组,可用插入“的/地”来区分。
三、加宾语测试。
让我们先从“名动词”作“准谓宾动词”宾语的情况说起。黄昌宁等[3]建议,“当孤立的动、名兼类词出现在非述语位置时统一标注为名词”,并且进一步认为当“a+v”(形容词+动词)结构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时,也应当视为名词词组。这两点应该说没有问题。该文又进一步建议:动名兼类词若受形容词修饰,“为了保证词性标注的一致性建议将其判为名词词组”。之所以说“建议”而不用“认为”,反映了作者的谨慎。事实上,文章中也注意到的确有宾语位置的“a+v”不宜处理成名词词组的情况:
(1)这/r也/d正/d是/vl我们/r要/vu继续/v深入/a研究/v的/u。/w(引者注:原文例句序号30)
黄文指出:“深入研究”是谓宾动词“继续”的宾语,且处于“是……的”句式中,所以被判作动词词组。
作者没有具体说明“是……的”这个语境为什么能够帮助判断“深入研究”是动词词组。我们猜想这是因为这个结构表明“这”是“深入研究”意义上的宾语,因此可判定“深入研究”是动词词组。但问题不这么简单。“这也正是我们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有着同样的“是……的”句式,但却不能因此说其中的“深入研究”也是动词词组。
如仅仅以“继续”为语境去判断“深入研究”,用提问测试、插入“的/地”测试和添加宾语测试,都表明“深入研究”兼有陈述性和指称性。但是若把语境框架扩大为“是我们要继续……的”,则提问似乎用不上,因为“怎么样/做什么/什么”都放不进这个语境。用加“的/地”测试,似乎加“地”比较好。用加宾语测试,能通过,证明“深入研究”是陈述性的。这说明黄文作者的感觉是正确的,但其中原因仍有待于解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语境框架的扩大,测试结果会不同。这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黄文中讨论到另一个例子。
(2)但/c这个/r时期/nt仅限于/V不同/a地物/n中/nd雄性/n不育/v的/u观察/v,/w缺乏/v深入/a研究/v。/w(原序号31)
黄文分析道:“深入研究”通常是动词性的,它在这里单独充当动词“缺乏”的宾语,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依据它所处的宾语位置把它判为名词词组。其实,用提问测试和“的/地”测试,就可以提供进一步证据:一般人会作出如下判断“缺乏什么/*怎么样?”和“缺乏深入(的/*地)研究”。并且,也通不过加宾语这一测试,“*缺乏深入研究有关事实”。
3.“准谓宾动词”还是“假谓宾动词”?
根据朱德熙[17∶58-60],在谓宾动词中分出特殊的两类,宾语只能是陈述性单位的“真谓宾动词”和宾语只能是名动词或带定语的名动词的“准谓宾结构”。
朱氏对于“准谓宾动词”的理解似有失误。其实,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并不限于名动词,也可以是表示行为意义的名词,如“进行仪式/战争/手术”[5]。此外,用以上三项测试,也都表明“进行”的宾语本质上是名词性的。因此,准谓宾动词其实是“假谓宾动词”。
朱氏虽然正确地强调了“词项”(概括词)和“词例”(个体词)的重要区分,但是在判断名动词充当的宾语的属性时,却放弃了这一区分。说“进行”是“谓宾动词”,是根据名动词的“词项”性质(具有谓词性)。而其实,当名动词作为“进行”宾语时,作为“词例”所落实的是十足的名词性。
“准谓宾动词”的句法表现既区别于一般体宾动词,又区别于一般谓宾动词。
“准谓宾动词”跟“缺乏”等一般体宾动词的句法区别在于,它只能带表示行为、事件的名词,而后者可带的宾语名词范围不受此限制,如“缺乏资金”。
“继续、开始”也是可带体词宾语的一般谓宾动词。根据前面所提到的三项测试,很容易跟“准谓宾动词”区分开来。它们跟准谓宾动词间一个不易觉察的区别是,宾语表示动作行为时,可以是普通动词(下例的“商量、发动”),而不限于名动词(“协商、动员”),试比较:
(3)a.继续协商/商量//动员/发动
b.进行协商/*商量//动员/*发动
其中“商量”和“发动”都不是名动词,因此不能做“进行”的宾语,但是却可以作“继续”的宾语[5]。
也许,可以把“准谓宾动词”的定义限制为,“能带,并且只能带表示行为、事件意义的名词的动词”。
根据这个定义,朱德熙[17∶60]提到的七个准谓宾动词,“进行、有、作、加以、给以、受到、予以”,其中至少“有”要排除,因为它跟“缺乏”一样,可以带的体宾类型太多了。黄昌宁等[3]补充提到的“准谓宾动词”有“受、遭到”,其中“遭到”可以带体宾,但体宾限于包括“天灾人祸、火灾”等事件性名词,所以,可以算“准谓宾动词”。此外,还有一个“从事”,性质跟“进行”相似,如“从事协商/*商量//动员/*发动”。不管如何,“准谓宾动词”的数量是极其有限并且可以列举的。
既然根据上述更加严格的定义,真正的“准谓宾动词”,即“假谓宾动词”,少到了可以列举的程度,是否有必要单独划出这一类就很值得考虑了。也可看作体宾动词中特殊的一类,不过其体宾必须是表示动作、事件意义的名词而已。
关于“准谓宾动词”,还有一点要指出。它们的宾语不必看作是名物化的结果,因为作其宾语的名动词本来就有名词性,在入句前作为“备用单位”的词项就已经有名词性了。有必要严格区分陈述性宾语的指称化和词项本身具有的名词性这两种情况。真正的动词是无法通过名物化而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的,如上面“进行协商/*商量”和“进行动员/*发动”的比较所显示的。
吕叔湘[19∶29]在谈到词类转变的第四种情况时说④:
语义没有明显变化,但是语法特点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就该认为词类已经转变,颇难决定。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动词名用”上,情况相当复杂,需要专门研究。有人主张一概称为“动名词”,以为可以解决问题。其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动名词”只适用于一般的“动词名用”,不能兼指已经转变成表示动作的真正名词。例如捱批评的批评只是动词名用,而文艺批评的批评则是正式的名词,二者是有区别的。
根据这一说法,不难看出,“进行”后的宾语本来就是名词,跟“文艺批评”中的“批评”本来就是名词,性质完全一致。
4.指称化等级
宾语为谓词性的成分,即“谓宾”时,是否在语用上已经“指称化”,除了用第2节所说的三个基本标准去检测外,还可用下面两个补充标准进一步检测⑤。
一、“名词性同位语添加/替换”测试。
(4)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承认
(自己犯了错误)(这个事实)
原有宾语也可保留也可删除;如果删除,就不是“添加”而是“转换”了。两种情况都反映了原有宾语带有指称性。
二、“分裂句转换”测试。
(5)承认的是自己犯了错误
“进行”类“假谓宾动词”的宾语,除了本身不能再带宾语以及只能带定语而不能带状语外,也可以通过“同位添加转”和“分裂句转换”进一步证明其指称性⑥。
(6)进行(环境保护)这一项工作。
(7)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
“觉得、希望、打算、企图、以为、认为”等“真谓宾动词”的宾语,这些测试都通不过,如“*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这一事实”“*觉得的是自己犯了错误”。由此可见其宾语是十足陈述性的。
“真谓宾动词”的宾语如果需要用代词来提问或指代的话,除了用“怎(么)样”和“这/那样”外,只能用副词性的“怎么”和“这么”,此时要出现在“真谓宾动词”前,如“他认为这样>他怎么认为?/他这么认为”。
“怎么”、“这么”有没有指称性呢?这牵涉到“指称”的意义。不妨说“怎么”、“这么”有“指代”或“直指”(deictic)意义,但无“称名”(name,term)功能。因此,虽然跟“指称”沾点边,可看作最低程度的指称化,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指称化”。
上面我们所说的“真谓宾动词”,不包括助动词,即“模态词”⑦在内。事实上,是否可用前置的“怎么”、“这么”指代宾语,可作为区分“真谓宾动词”跟“模态词”的标准:
(8)a.他希望/打算竞选党委书记
>他这么希望/打算
b.他愿意/能够竞选党委书记
>*他这么愿意/能够
可见,模态词的宾语连最低程度的指称化都没有。因此,我们可以把是否可用“这么”指代,看作鉴别真谓宾动词和模态动词的标准⑧。
朱德熙[7∶62]指出“想”的四个义项中,只有下面第四个是助动词:
(9)a.很想他(思念,怀念)
b.想办法(思索、动脑筋)
c.我想他不会来了(推测、料想)
d.他想去学习(愿望)
朱文认为其中只有(9d)的“想”才是助动词(模态动词)。区分(9c)和(9d)中“想”的标准是前者不能用“想不想”提问。若不指明具体条件,这个标准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一般动词都可以有“X不X”的形式。但是用前置的“怎么、这么”去指代宾语,就可以明确区分两者。
小结:模态词的宾语完全没有指称化,真谓宾动词的宾语虽然没有指称化,但却可以“指代化”,而一般谓宾动词(“开始、主张”类)的宾语是不同程度地指称化了,至于“准谓宾动词”,即假谓宾动词,其宾语根本没有指称“化”,原本就是指称性的,即它们即使不作“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在作为备用单位时就已经具有名词性。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谓宾指称性等级把似乎可带“谓宾”的及物动词分成5类:
(10)根据宾语指称化等级的及物动词分类
1.“应该、愿意”类模态动词
(“模态动词”)
2.“以为、觉得、打算”类真谓宾动词
(带陈述性宾语的“唯谓宾动词”)
3.“开始、继续”类一般谓宾动词
(宾语指称性、陈述性两可的“宾语两可动词”)
4.“进行、加以”类准谓宾动词
(“假谓宾动词”)
5.“有、缺乏”类体宾动词
(“唯体宾动词”,即正常的动词)⑨
其中越是下面的动词,其表面上的“谓宾”的指称性越强。最下面的“唯体宾动词”,当然还包括一般只能带体词宾语的及物动词,如“吃、看”等等。我们这里例举的只是跟本文有关那些所带看似为“谓宾”而实为“体宾”的动词。“有/缺乏”类唯体宾动词和假谓宾动词的宾语,虽然指称性最高,但是并没有“指称化”,因为其指称性是先天“胎里生”的,不需要“化”就已经有了;而这也是其指称性最强的原因。
上述5类动词,如仅仅根据宾语的指称性/陈述性,可以分成三类。最上面的模态动词和唯谓宾动词,都是真谓宾动词。最下面的假谓宾动词(也就是朱氏所说的“准谓宾动词”)和唯体宾动词,都是体宾动词。只有中间的两可动词,其宾语的地位在指称性和陈述性中间动摇。“宾语两可动词”的情况最复杂,其宾语的指称性程度,受到语境的极大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模态动词跟其他四类及物动词有明显的不同,其宾语不但没有任何指称化,也不能“指代”。并且,由于模态词在句法理论和跨语言比较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将其分化出来[8]。
这里顺便指出,朱氏的“体宾动词”概念跟“谓宾动词”概念是不对称的,前者是“只能带体宾的动词”,后者是“能带谓宾的动词”。这就是说,后者也能带体宾。这种分类很容易引起混乱和误会,逻辑上无法排除把“体宾动词”理解为“能带体宾的动词”,把“谓宾动词”理解为“只能带谓宾的动词”。逻辑上合理的分类就是三分,“体宾动词”、“谓宾动词”和两可动词。根据这个标准,(10)中的第1、2类都属于“谓宾动词”,而第4、5类都属于“体宾动词”。
5.决定宾语指称性强弱的一些因素
5.1谓语动词的控制力
现在考虑一下上一节所讨论的谓宾指称性的强弱等级是由什么决定的。
王冬梅[14]对谓宾的名物化的原因,作了很好的分析。她认为谓宾动词受施事的控制力越强,则谓宾作为独立事件的独立性越小,名物化程度也越高。实际上“控制力”跟动作性密切相关。王文的这一分析是成立的,但是不全面,下面做些补充。
王文的分析对于(10)中5类动词的前4类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模态词的控制力最小,其谓宾的独立性也最大;“助动词”这一名称反映了其作为独立动词的地位的丧失。从模态动词到感知类“唯谓宾动词”,直到“进行”类“假谓宾动词”,可以说动词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只有第5类“有、缺乏”等动词,表示状态,动作性不强,因此控制力也不强,但其宾语却是十足指称性的(如不能提问“有怎么样?缺乏怎么样?”)。看来,控制力之外,还有其他影响宾语指称性的因素。
5.2宾语的“事实性”
我们这里补充另一些影响宾语陈述性/指称性的因素。首先就是“事实性”(factuality)。宾语所指越作为事实的可能性越大,指称性也越强。下面的对比证明了这一点。
(11)a.宾语两可动词:他相信地球是平的
(这一说法)。
[可能是事实]
b.唯谓宾动词:他以为地球是平的
(*这一说法)。[通常不可能是事实]
(12)a.宾语两可动词:尝试发动政变
(这一行动)。[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b.唯谓宾动词:企图发动政变
(*这一行动)。[不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因此,“相信、尝试”是宾语两可动词,而“以为、企图”是唯谓宾动词。但仅仅这样分类是不够的,还需要寻找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原因显然跟动词及其宾语的语义关系有关。宾语两可动词“相信”和“尝试”的宾语可以是事实,因此可以用可别度较高的名词复指,而唯谓宾动词“以为”的宾语通常是违背事实的,“企图”的事情总是尚未实现的。试比较:“他所相信/*以为的事实”,“正在尝试/*企图的事情”,就可看出这种差别(关系子句中能提取的宾语必须是名词)。当然,是否事实是指“话语世界”中是否事实。地球是平的不是事实,但是在上面的话语世界中当作事实。
又如,“结束”的宾语只能是指称性的,“继续、开始”的宾语两可,这一差别也可从事实性得到部分解释。已经“结束”的行为,当然是现实的,因此指称性大。“开始”的行为还未完全实现,因此指称性小。英语中表“结束”的finish的动词性宾语只能用动名词(gerund)V-ing形式,而表示“开始”的begin、start的动词性宾语可以是to do和V-ing,也跟这种区别有关。在英语中,同为限定形式的doing的指称性比to do高。doing是现在分词,更大程度上暗示行为已经发生。这从下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forget to do something(忘记了去做什么事情)和forget doing something(忘记了做过什么事情)⑩。
事实性也能解释“开始认真的/地学习”跟“开始了认真的/*地学习”的差别,或“开始认真(地)学习数学”跟“*开始了认真(地)学习数学”的差别。“了”表示已然。已然行为的宾语比非已然行为的宾语具有更大指称性,因为已然的事件,比起非已然的事件,是更旧的信息,可别度也更高。这就使“开始了”的宾语具有更大的指称性,因此内部不能作动词性的扩展。
5.3 宾语的“具体性”
另一个影响宾语指称性的重要因素是“具体性”(reification):内容越具体的宾语,指称性也越大。下面的例子可显示这一点。
(13)a.宾语两可动词:计划发动政变
(这一步骤)。
b.唯谓宾动词:打算发动政变
(*这一步骤)。
唯谓宾动词“计划、打算”的宾语所指虽然都是未来的,都不是事实,但两者具体性有别。通俗一点说,“打算”是不成熟的“计划”,“计划”是周密、成熟的“打算”,周密、成熟的计划的内容,当然是更熟悉的,更具体的,因而也具有更大可别度,指称性。从认知上说,也就是脑子中考虑较多的内容,也就是较熟悉的信息,可看作较旧的信息。
(11-13)测定宾语指称性所用的是“名词性同位语”测试。但是同样通不过这个测试的唯谓宾动词“以为、企图、打算”(因为其宾语都没有现实性),内部的指称性大小还会不同,这表现在下面的“分裂句”测试上。
(11')a.宾语两可动词:
他相信的是我去过南极。
b.唯谓宾动词:
*他以为的是我去过南极。
(12')a.宾语两可动词:
他尝试的是发动政变。
b.唯谓宾动词:
???他企图的是发动政变。
(13')a.宾语两可动词:
他计划的是发动政变。
b.唯谓宾动词:
?他打算的是发动政变。
以上b句的接受程度的差别,表明了三个动词的宾语的指称性以这个顺序递增:以为<企图<打算。(13'b)表明尽管“打算”是个唯谓宾动词,但其谓宾的程度还是比“以为、企图”高一点。
“进行”和“继续”的宾语会有指称化程度的不同,这也跟宾语的具体性有关。“进行”的对象是计划好的、比较正规、严肃和程序化的一整套行为(试比较“进行协商/*商量”),而“继续”的对象可以不那么正规,比较随意和即兴,试比较:
(14)a.进行比赛/*打闹
b.继续比赛/打闹
这里反映了计划好的、程序化的整套行为比起随意、即兴的行为具有更大指称性、可别度。
被朱德熙同样列为“准谓宾动词”的“作”,跟“进行”,也有类似的差别,不过程度小一点。“作”比较随意,因此偶然可带陈述性宾语,如“作商量”,但是不能说“*进行商量”。
上述差别也牵涉到行为时间的长短,计划好的、程序化的整套行为往往是长期行为,因此表示长期行为的谓宾也具有较大指称性:
(15)a.两点钟开始学习(“学习”更倾向于陈述性,begin studying at 2 o' clock)
b.五月份开始学习(“学习”更倾向于指称性,start the study in May)
(16)a.劳动是愉快的(“劳动”更倾向于陈述性,to work is fun)
b.劳动是神圣的(“劳动”更倾向于指称性,work is sacred)
c.劳动有利于健康(“劳动”更倾向于指称性,work is good for health)
英语中不同的名物化形式的确也代表了不同的指称化程度。一般可以分成三个等级:指称性最大的是表示动词意义的名词,如study、transformation等,其方式修饰语只能是形容词。其次是—ing不定式动名词(gerund),其方式修饰语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指称性较小的是to不定式(包括无to的光杆不定式),其方式修饰语只能是副词。后两者的区别如下所示。
(17)a.She likes constantly/constant reading magazines.
‘她喜欢不停地读杂志。’
b.She likes to constantly/*constant read magazines.
关于两种不定式的区分,Bolinger[19]认为,是“潜在性”(potentiality,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事实性”的反义词,即“非事实性”)跟“具体性”(reification)的区分,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Bolinger 1974)。
(18)a.I saw John being noxious.(percept)
‘我见到约翰在作恶。’
(表示感知到的实况)
b.I saw John to be noxious.(concept)
‘我知道约翰居心不良。’
(表示认识到的概念)
(19)a.John started to get angry.(potentiality)
‘约翰好像要生气了。’
(表示潜在可能)
b.John started getting angry.(reification)
‘约翰已经开始生气了。’
(表示具体状况)
(20)a.Waiting was a mistake.
(表示具体状况)
‘这么等着是个错误。’
b.To wait would be a mistake.
(表示潜在可能)
‘等待(会)是个错误。’
光杆动词也可以归入to不定式:
(21)a.He saw John stealing.
(感觉到的栩栩如生即时情景)
b.He saw John steal.
(认知到的事实)
(2lb)的省略to,是因为感觉动词的宾语所代表的事件,跟感觉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关系更密切的缘故。
5.4“S+之/的+VP"和“S+VP”结构中指称程度的细微差别
事实性和具体性都可以看作“可别度”(identifiability,即所指为听话者容易确定的程度[6])这一基本原型范畴的成员。并且,不同词类的可别度是不同的,存在如下这样一个“跨范畴可别度”[6]。
(22)名词>动词>形容词>虚词
即名词的可别度最大,虚词的可别度最小。
按照沈家煊[11]的看法,汉语的动词都有名词性,可看作名词中具有动词性的一个小类。我们把这个观点引申发展,可以说(22)也反映了名词性从大到小的一个等级。
以上我们讨论宾语指别性大小,即可别度大小问题时,主要根据宾语的扩展和转换的可能性。下面我们来看宾语本身的指称性/名词性标志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S+之/的+VP”结构中的“的/之”具有名物化/指称化标志的作用。以下我们讨论,“S+(之/的)+VP”带“的”的可能性大小,也反映了谓宾的指称性大小的微妙差别。
古汉语中,“知”和“闻”的宾语为事件时,“知”倾向于选择指称性较大的“之”字结构“S+之/的+VP”而“闻”倾向于选择主谓结构“S+VP”[2;4],这也可以解释为:所“知”(亲自知道)的对象事件比所“闻”(间接听说)的对象事件更确切,因此具体性更高。
宾语两可动词“喜欢”表示心理感觉活动,其对象比认知的“结论”更具体,因此宾语可以是实体名词,如“喜欢他”等。
“希望”倾向于用“怎么样”提问而“害怕”倾向于用“什么”提问,这也可从宾语的可别度得到解释。“希望”的事情总是尚未发生的,而“害怕”的对象却可以是已经发生过的。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指称性比尚未发生的事件的指称性强。古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洪波[2]用统计表明,在“患、恐、惧、恶”的宾语位置上,基本上都是带“之”字结构“S+之十VP”,而“愿”的宾语位置上正好相反,基本上都是主谓结构“S+VP”。可见,心理动词中“患”类比起“愿”类,其宾语的指称性更强。这跟现代汉语中“希望”和“害怕”之间的差别是一致的。这也是“愿”类动词具有更大模态性的原因之一。
沈家煊、完权[12]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由于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希望发生的事情跟人的心理距离近,可及度高,倾向不加“之”,害怕发生的事情跟人的心理距离远,可及度(accessibility)低,倾向加“之”去提高指别度。
两种解释虽然角度不同,但基本意思都承认“S+之/的十VP”的指称性比“S+VP”高(11)。
6.结语
以上讨论了指称性或名词性的高低的种种句法表现及其认知解释。表示动作、行为的语言单位的指称性高低的差别,在我们语感中是客观存在的。其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差别之外,还有许多,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
由于指称性是渐变的,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彻底解决文本中谓宾的词性标注问题。如(9)中5类动词中,处于这个渐变等级中间地段的体宾、谓宾两可动词,有时无法决定其谓宾究竟是指称性的还是陈述性的。但是现在我们至少把不确定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例如,可把以前处理不明确的“进行”类动词和“有、缺乏”类动词的谓宾,明确标注为指称性的。
注释:
①实际上也就是“型”(type)和“例”(token)的区分。不过若把词的type翻译成“词型”,也容易误会成词的类型,类似于“词类”。因此,计算语言学界一般用“词”和“词例”来区分。但是用“词”来表示词的type,难免跟原来包括词项和词例在内的、广义的“词”混淆。因此建议用“词项”来表达词的(跟token相对的)type。
②“词项”似乎也有不明确的场合,如“翻译”理解为“翻译者”时,跟表示行为的“翻译”究竟算不算一个词项?似乎看作两个词项(同形词或同音词)比较好,因为意义差别较明显。“词性”不等于黎锦熙的“依句辨品”中的“(词)品”。在“依句辨品”的框架中,“品”几乎是句子成分的对应,如做定语的都是形容词,作主语、宾语的都是名词。我们承认动词也可以充当宾语,如,“主张去”。
③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修饰语标志“地”和“的”的分化只是文字形式的不同,但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群众对两个字的选用显示某种明显的分工倾向,而这种倾向并不服从语法教科书对“定‘的’状‘地’”分工的规定,如“总de说来”中的状语“总de”。很少会有人写作“地”。这种倾向背后显然有某种机制在起作用,看来反映了说话者对陈述性和指称性的语感区别。
④吕氏把“学习、劳动”类兼类词称为“动名词”,但现在文献中一般称为“名动词”。采用“名动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跟英语gerund的译名“动名词”区分;二是如朱德熙那样认为是动词的一个小类。又,吕氏在同书28页说,“又如双音动词都可以放在进行或予以后头做宾语,不因此就变成名词。”这显然也是个误会,并非所有双音节动词都能放在“进行”、“予以”后。
⑤这两个测试,杨成凯[15]分别称为“体词变换”和“宾语强调变换”测试,被用来区别“小句作宾语”和兼语式、双宾语。我们则用来作为鉴别“指称性”的标准。
⑥以下两个句子都不那么自然,但在笔者的语感中还是合格的。并且,同类的“从事”用于这两个句子就很自然了。这也许表明“进行”虚化的程度比“从事”高。
⑦一般称“助动词”,外语学界也常用“情态动词”,我们取“模态词”,一是为了跟逻辑学接轨,二是读音也更接近英文原名modal。
⑧“他这么愿意竞选党委书记吗?”中的“这么”是表示程度的,没有指代作用,要排除。
⑨某些南方方言中,包括受其影响的地方普通话,如台湾普通话,“有”可以带一般的谓词性宾语,接近完成体标志,应该看作模态动词。我们也要注意某些词的多义性。如动词“要”在“他要去竞选了”是模态动词,“他要去北京”若取“需要”或“想往”这两个意义,是两可动词;若取“将会”意义,是模态动词。动词“想”,有些语法书也认为有模态动词性质,其实并非如此。在“想家”或“想去北京”中,意义分别为“想念”或“想往”,都应该算两可动词。
⑩Stop to do something(停下来去做什么事情)跟stop doing something(停止做什么事情)的区别有些类似,但不全相同。Stop to do something有停止做一件事后即刻去做另一件事情,即表示两个行为,其中的to do something不像严格的宾语。
(11)他们认为要区分对听话者而言的“可及度”和对说话者而言的“指别度”,“可及度”是就指称目标(所指)而言,“指别度”是就指称词语(能指)而言。
标签:行为动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