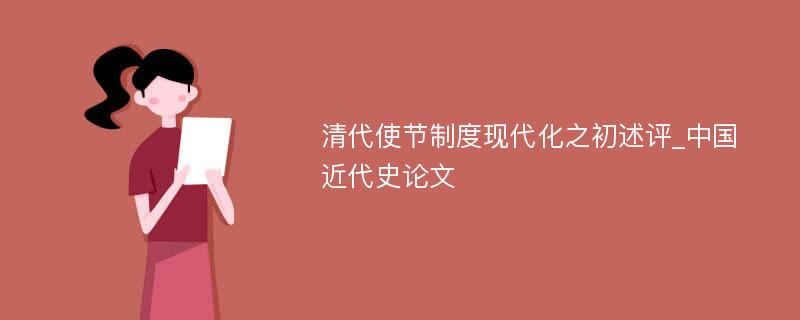
清季使节制度近代化开端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节论文,述评论文,开端论文,制度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总体上看,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1861年到1875年的尝试阶段;从1875年到1894年的建立阶段;从1892年到1911年的纵深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点,本文只就第一阶段尝试阶段作些粗浅的论述,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的回顾
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向华遣使达25次之多,命运之神多次叩响中国的大门,但是,乾嘉道咸时期的清政府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没有捕捉住这些机会。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外交价值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妨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世界的正确认知,生长在这种封建文明躯壳里的中国政府很难平等地对待域外的民族,国防和外交也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问题相关时才偶尔显示出它的意义,在更多的场合,则多半成了一种炫耀国威、唯我独尊的宣传工具。
乾嘉时期的清政府中衰之象已现,但鼎盛之形犹存,正所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1〕因此,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中国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不可能重视前来叩关的西方国家。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来华的西方外交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严加排斥,没有引发出丝毫的兴趣。不但如此,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不贵其物,惟贵其诚”〔2〕,满以为“天威能使万心降”〔3〕,西方国家可以被感化在中国儒教文明之下,对于天朝体制顶礼膜拜。在乾隆时期,清政府把马戛尔尼使团当贡使团接待。在嘉庆时期,清政府把阿美士德使团也当贡使团接待。结果是两次交往,双方都未能如愿以偿。对于来华的西方使团,嘉庆皇帝谕曰:“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4〕。充分显示了蔑视西方、唯我独尊的大国文化心态。
鸦片战争后,时移势异。两次鸦片战争表明了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国家已经滋长了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野心,在外交上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手段,决心用强力来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关系。但是,道咸时期的清政府仍旧缺乏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保留着天朝大国的空架子,继续推行着闭关自守的传统御外政策。
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虽然态度动摇,剿抚不定,但是,他仍然感觉到来犯英人“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5〕,因此, “惟有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设法进攻,扫除异类,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方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6〕尽管在实际上他也不得不于某种程度地接受西方,但是,这决非道光皇帝之所愿为,也非清延政策倾斜之重点。尽管清政府接受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口服心不服的心态,反而愈加膨胀,没有人去认真的检讨外交政策。
咸丰皇帝继位后,很想在内政外交上有所作为,对外政策趋向用强,对于西方使节提出的新要求,严排固拒,但也没有去认真地研究西方。例如,在1854年,咸丰皇帝在两江总督怡良关于新任美使表麦请求晋见皇帝而上的奏折中有这样的批示:“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事,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 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7〕。即使在1858年广州陷落,部分地方大员如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请清政府能否将英、法所请通商、保教等事“先行办理,以解危机”〔8〕时,他仍然严厉批评谭不识大体,指出“现在广东省城尚未交还,叶总督尚未送回,岂有不加罪反与加恩之礼?”并指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断难更改〔9〕。待到签约时, 咸丰皇帝指示中方代表:公使驻京,“为患最钜,断难允行。”〔10〕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情势发生剧变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外交政策,没有对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
然而,道咸时期的闭关外交与乾嘉时期的闭关外交不一样,在乾嘉时期,由于国势鼎盛之形犹在,傲视西方仿佛还有本钱,因此,把西方使节当作贡使接待并不感到是在用损人利己的办法维护天朝大国的威严,好象东西中外的格局本来就该如此。而在道咸时期,大国梦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破碎,因此,这时期的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硁硁不与人交接,拒绝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就成了自欺欺人。而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骗术态度妨碍了道咸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西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时,清政府中比较务实的洋务派才以比较积极、主动、求实的姿态接受西方事务,对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即所谓“今日夷务,在筹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11〕。近代使节制度也终于在这一历史情境下被当作一种处理中外关系,解决中外矛盾的手段而步入它的尝试期。
二、痛苦的选择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要从中世纪的外交体制中走出来,采用西方的使节制度,选择和适应面临着重重困难。
首先,它是被迫的,非自愿的,这也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西方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才被移植到东方世界。在西方,它是社会内部的发展滋生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在东方则完全相反,它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造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它是被当作救亡图存的一种手段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即所谓“外患亟而使职重”〔12〕。因此,外因是它发展的前提。可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长期以来,无待外求,“诸边藩属文教,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至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13〕,也就是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本来就构成了向外学习的障碍。而在近代中国,西方侵略突如其来,不断地打击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把中国从天朝大国的至尊地位上拽下来,推向被列强侮辱的痛苦深渊,这就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狂热情绪,并且又很容易导向盲目排外的歧途,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倍加艰难。因此当一部分逐渐觉醒的中国人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并不能摆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而只有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才能制夷时〔14〕;当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路上艰难跋涉时〔15〕;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却是无法摆脱的。正所谓“打脱牙,和血吞”〔16〕,不得不忍辱负重罢了。
其次,它逼迫统治阶级放弃在传统的外交体制下所享有的特权和殊荣,而又把中国置于一个没有安全可言的新世界之中,清廷上下因失落而痛苦,因不安而惶恐。
在传统的外交体制中,册封制度和贡使制度充分地表现了中国的至尊地位,统治阶级由此而获得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以天朝大国地位自居,对于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是几分轻蔑,几分仁慈。在宗藩关系中,中国完全处居主动的一方。而近代西方的使节制度,在理论上标榜资产阶级的平等意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必须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主权不容伤害。两相比较,差别显然。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放弃前者而采纳后者,等于自撤藩篱,放弃特权,“张外夷之气焰,捐中国之威灵”〔17〕,因此,习惯于传统外交体制的中国人对于新旧两种外交制度的取舍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当然希望维护旧的,拒绝新的。一方面,旧的是中国的,新的是西方的,另一方面,旧的给他们以荣誉和骄傲,新的给他们以屈辱不安的感觉。但是,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的梦破碎了。西方国家不但不接受中国的至尊地位,而且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人放弃传统的外交制度,接受西方的外交制度,而且清政府也只能作出舍旧取新的历史选择,这就打破了中国人的“安乐好梦”。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的部分务实官僚终于认识到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招牌的洋务运动,近代西方使节制度的采纳即其一端。奕、文祥等总署王大臣和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洋务派都认为建立近代使节制度既是当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取利去弊、解决近代中外矛盾的重要法门。
第一,他们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关系中,由于西方国家向华遣使,而清政府却没有向西方派遣使节,已经对中国的权益造成了严重伤害。奕等在1866年奏请派遣斌椿代表团游历英国的奏折中指出了办理洋务而昧于外情的难处:“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18〕在1868年奏派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有约各国时,奕等就说得更为明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崛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切诘责,默为转移”〔19〕。言下之意,如果清政府能够破除陈见,也向西方列强派遣使节,中外之间就可能避免交涉中的许多麻烦,由仇雠变为盟友,缓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反之,一味深闭固拒,受害者不是西方,而是中国,“殊非长策”。〔20〕
第二,他们认为,只有向西方列强派遣使节,才可能打破中外之间的僵局,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并从中获取种种好处。一是“奉使之员,既履彼土,相处切近,闻见逼真,其可以得彼国之动静,杜使臣之蒙蔽”〔21〕”,摆脱外交困境;二是“诚得其人,与之习处,宣布朝廷德意,备述中国礼教,使之因敬生羡,因羡生惮,……感化所至,于和好大局,甚有关系”〔22〕,把握外交的主动权;三是“洋人所恃者轮船之迅速,枪炮之精利,频年雇募洋人教之制器,或不能尽得其术,今久居其土,随带知巧之士留心学习,终必和盘托出,夺其所恃,而为我所长”〔2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四是联络海外华侨,以成一体,“今得才略之臣,要结抚驭之,转为我用,则干城腹心,不劳招募而集,缓急均有所恃”〔24〕;五是只要“遴选体用悉备之人,见微知著,通变达权,善于其职,不但所至之国如镜鉴人,情状毕露,即各国使臣亦可笼络一气,指臂相助”〔25〕,并能促进中外之间的互相了解,消除隔阂,“籍通悃款”〔26〕。
第三,他们认为,派遣使节,虽然没有先例可循,“于礼制或有所乖”〔27〕,但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已不同于往昔,中国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28〕,中外往来,已成不易之局,“若不预筹良法,为有备无患之谋”,“必致多方要挟”〔29〕,因此,“穷则变,变则通,此其时也”〔30〕。而在此时,“若不早事图维,绸缪未雨,设至甚于今日,际不可以收拾之时,更复何以为?”这样,他们就撕毁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一层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大胆地避开了中国文化最重视的礼制问题,表现出一种迫切的变革心态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意向,放弃了“华夷之辩”的最后一道关卡。但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损害国体,又特别指出:“西洋诸国自立约后,遣使互驻,交相往来,各处皆然。”〔31〕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舍旧取新,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艰难,太痛苦,但是,时势逼迫,不能因痛苦而拒绝选择,也不能因艰难而放弃选择。明知痛苦,而必须选择,这才是真正痛苦的选择。他们不得不承受舍弃从中可以获取特权和荣誉的旧体制的痛苦和选择利害未形的近代西方使节制度的惶恐,顺从历史发展的趋向,一步一步从传统的外交体制中艰难地走出来。唯一能够使他们的痛苦心灵获得某种安慰的是,移植西方使节制度被认为是解决近代中外矛盾的法子。
当他们认识到遣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准备付诸实施时,遣使的尝试也就开始了,使节制度近代化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三、艰难的尝试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尽管部分满族中央权贵和汉族地方大吏逐渐认识到了遣使的意义,但是,他们又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32〕,因此,遣使之事,从筹议到举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尝试阶段。
一方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清政府虽然必须推行使节制度的近代化,但又不可能采取快节奏。因为,它有昔日的荣光不可忘怀,又有历史的包袱不易遽弃,还有殖民主义侵略刺激了与其说是拒洋排外意识的发生,不如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意识的逐渐觉醒,因此,主持外交大计的奕、李鸿章等就必须向他们的支持者,同时也必须向反对遣使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证明建立近代使节制度的意义,在统治阶级中间达成一种共识。而在这方面,历史已经明示,即使正确的认识也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才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堵住保守派的攻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是在本土尚不完全具备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的情况下,而被西方的武力侵略所逼迫,从而走向近代国际社会的竞技场中的,因此,先天不足的毛病十分突出。在遣使方面就突出表现在缺乏适当的外交人才,不了解近代国际政治,缺乏基本的近代外交常识等等。奕等在六七十年代就特别强调这些具体困难牵掣了遣使的举行。他们认为,“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是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33〕。甚至还暴露了他们对于得人之难的惶恐心情:“循分供职,中材亦知极称,沉几观变,知者亦有难周,非为守兼优,识力俱卓,洞悉洋情之员,转足见轻于外族,而贻患于事机。至于羁旅势孤,易为所胁,贪狡计出,挟以为质,流弊之端,在所不免。”〔34〕在这种情形下,于正式遣使之前,用一个适当的时段来进行筹备和尝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
奕等务实派官僚虽然比守旧的士大夫要开明,对西方的和对中国前景的分析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们毕竟是封建君主的臣仆,尽管历史选择了他们,但是他们显然缺乏历史所呼唤的时代巨人的智慧和胆略,他们那谨小慎微的办事态度和行为方式也是导致使节制度近代化慢节奏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在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的遣使尝试花了整整十五年。在1861年到1875年的尝试阶段,共进行了三次遣使尝试,这三次尝试的时间分别发生在1866年、1868年、1870年。我们认为这三次尝试是洋务派在认识到遣使的必然性之后,对遣使的可行性所作的进一步实验和论证。
1866年,积极鼓动清政府向外遣使的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国休假,总署利用赫德此行之便,派遣斌椿代表团随赫德赴英考察,于是有了第一次遣使的尝试。
首次尝试的任务很简单,“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35〕。
任务虽然简单,但在遣使的方式上,总署王大臣却颇费心机。从奕等总署王大臣的奏折来看,与其说这是一次遣使的尝试,还不如说它是一次没有官方性质的公费旅游。第一,从派遣的对象方面言之,是先有派遣同文馆学生的筹议,后才有派遣斌椿的设想。奕等说,同文馆学生“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初识大概,若令前往该国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唯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以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36〕。第二,从斌椿此行的任务言之,管带学生是他此行的根本任务,而考察异域风情只是附属任务。所以,若没有派遣学生出游之举,也就没有派遣斌椿之事发生,没有带学生的任务作遮羞布,考察的任务被管带学生的任务所掩盖,斌椿的被派遣也以同文馆学生的被派遣为理由。
但从使节制度的近代化角度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派遣斌椿去考察欧洲才是这次尝试最关键的一着棋,因为总署派遣斌椿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遣使的可行性。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他们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遮遮掩掩,唯恐跋前踬后的行为方式是此次尝试的最明显的特征。
总署之所以选派了斌椿这个人作为马前卒,看来也曾煞费苦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分析斌椿此人的基本情况就会一目了然。第一,他是汉军旗人,朝廷官员,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派遣自有某种官方的意义在。第二,他又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37〕,位秩不尊,如果此行未获积极结果,既无伤大清体面,也不至对近代使节制度的建立产生致命的消极影响。第三,他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襄办年余以来,均尚妥恰”〔38〕,说明他思想并不保守,行为也比较可靠。因此,他正是首次尝试的最适合人选。
斌椿此行写了一本《乘槎笔记》,此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斌椿完成了清政府委派的考察任务,还在于该书是清末政府官员首次站在官方立场上亲身考察仍有“蛮貊之邦”之嫌的欧洲社会,无论是从考察言之,他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传之于人,必然会对中国朝野士大夫产生强烈的反响。他肯定了西方的先进,并没有把英国描绘成中国人设想中的夷狄之邦,他的观点虽然不受顽固派的欢迎,但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走向世界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斌椿一行受到英国政府的欢迎,西方国家对于清政府的遣使之举所表现的温和和鼓励态度,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如意算盘,但还是部分地打消了清政府对遣使异域所怀有的疑惧心理,初步验证了遣使的可行性。因此,此行是成功的。
1868年,奕等奏请派遣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毂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会同接受清政府聘请担任清政府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前往欧美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是为遣使的第二次尝试。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蒲安臣使团是正式的官方外交使团,负有正式的外交使命。
当时,清政府面临着“转瞬又届十年修约之期,(西方列强)必致多方要挟,如开铁路,造铜钱等事再三恳请”〔39〕的严峻形势,尤其令清政府忧虑的是西方列强有可能“互相要约,群起交争,甚至各带兵船,希冀胁制,务满所欲。若不允准,无难立启衅端”〔40〕。因此,总署王大臣认为遣使已至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41〕。在他们看来,派遣一个使团访问欧美有约各国,可以“笼络外洋”,缓和中外之间的紧张气氛,“派大臣前往各国,遇有中国不便事件,即可商之该国,以免隔膜,外国使臣亦不至动凭臆见,肆其要求,而该国政令之得失,形势之强弱,亦可洞见端倪,以凭筹策”〔42〕。奕等在奏派蒲安臣为使时明确提出了外交任务:“现值修约之期,但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总理衙门覆准,方能照行。”〔43〕因此,第二次尝试并不是第一次的简单重复,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它表明清政府在遣使之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第二,清政府在关键时刻起用了一个美国人来作使团的首领,引导中国前进。
礼节问题一向是中外交往最敏感的问题。在第一次尝试时,虽然也用了外国人,但是,赫德只是以向导的身份出现,而且由于第一次尝试没有外交使命,也就避免了外交礼仪的麻烦,因此,居前台的始终是斌椿,赫德则隐藏在幕后。第二次尝试就不同了,它有外交任务,必然牵涉到礼仪问题,而坚持中国的礼制被认为是维护天朝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在当时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总署诸公当然不敢轻率处之。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44〕。也就是说,用外国人为使可以避开长期纠缠不清的礼节问题,因此,他们聘请了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实际担任此次外交行动的总首领。因为他是美国人,因此,即使他在外交场合没有遵行中国礼制而行西方礼节,也并不能够表示中国政府在礼制问题上已经让步,而只能解释为暂时回避。清政府还特别训令蒲安臣,“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礼节,再行照办”〔45〕,其态度非常鲜明。但这只是清政府的一厢情愿,蒲安臣使团出访的结果表明:清政府既想收外交之实益,又避开外国人争持的礼节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出访中,蒲安臣遵行了西方外交礼节,使得清政府在后来的外交礼节争论中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外交礼节并没有因为用外国人为使而取得妥善的解决,倒是蒲安臣赫然居于使团的头面人物位置上,引人注目。
清政府在第二次尝试中,仍然采取了稳健、谨慎的态度,有限地追求新的目标,这与第一次是一致的。他们虽赋予此次尝试以外交的使命,希望从遣使的外交效益方面探索遣使的可行性,但又在企图避开礼制的问题,把它留到以后去解决,因此,他们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派了一个外国人来充任使团的首领,完成这艰难的一步。
这次尝试从1868年2月持续到1870年10月,历时两年又八个月, 遍访了欧美有约各国,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的普遍欢迎。奕等认为此举“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46〕,从而增加了遣使出洋的信心。但是,用外国人为使的负效应却表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清政府非常震惊,再不敢在外交大政上假手于人。第一,由于中国代表志刚、孙家毂等不熟悉西方的外交程序,所以,访问、谈判等一切外交活动皆听蒲安臣的摆布,从而丧失了中国代表的主动权,背离了总署“专重中朝二使”〔47〕的初衷。第二,蒲安臣还有违训越权行为,在出使的第一站美国,即擅自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当美国公使劳文罗斯携约来华要求立即互换时,总署极感困窘,只好设词延宕。第三,礼节问题也并没有因为用外国人为使而获得妥善的解决,由于蒲安臣一行自始至终都实行西方的外交礼节,这就给西方列强在中外礼节的争论中打开了方便之门,外国驻华公使“因即援以为例”〔48〕,要求解决觐见问题。
从使节制度的近代化方面言之,由于用外国人为使发生了上述种种问题,清政府就不得不引以为戒,从中吸取教训。如果要真正从传统中走出来,就必须挣脱外力的影响,独立地行动。在遣使方面,就必须摆脱外国人的帮助和掣肘,采取正面行动,任用中国人为使。否则,就不能排除用外国人为使而产生的流弊,就有可能为守旧者制造攻击的口实,也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损害国家权益的恶果,从而也必将延宕非常难产的出使事业,这当然是主持外交大计的奕、李鸿章等所不愿看到的。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遣刑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一个陪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是为第三次遣使尝试。
这次遣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清政府派遣了一个满族官员作为使团的首领,终于在遣使的主要方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已经取得了遣使的初步经验,对于遣使具有比较充分的信心,同时,它又吸取了用外国人为使的教训,迟早得派中国人为使;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次遣使是应法国公使的强烈要求和外国公使附和而专往法国完成道歉的特殊使命,也只有任命中国人为使之一途。就主持者而言,尽管他们也感到此次出使是一种屈辱,但是,也正好借西方国家驻华公使的要挟钳反对派之口,使得独立遣使之事可以早日完成。但从使节制度的近代化方面言之,它表明清政府又向前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没有聘用外国人为使的情况下,中国官员终于跨出了国门。它标志着清政府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经走出了传统的藩篱,取得了某种独立办外交的信心和能力。因此,建立近代使节制度的时机已开始成熟,当1873年觐见礼仪获得解决后,清政府的遣使尝试工作就算完成了。
四、开端的意义
黄河九曲十八弯,但最后还是汇入了大海。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尽管有不少艰难曲折,但序幕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拉开。尽管尝试阶段的时间长了些,但是,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在。
从清政府三次尝试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尝试是成功的。它以派遣旅游观光团开其端,而以派遣外交使团继其后,由前两次用外国人为中西交接的媒介和使团的首领,到第三次独立派遣中国人走出国门,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完了尝试的全程,而且每次遣使的预定目标,成功地证明了建立近代使节制度的可行性。主持外交的洋务派对此是非常满意的,他们对遣使出详已不再犹豫,决心一试了。正如李鸿章所说:“近年奉诏迭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将来与之(即日本)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49〕
第二,尝试是艰难的。清政府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来摸索遣使的利弊得失,时间之长,本身就是尝试艰难的很好的注脚。东邻日本打开国门的时间比中国晚,而向外遣使的时间却比中国早,以中日互遣使节论,日本在1872年即向中国派遣副岛种臣为公使〔50〕。而清政府迟到1876年才有遣使日本之命,1877年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才到日本履任。中日两国对此作出的反应的快慢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富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国际社会时反而为传统文化所拖累,节奏要慢得多。
第三,它表现了清政府欲以满人、旗人办外交,操持外交政柄的决心。三次尝试的重要人物斌椿、志刚是旗人,崇厚是满人,只有孙家毂是当时真正的“汉人”。但由于满人长期习于优闲的生活,洋务人才比较缺乏,而同文馆教育又不能骤解燃眉之急,因此,在1878年派遣崇厚为特使出使俄国,而不幸招辱后,满清政府也只好暂时放弃任用满人操持中国外交
注释: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4,四裔四。
〔2〕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页525。
〔3〕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页130。
〔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4,四裔四。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页15。
〔6〕《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46。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第38册,页267。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 页265。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页736。
〔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页737。
〔1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4,四裔四。
〔11〕《筹办事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页77—78。
〔12〕马其昶《清故出使义国大臣许公墓志铭》。
〔13〕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清廷之改革与反动》,第172页。
〔14〕魏源《海国图志·叙》。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页1474。
〔16〕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同治5年12月18日。
〔17〕史策先《梦余偶抄》,卷1,页24。
〔1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页1。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页27。
〔20〕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3。
〔21〕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4。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书,页5。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书,页3。
〔2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页45。
〔29〕《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3
〔30〕同上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页32。
〔3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页59。
〔3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页1—2。
〔34〕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4。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页2。
〔3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页1。
〔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页1。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页2。
〔39〕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3。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页25—26。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页32。
〔42〕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页3—4。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页27—28。
〔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页27。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页4。
〔4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9,页14—15。
〔47〕方浚师《退一步斋文集》,卷4,页21。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页16。
〔4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页54。
〔5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页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