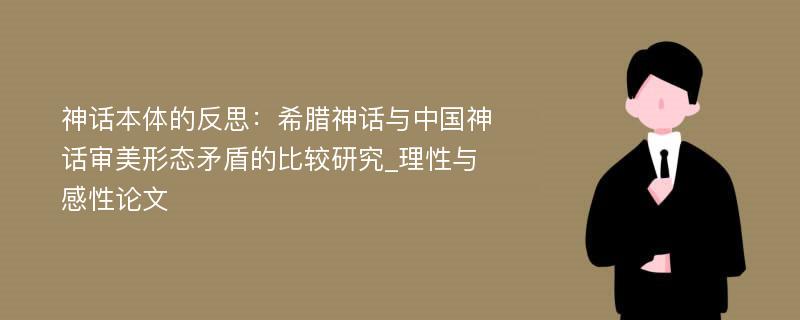
神话的本体反思——关于希腊神话和华夏神话审美形态悖立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华夏论文,本体论文,形态论文,希腊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神话空间在原始初民逃避死亡追求永恒和无限的历史中创生
从生命本体论的视角审度,原始自律理性作为原始初民生命本体的自律构成因素,其决定了原始初民的生命本质是在自我规定的意义上被界定的。这也正是人与动物在心理机制上的本质区别。也正是在生命的洪荒中觉醒的原始自律理性,给原始初民带来一个生与死悖立的情感世界。
当原始理性的自律启蒙使原始初民意识到生,以孩提般的原始童贞心态去拥抱生命生存的欢悦时,他们又无可抗拒地意识到死,他们又必须以孩提般的原始童贞心态去体验生命面对死亡的恐惧。这正如华夏哲人庄子在抽象的玄学本体论中对生与死的辩证体验,《庄子·齐物论》载:“方生方死,方死主生”,①《庄子·田子方》又载:“生死亦大矣而无变乎己。”②的确,人在意识到生之欢悦的瞬间,死亡便热烈地拥抱着人。
宇宙时空的无限与永恒和生命时空的有限与短暂同步悖立,从而形成了生命的双项终极价值反差。人以无限、永恒的宇宙时空为参照系,生命的短暂和有限就意味着死亡。从生命本体论意义上审度,在意味着死亡的生命躯壳中,无疑颤栗着人类的生命时空恐惧感。觉醒的原始理性使人意识到生的瞬间,其心态就偏失于生命时空恐惧感的煎熬。
原始自律理性使人意识到生,且又使人面对着死亡别无选择。生与死的轮回也正如昼与夜的交替是大自然的律令。《庄子·大宗师》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③人不可抗拒死亡就象人不可抗拒生一样。这正如马林诺夫斯基讨论宗教和神话创生时所言:人类不能不在死的阴影之下去生活。因此,逃避死亡追求精神的永恒和无限,成为原始初民生存的第一要义。
但是,人不能超越生命自身的肉体极限,去追求生命占有时空的永恒与无限,以达到逃避死亡的终极目的。因此,原始初民只有乞助在生命本体中觉醒的原始理性,在生命的内心世界构建一个使自我得以在宁静的永恒和无限中栖息的理想国度。当这一理想国度从原始初民的内心世界外化为既成的文化表象时,人类文化的始态——神话空间,在原始初民积极逃避死亡的历程中辉煌地创生了。
二、希腊神话:理念的感性显现;华夏神话:有意味的形式
原始自律理性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Bing),其无法赤裸裸地直面人生;只有符号化的感性形式才是原始自律理性得以生存的家园归宿,作为始态文化的神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的。而原始自律理性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对负载、显现自我的符号化感性形式的不同选择,导致希腊神话与华夏神话走向原型的悖立和表象形态的分野。
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美时,其根据理念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对负载、显现其形式的不同选择,把人类艺术界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如果我们遵照黑格尔对艺术界分的归类,我们只能把华夏神话作为“艺术前的艺术”归置于古朴、抽象、朦胧、隐喻的东方象征型艺术范畴。的确,华夏神话缺少希腊神话那种古典型艺术理念和形式的完满与合一。希腊神话作为古典艺术,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在理念与形式的合一中,显现出审美的完善、和谐、统一、均衡、庄严、凝重与静穆。而华夏神话则在其抽象的感性形式变形中,显现出悖于黑格尔美学命题的神秘、怪诞、奇壮、浊重、恐怖、敬畏、荒野与狰狞。黑格尔的美学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已把古老的华夏神话(东方古代艺术整体)降解为低级形态艺术,并把其从美的空间中驱逐出去。而面对黑格尔对东方艺术的贬斥,百年后的克莱夫·贝尔以更精彩的美学命题: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又把古老的华夏神话(东方古代艺术整体)救解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抽象变形艺术,而最终又重新把其带入美的空间。
华夏神话正是如此悲剧般地在黑格尔与贝尔的美学命题冲突中,从审美的空间失落又复归其中。
实质上,黑格尔的美学命题,及至克莱夫·贝尔对黑格尔美学命题的回敬和反动,两者均没有在理论上回答希腊神话(理念的感性显现)和华夏神话(有意味的形式)在形态上悖立的深层终极原因。而这也是存在于人类东西方文化始态的一个古老而诱人的美学之谜。
三、希腊初民敬奉的神话圣地:奥林波斯
让我们的思考来到希腊初民敬奉的神话圣地:奥林波斯。
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大壁上的希腊神谕:“认识你自己”,就是希腊初民在原始理性觉醒后,力图走向主体自觉而自识为人的格言。原始自律理性逃避死亡而追求永恒与无限,这实质上昭示了原始初民积极地逃避于神话空间认识自我的生命本能。希腊神话的创造主体正是遵循神谕的宗教教义,按照人的自我形象去塑造了人格化的奥林波斯诸神。黑格尔之所以把希腊神话投注于古典艺术的审美范畴,正因为希腊诸神及其造型本身就是人的理念与形式的完满合一。
而希腊初民为什么能够按照人的自我形象去塑造人格化的希腊诸神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母题。值得我们观注的是希腊初民在建构创世神话时,其觉醒的原始自律理性就把人之自我投注于奥林波斯空间的创世本体。赫西俄德《神谱》把卡俄斯界说为于创世前而存在的一个有着人格化生命繁殖能力的最高神,也正是卡俄斯孕育了地神该亚,小爱神厄洛斯等之后,从此希腊神话得以开始了它诗一般的人格化故事。卡俄斯作为希腊神话的人格化创世本体,昭示了希腊初民原始自律理性已觉醒到把人之自我投注于神话空间逻辑序列倒溯已尽的极限。因此,人,就是希腊神话的本体;又因此,人,就是希腊神话的最高创世主。
中世纪的第一教父哲人圣·奥古斯丁宣称:在基督教的创世纪中上帝是永恒的;费尔巴哈在反基督教义中也宣称:“基督教允许人以永恒的生命,以此断送了人的受时间限制的生命,要人去信仰上帝的帮助……”④值得回味的是,希腊神话诗人俄耳甫斯的徒子也诗一般地把创世主卡俄斯咏叹为永恒时空的产物。无疑,卡俄斯又象征着时空的永恒。这是一个再精巧不过的暗示了;希腊原始初民凭借觉醒的理性超越了生命的肉体占有时空的短暂与有限,把自我投注于神话空间的本体,在神话空间的本体极限上热烈拥抱着永恒与无限。最终,死亡被抛弃了,与此同时,希腊神话空间及其本体在无限与永恒中被希腊初民人格化了。
希腊诸神,本质上就是希腊神话的创造主体按照人之自我形象所塑造的,并超越了自我生命肉体的有限与短暂趋向于无限与永恒的人。
四、华夏初民敬奉的神话圣地:古昆仑
让我们的思考从西方奥林波斯回溯到东方华夏初民敬奉的神话圣地:古昆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所在。”⑤华夏百神正是栖息在这一理想国度,象征着、隐喻着华夏初民逃避死亡而对永恒与无限的追求。在古昆仑这块始态文化圣土上,华夏初民没有象希腊初民那样在昆仑的玉槛上执着地镌刻下诗一般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正因此,这块圣土的文化色调似乎在原始洪荒的扑溯迷离中比希腊神话显得更加古老、神秘、怪诞和朴野。华夏神话的创造主体,大多是没有按照人的自我形象去塑造人格化的华夏百神。
华夏初民为什么没有能够按照人的自我形象去塑造人格化的华夏百神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母题。值得我们观注的是,华夏初民在建构昆仑神话时,原始自律理性的觉醒就没有完满地把人之自我投注于古昆仑空间的创世本体之上。因此,华夏神话的创世主(造物主)作为最高存在一生成,其在造形上就趋向于准人格化的元宗教崇拜。
华夏神话在创世本体上真的缺憾人格化的造物主吗?让我们沉入浩瀚的华夏史典中精确地考证华夏神话创世主的造型,去验证这个危言耸听的命题。
积淀在华夏民族集体心理结构中的标准创世神话就是女娲开天辟地之说。那么女娲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于古昆仑空间的本体之上呢?
两千年前,屈原曾最早于《天问》的质疑中透露出华夏初民对神话本体的终极追求意识:“女娲有体,孰能匠之?”⑥汉人玉逸在《楚辞章句》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⑦王逸之子王延寿在其《鲁灵光殿赋》中也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⑧我们从女娲人首蛇身的造型上可以看出,女娲作为古昆仑空间的最高神,其感性形象界于人格神和非人格神之间,呈现为半人半兽的准人格神。那么,女娲作为华夏神话空间的造物主,其人首蛇身之躯,又究竟是“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呢?屈原和王逸于千年前就带着一种对神话本体的终极追求困惑,向华夏神话的最高造物主的“制匠”者设问。当然,这个“制匠”者只能在神话空间之外寻找,即创造始态文化(神话)的主体——人,也即华夏初民。
我们从女娲的准人格化造型上判断,原始自律理性还没有完全觉醒到使华夏初民能够按照自我形象去塑造华夏神话空间的最高神。关于女娲造型的非人格化因素,不食官遗之粟的列御寇于千年之前即也有所明视,且偏激地把女娲置于非人行列。《列子》曰:“……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⑨
王逸,王延寿,列御寇对女娲造型的非人格化因素载录是共同的。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审度,是华夏初民的深层心理结构支撑并构成了华夏神话的现象文本结构。深层心理结构必然?也必须与其所对应的现象文本结构是同构对应的。因此,原始自律理性给定华夏初民深层心理结构的非人格化造神因素,也应该普泛化在其所造之神的其他行为方面。
五、华夏初民没有把诗一般人格化生命孕育投诸女娲
华夏初民赋予女娲创生人类的方式,也非同于希腊神话空间的本体卡俄斯。卡俄斯对生命的创生是诗一般的人格化生命孕育。而《太平御览》载:“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⑩从“女娲抟黄土作人”考查,发生于华夏初民深层心理结构的原始自律理性还没有觉醒到把人类自身人格化的生命孕育诗一般地赋予女娲。因此,女娲创生人类的方式也是非人格化的。学术界众多学者历来把女娲创生人类的方式读解为人格化的生命孕育,这一观点在本质上是悖于华夏初民创神的深层心理结构的,是不能成立的。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袁珂从文字学的角度把女娲“一日七十化”之“化”读解为生命的人格化“孕育”和“化生”,以为女娲是以人格化生命孕育的方式创生人类的最高人格神。但这一“化”字究竟能否读解为人格化的生命“孕育”和“化生”呢?我们为了求证原始自律理性在华夏初民深层心理结构中觉醒的程度和女娲创生人类的方式,我们必须“我注六经”式地去正确读解这一“化”字。
在文献典籍中,除了王逸有女娲“一日七十化”之说,《淮南子·说林训》又有“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之说(11)。高诱在此把“化”读解为“变化”,曰,“女娲王天下者,七十变造化。”(12)但是,袁珂以为“变化”并非是人格化的生命孕育,因此不能把“化”读解为“变化”。这样袁珂又重新去读解这个“化”字。袁珂在《古神话选释》中以《吕氏春秋·过理》“(纣)剖孕妇而观其化”来验证,“故‘一日七十化’只能作‘孕育’解,不能作‘变化’解”。(13)袁珂把《过理》“观其化”之“化”读解为生命的人格化“孕育”,实际上是依照高诱对此句望文生义的误注:“化,育也,视其包里”。(14)并且袁珂又进一步把这个“化”读解为名词,释义为“胎孕”。既然《过理》“观其化”之“化”被读解为生命的人格化“孕育”,那么女娲“一日七十化”之“化”也必然应读解为生命的人格化“孕育”。而实质上,《过理》的“观其化”只能读解为“观其死”。《吕氏春秋·过理》前面一篇《知化》,就是讨论子胥知死而以死谏夫差之事绩:“子胥非不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邱墟祸及庐。”(15)“知化”即“知死”。“化”读解为“死”之意,在文献典籍中不乏其例。《孟子·公孙丑》有:“且此化者,无使土亲肤。”(16)朱熹注曰:“化者,死者也。”(17)《淮南子·精神训》又有:“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18)高诱在此所注才是正确的:“摩,灭;犹死也,……化,犹死也。”(19)因此,如果用《吕氏春秋·过理》“观其化(死)”去注释《淮南子·说林训》“此女娲所以七十化”,实质上只能得出“此女娲所以七十死”之误说。因此,袁珂把女娲“一日七十化”读解为人格化的生命“孕育”,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
但问题并非就此罢了。袁珂把“七十化”之“化”读解为“化生”,这似乎并不错。但从话语的文本内涵审度,“化生”也没有人格化的生命孕育之意。《俱舍论》载六道众生有四种形态:其一为卵生。其二为胎生。其三为湿生。其四为化生。化生,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因此,“化生”的文本内涵应是指从虚无的无所依托中变化和创生万物表象的非人格化方式。这也正是华夏文化道家和阴阳家把宇宙本体如何创生的猜想引入虚无之中的一贯心理。所以,把“七十化”之“化”的文本内涵误解为形而上的“化生”,这也不符合女娲从形而下的非生命黄土变化和创造人类的本义。高诱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把“化”读解为“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女娲“一日七十化”创生人类的行为方式不能读解为生命的人格化孕育。
从女娲的造型和创生人类的方式审度,原始自律理性在华夏初民深层心理结构中还没有觉醒到使华夏初民把人之自我完全投诸于神话空间的本体,从而去塑造一个人格化的最高造物主。正因为华夏神话在本体上失落了人格化造物主,也更因此使华夏初民没有能够按照人的形象去塑造华夏百神。据笔者统计,栖息在《山海经》中的华夏百神共有数百种,其绝大多数都是人的理念与形式在变形中分离的半人半兽的准人格神。但无疑,华夏神话空间的建构同样昭示了华夏初民对自我生命肉体生存之短暂和有限的超越及其对无限与永恒的追求。死亡在人兽合一的古昆仑神话空间中被悲壮地抛弃了。
六、三个神话世界的界分与二种造神原型的审美价值取向
荣格把一个种族神话的古老原型追溯到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最遥远处。而任何一个种族的神话原型都必须以负载它的感性形式而显现自我。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潜藏在希腊诸神和华夏百神感性造型表象下的诉诸视觉直观的造神原型。造神原型也就是原始自律理性使原始初民按照怎样程度的人之自我形象和动物的形象塑造诸神感性形式的典型心理经验,它昭示了原始自律理性觉醒的程度。
让我们从现象学的还原理论启步,把藏匿在远古文化心理结构深处的造神原型从诸神的感性造形表象上把它还原出来。在理论上,我们按照诸神审美造形可以把人类的神话空间界分为三个神话世界:第一神话世界,第二神话世界,第三神话世界,(简称神界Ⅰ,神界Ⅱ,神界Ⅲ)。
神界Ⅲ是非人格神崇拜的神话世界。栖息在神界Ⅲ的神是原始初民完全按照动物(植物)的形象(20),借助动物肉体的强健和蛮力所塑造的兽形神。在这个神话空间中,原始自律理性还没有觉醒到超越生命的原始荒蛮,使原始初民能够部分地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去塑造神。
神界Ⅱ是准人格神崇拜的神话世界。栖息在神界Ⅱ的神是原始初民部分地按照人之自我形象,部分地按照动物的形象,乞助人的智慧和动物肉体的强健和蛮力所塑造的半人半兽形神。在这个神话空间中,原始自律理性已开始在生命原始荒蛮中觉醒,并力图使原始初民退出兽形神崇拜的神界Ⅲ,能够部分地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去塑造神。
神界Ⅰ是人格神崇拜的神话世界。栖息在神界Ⅰ的神是原始初民完全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和人的行为尺度所塑造的人形神。在这个神话空间中,原始自律理性已完全在生命的原始荒蛮中觉醒,并使原始初民退出兽形神崇拜的神界Ⅲ和半人半兽形神崇拜的神界Ⅱ,完全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去塑造神。
让我们从三个神界的界分理论反观希腊神话和华夏神话。
在希腊神话空间,奥林波斯诸神都是栖息在神界Ⅰ的人格神。只有从古埃及神话空间引渡过来的司芬克斯是唯一的人首狮身的准人格神。希腊神话空间的造型整体上隶属第一神界。希腊诸神在神明的庄严典礼中展览的是人的肉体造型的完美。在这个神话空间,原始自律理性完全觉醒,它使希腊原始初民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塑造的希腊诸神的人格化造神原型被凝固的希腊雕塑群体永恒地表象着、复制着、回忆着。
胡塞尔把直观的“悟”觉带入本体论,以为现象就是本质的直观。这不无给我们某种启示,希腊诸神群体的造形表象本质上就是奥林波斯造神原型的本质直观。奥林波斯的造神原型,正是原始自律理性在历史的积淀历程中,觉醒到使希腊初民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塑造希腊诸神的典型心理经验。正是这一凝固为典型心理经验的奥林波斯造神原型作为一种文化惯性,不可遏制地在西方视觉艺术史上成就了漫长的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又成就了无数高扬古典艺术风格的造型艺术巨匠。
而在华夏神话空间中,华夏百神大多是栖息在神界Ⅱ的准人格神。人首与兽身的奇异嫁接,使华夏百神在表象的变形中显现出古昆仑造神原型的朴野、古老和原始的求生力量。
《山海经·山西经》载:“其十神者,皆人面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西次三经》载:“神英招…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又载:“神陆吾……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虎爪。”《中次三经》载:“吉神泰逢……其状如人而虎尾。”《海外北经》载:“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21)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华夏初民用“神”这样一个文字符号所指称的文化对应物是明确的。“神”仅指称栖息于神界Ⅱ的准人格神。严格地讲,在古老的华夏神话系统中没有栖息在神界Ⅲ中的非人格神。《山海经》把栖息在神界Ⅲ的奇鸟怪兽称为“兽”,或称为“神兽”。“神”与“兽”的界分是华夏神话的文化特色。因此,华夏神话空间在造神原型理论上基本上隶属第Ⅱ神界。在古昆仑神话空间中,原始自律理性还没有觉醒到使华夏初民完全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去塑造华夏百神,而是部分地借助动物肉体的强悍和蛮力去平衡其生命的时空恐惧感,从而满足原始生命逃避死亡对永恒和无限的追求。
神界Ⅱ是一个怎样的神话空间呢?人首与兽身嫁接所显现的视觉变形造形符号偏离了人之理念感性显现的审美和谐,走向了抽象的审美意味。华夏百神群体的审美造形就是古昆仑造神原型的本质直观。古昆仑造神原型,即是原始自律理性在历史的积淀过程中觉醒到使华夏初民部分按照人王自我形象,部份按照动物形象,乞助人的智慧和动物的强悍塑造华夏百神的典型心理经验。也正是这一凝固为古昆仑造神原型的典型心理经验作为文化惯性,使华夏后代无数艺术大师在创作的激情中永恒地体验着、回忆着、重复着同一种抽象的变形的视觉造形艺术符号。如果说希腊诸神的造型显现了古典的和协美,而华夏百神的造形在变形中显现了稚拙的抽象美。这不正是几千年后的西方现代派艺术家企图超越理念之感性显现的古典艺术的和谐,刻意追求的有意味的抽象变形艺术吗?
七、空间恐惧感和空间信赖感导致原始自律理性向两种文化表象形态生成
在华夏神话空间,原始自律理性为什么没有觉醒到象希腊初民那样按照人之自我形象去塑造神界Ⅰ的人格神,而是塑造了神界Ⅱ的准人格神呢?这是一个绵亘华夏神话空间的司芬克斯之谜。
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审度,华夏神话的发祥圣地古昆仑缺乏奥林波斯圣地那种使人易于为生的自然生态条件。
何幼琦在《海经新探》把古昆仑考证为东岳泰山。而正是作为古昆仑的东岳泰山被中原齐鲁两地拥抱着。《史记·货殖列传》载:“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22)这是怎样的一个方栖息营生之地呢?《汉书·地理志》载:“泰山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23)《汉书·食货志》载晋灼注曰:“舄卤之田不生五谷也。”(24)《汉书·地理志》又载:“泰山鲁地狭民众……无林泽之饶。”(25)簇拥古昆仑的齐鲁之地,其艰险和困苦又是整个华夏中原的写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也描述了在黄河两岸上居住的华夏先祖们拥有一个艰苦的为生环境。我们从《汉书·食华志》载录可窥视华夏初民的营生状况:“天寒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26)华夏大地的艰险和困苦就是这样非但不接受并且拒斥华夏初民在其中的栖息和营生。
但是人的求生原则和求生欲望决定人必须借助一个中介因素来调整其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的《文化与进化》就把这一适应性中介称之为文化。文化就是人调节其适应地理环境的机制。
原始自律理性在原始初民生命本体中觉醒后便开始外投,寻找负载它的感性形式,且向文化生成。原始自律理性使华夏初民认识到他们面对的外部物质空间世界是艰险的,可怕的,是拒斥自己的。因此,从认识论意义上审视,空间恐惧感又成为他们的心理特征。原始理性在觉醒的历程中从华夏初民生命本体内外投,但遭到了外部空间世界的拒斥后,只有从外部世界退缩回来,内投于生命自身,来平衡其面对自然之艰险所产生的空间恐惧感。这个文化意象也就是华夏初民调节其适应地理环境的中介;这个适应性中介就是作为华夏始态文化的华夏神话。华夏神话,这是一个在内心世界的抽象中营构的理想世界。由于外部物质空间世界的拒斥,原始自律理性无法从华夏初民的生命本体内部完全外投而走向完全觉醒。因此,理性也就没有能够把华夏初民从其自我的内心世界完整地投入到外部世界,作为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去摹仿、再现、塑造。只有人把自我认可为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去塑造,这才象征着理性完全外投且走向完全觉醒。华夏百神,就是理性内投后,在抽象中部分乞助人的智慧(人首),部分乞助兽的力量(兽身)而综塑的那个艰险的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华夏初民正是乞助这样一个适应性文化中介:人首兽身的准人格神,作为调节其适应华夏中原生态环境的文化机制。
人首兽身的准人格神,也正是原始自律理性在古昆仑空间中寻找到的赖以显现自我、负载自我的感性造形形式。
让我们的视界回溯到在爱琴海的怀抱中漂弋的希腊半岛。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温情的诗意描述了拥抱着奥林波斯的古希腊,认为他们的气候是上帝的恩赐:“在希腊文明中心雅典,南方最上品的果树不用载培就能生长,那儿每隔二十年才结一次冰,夏季的炎热有海上的微风调剂,除了从色雷斯偶吹来的几阵东北风,地中海上有一股酷热的东南风以外,气候非常温和。”(27)丹纳又慨叹道:“在这样的气候中长成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更快,更和谐。没有酷热使人消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他们既不会象做梦一般的麻痹,也不必连续不断的劳动,既不沉溺于神秘的默想也不堕入粗暴的蛮性。”(28)觉醒的原始自律理性使希腊初民认识到他面对的外部物质空间世界是友好的、和谐的,是随时准备接受欢迎自已的。因此,空间信赖感又成为他们的心理特征。在这样一方使人易于为生的环境中,原始自律理性从希腊初民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完全外投出去,坦然的与外部世界对话,且走向完全的觉醒。又正是如此,觉醒的原始自律理性也就能够把希腊初民从其自我的内心世界完整地投入外部世界,把自我作为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去安然地玩味、再现、摹仿和塑造。这个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希腊初民,也就是希腊诸神。希腊神话空间就是外投的原始自律理性对希腊现实世界的真实摹写。在希腊神话空间中,人就是神,神也就是人。希腊初民赖以适应这一地理环境的文化机制,也就必然表现为人的理念感性显现的文化中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讨论希腊艺术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形态时,把人类古代民族界分为三种心理成熟质:“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29)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又为我们界分三个神话世界提供了理论的阿基米德点。栖息在神界Ⅰ的希腊诸神,其人之理念感性显现的人格神表象形式作为适应性文化中介,是“正常儿童”心理的同构对应物。栖息在神界Ⅱ的华夏百神,其半人半兽的准人格神表象形式作为适应性文化中介,是“早熟儿童”心理的同构对应物。栖息在神界Ⅲ神话现象,其非人格化表象形式作为适应性文化中介,是“粗野儿童”心理的同构对应物。
原始自律理性作为原始初民的心理机制,从荒蛮走向觉醒的历程也昭示了原始初民心理结构从荒蛮走向成熟的历程。而神界Ⅰ、神界Ⅱ、神界Ⅲ也正是界分原始初民心理成熟质的三种文化界标。参照希腊诸神栖息的神界Ⅰ,这的确昭示了华夏神话创造主体其心理结构的早熟。
八、希腊神话:向艺术生成 华夏神话:向历史生成
原始理性作为原始人性的构成因素,对负载其形式的不同选择,终于导致东西方两大神话系统趋向审美形态和审美品质的分野。
外投的原始自律理性建构了希腊神话创造主体的外倾性人格。希腊初民正是在人格外倾的移情中高扬着现世的乐生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使希腊诸神那不种在理念的感性显现中走向和谐的人格神造型充斥着审美的诗性智慧,因此希腊神话一发生就不可扼制地向艺术生成。黑格尔正是立足于再现艺术本体论的视角,把希腊神话作为再现现世的古典艺术慨叹。希腊神话,首先是作为独立形态的艺术,其次才是历史。黑格尔界定的美,也正是高悬在希腊诸神人之理念感性显现的和谐上,为后人仰之弥高。
内投的原始自律理性建构了华夏神话创造主体的内倾性人格。华夏初民也正是在人格内倾的抽象中高扬着伟岸的原始人格求生力量,使华夏百神那种在抽象中变形的准人格神造型充斥着沉重的史性智慧。华夏百神那种在抽象中变形的准人格神造形,在人类文化发展史程中,直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始终没有被人们作为一种能直接给人以视觉审美和谐的艺术而承诺。因此,华夏神话最终没有从历史文献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审美艺术形态。华夏神话沉落在历史中,华夏的智者往往苛求以历史求证神话,以神话求证历史。因此,“黄帝四面”、“夔一足”能够在孔子那里得到合理的史性解释。最终,这种神话与历史双项循环求证的文化惯性使华夏的统治者以神的身份走进了神界,而神界的主宰者又以人的身份走进了历史。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的双项循环惯性,终于冲积成了神话与历史交融构成的华夏二位一体文化。正是如此,孔子于《论语·述而》中才背负着历史的优患意识郑重宣告:“子不语怪力乱神。”(30)
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行程就是一个在偏失中追求平衡,在平衡中追求偏失的怪圈。原始自律理性的觉醒使原始初民渴求以思辩的逻辑力量追求人格心态的理性和谐,摆脱人格心态的原始偏失。当黑格尔在思辩中承继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把理性的审美和谐带到宇宙本体,完成了终极的体系建构;人,却又无法接受理性给人自我设置的那个和谐而严谨的审美规范。因此,当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冲击宇宙本体论的理性审美和谐,对黑格尔进行反对时,作为哲学附庸的艺术必然同步转换了它的审美价值取向。还是那个西方人克莱夫·贝尔驻足于表现艺术本体论的制高点,使美从希腊诸神的理念的感性显现中失落,回归华夏百神的有意味的形式。
美,从西方圣地的奥林波斯空间失落,回归到东方圣地的古昆仑空间;这究竟意味着西方古典艺术的没落,还是东方古典艺术的崛起?
是美愚弄了人,还是人愚弄了美?
注释:
①②③ 《庄子》,参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17,60,28页。
④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三联书店版,下卷第781至782页。
⑤(21) 凡引《山海经》皆见《二十二子》同上,不注明页码。
⑥⑦ 凡引楚辞和王逸章句皆见《楚辞补注》洪兴祖撰,中华书局版,不注明页码。
⑧ 《文选》,萧统编,中华书局版,第171页。
⑨ 《列子》,参见《二十二子》同上,第202页。
⑩ 《太平御览》,李肪著,中华书局版,第365页。
(11)(12)(18)(19) 《淮南子》,参见《二十二子》同上,第1285,1285,1235,1235。
(13) 《古神话选释》,袁珂著,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
(14)(15) 《吕氏春秋》,参见《二十二子》同上,第716,716页。
(16)(17) 《孟子》,参见《四书集注》朱熹注,岳麓书社版,第303,304页。
(20) 本文把神话现象中的植物崇拜也归属于神界Ⅲ,但不专门论述。
(22) 《史记》中华书局版,第3265页。
(23)(24)(25)(26) 《汉书》,中华书局版,第1660,1120,1660,1131页。
(27)(28) 《艺术哲学》,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45,24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114页。
(30) 《论语》,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版,第24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