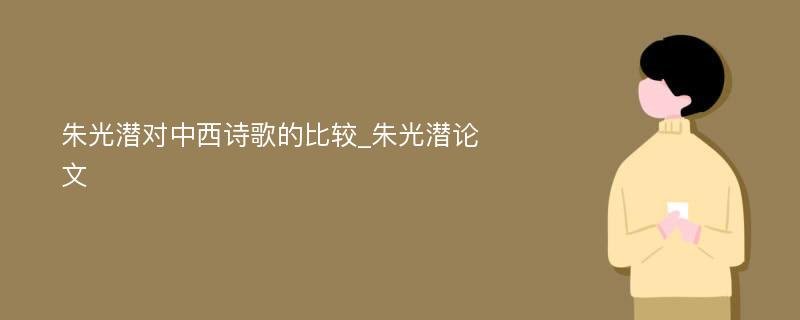
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诗歌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光潜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学问家。他在二三十年代曾写过一组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文章,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精湛,析理之透辟,文笔之优美,至今少有出其右者,对今天的诗学研究仍极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
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朱光潜首先注意到中国和西方有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是短小的抒情诗,而西方各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则是长篇叙事诗;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抒情诗一直比较兴盛,而西方各民族的叙事诗则相当繁荣。
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里,他指出:古希腊文学的发端,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为先导,这两部宏篇巨制的长诗,杂糅神话和历史传说而成,既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渊源,也开创了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英、法、德和芬兰诸国文学的发展,最早的重要作品都是长篇英雄史诗,如英国的《贝奥武夫》、法国的《武功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芬兰的《卡勒瓦拉》等等,莫不如是。与此相异,中国最早的诗歌,如《诗经·国风》里的篇章,不仅内容十之八九是抒情诗,而且篇幅千篇一律都比较短小。在随后的演进中,西方像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一类的长篇叙事诗,可说多得举不胜举。但在中国,虽然偶尔也出现一两篇长篇叙事诗,如被沈德潜称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却只有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多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短篇叙事歌(ballad),而无法算长篇叙事诗(epic),因为它和西方长篇叙事诗动辄数万或数十万字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为什么中国最早出现的是抒情短诗而不是英雄史诗?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长篇叙事诗一直不发达?在朱光潜看来,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中国文学偏重主观表现,讲究含蓄简约的特点所致;二是由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
就前一方面言,十分明显的是,《尚书·虞书》中提出的“诗言志”思想,可说是中国历代诗人和诗论者的共同信条。《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这种偏重主观表现的诗歌思想,在中国文人心田里生根发芽,使历代作诗者和论诗者在创作、评论时,一般都把文学当作抒发自己观感和怀抱的器具,而并不重视作品是否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客观对象。所以在中国诗话里,“风骨”、“气韵”、“胸次”、“性灵”、“高格”、“才情”等种种强调主观志趣的论说,比比皆是,而探讨如何模仿和刻画客观对象的论述,则较为少见。这一注重主观表现的倾向,加上讲究“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的含蓄风格,是长篇叙事诗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抒情短诗在中国尤为兴盛的缘由所在。而西方之所以长篇叙事诗萌发甚早并绵延繁荣,则与西方文艺思想(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开始就强调“文艺是对自然的摹仿”密切相关。受这种文艺思想的主宰,历代西方文艺家多追求细腻、逼真地反映客观世界,以为能够像“镜子”一样再现对象才是文艺的极境。对此,朱光潜曾拿中国“游仙派”诗人描写的仙境,和西方诗人描写的天国相比较,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游仙派”诗人所见到的仙境大半根据道家的传说,他的意象很模糊隐约……,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所以我们在游仙诗中寻不出动作,找不到一个首尾贯穿的故事来,最多只有骑鹤乘云,持芙蓉,吹玉笙,饮琼浆,启玉齿之类做哑戏似的静止的姿势。……西方史诗中的天国却不如此简单,例如荷马所写的巴腊斯仙山,但丁所写的天堂,弥尔顿所写的乐园,都是一座轰轰烈烈的戏台,其中神仙仍然有婚嫁宴享,有刑赏争战,开很长的会议,起很激烈的辩论。他们所居的宫殿园囿,所用的衣服器皿,也件件都写得尽态极妍。一顶冠有几种颜色的宝石,一座楼台有几根楹柱,几扇窗牖,都很明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李白以“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区区十四字就写尽仙境的状况和仙人的姿态,但丁和弥尔顿却要用一部书来写。[①]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比较分析,中国诗和西方诗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很可以从中窥见一斑。由此,朱光潜进而借鉴心理学成果解释说:依瑞士心理学家荣格(Garl Gustav Jung)的研究,不论是个人心理或民族心理的原型,都有“内倾”(introverts)和“外倾”(extroverts)两类。“外倾”者好动,多把心力用到“外物”(objects)上去变化环境,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客观。“内倾”者好静,多把心力注在“自我”(ego)上作深思内省,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主观。中西民族比较,西方民族更属于外倾类,中国民族更属于内倾类;所以大体看,西方文学偏重客观,以史诗悲剧见长,中国文学偏重主观,以抒情短章见胜。
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的后一方面原因,即在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朱光潜指出:长篇史诗不同于短小的抒情诗,抒情诗以一时一地的主观情趣为主,是描写人生的一个片段或一种感情;而史诗却同时从许多角色着眼,须写出整个人生或整个社会,甚至包括全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史诗的作者须有深广的眼界,才能在繁复多变的人生世相中透析出条理线索来;同时又要有较深厚的情感和较长久的“坚持的努力”,才能战胜性情的疏懒和环境的阻碍,创造出完整伟大的作品。深广的观照常有赖于哲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因为中国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哲学,重视世俗人伦的探讨而疏于纯粹“知”的寻求。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更微弱,不少人根本不信奉宗教,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恰恰不外是“怪力乱神”)。这些,再加上中国儒家和道家推崇直观感悟,淡于理智分析的认识方式的影响,中国长篇叙事诗不发达和抒情短诗的兴盛,不是理所当然并势所必然的么?
值得指出的是,朱光潜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篇史诗,可谓确论;但说古希腊文学的早期作品都是长篇叙事诗,似不甚严密。事实上,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早三百年左右,古希腊文学中即出现了相当精采的抒情诗,如萨福(Sappho)和品达(Pindar)两人都是当时写抒情诗的大家,尤其是萨福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第十位诗歌女神”之称。她共留下九卷诗,由于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会认为其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有伤风化,曾作为禁书查毁。尽管她留下来的诗篇不多,但对后代还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古罗马时期朗吉纳斯(Longinus)写的重要文艺批评著作《论崇高》,就引用了她的抒情诗,并认为是诗歌的一个楷模。英国著名诗人拜伦(George G·Byron)在《唐璜》中咏叹希腊光荣历史,一开始就提到“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在近现代欧洲,不少诗人袭用她用过的一种诗歌体裁,称之为“萨福体”。
不过,亚里斯多德在其名著《诗学》中,主要大谈史诗和悲剧,认为它们是文艺的正宗,对于抒情诗只说是“另一种艺术,用语言来模仿,用不入乐的散文或不入乐的韵文,这种艺术至今没有名称”[②]。抒情诗当时连个名称也没有,其在正统文艺家那里不受重视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英国访学时得知,直至本世纪初,西方教授开英诗课时,讲的都是史诗和诗剧,抒情诗一般提都不提。像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这样的大诗人,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并以此闻名遐迩,但他仍立志要写一部伟大史诗,定名为《隐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朽,名垂后世[③]。西方文艺史上重视长篇叙事诗而轻视抒情诗的传统观念之顽固,由此足可见出。就此而言,朱光潜从总体上比较中西诗歌发展的差异时,忽略古希腊抒情诗也并不算什么过失,也许他仅仅是为了论述的简洁明了,有意略而不谈罢。
总之,尽管朱光潜这里的一些看法并非十分精当(如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也不一定非信奉宗教才能获得),但他能在当时自觉地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率先提出“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的问题,并作出比较系统且有相当深度的论述,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二)
中西诗歌的差异,除了在发展轨迹上有侧重抒情和偏向叙事的分别外,还在相同题材的不同表现方式上,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朱光潜不仅从宏观上对中西诗歌发展的不同路径进行了比较,而且从微观上对中西诗歌的情趣差异,做了精微的分析。他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谈中西爱情诗》等文,即从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等方面,发掘了中西诗歌在情趣上的异同之点。这里先评述他从人伦方面考察中西爱情诗的论说。
人类诗歌虽然千差万别,但从题材上看,人伦却是各国诗表现最多的方面。在《谈中西爱情诗》里,朱光潜很独到地指出:
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当然也很多,但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谊在西方诗中几无位置,而在中国诗中则为最常见的母题。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诗人的忠君爱国忧民的部分剔开,他们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他们便不成其为伟大。友朋交谊在中国诗中尤其重要,赠答酬唱之作在许多诗集中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他们的来往唱和的诗有很多的杰作。在西方诗人中像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雪莱与济慈,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以交谊著,而他们的诗集中叙朋友乐趣的诗却不常见。[④]
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他还指出:
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⑤]
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样的差异?或者说,在倾诉男女恋爱情感方面,为什么中国诗远比西方诗逊色呢?在朱光潜看来,这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发展较充分,以至常常掩盖了其他人伦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这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往往大半生的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更兼儒家所宣扬的“礼教”,在男女之间筑了一道很严密的防线,男女恋情多半为社会所不齿,这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的影响,尊敬女子是社会称颂的事,女子的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契合。在中国得之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一般都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男尊女卑”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且许多男子把女人看作一种牵挂或不得不有的一种累赘。女子的最大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一种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和志同道合是十分罕见的事。更何况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多半被社会视为耻事呢!
第三,中西恋爱观也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的口号。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到无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而他们向来为社会所诟病。如果说,在西方诗人那里,恋爱本身即具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面意义;那么,在中国诗人身上,恋爱则多半含有消遣或虚度人生的贬意。正因为中西在社会文化和人情风俗上有这些分别,所以中西诗人表现爱情时大异其趣。
当然,任何概括都有例外。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中国也有大胆表述恋爱的诗,如《诗经·国风》和“汉乐府”里一些出自民间的情诗,情感表达就相当直率和深挚。而西方的爱情诗中,最动人的篇什也有一些是惜别悼亡之作,如拜伦的《当我俩分别时》,是惜别的名篇;华兹华斯被人广泛传诵的六首写露西的诗,是露西去世后的产品等等。细读这些诗,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比描写幸福爱情和婚姻生活的诗,更为感人,更为深沉。这一点在中国也是一样,如李清照与赵明诚,陆游与唐婉,将他们表现爱情欢乐和惜别悼亡之作相比较,前者几乎都是平平之作,而后者则多堪称千古绝唱。之所以如此,大概正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其名著《苦闷的象征》里所说,文艺是内心深处苦闷的宣泄,其苦闷越深刻、越强烈,倾吐出的文艺就越感人。
检索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对中西爱情诗进行专题比较研究,朱光潜是第一人。他不仅可说是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主题研究的拓荒者,而且一开始的起点就相当高,不论是从问题把握的准确度和探讨的深度上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当然一方面得力于他的学术敏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国学”和“西学”都有深厚的功底。
朱光潜是如何突发奇想,对中西爱情诗进行比较研究的?一般说来,一个作家或学者在创作和研究中选择某个题目,并非莫名其妙地空谷来风,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某种机缘的触发和启迪。我以为,朱光潜之所以起意做中西爱情诗比较这题目,最初的灵感可能来源于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本是英国人,原名为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他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过六年文学教授(1896—1902),向日本学生讲解西方文学。他当时有一讲的标题是《英诗中的爱情》(Love in English Poetry)。在这篇讲演中,小泉八云说,日本学生读英国文学越多,对其中爱情作品的数量之大和地位之突出就越会感到诧异。他自己在准备讲稿和选材料时,发现丁尼生、勃朗宁、罗塞蒂、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中,不涉及爱情的诗篇很少。究其原因,乃在于恋爱和婚姻是欧美人生活中一桩十分重要的大事,因此文学作品多谈这件事是自然而又必然的。西方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恋爱和婚姻也一样,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要独立地通过竞争来找到自己的对象。因为恋爱在人们生活中是头等大事,大家都对这问题感兴趣,所以爱情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的永恒的主题[⑥]。朱光潜到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头一年,曾深深沉迷于小泉八云的四大本“文学演讲集”,自称是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最感觉受用”的著作[⑦],并专门写了长文《小泉八云》,向国人介绍其特异的生平和富有魅力的学术成果[⑧]。由此可以想见,朱光潜当时读过《英诗中的爱情》一文当无疑问。他的关于中西爱情诗的比较,最初的念头从中受到启发,也属情理之中的自然事。
(三)
朱光潜还对中西诗歌表现自然方面的异同特点,作了富有开拓意义的比较研究。
从自然方面看,中国和西方一样,诗人对自然的爱好和描绘都比较晚起。最初的诗都偏重表现人事,纵使偶尔涉及自然,兴趣的中心却不在自然本身,而只是拿自然作为人物的背景。如《诗经》中“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只是作为“窕窈淑女,君子好逑”的陪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只是作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陪衬。诗人的兴趣由表现人物扩大到呤咏自然,是诗境的一大解放,不但题材因之丰富,自然诗由此诞生,而且描写人事的诗,也因之得到更为深广的意蕴。所以,自然诗的兴起,是诗歌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朱光潜别具慧眼地指出:“这件大事在中国起于晋宋之交,约当公历纪元后五世纪左右;在西方则起于浪漫运动的初期,在公历纪元后十八世纪左右。所以中国自然诗的发生比西方的要早一千三百年的光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朱光潜说:
中国诗人对于自然的嗜好比西方诗要早一千几百年,究其原因,也和佛教有关系。魏晋的僧侣已有择山水胜境筑寺观的风气,最早见到自然美的是僧侣(中国僧侣对于自然的嗜好或受印度僧侣的影响,印度古婆罗门教徒便有隐居山水胜境的风气,《沙恭达那》剧可以为证)。僧侣首先见到自然美,诗人则从他们的“方外交”学得这种新趣味。“禅趣”中最大的成份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悟,中国诗人所最得力于佛教者就在此一点。[⑨]
这里关于自然诗为什么起于魏晋以后的论述,当然受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里“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影响;但说中国诗人对自然山水的爱好,是从与佛教僧侣的“方外交”中学得的新趣味,则是朱光潜的独到发现,验之史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有趣的是,与中国诗人对自然的兴趣起于外来文化(印度文化)的刺激一样,西方浪漫诗人卢梭、华兹华斯等人提出“返回自然”等口号,也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国等东方文化)的启发密切相关。关于这点,笔者曾作过专门探讨[⑩],此不复赘。
至于中西诗人欣赏自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两者之间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异点”。中国诗人神的观念很淡薄,自然观中虽然偶尔杂道家的神秘色彩,但不甚浓厚。中国人对待自然多取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相悦相安,与自然之间多保持“情趣的默契欣合”的关系。“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诸诗,即是这种关系的表现,也是多数中国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此相异,西方诗人因为有一千余年基督教的滋养,对大自然多抱一种“泛神主义”的态度,将大自然看作神灵的表现,以为它有超越人并时时支配人的力量,常常在其中看出不可思议的妙谛。这种自然崇拜,多半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使诗人往往能从自然中感受到巨大的力量和彻悟到深沉的思想,而中国诗人却很少达到这种境界。[(11)]
关于这点,只要拿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两人的自然诗作一比较,就可见出中西诗人对待自然态度的径庭。请看陶渊明《饮酒》第五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把陶渊明陶醉于自然之中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且意味隽永。但是,尽管他讨厌“车马喧”的“俗情”,喜爱“悠然见南山”的恬静,却对其中的“真意”不求甚解。末句说对自然园林之趣“俗辨已忘言”,实际上不过是个托辞,真实情况是:他压根儿就不想辨。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和华兹华斯及一般西方诗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华兹华斯也讨厌“车马喧”的“俗情”,也喜爱大自然的静谧,但他是一个对大自然怀有宗教情感的崇拜者,时时都想从大自然中寻出不可思议的奥秘和力量。请看他的下面这节诗:
And I have felt
A presence that disturbs me with the joy
Of elevated thoughts;a sence sublime
Of something far more deeply interfused,
Whose dwelling is the light of setting suns,
And the round ocean and the living air,
And the blue sky,and in the mind of man,
A motion and a spirit,that impels
All thinking things,all objects of all thought,
And rolls through all things.[(12)]
严格地讲,我很相信“诗不可翻译”之说。我没有能力也不会翻译诗,这里为表达意思的需要,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诗的神韵无从谈起,最多只能说保留了形骸:
我感到
一种东西让我惊诧,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升华之感
像是融汇万物的魂灵,
来自落日灿烂的余辉,
来自浩瀚的汪洋和清新的空气,
来自碧蓝的天宇和人们的心田,
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它驱动
一切深思的生灵,一切思想的对象,
又穿过一切事物而运行。
这节诗,摘自华兹华斯的名作《丁登寺旁》(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写的是诗人在一个古寺废墟上的沉思感受。非常明显的是,这决不像我们中国的一般山水诗,其所呤咏的也远远超出了山野田园之趣。诗人仿佛要传达一种捉摸不透并难以传达的神秘思想,因而不得不求助于一连串很难翻译的抽象名词和情感形容词(如 a presence,a sense sublime of something far more deeply interfused,a motion and a spirit,all thinking things,all objects of all thourght,and rolls through all things)。诗句选词的独特和句子结构的曲折,这本身就表明诗人企求把难以言说之意说清楚的努力,但我们仍然很难把握它每句诗的确切意思,只可得到这样一个大概的主旨: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魂灵息息相通,融为一体。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兆象》一诗里曾说:“我看一朵最平凡的花都有深刻的思想,深藏在连眼泪都达不到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前西方人对待自然的共同特点,即总希望在自然中寻出什么奥秘来。而中国诗人却只求逍遥于自然之中,只要能在自然之中得到一份慰藉和欢乐就足够了。
依朱光潜的意见,中国诗人在自然中不能像西方诗人那样有深广的沉思和彻悟,似乎是一缺点。他说:
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中国诗在荒瘦的土壤中居然现出奇葩异彩,因然是一种可惊喜的成绩,但比较西方诗,终嫌美中不足。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方诗所能及,但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13)]
其实,在我看来,用诗来作哲学沉思并不一定是好事,它往往会让人感到“味同嚼蜡”,难以卒读。如果谁要探寻大自然的神秘奥义,尽可以用论说文或专著的形式来沉思,而不必用诗来越俎代庖。因为尽管诗歌中可以寓含哲理和宗教情感,但有意用诗来表达对自然的哲学思考和宗教虔诚,毕竟是诗的所短而不是它的所长。即便以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这首名诗来说,其精彩和动人的地方,也不尽在作哲学沉思之处(像上文所引的那样),而主要在表现诗人内心真情和对自然景象的敏锐感受之处。更何况像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及何尔律治《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这样深蕴哲理的长篇自然诗,写得那样精彩在西方也是很难得的情况呢。
另外,朱光潜所说的中国诗不如西方诗“深广远大”,除了指中国诗的内容不够深刻博大外,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中国诗多篇幅短小,不像西方诗多宏篇巨制。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长篇诗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14)]。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诗歌还是要讲究精炼含蓄,写得过长多半吃力不讨好。我在英国访学时,曾与英语系和东亚系的学生随谈,问他们有没有读过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拜伦的《唐璜》、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篇诗,绝大多数都说没读过,说那样的诗太长没时间读,读起来也太沉闷。相反,短小的抒情诗许多人都能背出几首,可见尽管西方具有长篇叙事诗的传统,但真正受人们喜爱的还是抒情短诗。当然,对于那些长篇叙事诗,也有的大学教授从专业研究出发,对它们情有独钟,但广大读者对其多半敬谢不敏。任何文学作品,只有广为流传,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如果只有极少数人阅读,其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之所以在近现代西方越来越衰落,以至今天几乎无人问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失去了读者。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美国诗人兼评论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对长篇诗的独到意见。他在其著名的《诗歌原理》(1850)里反对写长诗,认为只有洗炼的短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长诗”这个词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因为从心理学上来看,诗当中要有激情,要能使人激动,而“激情”和“激动”都是短暂的、难以持久的。他相信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原来决不是现存的长篇形态,而是一系列的短诗,是后人把它们加工拼凑成了长诗。即使像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那样的近代史诗,也只能将其看作一系列小诗的连接,因为其中真正可称得上诗的段落都不长,大量穿插其中的段落都是不能称作诗的平庸文字。所以,爱伦·坡说:“长诗是不存在的,如果长诗过去曾经盛行过(他很怀疑),那么它今后再也不会流行了”。[(15)]
爱伦·坡的观点当然也并不完善,有些看法明显存有商榷的余地(如他从激情难以持久说明“长诗”是个矛盾的词语等),但他的总的意见我以为是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近一两百年来,世界文学的发展实际,正像他所说的那样,长诗不再流行了,而短诗却在持续发展。本世纪初,不少英美诗人曾将中国的抒情短诗译成英文,如爱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汉诗译卷》(Cathay)、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的《松花诗笺》(Fir-Flower Tablets)等,在英美诗坛引起很大轰动。英美诗人竞相向中国诗学习,以至掀起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意象派运动”。意象派作家所写的诗,都比较凝炼含蓄且形象鲜明,给英美诗歌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可谓西方诗坛的一次革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许多营养,但对西方的长篇史诗,虽然早已有多部作品翻译介绍过来,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也没有人身体力行,尝试创作。与此相反,倒是西方诗人对中国的短小抒情诗特别青睐,并在英美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诗的热潮。这现象或许能说明:就诗这种文学体裁言,简洁隽永当是它追求的胜境,而冗长繁复则是它过重的负担。
注释:
①《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1934年2月);又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355页。
②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6页。
③华兹华斯的这部史诗最终没有完成,只出版其中第一部《序曲》。
④《谈中西爱情诗》,《华北日报》1948年8月8日;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83页。
⑤《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76页。
⑥小泉八云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由日本学生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他去世后,哥仑布大学教授阿斯肯(Prof.Erskine)把日本学生的笔记搜集起来,整理出四巨册付印。第一、二册名为《文学导解》(Interpretaion of Literature)、第三册名为《诗歌鉴赏》(Appreciations of Poetry)、第四册名为《生命与文学》(Life and Literature)。《英诗中的爱情》一篇收入第三册《文学鉴赏》之中。
⑦参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66页。
⑧参见《小泉八云》,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8号(1926年9月);收编《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53—467页。
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85页。
⑩参见拙著《文学横向发展论》第三章第二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93—112页;另见拙文《欧洲浪漫派与东方文学》,《学术界》1987年第3期。
(11)参见《文艺心理学》第九章“自然美和自然丑”,《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27页。
(12)《哈伯世界诗选》(The Harper Anthology of Poetry),纽约 Harper & Row 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50页。
(13)《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79页。
(14)《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352页。
(15)参见罗伯特·斯皮洛(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第4章,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5年出版。
标签:朱光潜论文; 诗歌论文; 华兹华斯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爱情诗论文; 失乐园论文; 复乐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