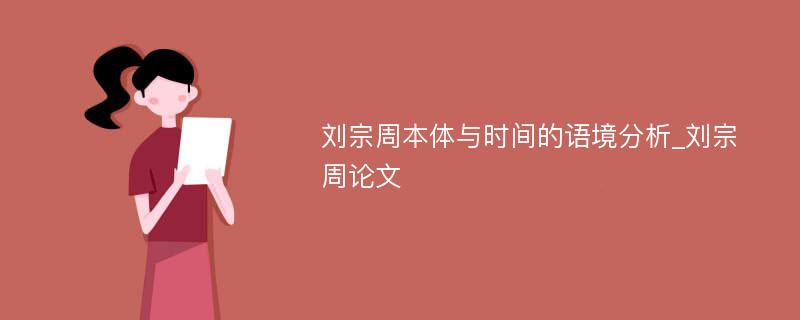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本体论文,工夫论文,刘宗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6)04—0018—06
儒家哲学,其实质是以成就理想人格为宗旨的道德实践哲学。所以在儒学传统中生活的古典中国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所谓“修身”即在个体人格中实现内圣外王理念的道德践履工夫。在儒家哲学系统中,形上学和心性论中的思辨成分不是出于纯粹的“爱智”,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价值的关怀。所以道德是儒家的根基,而形上学、心性论是儒家成德立人道德实践的注脚。理学家常将道德实践称为“工夫”。本文从本体与工夫这一特定视域疏解晚明重要心学家蕺山刘宗周证人之学的工夫理论。
一、本体与工夫的内在统一性
在理学中,本体与工夫是工夫论中的一对轴心范畴。本体指人生而具有的先验的道德理性,简称为义理之性。此“性”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主体的形上根据。但是按照理学家的理解,性体虽为人人所普遍具有,但此性体并非人人都能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和后天经验意识中得到圆满的呈现。只有通过一定的精神修养,此先验的理性本体才能圆满呈现于人的现实生命活动和后天经验意识中,从而达到道德理性之自觉。先验道德理性在现实生命活动和后天经验意识中呈现的过程,理学家称为“复性”。以“复性”为宗旨的精神修养过程,即理学家所乐道的“工夫”。
蕺山关于本体与工夫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本体是工夫的主脑,或曰以本体提领工夫;工夫是本体的落实,或曰于工夫中见本体。本体与工夫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故曰即工夫即本体。其言云:
本体只是这些子,工夫只是这些子。并这些子仍不得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即无本体工夫可知,则亦无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1](《学言上》,《全书》卷十)
一诚贯所性之全,而工夫则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诚身”,曰?“明善”,《大学》曰“诚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诚,明之所以诚之也。致知之知不离此意,致之所以诚之也。本体工夫委是打合。[1](《学言下》,《全书》卷十一)
这些话在《学言》中还可找到不少。都说明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性。依蕺山,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所以正心、诚意、致知与格物皆为一路工夫。正、诚、致、格是工夫,心、意、知、物是本体。工夫以本体为提领,本体以工夫为落实。正、诚、致、格不在心、意、知、物之外,而恰是心自正,意自诚,知自致,物自格而已。这就叫做“工夫结在主意中”。
本体所以能为工夫所落实,就是因为工夫是本体自身的展开。本体是自在的工夫,工夫是自为之本体,本体向工夫的落实恰恰是本体由自在到自为的展开过程。这一辩证关系在下面一段话中指点甚明。蕺山云:
良知一点,本自炯炯,而乘于物感,不能不恣为情识。合于义理,不得不胶为意见。情识意见纷纷用事,而良知隐覆于其中,如皎日之下有重云然,然其为良知自若也。覆以情识,即就情识处一提便醒;覆以意见,即就意见处一提便醒。便醒处仍是良知之能事,更无提醒此良知者。[1](《学言上》,《全书》卷十)
此处“良知”即本体。当良知受到乘于物感而生的情识和意见的隐覆障蔽时,良知“一提便醒”,将情识意见顿扫,而良知之灵明觉知性光毕露。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提便醒”不是良知之外的另一个心对良知的提醒,实是良知之自提自醒。如要说“提醒”是工夫,良知是本体,此“提醒”之工夫恰恰是良知本体的自我呈现的方式。可见,在蕺山那里,本体是即自为又自在,即存主即发用的动态的精神实体,其自身便有不容已止的生意。工夫虽有后天人为培植、保任、护养的因素,但工夫发动的最初动机,仍是本体自身的生命意力。故其言:“诚无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系乎人。此中原不动些子,何为之有?《章句》‘实用其力’,不知如何叫做实用其力。”[1](《学言下》,《全书》卷十二) 可见,诚意不过是让善良意志自作主宰而已。蕺山又云:
朱子云略绰提撕,言用力之不多也。良知一点炯炯不昧,本自提撕,何用着力?才著力时便有眼中金玉屑之病在。孟子谓之助长。然不著力时,又一味放倒,凭地昏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谓勿忘勿助之间。[1](《学言上》, 《全书》卷十)
“良知”本自知善知恶,好善恶恶,良知本自能醒能照。道德修养之工夫不过是对良知本体略加提撕保任而已。如无视良知本体之自提自醒,一味用外力致之,便属助长。
二、以本体提领工夫
蕺山认为,既然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所以当以本体提领工夫,不然工夫便是没有主脑、没有定向的工夫,此种无本体之工夫便是“支离”或盲修。基于这种理解,蕺山经常强调学问工夫不能脱离本体。他十分推崇北宋程颢的《识仁篇》,认为:“程子首言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1](《圣学宗要》,《全书》卷五) 朱熹曾认为《识仁篇》是地位高者之事,蕺山不以为然,说:“先儒以为地位高者之事,非浅学可几,学者只合说克己复礼为仁。周海门先生深不然之,以为不识仁而能复礼者无有是处。极为有见。”[1](《圣学宗要》,《全书》卷五) 蕺山对泰州学派的海门之学并不完全认同,因为周海门主张一悟本体便是工夫。在蕺山看来这容易沦于“有上截无下截”之狂妄浮夸,而此处以周海门以“仁”统“礼”的观念为有见,实是因为与蕺山工夫必须吃紧本体用力的见解有契合处。
关于工夫必须吃紧本体用力的思想,在蕺山作于五十五岁的《气质说》中陈述甚明。蕺山云:
圣贤教人,只指点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观《中庸》一书可见。盖提起上截则其下者不劳而自理,才说下截事,如堂下人断曲直,莫适为主,谁其信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也。人生而有形骸,便有此气质。就中一点真性命是形而上者。虽形上不离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块。学者开口变化气质,却从何处讨主脑来?《通书》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中”便是变化气质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却又无可著力处。从无可著力处用得工夫来,正是性体流露时。此时刚柔善恶果立在何处?少间便是个中节之和。这方是变化气质工夫。若已落在刚柔善恶上,欲自刚而克柔,自柔而克刚,自恶而之于善,已善而终不之于恶,便落堂下人伎俩矣。[1](《气质说》,《全书》卷八)
这里蕺山讲圣贤教人“只指点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是就《中庸》言性体之客观超越之逻辑向度说。它并不是说“上截事”(本体)完全可以离开“下截”(工夫),而是说要以上达本体来统领下学工夫,从而凸现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具体地说,要变化气质,不能仅仅在气质上打转转而流于刚恪把捉之死工夫,而当以透悟本体来提领工夫,此即“从无可著力处用得工夫来”,无可著力处即“超越在天、于穆不已”之性天本体。性体为形上之道,即莫见莫闻无可用力处。但性体并非与人的心体完全隔膜的枯槁死板之抽象本质,它内在于人心中,而成为心之精神活动的善良意志。当人的经验意识活动时,道德意志当机呈现,恰是性体流露处。此时见几而作,守定意志本体,不使喜怒哀乐泛滥走作,过与不及,如此修养,久之便能变化气质。在意根本体上用工夫,便是以本体提领工夫。蕺山早年曾批评:“象山、阳明授受终是有上截无下截,其旨险痛绝人”[2](《与陆以建二》.《遗编》卷四)。一是蕺山那时36岁,认定陆王心学直信本心以证圣,而缺乏工夫之指点,其为学宗旨过于高危;二是早年蕺山在为学路径上宗信程朱,当时尚不悟,倘若不使本心豁省,先识个大本所在,则工夫由于缺乏本体之提领不过是死工夫而已。中年开悟慎独之学,所以反对专就气质(刚柔善恶)而言变化气质的“堂下人伎俩”,而强调由上截统摄下截,以本体提领工夫之重要。
另据《年谱》崇祯十二年条记载,此年九月武进大理寺丞张玮谒蕺山问学。张云:“读先生所著《人谱》而知学者得力莫过‘损’、‘益’二卦。惩忿窒欲,克己也;迁善改过,进道也。固有终身用之不尽者。”蕺山回答说:“不然。要识得乾元,乾知大始,惩窒迁改之纲领也。得此纲领则工夫入粗入细皆为有益。不然,即少有得力,总入人为凑泊,于身心了无干涉,几何而达本源之地乎?”[1][3]( 《年谱下》,《全书》卷四十) 同年在答叶润山的信中也说:“等是惩忿窒欲耳,常人有常人之惩窒,学人有学人之惩窒,圣人又有圣人之惩窒,不特取效有难易之分,亦其下手有精粗之分。仆意读《易》,须以乾道为纲领。乾知大始,便是惩窒工夫纲领。处得此纲领,则入细入粗把柄在手矣。”[1](《答叶润山二》.《全书》卷十九) 这两条材料均说明须吃紧本体来做工夫,吃紧本体做工夫即以本体提领工夫。蕺山以“乾元”为工夫之大纲,乾元即太极,即性天之理,此理存在主宰于心即意根独体。为学证人之工夫当从深根宁极处下手,故曰“深根宁极之后正一点灵明葆任得地处”[1](《学言中》.《全书》卷十一)。不识道德本体而盲目做惩忿窒欲之工夫,此工夫不论是粗是精,均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此用功,如何能达到内圣人格之自觉自证。诚如蕺山在《学言中》所云:
独知之知即致知之知,即本源即末流也。独知之知即知止之知,即本体即工夫也。
《大学》言至善,《中庸》言至德、至道、至圣、至诚及天载之至,皆指出独中消息。《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乎此者谓之到家汉。[1](《学言中》.《全书》卷十一)
只有在本体上用工夫,或以本体提领工夫,才能知止,知至,知本,才能对至善之道德本体有所自觉。道德本体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归属,明乎此,人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故工夫以本体为提领。
关于认定本体做工夫之理,蕺山在《答祁生文载》的信中再次点出。蕺山云:
所云“工夫本体只是一个,做工夫处即本体”,良是良是。即如是说,便须认定本体做工夫,便不得离却本体一步做工夫。而今工夫不得力,恐是离却本体的工夫。本体正当处只是个天理,工夫正当处只是存天理。若已存之自我,则天理之外原无人欲,何故又有天理人欲夹杂不能自断之疑?此知平日工夫未必本体也。[1](《全书》卷十九)
蕺山并不否认做工夫处即本体,并不反对本体须在工夫中落实。只是强调须认定本体做工夫,性天之理即是心之本体,只有以性天之理贞定人心,使心灵深处妄机不发,此处一真而无所不真,此处一诚而无所不明。只有洞彻了理性本体并认定本体做工夫,本体才能在工夫中落实和展开。故其言:“《中庸》是有源头学问。说本体,先说个天命之性,识得天命之性,则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1](《学言上》.《全书》卷十)
三、于工夫中见本体
上面从以本体提领工夫的一面论述了蕺山关于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思想,下面继而从另一方面,即从在工夫中见本体,由下学而上达这逻辑向度解读蕺山即工夫即本体的思想。
所谓于工夫中见本体,或者说本体藉工夫而落实,不是说本体在人之外,是人主观设定的一个“可能的”或“当然的”理念,它须由一种外在的工夫而变为现实。而是说,本体白天而言,它是万物之必然;自人而言,则是人性之本然。理性本体上与天命之必然相通,故其超越而至尊;理性本体又内在于人,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义理之性,故其内在而至善。不过,此既超越而又内在的理性本体若无工夫之实践实证,它便只能自在地、抽象地存在于人的主体心灵之中,而不能具体化为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理性主宰。只有通过某种心性修养之工夫,使先验的道德理性本体呈现于人的后天经验意识中,自在的、抽象的理性本体才能具体化,肉身化,变为人的自觉的能动的人格德性。按照蕺山和不少理学家的理解,虽然天理人人自足,但不加印证,理性之光终难显发,虽然道德本心人人皆具,如无精一之工夫保护扶持,终将为随感而生的欲念情识所遮蔽尘埋。所以,蕺山在强调吃紧本体用工夫,以本体提领工夫的同时,更加强调于工夫中见本体。
从总体上说,强调于工夫中见本体,更代表蕺山证人之学工夫论之特色。与阳明学相比,蕺山之学术性格的特色是“归显于密”,密就密在工夫之严毅无漏上。关于这一点,其及门高足黄宗羲言之甚明。他在《子刘子行状》中说:“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亦无些子可指,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1](《全书》卷三十九) 可见,无论早年、中年和晚年,蕺山始终不放松工夫之讲求,所以能在晚年达到工夫与本体圆融无碍之化境。“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足以见到蕺山治学精神和为人之道的良工苦心。
蕺山早年师事许敬庵(浮远),敬庵之学近朱子,注重工夫次第。在敬庵和东林人士的影响下,蕺山在为学之方上主静敬,重存养,故不满于陆王之学。万历四十一年,蕺山36岁,在与陆以建的论学书中明显流露了对陆王之学不重工夫但求顿悟之不满及对阳明后学之担忧。蕺山认为,陆王之学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治、省察边事,因而“终是有上截,无下截”,及其发展,致使晚明士心浮荡,圣学几成绝德。蕺山云:
今世俗之弊正在言复不言克,言藏密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慎独,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不免离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扫除一切为学,以不立文字,当下即是性宗,何怪异学之纷纷也。[1](《与以建二》.《全书》卷十九)
蕺山对“世俗之弊”的指责,实非虚说,因为王门后学如龙溪和泰州之学,往往把本体看得太现成,把工夫看得太简易轻忽。如龙溪主顿悟,似乎一悟而无余事。王艮常以当下即是妙道,“满街皆是圣人”为口谈。这是蕺山所不能不反对的。为扭转王门末流“不喜言工夫边事”,悬空悟个本体的流弊,蕺山主张下学而上达,即通过工夫之实践而上达本体之彻悟。故其言:“道形而上者,虽上而不离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学而上达。……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惧之功焉,在虞书所谓精一,在孔门所谓克己,在《易》所谓洗心,在《大》、《中》所谓慎独,一也。”[1](《与以建二》.《全书》卷十九) 此时蕺山学路尚未成熟,但执定工夫上用力的方向一生未变。
万历四十五年,蕺山40岁著《论语学案》。《年谱》于该条下注云:“按先生壮年学力不可尽考。读《论语学案》而知当时进修之敦笃,居身之严谨。有宁卑毋高,宁峻毋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学法门。人第见晚年德器和粹,以为先生之学得力在涵养,而孰知植基于艰苦刻厉也哉。”[1][3](《年谱》上.《全书》卷四十) 在《论语学案》中,蕺山反复强调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之理,提倡修身有恒,启悟于渐。他说:
圣人之学因有本而以渐达也。惟有本,故渐达。“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是也。夫有恒,其本也。有恒者,常心也。常守其作圣之心而不二,则渐进于善人矣,渐进于君子矣,渐进于圣人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一路浮夸,欲之蹬善人、圣人之地,以为学主顿法,而不知适以自贼其本心之德矣!故曰:“难乎有恒矣。”然则凡顿学者皆伪学也。[1](《论语学案二》.《全书》卷二十九)
可见此时蕺山学主平实渐修,认为君子、圣人不可一蹴而就,要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常守其作圣之心而不二,久之则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圣人。由于强调于工夫中见本体,故以顿悟之学为“伪学”。
蕺山50岁(即天启七年)时编《皇明道统录》,由于遍读阳明之书,对良知之教有了更深切的理解,遂尊信阳明之说。但即使在此时,蕺山对阳明学也是信中有疑。他一方面认为阳明“良知即天理”之说对于克服后儒之支离,启发人心之本善有“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之圣功,另一方面对阳明之学在教法上往往将“向上一机”轻于指点,重本体之悟而轻忽渐修工夫之弊漏心存疑虑。蕺山认为,阳明将良知本体看得过于活泼灵应,若无真实工夫之贞定,难免会走作变形,或参以情识,或荡以玄虚。为弥补阳明学工夫论之不足,蕺山中年专提慎独工夫。崇祯二年,蕺山著《大学古记约义》,发《大学》之旨而明慎独之要。他说: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情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在虞廷为允执厥中,在禹为克艰,在汤为圣敬日跻,在文王为小心翼翼,至孔门始单提直指,以为学的,其见于《论》、《孟》,则曰非礼勿视听言动,曰见宾承祭,曰求放心,皆此意也。[1](《大学古记约义》.《全书》卷三十八)
在此以慎独工夫统领圣门一切工夫,并言“慎独之外别无学”,足见工夫之重要。在蕺山看来,《大学》明德至善之本体要籍慎独之工夫而落实。独体即在执中、克艰、诚敬、四勿、求放心等慎独工夫中而呈现。
四、晚年本体与工夫之争
崇祯四年,蕺山54岁,是年三月三日率缙绅学士200余人于陶石篑先生祠集会,成立证人学社,以阳明良知教为宗旨,揭明人心之本善,故人人皆可成圣贤,庶几拔去自暴自弃之病根。同主事者为石篑之弟陶石梁。石梁与蕺山在为学工夫上意见相左,遂有二人关于本体与工夫之争。对此《年谱》记之甚详:
越中自阳明先生倡学,后其门人最著者为王龙溪,由龙溪而传及周海门,海门同时为陶石篑,俱本良知为宗而递演递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尝从事于斯而有得,是时会讲仍揭良知以为指归。每令学者识认本体,曰: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恁工夫?先生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诸生王朝式、秦弘佑、钱永锡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先生间尝过从。一日座中举修悟异同,复理前说以质。弘佑曰:陶先生言识认本体,识认即工夫,恶得以专谈本体少之?先生曰:识认终属想像边事,即偶有所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且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凑泊,无乃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乎?[1][3](《年谱》上. 《全书》卷四十)
蕺山与石梁之争,实是工夫论上的顿渐之争。石梁认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属于顿悟一路工夫。蕺山也不否认“识认本体”之必要,不识本体则工夫便无主脑,更向何处用工夫?但蕺山认为,即识本体之后,更应将此本体向工夫中落实,工夫越是精慎缜密,则本体之呈现越是圆满如量,昭荧不昧。若将工夫仅仅局限于“识认本体”一隅,此种“识认终属想像边事”,岂可据之以为“了彻”本体?只有识得本体后继之将本体向日用常行中落实,才能使自在的、抽象的先验本体在人的后天经验意识和道德实践中如量呈现,从而化为人的自觉自为的人格德行。
蕺山与石梁的本体与工夫之争,不在于是否应该识认本体,而在于如何识认本体。石梁以“识认本体”为彻上彻下工夫,既识之后不须再做工夫;蕺山主张以识认本体为主脑,既识本体之后仍须将本体向日用常行的道德实践中去落实。以本体为主脑提领工夫,并继而在工夫中呈现本体。故其言:
学者但就本心明处一决,决定如此,不如彼,便时时有迁改工夫可做,更须小心求理,使本心愈明,则查简愈细。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见得如此如此,而即以为了手地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1](《人谱续篇二.证人要旨》.《全书》卷一)
在工夫中落实本体,就是要在日用常行中时时慎独,处处诚意,动察静存,迁善改过,使视听言动无不循规合矩,喜怒哀乐无不中节而和。如此修身养性,久之必达圣域。
总之,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的轻浮狂放之风[4](《东林学案》.《明儒学案》卷六十),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在给学人的信中蕺山指出: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著不得一语。才著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1](《答履思二》.《全书》卷十九)
这里蕺山并不否认本体之存在,只是说本体不能离开工夫而存在,当就工夫中体认本体。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本体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理性。后来黄宗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正是从蕺山“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的思想演变而来。
收稿日期:2006—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