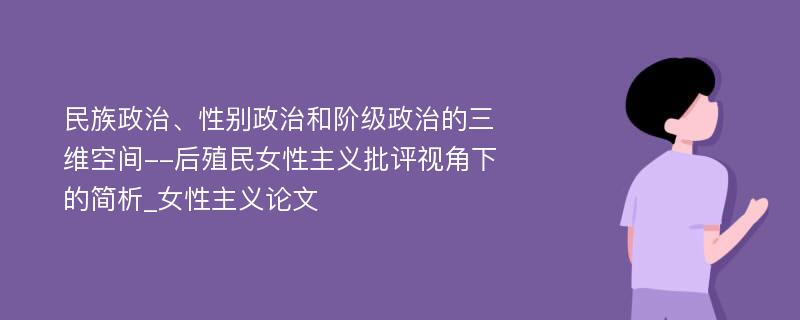
族群政治、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三维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族群论文,视角论文,阶级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3-0110-06
后殖民主义是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声浪鼎沸中登场的,以1978年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出版作为先声,一群兼具“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身份的知识分子,模仿了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策略和阐释模式,借用米切尔·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揭露西方对东方知识霸权的权力生产机制和文化殖民关系,力图消解西方在世界的文化中心地位。处于西方文化边缘的后殖民主义与同是“少数话语”的女性主义逐渐结合,被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以其处于双重边缘的强烈批判性,直指西方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族群政治、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因而在同一历史时空纠葛在一起,开启了一个极富启迪的三维批评空间。
一、揭露西方知识生产的机制
后殖民女性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但“第三世界”已不仅仅是曾受欧洲殖民过的地缘政治上的“东方”,而且引申为“包括剥削、压迫的民族、种族和人群,也包括在发达国家中受压迫受剥削的各种人群”的政治图象中权力关系范畴的“东方”。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反对的是霸权关系,因而既包括具有“东方”文化身份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西方国家内部处于边缘抗争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印度裔美国学者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和莫汉蒂,美国黑人学者贝尔·胡克斯和华裔美国学者周蕾等,她们从不同的维度剖开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生产的秘密机制和霸权关系的生产和复制过程,使人们看到了“东方”如何在西方镜像中变形和扭曲。
(一)西方知识建构和编码的机制。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判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4)由此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的一套知识论述方式,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东方被建构出“女性的”、“专制的”、“落后的”、“妻妾的”文化象征,东方自身对自身的知识被贬为“幼稚的知识”,处于“等级之低层的知识”。西方女性主义是居于边缘反对西方的知识体系的,但它没能摆脱帝国主义霸权地位的痕迹,在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描述中不断复制着帝国主义对东方的知识生产的霸权。它按照自身的知识生产谱系来建构第三世界的妇女形象,并把它编码为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系统的知识表述,进而通过文化优势造成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规约和知识内化,抹杀第三世界妇女认识自身、表达自身的能力。莫汉蒂指出:“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物质生活和历史的异质性方面漫无边际地殖民化,从而产生/描绘出一种混合体——单独的‘第三世界妇女’,一种似乎是任意构成、但仍然携带着西方人本主义论述的权威性的署名。”[2](P208)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狭隘的知识暴力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不完善的讽喻,象征着一种知识可能性的普遍暴力。”[3](P125)西方女性主义在建构出她们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和话语时,也在复制着帝国主义新的文化霸权。
(二)“他者”——东方在西方镜像的投射。西方将东方文化形象在西方的镜像中朦胧化、变形化,居高临下把东方文化的异质性解读为“神秘、花哨、野蛮、愚昧、落后、肮脏、惫懒、迷信”的畸变形象,这样西方在镜像中凝视着沉默的异质的“他者”,这是一种文化优越性的凝视,凝视也就是一种无声的话语和压抑,是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西方在对东方虚假的镜像凝视中恍若看到了在历史延续阶段上“异时性”的自身形象,因而得到了历史优越感的满足。赛义德指出:“东方也有助于欧洲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欧洲文化是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身身份的。”[1](P5)莫汉蒂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把第三世界妇女均匀同质化,设想出妇女的普遍形象是“愚昧无知的、贫穷、没有受教育、受传统的束缚、被禁锢在家里、受欺骗的”,诸如“戴面纱的妇女、能干的母亲、贞洁的处女、温顺的妻子”,“这与含蓄地把自己描绘成受教育的、现代的、对自己身体和性欲有控制权和能自由做出决定的西方妇女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P211)。西方女性主义在知识的再生产中再生产出“第三世界普遍妇女”的形象,这样“使殖民论述运转起来,这种论述在行使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权力,解释并维护存在于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联系”[2](P235)。
二、破解统一的分析范畴——“妇女”
后殖民女性主义反对西方女性主义不加历史分析地把“妇女”作为统一的分析范畴。在第一个维度上,西方女性主义创设出统一的“妇女”范畴,把父权制设想成惟一的妇女共同受压迫的根源,创设出一种基于妇女共同受压迫上的普遍的超阶级、种族和民族的虚假的“姐妹情”,而没有看到父权制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权力关系勾结在一起的。在第二个维度上,西方女性主义又把“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个均质化的分析范畴,以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斗争模式作为标准,忽视第三世界妇女特殊的历史经验和斗争历史,把“第三世界妇女”同一地制造成为“沉默的被言说的他者”和“纯粹的受害者”,第三世界妇女因而被对象化和客体化,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遭到抹杀。
(一)打破“妇女共同体”的神话。西方女性主义从作为中产阶级白人的阶级地位和历史经验出发,把父权制造成的性别压迫普遍化,并把其提升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惟一的分析因素,因此制造出妇女共同受压迫的“姐妹情”,旨在凝聚各阶层各种族各国家的妇女一起反对父权制。而后殖民女性主义反对把性别作为惟一分析因素的“铁板一块”的“妇女共同体”的神话,认为第三世界妇女所受的剥削、歧视和压迫不仅有性别压迫,还有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包括来自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压迫,超越阶级、种族和民族的“姐妹情”是虚假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查拉·提·墨罕提(ChandraT.Mchanty)呐喊道:“在姐妹情之外,仍然存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4](P35)父权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压迫是通过变形的方式勾结、渗透在一起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第三世界妇女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西方女性主义忽视了她们在特殊的压迫和政治选择层面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美国国内的黑人女性主义也批判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阶级的、种族的歧视和偏见,认为“各个阶级的黑人妇女,土著印地安妇女和亚裔妇女,包括劳动妇女,无法称白人妇女运动的先锋——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自己的姐妹”[4](P43)。建构超阶级、超种族和超民族的“妇女共同体”在理论上是虚幻的,在政治斗争实践中,也起到了加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效果;预设男人/女人在自然性别上的对立,分化了共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男人和女人联合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的可能性。因而,妇女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和反对其他形式的压迫结合起来,如果“种族不解放,就没有妇女本身的解放”。
(二)第三世界妇女的失语和主体缺失。西方女性主义不仅把“妇女”作为与男人对立的均质的分析范畴,在第二个维度上又制造出与西方妇女相对立的普遍的均质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单一范畴。作为“群体或范畴”的第三世界妇女便同时被解释为“传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愚昧无知的”、“落后的”。因而她们的历史经验和斗争经历都是无足轻重的、次要的,无需言说的,这样第三世界妇女受到了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掩盖,她们成了丧失自身语言和行为的空洞的“所指”。在话语生产层面上,作为属下的妇女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在历史创造层面上,妇女作为历史过程真实主体的主体性受到了抹杀,成为空洞无力的客体和对象。莫汉蒂揭示道:“把妇女是同类范畴的概念应用于第三世界妇女就是把各种不同妇女群体同时局限在社会阶级和种族框架内加以殖民化,并且利用这种局限性;这样最终剥夺了她们的历史和政治作用。”[2](P233)第三世界妇女被塑造成纯粹受男性控制的消极的缺乏反抗的牺牲品、性对象或“落后”社会中最无知、最落后的成员,她们独特的政治斗争经验、创造力和历史价值被涂抹掉了;而西方女权主义把自己自我描绘成“现代的”、“进步的”、“聪明的”、“理智的”,把自己的模式塑造成全世界妇女解放的标准和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女性主义是如何变成违背历史的真正‘主体’的。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妇女从来没有超越其‘客体’地位的普遍性。”[2](P233)
三、质疑普遍化的方法论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些错误。西方女性主义从她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仅凭一些未经分析、未加证实的先验理论前提和概念来加以普遍化推演,而忽视将第三世界妇女的性别压迫问题放到国家、种族、地理区域、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各种背景因素和社会关系中去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和考察,因而在作为真实历史主体的第三世界妇女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描述的各种“话语场”中的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出现了省略”。莫汉蒂指出:“像生育、性别分工、家庭、婚姻、家务、家长制等概念经常在没有说明特定和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使用。女性主义利用这些概念来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提供说明,显然是设想这些概念有普遍的适用性。”[2](P227)
(一)归纳法的非历史性,即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来归纳复杂的社会现象。如用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埃及的妇女戴面纱的数量推论出对妇女性别控制的严重性。但是戴面纱的妇女数量能够必然推论出妇女的受压迫程度吗?1978年伊朗革命期间,中产阶级妇女戴面纱是为了表明对戴面纱的工人阶级姐妹的支持,所反抗的正是伊朗国王和西方的文化殖民,这正表明了妇女的斗争性和主体性。而另一个场合则是强制性的伊斯兰法规规定,所有的伊朗妇女必须戴面纱。在这两个场合中妇女戴面纱的政治含义是不一样的,不能剥离历史条件单独去推论第三世界妇女的受压迫程度。
(二)概念推演的不适应症,即把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概念普遍地推论到第三世界妇女身上。如家务概念,美国女权主义提出“妇女主持家务是伟大独立和女性主义进步的标志”,但是把这一概念扩展到拉丁美洲、美国黑人妇女和墨西哥妇女中,则看到妇女主持家务的增多集中在最贫穷的阶层中间,她们更加在经济上贫困化。再如工作概念,西方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是走出家门工作,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但“能够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指出,这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指的是能够从事有意义和创造性的工作,在种族主义猖獗的美国,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才可能找到这类工作。事实是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和少数种族妇女,为了生存,早就必须在外工作了。她们干的工作是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既不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不是解放,她们在这些工作中受到资本家的非人化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5](P112-125)
四、批判政治关系中的压迫
在“西方”对“东方”的论述中,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现实在话语层面上的折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旧有殖民地的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军事压迫的殖民统治体系土崩瓦解了,但以隐蔽的知识暴力为理论基础、以跨国公司的剥削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却在向第三世界渗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勾结起来,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在政治上遭受“互相连锁的”种族压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经济上表现出日益贫困化和边缘化。
(一)揭示殖民话语的知识霸权性质。后殖民知识分子借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揭示西方知识界的殖民话语如何为新殖民主义提供了阐释和论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对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的非强制性控制,促使被压迫阶级自觉认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赛义德把葛兰西所指的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格局,他指出:“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P10)米切尔·福柯曾指出,知识、话语与权力机制是互相关联的,殖民者已拥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操纵话语,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而他们拥有的知识反过来论证殖民者的权力,又使这种权力合法化。殖民话语的隐蔽暴力和话语的再生产不仅使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的文化霸权,压制第三世界的话语,最为可怕的是造成第三世界的内心自觉认同,丧失自身的文化身份,泯灭反抗意识,使殖民关系再生产下去。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话语表述,并通过文化优势造成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内化、自我建构和自我规范,实质上也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在第三世界妇女身上的复制和再生产。周蕾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者应该首先认识和批评自身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和理论。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强加在第三世界妇女身上。[4](P34)
(二)揭露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勾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许多偏远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大工场和消费市场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经济剥削中,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妇女处于多重压迫系统的最低层,遭受到更强的连锁形式互相强化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迪·哈特曼(Heidi I.Hartmann)曾指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两种连锁制度,父权制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2](P49)在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新殖民压迫、跨国公司中的阶级压迫和父权制的性别压迫勾结在一起,加剧了妇女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状况。如国际劳动分工和性别分工的普遍存在。玛里·埃·萨万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大部分是年轻的、贫困的妇女。[4](P30)在跨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如缝纫和组装等,妇女处于技术低层的工作,报酬低,是流动工、季节工和劳动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求被雇佣的人数上下波动,因此“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和基本的特性”[2](P92)。妇女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又加剧了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强化了父权制,而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又会损害男性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又加剧了阶级压迫和种族剥削。
五、结论
后殖民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直接指向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启了阶级、种族、性别的三维政治空间,拓展了西方女性主义只关注性别压迫的改良主义视域,力图颠覆西方和东方在世界权力关系结构的“中心—边缘”格局,从边缘挑战了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开启了一个极富启迪的批判空间。它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女性主义内部的异质性和平等性。女性主义本身是对现存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的反抗。各个国家、民族、种族在世界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境遇,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处于不同的父权结构、阶级结构和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的空间上,多元化、流动化、异质性应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女性主义应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阶级、地区、种族的妇女表达自己利益的五彩缤纷的舞台。应打破二元论和等级制,尊重不同种族、民族、阶级、宗教信仰的妇女从物质关系出发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文化差异,在差异中寻找联合共同反抗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第二,反对性别压迫必须和消除一切压迫关系的斗争结合起来。性别压迫是处在复杂的压迫体系中的一种压迫形式,性别压迫和其他形式的压迫是纠合在一起的,殖民压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连锁的”“互相强化”的。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压迫、跨国公司的经济剥削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结合起来。消除两性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必须在颠覆所有的压迫权力关系结构时才能实现。
但后殖民女权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令人困惑之处。第一,文化身份问题。后殖民知识分子大都作为在西方生活的有着东方血统的“东方人”,文化身份经历了变形,知识生产的系谱是西方的,而且她们(他们)往往来自本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她们(他们)能否代表和再现第三世界下层人民包括下层妇女的经验?第二,批判力量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居于边缘的边缘,指向西方文化中心,但当它在西方的话语圈居于高位并向学术中心移动后,其批判力量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形成新的西方知识对东方造成新的文化殖民?第三,实践力量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种族压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纠合在一起的,这在理论是开拓的,但是如果妇女和男人联合反对殖民主义和阶级压迫,父权制就能自然消失吗?在实践中妇女和男人怎样来反对殖民主义、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呢?这些都是后殖民女性主义在理论发展中必须回应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4-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