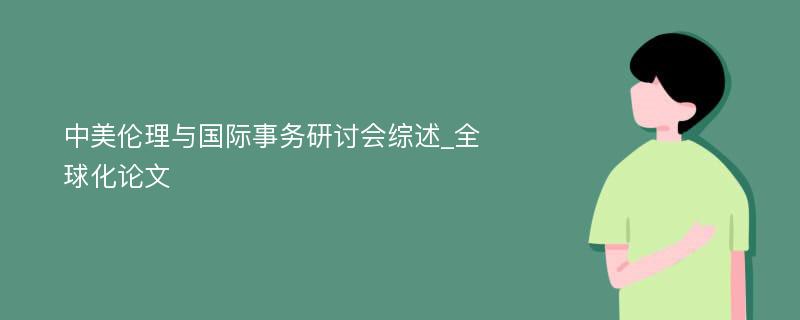
中美“伦理与国际事务”学术讨论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述评论文,伦理论文,国际事务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关于国际政治的伦理思考和判断几乎始终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主题。它赋予各种类型或流派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甚至主张非道德立场的现实主义理论)深切的人文关怀意义和显著的哲学思辨色彩。不仅如此,由于当今许多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世界政治“法制化”与霸权,“民主和平”,全球性军事安全、种族或民族冲突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关于国际政治的伦理讨论和争辩已变得更加重要。在冷战后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认识现有的世界秩序究竟如何,还需要确定它应当如何。由此做出的取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至少新世纪初叶的世界秩序将会如何。
无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还是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与建设理论,都有其关于国际关系伦理的丰富内涵,然而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此应作的探究和阐发迄今仍处在几乎尚未着手的地步。不仅如此,国际政治伦理思考虽然对理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和进行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至关重要,并且可以说是为真正全面深入地讨论当今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所必不可少,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就此所作的努力依然很不充分。所有上述情况,使得今年7月26至27 日在北京举行的“伦理与国际事务学术讨论会”饶有价值。它是首次在我国专门就国际政治伦理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伦理与国际事务部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国际问题研究项目。卡内基基金会伦理与国际事务部主任乔尔·罗森塔尔(Joel Rosenthal)和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分别致开场词,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对外事务副教授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里·纳尔丁(Terry Nardin)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等多名中外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讨论会。
史密斯教授按照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思想家马丁·怀持( MartinWight)和海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作的区分,将关于当代国际体系中正义问题的思想归纳为三种形态,即现实主义、康德(Immanuel Kant)式观念和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式观念(它们又分别被称为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和国际社会模式)。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中的正义主要定义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它尤其表现在均势和互相尊重势力范围;康德式观念着重于全人类共同体中的个人正义或人类正义,它的伦理要求和规范集中在实现或维护人权方面,带有普世主义的激进色彩甚或意识形态征服狂热;格劳秀斯式观念则在内容和精神两方面皆可谓介于前两者之间,其正义主要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依据至少起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实现协调,或者说将正义当作一个“国际社会概念”。史密斯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不同的伦理思想模式意味着不同的世界政治观、不同的国家利益定义和不同的对外政策。他强调,所需要的是一种能使上述三大形态共存互补的综合,它将大大有助于实现一个正义的世界秩序,而国际关系学者本着“对权势正告真理”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能够、也应当为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逸舟研究员以上述西方国际伦理三大思想模式为辅垫,指出当代中国人看待世界事态时一般总有其伦理取向,而且并非总是一致的。依据他的观察,中国人更熟悉、甚至也更愿意接受的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是“全球伦理主义者”,特别重视全球性问题,并且因此倾向于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问题上超越“主权绝对观”的束缚。他提出了一个所有与会者都相当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不同的价值观和正义观如何互相协调、互相适应和互相学习。时殷弘教授对于将格劳秀斯大致纳入第三种伦理思想模式提出异议,认为真正的格劳秀斯同怀特和布尔解释的格劳秀斯有区别,他在某种程度上较接近关于人权的正义观。时殷弘还认为,似有必要提出第四种国际政治伦理思想模式,其核心是当代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正义观,它较接近上述现实主义正义观,但注重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反对外部干预和强国的势力范围政策。
纳尔丁教授以国际政治伦理哲学研究著称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他以“国际事务中的伦理传统”为题强调以自然法观念和康德义务论为主要代表的“普遍道德”(common morality )的存在及其意义:普遍道德是人类来自理性的必然物,可以在习惯和理性思考两种形式上存在;它对于思考伦理问题必不可少,它的信念同利益优先、结果优先的结果主义(现实主义)伦理截然相反。纳尔丁着重谈论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思想: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到当代的《联合国宪章》,正义的战争都必须是为正当的理由并且以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的战争,前一方面当今最尖锐也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将武装力量的使用局限于自卫?是否允许追求维和或人道主义干涉之类更广泛的目的?”至于后一方面,资中筠研究员的发言犀利地指出了纳尔丁教授未谈及的当今一大论题,即北约就科索沃问题进行武装干涉的手段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和平的伦理主要涉及防止甚或消除战争,或者说取得普遍持久和平的条件。 纳尔丁从谈论17 世纪霍布斯(Thomas Hobbes) 关于自然状态即为战争状态、和平有赖于法律秩序的命题出发,经过对康德提出的普遍持久和平道路——所有各国奉行“共和”政体并相互间结合为一个邦联——的论说,如此总结了实际上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世界观:天下一分为二,一边是实现了内部持久和平的“自由世界”,另一边则是“自由之敌世界”,其范围内的各国因专制制度而不爱和平;不仅如此,“自由国家”可以干涉(包括以武力干涉)“非自由国家”的内部事务。
负责评论此项演讲的时殷弘教授以格劳秀斯式的道德主义对康德式的道德主义为分析框架和比较基础,作了题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传统:西方与中国”的发言。他一方面认为纳尔丁对西方有关伦理思想的阐析准确无误,另一方面进一步指出格劳秀斯式的道德主义在目标上远比康德式的道德主义讲求实际,而在道德色彩的强烈程度上则不及之;然而,康德式的道德主义在实践当中容易走向反面,导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自由国际主义“圣战”)和频繁的国际“警察行动”,并且促成很不道德的霸权目的。关于中国传统的和当代的战争伦理,时殷弘认为它们在战争目的或理由的道德性问题上同西方格劳秀斯式的道德主义甚为相似,但缺乏对战争方式和手段的道德性问题的思考和规定;中国传统的和平伦理同康德式的道德主义有很大差别,并且在道德含量上不及后者(特别同康德本人相比是如此),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伦理更是与之截然相反。他强调,当今在如何实现普遍持久和平以及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普遍持久和平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对立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政治歧异或政治对立的最本质的原因之一,若不逐渐得到协调或淡化,双方较为经久和牢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与战争方式和手段的道德性问题密切相关,陶文钊研究员在会上尖锐地指出“不能用军事侵略的方法来维护人权,否则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他提出,应当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实体、用什么手段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才是合理合法的。
布鲁斯教授对美国例外主义作了深入解剖,阐析了参与塑造美国政治文化及对外政策传统的那种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从何而来,论证了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理想卓越超群并适用于全世界的理念之历史悠久和经世不衰。
笔者以为,这些思想确实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而待到美国接近或占据物质力量方面的世界优势地位,它们就必不可免地转化为世界霸权心理,其特征在于自认为是全人类自由、进步的唯一真正代表,强烈地希望改造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想象其余人类依本性当乐意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体系,非常不愿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民族(特别是非西方不发达民族)的价值观念及其存在理由。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层出不穷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和侵略战争表明,布鲁斯阐述的那种道德傲慢往往离道德跌落只有一步之遥。
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主流,在于宣告国家主权已经、并将继续受到日益发展的全球化的严重侵蚀,这一人类“进步趋势”导致民族国家及传统国际体系迅趋过时,要求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确立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性治理,并且废弃(或至少大幅度修改)不干涉内政原则。凯格利教授的演讲——“国内伦理文化与国际事务中的国务家”便表达了这种西方流行信条。按照他的概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包括其伦理和法理观念)以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截然区分为前提,认为在国内一般盛行中央权威治下的高度有序状态,法律和道德伦理有效地发挥规范个人或社会群体行为的作用;而国家相互间却盛行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一般优先于伦理和法律考虑,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保护国家主权免受外部侵扰,并且使得各国大致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和伦理文化价值来规定自己的基本政策取向。然而他强调,在金融、贸易、生产、通讯、文化和人口流动等一系列领域进行着急剧的全球化过程,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大大减小国家对国内事务的控制能力,使得国家主权、国际领土分野以及国内与国际事务的区别迅趋丧失其意义。与此相应,70年代以来,尤其自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愈益衰朽,而所谓“改良性的干涉主义”日益成为在欠发达国家内部制止战乱和屠杀、维护人权、甚而扶植自由民主制的合法工具。反过来说,倘若墨守不干涉原则,“就会使国际社会得不到实现道德目的的一种正当手段”。不过,凯格利也承认旨在“人道主义”甚或“民主”的干涉会引起复杂的政治和伦理困难,甚至加剧干涉试图解决的同一些问题。他仅仅非常笼统地提议要区分“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干涉,这当然远非应付上述困难、防止出现道德灾难的可靠办法,北约关于科索沃的干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凯格利教授的上述议论过于激进,那么负责评论的贾庆国教授的意见便恰好与之相反。贾庆国对“国家主权过时论”和“国际干涉有理论”进行了一番批判。他指出,西方“全球主义者”漠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干涉的忧虑和干涉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且全不理解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真正需求。他认为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应当无条件予以维护,而进行这种维护显然不能指望国际组织,因为在他看来国际组织的效力一般由强国决定,并且为强国的利益服务。他强调,应当以缔造国际共识来取代国际干涉,多样化的世界比一体化的世界好,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比国际社会的霸权化好。
陶文钊研究员较为精细地指出:国家主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侵蚀,但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因全球化得到了加强;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仍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全球化之上,而不同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和受到的损害很不相同。
蔡斯教授的观点有如下述,比较接近中国的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他认为,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单元,而且仍有生命力,它们大多数仍不愿受到外来干涉。
面对所有这些异议,凯格利教授补充说全球化有成为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危险,而实际上已在进行的“国际共识缔造”有时是以特别残酷的方式进行。他承认,在全球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多样性确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时殷弘教授指出:自16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欧洲的扩张,世界一直在经历全球化进程,目前的全球化状况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急剧的飞跃。前450年“全球化”的结果之一, 是作为吸取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西方造反”并取得伟大成功,它使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也就是出现了一大股与全球化至少不够协调的新力量,今后全球化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反弹”?
蔡斯教授的演讲题为“走向全球协调:一种美国看法”。他以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这一模式概述了自建国初年到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史, 褒扬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 和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为代表的均势思想和相对安全观,贬抑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等人的美国道德例外主义、共和(或民主)帝国思想以及绝对安全观。蔡斯断言,在冷战后世界上,“一种对待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方针大可再次在均势的运行中找到自己的最佳表达”。不过,它必然有如拿破仑战争后以欧洲共同价值之伦理概念为基础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 是一种寻求合作性行为规范和价值共识的均势。这一被蔡斯称为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 or Concert of Nations)的构造以美、中、俄、 日和欧盟互相间的大均势为主要骨架,它不一定要求各国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相同的体制,但“必须有一种共识,即大国间的冲突不可允许,避免一个盛行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世界,以社会正义为世界秩序的必要条件。”为此,蔡斯认为美国应当放弃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世界面貌的意愿,放弃绝对安全观念,但同时(在这里蔡斯多少自相矛盾)促进“自由体制的成长”和世界的物质与精神进步。
王缉思研究员在评论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大国之间(例如中美之间)的某些基本观念和重大利益对立,几乎不可能像蔡斯教授所说的那样成为“不可容许”的。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它们无论对评价蔡斯的观点,还是对认识美国对外政策或规定冷战后世界秩序与正义都是重要的:什么力量或观念在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形成中起主要作用?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是全球主义还是所谓新孤立主义?在大国均势或大国协调的世界上,许多次大国和小国的位置在哪里?
在有关未来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台湾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资中筠研究员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也最危险的问题;中国人传统上判断统治人物的底线是看他是否将领土牺牲给外人,而最高的道德标准则是“民族大义”,中国人的这种传统伦理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显著。
在会议讨论中,中美学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那就是前者大都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或许可以说多少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而后者则大都以存在普遍和绝对的根本道德原则为前提,很少在理论上谈及制约道德伦理的各种因素。王缉思在其开场词中强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一国不应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强加给另一国。资中筠则进一步指出,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都有不同的道德观。中国学者谈论了道德与权势、道德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并且将它们同中美关系和科索沃冲突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看法的价值取向,正是王缉思上面所说的国家间价值观平等,那是它们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相处、平等交流的必要条件。
此次伦理与国际事务学术讨论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即中美双方学者共同探讨若干基本的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并且交流各自己有的一些研究以及由讨论引发的新思考。会议的论题既包括国际政治伦理的基本历史传统和原理,也包括具备丰富的伦理内涵、需作重要伦理判断的当代世界重大问题。双方的发言反映出了中美两国学者当前在世界地位、国家实力、政治价值观和国际问题关注重点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但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共识,特别是希望中美两个民族以及世界所有各民族在道德观方面互相理解、适应和协调,以此为持久的和平共处提供一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