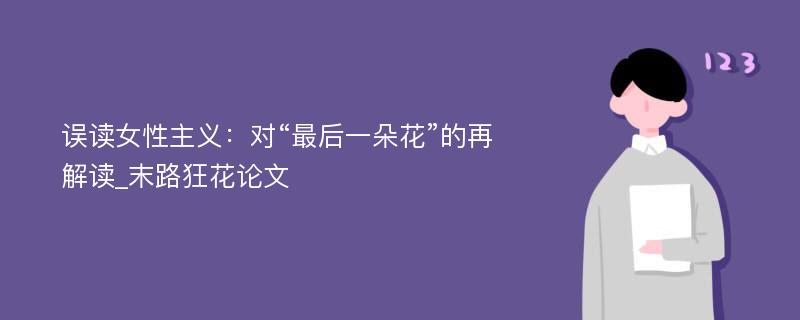
被误读的女性主义——《末路狂花》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末路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2-0099-04
《末路狂花》一直被视为经典女性主义电影①,这或许是种误读。劳拉·穆尔维曾尖锐地指出:“父权制对电影的影响主要在‘快感’上,即‘看的快感’,或弗洛伊德说的‘窥视癖’。”“任何有文化的地方,凝视的力量都呈现在电影艺术和性别政治中。[1]”仔细解读《末路狂花》,就会发现,片中女主人公并未摆脱“被窥视”的命运,她们所谓的奔向自由之旅不过是在男性监视下的短暂放风,最终还是悲剧地印证了男权的不可颠覆。
一、男性凝视下的“她”
《末路狂花》主要围绕两个女性展开叙事,片中安排的男性形象模糊而笼统,只是象征男性世界的简单化符号。正因如此,影片很容易被解读成一部致力于建立“女性中心地位”的女性主义电影。然而,女性主义电影的本质,并不在于讲谁的故事,而在于“谁在讲”。女性究竟有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观看者,并进而成为言说者,这是判断女性主义电影的关键。
在福柯看来,“看”是一种权力的体现。那么,在《末路狂花》中,究竟是谁在行使这种“看”的权力?虽然影片讲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甚至都没有一个较饱满的男性角色,但我们的女主人公依然自始至终无法逃离男性隐匿的目光。影片中男性注视有两种,一种是事实上的注视,从这两个女人射杀了强奸犯哈伦踏上逃亡之旅,检察长到停车场展开调查起,她们就时刻处在男性追踪和监视的目光之下:以警方为代表的男性通过监听电话、监控录像、问询所有和两个女子有过接触的人等方式布下天罗地网,严密监视这两个女性的一举一动。
另一种注视是已经“内化”到她们体内的男性目光,这种注视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却更无处不在,更有权力。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边沁的圆形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瞭望塔。这种监狱最大的好处就是被囚禁者可以被无条件地被观看,而在中心瞭望塔的人可以无条件地观看。其结果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2]影片女主人公,似乎也处在这样的“圆形监狱”之中,即便她们离开了男人,监视仍无处不在。露易丝接上塞尔玛,刚刚踏上旅程,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跟达里尔说的?”男人的反应,即使是他们不在场的时也显得那么重要。“男人会怎么看”,这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提问在之后反复出现,意味着男性目光如影随形。露易丝在停车场神经质地射杀了强奸犯哈伦,这显然超出了自卫范畴,为什么涉世颇深的露易丝会做出这样冲动的举动?因为她心中有一双眼睛——曾经在德州侵犯了她的那个男人的眼睛——在凝视,正是这不堪回首的目光和眼前哈伦挑衅的目光叠加,导致露易丝愤而举枪报复。
从她们外出旅游到后来的逃亡,本该是一次奔向短暂自由的旅程,一段可以张扬自我的美妙时光,但是,当画面中汽车自由驰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张扬,相反,“男人”始终是萦绕她们的永恒话题,她们谈塞尔玛的丈夫、谈露易丝的男友、谈强奸犯哈伦、谈路上遇到的牛仔,唯独不谈她们自己。男性变成了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使得她们无法拥抱自我。因此,任何时候,塞尔玛和露易丝都没有摆脱男性凝视下的“她”的身份。
那么,塞尔玛和露易丝有没有尝试主动地“看”呢?女性角色能不能主动地看,甚至挑衅地看、充满欲望地看,往往是评价一个女性是否具备独立性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能看到她们大胆直视的目光,影片并没有依赖女主人公的主观视角叙事,哪怕是出现一个主观视角镜头。反而是在她们的旅途中,露易丝反复规劝塞尔玛“不要看”。旅途刚刚开始,在酒吧遇上哈伦,没心没肺的塞尔玛和他搭讪调情,露易丝就不止一次地制止;之后遇上搭车的牛仔,露易丝态度依旧,如一个良家妇女一样地拒绝;再后来,他们俩遇到了卡车司机无休止的性骚扰,露易丝就一脸戒备地告诫:“不要看”,而塞尔玛则是一副天真无辜的表情“我没有看”。
不看不听不言,是露易丝一路上自保的准则,表面上看,这是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她对男性世界的戒备和防范,事实上反映了女性对自身力量的不自信。琳达·威廉姆斯在其著作《当女人观看时》中指出,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中,“女人时常以其象征性的盲者身份来显示其纯洁性。”[3]“不要看”内化成了她们自觉的自我约束,主动放弃了“看”的权力,安于“被看”的地位。
既然她们放弃了“看”的权力,“凝视”的快感也就无从谈起,但是与传统影片不同,这部影片毕竟以女性作为叙述的主体,关怀的是女性的心路历程,人们确实看到了她们在公路上驰骋时的放纵和狂欢,那么这种“快感”又从何而来呢?
二、被看的快感
劳拉·穆尔维也谈到:“在有些情况下,观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正如相反的情况,被看也具有快感。”[3](4)但是对于被看的快感,在她的文章里并没有展开论述。倒是可以在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中找到一个恰当的注解:
“女人必须不断地注视自己,几乎无时不与自己的个人形象连在一起。当她穿过房间或为丧父而悲哭之际,也未能忘怀自己的行动或恸哭的姿态。从孩提时代开始,她就被教导和劝诫应该不时观察自己。……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4]
约翰·伯格在描述女性和“被看”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一针见血。女性模拟男性目光对自我的审视,或许可以认为是劳拉·穆尔维所提到的三种目光(摄影机、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的目光)之外的第四种目光,这些目光共同建立起了女性的自我印象。他人的凝视和评价,取代了女性应有的自我感觉,假想中的男性目光和评价时刻纠缠着女性,她们一生都在为他人的目光而活,这难道不是女性丧失主体性的最深刻写照吗?
《末路狂花》中,我们的女主人公并没有突破这样的女性形象,正如前面讨论的,她们时刻感到男人在看,并且从这种凝视中获得快感和满足,唯一和传统女性形象不同的是,这是报复、激怒男性世界的快感,而不是一种被认同、被赞美的快感。如同一个叛逆期的孩子试图通过激怒父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她们的每一次疯狂举动都是男性凝视的反射,有着一个想象中的或者是事实上存在的目瞪口呆的男性观众。
在挟持警察的时候,露易丝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丈夫对我不好,你看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她们的叛逆和反抗,是做给男人看的姿态。男人的目瞪口呆,给她们带去极大的满足。最典型的莫过于塞尔玛抢劫了便利店之后,坐上车子眉飞色舞地向露易丝叙述刚才的经历,这时镜头出现的不是塞尔玛的叙述,而是达里尔和警察一起观看监控的场面。画面中,达里尔目瞪口呆的画面其实也浮现在塞尔玛的想象中,成为她狂喜的来源。这样的情节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每当这两个女人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紧跟着就能看见男人的反应:狂怒、迷惑、不可置信,或者其他。这是一个男性导演所能想到的表现男性无能的方式,但无意中却渲染了男性监视的能力——女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引起这个潜在观众的注意,不然她们的胡作非为也就毫无意义。
当影片接近尾声时,看着庞大的追兵,塞尔玛惊诧而又兴奋地说,“难道是军队?为我们而来的?”这时,她们的出走在塞尔玛过分兴奋的眼神中完全沦为一个孩子气的叛逆游戏。
整部影片,事实上都不是出自自我的呼唤,而仅仅是一种叛逆。两位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一片模糊。她们的快乐建立在男性的反应之上,她们的自我形象定位在男性的评价之上,因而,她们的命运之路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男性的股掌之中了。影片所描述的两个女性寻找自我之路,追究不过是一次孩子气的叛逆游戏、一个离家出走的陈旧故事罢了。
那么,女性在这个叛逆游戏中,在虚幻的自由中找到的所谓的“新的自我”又是什么呢?
三、变性和毁灭
既然我们的女主人公意识到男性无处不在的凝视并以激怒这样的凝视为乐,那么她们所谓的“新的自我”必然是冲着这种“凝视”来打造的:“既然要把我当作一个女人来看,我就偏偏不像个女人;既然要看我柔情万种,我就偏偏粗粝不堪”。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就曾主张男女同质化,其中的一种选择就是女性为了摆脱男性的凝视而故意抛弃象征女性美的东西,将自己伪装成男人。这种做法在当时当然有其革命性,但反过来也强化了男性第一性的印象。况且,《末路狂花》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连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也已开展了十几年,男女同质化早就被男女异质化的追求代替,影片却依然停留在男女同质化的简单化处理上,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影片的开头有一个有意思的镜头,穿着白纱长裙的塞尔玛坐上汽车开始她的“自由之旅”。她靠着椅子,故作熟练地点燃了一支烟,露易丝看了既惊且笑:“你这是在做什么”,塞尔玛得意地说“我是塞尔玛”。这是她自我意识的萌发吗?何等的荒诞和幼稚,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把对男性(成人)世界的刻意模仿当作自我的张扬(或者“长大”的标志),这恰恰反应了她在女性(自我)意识上的一片空白。
塞尔玛和牛仔的一夜情在影片中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段落。一夜情、婚外情如果不倾向于道德上的谴责,其背后往往有着“寻找自我”的暗喻,但在《末路狂花》中却没有进行类似的尝试。影片中,牛仔是另一种于连式的“坏男人”,有着多情英俊的外表和冷酷的内心,他们给女人的打击更致命。影片的探讨仅此而已,我们原本可以期待看到塞尔玛作为一个女性的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无论这场短暂的爱情是不是欺骗。作为一个第一次品尝“爱情”滋味的女人,塞尔玛难道不应该表现地更加积极,更加主动,以及更富有女性魅力?她难道不应该从中发现作为一个女性的美好和强大?然而,我们却非常失望地看到,塞尔玛这个没心没肺的年轻少妇,在英俊多情的牛仔面前,直接又回到了她“离家出走”前的女性形象,无知、单纯、头脑一片空白,易于被挑逗和欺骗,唯一的区别是她尝到了丈夫没有给过的高潮滋味,就算这高潮不也是男人赐予的吗?换言之,这是“离家出走的娜拉”离开她的统治者之后,并没有自发地找到了爱情,更谈不上支配爱情,而仅仅是又做了一次那个懵懂无知的塞尔玛罢了。
影片中一夜情的安排,不是为了给塞尔玛指出一个寻找自我的方向,反而证明了“作为女性毫无出路”的粗暴断言。爱情泡沫的破灭,以及紧跟着的塞尔玛的巨大转变(抛却了女性身份,转而以男人的方式抢劫了便利店,从而完成了她的转型),暗示着一个绝对男权中心的荒诞寓言——要么做愚蠢无能的女人,要么做强大机智的男人。
这样一来,我们的女主人公迅速向男性转型(变性)也就理所当然了。塞尔玛脱下长裙,换上T恤,露易丝颓然地把她的口红扔到车外,又除下了身上所有的首饰,换了一顶牛仔帽。凌乱的头发,布满尘土的脸,牛仔的打扮,女性特征已经被完全抛却。在接下来的惩罚卡车司机的情节中,两位女主人公脚踏蓝鸟汽车、双手持枪的身影被卡车爆炸的冲天火光映衬地英气勃勃,令观众击节赞叹,但是这是女性对男性的反抗吗,不,这是用男人的方式来惩罚男人,是以暴制暴,这里没有自觉和自我拯救的意味,有的不过只是放弃自我之后向男性世界的快速堕落。
抛弃女性身份,这已经是女性对男性世界做出的屈辱妥协,但影片把观众引向更加令人绝望的结局——男性世界甚至无法容忍女性对他的效仿,把这视为越轨和侵犯:当警方率领庞大武装将她们逼到悬崖边缘,当检察长依然徒劳地尝试劝说她们踏上归途,摆在她们面前的是两条路:做回“乖乖女”活下来,或者作为“男人婆”走向毁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男权中心的世界牢不可破的价值观,他们只要毫无主体性可言的“乖乖女”,即使连“男人婆”也不被他们接纳,当然更不必提拥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新女性。因此,即使是蓝鸟汽车冲出悬崖的瞬间,我们看到的也不是新女性的浴火重生,而仅仅是绝境之外的绝境!
《末路狂花》远不能算作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虽然影片毫不客气地揭露了男性世界的丑恶,但全然无意撼动男权的中心地位,我们看不到一丝改变这种中心地位的可能,有什么能比既丑恶又牢不可破更加令人绝望的吗?而事实上,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女性都应该比影片女主角更加地强大、从容、也更像一个女人地生活。
注释:
①《末路狂花》,美国MGM公司1991年出品,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