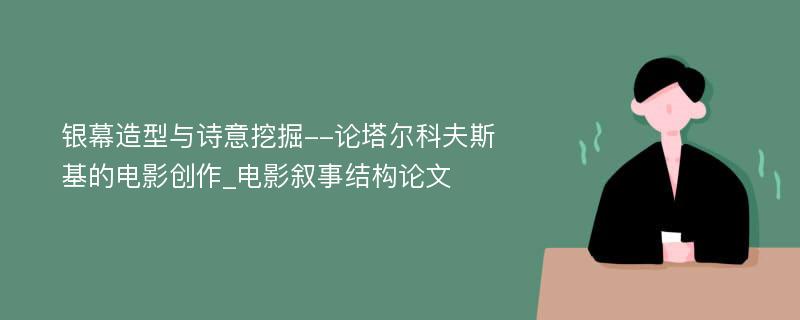
银幕造型与诗情采掘——塔尔柯夫斯基电影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情论文,银幕论文,夫斯基论文,塔尔论文,造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塔尔柯夫斯基是享誉世界影坛的前苏联电影导演。他一生共有影片七部。自六十年代第一部作品问世起,经历了曲折的人生和创作历程。其最后两部影片,摄于异国他乡。经岁月流逝和历史演变,塔氏的影坛声誉也由“出口转内销”,终于在改革之年的苏联和俄罗斯重受青睐。这位曾被视为异端而实质始终眷恋俄罗斯大地的爱国影人,是一位在电影创作上富于独创性并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家,被世界影坛尊为“银幕诗人”。笔者在塔氏母校、莫斯科全苏(俄)国立电影学院访学期间,有机会观赏了他的全部作品,深感他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影坛添加了若干别具一格、富有魅力的上乘之作,而且为银幕造型采掘诗情积累了开启性的可贵经验。有感于国内尚较少对塔氏影片的系统研究,遂不揣浅陋,写下自己的初步心得,以求抛砖引玉。
大跨度联想──人生感悟的飞跃
联想,几乎被所有的艺术作品所普遍采用。在抒情类作品中,更是不可或缺,而且永葆其美妙之春青。百用不衰的联想术,其生命潜能的奥秘的确值得深究。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联想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它把相干、不相干的自然和人生现象联结在一起,使之在某一点上发生关系并产生强烈的迸发性效果,使人有所发现,从而给予人们教益和启示,让人享受到获取的喜悦。由此可见,凡是掌握了联想基本法则的艺术家,便可借以创造某种艺术效果,这也许便是上述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的一个缘由吧。然而,联想手法运用水准的高低,则是大相径庭的。塔尔柯夫斯基影片中的联想运用,不仅效果脱俗,而且方式格调也显示出独家的风范,堪称鲜见。
在塔尔柯夫斯基饱含审美蕴涵的抒写性叙事之作中,富于超常力度和厚度的大跨度联想,有机地交融于作品的整体之中,引发观众于诗情醇厚的品尝之中深深地感悟人生。这种借联想思维作动力,推动观众实现艺术感受和认识的某种飞跃,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艺术创造。
塔尔柯夫斯基银幕造型的这种大跨度联想,在作品整体构思上表现为全局性纵横交叉的立体构架。
影片《镜子》便是最鲜明的例证之一。这本是一部按照导演本人家庭生活“原样再现”的自传性影片。导演别开生面地将事实与联想、回忆与潜意识深处的感受有机地融成一体,组成一部逝去了的岁月的家庭小史。表面上看,影片似乎显得芜杂、凌乱,甚至有些捉摸不定,神秘莫测,实际上,导演将不同时空的情节及内在构成借大跨度联想勾连贯通起来,通过片中的主人公、又是叙事者、也是作者、导演本人的“分裂”式多重视角与不同层面的时间结构纵横交织,顺着作者心理思绪自然流淌的意识流动过程,以诗意般的联想断片,精心建构成一部构思新颖、构造奇巧的艺术精品。它既保留了生活的“原样再现”,又以片断性、跳跃性联想思维结构故事,几重视角所形成的多条线索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情节的,而是联想的。例如,影片开场几个片断的构成,就是大跨度跳跃性联想思维结构的典型。片头发生在现代,以一个电视镜头比喻作者终于克服了某种顾忌,开始向人们述说自己的故事。第一个片断时光倒流至许多年前的卫国战争时期,主人公回忆年轻时的母亲总是站在篱笆墙前,忧郁地企盼丈夫归来。由母亲而联想起当年居住于乡间的一场大火。由火的蔓延,又忆想到水的漫溢,时间又追溯至更为遥远的战前。想象中,那时母亲洗头,总让父亲提着水罐帮他冲洗头发。第二个片断,镜头再次切回现实,只听得并未露面的主人公与长得酷似他妻子的母亲对话。当主人公闻知母亲的女友丽扎去世的消息,影片又转入第三个片断,回忆战前斯大林崇拜时期母亲当校对员时,与丽扎一起经历的一段故事;由丽扎过去成天要丈夫给她“拿水来和拿鞋来”,丈夫终至离她而去,作者又从叙事人角度引出一个语意双关的结论:丈夫的出走是“你”(意指母亲)亲手造成,也直接造成孩子的不幸。紧接着第四个片断,画面又返回现代,作者与前妻娜塔丽娅对话,由妻子口中道出他们离异的原因,是因为他总说她太象自己的母亲,而主人公至今都因父母离异而与母亲失和。仅此开场几个片断,时间跨度很大,但联想自然流畅,角度迥异,内容配置合理而又逻辑。此后的各个片断,无论是战时或战后,西班牙、布拉格或莫斯科,也都细密准确地体现着此种看似芜杂实质严谨的构造特点。这种传送复杂思绪的跳跃式大跨度立体化联想构图,组成了一幅幅梦幻与现实视觉朦胧交融的独特艺术图象,牵引着观众在视听中记取鲜明深刻的银幕印象,在回味中追寻感悟,领受作品中主人公、作者、导演,也即做梦的我与梦中的我,对逝去历史中种种至深印记的强烈感受:那残酷的战争,那骇世的个人崇拜,那令人惊悸的核威胁……并进而从主人公所承受的深沉精神痛苦中,获取深刻的启迪,引发厚重的沉思。同时,影片在近乎精神裂变的幻化和大跨度联想中,还对人生和未来注入了生机和希望,作为大自然和世界和平女皇象征的母亲,成为大幅度转换联想中倾注希冀、展露期待的有力依托,对人类命运悲剧性与乐观性相统一的极富历史纵深感的感受和思考,诗意地熔铸和展现在五彩纷呈的银幕造型之中。
塔尔柯夫斯基在《镜子》中所显露的电影思维特征,无疑接受了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对传统戏剧结构大胆反拨的新奇尝试。如果说,60年代初,法国新浪潮运动中“左岸”派导演曾将一味追求虚无的潜意识心理实验标谤为“内心现实主义”只是一句空话的话,那么我以为,塔尔柯夫斯基的这种诗情联想式建构的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真正称得上“内心现实主义”的。尽管影片的某些传达方式,颇有些令人费解,朦胧而又暧昧,但是,略带晦涩的朦胧一旦被征服,其强大的审美弹性给予观众的巨大审美快感是传统叙事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影片题名为《镜子》,也蕴蓄颇深地从一个侧面透示出作者的创作立意:那些逝去了的生活片断,就象摄入于他老家那口厨上的镜子似的,重又映现出来。而片中时而穿插导演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尔柯夫斯基旁白式的动人诗句,则更为作品的诗体构造插上了灵感的双翅。
历史片《安德烈·鲁勃谬夫》由七组银幕造型有机构建而成。前6组是壁画与圣象画家安德烈.鲁勃谬夫在俄罗斯大地亲眼目睹人民备受凌辱的苦谁生活景象,第7组则是由巨大的人生苦闷幻化而生的体现美的理想追求的系列壁画珍品,影片新奇的构思突出地表现为由“丑”生“美”的反弹式飞跃性联想及其艺术升华,精心地将丑恶的生活现象转化为优美的艺术造型。那6个以黑白片映现的相对独立的“苦难”篇章,象乐章上的一组衬托性“和声”,最后一组动人心魄的彩绘与壁画才是鲁勃谬夫倾心讴歌的“主旋律”。美由丑生,善从恶来,个性的热切召唤,源于非人道的现实。影片运用大胆的诗意想象所构筑的既互为烘托又鲜明映照的七个断片,融成一首音调起伏、音域宽广、音质纯美、和谐统一的辉煌乐章,展示出深刻的历史内涵。《牺牲》中则把人类核环境的威胁与宗教祭奠奇思异想地勾连成一个整体,表达作者对世界秩序的深切忧虑。这一类构思与构造上大跨度联想的成功运用,无不深深地拨动人们的思想琴弦,引发人们对宇宙世界的深入思考。
幻化为梦境折射,是超越联想常规的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在各种艺术表现中也时有所见。我们通常所见,均属局部性偶尔穿插运用。但在塔尔柯夫斯基的电影中,梦幻造型,却成为其展示心灵、采掘诗情的重要手段,这是值得注意的。自1895年活动电影面世以来,叙事几乎成为各类片型展现内容的主要手段。20世纪中叶国际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中,诗电影产生。它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力避传统的叙事方式,将与叙述因素有关的情节纠纷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都视作电影的“敌对元素”,一味追求纯光影、线条、节奏的技巧处理,展示紊乱的下意识活动,力图探索电影的所谓纯诗性。塔尔柯夫斯基创造性地吸收初期诗电影缔造者们的合理电影思维,有机地融入散文电影的表现方式,努力寻求隐喻因素与叙述因素的结合,产生“某种比单纯事实更具宽广和普遍精神意义的东西,一个具感情、思想和景象为一体的完整世界”。①这种融叙事于诗境中的电影,在概念上更接近于文学作品中的散文诗,既蕴含着浓浓诗情,又有一定的情节因素,拓宽了观众的读解面及对影片的审美接受。
如果说,叙事因素的有机吸收,是塔尔柯夫斯基对诗电影表现领域的一次拓展的话,在叙事中创造诗意的梦境,更增添了诗电影的内在魅力。众所周知,梦境,乃是人的某种心理活动的折光显示。它“是一种非意愿的自发的心理产物,是自然的一个声音”。②尽管它极少精确地复现以往的生活情状,然而,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有意识”的一种补充。事实上,梦境通常与梦者的个人生活有关,那些出现亲朋好友、家庭与日常生活事件的梦更与个人所处的时代历史及社会环境有关。同时,梦中的情景,往往还是梦者人格精神的某种显现。综观塔尔柯夫斯基的所有影片,我们不难发现,他常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梦境与幻觉,传达意识深处的东西,将那些无法用话语来表达的藏匿于潜意识、下意识深处的东西,巧妙地通过银幕形象体现出来,使如诗如画的梦境、幻觉与散文体的情节片断构建成风格独具的叙事形态,展示最为复杂的内心世界。
1962年,塔尔柯夫斯基拍完他的处女作《伊凡的童年》后,虽然他曾自谦地说“还不懂得什么导演业务”,然而,他却承认,在那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中,他曾努力探索电影与诗歌的联系。他认为“接触某种文体的精神实质,能对电影有所帮助。”③他对诗电影的探索正是从表现梦幻开始的。《伊凡的童年》中,处于严酷战争环境中的伊凡,对业已成为过去的那段和平时期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就颇具梦幻性,他梦见幼小时的自己,在静谧而又美丽的乡间,跟随妈妈,一起去井边汲水。忽然,天空中传来布谷鸟的鸣叫声,小伊凡兴奋地对着井边的母亲说:“妈妈,那里有布谷鸟!”年轻的母亲与小伊凡一起望着兰天白云中自由翻飞的小鸟……。这是一首逝去了的田园诗。简洁的梦幻镜头中,蕴含着何其丰厚的思想容量!它既是主人公伊凡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恋与眷念,也是艰苦酷烈的战争环境与祥和恬静的和平生活的鲜明比照。正常的童年,本应象过去那般绚丽、甜蜜,然而,战争将伊凡幸福的童年生活剥夺了,对伊凡来说,逝去的五彩童年不仅是美丽的,更是短暂的。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和平时期童真无邪、健康活泼的小伊凡已一去不返,如今的他,为适应战争,已被战火的烈焰熏染得扭曲了人性……。这是用诗意的梦境对照反衬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的颇为巧妙的一笔。短短一组镜头,如几句简约的诗行,以少胜多,激情无限……在这个片断里,童年的美梦,既是情节,又不完全是情节,它更象一种情绪。导演让小伊凡扬起心灵的翅膀,以孩子心中最质直的感受与情绪感染观众,影响观众。伊凡情绪中释放出来的潜在能量,深深叩动每一位观赏者的心扉……
早期的诗电影,由于过分雕琢于纯电影技巧,一味热衷于下意识领域的开掘,难免产生脱离实际的虚无倾向。塔尔柯夫斯基从不主张重复“使用我们父辈的经验”,而是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诗电影领域比他的前辈提供更多更为积极的新质。他表现的梦境与幻觉,并不停留于浅层的展览,而是将个人意识深处的感知与对宇宙深处的兴趣对应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时代历史的深度使他的梦幻诗意迸射出现实主义的奇光异彩。西方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在阐释梦境时,曾将梦幻归作两类,一类梦是“个人的”,来自于个人的无意识,并与做梦者生活的个人方面有关;另一类梦则大大超越于个人的范畴,荣格把它称作为“集体的梦”。它们来自于“集体无意识”。因为它们投射着人类远祖的思考及某些历史、神话的意蕴。对于《伊凡的童年》中那段“布谷鸟”生活的梦幻记忆,导演的妹妹塔尔柯夫斯卡娅曾作过阐释。她说,电影中伊凡向他妈妈指说布谷鸟的那句话,曾是安德烈三岁时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同他母亲一起渡过第一个夏天时所说。这无疑是一个关于伊凡的“个人的梦”,也是塔尔柯夫斯基的童年之梦。然而,它又是一个“集体的梦”。梦境的出现,将时光倒转至战前苏维埃和平生活时期。这是烽火岁月中的伊凡们共同神往的历史时光。它的闪现,何止于一个伊凡意识深处的希望之梦?它已远远地超越于“个人的梦”的范畴。梦境的诗意美的展现与廓大,更蕴含着特别厚重的历史内涵。人物意识深处行为动机的描画,最终以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无疑是塔尔柯夫斯基对诗电影的一个突出贡献。
塔尔柯夫斯基对生活与历史的强烈感受及深沉思考,使他有意识地在影片梦幻诗境的创造中,着意展示浓重的悲剧意识。影片《镜子》通过不同时间层面诗意朦胧的梦境般的回忆,艺术地展现了作者母亲的心灵悲剧。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虽已被丈夫遗弃,但她仍深爱自己的丈夫,久久地等候他归来。然而,从年轻时起一直等到斑斑白发之日,总不见丈夫在门前的小道上出现。悲剧主人公一生的情感挫折,并非出于道德上的罪过,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缺点”所酿成的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因而使人因怜悯、同情而产生悲剧美感。另一方面,女主人公抚儿育女、独持家政的献身精神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美德,越发增添了动情的悲剧的意味。
塔尔柯夫斯基不仅注意对这些具有一般正面素质的普通人悲剧命运的诗意揭示,更把诗情通向富于崇高感的悲剧造型。
《怀乡》、《牺牲》中的悲剧冲突,便渗透着某种高尚的人格力量。《怀乡》可以说是一首满贮着乡愁梦幻的抒情诗,浓浓的故土深情与淡淡的游子哀愁浑然成一完整的艺术整体。结尾时主人公戈西亚科夫怀着热望,手持一支小烛,希冀能如愿抵达枯池的彼岸。几经努力,终于趋于目的地了,却心疾瘁发而病逝。作家身染“怀乡”绝症(俄语中“怀乡”与“绝症”二词同义),空怀着心造的幻影离别人间,悲剧的结局里,投射了戈西亚科夫崇高的精神力量。《牺牲》中的亚历山大,通过宗教色彩浓重的祭祀,传达了他对人类未来、世界命运充满忧患意识的悲剧性思考。尽管主人公代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换取社会进步,然而,宗教观的局限及对自身的认识不足,决定了这是一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④。主人公幻梦般的虔诚追求和努力,随熊熊烈焰焚灭,但人们却在悲悯与赞叹中感悟到了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
隐喻性的构图──象征内涵的升华
隐喻,是修辞手法之一。运用得当,其艺术功能显然不可小视。惟其如此在艺术表现中,它被广泛使用。然而,仅仅作为比喻手法之一的隐喻,其使用范围与能量所及,也便如此而已。塔尔柯夫斯基电影创作中的隐喻性构图,情况就不同了。构图,固然仍有范围、规模的区分,但与影片创作整体相联系的构图,恐怕就不能孤立、局部地看待了。隐喻性,源于隐喻而又有所超越,也是显而易见的。塔尔柯夫斯基的隐喻性构图,作为不同凡俗的银幕造型,其主要特征在于:既借鉴吸收隐喻技法运用的基本准则和丰富经验,更广为拓展其空间层面,其要旨为因势利导、自然引伸,实现象征内涵的艺术升华。影片《向导》的结尾,便是塔氏隐喻性构图的一个典型例子。故事的主体部分,是描述作家皮萨捷尔与科学家普罗菲索尔怀着各自的目的,在向导斯塔尔凯尔带领下潜入一废弃的象是核试验的化学实验“地带”探察的经过。结尾时,影片却将艺术笔触落在向导的女儿马尔蒂什卡身上。房内一角,向导卧病于床。小马尔蒂什卡坐在一张桌子前凝视桌上放着的三只高矮不一的玻璃水杯。当她那沉思的目光注视某只水杯时,她那平移的视线,便“推”着那只杯子在桌面上横移。末了一只玻璃杯在她目光的“推动”下,渐渐向桌边滑去,坠落于地,在一声极为夸张的粉碎声中,画外传来连成一片的火车驶过的巨大车轮声与房屋、桌子的震颤声、狗吠声。联系作品的现实环境,这落地的水杯、特别强调的粉碎声,似乎隐喻着生命虽然“坚硬”,却又十分脆弱的特点。它象自然界的一串音符,“消失”只是个“时间”的过程。以此返视全片,贯通整部影片深刻的思想内涵,别具一格地透视出作者对核试验环境中人类命运的真诚关注。影片最后伴随着斯塔尔凯尔妻子画外的忏悔性独白,更使这一结尾余音缭绕,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思索回味的艺术空间。又如《镜子》中,叙事者回忆那不堪回首的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的烽火场面中,突然插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举着语录本狂热欢呼的“红海洋”场景。这一隐喻性插图,显然恰到好处地突出了战争进入白炽化的疯狂程度(作者对战争的评论视角当作别论)。在《牺牲》一片里,主人公亚历山大去使女玛丽娅家中恳求她的帮助时,决意留宿于玛丽娅处,否则就开枪自尽。影片让亚历山大与玛丽娅睡在一张吊床上梦幻性地凌空摇曳。这一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显然暗合着玛丽娅具有超自然力量拯救世界的宗教力量,同时也与整个故事的叙述格调相一致。
上述隐喻性构图,喻体同客观对应物之间没有形态与性质等方面的内在必然联系,然而,它们大都在影片的某一局部性范围内映现,联系其上下画面的含义,尚不难领会其蕴蓄的象征深意。在塔尔柯夫斯基的影片中,还有一些隐喻性构图,具有全局整体意义,有的需要在整部影片观赏完之后细加辨析才能领悟。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镜子》中的“序”。影片一开始出现的题辞是“我能说……”紧接着第一个镜头是主人公的儿子伊格纳特在观看电视。荧屏上是一个患口吃症的病孩正在医院就诊,在医生的启发与矫正下,病孩终于克服了口吃,吐出清晰流畅的话语来。然后影片返回至数十年前的历史时段,进入了正题。这“口吃被矫正”的开端,与全片的内容可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联系影片的上述题辞,便可理解下面所叙述的家庭故事,是主人公,也是作者、导演如口吃病人似地克服了某种精神与心理障碍之后说出的一切。诚如塔尔柯夫斯卡娅所述:“影片的题辞是‘我能说……’,依我看,它意味着安德烈终于冲破了禁忌:很多年内,我们都不愿与双亲取得谅解的童年时那段痛苦经历。”十分明显,埋在导演内心深处的这段苦痛,犹如处过“矫正”、“克服”的过程,终于向观众明晰地吐露了出来……。如果说,这个“矫正”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正面加深对整部影片的读解的话,那么,《安德烈.鲁勃谬夫》则是从整体反喻中完成影片哲学主题的升华的。现实的黑暗,人间的丑恶,贵族农奴主的凶残暴戾,入侵鞑靼人的野蛮行径,映衬着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对仁慈、博爱的追求,对绚丽多彩和谐美好世界的憧憬。值得一提的是,鲁勃廖夫笔下的圣母、圣徒的形象,一改以往创作中庄严肃穆的圣人形貌,力求揭示人物心理,使宗教形象人性化、平民化。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三圣图》,成功地把“神学象征题材同高尚的人道主义和普通人的真实感揉合在一起”,⑤深切地体现了他对理想人生的大胆探求。影片导演与摄影师为了着力渲染这一良好的道德愿望,刻意将影片前6个展现人间苦难的篇章拍成黑白片,唯独将抒写理想的第7篇章摄成彩色,用长达几分钟的空镜头,移动拍摄了鲁勃廖夫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艺术画卷。通过仰拍、摇镜头摄影,将一幅幅静态画面连接起来,组成了一个气势恢宏,色彩斑澜的动态世界。导演这一理想化结尾的反喻效果,准确地传达了主人公对人性、人道主义复归的热切呼唤。导演本人在该片公映时也曾说过,描绘那远离我们时代与生活的人们,目的在于表现今天必不可少的最为人道的思想。
塔尔柯夫斯基的隐喻性构图,还有一个效用,在于展示宽广的时代画面,使作品更具历史感与真实感。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论他是否出于自觉,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做的一切,都会在客观上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或意义。因此,严格地说,每一个人都属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都从属于一个塑造了“自己”的环境。塔尔柯夫斯基显然也十分敏感于这一点,并极为艺术地通过隐喻性构图使之发挥特有的艺术效能。这里,借助新闻历史镜头进行横向类比是常用的方式。如前所述,《镜子》是主人公、作者,也是导演本人独特的内心自白。然而,西班牙飞机的狂轰滥炸,苏联红军抢渡西瓦什湖,广岛升起的蘑菇云,莫斯科红场的绚烂礼花等等,或回忆、或纪实镜头的先后出现,都为这部个人色彩很强的影片,涂上浓重的时代色泽,从而使影片所抒写的个人命运,归属于人类文化历史的一部分中去。即使是在母亲当校对员时经历的那段“事故”插曲的回忆中,我们也可透过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与她同事惊恐、惧怕的行为,看到庞大的时代的影子在它的身后隐现。在《伊万的童年》中,导演匠心独具地将伊万的个人遭遇同历史车轮的推进相映照。影片结尾处,精心地插入了被攻克的柏林议会大厦与日本法西斯分子受降两个新闻镜头。这两个新闻片断的表层意义当不言自明。影片接着俯拍了一个镜头:戈培尔的孩子横尸于废墟。明白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孩子并非死于战火,而是为其母亲亲手所杀。历史的回顾映照着主人公的遭遇,二者扭结在一起,揭示了悲剧的实质:已被战争摧残扭曲了身心的伊凡,犹如戈氏的孩子,即使战后活了下来,也已无法再恢复常人的生活。时代面影的鲜活映照,还同时蕴蓄着何等深刻的时代内涵!
展示时代面影,烘托历史背景的隐喻性画面,在塔尔柯夫斯基的影片中,达到了信手拈取,点画写意的境地。例如在《安德烈.鲁勃廖夫》中,看似淡淡地描绘了俄罗斯底层百姓的一些生活情状,没有着力地勾画时代的轮廓,但是,鞑靼人的瓷意横行,鲁勃廖夫彩绘精品的艺术复现,无疑将观者带进了5个世纪之前俄国的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去。一动一静、纵贯与横向的简笔勾勒,巧妙地映现出时代历史的剪影。古迹让人触摸着历史,绘画便是时代的印证,塔尔柯夫斯基深谙个中奥秘,独辟蹊径地将历史画卷超越时空地平展在人们的面前。即使在科幻片里,塔氏也不忘勾织时间的网眼。在影片《索里亚里斯》中,宇航员贝通沿着城市驾车夜行的长长一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汽车时断时续地在长长的地道里行驶,仿佛带着人们一起穿越时间的隧道,通向新的纪元。最后当汽车终于驶上街面时,那高大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全玻璃装饰的楼房屋宇,绽露出未来新世纪的都市风貌。十分显然,地道与房屋的造型,在这里成了时代的标示与象征,它与某些新闻历史镜头的插入,具异曲同工之妙。
抒写化摄景──意境创造的完善
银幕诗人创作诗电影,着意采掘诗情,理所当然。大凡堪称诗作的艺术品,无不注重意境的创造。塔尔柯夫斯基的电影,寓诗意于叙事、抒情的交融之中。在这些银幕诗作中,常常呈现出抒写性的叙事与叙事性的抒情水乳一体的格局。这一格调别致的风格,便带来了景物选配和境界构建的诗意追求。抒写性摄录景物和力图有利于创造完善的意境,也就成为塔氏影片一个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
塔尔柯夫斯基影片中抒写化拍摄自然景物的一个鲜明表现,是景物的选配和拍摄,透示出特有的诗意氛围和意趣情绪。我国现代作家钱钟书说过:“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镕,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⑥这说明自然景物在作品中出现,是经艺术家“驱遣陶镕”精心选择配量而成。经塔氏影片“抒写化”之“补”而创造的意境,很值得我们细加品味。《镜子》一开始,有一个干草棚失火的场景。火愈烧愈旺,火势也愈来愈大,最后整屋草棚都被烧毁,这个失火场面,几乎都用中远景的长镜头拍摄,且不用音乐陪衬,与下面情节的开展似乎也无甚联系。既不明着火的缘由,又不见有人去扑救,只是远远地在云杉林的那边不断地升腾着烈焰。这把火烧得很有意境。它是主人公对童年时代一次火灾事故的遥远回忆,童稚的记忆中,除了远远的冲天烈火,其余什么也没留下印象。这场火灾发生在故事的开端部分,无疑为全片定下了一个不祥的基调,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气氛隐隐地笼罩全片。从思想意义上讲,则预示着片中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严格说来,它是主人公潜藏于意识深处的一种人生情绪的物化反映。它给予了观众远比画面内容博大深邃得多的想象空间。可谓“熔人事入风景,则实处皆空”。⑦影片的编导者将多重内涵的复杂心绪熔入一把火中来表现,超越了一般的人与自然景物关系的描写范围,为画面“写景”提供了新质,真乃“神来之笔”!
《镜子》中那口带穿衣镜的大橱,虽不是严格意义的自然风景,但也可称作主人公家中的一“景”。影片以“镜子”命名,也可见这个带镜的大橱在人物心中所占的位置,它作为主人公过去家庭中的一件家俱、一个摆设来回忆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童年的故事、家事的变迁、亲人的温情、世态炎凉都曾在它的周边搬演过。无形中它成了主人公以往岁月中的一名忠实观众、一位生活的见证人,甚至构成了这个家庭历史的一部分。作者的妹妹塔尔柯夫斯卡娅就说,它“是我们家庭陈设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一种鼓舞,几乎成了家庭的一员”。因此,这面镜橱在影片中尽管是一件室内的装饰物品,用于加强特定的忆旧氛围,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家族的一员出现的。这种“人化的自然”的诗意摄照,无疑增添了作品的醇厚的审美情趣。
塔尔柯夫斯基影片抒写性摄景的另一显现,是直接采撷富有诗意的自然景物,以正面抒发的常规技法,在诗情画意的审美享受中收取衬境托意之效。电影作品,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离不开对生活事件的描述。无论从哪一角度起始,总需将事件发生的缘由交代清楚,尽管自然景物并不能承担提供背景的全部任务,然而它常常在作品的开端部分出现,是紧紧服务于事件叙述需要的。银幕诗人的高妙之处,便在于自然地注入浓郁的诗情。《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开场,是典型的俄罗斯乡村的自然风光。一望无垠的荞麦田,长得丰丰满满、蓬蓬勃勃,紧接着一场急风骤雨倾泻而下,荞麦丛中主人公鲁勃廖夫曲曲折折地由远处向镜头走来。广袤的大地,生意盎然的庄稼,摇曳的树林,路边的村落,一片富饶美丽的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光!春夏时分的勃勃生机,正孕育着美好的未来与希望。然而,秀美的河山,辽阔的大地,却正遭受到外侮内暴的践踏与蹂躏,如此宁静丰饶的土地,正为人民所遭受的非人道生活提供了意味弥深的背景。开篇的这一抒写性景物拍摄,显然是为引出中心事件并增强其艺术感染力服务的。
抒写化的景物摄制,在塔尔柯夫斯基的影片中,还自然地融入事件的进程,成为情节的有机构成部分。《伊凡的童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丛林的绿色背景前,溪边浅滩上,慢镜头摇出伊凡同一位少女追逐奔波的镜头。伊凡赶过了那位姑娘,径直向前跑去。紧接着镜头切换,我们看到的不是伊凡进入镜头,而是一株枯死的黑树。这棵黑树的映现,虽是隐喻性的,但它却顺着伊凡之死的情节作了内容上的必要补叙、增进,它向人们形象地诉说着,即使到战后,心灵已被戕害的伊凡也已无法与别人一样,在正常环境中生存下去了。这一自然景物在补白性描写,突出地体现了塔尔柯夫斯基对视觉造型艺术根本特点的深刻把握,用简洁的画面,形象的造型,合理合情而又自然熨贴地完成了对人物命运最终结局的描叙。
作为银幕诗人的塔尔柯夫斯基,才气横溢,在景物的选配摄录中,几乎达到了呼风唤雨,自由抒写的境界。借景生辉之象,随处可见。风、雨、火、水等大自然生动的原色,在塔氏的镜头中,无不散发出浓厚的诗情。《安德烈·鲁勃廖夫》的第一个镜头,大片的荞麦田里,秋风吹拂,麦波荡漾。接着原野上罡风骤起,麦浪翻滚,随着昂奋的音乐旋律,一阵瓢泼大雨由远而近奔袭而来。风雨声中,传来一个男中音的画外音:“谨以此片的开端,献给亲爱的妈妈!”乡野,大地,村落,是童年时的安德烈同他亲人们蛰居过的地方。那里留着他诗一般美丽的记忆。乡村,被塔氏视为心目中的真正故乡。蓬勃成长期的荞麦,更为他母亲所喜欢。他们总爱静静地伫立于麦田旁土埂上,领略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当塔尔柯夫斯基在摄影机前再一次面对这一切时,他情动于衷地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妈妈,那骤起的风是他激荡的情感,那如注的雨是他翻腾的心律节奏。风与雨,在这里染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自然的风雨成为情感律动的载体,“景语”成了“情语”。我国古代居士吴衡照说过:“言情之作,必借景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⑧此处的风雨,用得深宛流美,出神入化,不失为借景抒情之范例。
在塔氏的景物拍摄中,那流淌着的河水,也都会因情境不同而染上不同的色泽。伊凡回忆童年时光的小河,是一条充满欢乐与幸福的彩色的河;他牺牲后出现的林边小河,则近于墨色,毫无生气,变为死亡的征兆。同是森林,小桦树林,显现出清新与快乐的氛围,“暗沉的云杉林”,则预示着不祥事端的将出现。《索里亚里斯》里的暴雨、树林、老屋,也都带有主人公克里斯·科文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及不堪往事的忏悔色调。这里,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表情达意,塔尔柯夫斯基都能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融情于景,化意入事,布设自然,意味醇厚,集中体现了银幕诗人对诗电影的探索所作的有益贡献!
注释:
①A.塔尔柯夫斯基《用时间雕塑:对电影的思考》
②F.弗尔达姆《荣格心理学导论》
③A.塔尔柯夫斯基《为了崇高的目标》
④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⑤查希里扬《银幕的造型世界》俄罗斯《文学报》1992年4月22日
⑥钱钟书《谈艺录》
⑦陈洵《海绡说词》
⑧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