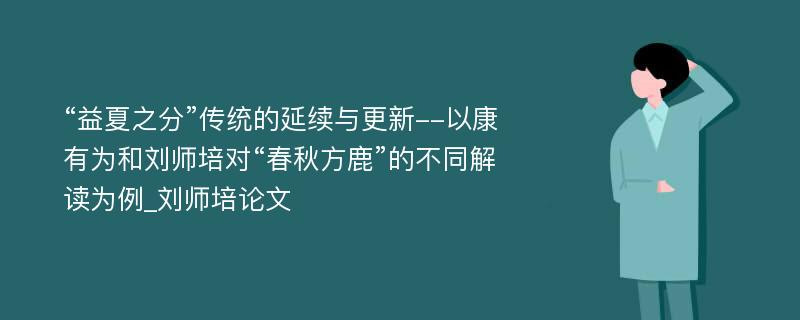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春秋论文,康有为论文,传统论文,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戊戌维新前后到辛亥革命之时,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变动最剧烈、纷争最多的时期之一。其中,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因关涉中国的基本走向而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在这一讨论中,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命题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夷夏之辨”命题所进行的讨论,确也促进了当时的政治革新和思想更新。所以,这一问题非常值得关注。①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一个极小的个案入手,通过考察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两事的不同解读,分析“夷夏之辨”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力求由此对当时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希望由此出发,将政治思想的分析与对思想背后的学术资源的探讨结合起来,使思想史研究的蕴涵更为丰富。
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董仲舒说:“《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②“晋伐鲜虞”事见《春秋》昭公十二年经。鲜虞属白狄,但为姬姓,与晋侯同姓。晋本为中国(华夏)诸侯之一,经中通例提及时是要“连国称爵”的,这里单言一“晋”字,是予晋国与夷狄一体看待,表达了对晋伐鲜虞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出现,在董仲舒看来,是因晋之所为不合“尊礼而重信”的“《春秋》大义”,“礼而信”方为“天下法”,诸夏共遵之,否则就流于夷狄了。
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董仲舒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③“邲之战”事见《春秋》宣公十二年经。邲属郑地。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伐郑,击败郑军,郑国君肉袒投降,庄王应允。此时,晋大夫荀林父率领救郑的军队到达,请与楚国作战,庄王命楚军迎战,在邲地击败晋军。董仲舒认为,《春秋》记事之通例是“礼”仅予中国(华夏)而不予夷狄,但记“邲之战”事,却偏偏相反,将“礼”予夷狄(楚)而非予中国(晋),这是因为楚不取郑地,“有可贵之美”,其行合“礼”,而晋之所为“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故“不使得与贤者为礼”。在《春秋繁露·观德》中,董仲舒再次表达此意:“《春秋》常辞,夷狄不得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夷狄反道,中国不得与夷狄为礼,避楚庄也。”④
对于《春秋繁露》所言“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两事,康有为在1897年刊行的《春秋董氏学》中有所评价。《春秋董氏学》“夷狄”条中,有署名弟子徐勤的按语,可以体现康有为的基本看法。文中引述《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晋伐鲜虞”的事例后,所加的按语指出了划分夷与夏的标准:“《春秋》之义,尊礼、重信,故能守乎礼、信则进之,违乎礼、信则黜之,其名号本无定也。‘晋伐鲜虞’与此相背,故拟诸夷狄。”⑤即在康有为师徒看来,依据董仲舒的思想,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守“礼”和“信”。在这一标准下,背信弃义的晋国虽为华夏,但已堕落为“夷狄”。⑥《春秋董氏学》“夷狄”条在引述《春秋繁露·竹林》和《春秋繁露·观德》中“邲之战”的事例后,分别加按语说:“《春秋》无通辞之义,《公》、《穀》二传未有明文,惟董子发明之。后儒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无董子,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⑦“泥后儒尊攘之说,则当亲者晋,不当亲者楚也,何德之足云?不知《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⑧这两段按语集中批评了主张严“夷夏之防”的“后儒”们,如宋代大儒孙明复、胡安国等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其实未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夷夏观,而且在现实中造成严重后果,罪莫大焉。此外,康有为师徒强调,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德”,“《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
综合来看,康有为通过阐发董仲舒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夷夏观颇为明确,即以是否遵守“礼”、“信”、“德”作为准绳,遵之即为“夏”,不遵则为“夷”。依照当今的概念,这样的标准实为文化标准。依此标准,“夷”与“夏”其实是可变的,“夷”若按“礼”、“信”、“德”行事,可被视为“夏”;“夏”若违“礼”、“信”、“德”,则可视为“夷”。这样,“夷夏之辨”就成为了“夷夏之变”。董仲舒乃西汉经今文学之宗师,康有为是清末以今文言政的大家,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今文学派在夷夏观方面的主流看法。
与康有为见解相异的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刘师培。作为清季著名的革命派学者和民族主义者,1907年前的刘师培致力于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寻求思想资源,以利于排满兴汉,实现革命目标。⑨为此,他极力宣扬《春秋》严“夷夏之防”的微言大义,说:“《公》、《榖》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吾思丘明亲炙宣尼,备闻孔门之绪论,故《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⑩即《春秋》三传之旨皆为“严华夷之界”。
对于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刘师培同样予以较高评价。在1905年发表的《两汉种族学发微论》中,他认为最能体现“夷夏之辨”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惟《公羊》大义,朗若日星”。于汉代最能传承这种思想并光大之的学者,当为董仲舒,“董子《繁露》,翼辅《麟经》,于晋伐鲜虞,则讥晋人之同狄;于晋败于邲,权许楚子之称贤。又谓《春秋》常辞,不予夷狄(见《竹林》篇)。则华夷大防,董子曷尝决其藩哉?”(11)同样是以“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为例,谈董仲舒《春秋繁露》所反映的夷夏观,但所表达的见解与康有为截然不同,不讲遵守“礼”、“信”、“德”之为“夏”,强调的是“《春秋》常辞,不予夷狄”,认为董仲舒也是讲“华夷大防”的。在《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一文中,刘师培亦谈及《春秋繁露·竹林》关于“邲之战”的议论,认为“夷狄乱华,是董子最伤心的事情”。“董子的宗旨,还是主张攘斥夷狄的,还是主张不共夷狄同化的。如若共夷狄同化,就连中国也带坏了,不可是中国顶大的羞辱么?后世的人,多以土地分华夷,说中国以外的人种,全是夷狄;夷狄进了中国,也同中国一般。所以,不晓得邦交的道理,也没有攘夷的宗旨,这真是不懂董子的学术了。”(12)
实际上,《春秋繁露·竹林》既讲“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的“《春秋》常辞”,也讲“《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而且强调的是后者,看重的是“从变而移”。刘师培仅强调“《春秋》常辞,不予夷狄”,将董仲舒文的宗旨,界定为“攘斥夷狄”,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充分反映出他其实是借古人之言,表达自身的严“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观念。
康有为、刘师培都是清季的经学大师,他们对《春秋繁露》中“邲之战”和“晋伐鲜虞”两事的理解,与他们的经学修为密切相关,体现出经学系统里“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梳理一下原始文献和康、刘以前的相关解说。
《春秋繁露》是解读《春秋》的著作,其所议之事无不关联《春秋》及其三传,所以首先需考察《春秋》三传对“邲之战”和“晋伐鲜虞”的记载。
在《春秋左传》中,对“邲之战”和“晋伐鲜虞”皆有客观记录。关于“邲之战”,记曰:“经:十有二年(鲁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传”则对“邲之战”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13)关于“晋伐鲜虞”,《春秋左传》记曰:“经:十有二年(鲁昭公十二年)……冬,十月……晋伐鲜虞。”而其“传”则仅言“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14)
在《春秋公羊传》中,对“邲之战”有以下描述:“(鲁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曷为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曰:‘寡人无良,边垂之臣,以干天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使帅一二耋老而绥焉,请唯君王之命。’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庄王亲自手旌,左右撝军,退舍七里。”(15)而“晋伐鲜虞”,《公羊》有经无传。
在《春秋穀梁传》中,对于“邲之战”的记载,同于《左传》之“经”。对于“晋伐鲜虞”,则曰:“冬,十月……楚子伐徐。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16)
董仲舒是西汉景帝时的《春秋》博士,主公羊学,他之解读《春秋》,自然取《公羊传》之微言大义并发挥之。与此同时,从他对“晋伐鲜虞”的解读看,与《穀梁传》也不无关系。(17)《公羊传》对“邲之战”的描述,其核心在于说明“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的《春秋》微言大义;董仲舒则解说因邲之战时,“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的“《春秋》之常辞”,才“偏然反之”。《穀梁传》对“晋伐鲜虞”的记载,关键是要说明《春秋》仅曰“晋”,不“连国称爵”,是将晋与夷狄同等看待;董仲舒则有发挥,认为《春秋》将晋视同夷狄,是因“《春秋》尊礼而重信”,晋伐鲜虞,礼、信俱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已等同于夷狄。
董仲舒之后,公羊学最主要的代表是东汉何休。在何休解诂、唐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中,也对“邲之战”和“晋伐鲜虞”做了阐发。前已言及,《公羊传》谈“邲之战”时说:“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对此,何休解诂曰:“不与晋而反与楚子为君臣之礼以恶晋。”就何休此解,徐彦疏云:“内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叙晋于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恶晋者。但楚庄德进行修,同于诸夏,讨陈之贼,不利其土,入郑皇门,而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宁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是晋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于其上?既序人君之上,无臣子之礼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恶晋也。”(18)对“晋伐鲜虞”,何休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19)从何休之言可以看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主张与董仲舒是一致的,也以是否遵“礼”、“义”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
同属今文系统的《穀梁传》的疏解者亦是抱有与董仲舒、何休相似的主张。在《春秋穀梁传注疏》中,对于“晋伐鲜虞”,晋人范宁注曰:“鲜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国。夷狄谓楚也。何休曰:春秋多与夷狄并伐,何以不狄也?郑君释之曰:晋不见因会以绥诸夏,而伐同姓,贬之可也。狄之大重晋为厥慭之会,实谋救蔡,以八国之师而不救,楚终灭蔡。今又伐徐,晋不纠合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鲜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称之焉。”(20)此言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之晋其作为尚不如“夷狄”之楚,所以晋可称“狄”,亦即夷夏之位可互换。
上述今文学者对“邲之战”和“晋伐鲜虞”的解说,到清代仍为经学家所认同。如孔广森对《公羊传》所言“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做了以下解读:“言不以晋人为直而善楚子为有礼也。林父录名氏反为不与晋者,庄王之师进以义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轻取败衄,中国遂衰,故特出主名,专见其罪……董生言:《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辞,城濮伯莒已明,故于此得变文以托别义。”(21)对于“晋伐鲜虞”,孔广森评论道:“晋为诸夏盟主,楚剪覆姬宗,坐视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称国狄之,《春秋》特于此责晋之甚者。初,楚人为申之会,请诸侯于晋,晋弗敢竞,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国,放乎灭陈、蔡者,晋君臣为之也。苏辙曰:楚灭陈、蔡,而晋不救,力诚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鲜虞,而不救陈、蔡,非力不足也,弃诸侯也,故以夷书之。”(22)这些议论,所强调的还是“礼”、“义”、“仁”、“信”等“华夏”诸国本应遵守的信条,如若不遵,则“华夏”转而为“夷狄”,晋即因此而被视为夷狄。可见,今文学者一脉相承,始终坚守夷夏之别的文化标准,认为《春秋》大义在此。
作为清季今文学者的代表,康有为的夷夏观显然是延续了历代今文学者的主张,其对《春秋繁露》中“邲之战”和“晋伐鲜虞”的解说,无非是一个显例而已。他还曾明确说过:“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春秋》之义,夷狄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其许楚庄入郑是也。中国而为夷狄之行,则夷狄之,卫伐凡伯、晋伐鲜虞是也。惟德是辅,故董子曰:‘中国、夷狄无恒,随变而移。’由文明而野蛮,下乔木而入幽谷也。由野蛮而文明,出幽谷而迁乔木也。滕文公行仁政,而各国志士负耒受廛,可知民心之归仁。今欧洲各国之人,多迁于美国,德、英欲极禁之而不可得,亦可见滕文公得民之盛矣。”(23)这样的言论,清晰地表达出康有为继承先辈学说而又与时俱进的特点。
相对而言,《公羊传》、《穀梁传》及其注疏对“邲之战”和“晋伐鲜虞”的解说较为完善,而《左传》除客观记录外,对此少有解说。在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晋伐鲜虞”条下,疏云:“正义曰: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定四年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二者皆书将帅,此独不书将帅,知是史阙,或是告辞略史阙不得书,亦得言史阙文也。穀梁曰:其曰晋,狄之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贾、服取以为说。左氏无贬中国从夷狄之法,传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又曰:间携二覆,昏乱霸王之器也。鲜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诸夏,不事霸主,伐而取之,惟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讨夷,反狄中国?从此以后用师多矣,何以不常狄晋更复书其将也?杜以其言不通,故显而异之。”(24)这段话表明,注疏者认为《左传》记载“晋伐鲜虞”一事不合其书常例,疑史有阙文,而且强调“左氏无贬中国从夷狄之法”,不赞成《穀梁传》“其曰晋,狄之也”的说法,显示出立异于今文经学的态度。
作为四代传经、长于左氏之学的学者,刘师培当然熟知左氏之传、注、疏,并极力从《左传》中寻求严“夷夏之防”的证据。他说:“左氏亲炙孔门,备闻宣尼之绪论,故《左传》一书,斥杞子之从夷,先晋人之有信,辨别华戎,大义凛然。及贾逵、服虔诠释传文,而进夏黜夷之谊,隐寓其中。天王天子,夷夏殊称,则华夷殊等,典礼不同,彰彰明矣。即外楚外吴,亦含屏斥夷蛮之旨……攘夷大义,咸赖贾、服而仅存。此左氏之微言也。”(25)实际上,仅就“晋伐鲜虞”而言,贾逵、服虔所申言之夷夏观乃取《穀梁传》之说,并非遵《左传》之辞。而刘师培看重贾、服之注,一个重要意图是强调古文经学家对阐发《左传》“攘夷大义”所起的作用,由此,某些细节甚至可以忽略。不仅如此,为了申言“夷夏之辨”,刘师培把今文学大师何休也塑造成严“夷夏之防”的学者,说:“邵公(何休字邵公)《解诂》,于内外之别诠释详明,而戎伐凡伯,排斥尤严。以中国为礼义之国,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则文物之邦,岂可屈从于蛮貉乎!推之贬邾娄为夷狄,美鲁庄之追戎。于吴会黄池,则嫉诸夏之事夷。于荆败蔡师,则愤华夷之入伐。驭外之心,至深且密。”(26)这里仅是强调何休严于“内外之别”,“驭外之心,至深且密”,而于何休据“礼”、“义”标准区分夷夏、故夷夏位置可变之说,却忽略不提,显然是出于自身论点的需要。
至于对“晋伐鲜虞”和“邲之战”的解说,认为董仲舒也是据此讲“华夷大防”,恐怕系刘师培的一个创造,属“夷夏之辨”解说传统的更新。因刘氏所传承之《左传》及其注疏并无此类说法,就连康有为所指斥的“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的宋儒孙明复、胡安国,在谈及“晋伐鲜虞”时,亦是强调“天理”、“信义”在区分夷夏时的作用(27),而非由此大讲“华夷大防”。在“夷夏之辨”问题上,刘师培与孙明复、胡安国最为合拍,但刘氏解说“晋伐鲜虞”,与二人却不一致,这更可见出刘氏不依前人之创见。
围绕《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两事,康有为、刘师培分别做出自己的解读,其不同主张的背后,自然有其传承的解经传统和所倾向的经学流派的因素。不过与此同时,两人所处的时代语境亦发挥了制约作用。
清季,维新保皇和反满革命共同构成政治上的一大景观,围绕此二者,不同立场的人们争执不休,而且政治主张往往关联着学术见解,经学纷争也就因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作为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力主满汉一体,历代今文学者的夷夏观恰给他以学理上的支持;而作为革命派的骨干,1907年前的刘师培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排满兴汉是其首要政治目标,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自然成为其取法的资源。
自从清朝统治建立后,其合法性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多以“夷夏之辨”为由,质疑或反抗其统治,而清廷也搬用历史上夷夏位置可变、“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证据,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并采用或笼络、或镇压的各类手段来巩固这一合法性。“遗民不世袭”,渐渐地,士人与朝廷形成共识,不再对立,也不再对清廷以“夷狄”视之。鸦片战争前后,“夷”之称呼已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但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排满革命风潮的兴起,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夷狄”再度成为满人的指称。而坚守保皇立场者,则力证满人已非夷狄,而是华夏一体化的成员了。在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康有为曾就此指出:“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故晋伐鲜虞,恶其伐同姓则夷晋矣……国朝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28)与之相反,刘师培认为“夷夏之辨”是百世不易之理。在1904年的《致端方书》中,他说:“孔子有言,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想亦尔之所悉闻也。自满洲肇乱,中原陆沉,衣冠化为涂炭,群邑荡为邱墟,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毡腥之壤,盖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光汉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垂髫以右,日读姜斋、亭林书,于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29)其视满人为“夷狄”,从事排满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与此同时,和保皇、革命等政治风潮相交织的,是思想学术领域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西方思想对当时学界冲击之大,使得学者们在处理思想学术问题时难免要倚之为利器。关于“夷夏之辨”的论争,实际就关联着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
这一时期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对此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以血统、种族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二是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前者与欧洲19世纪强调血缘关系的“族群民族”(Ethno-Nation)理念分不开。这一理念的传播,使得民族与国家应融为一体、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颇为盛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赫尔德说:“最自然的国家,莫过于具有一种民族特点的一个民族……把一百个民族硬捏在一起并由一百五十个省份组成的帝国,决不是个政体,而是一个怪物。”(30)这实际主张的就是国家由单一民族组成,一民族一国家。这样的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流传,对革命派知识分子产生较大影响。1903年,《浙江潮》发表的《民族主义论》说得很直接:“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31)并主张“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32)后者在西方政治学界也颇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传至中国。如伯伦知理的理论,认为文化因素(语言、文字、风俗等)比血统对一个民族的形成更重要,所以一些不同血统但文化相同的民族,可以联合在一起,建立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理论,为梁启超等人所广泛接受。梁启超曾引用伯伦知理“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强调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33)并由此提出他的“大民族主义”,认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34)实际上,“大民族主义”的建国主张,也就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主张。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两种不同趋向,自然反映到当时革命与保皇两派的政治论争中,刘师培和康有为也是各取所需。刘师培在一系列论著中阐发他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他曾力证满族(人)不属中国,为“排满建国”的合理性辩护。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他说:“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俱]在,固可按也。”(35)当然,他也深知满族统治者与普通满人的区别,所以强调排满是为夺取政权,即“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统治权。民族主义即与抗抵强权主义互相表里,固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辨不同也。使统治之权不操于满族之手,则满人虽杂处中国,亦无所用其驱除。”(36)也就是说,他所努力奋争者是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汉族统治的国家,此即他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为此他曾专门言道:“凡一族之人民,必有特立之性质……合数国而同一种族,则数国可并为一国(如德意志联邦是);合数种族而为一国,则一国必分为数国(如土耳其各小国)。”(37)很显然,他所认同的是以血统、种族之别为根基的民族主义,实际是种族民族主义。他还用此来强化“夷夏之辨”,说:“三代之人,无人不明种族之义。盖邦国既立,必有立国之本。中国之国本何在乎?则华夷二字而已。上迄三代,下迄近今,华夷二字,深中民心,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言于孔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言于季文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言于管夷吾。故内夏外夷遂为中国立国之基。汉儒之言,亦即此意。日本倡攘夷之说,始知排外。中国倡攘夷之说,始知开边。”(38)这段话表明,“夷夏之辨”为立国之本,讲求的是种族之分。
与刘师培相较,康有为对种族问题大多时候抱有较开明的态度,尽管有时也讲种族之别。1879年,他“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39)从此,他认为不能再对西方人“以古旧之夷狄”的传统观念看待。但在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他则警告说:“西人最严种族,雠视非类”,并以法国殖民越南和英国殖民印度为鉴,强调“吾神明之种族”必须及早为计,免蹈覆辙。(40)在其影响下,弟子梁启超等人也在此时倡导过种族之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周游列国,了解了更多的西方政治、民族、国家学说,就很是不以种族之别为意了。他明确反对以种族区分中国与夷狄,说:“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故中国、夷狄无常辞,从变而移。当其有德,则夷狄谓之中国;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狄。将为进化计,非为人种计也。”(41)即中国与夷狄,仅是进化程度之分,非为种族之别。所以,他反对一些革命党人排斥满人的单一民族国家论,主张“合满建国”,说:“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苟汉之于满,割而为台湾,亡而为印度、波兰,则必不得政权平等自由之利,是则可忧也。”(42)这样的论调,当然是为反对排满革命服务,但不能不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与“大民族主义”相合。
正是出于上述差异,在解读《春秋繁露》“晋伐鲜虞”和“邲之战”时,康有为和刘师培的态度有所差别。康有为延续了以往今文学者的解说,其辞相合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某些理论,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刘师培的解说则较少依托经学传统,甚至有强为之解之嫌,但亦相合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某些理论,具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这表明在“夷夏之辨”问题上,两人依托传统的程度不同,结合新知的方向亦不同。中国传统特别是经学传统错综复杂,两人又有不同的学派背景,加之西方新知亦是错综复杂,故对其各取一端,以之与本人的经学修为结合,自会得出相异的结论。
平心而论,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虽也涉种族之别,但核心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夷夏之辨”最初出现时,人们主要是从族类差异来区别夷夏的。所谓族类差异,既指人种之别,也包括地域、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等的差异,而且后者渐居主导。人们认为华夏诸国在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都高于、优于夷狄,华夏乃“礼仪之邦”,而夷狄则“被发左衽”、未臻开化。孔子虽也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重族类差异,但更强调“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即以礼(文化)来区分夷夏。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提出“用夏变夷”,强调“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即只能用华夏文化改造夷,绝不可能以夷变夏。此种“夷夏之辨”,已超越种族、血统等因素,而视文化因素为最高认同符号,其所体现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精神。就此而言,康有为对《春秋繁露》“晋伐鲜虞”和“邲之战”的解说应属正解。而刘师培的解说虽有新意,但于学理有亏,更多是出于现实应用目的。因为对于“夷夏之辨”关键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可以“用夏变夷”,刘氏并非全然没有认识。他曾指出,“用夏变夷”的提出,是因孔子认识到世界总有文明普及之日,“使无礼义者化为有礼义”,“特以声名文物非一国所得私,文明愈进则野蛮种族愈不能常保其生存”。但是目前“据此以荡华夷之界则殊不然”。(43)也就是说,谈“夷夏之辨”时强调种族之别是时势所需,是排满斗争的需要,而文化上的“用夏变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目标,两相比照,刘师培更重视眼前的政治目标,所以更强调种族之别。
进而言之,一向被视作“以经术作政论”、甚至被刘师培“开除”出学者队伍的康有为(44),在“夷夏之辨”问题上倒是基本依遵今文学统,以正统今文家说作为自身思想观念的依托。而一直为学谨严、以“学术持平”“不主门户”理念治学的刘师培,却在这一问题上不那么谨遵学统,显示出更多的变通。这表明在学者那里,思想观念源于学术资源虽可作为一种通例,但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一旦出现特殊情形,则有变通的空间。对刘师培而言,坚守“夷夏之辨”立场,相符于排满革命的最高政治目标,所以就要在解说经典时做些更新,姑且“以经术作政论”。而康有为在“夷夏之辨”问题上的表达,虽合于学统、学理,但只是因为固有学术资源和他的现实理念乃至政治策略恰巧相符罢了。这仅是一个案,不能据此说他整体上摆脱了“以经术作政论”的为学理路。
注释:
①近年来,学界对清季民族国家认同讨论中“夷夏之辨”命题的表现、地位、作用以及康有为与刘师培之“董氏学”等问题已有所研究,如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曲洪波《刘师培与康有为“董氏学”研究之比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等论著,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探讨,但以宏观论述为主,相对缺少从个案入手的细致分析,尤其疏于对思想命题背后的学术资源的探究。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袁长江等校注:《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
③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董仲舒集》,第60页。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观德》,《董仲舒集》,第215页。
⑤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
⑥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康有为评论“晋伐鲜虞”时,又说:“不能拯中国之弱,乃自伐同姓,此野蛮之行,即以文明为敌,故以晋为狄也。能守礼信则为中国,违礼信则为夷狄,名号本无定也。”(《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康有为1901年董理旧作而成,其中夷夏观方面的主张仍同于《春秋董氏学》,可见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戊戌前后没有变化。
⑦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14页。
⑧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15—416页。另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康有为又说:“后儒尊攘之说,则当亲者晋,不当亲者楚也,何德之足云?不知《春秋》之义,中国、夷狄之别,但视其德。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后儒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胄,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义,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179页)这段话显然是将《春秋董氏学》引述《春秋繁露·竹林》和《春秋繁露·观德》中“邲之战”的事例后分别所加按语,重新组合而成。
⑨按:1907年起刘师培在思想观念上转向无政府主义。
⑩刘师培:《读左札记》,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93页。
(11)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3页。
(12)刘师培:《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416、417页。
(1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23卷,《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878-1883页。
(1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23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61、2064页。
(1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84-2285页。
(16)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第17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36页。
(17)有学者认为《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联系极为紧密,是西汉时人“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为《穀梁传》”。参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1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84页。
(1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20页。
(20)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第17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36页。
(21)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第7卷,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5849页。
(22)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第10卷,《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5册,第5879页。
(23)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2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23卷,《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61页。
(25)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3页。
(26)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3-534页。
(27)在《春秋尊王发微》中,孙明复说:“直曰晋伐鲜虞者,楚灵不道,殄灭陈、蔡,晋为盟主,既不能救,其恶已甚。今又与楚交伐同姓,无复天理之存矣,故深恶之。”(《春秋尊王发微》第1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春秋传》中,胡安国说:晋伐鲜虞“是中国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春秋传》第25卷,四部丛刊续编本)
(2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7页。
(29)刘光汉:《致端方书》,《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第110页。
(30)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第16页。
(31)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1903年,第3页(文页)。
(32)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2期,1903年,第11页(文页)。
(3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3-75页。
(3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35)韦裔(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8日,第1页(文页)。
(36)韦裔(刘师培):《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民报》第18号,1907年12月25日,第22页(文页)。按《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连载于《民报》第14、15、18号,但自15号起,题目为《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与14号标题有一字之异。
(37)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3页。
(38)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2页。
(39)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3页。
(40)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89页。
(41)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7页。
(4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9页。
(43)刘师培:《攘书·夷裔篇》,《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1-632页。
(44)刘师培大体不把康有为视作学者,他基本不与康氏讨论学术问题,其驳斥康说的文章多属政论,如《论孔子无改制之事》、《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等;而且刘师培也不认为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传承人,他回顾清代今文经学演进历程的论著讲到同时代的王闿运、廖平等人,却根本不提康有为,如《近儒学术统系论》、《近儒学案序》、《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