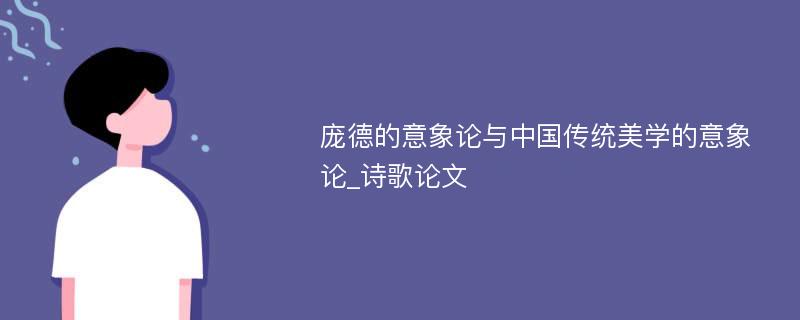
庞德的意象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庞德论文,中国传统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057-07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古典的、现代的文化产物空前丰富地涌入,学术界乃至民间,人们接触到一个个“新鲜”而又“陌生”的理论术语。在其中,以意象派名义曾在西方诗坛轰动一时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1885-1972)等人的作品被再次译介入中国,并引起了许多青年诗人、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意象”在人们心目中,仿佛有一种“舶来品”的意味,比如自3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在美学上谈意象,梁宗岱、艾青在诗论中论意象,所用一语,大抵是西方'image'一语的转译”[1](328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在当今东西文化相互交流空前频繁的情况下,人们对异质文化热切关注是应当的。但是如果重新审视与回顾“意象”这个问题,就应当梳理一下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象派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意象说的关系,以利于我们与世界之间有更好的认识与交流。
本文拟从庞德的意象论诗艺主张及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意象说的内涵,庞德的意象论与中国传统意象说的重合与差异之处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
与其他现代派文学一样,“意象派”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在它们的背后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尤其是近现代的工业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给人们传统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压力。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压抑在人们心中,西方世界成为一个失去信仰而弥漫着幻灭的精神“荒原”。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着文学的嬗变。作家们虽然在精神的“荒原”上迷惘、痛苦,但又寄希望于新的文学形式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各种现代派文学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应运而生。
就欧美诗歌而言,一向以英国为传统,但这些传统诗歌已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痛苦不相吻合。曾经产生过济慈、华兹华斯等优秀诗人的英国诗坛,此时却充斥着矫揉造作之风,庞德据此批评道:“自由体诗确实象它以前任何一种弱无力的诗歌一样,变得冗长、噜苏。……就如我们的前辈们,甚至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也堆砌大量词汇,以填满格律,或完成一种‘韵律——声音’的噪杂。”[2](421页)因此,作为对传统的一种反拨,也是对西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上的反映,1908年前后,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以庞德为首的西方诗人们,发起了一场旨在改变英国维多利亚王朝颓靡诗风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1912年,庞德与希尔顿·道利特尔和奥而丁顿讨论了意象派诗歌的原则,并在1913年第6期的《诗刊》上发表了意象派的纲领,主要有三条:1.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2.决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没有作用的字;3.在韵律方面,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3](107页)。1914年,经庞德的努力,《意象主义者》诗集出版。从此,意象派诗歌在英美诗坛上激起强烈反响,成为阵容强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派别。虽然其存活时间仅仅只有1914-1917年的四年时间,但其诗歌的主张和纲领仍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在我们看来,理解意象派提出的“意象”是了解意象派的诗学主张的关键。庞德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表现的是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3](108页)他还进一步解释道:“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4](251页)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解释:“意象”是一种“复合体”,它内在包含着作家对生活理性的认识和感情的体验,这“认识”和“体验”是构成“意”的两个因素,它们是纠合在一起的,成为“一堆”或“一团”,并且是相互交融,而不是生硬的牵强杂揉。而这情、理的“复合体”,又需要“象”(形象)来呈现,而且是“一刹那间”的呈现。庞德对这种“象”(形象)的要求又是要“精确”的。他认为,应该是“准确的物质关系可以象征非物质关系”[4](251页),认为优秀的艺术应该是“精确的艺术”,“拙劣的艺术不是精确的艺术,是制造假报告的艺术”[4](257、256页)。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那样:“意象是包含着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性与感情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两层缺一不可。”[5](21页)因此,以瞬时呈现且精确的“象”(形象)作为情绪、情感的“对应物”,应是庞德的意象理论的真正含义所在。
在诗歌的形式和韵律方面,庞德等意象派诗人主张力求用简洁、朴素、准确和浓缩的语言来体现鲜明的“意象”,含蓄地表达为上乘之作,要尽量排除主观的评价和侧面的烘托渲染,就是“不要用多余的字句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的形容词”[3](109页)。在韵律的安排上,也要以自然为上,不硬凑韵脚,“韵律结构不应当损害语言的形式,或自然声响,或涵义”[3](120页)。
必须指出的是,意象派的诗学纲领和主张,同其他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一样,都深深地刻下了时代的烙印。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观,强调“无意识”及直觉主义等等,乃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否定。事实证明,那种在艺术上持“直接处理”“主观或客观”事物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那种“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的主张,就颇具非理性主义的意味。具体而言,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构成了意象主义诗歌的哲学基础。
享利·柏格森(1859-1941)是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可以说,他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比叔本华、尼采等更为直接。他认为艺术家可以“凭直觉的努力,打破了空间设置在他和他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直觉却能使我们抓住智力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并指出提供这种东西的方法”[6](87页)。这些观点,启发和影响了意象派立足于内心,以直觉的方式处理现实物象与自身的情感、认识。柏格森进而论述到:“倘若我们是几何学家,我们便否认有不可预测的事物。倘若我们是艺术家,那么无疑地,我们也许可以接受这一点——一个不可预测的形式的创造。”[6](85页)现代派艺术家向内观照自己心中的激情和感受,向外靠心理本能去神遇一瞬间的印象和幻觉,从而与对象的生命之流撞击交融,这种认识和表现方法明显地深受柏格森的影响。回顾庞德的意象论,首先在对“意象”的阐释时,庞德强调的就是主体思想或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并在这种近似无预期目的的情形之下,瞬间生成;同理,就读者而言,也只有通过刹那间的直觉,对作品才有所领会。柏格森以阅读小说为例,描述当他读到主人公的种种行为和说话时的情景:“这一切根本不可能与我在一刹那间与这个人物打成一片时所得到的那种直截了当、不可分割的感受相提并论。”[6](82页)正如庞德所言,意象“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解放的感受;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一种我们在面对最伟大艺术品时经受到的突然长大了的感觉”[3](108页)。因此庞德清楚地坦陈他的诗歌理想:“它一定会变得较为坚实,较为清醒。……质朴、直率,没有感情上的摇曳不定。”[3](120-121页)显而易见,意象主义的意象论观点,意象派诗人及评论家对意象的看法,均直接受到了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
但必须指出,意象派的“现代”特色,已使它的哲学、美学基础呈现出多元复合并具有跨文化圈的色彩。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和仿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这种来自另一异质文化圈的文化魅力,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W.S.温默所说的那样:“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无法想象。”[7](130页)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学风格上表现出来的清新、简洁与凝炼,正如艾肯当时所说:“给了辩论的对方——矫揉造作的诗风,以慈悲的致命一击。”[7](133页)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主义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把它作为反拨陈旧的“感伤”与“做作”的19世纪的英国诗风的一种支持与武器。其次,由于中国诗歌在欧美诗坛的呈现是通过庞德等人的翻译与介绍的,因而难免不发生有意无意的误读现象,这就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成为庞德意象论的思想资源时发生了变异。例如中国古典诗歌中本身具有朴素、准确、浓缩的语言形式的一面,被庞德等人看作了整个中国诗歌语言的全貌。他们在翻译中的刻意求简,又常常将“典故”等一一略去。这样一来,中国诗歌语言被意象派强调的一面,成为了他们学习的范本和追求的新的诗歌语言的最高境界。因此,许多意象派诗人的作品在发表之前,都有意的压缩字句,均呈现出一种短小、精炼的特点。
二
在我们分析了庞德意象派的诗学主张及其“意象论”的内涵之后,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国传统文论与美学中的“意象”说。其实,在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里,意象是一个古老的范畴,它早于“意境”而生成,其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与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它带着浓厚的中国民族文化底蕴,而非简单的西学中由"image"转移而来的那个“意象”名词所能涵盖。
首先,在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中,意象的具体含义有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意中之象,可理解为“人心营构之象”[8],即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体的审美特性的有机统一。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9](《神思》),司空图在《诗品·缜密》里提到的“意象欲出,造化已奇”[10](《缜密》),其中的“意象”,实际上就是“人心营构之象”,就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在对外物的观照之后,于内心生成的意象。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郑燮《题画》中有云:“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11](161页)这里,此竹非彼竹,何也?就是客观的竹已在画家心中意化为审美的竹,形成了意象。所谓“成竹在胸”之称,也是艺术家头脑中营构出的意象。第二,意象指艺术形象,特别是在明清的文艺理论中,普遍被采用来评论诗歌、绘画和书法创作。李东阳《麓堂诗话》中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12](1372-1373页)胡应麟在《诗薮》中亦有:“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13](内编卷二)这些诗评家们无一不是把是否具有意象、意象是否生动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的。第三,还有以意象指自然景物的形象的。如唐岱在《绘事发微·游览》中所说的:“逸品者,亦须多游。寓目最多,用笔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浓粹者,间一寓于画。”[14](39页)最后,还有以意象指人物的风度神态的,《清波杂志》:“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簏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萧洒……。”[15](338页)
诚然,如果追溯一下“意象”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不难发现,其早在先秦时代就提出来了。《周易·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6](391页)这里的“象”指卦象,也可泛指一切可见之征兆,这里的“意”是指卦象或事物所包含的意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还有“圣人立象以尽意”,“夫象者,出意者也”,“意生于象,故可寻象以观意”[17](609页)之言。值得注意的是,意与象此刻虽还属两个词,但其联系与统一的特点也十分明显。王弼之观点实质,也是指可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形象,传达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意义。最早把“意象”作为一词使用的是王充,他在《论衡·乱龙篇》中说:“夫画布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18](248页)这里的“意象”只是指那种含有某种深度的画像。第一个将意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的是南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曾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9](《神思》)在这里,刘勰实际上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此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到“胸中竹”的中间环节,亦即意象成为了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即是第二个中介。在此,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
必须指出的是,既然意象作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有一个哲学、文化概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从中还可以发现一些更为深层次的涵义。从中国文化诞生的背景来看,先人与土地、农耕的感情非常深厚,是具有“农的概念”[19](32页)的哲学、美学思想产生的基础。农耕的社会对自然物象、天象、气象十分敏感,汉字构字以“象形”为起源;中医讲究“藏象”之说;天文历法讲究“观象授时”;中国美学以意象为中心范畴,将“意象具足”视为普遍的审美追求。就如汪裕雄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推重意象,即所谓‘尚象’……意象,犹如一张巨网,笼括着中国文化的全部领域。”[1](4页)所以,如从文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意象是一个指称范围极大、极广的概念,是物象、兴象乃至于指称道的“大象”和“罔象”的总称,几乎涉及了中国人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的方方面面。
具体说来,《老子》以一系列意象指称“道”,这些意象均可归为“大象”。《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20](二十五章)这里的“大象”即是“天地母”,意为可以人对母亲的情感体验去体悟道的功能,以母子关系的经验去意会道与天地的关系。所以,在老子的著作言论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意象”一词,但实则显示出了意象的象征、隐喻的功能。还有一类意象,只是对道的性能、功能作某一侧面的、近似的指称。如《老子》第八章以“水”喻道:“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20](八章)通过“水”的意象,人们或可把握“道”的因顺自然,处卑功高,功高而不自伐的抽象涵义。所以“执大象,天下往”[20](三十五章),“大象”(意象)成为具有可以指称形而下的世界和形而上的世界的功能。虽然道常常是不可言说,不可名达的,但通过意象或可以体悟。
庄子则更进一步对“大象”说进行了发展。他在“象罔掇玄珠”的寓言故事中这样写道: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21](《天地》)
在这里,“玄珠”喻道,“知”即指智识,“离朱”指感官,“喫诟”即“言辩”。那么经过智识的分析、解剖得不到“道”,仅限于形色的“感观”也不能得“道”,清晰、推理的言辩也得不到“道”,最后“象罔”出场了,它获得了“道”。“象罔”其为“有形而无体,为‘冥想’的产物”[22](51页)。“象罔掇玄珠”正是庄子用以说明通过“冥想中”“有形无体”的“象罔”即意象去意会“道”的心理历程。它是物象由语言的意指作用转化为隐喻和象征,诉诸人的想象;意象进而在想象的展开中生生不息,在语言暗示功能作用之下,把人引向玄远幽深的境界,去契合不可名状的大道。这也可以说是庄子把意象作为一种获得大道的途径和手段。通过意象去体道,庄子称之为“独与道游”[21](《山木》)、“与道徘徊”[21](《盗跖》)、“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21](《大宗师》)。那么,这“游”的最高境界就是“逍遥游”。到此,明显可见,老子之“大象”是体悟中的意象,即人经过反观内视,到达某种体验的境界。这种意象即“道之象”,经过庄子的发挥,成为对人生境界的体验的具有精神自由性的,无时空之限的逍遥之境。获取此境的途径就是上述的有形无实体的象罔即意象。这种象罔(意象)悟道的历程,它既非直接使用概念,也不仅是感悟的把握,更不是逻辑的推理,它是认知与情感的纠合,是体验与评价的同时获得。这样一种对现实物象及精神对象的态度,乃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换言之,以意象(象罔)的冥想方式,反观人生,体验人生,是中国人文化心理及艺术思维、审美方式的一种深层因素。因此,意象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术语,在进入审美领域和文艺理论后,它的指称与内涵有所变化,但仍保持着沟通形上(“道”)形下(物象)、沟通天人的功能。所以,在解读中国美学范畴中的“意象”时,绝不可如西方意象派所主张的那样,仅将它放在形式与技巧的层面去进行,而需把握它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方可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获。
三
当西方的艺术家们把目光投向东方艺术时,庞德等意象主义诗人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丰富的意象中又获取了什么呢?
首先,从“意象”这个术语来看,恐怕不仅仅是庞德自己说的那样:“我造了这个词——在休姆的基础上——认真造出一个法国也没有被使用过的名称。”[23](214页)实际上,当庞德读到曾来中国研究古典诗歌艺术的费诺罗沙的遗稿中的“汉字乃绘画之速写,一行中国诗就是一行速写画”,“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a image),一首诗就是一串意象(a sucession of image)”时,顿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24](77页)之感。可以说,庞德在以意象主义为旗帜,集聚那些志同道合的诗人们发起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时,就有在充满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获得的灵感,并揉合进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和作为其哲学背景的直觉主义,而最终才诞生了意象主义的诗学主张。
其次,就诗歌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言,他们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以意象来表达情感,排除主观评论和侧面的烘托渲染。在他们眼中,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首先就起源于其注重意象、精炼直接的艺术特点。与庞德一起始创意象派的英国哲学家兼诗人休姆就呼吁“诗人必须继续不断地创造新的意象”[23](219页)。他甚至提出诗人的“真诚程度,可以以他的意象的数量来衡量”[23](219页)的标准。
再者,就诗歌的语言而言,这方面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收的尤为明显。意象主义力求用朴素、准确、浓缩的语言来写作,并决不卖弄辞藻,诗歌语言大多源自生活,读来近似口语,这大有唐诗“清水出芙蓉”之韵味。如休姆的《日落》:“一位女芭蕾舞演员贪恋着喝彩,/迟迟不想走下舞台,/在全场不友好的嘁喳声里,/她施展出最后的魔力,/高高踮起她的脚尖,/露出了胭脂云织成的嫣红的内衣。”朴素、自然的语句,从表面看上去其句子甚至参差不齐,却因为内在“意象”的凸现,所以意味深长。是清淡而不平淡,是凝炼而不是随意的发泄。
庞德等人热情地翻译和仿写中国诗,如《神州集》中共收录了19首中国古诗,还有其他诗人如韦利的《中国诗170首》、艾米·洛厄尔与艾斯库夫人合译的《松花签》等。然而,从其译作来看,有意无意的误读时有发生。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只谈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到他们彼时的心态和需要。其误读首先就表现在意象主义者有意选择和强调了中国古典诗歌清新、朴素、凝炼的一面,以作为其对传统反拨的支持,故在翻译过程中甚至有意地避开了一些最重要的中国诗人。如《神州集》中,李白的诗章被他放弃的不少。更有甚者,译者也往往刻意求简,甚至如韦利译李煜《望江南》,就略去了“车如流水马如龙”这个比喻,以致于人们指责韦利译的中国诗读来几乎都相似。把中国诗歌意象风格单一化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无意的误读,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是语言形式、格律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一种文学体裁,讲究韵律与对仗,具有固定的模式和要求。在意象派诗人眼中,这一切都丢失殆尽,以至于当时的西方读者,可能包括庞德自己,皆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是自由诗,所以意象派诗人在批驳维多利亚传统诗风过于讲究韵律时,竟会将原本同样格律严谨的中国诗奉为无韵诗的典范。诗风的被单一化理解,典故的被忽略,格律诗样式的完全走形,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在庞德他们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显现之处。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来回答为什么把庞德的意象主义诗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论放在一起讨论的问题了,亦即要找出它们的重合之处,又要发现其差异之点。首先,最具重合意义的在于他们的“意象”皆是指主体身心受到外物刺激,客观物象经与主体内心情感、理性相纠合而生成的一种“意中之象”或“意想之象”,是情感与理智的“复合体”。正如那一日,庞德从巴黎的地铁车站走出,在拥挤、嘈杂而又喧哗的人群里,在匆忙驶来,忽又离站的地铁车辆之间,一张张不时闪现的美丽可爱的儿童或妇女的脸庞,触动了诗人的灵感,于是有了那首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在地铁车站》:“幻影一般出现在人群中的这些面孔;/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开放的许多花瓣。”作为现实人生图景的只是那嘈杂的地铁车站中种种物象,这与诗人心中含有的对都市生活繁忙、拥挤、阴冷的不愉快感受、厌倦情绪相纠合,便意化为了“湿漉漉的黑色枝条”。而诗人内心追寻美的热情又与不时掠过的可爱面孔相融合萌生出了“开放的许多花瓣”。这里没有比喻,没有象征,而就是那“人心营构之象”或“一刹那间情感与理智复合”的产物——意象。在中国古诗中不乏成功“意象”的例子,如陶渊明《饮酒诗·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作者理智的人生追求和深邃的情感的叠合。其次,意象主义诗人以写作出富有意象的诗歌为登上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庞德说过:“一生中能描述一个意象,要比写出连篇累牍的作品好。”[3](109页)这与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以意象作为衡量、品评诗歌等艺术作品的一个尺度来说也是一致的。因此,女诗人希尔顿·道利特尔的《山神》被庞德称为意象派登峰造极之作:“卷起来以,/海洋——/卷起你尖顶的松树,/将你那些大松树测泼到/我们的岩石上。/将你的绿倾泻到我们身上,/用你的松林之海淹没我们。”这首诗中,一个意象叠着另一个意象,意象重叠交融成一个新的意象。这里松涛似海,海浪又如尖顶的松树,二者融汇又和诗人内心的激情撞击,令人感到松海的猛浪中包藏着活跃的生命。再次,对意象本身的要求,中国诗学要求“虽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13](内编卷三)。这与意象主义要求“不要用多余的字句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的形容词”[3](109页)的看法,也有共同之处。孟浩然之《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20个字便写出了日暮时分的景物和传递出了人在旅途的万千感触,与桑德堡之《雾》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绝不可以把意象主义的意象论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说等同看待。如果分析其差异之处,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庞德强调意象之象是“形象在视觉想象上的投射”[23](228页)。休姆则进一步指出,诗歌意象主要是一种“记录轮廓分明的视觉形象”[23](219页)的手段,并且“这种新诗像雕塑而不像音乐,它诉诸眼睛而不诉诸耳朵”[23](219页),它提供给读者“形象与色彩的精美图式”[23](219页)。这种反复强调“视觉性”与“色彩”感的西方意象主义,已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意象有了区别。前者更专注于眼——“视觉”的感受,而中国之意象应是全身心地感受和体悟。第二,意象主义诗论中吸收了中国诗歌含蓄凝炼的特色,同时又强调其意象的“精确性”甚至提出“一门艺术的检验标准是它的精确性”[23](220页)。故而庞德被韦勒克批评为“一个天真的现实主义者”[23](226页)。这是针对意象主义对描写外物和表达内心情感都要做到真实的精确的观点而发的批评之辞。第三,由上述观点而来,意象主义同时要求使“准确的意象”成为情绪的“对等物”,这就与中国传统美学意象说以意象进入“玄远之境”,从而沟通自然与人生,可“反观”与“内视”人的精神自由的看法存在相左之处。李白《赠从弟宣州长史昭》:“长川豁中流,千里泻吴会。君心亦如此,包纳无大小。”林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这些诗作,皆含有自然生命形态和人的生命心态同构关系的自觉认识。这些也绝非是庞德以“黑色枝条”十分准确地去“对应”厌倦的内心情绪,也不是内心热情与“许多花瓣”之间的“对应”。
当我们讨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说和庞德意象主义之间的关系后,可以这样认为,意象主义作为具有多元复合性质的现代派文学,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了令其着迷并反拨陈旧诗风的支柱,但其意象论及作品与中国传统美学意象论及作品又有一些不似之处,其缘由当与以上分析中提到的中国传统美学意象论深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它可以欣赏、体验,还可以不断发展、变形,伴随着体验的不断加深,直到从中领悟出人与自然的和谐,领悟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是庞德之意象主义不能涵指的。我们可以说,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庞德对中国诗学中的意象是着迷过的,并吸收了部分因素,但由于其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之自觉和不自觉的误读,所以西方意象论只不过重在一种艺术主张、艺术手法,为20世纪西方新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收稿日期:2001-12-18
标签: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