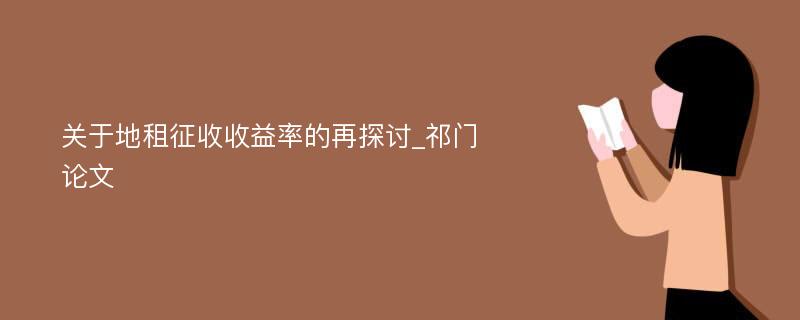
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2-0017-07
一、问题的源起
地租征收率问题,本属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范围,又因涉及面广,而成为一个及于农业生产、农村基层社会状况、农民行为、中国文化,以及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包括“典章制度”和“数据史料”二者)……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选题。
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曾是国内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近年史学学术化的发展,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针对地主经济即自然经济的旧说,提出地主经济不等于自然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某种结合;
第二,是过去认为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土地的说法,估计偏高;
第三,是关于地租率,尤其是它是否在50%以上的问题;
对于前两个问题,据说已纠正了那些过时的论点,而对后一问题,则仍在争论之中。(注:陈廷煊:“近代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关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为此,不少学者已列举出各地的各种史料(如有大量的“地租额”散见于各种文集和地方志中),今天看来,再重复这种做法,还有没有必要?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看一看地租的实际征收即“实收率”的情况?事实上,一些新的研究正是如此入手的(如章有义等)。进而言之,如果地租不是或不能做到“足额”征收,甚至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仅有那些地租额的记录,又怎能说明“地租率”的问题?看来,对所有这类问题,我们都不能只作单面的解释,就好象一个计划的提出并不等同于它的施行,也往往更与其结果有异,对一种制度也不能只看它的规定,而不看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一些租约规定:“不敢懒惰、抛荒”,“不敢少欠”,否则要“依数赔还”,“任业主别行招佃”。(注: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页47-48。)若单凭字面理解,好象上面如何定规,下面便如何办理执行似的(可惜好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其实这种事情,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恐怕都不容易办到。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处于另一方的农民的行为,这是提出农民抗租行为研究的主要原因。
对另一派重视农民起义,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的学者来说,也多少忽视了上述现象即农民日常的欠租抗租行为及其影响。“起义”或大规模的暴力反抗,毕竟不是农民经常的斗争,在“农民起义”中也很少提出土地和地租方面的要求。所以在农民的各种斗争中,抗租行为可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各种反抗中,似乎只有它才是针对着所谓“封建制度”的。也可以说,农民一直在用他们的方法悄悄地修改着制度,也许,正是这些隐蔽半隐蔽的、静悄悄的行为,在推动着历史的实际演进,和起着更大的作用?
历史上的农民到底是怎样的?应怎样认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农民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和状况?所有这些有意思的问题,恐怕也都有待于这一研究的完成。
另外应该指出,与地租率密切有关的,还有人们往往忽略了的地租“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例如,在征收所谓“正租”时,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如果考虑到这些,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点(而不是假定的50%)。(注: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年。)对于地租实收率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一个须要取得共识的“前进基点”。这类问题还有不少,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我们且把它们搁在一旁,先来考察地租的实收情况。
二、地租的实收率
了解地租征收量的升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1)以原额与实额(以及改订租额)对比;2)以租额(或最高实收额)与实收数对比;3)然后或可把它们每个都作成一个数列,并作出分阶段的对比。
1)原额与实额,以及租额修订前后的对比
中国历史上的租佃制度,除劳役租外,一向可区分为分成租与定额租(包括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清朝乾隆年间,一份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注: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八月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10。)但据对清代档案研究,定额租制也在北方流行,不过南方更为盛行罢了。据统计,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888件档案之中,实物定额租有531件,约占总数的60%,当居主导地位。(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文史哲》1984年第3期。)定额租,顾名思义即按一个事先规定的数额交租,其中一种即所谓“铁板租”(注:福建瓯宁的实例见赵冈、刘永成、吴慧、朱金甫、陈慈玉、陈秋坤:《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1995,页98。),但能够这样做到的只是少数,多数地方并不能照额征收。这是因为,首先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按原额折成交租的情况,前者称为虚额、虚租。犹如清人陶煦(《周庄镇志》附《重租论》)所说:吴农佃人之田,私租有至一石五斗之额者,“然此犹虚额也,例以八折算之,小欠则再减”;或如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所说:“照田根立券者曰虚租,有予议折实米数,不论水旱者,曰实租”;而在江西赣县等地,据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租约内虽注明缴纳足谷若干担,不得短少颗粒等语,实际上均有折扣,或七折或八折不等。(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39。)在明朝末年,据时人耿橘大说:江苏常熟田租之入,“最上每亩不过一石二斗,而实入之数,不过一石”,实额约为虚额的83%;又据陈继儒所说,计算地租折实率,约为76%。这些都是上等好田的情况。清代道光年间,据华亭县《张泽作善堂征信录》载,在中则田上,折实率高者为80%,低者为50%,平均约为62%,较上则田要低一些。(注: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页45-46。)在档案中也有一些例证,如江西乐安县周端生佃耕业主杨天爵土地,一律是八折交租;安徽望江县陈以太佃田的租额,就有35石、32石和28石(实额)的三种说法。(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
据研究,在清代安徽徽州地区,实收租额与原定租额的对比是:十八世纪前期为77%;十八世纪中叶为75%;十八世纪下叶为69%;十八世纪下叶到十九世纪初为80%;十九世纪上叶为83%;十九世纪后期为71%,平均为76%;总之,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在这一期间下调了租额,幅度约为四分之一左右。(注:江太新、苏金玉:“论清代徽州地区的亩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页39-44、57。)
另据研究,安徽徽州在明末有几宗在近期改订租额的地租,新额相当于原额的80%多;其中有3宗为原额的85%,但改额后的实收率仍不过六七成,另有几宗也不过七成到九成光景(为原额的六成多);一宗明末的租额,到清代十八世纪初下降了5%;另一宗康熙年间的,在雍正间增加了14%;到十八世纪中叶,休宁黄姓租簿中约定租额的十分之三有明显的下降;十八世纪下叶,租额的改动比较频繁,如祁门李姓租簿中有三分之二修定了租额,新额一律低于原额,最低为42%,最高为95%,平均为76%;同时或稍后,祁门廖姓全部定额租中,实额一律低于原额,差距最小的8%,最大的为50%,平均为原额的65%;十九世纪后叶,黟县汪姓修定租额为原额的84%;黟县孙姓在记帐期前已改租额为原额的84%,记帐期间改额的,为原额之66%;休宁隆阜镇冠记硬租为原租的88%,其中2件“折实租”,规定要再打八折交纳;祁门胡姓实租为原租的66%;综计十九世纪徽州14家地主292次改额中,1821-1844年以前改额的有165次,其中没有一次增额;1847-1893年以前改额的76次,内有增额9次;这241次合计,新额为原额的72%(前期较低,为64%);另51次有更为明确的改额年份可考,合计约当原额的78%,其中十九世纪上叶为六成,其后约为八成左右。(注: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页61、65、101、149、181、200、303、393、435-442。)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项关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中,徽州休宁吴氏绝大部分田租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内降低过租额,其中没有一次提高,平均降低了32%,租额下降的现象颇为普遍和显著。而在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中,大部分租额没有变动,只有小部分改额。(注: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页80-88。)黟县孙姓租簿中,从1863年以前至1890年,20宗田地中有12宗17次改额,全部都是减额,新额相当原额的79%。(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歙县汪姓截至1887年为止的一段时期,有记录可考的13宗14次改额,全部都是减额,新额相当旧额的66%。(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十九世纪末,祁门汪姓有14宗15次减额,平均减少50%。(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黟县汪姓23宗31次改额合计,新额相当原额的70%,其中2号田连改三次,由407斤改为100斤;24号田连改四次,由170斤改为140、115、102、100斤;26号田由100斤改为80、40斤;27号田由160斤改为100、70、60斤。(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其间有几次增租,多不过恢复到道光年间或过去旧额的水平。(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
从上可以看出,租额调整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虽然也有部分调高的例子——如福建泉州陈氏大宗祀田在万历初年租额平均增加了85%,若干学田、书院田、育婴堂田、军户田的租额在明清时期都有所提高(注: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页269、277-279。)——但总的说来,租额却是越来越低了。
以上所述,是租额的增减,但额租并不是说多少就能收多少的,它在实行中,往往要按照收成的分数交纳,很少能够十足征收。如陶煦所说,(实额例以虚额八折算之)“小灾则再减”;或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所述,“租额既定,丰年所还必足其额,其次则视年之高下,人之劳逸,而酌减之,谓之饶头”;或咸丰《南浔镇志·完租》载,“至丰之年,每亩不过一石左右,稍歉即减,有仅三四斗者”;或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所云,依额偿租,“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注:参见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这是影响地租征收情况的再一个因素。因此,为了解地租征收量的升降,必须进一步观察地租的实收情况,而不能仅依据其定额之多少。
应注意到,这些全是在同一块田土上作的比较,与各地粮食产量升降记录并不一定是在同一地亩上,其计量方法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2)实收数与租额(或最高实收额)的对比
定额租中实收量与实额的对比,即为“实收率”。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份观察报告中说:米租分为“实租”、“额租”或“正租”两种。实租系按契约规定数量全部缴纳,额租或正租则较契约规定数量少纳约四分之一。但由于佃户对租额的拖欠,地主实收田租一般不超过上数的十分之八。(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57,页266。)据说,这种“正租制”,是要视当年年成,少收部分的,这被称为“让租”。(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农业经济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9,页324。)清人王炳燮说:(苏州)“实收租米,多者不过五六成,少者才及三四成。是所谓租额,不过纸上虚名”(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北京,1982,页404。)。在分成租中,往往也不能“足数征收”,不过因为没有额数的参照,只好取一个最高数额或一个相应的基数,与之对比了。在不少定额租的材料里,因缺少租额的记载,也可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过其中的最高额,有时等于租额,有时距离租额还有不小的差距,也有个别的高出租额,那是因补交原先欠租的缘故(根据现有的材料,这类补交的数额都相当低,故多可略而不计)。现把各地情况分时期简述如下:
1、十六世纪下叶,明朝万历年间:
安徽歙县某姓公堂租簿(1579-1585),实收数为租额的八九成(83-91%或更低些),且呈下降趋势,它在6年中下降了8个百分点。(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43页。)
2、十七世纪上叶,明朝末年:
安徽歙县胡姓公堂租簿(1620-1640),实收率为七成多到九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63页。);其中有3宗最近改额的,实收率仅六七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63-65页。);内有数宗定额租皆呈下降趋势,实收率平均为78-88%。(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64。)
3、十七世纪下叶,清代初期:
安徽祁门十八都某祠租簿(约1666-1680),呈下降趋势,“实收额指数”(假定最高实收数额为100;再说一遍,它不一定是租额),平均为85%;(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104页。)
祁门十八都分成租簿,实收额指数平均为91%(参照各年收租最高数字,所谓最高额与之相差约20个百分点,其指数当为76%)(注:江太新、苏金玉:“论清代徽州地区的亩产”,表1。);
祁门十八都黄福坑某祠定额租簿(1666-1680),正斜率,即收租数量呈上升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6。);
安徽休宁吴姓祀产,此阶段后期(1694-1705)较前期(1681-1693)增加了12%,其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注: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253、445-446。)
4、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七成多到八成多,简言之八成左右(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58。);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0;《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50-152。);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5、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6、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以后的56%)(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7、十八世纪末: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85-186。);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负斜率,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8、十九世纪初:
安徽祁门廖姓租簿(1798-1828),实收数变动幅度不大,实收率为87%左右(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204-205;《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7一件似即其中之一,吴下降趋势。);
徽州五都廖姓分成租册(1807-1828),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9。);
歙县后坑坞相公凸分成租簿(1820-1830),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6。);
歙县古庵后相公凸分成租簿(1820-1830),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3。);草塘充相公凸定额租簿(1820-1830),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8、94。);
歙县培元老收租簿(1804-1828),定额租,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7。 );
福建闽清县(1803-182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9%。(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126。)
9、十九世纪中叶:
安徽祁门郑姓分成租册(1821-1858)和定额租册(1821-1846),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分别为75%和8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3、94、100、111。);
休宁祁门吴姓、郑姓公堂分成租册(1827-1845),正斜率(但上升趋势不很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1、93。);定额租册(1827-1845和1838-1858),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分别为93%和9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1-112。);
休宁吴姓启贤堂定额租簿(1827-1858),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69%或62%(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90、93。);
福建龙溪县(1801-185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3%。(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
10、十九世纪下叶(太平天国起义及其以后):
安徽黟县佚名公堂租簿(1847-18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91%和67%,合计为8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265。 )其分成租部分,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9%(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1。);
黟县汪姓租簿(1857-1873),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73%和75%,其中一部分由九成多下降为六七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10;《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2一件似即其分成租部分,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
黟县孙居易堂租簿(1865-1888),平均实收率,谷租为79%,豆租为75%(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74-375。);其分成租部分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期末降至四成多)(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3。);
休宁冠记定额租簿(1866-1875),平均实收率为65%左右(包括谷租钱租)(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94。);
黟县佚名分成租册(1864-1885),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2。);
福建云霄县(1865-1911),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
福建闽清县(1856-19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8%。(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6。)
11、十九世纪末:
安徽祁门胡姓租簿(1882-1896),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55%和58%,其中部分从八成降至四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412。);
祁门汪姓、江姓公堂租簿,下降趋势,实收率分别为80%和47%(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77-178。);
江苏吴县吴畲经栈收租记录(1893-1918),斜率有正有负,平均实收额指数,祭号85%,公号75%,庆号86%。(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3、96。)
此外,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到十九世纪末,据说未完之数各在二三分以上。(注:衣保中:“清代八项旗租地的租佃关系”,《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江苏吴县、长洲、元和三县,“绅等仰体皇仁,永减租额,计每亩约以一石为率。佃户依限交租者十有四五……三限不交,始由账船催收。佃户赴船交界者十又二三,交不足额,亦或情让了结。除抛荒无着,以及顽佃锢抗,统扯上腴,仅及七成,中下之产,不过四五成、二三成而已”(注:光绪七年苏绅公呈,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290。)。
江南某县,从1894-1903年,平均实收指数,麦季为87%,稻季为91%,且呈下降趋势(其中小麦下降了一半以上)。(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4。)
江西建昌郡城书院,租甚轻微,道光年间,一律清完,咸丰以来,颇形短绌,同治间尚有七成,光绪年间不过三四成而已。(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3。)
江西于都书院田租,每岁仅收十之二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4。)
江太新、苏金玉的研究,展现了从康熙到乾隆年间长时期的收租情况,并明确指出,实际交租数量与租额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不能“信手拾来”,“抓来就用”。在其引用的一批屯溪档案中,有许多十成交租的实例,比较罕见(特别是在光绪年间竟占据了2/3的比重)。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计算中,都排除了“受灾年份”,这可能是出于估算亩产量的需要,但对农民的交租行为来说,“灾害”云云却可能是大有名堂的(详说见后)。
《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还有一些安徽十九世纪下叶,以及数家合计的材料(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6-109、114-122。),都关系到实收比例情况,以上于此皆未计入。
3)分阶段的对比:
综上所述,地租的租额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大多数时期,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只在十九世纪略有不同)。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明代末年:80%多;
十八世纪上叶:77%;
十八世纪中叶:75%;
十八世纪下叶:69%,76%,65%;
十九世纪初:六成左右,69%;
十九世纪中叶:83%;
十九世纪下叶:八成左右,71%,79%,66%;
十九世纪末:50%,70%。
按道理来说,租额的变化是累加的,即下一个改动要追加在前一个改动之上,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可惜的是缺少这样长期变动的记录。所以我们只列出各个时期的百分比,而不作追加的计算。就是这样,地租额的变动也是很可观的了。虽然它们多是就调整过的租额而言,不一定计入了该租簿的全部地租。
另一方面,不但地租的原额和现额之间存在对比,实际征收到的数额(以“实收率”或“实收额指数”表示),也由于种种情况,出入很大。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十六世纪下叶至十七世纪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十七世纪下叶至十七世纪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十八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叶,约为七八成;
十九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十九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应引起注意,即实收率和实收额指数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在十八世纪下叶,祁门十八都的分成租簿之中,所谓最高额与各年收租最高数字相差15个百分点;十九世纪中叶,祁门吴启贤堂、休宁郑世德堂的定额租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多(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1-112。),而在同期有租额可考的租簿中,前者实收率只有69%,后者只有73%(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90-91。),所差也接近20个百分点。
另外,十八世纪中叶的五成左右和十八世纪末的三至五成,取自山东孔府和直隶旗地档案,未列入此一排比。另据研究,明清江南一些地方地租率在32%至48%之间(多在40%上下),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如据成化《新昌县志·风俗》载,田在远乡等处者,取租“或四分,或三分”,“较岁以为常,若古之员法也”,(注: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已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国历史上地租的实收率要低于租额很多(大约以七成左右为最常见),因此《安吴四种》说,苏松各处田租,“看收成定分数,大率不能过八分”,乾隆《(广东)增城县志》说,岁纳之租,“十常不及七八;(注:方行:“清代前期的封建地租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如果把这两个数列(关于租额调整的和实收率变化的)“拧”在一起,不难看出,实际收租数额将会更低;而且这一实收比率是越来越低,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大约到二十世纪开始有新的趋势出现)。这是我们研究土地和租佃制度时,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另一方面,上述史料在时间上主要是从明代末年到清代末年的。实际上,类似的情况从宋代就出现了,如据《吴学续置田记》等记载:“本宅优润租户,减退租额六石四斗六升(原额三十七石一升)。”“榷白粳米一石二斗,今减作一石……榷白粳米一石,今减作八斗……每亩榷白米八斗,今减作(七斗三升)。”其减少幅度分别为17.5%、16.7%、20%和8.8%不等。(注: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
三、小结
如果接受本文的上述论点,似乎便可得出如下的一个初步结论: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即70-80%),地租额约为土地产出的40%的话(即连同“正产物”与“副产品”合计亩产),如此计算起来(即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的样子,或是略多一点(如按陈正谟所说租率为43%计(注: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页24、94-95。),实际地租率约为32%),而远不是一向所说的50%。
对于地租征收量下降的原因,一向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不管这一原因是些什么,地租实收率即地租征收量相对租额比率的下降,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不过,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问题,我们还须考察主佃之间是如何达成这样一种局面,特别是农民一方都做了些什么和他们是怎样做的,等等问题。
[收稿日期]2001-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