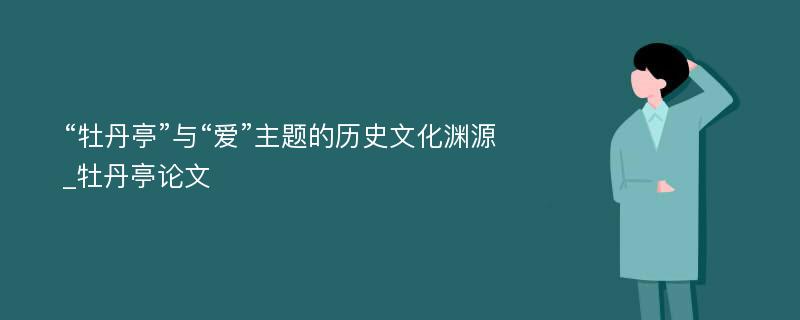
《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历史文化论文,主题论文,牡丹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奇作品,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 汤氏认为这种一往情深、超越生死的感情不同于普通的男女恋情,而是“情之至”。所谓“情不知所起”,是指这种“情”乃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具体缘由;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则是指这种“情”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这种不能“以理相格”的“情”,即是所谓“至情”。我们认为《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并非汤氏凭空创造,而是渊源有自。梳理浩瀚的中国文学史,人们将会发现这种“至情”主题早在原始神话中便初见端倪,并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演变且最终定型。
一、二妃殉情——“至情”主题的原始胚胎
关于舜帝之二妃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古书中较为常见,《山海经·中山经》即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② 的记载。在《水经注·湘水》中,传说舜之二妃是溺水而亡的:“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③ 而《群芳谱》则有如下文字:“世传二妃将沉湘水,望苍梧而泣,洒泪成斑。”④ 可见二妃是伤心欲绝,含泪殉情的。西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⑤
这个在民间传说中逐渐成型的凄美神话故事有三处情节特别值得后人重视:其一,二妃深爱自己的丈夫(这是其殉情的基础);其二,二妃因为丈夫的死悲痛不已,最终殉情而亡;其三,二妃死前,泪水溅竹而成斑状,故成“湘妃竹”(即斑竹)。考诸文学史可以发现,以上三个情节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后世表现“至情”主题文学作品的三大要素:男女互爱、殉情而亡,天显灵异。
如果说娥皇、女英的故事纯属神话,那么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则多少可从古代典籍中找到一些历史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杞梁妻郊迎丈夫灵柩的记载:“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⑥ 类似的记载还先后出现在《礼记·檀弓》和《韩诗外传》中,据考证这便是孟姜女传说的源头。到了汉代经学家刘向的《列女传》中,原先的历史记载不但加入了许多“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内容,而且掺入了不少神话成分:
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倚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⑦
汉末蔡邕《琴操》所录《芑梁妻歌》则以诗歌形式反映了《列女传》的上述内容:“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离别,哀感皇天兮城为堕。”⑧ 此后经过多番加工演绎,形成了各种版本的孟姜女传说。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有关孟姜女的传说,至迟在隋唐前后已基本定型。其后这一传说还被逐渐纳入史家笔端,清刘於义等撰修的《陕西通志》卷二十九即有如下记载:
秦始皇时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喜妻也,姓姜氏。归三日,范赴长城之役。姜女制寒衣,躬往寻范,不见,乃绕城而哭。哭声震地,城一隅为之堕。云雾之中,范见其像。女啮指出血,滴骸渗入者,知为夫骸,遂负之归。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姜女传说中,有种神异的现象与娥皇、女英神话十分类似。孟姜女滴血寻夫尸骸,枕其尸而哭,居然哭倒长城。而二妃悲痛之泪同样可以使自然界的竹子成为斑竹。这种冥冥之中天显灵异的现象表面上看来颇为神奇,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感性显现。早在《易传·文言》中即有如下论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⑩ 这种与天合德的看法正体现了古人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到汉代逐渐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春秋繁露·阴阳义》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1) 在董仲舒看来,天和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可以彼此感应的。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可以感应天。正是由于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所以在汉代《列女传》中基本成型的孟姜女神话传说中,天不仅能感应到人的痛苦,而且可以通过神异现象表现出相应的喜恶爱憎。当然,上述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先民灵魂不灭的观念。在先民眼中,躯体死亡,灵魂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可以寄寓在其他物体上,昭显一种精神和力量。
总之,我们认为二妃“洒泪成斑”的殉情模式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印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爱情类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为后世爱情文学的“至情”主题提供了最原始的神话范本和民族文化心理依据。
二、虚幻与现实的二重变奏——“至情”主题的两种雏形
汉乐府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个与二妃神话传说类似的爱情故事。刘兰芝、焦仲卿是相爱的夫妻,因为焦母不喜欢兰芝,兰芝自动遣归。刘兄逼婚,兰芝无法再与焦仲卿复合。婚礼之日,兰芝毅然“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讯后,则“自挂东南枝”。事后两家将死者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12)。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以合葬结束,且出现连理枝、比翼鸟,与娥皇、女英及孟姜女神话传说中天人永隔的悲剧结局相比,实现了虚幻世界的大团圆。神话传说中以斑竹和哭倒长城彰显爱情的超自然力量,表现了天人感应的观念。这种观念到了《孔雀东南飞》中,则表现为两人合葬墓中的连理枝、比翼鸟——在虚幻世界中用超现实的物象来象征大团圆的结局,以彰显爱情的力量。如果说神话传说中的爱情还只是体现“生者可以死”(一方为死去的爱人殉情),那么在《孔雀东南飞》中,不但可以看到“生者可以死”,而且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出“死可以生”(双方均为情而死,但是灵魂并没有消亡,合葬之后,寄寓其灵魂的物象在虚幻世界实现了大团圆)。
《孔雀东南飞》虽写于建安时期,但流传至六朝才定型,所以有学者认为其受了《华山畿》本事传说的影响。《华山畿》是南朝民歌,据《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华山畿·君既为侬死》来自一个动人的爱情传说。南徐一个读书人对客舍中的一个青年女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回家相思而病。其母亲自到华山客店找到该女子讲述此事。女子闻言,将自己用的蔽膝相送。书生发现放在睡席下的蔽膝,先是抱在怀里,后吞食而死。其母按其遗言,让葬车从华山经过。葬车行至女子家门前时,牛驻足不行。女子梳洗打扮后,来到棺前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木应声而开,女子跃入棺中,棺木合拢,再也敲打不开。双方家人只得把二人合葬,其坟墓被称为“神女冢”(13)。
显然,此传说中“合葬”情节被《孔雀东南飞》吸收且升华了。因此,《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合葬的地点也就被有意设定在华山旁。
《华山畿》本事传说完全具备表现“至情”主题文学的三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合葬情节,一方面象征两人在虚幻世界的大团圆,另一方面也是爱情的见证——“生不能共罗帐,死也要同坟台”。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合葬之后,有连理枝、比翼鸟出现以彰显爱情。这些都清晰地展现了早期的天人感应观念在民间文学中绵绵流传的轨迹。
实际上,从《华山畿》之后,以“同冢”为题材的悲剧性婚姻故事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民间传说大致产生于东晋,据清翟灏《通俗编》卷三七转引《宣室志》,这一传说可能于晚唐已经基本成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14)
南宋时,这个民间传说又开始出现化蝶的结尾,以表达人们对这对苦命鸳鸯的赞美与祝愿。成型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同样具有三个典型情节:第一,梁祝相爱(殉情的基础)。第二,梁山伯因祝英台嫁给马文才,忧病而死,出嫁的祝英台经过其墓时,天崩地裂,英台跃入墓中,墓遂合(殉情)。第三,死后同冢和后来添加的化蝶结局都显示了他们在虚幻世界实现了大团圆。于是二妃神话传说中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在翩翩双飞的神奇蝴蝶上再次体现出来。
而自《孔雀东南飞》之后,连理枝、相思鸟的情节也开始频频出现在不同的故事当中。例如干宝《搜神记》卷一一就有如下记载: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15)
韩凭夫妇双双殉情,二冢之树,枝叶交错,并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这种神奇的天人感应现象同样显示出原始神话的痕迹。
这些表现“至情”主题的悲剧性婚恋故事在不同的传说版本中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物与细节,但主体性情节始终如一,与原始的二妃神话传说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较之二妃传说,它们的结局或者合葬,或者出现成双成对的灵魂象征物,实现了虚幻世界的大团圆。
从二妃传说中一直遗留下来的灵魂不灭、天人感应的观念,还引发了后世爱情故事用另一种方式演绎这种类似的“至情”主题。在这类故事中,爱情的大团圆不是在虚幻世界实现,而是在现实世界完成。爱情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完全达到“死可以生”的程度。最著名的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故事。据孟棨《本事诗》记载: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16)
爱情的泪水和呼唤竟然有起死回生之力,充分显示了爱情具有超越生死,实现在现实世界大团圆的神奇力量。在天人感应的前提下,死亡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爱情的力量可以驱使灵魂返回躯体,重新复活。这正是对二妃爱情主题的另一种形式的演绎。崔护故事清晰地反映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雏形至此已基本成型。
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三五八记载的陈玄祐的《离魂记》,则与《牡丹亭》的情节主题有着更加惊人的相似之处。《离魂记》记载了王宙与张倩娘离奇的爱情故事。王、张两人互相钟情,但是张父毁约将女儿嫁给他人。王宙悲伤地远走他乡,倩娘郁病而亡。令人称异的是,倩娘死后魂魄却跟随王宙,两人居蜀中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后,夫妻归省张家,倩娘肉身与魂魄合而为一,实现现实世界的大团圆(17)。这一传奇生动地演绎了一段神奇的游魂故事,其思想基础无疑是早在娥皇、女英神话传说中即已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观念。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观念,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中一而再地出现游魂和起死回生的故事情节,从而让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实现在虚幻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大团圆结局。到了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成功地将《离魂记》改编为元杂剧《倩女离魂》,首次完成了以戏剧的形式演绎“至情”主题。
总之,在二妃含泪投湘江的殉情模式和天人感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两类表现“至情”主题的爱情故事逐渐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类是以《孔雀东南飞》等为代表的在虚幻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另一类则是以“崔护”等为代表的在现实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这种虚幻与现实的二重变奏完全可以视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两种雏形,并深刻地影响着“至情”主题的最终成型。
三、“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因梦中之情而相思成病,并最终香消玉殒。在阴间,杜丽娘以情感动判官,使得灵魂得以追寻梦中情郎——柳梦梅,实现在虚幻世界大团圆。这种出自本能、发自内心的情感追求最终使得杜丽娘还魂重生,实现与柳梦梅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肇端于二妃传说的“至情”主题所包含的三大要素,在《牡丹亭》中同样存在。但是,与以往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明显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此前的爱情故事言之凿凿,似乎总是在诉说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间传奇,人物、情节均体现出纪实的味道。而《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却别具匠心地构思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情境,在《题词》中明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18) 意在把戏剧中的杜丽娘作为“至情”典范来演绎,以戏剧形式展现其哲学理念。这种写作目的,明显有别于此前的爱情故事仅着眼于爱情本身的局限,而是将爱情演绎为普遍的人性,从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完成了“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一)感情基础上升为天赋人性。杜丽娘不是因现实中的爱情而死,而是为梦中之情而亡。在现实环境中,杜丽娘是个受重重束缚的官宦小姐,青春的活力和天性的本能在窒息的环境中受到严重的束缚。其父杜宝对女儿珍爱有加,请来理学卫道士陈最良做老师,希望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19)。但是这种出于封建礼教的“爱”,却是扼杀杜丽娘人性的罪恶之手。其母也同样深爱自己的女儿,以至于连衣服上绣花的样式也要管:“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20) 迂腐的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不外乎是依经解诗,这对青春貌美的杜丽娘无异于一种身心的摧残。处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封建贵族家庭,杜丽娘不可能有一见钟情或者青梅竹马的爱情机会。所以,她的爱情只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之中。在梦中,她品尝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千般爱惜,万种温存”(21),长久压抑的真情终于奔涌而出。这梦境是如此可贵,以至于让杜丽娘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病死在寻梦的徒然渴望之中,正所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22)。
不难看出,与此前类似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的爱情基础已不再局限于男女恋情,而是上升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23) 的人性高度。这种“天然”的人性正是“至情”主题产生的哲学基础和不同凡响之处。
(二)殉情结局演变为现世追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并没有在窒息的现实环境中退缩,而是展开了不懈的反抗,昭示出情的伟大力量。她不仅为这场梦中之爱耗尽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而且在阎罗殿据实禀告,争取到了化作游魂的机会。在梅花庵(即原来的杜府“书斋后院”),杜丽娘见到了反复把玩其画像的柳梦梅。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完全摆脱了当时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和爱人“幽媾”。但是,戏剧并没有在这种虚幻世界的大团圆情节中结束故事,而是继续展现杜丽娘为“情”而作的斗争。杜丽娘向柳梦梅说明真相,让他掘墓,使之还生。死而复生是杜丽娘为“情”斗争的继续,实现了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为梦中之情而死表明杜丽娘情之热切,死而灵魂相随表明其情之真挚,死而复生则表明其情之强烈。但这还不是杜丽娘“至情”的最终结局。杜丽娘在捍卫大团圆的成果上,也表现出果敢和坚定。在“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24) 的金銮殿上,面对父亲“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25) 的责骂,杜丽娘据理力争,坚称“阴阳配合正理”(26)。最后经圣上裁决,叫他们父女、夫妻相认,归第成亲。杜丽娘的“至情”不仅实现了现世大团圆,而且这种胜利的果实竟然还得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殉情结局的这种现世演变尽管只是汤显祖的一厢情愿,但无疑强化了“至情”主题的社会意义。“至情”的最终结果不是指向单纯的爱情团圆,而是具有了向当时社会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挑战的意味。事实上,汤显祖在《题词》中发出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7) 的诘问,完全可以视为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28) 的程朱理学的否定和批判。
(三)感情象征物包含“以情抗理”的哲学意蕴。在“洒泪成斑”的二妃神话中,湘妃死前泪水凝成的斑竹无疑是爱情的象征物。在后世类似爱情故事的发展中,合葬墓或连理枝、相思鸟、双飞蝶等成为感情的象征物。而在灵魂相从或者起死回生的神话故事中,人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窥见“至情”主题象征物的影子。在《牡丹亭》杜丽娘的身上,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女性对情欲的追求和斗争,而不仅仅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这种情超出了男女爱情的范围,而与汤显祖所处时代的“天理”相对,上升到“人欲”的范畴。当封建统治者所谓的“理”成为“情”的桎梏时,“情”必然要突破束缚,出生入死争取最终的胜利。因而,“至情”的象征物表面上看仍然是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但由于“情”的内核不同,“至情”的象征物也就有了一种新的意蕴。《牡丹亭》中的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不仅仅象征男女之情的胜利,更象征着人性的解放和胜利。左拉在评价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时说过:“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29) 在我们看来,《牡丹亭》中的“至情”象征物便具有这样的时代先锋意义。它们业已成为汤显祖“以情抗理”、“以情反理”思想理念的艺术显现。
通过分析“至情”主题所包含的三大要素在《牡丹亭》中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传统主题到汤显祖手中已经完成了哲理层面的升华,且具备了更加丰厚深刻的文化意蕴。汤显祖试图将剧中所表现的“至情”与现实中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和“青梅竹马”、日久生情区别开来,着力于表现其与生俱来的天性本能,并把它提升到人类精神的维度来加以论述:“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30)
不仅如此,汤显祖还明确表示其创作目的是“以情反理”、“以情抗理”,故发出了“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31) 的呐喊。我们认为,封建礼教反对的并不是爱情婚姻,而是反对像杜丽娘这样的青春少女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欲要求。杜丽娘身上所具备的自然人性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看来,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而正是在与封建礼教的激烈对抗中,《牡丹亭》“至情”主题的伟大力量和价值才最终得以彰显。事实上,《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业已成为汤显祖至真、至美、至善哲学理想的艺术象征,是其“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32) 的哲学理念的文学表达。毫无疑问,在压抑人性、人欲的明代社会晚期高扬起人性解放的大旗,完全可以视为《牡丹亭》“至情”主题不同于此前同类作品的明显表征。
注释:
①(18)(27)(30)(31)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③④⑤ 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第256页,第254页。
⑥ 郭丹:《十三经直解·春秋左传直解》,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499页。
⑦ 《四部备要·史部·列女传》(046),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版,第31页。
⑧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2页。
⑨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陕西通志》(5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0页。
⑩ 《易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1) 《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8页。
(1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80页。
(13) 《四部备要·集部·总集四·乐府诗集》(094),第315页。
(14)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通俗编》(19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按:今本晚唐人张读所撰《宣室志》无此条记载)。
(15) 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142页。
(16)(17) 《太平广记》,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0—1281页,第1682—1683页。
(19) 《牡丹亭·训女》,第10页。
(20)(21)(23) 《牡丹亭·惊梦》,第56页,第56页,第53页。
(22) 《牡丹亭·寻梦》,第67页。
(24)(25)(26) 《牡丹亭·圆驾》,第301页,第302页,第303页。
(28)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页。
(29) 刘月嵚:《杜丽娘形象浅议》,载《内蒙古电大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32) 徐朔方:《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0页,第1127页。
标签:牡丹亭论文; 汤显祖论文; 杜丽娘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爱情故事论文; 华山畿论文; 列女传论文; 神话传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