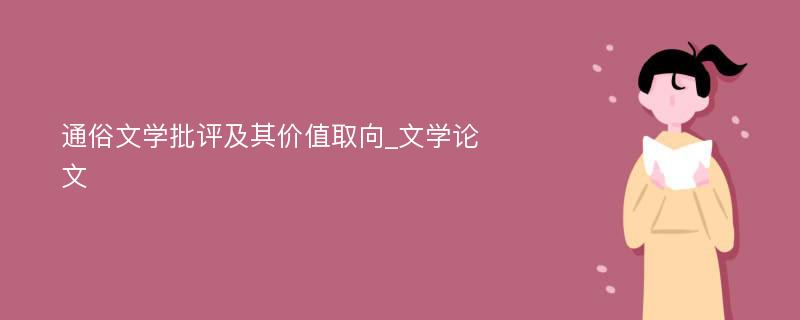
通俗文学批评及其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通俗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说清问题,应该先明确“文学批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据韦勒克考证,“在希腊文中,‘Krites’意为‘判断者’,‘Krinein’意为‘判断’”[①]。这是“批评”(Criticism)一词的词源学意义。判断有两种,一是判断真假,一是评价好坏。在以后的发展中,“批评”一词千变万化,但是这两种含义却延续下来。培根在《学术的进展》(1605)中指出,批评性的知识有五个特点:“(1)涉及对著者的正确校勘与编纂;(2)涉及对著者的解释和说明;(3)涉及作品的系年,在许多情况下,系年为作品的正确解释提供了重要线索;(4)涉及对著者的某些简短扼要的非难和估价;(5)涉及研究的处理方法。”[②]这里的五项中,前三项都涉及鉴定与解释,后二项则涉及评价。总之都是“判断”。前者是科学判断,后者为价值判断。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更是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但是这两种判断活动却包含在大多数理论家所说的“文学批评”之中。弗·克鲁斯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文学批评”条目中说:“广义而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艺问题的理性思考。作为一个术语,它对于任何有关文学的论证,不论它们是否分析了具体作品,都同样适用……严格说来,这个术语只包括所谓‘实用主义的文学批评’,即对意义的解释以及对质量的评价”。艾略特也说:“我说的批评,意思当然指的是用文字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③]
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文学批评就是对具体作品所做的意义阐释和评价。当然,两种判断在批评活动中的地位并不是同等的,阐释是评价的前提与基础。“判断正确与否的观念,显然来自解释是否妥当的观念;评价来自于理解;正确的评价又来自于正确的理解”[④]。于是,可以推论,通俗文学批评就是对通俗文学作品的解释和评价。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要对具体的通俗文学作品做出解释和评价,那么,解释的根据是什么?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的价值取向如何?
这得从什么是通俗文学说起。范伯群先生曾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过界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本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⑤]除去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特性,可以看出,通俗文学的共性大致有几点:1、它是文人创作或加工过的文学;2、它是精神消费品,具有趣味性、娱乐性、可读性;3、以广大市民为主要读者群;4、它是商品性文学,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对通俗文学的简易界定:文人创作的供广大市民消遣娱乐的商品性文学。
那么,通俗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文学的阐释与评价了?
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如此理解通俗文学批评,首先就要遇到意义阐释的标准问题。现代阐释学如下的几个假设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意义阐释提供了前提和理论依据:“1、意义是全部话语的特征,能够在解释过程中获得阐明。换言之,意义并非总是不证自明的,必须通过推演发掘才能获得。2、对意义的理解决不是中立的或客观的。因为,3、寻求理解的主体同客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对客体的理解则是通过他(或她)对客体(即话语)的透视角度与兴趣而取得的。4、进行研究的主体与接受研究的客体之间的联系或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主客体之间历史的或社会——文化(或二者兼有)的差距所造成的。”[⑥]
这些假说说明对文本的阐释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正是批评活动存在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各个批评流派才得以根据自己的标准解释文本的意义,并对作品作出评价。韦勒克说:“在这里,批评家之间的争论才最容易发生,因为作品被用各不相同的理由进行评价。艺术作品越是复杂,它所构成的价值的大厦就越是千变万化,因而对它的解释也就越是困难。忽略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危险也就越大。”[⑦]于是,社会历史学派要在作品中发现社会变化的风云与阶级斗争新动向;新批评则认为要回到文本去,在“细读”中玩味语词的肌质;精神分析学派又把文学当成作家的白日梦;在作品中找性心理;结构主义在文本中寻找认知世界的模型;叙事学又把人物的行动抽取出来,总结“叙事语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不同的批评流派存在的前提是,“意义并非总是不证自明的”,在纯文学中的确如此。作家追求的是“意图越隐蔽越好”,企求走出人们既往形成的文学能力和期待视野,去表现自己的创造能力。
然而,在通俗文学中,情况却恰恰相反。通俗文学作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品,它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通俗文学从不追求意义的多层性与模糊性,也不要求思考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社会问题。它的主题是简单明了、具有普遍性的。通俗文学不允许作者运用作品去探讨或表现只为少数人关心、理解的思想和高深玄奥的哲学问题,否则就很难成为通俗文学了。
就文本层次而言,通俗文学作为精神消费品,它是供广大市民消遣、娱乐的文学。因此,它的语言是直接指向意义的,避免歧义性发生。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可以割断能指与所指的固有联系,把文学变成能指的狂欢,让意义永远隐退。那样的文学不属于市民大众。市民们所能接受的是日常的、意义明确的,在他们的语词库中能找到的语言。就叙事模式而言,通俗文学的故事是高度模式化的,它拒绝创新,因为新的故事结构往往妨碍接受,从而使其失去可读性。
尽管通俗文学具有如上这些特点,仍然不能保证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是相同的,赫施说:“在约定俗成的语言法则下,几乎任何词语序列都能够合理地代表一种以上的复杂含义”,因此,“一篇文本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我们可以从它分析出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根本不相同的复杂含义”[⑧]。通俗文学的文本也一定具有多种含义。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大众读者可以认定它的意义是写江湖上侠客们行侠仗义、扶弱除暴、化解仇怨的故事。周宁博士都从这些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血缘关系混乱的故事模式中,发现了中华文化近一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从家族宗法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型的矛盾与迷惘[⑨]。美国著名文论家简·汤姆金斯则发现,“在《汤姆大叔的小屋》的世界里,亦即在一个堕落的奴隶制的世界里,有一幅既是乌托邦式的又是田园牧歌式的生动图画”,因此,“小说最深刻的政治雄心,在其对奴隶制的猛烈攻击中只是表现为第二位的,斯托的修辞行为的真正目标完全是在尘世上建立起天国”[⑩]。
对通俗文学的理解的差异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通俗文学”的定义。如果我们把“通俗文学”看成是一种静态的文本形式,那么,作为语言符号系统,它就必然也是一种文化文本,它也同样体现出了一个时代文化的面貌。此时,它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人们可以把它放在文化积层中,去帮助恢复那个时代的文化图景。同时,它也就与纯文学,与其它文化产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对它进行文化分析,得出全新的结论。如果我们对“通俗文学”持一种动态的看法,把它定位为市民大众的精神消费品,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读者的阅读活动引入“通俗文学”,此时,它的娱乐性、可读性就是重要因素。
这样看来,周宁博士对金庸作品的分析,简·汤姆金斯对《汤姆大叔的小屋》的分析,就是文化文本分析,而不是从读者大众角度进行的分析。这两种分析,实际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文艺学范畴。前者可以称为“文学研究”,而后者,则可以归之于“文学批评”。“这种狭义上的文学批评不仅可以和美学(艺术价值的哲学),而且可以和其它可能同学习文学的人有关的问题区分开来,如作家的生平、文献学、历史知识、来源与影响,以及方法问题等。因此,‘文学批评’与‘学问’常被看成是分开的,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这样。”[11]
通俗文学批评首先要保证批评的对象是通俗文学。也就是说,首先要从读者大众的角度来看待通俗文学。市民大众的兴趣、视角和认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可以对通俗文学的具体作品达成一致的认识。狄尔泰说:“在理解活动中,注释者的个性与作者的个性并不像两个不能比较的事实一样相互对立。相反地,二者都是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形成的,而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语言的彼此交流成为可能。”[12]读者之间也是这样。
更何况,意义问题,对于通俗文学读者来说从来也不会成为问题。没有哪一位读者读完一本通俗文学作品后宣称自己没有读懂,而需要与其他读者讨论。意义在通俗文学中是无须解释的,不证自明的。这样,通俗文学批评中评价的基础就与纯文学批评不同了。对于纯文学批评而言,评价的根据是对作品意义的分析与确定;对于通俗文学批评而言,评价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对于说明通俗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了保证批评的对象是通俗文学,必须确保被批评的具体作品被“通俗地”阅读。这是评价的前提。
原西德接受美学家鲍埃尔等人认为,文学作品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是人工的艺术制品,如一本书,一幅画等等,是物质形成的东西,这是“第一文本”;而语言符号、画的色彩、构图、布局在人的意识中经过领悟、融化、解释后形成的形象是“第二文本”,这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西方大多数批评流派都把注意力放在第二文本作用与意义的研究上;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更多地研究第一文本,阐释学与读者反应批评则关注读者所得到的意义是否正确,是否与作者本意相符合,以及解释所受到的影响问题。
通俗文学批评更应该注意从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化过程的质量问题。因为意义问题在这里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无所谓第二文本与第一文本的原意(作者意图)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并且,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化又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这样,通俗文学批评就属于阅读心理学范畴,至少也是以阅读心理学为基础的。它所关心的应该是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能否顺利地实现转化,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或者说,读者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感受如何。
从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化,首先涉及到第一文本。通俗文学批评对第一文本的价值判断应该以什么为指归,或者说以何为价值取向?必须再一次强调,通俗文学批评应该站在大众读者的立场上来对第一文本提要求。从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来说,第一文本的能指与所指必须是在市民阶层的语词库中有明确而固定的联系的,它不能是必须经过学院化的纯文学训练才能理解的能指的创造性组合;文本的结构应该是单线的,或者至少也要是层次分明的。而且故事应该是高度模式化的,才子佳人也好,行侠仗义也好,野史秘闻也好,都要是市民阶层已经耳熟能详的,似曾相识的。这样,才能保证第一文本顺利地转化为第二文本。
从理论上说,通俗文学批评对第一文本的评价,应着眼于其功能。沃尔夫岗·伊瑟尔认为,第一文本之所以能转化为第二文本,是因为第一文本中存在着一种“召唤结构”,就是说第一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吁求读者去填补,从而实现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化。对于纯文学而言,空白越大,读者在填补时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因而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作品也就越好。另外,空白的填补也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已经给出的暗示制约的。于是,暗示如果是歧义的,空白就可能有多种填补方法,读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通过判断来确定如何填补空白,以最终找到意义。因此,空白填补的可能性越多,第一文本也就越有价值。
然而对于通俗文学而言,第一文本的好坏不是以空白的大小或填补它的可能性多少决定的,而是由能否吸引读者去填补那些空白来决定的。填补空白的方法或是固定的,不存在填补空白时的犹豫不决。只要一有空白,读者便可以立即填补,准确而且迅速。关键在于能否引起读者的填补兴趣。这有点像打牌的游戏,出牌的规划是固定的,关键在于怎样让玩牌的人不停地玩下去。
因此,通俗文学批评活动中,评价第一文本的价值取向在于“召唤结构”的设置能否“召唤”读者去顺利地填补空白。
第一文本只提供了向第二文本转化的可能。只有当这种转化实现时,一部具体的通俗文学作品才真正出现。这个转化的目的在于娱乐消遣。因此,通俗文学批评作为对通俗文学作品的评价,就必须考察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转化的质量。这成为决定通俗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的关键。
纯文学的批评,在填补了第一文本的空白之后,确定已找到的意义,然后又要对此意义或者第一文本产生意义的功能进行评价。通俗文学批评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意义是可以不加思索就确定的。因此,评价从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转化质量的标准,不是读者在填补空白时由于读者思考、分析、判断,终于获得意义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人的创造能力,不是对于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也不是读者所找到的意义对读者的启发大小。通俗文学阅读重心不在这些方面。通俗文学批评中,评价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转化质量的基本尺度,应该是读者在填补空白时,由于不断被吸引去顺利地填满一个个空白而得到的欢愉或者满足。这种欢愉与满足主要来自于被吸引的过程,而不在于填补每一个空白时所得到的启发,也不在于填补空白时所得到的美感。举例而言,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常出现年轻美貌的小姐,由于偶然的机会而得以窥见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公子挥洒自如地题诗作画的情景。中国读者马上就会知道这对男女将有“戏”。这里的空白也就被填满了。尽管这里有良辰美景、才子佳人,但是中国读者不会停留在对这一个模式化的细节的玩味上,而是更关心以后怎样?小姐有何想法,将采取什么行动?公子的态度如何?等等。读者将对以后的故事感兴趣。即在不断被吸引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在这里,读者是被引诱、被推动去玩一种游戏,而在纯文学的阅读中,读者基本上是主动地去求索空白所暗示的意义。
至此,通俗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在第一文本转化为第二文本过程中,大众读者所得到的满足程度。对于第一文本而言,评价它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看它的“召唤结构”能否吸引读者去顺利地填补它所留下的空白。
艾·阿·瑞恰慈说:“凡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便是能使冲动得到利用并使其欲念得到满足。我们说某样东西是好的,这时我们指的是它令人满足,所谓好的经验,我们指的是产生这个经验的冲动得以实现而且是成功的。作为必要限制条件而有所补充的是,这些冲动的利用和满足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更为重要的冲动。”[13]通俗文学批评应该以读者在填补第一文本空白时所得到的欲念满足程度来判断其好坏或价值的高低。当然,欲念、冲动又是有区别的。首先,通俗文学作品的第一文本也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求真欲念。比如像周宁博士或者简·汤姆金斯所做的那样,在金庸的小说中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在斯托夫人的畅销小说中寻找它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对应,研究它的产生与流行的文化历史原因。这样,具有物质性的第一文本,作为一种文化文本也就具有满足求知欲的价值了。但是,如前所述,这样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研究价值,而不是批评价值。
通俗文学批评不是对第一文本所有价值的判断,而只是对把第一文本作为通俗文学来阅读,从而使之转化为第二文本时,读者所得到的消遣,娱乐性欲念满足程度的判断。也就是从市民大众的精神消费要求得到满足程度来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能够放弃学院式的纯文学训练培养出的对通俗文学的话语霸权,而采用市民大众的期待视野来阅读通俗文学的第一文本,否则,就无法保证批评的对象是通俗文学作品,遑论其它。
这并不是说要向市民大众的“低级趣味”投降。恰恰相反,由于通俗文学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通俗文学批评正应该反对那些为了商业目的而煽动人的恶劣欲念的作法。区分不同类别的冲动和欲念,也就成了通俗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了。
注释:
① ②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4页。
③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转引自《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④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6—27页。
⑤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评传丛书·总序》,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⑥ ⑧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202—203页。
⑦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6页。
⑨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⑩简·汤姆金斯:《感伤的力量》,见《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11《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批评》,转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页。
12转引自《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第205页。
13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