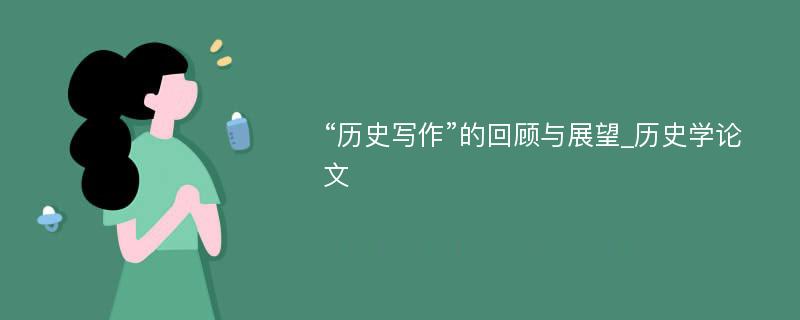
“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不少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推动着“史料论式的研究”向前发展。例如,2007年以来每年举办的“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上,关于史料论式的研究成果经常会占到一定比例,在综合讨论的环节,这一主题也时常被提起,不仅如此,参加该研讨会的青年学者中,已有同仁将史料论式的研究成果整理为著作。当前“史料论式研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分析文献资料新方法的出现,二是以墓志为代表的新资料的增加,并且随着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大量的史料可以被简便迅速地整理,从而更方便比较、讨论。
何谓“史料论式的研究”?在我们看来,即在理解史料内容的同时,重视史料的成书过程,主要从史料选择、文章构成和叙述形式等方面考察史料著者、编纂者的意图及其对历史的理解,同时将史料所要传达的内容与其成书的时代状况相结合。该研究主要通过对多种史料进行讨论,再将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进而窥探史料著者、编纂者的意图,历史理解的方向性及偏好,从而构建出新的“历史像”。虽然该研究方法受到了现代文学、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文本理论发展的影响,但是,19世纪以来传统的史料批判方法中,就已存在该研究方法的苗头。
史料批判原本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手段,把握成书过程和史料著者、编纂者的执笔编辑意图是史料批判的基础,从这方面来看,史料论式研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史料批判方法的发展和深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料论式研究并不完全是单纯地将传统的史料批判手法加以发展、深化,它不但受到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内涵也更加丰富。下面对日本历史学界尤其是日本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史料论式的研究”的源流加以概述,并简要地回应学界对笔者研究的批评。
19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初,日本史学界对“历史讲述者”愈发关注,讲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会对历史叙述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讲述者的解释和文脉的构建,历史叙述本身就不会存在),这一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当时对此甚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学者,而是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们。这一逐渐发展起来的议论并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未对历史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进行充分考察,因此,历史学者对此实际是感到困惑的(岸本美绪《现代历史学と“传统社会”形成论》,《历史学研究》742号,2000年;小田中直树《历史学のアポリア》,山川出版社,2002年)。
事实上,1970年代中期,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在问题设定、方法及研究材料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安丸良夫《表象の意味するもの》,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にぉける方法的転回:现代历史学の成果と课题1980-2000年》第1卷,青木书店,2002年),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学者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且已经存在使用史料时需要把握“历史讲述者”如何解释事实,对“历史讲述者”同时也是研究者自身的认知也要进行再审视等看法。例如,在这些新看法的研究中,有学者充分利用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的调查成果和文献、绘画等史料来进行研究,发现史料中讲述的民众形象与实际相比有很大的偏差(在支持这一视点的研究者中,有巨大影响力且广为人知的,可以举出日本中世史研究者网野善彦。网野善彦的成果推翻了学界对日本中世史一直以来的认识,常被称为网野冲击)。
进入21世纪后,基于以往的研究,历史学界对1990年代兴起的这一议论作出了各种提议(参前文注释所举诸论考,另外,上村忠男等编《历史を问ぅ》全6卷,2001-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是由历史学者及哲学者、社会学者等共同编纂的论集,可以说是这一动向的具体表现)。这些提议主要是说,应再次明确严肃面对史料并解读之的方式,依然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同时要注意史料中细微的矛盾、不合理之处,对此进行比较讨论,进而推翻史料讲述者的解释,阐明史料中隐藏的事实,审视研究者自身的认识,并对历史学及其他学科领域提出的问题加以解答。21世纪以来,着眼于史料执笔者、编纂者意图及认识的史料论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专门研究史料的特集在学术杂志上经常可见,可以说就是受到了这些提议的影响。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中,津田左右吉首先注意到史料的成书过程、文章构成和叙述形式,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性研究。津田左右吉主要以儒教经典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混入的不同时代、体系的思想进行了细致地比较考察,据此来推定文献成立的年代;继而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社会状况产生的种种不同思想最终合流成一的过程,来阐明从先秦到汉代期间儒教形成的经过(津田左右吉相关的研究载于《津田左右吉全集》,岩波书店,1965年,第15、17、20卷)。该研究方法以史料间的具体对照、比较为基础,关注细节上的矛盾和不同点,对其结构和背景中的思想进行细致解析,可以说这正是史料论式的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成果对日本实证性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津田左右吉先生在儒教经典研究的过程中多次提到过“史”的起源、由来和史书的性质,但他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史书只是积累记录的王朝史书。津田的评价缺乏史学史上的那种历史性发展的观点。如果按着津田的观点,在分析中国史书编纂者的意图时就会变得困难。
19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秦汉史的知名学者增渊龙夫反驳过津田的这种观点(增渊龙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ぉける中国と日本I—津田左右吉の场合》,《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年)。增渊龙夫是在讨论外国史研究工作的意义时提到了这一问题。相对于津田的观点,他提出需要分析中国的知识人是怎样解读中国的历史记述的,从历史记述中能学到什么并怎样行动。基于这种观点,他比较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与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意图从中解读胡三省和陈垣的历史意识,这就是通过解读著者的执笔意图来构建新的历史像,颇有意义(增渊龙夫《历史のいわゅる内面的理解について》,《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年)。川胜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来探究在庞大的历史记述背后有着怎样的观念和哲学,并以此来总结通史(川胜义雄《史学论集》,《中国文明选》第12卷,朝日新闻社,1973年。另外,其中的《总说》部分之后被收入《中国人の历史意识》,平凡社,1986年)。可以说,川胜深化了增渊的观点,使之适合观察中国史学史的整体状况。
当然,日本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除津田的研究外还有内藤湖南等人的重要著作。但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与史学史相关的个别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胜义雄的通史的影响。不仅如此,将增渊和川胜联系起来的上述观点注意到了时代当事者的认识与行动的内在因素,其性质与川胜的“贵族制社会”研究的观点相通。在此之前增渊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和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为材料,撰写了关于后汉时代党锢事件的论考,其内容对川胜提出的“贵族制社会”论有很大影响(增渊龙夫《后汉党锢时代の史评について》,《新版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书店,1996年)。从这两点来看,在思考日本学界史料论式研究的由来及其与中国史,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史之间的关系时,回顾津田的研究成果以及批判性发展其观点的过程,就显得很有价值。
在“史料论的历史再认识”这一主题下,笔者着重讨论的是至今为止日本中国中古史研究中,由川胜义雄带头发展起来的与“贵族制社会”成立相关的一系列研究(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中译本为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川胜的研究到1970年代已基本完成,由于比之前提到的1970年代中期的研究动向转换要早,因此很难认为其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川胜重视“清”、“义”以及乡里社会的名声等起到的作用,并基于此来讨论政治、社会的状态。“清”和名声表现了某种社会性评价,无疑是包含了“历史讲述者”对事实的解释。这种观点,在之前举出的川胜的史学史相关著作中也很明确。笔者也注意到这一点,继而以史学史的角度来验证当时历史史料编纂中加入的编者的解释(《后汉时代关系史料の再检讨——先行研究の检讨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4号,2000年),从而发现了史料被更改,且解释出现变化的事例(《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史料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刘平·赵孝の记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2000年)。由此,笔者尝试对川胜的“乡论环节的重层构造”进行批判性的验证。具体来说,笔者注意到党锢事件之际与“名士的排位”相关的史料,提出了范晔《后汉书》中记载的天下规模的“排位”是进入西晋东晋时期出现的这一历史理解(《党锢の“名士”再考——贵族制成立过程の再检讨のために》,《史学杂志》111-10,2002年)。
对于笔者的见解,有多位学者反驳在编纂史书时,虽然对史料进行了取舍,但还是很难想象编者会对作为研究依据的原始史料追加根据不足的新内容,还有人反驳史料不存在不代表史实不存在,也不一定是在成书阶段追加的。批评意见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笔者自己也有充分的认识。笔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充分基于史学史的背景,具体解析史料讲述者对事实的解释以及文脉的构筑。笔者不只是讨论特定史料的有无,而是与史料的文脉和结构一并讨论,因此预先谈到了史料的取舍和重构会引起解释发生变化的这种联动效应。另外,笔者通过收集与“天下名士排位”类似的“排位”事例来分析其性质,得出与“天下名士排位”有同样性质的天下规模的排位表在吴末西晋期之前还未出现的结论,以此旁证了并不仅仅是史料不存在这一问题。
虽然出土资料大量增加,但从根本上讲,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史料还是相当欠缺。因此在中古史研究中实践这种研究方法,推翻史料讲述者的解释,解析史料中隐藏的事实,那就如批评意见所指出的,无疑存在很多危险和困难。但笔者认为史料论式的研究方法不只是从个别史料的有无和改变中来讨论种种可能性,而是应该从史料整体的构造、构成中来推导出确实的结论。要意识到原有研究留下的成果和克服前人研究缺点的过程对于中国史研究工作的意义,要面对史料重新审视对人类社会已有的认识,并通过回答历史学及其他学科领域提出的问题来推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