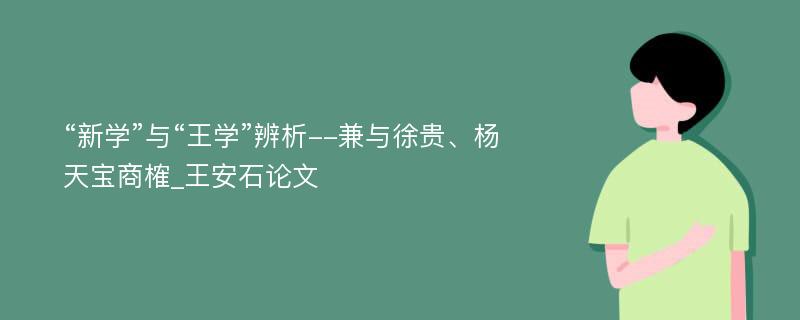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保论文,探析论文,新学论文,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6)03—0009—05
现代人研究王安石学术思想,大都将“新学”与“王学”相等同。如罗家祥说道:“《言事书》的问世,表明新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基本上完成了对新学体系的构建。”[1] 肖永明说道:“新学以王安石等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但新学的内容却并不局限于《三经新义》。它包括在此前后王安石及其弟子的一些学术著作。”[2] 简而言之,都是把“新学”作为王安石与荆公学派学术的简称。以“新学”取代“王学”,就其渊源,一般归结于明末清初的全祖望《宋元学案》里面的《荆公新学略》。这种用法,一直延用至今。最近,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合著《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以下简称《走出“荆公新学”》),从“王学”多种历史演变形态的角度,对这一用法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引起了不少王学研究者的注意。恰好本人正在撰写有关王安石的学术论文,在使用“新学”概念过程当中也发现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求精确、滥用等情况,与《走出“荆公新学”》可谓不谋而合。虽然如此,本人对于“新学”与“王学”的认识,与《走出“荆公新学”》却有着不同的见解,这里把它提供出来与徐规、杨天保两位先生商榷,并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关于史料中的新学
《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荆公新学”概念的精确性及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它从发生学的角度,将王学划分为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认为“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3] 显然,在《走出“荆公新学”》看来,“新学”实际上仅仅是“王学”中被作为官学的那部分,用来指代整个“王学”是不恰当的。且不说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单就这种打破常规的怀疑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新学”是否真如《走出“荆公新学”》所认为的不能用来指代“王学”?这首先就需要我们对“新学”与“王学”两者关系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界定,了解作为“王学”特指的“新学”概念的由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回答《走出“荆公新学”》所提出的有关“新学”概念是包含了王安石以前学术,还是仅仅包括《三经新义》、《字说》以及《宋元学案》所采用的那种以“新学”作为王学代称的合法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回到宋代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从司马光等宋代批评新学的儒士的相关史料记载看来,“新学”确实仅仅包括了《三经新义》《字说》。如司马光《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云:“昨已有朝旨:来年科场且依旧法施行。窃闻近有圣旨,其进士经义,并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仍罢律义,先次施行。臣窃详朝廷之意,盖为举人经义文体专习王安石新学,为日已久,来年科场欲兼取旧学,故有此指挥,令举人豫知而习之。”[4](234 页)
元祐元年闰二月侍御史刘挚进言:“今之治经以应科举,则与古异矣。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不可究诘之论,争相夸尚,场屋之间,群辈百千,浑用一律,主司临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虽有深知圣人本旨,该通先儒旧说,苟不合于所谓《新经》、《字说》之学者,一切在所弃而已。”[5] (853页)
陈师道《赠二苏公》诗有云:“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任渊注:“新学谓王介甫新经学也。”冒广生系此诗于元祐元年[6](25页)。 从熙宁八年颁布《三经新义》到元祐元年正好十年,故“十年新学”应指王安石新学无疑。宋人云:“《三经》、《字说》簧鼓群听,学者至欲以黄昏汤洗其肠胃,乃获与焉,正论安在?”[7[(65页)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诗。
上述史料表明,元祐更化时期,朝野对于“新学”的批评是针对《三经新义》、《字说》而言,而对于王安石其他的学术,则基本没有提及。但是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新学”仅仅指代王安石《三经新义》、《字说》呢?我个人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其一,新学作为北宋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与学派,单凭《三经新义》、《字说》是撑不起整个新学的;换而言之,整个王学与王安石学派才是作为官学的新学的实质。其二,反对派批判新学的《三经新义》、《字说》不等于他们就将新学仅仅限定于《三经新义》、《字说》。这是由于在形式上被立于学宫的《三经新义》、《字说》不但被作为新法的理论基础,担负着最直接为新法合理性辩护、统一思想的任务,以及作为天下举子科举应试、培养新学人才的教材,同时还是新学官学地位的象征。因此,无论是反对新法还是赞成新法者以及科举考试者,都必须直接面对《三经新义》、《字说》。《三经新义》、《字说》被立为官学或者被推翻,都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系列因缘和合的产物。故此宋神宗去世,太后主政,新法被废。王学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被立为官学的所谓《三经新义》、《字说》,其中《字说》被禁。
二 王学官学化与新学
既然“新学”是由于官学化而来,那么,很有必要结合王学官学化进程来考察“新学”与“王学”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总体上来把握王学与新学的关系。
官学化之前的王学,在嘉祐治平年间就已经形成并有着一定的影响,“王学”名称已经出现。既是王安石的女婿又是其弟子的蔡卞论及荆公学术,作如是说:“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8](257页) 弟子陆佃云:“嘉祐、治平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9](267页)
另据《续资治通鉴》卷第66熙宁元年记载:“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相友善,帝在籓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5](678页) 王安石的经学著述在治平年间除了主要在民间流传外,还在宋代朝廷中有所流传,并且开始形成了学派。
嘉祐治平年间的王学,基本上奠定了熙宁变法以来王安石学术的理论基础。从熙宁元年到熙宁八年《三经新义》完成并被立为官学前,王安石逐渐将嘉祐治平年间形成的王学思想运用于实践,主持新法,王学实质上被作为当时政治上的主导思想。熙宁元年是王学开始官学化的酝酿阶段。先是王安石的经术治世主张被宋神宗采纳,据《续资治通鉴》熙宁二年记载:“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5](682页)进而主宰经筵,罢《礼记》,讲《尚书》,属于儒家所谓的择术讲学、正心诚意阶段。“明日,帝谓安石曰:昨阅卿奏书,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安石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喻矣。”[6](679页) 熙宁二年前后,宋神宗准备以王安石执政开始变法,当时朝臣批评王安石“但知经术,不晓世务”,但是宋神宗“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5](682页) 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这一阶段王安石开始将自己历年来所学运用于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其他还有兴学,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大体本于所学古代圣贤所为、经典所记,都属于托古改制、致君尧舜之道王学的基本内容。
熙宁初宋神宗在讲学未明、同风俗、一道德、析名实“未实现的情况下,急于理财新政,《续资治通鉴》熙宁二年记载“安石曰: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5](682页)因此,儒士大夫、普通民众对新法很不理解,把它等同于生事、征利,伤风败俗,失国家大体。新法行之不到数年,已是群情纷纷,思想混乱,人人惧而远之,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新法实行三年多后,熙宁五年正月,宋神宗要求王安石等人撰《字说》、以后又设经义局,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编《三经新义》,为新法培养人才,以及统一国人思想、寻求理论合法依据。随着熙宁八年《三经新义》、元丰五年《字说》的相继完成并且被立为官学,元丰末年“新学”完成了从泛指意义到特指王安石新经学的转变。
可见,王学官学化包含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历程,《三经新义》、《字说》作为官学绝对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而是王安石的经学主张与实践在整个熙元变法进程当中逐步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的,是熙元变法进程当中一系列事件的产物。《三经新义》、《字说》里面所诠释的经学思想,是王安石历年来特别是嘉祐治平年间成熟起来的王安石经学思想的直接运用,而不是突然在熙元间出现的。《三经新义》、《字说》只是对王安石新政所运用的理论详加阐述,为新法作论证、理论辩护,并且以官学的形式固定下来,大体属于王学同风俗、一道德、析名实”的范畴。因此,被立为官学的《三经新义》、《字说》并不是什么脱离王学的新东西,所谓的新,不是针对以前的旧王学,而是王学里面最具体、与现实结合最紧密的那一部分。《三经新义》、《字说》的被官学化,实质就是王学的官学化。《三经新义》、《字说》的官学化只是形式,而王学才是真正的内容。对于王学而言,似乎并没有金陵之学或“新学”之间的界限,两者除了名称、内容不同外,在主导思想、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换句话说,“新学”完全可以等同于所谓“金陵之学”或者“王学”,将王学条块分割成为几个不同的形态,可能反而损害了王学的整体性、连贯性。
三 “新学”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
从“新学”概念的由来看,王学官学化期间,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相辅相成层面的出现,最终促使新学由普泛意义的称谓转化为王安石学术的特称。对此,本人在《新学名称的由来问题考辩》一文有详细论述,这里略微概括如下:就字义言,“新学”原本具有新学术的意味,包括新观点、新路径与新方法等。“新学”一词亦屡见汉唐至宋代文献。在北宋初期“新学”名称多用来泛指与汉唐章句训诂经学相对的包括王学在内新兴义理之学。熙元变法期间王安石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字说》先后被立为官学,带来天下学术、学风的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四者相辅相成的局面,并最终在元丰末实现了“新学”从普泛的称谓到具象化为王安石官学特指称谓的转换。
而就“新学”的内涵而言,“新学”有三种应有之义:官学、新经学、学派。作为官学,《三经新义》、《字说》被立于学宫,作为天下举子科举应试的教材,这只是一种官方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实质。真正的实质是整个的王安石新经学被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新经学,它是王安石及其学派、从事新学学术研究、探讨、阐发、传述的儒士们的基本内容,《三经新义》、《字说》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只是其中一方面,而不是全部;作为学派,新学学派是北宋后期最有影响、最有创造性的主流学派。他们所从事、所阐明的新学思想,对中国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实这三种含义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加以区分。另外还有由此三种含义流出的最为后人诟病的流于佛老的学风,以至于元祐更化时期特地下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书。考试官以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5](712页)
这表明“新学”虽然与《三经新义》、《字说》有着重要的关联,但又不完全局限于《三经新义》、《字说》,而是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从狭义上看,“新学”仅仅指代“王学”里面最直接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部分《三经新义》、《字说》,它不但不包括整个王学,而且也不被用来指代荆公学派,就这点而言,“新学”确实与王学存在区别;从广义上讲,“新学”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完全可以用来代替“王学”,作为“王学”的特称。由此看来,全祖望在《荆公新学略》里面把“新学”作为王安石与荆公学派学术的简称,其实绝非什么出于全氏的独创,既是出于常识,也是全氏对于荆公学术思想本有之意、思想一贯的认知与认定,其运用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不但符合新学的实质,还合乎古人分门立派、追根溯源的学术史撰写惯例。
《走出“荆公新学”》把“新学”仅仅局限于《三经新义》、《字说》,在于没有区分历史记载与学术史里面的荆公新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他们可能受了史料所记载的宋人的影响与误导,如文中说:“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做出整体评判”,荆公新学是“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等等。以至偏重于官学的形式,而忽略了思想的连贯性,导致一方面按照宋人的批评将王学分为前期“金陵之学”、中期的官学等三种不同的形态,另一方面却批评宋人将“荆公新学”、“三经之学”、“介甫之学”、“王学”混为一谈。
四 宋儒对新学的态度
其实宋人未尝不研读王安石以前的学术,如程颢批评王学:“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10](231页) 程颐认为:“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10](263页)“王介甫为舍人时,有《杂说》行于时,其粹处有曰:莫大之恶,成于斯须不忍。又曰: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有何不可?伊川尝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给事中,谁看得破?’”[10](322页) “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介父(王安石)之学,大抵支离,伯淳(程颢)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10](359页)朱熹将王安石之解《书》、解《诗》和二程相提并论,称赞王安石解《诗》“始用己意有所发明”等等,只不过其中暗含了将王学一分为二的倾向,对之前王学赞成的多,之后的主要是批评而已。宋人的这一态度,可以从熙宁二年范纯仁对王安石学术与新政的看法那里找到影子。范纯仁云:“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斥公论为流俗,合意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5](683页)从上述范纯仁对于王安石学术的批评看,范纯仁隐然将王学按照为政前后顺序将王学分新旧两个部分。范纯仁赞成王安石以前的经术,而批评新政理念及其具体措施,认为王安石“欲求近功”,背其旧学,以法先王政治之名,操管商尚法言利之术,聚敛天下百姓,违背了孟轲仁政学说。范纯仁对于王学的认识存在相当的偏差,显然没有认识到王学的道与术、经学与新政两者之间的连贯性,也没有领会王安石经学“道全”的思想。不过,范纯仁对于王安石的这一批评论调却很快为后来反对新法新学者所继承,甚至于一直到现在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就连最讲究性与天道的程颐似乎也有这样的看法:“荆公旧年说话煞得,后来却自以为不是,晚年尽支离了。”[10](621页)无疑,这对《走出“荆公新学”》有着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并没有将“荆公新学”、“三经之学”、“介甫之学”、“王学”加以区别对待。从程颢在熙宁初“新学”名称尚未出现前批评“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10](121页) 到“对塔说相轮”讥讽王学不正杂于佛老再到“参政之学如捉风”[10](421页),而讥其支离牵强。 以及前面范纯仁批评王安石操管商尚法言利之术,聚敛天下百姓、掊克生灵,可以说基本上与元丰后期“新学”出现之后宋人对于王安石新法学术的批评可谓如出一辙。这充分说明了“荆公新学”、“三经之学”、“介甫之学”、“王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交互使用。既然如此,批评《三经新义》、《字说》与批评王安石以前的学术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由于《三经新义》、《字说》与新法结合更加紧密,而且在形式上被立为官学,要打倒王学就必须先推翻《三经新义》、《字说》的官学地位。至于宋代理学家对于王学的批评或者赞扬,从伊川尝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给事中,谁看得破?”[10](421页) 看来,并不能说明理学家真的就赞扬旧王学批评新学。在同样发明道体、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追求的理学家看来,批评王学“于道不纯”、“流于佛老”、“杂于管商”是一以贯之的,是根本的原则性问题,赞扬王安石《易》、《诗》、《书》更多的是对王学学术造诣的承认。
对于宋人特别是理学家对于王学与新学的这种复杂态度,《走出“荆公新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从学术思想来考察“新学”与“王学”的关系,而是依据历史记载,按照是否在形式上被官方规定为官学、以及宋人的批评作为考察的标准,显然偏重于官学化外在形式的层面,如他将“新学作为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等等,从而人为的拉开了所谓“金陵之学”、“新学”之间的界线,而对于两者思想之间的实质联系有所忽略,这样不但将“新学”完全限定于《三经新义》、《字说》,而且颇有些将王学静态化了,实际上也把有着丰富内涵的“新学”概念处理简单化了。其实《走出“荆公新学”》偶尔对此也不是没有认识,如文中谈到“到熙宁八年(1075)六月左右,《三经新义》编撰成功并颁行全国,八年的官学化进程有了成果,王学最终确定为官学。”这里明显就是说王学,而不仅仅指《三经新义》、《字说》。只是他过于受到批评王学的宋儒影响而忽略了。
另外,《走出“荆公新学”》把王安石早期学术形态按照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称呼为“金陵之学”,并且举出大量的例子来加以论证,也很值得商榷。如果按照地域性和原创性这样的标准,显然,王安石的晚年形态更可称之为“金陵之学”,王安石早期学术很多都是在外为官所作,如王安石早年最著名的一些著述如《淮南杂说》等,都不是在金陵时期。相反,王安石的晚年学术全部都是在金陵,因此,无疑比早期学术更可以称得上“金陵之学”。其实,“金陵之学”在史料里面,也没有出现用以指代王安石某段学术思想的指称,而是指王安石的全部或者部分学术,这说明《走出“荆公新学”》在论据方面也是欠妥的。
五 结论
综上所述,《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通过发生学上的追溯,较早地对“荆公新学”概念的精确性与合理性进行了质疑,并且对“新学”与“王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看法,这对于王安石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走出“荆公新学”》没有将历史记载与学术思想史里面的荆公新学加以区分,偏重于官学化外在形式的层面,即是否在形式上被官方规定为官学、以及宋人的批评方面,而忽略了学术思想的层面,因此将“新学”仅仅局限于《三经新义》、《字说》,把王学条块分割成为原生形态“金陵之学”、官学化形态新学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不同的部分,显然有失欠妥,把有着丰富内涵的“新学”概念处理简单化了。不过,正是由于走出“荆公新学”,才促使我们进而对“新学”概念的由来、流变、内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在历史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两个“新学”:一个是见于史料的立于学宫的《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个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这是我们以前王安石研究里面没有注意到的“新学”。走出“荆公新学”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握对象,打破常规,走出不是目的,走出还是为了更好的走进。只有经过走出之后的走进,王安石的学术思想研究才可以达到更高的起点,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6—01—028 修回日期:2006—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