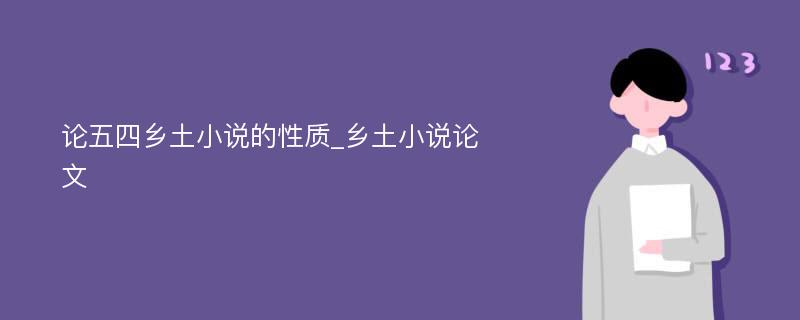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四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 (2000)03—0094—07
就乡土文学研究乡土文学,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一件事。我倾向于从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为什么在五四以后出现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这些乡土文学又是以怎样的艺术资格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潮流,乃至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的?这一论题要说的话很多,只能先从五四早期小说谈起。我们注意到“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鲁迅先生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在那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1](P247 )这里实际是说五四的乡土文学作者是在自身“侨寓”于乡土之外的文学创作,而他们所写的作品并不能算是“侨寓文学”,意思是说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异域的情调,来开拓读者的眼界,从而让读者得到作品的新鲜感。鲁迅这样谈论问题是基于五四时期强调小说创作向西方学习,广泛地借鉴外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借此让中国小说内容和写法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动。这正如他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时说过的,他开始写小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说到他写作《狂人日记》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2 ]( P511—512)这其实并不表示他的作品以及五四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说五四乡土文学没有异域特点,也许可以表明他们吸收外国文学不够,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不是旧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新文学,这一点是鲁迅没有加以否定的。那么,乡土小说在五四新文学的大潮中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这一个问题并没有被我们注意并很好地加以研究。
一、五四小说的思想革命意义与乡土小说现象
五四作家多是从乡间来到城市,然后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但是他们在文学启蒙之初却没有、或者很少写新奇的城市见闻,而是反观乡土,从而写出了一批乡土题材的小说,这一现象是值得很好研究的。这表明他们熟悉、也热心农民题材,或者说从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上是重视农民问题的。
对于一个古老的农业中国来说,历来的革命问题、生存问题、现代化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变动问题、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中国的任何变动,归根结蒂是一个关系农民生存与命运的变动。李大钊说:“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农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P648 )由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背景,也就形成了中国人性中的比较普遍的农民情结。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直觉情感、心理结构、个性性格、文化习惯、生存方式、人生理想、习俗积淀,无一不打着农业经济的烙印。在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革命家与文学家的思考是不约而同的。其实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大都有思想家的气质。这一点是我们思考问题时不能忽视的。这也就是五四以来的许多作家自觉地热心于乡土文学的最根本的原因。
五四文化革命、文学革命孕育了新文学。但是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以新诗打头的,小说、散文、戏剧也相继出现,这前后之间相差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人们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文学从整体讲是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产物。李大钊早在1916年《晨钟报》的创刊号上就发表《晨钟之使命》,论及:“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4]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如此。在1918 年所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之关系,他说:“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因此,他认为:“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5](P581 )这不仅可以看做对俄国文学的概括,也是对中国正在兴起的中国新文学发展趋势的希望和极好的预言,而且也是被后来的文学发展事实所证明的预言。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就明确而不无偏激地提出一个中心思想,主张中国必须“改弦更张”,不然“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他说,中国旧有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近于千年,甚至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这显然是从整体文化上着眼来考虑问题的。早期的文化先驱者注意文化的改革而不仅仅从文学上思考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鲁迅早期的杂文多是讲的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杂文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议论社会问题的兴趣所生出的文体。周作人在1919年写的一篇杂文《思想革命》中讲到思想革命是高于文学革命的:“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6 ]鲁迅在给徐旭生的通信中也谈到思想革命的重要。五四文学是带着思想革命的使命而来的,为着思想革命的目的而产生、发展的。思想革命是风头,文学革命便以自己具有个性、具有能动的气势烧起了旺盛不灭的野火。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五四新文学首先具有思想革命的性质。即使十分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格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小说是“遵奉前驱者的将令”的创作。这表明作者考虑小说所应该负载的思想启蒙意义远远超过了仅仅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实际上能够承担的社会职责;或许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是把文学的革命意义看成最高追求,革命性是第一位的,而艺术的追求是第二位的。只要看到这时期出现的小说家、文学家有相当多的人后来并未从事文学创作职业的情况,就可以明了上面的判断大致的不错。
纵观五四小说,我们可以认为当时作家们创作都是有所为的。适逢其时出现的郁达夫、郭沫若、周全平、王以仁、陶晶孙、庐隐、冯沅君等作家的个性主义小说,冰心的现实问题小说,王统照、叶绍钧、王鲁彦、许钦文等的社会写实小说,虽然风格各异,却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他们或者从反映下层人们的不幸上表现,或者从述说个性压抑上加以表现,或者是发现了有别于封建文学陈腐气味的清净、纯洁的题材,如童心、母爱和自然等等。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许地山的小说似乎有些特别的不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像他那样宗教气氛很浓的小说,居然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喜爱。他的作品难说是表现了真实的人生,也难说他小说中那种处理人生的方式就一定值得世人仿效。但是他却能够得到大家欣然通过,这就说明了当时的读者想从文学中寻求解放声音的如饥似渴的程度。《命命鸟》中的世家子弟加陵和俳优之女敏明之间恋爱毕竟是自发而且纯真的。他们在不能达到愿望时便情愿在月夜里双双“走”入水中殉情。作品中写他们“好像结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衬托着树林里萤火的闪烁,好像来赴他们的喜宴。这真是一首迷人意境的诗,不像是去死的气氛,倒有如人生的庆典。从现实性讲,这样写未免失真过分,但是因为服从了追求婚恋自由这样一个大主题,并不被看做是荒诞不经的胡闹。《商人妇》中的借官好心地送丈夫到南洋谋生,倒酿成丈夫抛弃她、还把她卖给了富商作小妾的后果。被生活折磨得几进火坑的惜官有着封建社会许多女性所共有的性格特征,作品这样写也并无多少新意。但是正如《命命鸟》中的恋人的宁可殉情也不向旧势力屈服,惜官在听天由命思想的支配下,却也并未让自己消沉下来,用了强大的承受力生活下去。《缀网劳蛛》中有更浓厚的宗教情绪。人生就好像自己制造了网,又不断地补缀。补缀不免有消极的意义,但是这种行为中混和了人生的无奈和执着,也表现了顽强生存的主题。总而言之,不管这些小说的倾向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性,它们毕竟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自觉地以封建文学中礼教文化为排斥对象的,都关注了具有反封建和启蒙意义的主题。
乡土作家来自乡间,而不热心写城市生活,首先就是他们的文学革命意识的强烈。他们是以文学这样一种形式参与现代文化的更生巨变的。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认识这一点,我们研究历史却不能不理智地看到乡土小说的思想革命意义。
二、五四乡土小说中的中国面影
与新文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乡土小说,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一样,多少总是在“思想革命”意义上取得读者认可的。在新文学开创期,在乡土题材上努力开风气的是鲁迅,他关注最多的是绍兴人的落后和愚昧。他的主要作品《风波》、《故乡》、《阿Q正传》、 《社戏》都以绍兴乡土为背景。语丝派的小说家继之而起。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的小说是将浙东乡土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来加以描写的。地域特点在鲁迅是尽力地加以消解的,作品中的未庄、鲁镇、吉光屯、寒石山,都是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整体典型加以表现的。作者固然写了许多风俗世象,但是这并不是独特风俗的渲染,似乎也看不出“乡愁”。鲁迅真正着力加以表现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中国古老的文化气氛。鲁镇的封建专制、皇权观念、礼教陋习、陈腐空气、庸人风尚,这一切曾经使夏瑜不但寂寞地死去,还不能免于用自己的革命热血喂养中国的愚昧;祥林嫂丧命集中了中国妇女苦难命运的大成;还有七斤一家闹了一场虚惊,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吉光屯里的人们围绕着对长明灯到底是吹熄、还是任其长明,展开了关乎生死的争论,结果是主张吹熄的人被打成了疯子,那一盏灯“绿莹莹”的小灯火亮个没完没了,实际上象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悲剧在寒石山也一样在上演着,那里的人们都沆瀣一气地逼迫觉醒者变成了孤独者。
还有阿Q无端被杀。阿Q这样的生命在中国并不希罕,但是他的死却离奇得值得写一个传记。鲁迅写小说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格调的,这样写也是为了让疗救者注意农民问题。对闰土、祥林嫂体现了“哀”多于“怒”,对阿Q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原因也耐人寻味。 鲁迅的小说虽然对国民性的愚昧多讽刺和鞭挞,但是他对女性常常留着情面,祥林嫂未必少愚昧,但是在旧社会女性比男性所受的苦更多几重,作者不愿意再过多地清算她所应该负的历史责任。只要女性不是像“杨二嫂”、“阿金”那样“伶俐”和逞能,作者总是手下留情的。闰土的精神麻木因为连接着“迅哥儿”的友情便多写他的不幸:“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无疑是故事语境谐和的要求。但是对于阿Q的描写则呈现出“怒”多于“哀”了。阿Q属于整个中国,鲁迅把他当做解剖民族劣根性的一个样板进入故事, 阿Q形象的“乡土味”于是被淡化了,反之其“中国味”则被强调了。未庄是虚拟的一个村庄,赵姓与钱姓也是任意设置的。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性带来了普遍性、典型性的艺术效果。鲁迅说过,他的阿Q 虽然生活在绍兴,但是他的形象“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至于示众的场面,“我用的是那时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着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个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作大车,七斤也可以叫做‘小辫儿’的。”[ 1]( P147)有意削弱阿Q的地方乡土性特征,强化他的民族性特征,只是为了实现其创作思想,即表达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与鲁迅同时期创作乡土小说最具相通构思的是同乡许钦文。他的《老泪》早于鲁迅的《祝福》,不知道他写的黄老太太到庙堂中赎罪的情节是不是启发了鲁迅写祥林嫂的“捐门槛”。但是我们知道鲁迅的《幸福的家庭》是“拟许钦文”《理想的伴侣》的。他的乡土小说与鲁迅的创作思想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上有共同点。他像鲁迅一样也不是不写风俗画,但是正如鲁镇的冰冷和阴郁,他的作品中也少欢容而多悲哀,以表现出当时作家所崇尚的平民意识。同为浙人的许杰创作的小说中,悲惨故事也多与反礼教这一个社会问题相关,《大白纸》中的香妹被不合理的婚姻逼疯、远卖,《赌徒吉顺》主人公沦为赌徒之后竟然典当了妻子。许杰在《飘浮·自序》中说,他写的都是“无灵魂的人生”。王鲁彦的笔致冷峻而且深刻。他写的《一个危险的人物》、《阿卓呆子》、《自立》、《鼠牙》多是写愚昧无知的人群冷漠,也有鲁迅之风。尤其是他的《柚子》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一点沈从文也看出了,他说:“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氛遮没了每个作品,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正是《阿Q正传》支配到大部分人趣味的时节, 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7](P180)因为题材的趋同, 连风格也逼似的范例并非绝无仅有。台静农的小说《红灯》、《人彘》、《新坟》、《负伤者》、《天二哥》也多写礼教压迫之下的人们的愚昧和不争气。这也是参与新文学革命变动的有力表现,只是他们在题材的提炼上总是不如鲁迅来得更为集中而且痛切地深刻。
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中我们应该谈到的还有语丝派小说家冯文炳。他的乡土小说与同时期的乡土小说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使他成为20年代语丝派为主导的乡土小说与30年代的京派小说之间的一个中介人物。鲁迅说过,废名的小说从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1](P223)。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 我们也许并未留心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和《社戏》中的一群可爱的娃娃们与京派小说之间的联系。因为鲁迅的独特艺术选择,他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多写人生悲剧苦痛,但是他也通过孩子们的身上描画了中国农民质朴的人性之美:闰土身上勃发的生命力与自然之美融和得如此地恰到好处;《社戏》中孩子们的质朴和天真又富有智慧正是极古朴的农民所固有的美好性格。这一题材在鲁迅的小说中并没有能继续下去。我们似乎只有在他的回忆散文中大略了解到他的这一追求。但是语丝派的冯文炳在这一题材上把文章作到了佳处。
其实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语丝派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鲁迅为代表的干预现实、热心于社会批评的“人生倾向”;一种是周作人代表的追求宁静、恬淡、纯真的“人性倾向”。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入世”与“出世”两种倾向走向现代的新风度。“人生倾向”虽然反儒家,但具有儒家思想内核,是“有所为”的;“人性倾向”并不说继承道家,他们的文学意境多少带有道家的恬淡和佛家的解脱味儿,在他们那里是“一切静观皆自得”。“人性倾向”的作家除了周作人,最集中的表现者就是冯文炳。这在周作人也是承认的。也难怪冯文炳的所有书都由周作人为之作序了。冯文炳已经与五四时期众多的小说主要构思路向不同,强调通过文学净化人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容易复活的文学意识。它后来一直顽强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创作思想。冯文炳后来发展为废名。语丝中的“人性倾向”也就变为京派文学的主调。
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性质
我们在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中,一来从时间、空间和内容上把乡土文学限制得过于狭窄,二来又常常把乡土文学当成民间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不利于我们进行文学研究的。
首先,我认为乡土文学不能只是五四以后特定情况下的文学现象。要研究这一个问题,只能从题材上加以认定,并且将这一题材现象加以扩展,才能准确地把握问题。
再有,不能把乡土文学当成民间文学。乡土文学与民间文学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由于以上的误会,我们很容易发现“乡土文学”与“乡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名实相悖、名不副实的三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毫无疑问,乡土文学是作家乡土情结的产物。可是,从乡土文学的作者看,乡土文学大都不是在乡人所作。这有点像鲁迅所说的隐士的概念。鲁迅说,真正的隐士是乡间的农民,他们“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没有时间吸烟、品茗、吟诗作文,一称为隐士,倒是不怎么“隐”了。[1](P223)乡土文学这样一个词, 从字面上看有点类似“土特产”,一般人也是这样认识这种形态的文学。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土特产是指囿于一地的地理、气候、人文等条件长期传承、积淀下来而形成的某种地方性很强的物产。文学如果真如土特产那样,就不叫乡土文学,而应该叫做民间文学。五四的“乡土文学”作家差不多都是生在乡土,而又离乡背井,只身乡土之外才开始创作,至少是在心灵上有一个逃离乡土的意识才产生真正的乡土文学。这一事实表明,乡土文学作家大多被来自乡土以外的新文化思潮激动或者裹挟,从而关心着乡土以内的世界;从而又关心乡土以外的世界。正如创造社成员身在国外却以强烈的爱国感情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化。因此,我们进行乡土文学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层性质。这种现象可以叫作“离乡反观现象”。反观,实际上是一种反思。纯粹的迷恋故土,并不能产生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因为一处乡土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封闭性环境。在封闭的环境下,人们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没有气压的变化就不会有风雨和激流,就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文学。乡土文学实际上不过是用乡土题材写成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与其说它们忠于乡土,不如说忠于中国某一时代。浏览中国现代的乡土文学,每一个时期,乡土文学负载的文学任务是并不相同的。
第二个现象,从作品的接受者来看,乡土文学多半并不是写给乡人读的。当时主要是考虑给知识分子阅读,以激起他们改革的兴奋和思考。这一特点来自晚清启蒙主义者的影响。我们知道晚清思想启蒙时期,中国文学有一个让人最不满意的现象,就是当时的文章是:俗者滥而不雅,雅者矜而不俗。晚清的大量白话小说泛滥,简直可以说那时有过一个白话文的运动,但是这些作品多思想陈旧,缺乏现代性,还不能从根本上取代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作为新思潮的梁启超等人的“新文体”,思想激进、热烈,可以代表当时的启蒙意识,可是他们的作品采用的几乎都是半文半白的语言,用这种文体是不能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因此大力提倡白话文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艰难境遇的考虑,他们要写得既通俗,也要思想崭新。这二者都做了巨大的努力,可是通俗也还是向着知识阶层开放的,他们的作品如果硬要给乡人看,人家多半也并不一定感兴趣。鲁迅写的小说,他的母亲也不喜欢读,她说她还是爱读张恨水的小说。鲁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8](P24)赵树理的那位二诸葛式的父亲不仅不爱读鲁迅小说,也不会爱读赵树理的小说。这就很明白地表明乡土文学有乡土以外的特殊追求。这一点,新文学的倡导者其实是很明白的。鲁迅的书当然有浓厚的农民情结,但是他是“写”农民,而不是“写给”农民的。《故乡》根本不是写给闰土们看的,而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所以从五四开始就有提倡文学大众化的说法。看来通俗化与乡土化实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第三,从创作思想看,乡土文学的构思并不局限于乡土,而常常是笔在乡土,心向华夏。换一句话说:作家关心的“农民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农民关心”的问题。农民关心的是什么?阿Q 每天关心的是为头上的癞疮疤辩护,同王胡比捉虱子能否取胜,与小D 打架能否赢等切近的利益(?);闰土关心的是衣食、儿女、祭祀;爱姑关心的也是她的离婚问题,更准确地说关心的是她自己不让丈夫给赶出去。作者与主人公思维的区别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表达的:“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二者并不相同。我们注意到周作人在1923年为刘大白的诗集《旧梦》作的序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谐和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9](P117 )这与鲁迅说过的“有地方色彩的,容易成为世界的”[10](P391)意思大体一致。他们的意思可不是主张把文艺的题材拘泥于乡村,而是让乡村走向世界。这又是我们常常误读的。
所以,乡土作家关注乡土问题,归根结蒂,他们在关心人生的同时关心的是人性问题。了解这一个特点就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从而比较准确地认识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科学地位。不过,要认识文学的基本规律,必须排除来自许多方面的障碍,一是来自作者自述的局限;二是来自史家的偏见。也就是说历史现象有时是比较隐蔽的,有时表现得比较显露;有的表现得直接,有的表现得不那么直接。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能仅仅靠作家自己公开承认的创作意图,虽然那一直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最权威的。实际上,除了这一层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沉淀在作家内心和沉淀在大众内心的、时时影响着作家的集体文化意识。这比起作家临到拿起笔来时想到的创作目的要重要得多。因而批评常常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发掘。这是我们研究文学常常忽略的方面。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就说过,把作家的“创作意图”视为文学史是十分错误的。“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历史重建论宣称这整个累积过程与批评无干,我们只须探索原作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即可。这似乎是不必要而且实际上已不可能成立的说法。我们在经历批评历代的作品时,根本不可能不以一个二十世纪人的姿态出现:我们不可能忘却我们自己的语言会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我们新近培植起来的态度和往昔给予我们的影响。我们不会变成荷马和乔叟时代的读者,也不可能充当古代雅典的狄俄尼索剧院的观众。想像性的历史重建,与实际形成过去的观点,是决然不同的事。”[11](P35 )考察乡土文学的现代性质不仅是要给乡土文学一个准确的存在判断,也是同样有着当代意义的一个问题。
20年代的乡土小说虽然各具自己的性情,但是他们又都服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整体思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行为的直观性与其目的性之间总是难以修成一条豁然敞开的通道,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文化现象。立足于表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或者解决社会问题,当然是一种五四精神最为直观的表现;但是立足于写乡土人性的落后与经济之落后交织的情形也是五四思想革命所关注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讲“历史乃当代史”的历史,现代性理论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野蛮人的思想》(或译为《野性的思维》)的人类学理论,也都是为了研究当代世界文化。但是在小说创作中强化一种主体意识或使命意识,恐怕不是今天的青年读者和评论者所感兴趣的创作倾向,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另外加以讨论的。但是王元化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经征引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艺术作品可能是某种思想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作者在他创作的时候听从了这个思想,而是因为那作品的作者被现实的事实所征服,而这思想正是自然而然地从这种事实中流露出来的。”然后他说:“作家在写作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效果问题,但是,这种考虑首先必须尊重生活的真实,不能违反艺术的规律。只有在作家的思想感情适应并服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情况下,他才能使自己关于社会效果的考虑步入正轨,否则就会出现有时令成功的作家也难免感到不安的二元化倾向,这也就是说,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潜在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强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牾的矛盾,从而造成思想感情本身之间的分裂。这势必破坏了艺术必然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12](P73)所幸的是,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家多是有丰富生活阅历的。 他们的创作即使是有些单纯的,也并未发生那种“不安”。
收稿日期:1999—12—01
标签:乡土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乡土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故乡论文; 社戏论文; 冯文炳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