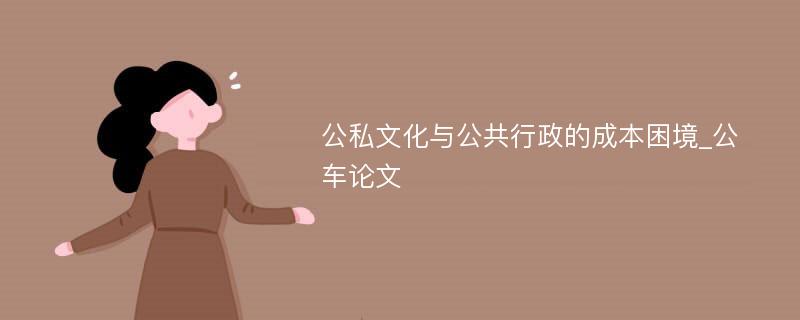
公私文化与公共行政的成本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私论文,文化与论文,困境论文,成本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私不分:行政成本困境的文化根源
公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观念中,一直存在着扬“公”抑“私”的成见,认为“公”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公”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皇帝、平民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文化领域大一统局面。社会对“私”价值的否定造成了个人对“私”追求的畸形发展,这种畸形发展表现为人们总是把对“私”的欲望隐藏在“公”的范畴之内。于是虽有“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管子·任法》)的说教,却仍不能阻止假公济私行为的出现。“以公废私”(《周官》)、“废私立公”(《管子·正》)的结果是对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个性的极度压抑。中国公私文化对“公”的过高褒扬不但压抑了人主体性的发挥,同时对人性恶的一面缺少思考,一味追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仅从道德范畴靠人的自觉来限制自身,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中国传统公私文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公私不分,而正是公私不分对当代中国行政主体的影响造成了公共行政的成本困境。成本困境表现为政府的花费不断攀升,虽然政府自身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精减机构、节省花费,但中国的现实是,政府的行政成本就像一根弹簧,一压就缩,一放就伸。这与中国传统的公私文化不无关系。传统的公私文化提倡道德自觉性,忽视制度化的措施,这就为行政主体的徇私提供了可能。显然,借“公”的名义行私是导致高昂行政成本的祸首,对于降低行政成本来说,无论治标还是治本都有必要在公私问题上下大功夫。
行政成本即政府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活动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由于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一直将自己视为“公”的化身,因此他们总以为只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花费公共资源。由此,中国的行政成本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9.13个百分点”[1]。全国政协委员姜笑琴甚至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2]另一种情况就是假公以济私了。显然一些行政官员在“公丑忘私”(《新书·阶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把一些正常的个人私利的获得当成是丑事,掩掩藏藏,最后竟然闹得分不清公与私了,当然最后遭了殃的还是公共利益。有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的公车消费达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全国1年的公款吃喝达2000亿元以上,两项相加高达6000多亿元,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此外,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资源就达3000亿元;2000年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3]。另“有资料显示,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3项合计高达6000亿,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4]。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徐创风认为,行政高消费应缩减一半。尽管统计数字可能有所出入,但中国行政费用高昂,而高昂的行政费用有不少是私人消费公家买单,这是事实。显然,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问题,是造成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要办公事,少不了用公车,但公车是否完全用于公事?有人估计,许多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其所有使用时间的1/3,其余时间分别被领导和司机用于办个人的私事。办公事,少不了起码的接待,但是否需要大吃大喝?同时,有多少推杯换盏是个人消费公家买单,也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出国考察和学习很有必要,但是否有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等,内含着种种以私乱公、公私不分的现象。在各种行政费用中,如能挤出“私”的水分,无疑将节省一大笔纳税人的血汗钱。
以公乱私、公私不分,显然是与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的“廉洁”文化相违背的。就现代政治而论,行政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因人民的利益而设的,归根结底要为民众谋福利的。为权力的行使所配备的各种设施、便利以及掌权者所掌握的各种资源都应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民众利益服务的。行政资源来自于民众,是人民群众用赋税等形式积聚起来的、支撑行政权力运行的物质,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体恤民情、珍惜民力。公车私用、个人消费公家买单把公共权力和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公共财产用于谋取公务人员的私人利益上,违背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二、传统公私文化前在预设的结果:公共行政的制度贫困
传统立公灭私的文化观念造就了一个理想化的道德主体,并使该主体逐渐脱离了正常人的发展轨道,成为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圣人”。显然,中国传统的公私文化为国家的治理者预设了一个前提: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为了实现“公”的利益而努力,因此,他们无疑都是“圣人”,都能靠道德进行自我规范。既然国家的管理者都是“圣人”,那么就不存在对其进行制约、监督的必要,制度化的国家治理措施显然就显得多余了。这样的传统文化造成了3个结果:其一,造成了中国制度化管理的长期贫困;其二,造成了相对于“公”领域(国家)来说极端弱小的“私”领域(公民社会);其三,造成了社会上出现大量“行公道而托其私”(《管子·君臣上》)的“假人”。这3个结果对当代公共行政的影响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制度贫困造成了公共行政活动缺乏明晰的财政预算制度和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到底需要多少钱,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人好好计算过。各级财政预算也很不透明,各级政府每年的行政费用怎么花,老百姓一无所知,甚至连人大代表也懵懵懂懂。预算的弹性和模糊,使各级行政机关不必对行政费用进行严格控制,不必精打细算,对浑水摸鱼的现象听之任之。财政预算不透明,公众对行政费用无知,自然也就谈不上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可以说,政府财政预算缺乏应有的刚性约束,是公款私用的祸根。公款吃喝屡禁不止还因为监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手段和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比如,对众多“吃财政饭”的单位而言,招待费标准是多少?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人员可参加公务接待?一年该花多少招待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在那些大额的招待费发票上注明的都是“招待省、市领导”、招待“县里来客”等模糊文字。哪些人吃了?究竟吃了些什么?无从知道。从财务记录来看,招待费没有明确的原始清单,只凭一张汇总的招待发票就可以做账。正如政协委员所说:“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万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1]如此松懈的管理,难免有漏洞、出问题。
2.极端弱小的“私”领域(公民社会)形成不了对国家进行有效社会舆论监督的外部监督机制。
传统的公私文化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起来,以“公”为体现的“礼”(儒家)、“法”(法家)、“义”(墨家)把君主、国家置于市民社会之上。传统的公私文化一向把“私”作为与“恶”相等的事物,因此它对私人力量极端蔑视,故应以“礼”来教化,以“法”来制约,以“义”来使其相互爱护。这个文化传统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市民社会缺乏对国家进行有力监督的自信,形成不了有力的制度化的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的治理者忽视民意的存在,我行我素。这样,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些人不在领导岗位时,这些人对腐败深恶痛绝,但一旦他们上升到领导岗位时,就开始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办事。甚至一些人公开表明,假如他在某个位置上也会大捞一把。这样,市民社会在中国开始畸形化: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这些意识增强的公民却以脱离市民社会、加入国家体系为目的,极力追求国家权力,而不是壮大市民社会,以对抗国家权力。换言之,公民对权力的追求不是以壮大市民社会为目的,而是以寻求进入国家体系为目的。因此中国市民社会的主体本身就带有传统公私文化赋予他们的劣根性。这样,极端弱小的市民社会根本监督不了强大的国家,行政成本花费的外部监督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缺失了。
3.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在造就一批“假人”的同时,严重阻碍了行政成本核算制度化的形成。
官本位意识是指以拥有权力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的官至上观念。受官本位意识附身者,以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我们称之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假人”。对这些“假人”来说,隐藏在权力最大化目标后面的,当然是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当了官似乎就要比别人更阔绰些。但现行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显然与他们的期望有差距。于是他们在工作待遇上寻找补偿,千方百计揩国家的油。一些领导干部特权思想还很严重,认为当了领导干部,就应该享受各种服务,把公车送迎(无论为私还是为公)视为理所当然。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竟把家庭的日常费用让公家来买单。如原广东汕尾市原市长马红妹落网后,检察官问她为什么把水果、鸡蛋、面包、衣服、油、米等家庭消费品也以公用品名义报销时,她竟然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以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我花人民的一点钱算什么?”检察官再问:“你知道什么叫公仆吗?你能算公仆吗?”马红妹嘀咕:“公仆就应该是公家包养嘛,怎么就成了贪污犯?”[5]一些不检点的干部,甚至延传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思想,把其特权荫及其家庭成员。在一些权势者看来,谁能占有、享用越多的公共财产,谁就越有本事,越风光;一些腐败分子,甚至把越能不守规矩看成是越有势力、有面子的表现。这些人造成的危害不仅在增加行政成本本身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掏空了制约行政浪费的制度,使行政核算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三、走出成本困境:从公私文化的视角分析
中国公私文化所主张的“立公灭私”、“崇公抑私”是传统治国之道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其所追求的是大公无私的政治境界。如果单从把大公无私的大同世界作为追求的理想来说,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采取极端的对私完全否定的方式并不能使“公”的利益得以保障。相反,对“公”的刻意追求,采取无“私”的措施,反而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公私两无”[6](P351)。那么如何在公私问题上做文章以减少行政成本?我们认为应该在文化建设上倡导公私分明,在确保“私”的应有地位的同时,从制度上保证公私不相侵,使公私分明成为公共行政的常态。
首先,对人性中的自私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人有私欲是不争的现实。人的私欲在个人道德自觉心不够强且缺乏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就容易膨胀,容易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有意或无意的侵害。在干部队伍中确实也有一心为公、鞠躬尽瘁的人,但相当多的人还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廉政建设要以多数人的思想境界为基点。无视人的自利的一面,要求人人都成尧舜,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何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坚持扬善原则,即假想人性本善,并通过道德教育来扩充人的善性,最高的境界就是“圣”。近代以来,西方主要是坚持抑恶原则,即假想人性为恶,并设想出种种办法来抑制恶性膨胀。人性是善还是恶,是公心多还是私心多,很难说得清楚,但在制度建设上还是把人当作“经济人”为好。休谟的无赖假定对于制度建设有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他说“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不这样的话,“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和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7](P27)。布坎南认为,“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也是利己和理性的,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说:“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81(P341)尽管布坎南的经济人假设的普遍性及其在政治领域的适用性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但至少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每个人都要仔细斟酌自己的利益,不要对“政治人”心存太多的幻想。假想人性中有为私、为恶的一面,我们不应殚精竭虑去灭私,而应明晰公私界限,让一己之私不敢损害他人之私和公共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最应强调的。
其次,实行财政预算和支出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应该尽快把部门预算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强化预算约束,全面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杜绝大笔公共财政资金随意支配现象的发生。要把政府支出置于阳光之下,除涉及国家安全、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以外,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预算都应向社会公开,部门的预算草案应该提交各级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和支出的法制化、民主化是杜绝公私不分之本。民主是具体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应该包括知晓政府财政开支情况的权利。因为政府的税款来自税收,如果公民连政府的税款用在何处都不得而知,这就很难说是人民当家做主。公民没有知情权,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让公众主导事关官员福利和政府运行成本就叫民主财政。暗箱操作,以私乱公的现象就不能得到遏制,政府的行政费用就要扩张。我们都在要求村财政公开,为什么不能做到乡镇、市政府财务公开?
再者,明晰公私界限,加强监督。
当一种物品的归属不明确时,受利益驱使的人们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其占为己有。法家的重要人物慎到曾说:“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免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慎子·佚文》)如果在制度上分清公私、你我,限定什么行为应该被禁止,违规者应该得到什么的惩罚,人们自然就会好好掂量一下损公肥私的成本。我们过去在舆论方面宣扬“为公精神”的多,在防范以私乱公的制度建设方面则少,以致于一方面是大公无私的道德宣传,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损公肥私现象。
为了减少公车私用的现象,各地政府正在实行交通补贴制度。但到底应该补贴多少,什么人应该享受补贴,又成了问题。如威海市公车费用达5200万元,车改后,政府公务人员按照级别每月领取200~2400元不等的交通补贴,据说1年可以节省交通费用41%左右。有人支持,也有人提出非议。非议者认为,领导干部一年领取的交通补贴相当于几个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以普通工人每月1000元计算)。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的“节省”还不是真正的节省。按照一般的估算,公车私用占去了所有公车费用的2/3。所以,确定补贴的数额,首先要把公车私用的那部分费用剔除出去,然后在这个基点上节约。如果以现有的包含很多水分的公车费用为基点来计算,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公车私用合理化了。
应该说,西方一些国家保护公共财产的制度是比较完备的,在禁止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物私用方面的规定比较具体、确实有效。如瑞典用电脑帮忙遏制公车私用,车上有“公务”、“私车”按钮,必须按下一个汽车才能启动。博茨瓦纳的公务车为“红底白字”以与民用车区分,使用另类的粉红色汽油,在休息日提供这种汽油的加油站都休息,公务车无法加油,总统也不能例外,遇到节假日只能使用自己的车,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腐败的发生。芬兰的赫尔辛基市政府,则干脆规定只有一人即市长享有使用固定公务车的权力。制度的规范使他们不得不公私分明,如果他们公私不分,侵犯了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治丑闻,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意大利锡耶纳市市长布赞卡因妻子搭乘其公务专车违法,被判6个月监禁。澳大利亚有位叫彼得·里斯的部长,其仅能用于公务的电话卡被儿子用于私事,被媒体披露,舆论哗然。事后,他尽管补交了电话费,保住了部长的职位,但本来看好的政治前程则因“小事”变得黯淡。瑞典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此事被发现后不得不辞去职务。有制度规定,又有前车之鉴,公务人员自然就要谨慎处理公私问题。
但目前,在我国用公家的手机或电话办私事、公车私用、公款消费、公款旅游似乎不算真正的腐败,不会成为政治丑闻,更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人把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归为“亚腐败”。所谓的“亚腐败”就是还不到腐败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制度处罚的程度。笔者认为,上述行为就是腐败,与盗用国家财物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于上述腐败,仅仅舆论引导是不够的,必须有制度规范。如实行招待管理“实名制”、定期公布招待费开支情况、对那些滥用公共财物的给予处罚等。此外,我们应该发动全社会进行监督,形成对滥用公物如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应该发挥作用,对那些公车私用等现象进行曝光,有关部门要对举报者给予奖励。
最后,在全社会普遍进行“公私分明”的教育。
我们的传统价值取向是“崇公抑私”、“大公无私”,但另一方面,国民又往往对公共利益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公共财产缺乏应有的珍惜。公家的东西好像是免费的午餐,谁都想更多地占有。大公无私确实值得赞扬,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此,我们在对那些公而忘私人的赞赏之余,社会舆论、道德宣传应该把重心放在公私分明和公私兼顾的观念上。对于一个公务人员来说,不是停留在“大公无私”的道德灌输上,而是要他们理解权力的“公”的属性,把公共权力用于服务社会。我们反对“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但不因此就要人做到“大公无私”,而是要所有的人都做到公私分明。对公务人员来说,在公务上要秉公执法,但在公务之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以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这种现实、宽容的态度,要比一方面要求大家都来做尧舜,另一方面又存在不分公私的社会更健全一些。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腐败丛生,但崇尚公义的传统也确实培养了公私分明的清官,他们可以成为现代公私分明教育的资源。南宋诗人周紫芝在他的《竹坡诗话》中,记载这样的故事:李氏家族有一人当官“极廉洁”,公是公,私是私,泾渭分明,分毫不苟。有一天,他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家书。他便灭掉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阅家书。明朝的海瑞,一日办完公事后,顺便去探访一位朋友,走到岔路口,他便脱下官服,走下官轿,坐上事先准备好的私轿。在特权流行和缺乏制度规范的古代社会,像他们那样做到公私分明,需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今天,公私分明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一种起码的道德要求。
在西方社会中,公私分明观念也可以成为公私分明教育的素材。在西方,公私分明是对公务人员起码的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打私人长途,要填一张单子,说明这个电话由私人付款。当然,在家里为公务打长途,也要填写表格,由政府付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时,星期天外出,不坐政府配备的高级防弹轿车,因为私事用车,必须按规定付费。为了省钱,他只好用自己的“大众”车。在《中国警官走进美利坚》一书中,谈到一位美国警官带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公家的,一部是私人的。公家的事用公家的手机,私人的事用私人手机。
对于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道德选择,还不如说是权衡利弊的经济选择。很难说美国的警察就比中国的警察觉悟高,而是因为如果家里的电话号码出现在公家的账单上,一旦被追究起来,不仅名誉受损,而且还要接受处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值得学习的。公私分明应该是我们道德教育的基点,做不到这点,谈大公无私就是伪君子,就是自欺欺人。
标签:公车论文; 行政监督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