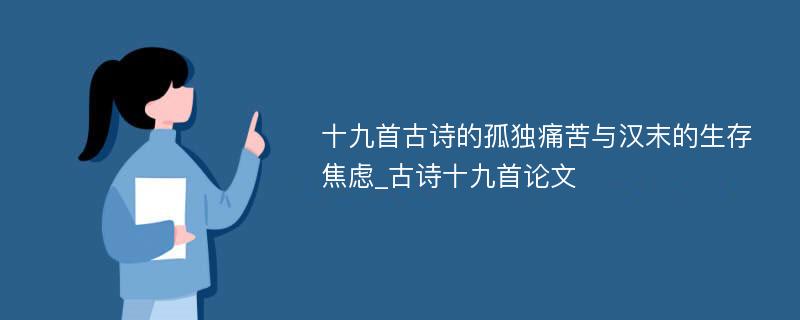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古诗论文,焦虑论文,伤痛论文,孤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不同凡响的诗歌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确非虚言。由于诸多原因,其作者虽有各种推测,诸如枚乘、傅毅或曹植、王粲所作,均无据可考,皆属妄言虚谈。目前学界公论以为,《古诗十九首》约为东汉末期非一人一时之作。
尽管这些作品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我们却发现它们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共性,即都拥有一个颇为一致的主题:对时光易逝的感伤和空间辽远的恐惧,这是寂寞中的无奈,亦是孤独中的伤痛。比如《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流露的是面对辽远空间的畏惧感;又“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是对人生时光易逝的感伤。《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远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说的是人处广袤空间中的孤独。又《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则是人生苦短的哀叹。如此等等,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似乎时时处处都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这一现象实在令我们动情,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古诗十九首》从题材上看,占绝大多数的是游子思妇诗。思妇伤怀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相当传统的主题。《诗经》中就有如《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一些优秀诗作。“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1]这其中落寞无偶的孤独感因主人公的自我宽解而显得多么沉重啊!人生在通常的情况下,夫妻应是相厮相守最亲近的人。尤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她们没有现代女性那样的机会和可能,去参与各种社会工作或进行社交活动。婚后的她们,丈夫也许是唯一的情感交流者和寄托者。丈夫远行了,这唯一的也不再拥有,那种难挨的孤寂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排遣和抚慰内心的孤独感大约应是中国古代思妇诗的主要基调。
《十九首》也不例外。《行行重行行》的孤独感是借时空之辽远、漫长与人生之短暂、易逝间的对比展现出来的。如前文所述,对生离,女主人公先感到的是空间间隔的辽远和漫长。漫漫长路若有漫长人生与之相抵,似还可存终有相守之一念。然而,人生恰恰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竟是那么短暂易逝。这份孤独真如在大漠中独行的旅人时时被死亡提醒般的恐惧。《青青河畔草》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寂寞直言不讳:“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直白的表露不是没有原因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河边的草地发芽泛青了;园中的柳树吐叶变绿了。这节候的变化猛然间提醒了站在窗前的她对时间的记忆。正是“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2]节候向她们提醒着逝去的时光,时光又压迫着她们的孤独。《冉冉孤生竹》的主人公是把自己比作“寂寞开无主”的幽兰,无奈地怨嗟着“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像《行行重行行》一首那样,她也耿耿于“悠悠隔山坡”,道阻且长,会面已不可知。可以说,在思妇诗中饱含的孤独之痛、寂寞之苦大体都是相同的,只是她们各自痛苦的表达方式稍有不同而已。
与思妇相关联的是游子,正是有了游子才多了闺中的思妇。这一种关联也很自然地联带着游子们的孤独。但游子们的孤独似乎比思妇的孤独更有许多异样的味道。因为思妇多是单纯的闺中思夫的孤独,而游子却多了一层在人世间、异乡的人群中那种无助少援的孤独。请看《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严格地说,这是一首游子思乡之作。《古诗笺》注“去者日以疏”句谓:“《吕氏春秋》:‘死者弥久,生者弥疏’”[3],显然是望文生义。《庄子》里有一段话应是这句的前文本,“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其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4]这岂不是所去弥远、弥久,所见来者弥亲吗?“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恰是思乡的情绪。这乡愁的根源一看诗的下文便可知晓,出城门所见的无非是“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这是时光之流带给生命的死亡气息。诗人似独自伫立于时间的旷野,他感到是那么孤独无助,那么悲凉。这正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感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5]这种难以抑制的孤独感不由得勾起了诗人的乡愁。因为故乡是他的根,那里有养育他的土地、山川,有生育他、帮助他的亲人、朋友。也许故乡的这一切能给他的孤独以些微的慰藉。然而,“欲归道无因”,这些微的慰藉也难拥有,他所剩的唯有孤独。
《明月何皎皎》一首比较复杂,论者多以为“这是一首写女子闺中望夫之诗”[6]。但我们觉得拐这个弯着实不如把它看作游子思归之诗来得直接。且看原诗: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清冷的月光洒在床前,越发显得旅人的形单影只,这孤寂之苦搅扰得诗人难以入睡,顿时惹起了他的乡愁,“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持思妇诗论者多以此二句为依据,以为这是思妇的心情和口吻。其实如上一首诗,游子又何尝总是乐不思蜀呢?单单是思妇在盼归吗?李白《静夜思》诗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本诗恰是同一种境界。孤独惹起乡愁,乡愁更加剧了孤独。诗人只好出门独自彷徨,愁思仍无可告语处,无奈的彷徨排遣不掉心中的苦闷,所剩唯有回房独自落泪。孤独缠绕着乡愁像粘乎乎的胶液裹在诗人的身上,他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游子、思妇的孤独是不言而喻的。而那些热衷仕途利禄的官场斗士仍被这孤独所胶着。比如《回车驾言迈》中,诗人倒是悟得了“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但这仍不过是他试图逃脱孤独的一种狡黠。因为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就感受到了世间的空旷。“回车驾言迈,悠悠涉远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在这空旷的世界中,他怎能不孤独?这世界的空旷不仅体现在空间层面上,也同样体现在时间层面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为摆脱空旷中的孤独,诗人只得暂时选择“立身”、“荣名”以为自己逃跑的路径。《西北有高楼》又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诗人首先听到了从远处高楼上飘来的歌声。他于是猜想这唱歌的女子“无乃杞梁妻?”悲苦的曲调牵动了诗人的心。“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女子的歌唱出了诗人心中的苦闷,这就是他难遇知音的孤独。这是诗人在仕途宦海中汲汲追求后而终无所得的孤独。这孤独他无法摆脱,恰好又被与他同样孤独的楼上女子唱了出来。“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这深深的孤独之苦压迫得诗人对人世已有了厌倦之感,他真想与那同孤共苦的女子化为“双鸿鹄”超离这令他苦闷无助的人间。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即使有的在宴饮欢歌、盛友如云的欢乐时刻也不能忘却这份孤独。比如《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如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虽说是“良宴会”,有清歌妙曲,可谓欢乐至极。但是诗人要求,“识曲”要“听其真”。“其真”为何?下文便有交待:人生苦短,应及时干进,不然的话,连这本无数量的短暂人生也同时没有了质量。只能落得个“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的境地。《古诗笺》注“轗轲,不遇也”[7]。显然,“其真”隐藏的是一种对人生必然的孤独和可能的孤独的恐惧。说必然的孤独,是人生短暂,他会在无限的时间中孤独,这谁也无法逃脱,故谓之必然;说可能的孤独,是在短暂的人生中若不能显达,则有穷困潦倒、不遇时、不遇明主、不遇知音的孤独。
有时,这种孤独感把诗人逼到几近绝路。《驱车上东门》的作者满眼弥望的一派死亡的气象,那是松柏夹道、白杨萧萧的墓地。由此,诗人联想到地下死人的寂寞,更想及世上活人的孤独。“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这孤独是谁也逃不掉的,服食成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于是,诗人只好退一步想,“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准备暂时从世间短暂而虚幻的富贵荣乐之中寻求寄托。
《十九首》中即使是歌颂爱情的诗也抹不掉那种单相思式的孤独感。比如《涉江采芙蓉》,诗人述说的是自己采摘芳草、鲜花,准备送给自己的恋人。可是,欲送却不得送,因为“所思在远道”。他只好遥望着通向恋人居所的漫漫长路而浩然兴叹。不难看出,全诗话语背后所潜隐着的那种“同心而离居”的不尽孤独。《庭中有奇树》的表现方式亦如此,同样是“将以遗所思”,而“路远莫致之”的单恋情绪萦绕在诗人的心间。因空间的阻隔,爱情得不到表达和实现而孤独。那么,没有空间的阻隔又会如何呢?在《迢迢牵牛星》中诗人借传说加以想象,回答了这个问题。诗人遥望星空,看到牵牛和织女二星离得并不是很遥远,而是“盈盈一水间”,竟也是“脉脉不得语”。他们同样是孤独的。显然这孤独不单是空间距离造成的,更深的根源在人的心底。其实,这孤独正是诗人内心孤独、苦闷的曲折反映。
细味《十九首》,我们无时不感到诗人的孤独和苦闷。独守空床者孤独,浪迹天涯者孤独,在官场上孤独,在欢歌宴饮中亦孤独。总而言之,居也孤独,行也孤独。喜也孤独,悲也孤独。这无尽的孤独常裹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用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了这千古绝唱《十九首》。
二
造成《古诗十九首》这些作者心中此一份沉重孤独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由作品出发联系其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可以发现一丝蛛丝马迹。而且,以往的论者也多有揭示。
首先,从《十九首》的内容上看,按其咏叹的主题重心虽可分为思妇伤怀、游子思归、热衷仕宦及时行乐、歌咏爱情、友情、感叹人生苦短、年命无常等若干类别,但就题材看,《十九首》却不过两大类:一是思妇之词;一是游子之歌。其它内容也大多是从这两类题材衍生开去的产物。比如热衷仕宦、歌咏爱情、友情等,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这些游子们从不同的经历、境遇出发,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地点所产生的不同心理反应的具体表征。再进一步,就游子、思妇这两类不同的题材而言,其实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正如马茂元所说:“在安定的社会里,正如孟轲所说‘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反之,有天涯飘泊,欲归不得的游子,也就有空闺寂寞,忆远怀人的思妇。这一凸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正替《十九首》安排了时代的题材;《十九首》的作者就是通过这两种题材来写出他们的人生感慨的”。同时“《十九首》的语言,篇篇都表现出文人诗的特色,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8]这说明,表现于《古诗十九首》中的孤独伤痛,其第一个最直接的来源便是其诗作者——那些游子们受压抑的心底。
“游子”似乎并不是一个包含特定历史意义的社会群体。上溯历史到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兴起养士、游说之风,按其生活状态,那些抛家舍业的食客、说客都可视为“游子”。西汉武帝时,开始推行明经取士的政策。史载:“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候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鄉风矣。”[9]这无疑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了希望和振奋,同时也鼓励了青年人读书、游学的风气。当时,武帝还接受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10],把这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在这种政策的诱惑下,大批农民子弟纷纷离开家乡,涌向首都长安和其它一些文化较发达的城镇。这些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读书、游学获得举荐、征辟,以求显达。仅讲《诗经》的鲁人申培“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11]。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子弟也应当说是无家可依的“游子”。可是,奇怪的是我们无论在有关的历史典籍中,还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发现如《古诗十九首》般孤独失意的游子心态,相反,却总有着一股子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
在徐干的《中论》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差异的原因。原来,东汉末年的游学和宦游风气之盛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徐干在《中论·谴交》中描述道:“……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以至于许多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一般说,在同一个竞技场上角逐者越多,失败者也自然越多。结果,正如徐干所批评的那样,那些宦游的士人“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在这样的特定时代,“游子”之名也便有了特定的历史内涵。他们不单是出行的旅人或游学的学子,而更多的是宦游失意的士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所普遍、经常共有的失意孤独心态,恰恰是弥漫于《古诗十九首》中那种孤独情绪的直接原因。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还想从哲学的角度探寻一下它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我们认为这个深层的社会原因就是汉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焦虑”是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克尔凯郭尔称其为“在自由面前的焦虑”。海德格尔把它看作是“对虚无的把握”。萨特直接称之为“对自由的意识”。[12]萨特对“焦虑”这种生存状态尤其关注,他甚至把“焦虑”分为“面对未来的焦虑”和“面对过去的焦虑”。而汉末知识分子的“焦虑”正是一种“面对未来的焦虑”。因为,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将来怎样的问题,而不是面对过去的忏悔,不是昨天已然而今天不然的问题。未来的社会走向何方?我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将是怎样的?这才是汉末动荡年代知识分子普通关心的问题。萨特对这种状态表述道:在我将来的存在与现在的存在之间的某种联系中,“一个虚无溜了进来:我现在不是我将来是的那个人。我不是将来的那个人的原因首先在于,时间把我同他分开了;其次在于我现在所是的人不是我将来要是的那个人的基础;最后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现实的存在物能够严格规定我即将是什么。然而因为我已是我将来所是的人(否则我不会关心成为这样还是那样),所以我以不是他的方式是我将是的那个人。……以不是的方式是他自己的将来的意识正是我们所谓的焦虑。”[13]中国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正是生存在这种“面对未来”而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为加强统治、巩固政权,进一步发展了西汉中期以来的养士、举荐、征辟制度。这一制度确实鼓舞了读书人的“进取心”。但是,随着整个东汉王朝的日益衰败,这种取士制度本身的流弊也日趋严重。知识分子们的进身之路不再像以往那么畅达了。首先是各级官吏在察举中的舞弊行为愈加猖獗。史载,东汉和帝之后,“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14]顺帝初,河南尹田歆所察举的六名孝廉中,由当权贵人勋戚指定者就占了五名。[15]史家评论道:“窃名伪服,浸以流变,权门贵仕,请喝繁兴。”[16]从而致使许多士人“奉货而行赂”。[17]其次,与此相应的,知识分子内部的学风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比如当时家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从杨震之后,四代为三公;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自袁安始,四代有五人位至三公。于是,家学成为显学,许多读书人便把投靠名师、盗取虚名当作了进身的捷径。这样,读书人间的竞争就自然失去了昔日的公平。
以上是汉末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即自身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多数是茫然的,正如萨特所描述的,“我现在不是我将来是的那个人”。因为,他们正面对着将来,作为现在的读书人依照以往的人生发展逻辑将变成未来的官吏。然而,这个逻辑现在已经失灵了,进身的通路已没有了秩序。他们都是前途未卜,就像空中的氢气球,不知会飘向何方。既然如此,那么读书的他,这个“现在所是的人”也就不能构成他“将来要是的那个人的基础”。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现实的存在物”比如学识、德行等“能够严格规定”他们即将是官吏或是什么。他们不能预见自己的命运,却以自己将来的身份关心着这将来,从而深深地陷入到了“以不是的方式是他自己的将来”的“焦虑”之中。
汉末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性的,这就是社会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西汉初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西汉中期武帝时代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全面形成。随着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发展,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也明显表现出来。其标志则是武帝刘彻按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儒家思想变成社会统治思想的同时,经学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明经取士成为两汉官吏制度中一项重要内容。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这一方面带来的是社会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整体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全面建立,带来了社会的安定。整个社会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似乎是在一种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按着既定的思路和方式在寻求着生存和发展。这种局面经过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政权交替得到简单调整之后,到东汉初期达到了顶峰。
但好景不长,到东汉末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表现得日益尖锐、激烈,尤其到桓、灵之际,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党锢之祸”发生之后,宦官控制了朝政,一批大臣接连遭到杀戮。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汉末政治的腐败和堕落在其王朝即将灭亡的前夕达到了顶点。这样,两汉社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便也随之分崩离析了。整个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面临着当时知识分子自身那样的选择,处在“焦虑”之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在日趋塌陷,新的思想和理论支撑点却没有找到。社会一片混乱。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18]“世之衰也,上无胆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19]社会由安定走向混乱,由有序走向了无序。汲汲皇皇,不可终日,矛盾、焦灼、空虚、孤独,这可以说是整个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共同心态,何况是那些与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呢?
社会的发展没有了既定的规定性,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失去了原有的基础和既定的规定性。他们似是被抛向了茫茫的宇宙,没有一点依托和把握。它在情绪上的直接表露更是孤独。汉末广大知识分子正处在存在主义哲学所描述的“自由”面前。可是,“自由”并不总是那么诱人的,相反,却常常令人感到焦虑和恐惧。萨特说“焦虑”是人对“自由的意识”便是这个意思。国内一位学者在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时也说:“‘自由’原来就是一种‘刑罚’。面对这种所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把握的自由的自由存在’,亲在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惶惶失其所在’,感到‘无家可归’,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20]。这正是《古诗十九首》所表达出的那种孤独无依之感。他们慨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迷惘的心绪不由得使他们哀叹“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他们拼命想在历史的漩涡中抓住一根救命的绳索,寻找一分的安定。可是,这一点愿望他们也终究难以实现,于是,他们转而想起故乡这最令人安定的根、居家这令人安定的窝、显达这能暂时平衡心理倾斜的砝码、宴集诗酒这瞬间的心灵慰藉。对《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一份深深的孤独伤痛,海德格尔、萨特等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在上千年之后的另一个地域有了深深的领悟。我们借着他们的领悟,也终于对《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以及他们共同的“焦虑”有所理解了。
注释:
[1]《诗经·卫风·伯兮》,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2]王昌龄《闺怨》,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卷一四三。
[3]王士禛、闻人倓《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4]《庄子·徐无鬼》,据中华书局1961年版《庄子集释》。
[5]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四部丛刊》影印本《陈子昂集补遗》,据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八三。
[6]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上编第1册。
[7]王士禛、闻人倓《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8]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9]《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页。
[13]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页。
[14]《后汉书·曹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后汉书·种暠传》,同[14]。
[16]《后汉书·扬雄传论》同[14]。
[17]徐干《中论·谴交》,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百子全书》。
[18]《后汉书·儒林传》,同[14]。
[19]徐干《中论·谴交》,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百子全书》。
[20]周国平《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