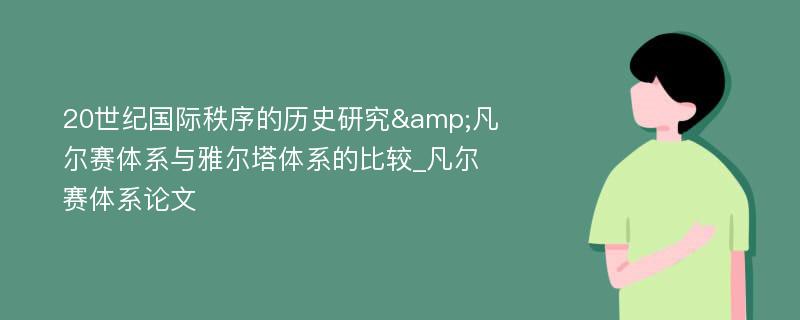
20世纪国际秩序的历史研究——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尔赛论文,雅尔塔论文,体系论文,秩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世纪。先是出现了以国际联盟为支柱的凡尔赛体系,后又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不过,20世纪的国际秩序,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和平的喜悦,也有战争的创伤;有值得称道的功劳,也有不少问题。故此,笔者拟就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作一比较,以便对20世纪的国际秩序进行历史的研究,这对于建立未来“国际新秩序”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首先来比较一下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不同的创立过程。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狂潮席卷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各国舆论普遍支持战争,交战各国抱着短期取胜的如意算盘冲向战场;然而,战争很快进入胶着状态,速战速决成为泡影。直到1917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美国人参战,战争才渐显胜败之端倪。可是,欧洲列强仍然忙于厮杀而无人考虑未来世界的安排,还是威尔逊在1918年1月抛出了“十四点纲领”,率先提出未来国际秩序之设想。他宣称:“征服和追求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论是强还是弱,都享有同等“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他还强调,必须建立各国的联合组织,以相互保证“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①a]然而,到战争结束时的十个月间,协约国并未认真实施“和平计划”。即使战争结束了,威尔逊的“十四点”也并未引起广泛的兴趣,它们被军事上的“胜利”所陶醉,只想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确保长治久安。于是,战争结束仅仅两个月,缔结和约的会议就在巴黎召开了。
但是,缔结和约“与其说是协商解决,倒不如说更象法庭上的判决。”[①b]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相继在“被告席”接受战胜国拟定的“和平条款”。一切都是那么匆忙,那么快速,那么简单。没有调解的场面,没有磋商的气氛。从凡尔赛到圣日耳曼、纳伊、特里亚农、色佛尔,“和约”一个接一个产生。这么短的时间签订如此多的媾和条约,其“速度之快似乎是不可思议的”。[②b]条约制订者们根本无法就条约的具体内容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研究,甚至当德国人已应召来到凡尔赛时,“条约仍然很不完备,德国人仍然在等待。”[③b]更有甚者,当巴黎和会讨论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时,“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称……还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④b]可威尔逊等竟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11天内,把国际联盟的协议草案提交和会的全体会议。”[⑤b]这真是一个惊人之举。屈指细数,从1918年1月威尔逊提出“十四点纲领”起,到1920年8月色佛尔签订最后一项条约止,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就创建了一个不同于1914年的国际秩序——凡尔赛体系。而且,即使这个“两年半”的数字也还是个虚数。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只打雷不下雨,它并没有真正开始创建凡尔赛体系的行动,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实际上是从战后的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开始的,甚至其主体部分——《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盟约》连同《圣日耳曼条约》、《纳伊条约》,都是在巴黎和会这一次会议上完成的。所以,实际创建凡尔赛体系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919年1月至1920年8月。若不是1919年匈牙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土耳其爆发凯末尔革命,协约国恐怕也不会将对这两国的条约拖至1920年1月21日巴黎和会正式结束之后签订,那创立凡尔赛体系的过程会更短。
雅尔塔体系就不同了,它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还在战争进行之时的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就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上的一次会晤中拟定了《大西洋宪章》,这是“第一份预见战后‘建立普遍和永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英美文件”,[⑥b]从而拉开了创建国际新秩序的序幕。此后,以苏、美、英、中为主的反法西斯国家不仅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而且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行动。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到处都留下了新体系创建者们奔走的足迹。他们经过三年的酝酿和磋商,在敦巴顿橡树园拟订出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后又在大小国家一致参加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一年。据统计,截止1945年5月5日午夜12时,先后共有36个国家提出了1200件修正案。[⑦b]这的确是空前之举。1945年6月宪章获得通过。这期间,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者们也曾探讨过对德国及其仆从国进行制裁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急于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他们处置战败国的“和平条款是分段产生的,起先在战时,由战胜国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继而在1945年以后的若干年内又作出了一系列事实上的安排。”[⑧b]在波茨坦,三巨头就决定设立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准备签约。战后四国外长(中国除外)又接连会晤,“以期能找到协调各方立场的办法。”[①c]直到1947年2月10日才签署了对意、罗、保、匈、芬的“五国和约”。而对主要战败国德国,甚至始终没有一个类似于《凡尔赛和约》那样的解决方案。1949年德国的分裂也只是一种既成事实,而非雅尔塔体系的刻意安排。对另一主要战败国日本的媾和会议,1951年9月才在旧金山召开,并达成了战后的战败国的最后一个和约。至此,雅尔塔体系宣告形成。从《大西洋宪章》到《旧金山和约》,历时整整10年。
很显然,凡尔赛体系的确立是仓促的,它没有经过认真的酝酿和讨论,即使对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也没有详尽地分析和磋商,许多问题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才论及。更重要的是,尽管英法认可了威尔逊关于创建国际联盟的主张,但它们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对威尔逊的观点大有异议。英法之所以接受了威尔逊的主张,一是因为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英法民众的要求,英法急于以新的和平体系向人们展示其“军事胜利”;二是因为英法得罪不起美国,它们需要美国的“关照”,要把灾难性的条款强加给德国及其盟国以防东山再起,没有美国的支持是办不到的。无怪乎国联盟约的制定与媾和条约的签署同步进行,美国关心前者,英法(特别是法国)则看重后者。结果巴黎哪还是什么“和平会场”,简直成为一处“交易市场”。英法答应威尔逊用国际联盟取代均衡外交,而当威尔逊近乎发狂地向全世界宣布“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诞生了”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再去考虑法国对德国的惩罚是否适度了,交易一拍即合。而作为“和约”的另一方德国的态度,它们干脆置之不理,甚至宣称要德国人在“是接受条约还是忍受协约国的侵犯”中作出选择。[②c]不难想像,靠交易和威胁而匆忙建立的国际秩序会有多大的稳定性。仅仅20年,凡赛体系的创建者们就收到了一张烫手的“罚款单”——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创建雅尔塔体系时,各大国显然是吸取了上一体系创建时的教训,表现得十分谨慎。这一体系的创建者们确定了“轻重缓急次序,即在战时重点创建联合国,战后再处置战败国。盟国有意把制宪会议安排在战争结束之前,让制宪会议与媾和会议承担不同的责任:前者是规划未来的和平;后者是严肃地清算过去。”[③c]盟国(主要是美国)之所以要在大战结束前建立联合国,“是有鉴于旷日持久的战争苦难使人们几乎普遍渴望建立一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基础。”[④c]在确定了未来和平总体框架与原则的基础上清算过去,惩罚战争发动者,将会避免出现单纯为保持军事胜利而确立的“和平”,和平与军事胜利并不是一回事。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者们没有操之过急,他们并没有急于在一次或几次会议上解决问题,而是审慎地进行着细致的工作。战时仅三巨头聚首就有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其他级别的会晤更是频繁,他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球人民的愿望和舆论的要求,这必然会产生良好而稳定的和平基础。前苏共《真理报》1994年10月11日撰文称赞道:三大国“已意识到必须避免重复国联的失败的教训”,“避免重复它的缺点”。[①d]难怪战后半个世纪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大战,甚至雅尔塔体系的崩溃也是通过渐进的、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是给雅尔塔体系创建者们最好的“奖赏”。
二
其次来比较一下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下的不同格局。
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家曾经预言,未来的国际舞台将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影响,事实正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德国因发动世界大战而在20世纪初期失去了它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并被作为战败的罪犯来处理。只有俄国和美国令世界刮目相看。1917年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即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②d]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两个新兴大国就提出了重新改造世界的方案:一个是列宁倡导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另一个是威尔逊为了抵消苏俄影响而提出的以国际联盟取代均衡外交的构想。[③d]但苏俄在经济上百废待兴,在政治上势单力薄,在资本主义的“集团式”冲击面前,列宁的方案受到冷落。相反,美国财大气粗,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西欧传统大国英法也不得不唯美国马头是瞻,在历史上“约翰牛”害怕“山姆大叔”这还是第一次。威尔逊在说明其“十四点纲领”时表示:“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不能保持孤立。”[④d]威尔逊带着这种自信亲飞巴黎,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到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在他看来,除了他再没有什么人能够实现创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了。他成功了,但接着又失败了。成在巴黎,败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不愿意”退出孤立,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威尔逊在巴黎的努力。这样,凡尔赛体系建立时,苏俄和美国,一个被“拒之门外”,一个“自动隐退”,历史的重担又交给了英法,它们替代了苏俄与美国的地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看似如故。
和凡尔赛体系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不仅德、意、日一败涂地,就是英法也跌至低谷。法国因1940年败降而使昔日威风荡然无存。英国虽属三大国之一,但英帝国大势已去。丘吉尔看得很清楚:“欧洲的力量均衡已岌岌可危”,英国将来“很可能被置于一个极不舒服的地位,夹在两块大磨石之间碾着。”[⑤d]的确,美国、前苏联的势力已赫然显现,没有谁能再来代替它们的位置,而且这一次它们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前苏联无可争议地成为强国这一事实,使英美领导人都不能等闲视之,再也没有歧视和冷落了。罗斯福在安排战后世界时,可以不与丘吉尔协商,却不得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他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我们忘不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保卫战,也忘不了1943年和1944年惊人强大的俄国反攻。”[①e]难怪在首次首脑会议召开前,罗斯福曾两次向斯大林发出邀请;难怪在苏军挺进东欧后,丘吉尔急不可待地请求到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与凡尔赛体系拒苏俄于门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美国随着传统西方大国的衰落,稳步地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它已经失去了一次“加入世界”的机会,这一次它“再也不能将自己限制在两个海岸中间,甚至也不能只限于自己这个半球了。”[②e]结果,美国和前苏联成为雅尔塔体系的主宰,从而完全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
不难看出,凡尔赛体系的主体是传统的欧洲强国英法。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并不是当时国际社会中最有发言权的国家,而且其地位正处衰落趋势,过去在欧洲指手划脚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们已经失去了对国际事务的仲裁能力。况且英法是靠美国的帮助而成为战胜国的,若不是美国参战,英法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如此得来之胜利以及随之靠他人“恩赐”而签订的条约,都不能使我们把英法看成是真正的胜利者,特别是当美国宣布不参加国联时,英法几乎被搞懵了,法国人甚至大呼上当。它们先前在巴黎得到的保证,一下子变成了“空白支票”。英法本来就对国联毫无兴趣,现在美国的突然退出,使它们没有勇气和信心去接过美国人扔下的这付担子。更严重的是,既然美国不是凡尔赛体系的一员,那么美国和国际联盟就完全是两回事了。而德国恐怕宁愿接受美国的领导也不愿受控于英法。果然,德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与国联分离的现象,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常规,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一跃而重入世界强国的“排名”,与英法平起平坐。英法惊呆了,更是不敢说东道西了。“国联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③e]它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妥协退让这一被称之为“绥靖”的办法来满足对和平的愿望。1935年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开始向凡尔赛体系挑战时,英国不仅未予制裁,反赐德一纸“海军协定”;1936年希特勒冒险进入莱茵兰,也未遇到凡尔赛体系最忠诚执行者法国的抵抗;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凡尔赛体系严加看管的奥地利,英法的默认“对于各民主国家来说,是一次新的退缩。”[④e]之后英法又联袂导演了慕尼黑丑剧,尽管希特勒当众宣布:苏台德“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对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也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⑤e]但他还是于1939年3月鲸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威逼波兰。英法本想“以绥靖换和平”,但结果适得其反。不断地妥协退让愈发满足不了希特勒的野心,美国学者称之为“闻所未闻的和平”。[⑥e]正因为英法的无能和凡尔赛体系的无力,才使其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国联也越来越不象是一个国际组织了,而更近乎一个来去自由的国际俱乐部。作为国联的创始会员国,日本和意大利于1933年和1937年先后退出;德国1926年被接纳,1933年效法日本而退出;前苏联1934年加入,1939年被开除。再加上从未加入的美国,可以说称得上是大国的国家,在凡尔赛体系的20年中没有在一起共事,更谈不上协调一致。英法虽然一直“坚守岗位”,但双方也有龃龉。大国的四分五裂也使小国“身在曹营心在汉”,许多小国如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但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之后,这些国家先后“背弃了国际联盟,奉行了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①f]致使国联犹如一盘散沙。1937年5月2日埃及“被欢迎加入国联”,“这是国联最后一次接纳新会员国”。[②f]在此之后最紧张的两年多时间里,世界上竟无一国申请加入,相反退者纷纷。这说明各国已经不把安全寄托在国联身上了,英法无力为它国担保甚至自身难保,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是,雅尔塔体系的主宰国美国、前苏联是当时国际社会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二号强国,具备了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能力,双方也互相承认对方为第一谈判对手。这是雅尔塔体系稳定发展的前提。最主要的是,作为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支柱,联合国也越来越取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已经离不开联合国了。在联合国中,虽然美国、前苏联是主宰国,但中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也显示出来了,它们与美国、前苏联共享“否决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五大国之一。这块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国地位是靠美国的“恩赐”,因为“美国关心要有一个强大而友好的中国,以制衡日本实力在远东的东山再起”,[③f]或者“用来作为对苏联的一支政治抗衡力量”。[④f]如果说前苏联的地位是靠卫国战争和解放东欧的功劳所获得的话,那么中国的大国地位无疑是8年抗战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是美国封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不是哪个国家可以改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有能力承担大国的责任。同时还应看到,联合国没有忽视小国的地位,象国联那样来去自由的现象已看不到了。1945年联合国创建时有51个成员国,20年后的1965年增至118国,再过20年的1985年又增至157国,甚至雅尔塔体系崩溃、瓦解之后产生的新国家,在1990年—1992年又掀起了一个“入联”高潮,使联合国成员国增至179国。[⑤f]联合国的这种吸引力是国联所无可比拟的,各国对加入联合国看得很重,因为它不再是国联那样的软弱组织了,也不再是一个欧洲体系的支柱了,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全球体系的支柱,即使是“最小、最无足轻重的成员国也感到它们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⑥f]
三
再来比较一下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对战败国的不同解决办法。
无论是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它们都是战争的产物,所以处置战败国就成为两大体系创建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说,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讲,清算过去、惩罚战犯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清算,如何惩罚,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失败的。《凡尔赛和约》签订时,战胜国标榜为了和平,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但事实上,它们更多地是为了复仇。在“绞死德国皇帝”的切齿痛恨之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而只能是“胜利者的和平”,[①g]对战败国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法国为报普法战争之仇,使尽浑身解数打击德国,力图使这个国家最大限度地遭到削弱。它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坚持国联是一个遏制德国的体制。[②g]甚至为压德就范,不惜冒风险入侵鲁尔。这些做法都只会给德国的不满火上加油,德国人普遍把《凡尔赛和约》斥之为“奴隶条约”,“差不多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修正条约派’。”[③g]1924年以后,法国人醒悟过来想改善法德关系时,为时已晚,凡尔赛体系就象一把利剑刺在每个德国人心头。“无论是谢德曼政府、斯特莱斯曼政府,还是希特勒政府,都难以容忍,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是他们的既定政策”[④g]而德国百姓对这种始终如一的“既定政策”也持积极态度。当1938年希特勒“不经流血就消除了最使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受到压抑的凡尔赛和约的后果”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信仰已大大加深”,“只有少数人怀疑这种政策的诚实性”,“而看透希特勒魔鬼本性的人则更少”。[⑤g]这足以说明,为复仇而确立的凡尔赛“和平体系”又准备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温床。
相比之下,雅尔塔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小心翼翼的。在战时,丘吉尔就一再提醒罗斯福和斯大林,要“明智一点”,要记住“第一次世濈大战之后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⑥g]为此,英美前苏在处置战败国时,既要确保德国和日本不再对新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又要避免把太多的重担强加于它们。在以雅尔塔为核心的一系列会议上,人们再也听不到“绞死德国皇帝”的誓言了,“德国人还要吃饭”则成为新的口号。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讨论了战后德国可以分割或肢解成几部分,但推迟了决定的时间。之后再也没有提到分割德国,只是实施了对德国分区占领的管理体制。德国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并非雅尔塔体系所为,而是历史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而日本在投降后由美国全面占领,1951年旧金山体制改为半占领。同时,雅尔塔体系更多地注重战后对战败国的民主建设。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声明,三国将“共同协助所有欧洲被解放的国家之人民或欧洲前轴心的附庸国之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遗迹,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程序来实现。”[①h]波茨坦会议又强调要在民主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五国和约》也明确规定了政治民主化与限制军备两大内容。这对欧洲的和平与民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应当说,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残酷的、无情的,带有明显的复仇痕迹。但是,由于德国在英、法、美等大国战略中的不同地位,构成凡尔赛体系的一系列条约又存在种种矛盾,它们“既不是铁一般的和约,也不是和解式的和平;它既不像法国人希望的那样严厉得足以把德国人永远踩在脚下,也不是宽大得足以使被征服的人安于自己新的处境。”[②h]德国虽然是凡尔赛体系的受害者,但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者——这看起来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但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象。德国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其军事潜力仍然很大;德国按约要支付巨额赔款,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支付多少,相反却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贷款。保罗·肯尼迪断言:“1919年后它(指德国,笔者注)仍然是一个潜在的了不起的大国。”[③h]许多德国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战败,随着星移斗转,德国人把凡尔赛体系中严厉的条款变成了仇恨,随之又变成了战争。而当它发动战争时,距所谓“和平体系”的建立只有20年,凡尔赛体系的和平之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破灭了,而且打破这一梦想的恰恰是凡尔赛体系的打击对象,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和平缔造者们”处置战败国的措施。也难怪西方学者对凡尔赛体系罗列了一大堆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诸如“不可靠的和平”、“不平静的和平”、“迦太基式的和平”、“失去的和平”,等等。战争导致了凡尔赛体系,而凡尔赛体系又导致了战争并埋葬了自己,这正是它的悲剧之所在。
仔细分析雅尔塔体系,不能不承认,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宽容的,并收到了一定成效。雅尔塔体系对德政策的目的,“是破坏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使之永远不再能够威胁世界和平。”[④h]1945年2月6日,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筹建联合国提案时曾有一个明确的表示,他对“世界即使不能保持永久和平至少要保持50年的和平抱有信心”。[⑤h]战后50年来,国际形势变化万千,但雅尔塔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并几次达到“战争边缘”,但最终均没有打破雅尔塔体系的安排。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才和平地崩溃。凡尔赛体系因制裁德国而导致德国发动一场新世界大战的情况没有再度出现,德国没有因雅尔塔体系的制裁而滋生新的复仇主义,实现了雅尔塔体系创建者们“摧毁纳粹主义”的构想。在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时还有舆论担心统一的德国对欧洲及世界和平的不良影响,但德国政府在199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时,庄重地向波兰等被侵略国公开道歉承认过去的法西斯侵略史,把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日说成德国人民的“胜利日”。这些举动足以让世界人民放下心来,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雅尔塔体系对德政策的成功。不过,另一战败国日本则是例外。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有根除,日本时常出现一些复活军国主义的闹剧,甚至一些政府要员也公开篡改日本的侵略史。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时,日本的表现和态度也令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不满。它对过去的历史总是遮遮掩掩,更有甚者,日本竟然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活动延至1995年12月举行。当然,日本一幕幕复活军国主义的丑剧与凡尔赛体系下德国的复仇主义是不同的。德国是因为凡尔赛体系处罚过重,而日本则是因雅尔塔体系处罚太轻。看来,对战败国的处罚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罚太重易于导致复仇主义,而处罚太轻则易于使战争发动者认识不到应负的战争责任。
小结
通过对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比较,我们对二十世纪的国际秩序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20世纪前半期的凡尔赛体系,从建立到内部机制的运作,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而它不仅没能消除战争,反而又引爆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作为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可以想象,如果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凡尔赛体系的存在,那么“20年的休战”会大大缩短。同时,正是由于凡尔赛体系的深刻教训,才使国际新秩序的创建者们引以为鉴。20世纪后半期的雅尔塔体系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体系创建者的最初设计和梦想。当然,雅尔塔体系也并非尽善尽美、包治百病。所以,世界人民才迫切盼望着有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世界不能没有“秩序”,“秩序”不能抛弃人民。
注释:
①a 理查德·B·摩雷斯:《历任总统的重大决定》(Richard B.Morris,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哈泼——洛公司1973年版,第390—396页。
①b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页。
②b C·E·布莱克、E·C·赫尔姆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③b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④b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第7页。
⑤b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第41页。
⑥b 罗宾·艾德孟兹:《三巨头——在和平与战争中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 and Stalin in Peace & War),伦敦1991年版,第223页。
⑦b 李铁成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⑧b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37页。
①c 美国国务院:《和约的制定,1941—1947》(U.S.A:Department of State,Making the Peace Treaties,1941-1947),华盛顿1947年版,第25页。
②c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第34页。
③c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第123页。
④c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Herbert Feis,Churchill,Roosevelt and Stalin),普林西顿1957年版,第428页。
①d 瓦·米·别列日柯夫:《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②d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93页。
③d A·J·P泰勒:《为欧洲霸权而斗争》(A·J·Taylor,The Strugglefor Mastery in Europe),牛津1977年版,第567页。
④d 阿瑟·S·林克:《外交家威尔逊——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一瞥》(Arthur S.Ltnk,Wilson,the Diplomatist,a Look at His MajorFor eignPolicies),约翰——霍普金斯1957年版,第145页。
⑤d 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H·Mcneil,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牛津1953年版,第320—321页。
①e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②e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③e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76页。
④e 让—皮埃尔·阿泽马、米歇尔·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0页。
⑤e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11页。
⑥e 罗杰·劳·威兼斯:《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页。
①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23页。
②f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第322—323页。
③f 里兰德·M·古德里契:《变化世界中的联合国》(Leland M.Goodrich,The United N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版,第16页。
④f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0页。
⑤f 根据拉姆基·巴苏《联合国—国际组织的结构与作用》(Rumki Basu,The United Nations: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统计,新德里1993年版,第347—353页。
⑥f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第124页。
①g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四卷,第31页。
②g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A.J.P.Taylor,The Origins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61年版,第39页。
③g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45页。
④g 张之毅:《世界秩序机制转换的历史反思》,载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⑤g k.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⑥g 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第550页。
①h 罗宾·艾德孟兹:《三巨头—在和平与战争中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第493页。
②h 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
③h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28页。
④h W.L.纽曼:《缔造和平,1941—1945》(W.L.Neumann,Makingthe Peace,1941—1945),华盛顿1950年版,第79页。
⑤h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第552—5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