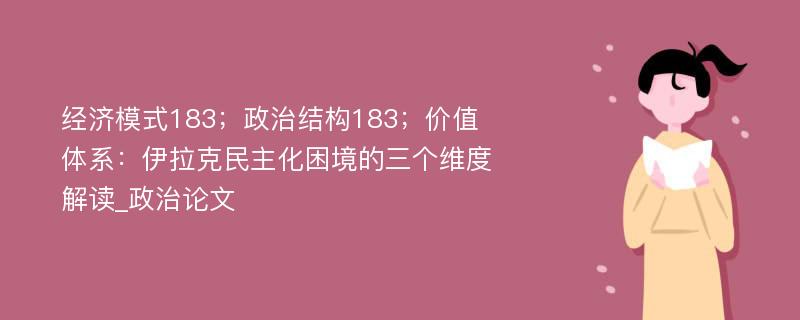
经济模式#183;政治结构#183;价值体系——解读伊拉克民主化困境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维度论文,困境论文,体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一直被美国视为中东民主改造的“榜样”,因此这一进程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美国“民主改造战略”的前景。当前,表面上看,伊拉克正迅速由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美国这一外力的推动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困扰民主发展的诸多结构性难题却始终难以逾越。日前,因权力分配争执不下,伊拉克新政府在大选后3个多月才迟迟出台,这种拖延直接影响了原定的制宪、宪法公决、选举正式议会和正式政府的政治重建议程,也极大打击了普通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厚望。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伊拉克民主化困境的缩影。深入探讨伊拉克民主化困境,对于把握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的局势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依赖石油的传统经济模式妨碍民主制度生成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成熟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将决定政治制度特性。就伊拉克来说,严重依赖石油的发展模式对其民主政治建设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庇护—附庸型的垂直生产关系容易导致集权政治和威权心态。庇护—附庸(patron-client)型的垂直生产关系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生产关系,它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地方性关系。这种松散性和地方性,决定了它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以致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彼此隔绝。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其资源分配方式也是落后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相对弱小的个人和团体将自身安全和其他基本需求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对身处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重要。附庸关系是“社会缺乏有机联系的产物,它往往维持了社会的分裂和无组织状态”。(注:[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它铸就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结果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不利于现代民主的开展。当前,在伊拉克这种“自上而下”分配资源的生产关系依然占有主导地位。国家控制、分配石油财富的资源配给方式,使它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这里,民众生存更多地是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地分配石油财富,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自下而上的公民纳税。(注: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20.)如果依赖石油财富支撑整个经济,传统的社会关系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石油的提炼、运输和销售并不需要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相反他们可能会固守各种中世纪的行为习惯。(注:Spengler,“民主为何不会光顾伊拉克?”《亚洲时报》,2005年2月2日。)因为政府不需要向民众征税,结果使政府像王室一样高高在上,脱离社会。(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选举不是民主”,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2月7日。)这样,在西方国家是“无代表”便“不纳税”,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而在伊拉克则是“不纳税”便“无代表”,石油美元束缚公民社会的发育。
其次,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妨碍了现代政治力量的孕育。伊拉克发展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严重依赖石油。该国绝大部分的公共和私人收入都来自石油;石油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人人都依靠国家补贴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根据美国中情局《世界实用手册》,伊拉克2003年的GDP大约380亿美元,而其中石油出口额为300亿美元。这足以说明其他产业在伊拉克所占比例之小。
这种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石油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获取石油财富之易,也使发展其他产业因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缺乏动力,或因成本高昂而在国际市场不具竞争力。“大量的石油储备提供了一条致富的途径,使之无需经过工业化、分工专业化、提高教育水平等(发展阶段)。”(注:[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黄语生译:“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3期。)因此,这种过分依赖石油的发展模式,看似能为产油国推行民主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但实际上妨碍了经济现代化,进而抑制了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因为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专业分工始终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形成相互依赖的横向生产关系以及大量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主体,更不可能在民众中培育出经济共同体意识及现代公民观念。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石油租金的存在,加深并扩大了业已存在的以国家为中心、进口替代性的内向型经济政策。同时,石油收入还使19世纪以来独裁和专制统治的有害传统遗产得以继承。”(注: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pp.61—62.)要想在伊拉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建立不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和政府。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可以轻易筹措到钱,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必要建立真正的经济。实际上政府也就不需要它的公民了。(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选举不是民主”,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2月7日。)
二、种族、教派特质的政治结构潜含政治分裂危机
一般来说,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更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政体,而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严重分化与相互冲突的亚文化,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注:[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8页。)中东地区民族宗教构成十分复杂,(注:哈得森曾把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宗教结构分为四类:是阿拉伯人但宗教信仰不是逊尼派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但根本不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参见Michael C.Hudson,Arab Politics: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59.)这在伊拉克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民族构成看,伊拉克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犹太人、土库曼人等;从教派构成看,有伊斯兰逊尼派、伊斯兰什叶派,以及少量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由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版图引发的种族、教派矛盾,始终是笼罩伊拉克政治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因此,伊拉克的政治建设并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依序进行从分散割裂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整合,以及从少数人掌权的专制国家向人民民主国家过渡,而是同时进行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民族建构强调的是国家化,也就是政治认同从传统部族、教派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国家建构强调的是民主化,也就是摆脱极权主义,建立民主政体。国家化(或国族化)更强调整体性和强制性,民主化更强调个体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当前的伊拉克政治重建中,国家重建与政治重建进程非但不均衡,甚至还有些相互抵触。而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正是在民族建构没有完成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其政治民主化有可能沿着种族、教派界限产生政治断裂。
首先,民族建构(文化整合)的不成功导致教派隔阂加深。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拉克是个不成熟的“人造”国家。它是在英国实行委任统治时期建国,并由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三大地区拼组而成,连名都是英国起的。伊拉克虽然历经英国统治、费萨尔王朝和复兴党统治多个时期,但从未真正完成整合伊拉克国民性的任务。萨达姆政府曾竭力把伊拉克历史追溯到古巴比伦文明时期,并通过普及全民教育来培养民众对新国家的感情,但更多的时候,出于生存本能却又大肆渲染和借用种族、教派这些先天特性以巩固统治(如萨达姆权力核心圈基本都是逊尼派,特别是提克里特家乡的人)。与此同时,萨达姆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起义无情镇压。1988年3月,他甚至动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有分析认为,萨达姆根本没有把库尔德人当作是国家的公民,仅仅把他们作为外来的部族成员。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伊拉克越发陷入严重的族群对立。(注:Dr.Michael A.Weinstein,“Iraq's Transition to Dictatorship”,The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PINR),20 July,2004.)
因此,表面上看,伊拉克领土、主权、政府、人口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俨然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然而,事实上,伊国内不同种族之间历史和政治意愿迥异,民众的忠诚对象是诸如教派、种族、部族、血缘和家庭等传统性内容,对国家的认同陌生而且脆弱。目前,新一代伊拉克库尔德人多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不把巴格达视为首都。(注:Dr.Nimrod Raphaeli,“Iraqi Kurds at Crossroad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March 30,2004.)相反,一项非官方统计表明,倒是有98%伊拉克库尔德人赞成独立。而且当地库族聚居区至今仍在出售一种“库尔德斯坦”地图,其版图涵盖了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多个国家。
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随后的“民主改造”,则让世人亲眼目睹了伊拉克族群分裂的严重程度:他们对外各行其是,缺乏同仇敌忾的抗敌意识;对内则出现了以教派、种族版图瓜分政治权力的“分裂型民主”。由于战争破坏和战后动荡,伊拉克百废待兴。而伊拉克当局在处理国内安全和经济重建问题上办法不多,伊拉克人为生存而不得不更加依靠当地教派首领,(注:By Erich Marquardt,“A dent to Washington's Iraqi designs”,Asia Times,Feb 17,2005.)从而使部族、教派、家庭等原生性组织形态日益成为重要的认同对象,由此使得类似西斯塔尼这样的宗教领袖和地方部落首领更加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其次,教派隔阂反过来导致“分裂型”的政治建构。在那些种族、教派多元化的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和彼此妥协方式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对于伊拉克这类文化整合尚未完成的国家来说,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很难。相反,对自身种族、教派的执迷,反而使其在政治冲突中愈发不肯妥协。“某一文化的支持者,往往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看作是关系到原则、关系到深刻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关系到文化的保持和团体的生存的大事,认为这些要求至关重要,不容妥协。他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59页。)随着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的展开,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教派认同阴影日益浮现,并使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同时,由于人们的种族、教派认同强于国族、国家认同,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种族、教派等亚文化认同很容易直接转变成政治认同和政治旗帜。这样,政治动员就必然容易转换成种族、教派动员,从而种族、教派利益直接转换成政治利益。由此形成一种分裂型的政治民主。
今年5月初成立的伊拉克过渡政府明显带有这样的色彩,它模仿的是“黎巴嫩模式”。总统、总理、议长“三驾马车”分别由库尔德领导人塔拉巴尼、什叶派领导人贾法里、逊尼派议员哈桑尼担任,各部部长也基本按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这样组阁看似照顾到各派利益,实则巩固强化了种族、教派意识。当年黎巴嫩“教派分权制”曾使黎巴嫩陷入长达15年的内战,伊拉克即使不重蹈覆辙,也难避免内部纷争。目前,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在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归属问题上各执一端,使其有可能成为“导致分裂的火药桶”。伊拉克教派矛盾也开始向民间蔓延。逊尼派袭击什叶派事件时有发生,还有逊尼派扬言“先杀库尔德人,然后杀美国人”。事实表明,“在像伊拉克这样脆弱、矛盾重重的社会中,选举会使其更加极化。它能够加深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的鸿沟。”(注:James Dobbins,“Iraq:Winning the Unwinnable War”,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5,Volume 84,No.1,p.18.)
三、缺乏价值共识易使民主体制发生畸变
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是与制度背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伴相生的。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和文化。战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却不能建立新的文化与价值观。(注:安东尼·寇兹曼著,曾祥颖译:《伊拉克战争经验教训:大战略之课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译印,2004年,第80页。)就建设过程而言,“民主不只是一个精英阶层安排的问题,公众基本的文化倾向在民主的生存当中也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注:[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转自[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然而,在伊拉克,许多陈旧观念仍然束缚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首先,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宗教干政。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信仰和民族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的宗教改革,因而它未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因而其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民主显得格格不入。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现代民主的重要根基之一,就是政权与教权、国家与教会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而伊斯兰教则与此相悖,它试图通过强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权威乃至建立神权政体的办法,来使自己发扬光大。各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组织(如“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和“伊斯兰达瓦党”)则凭借伊斯兰外衣韬光养晦,成为能够左右伊拉克政局的主要政治反对派。尽管这些政治宗教组织存在形态和基本主张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政治主张仍体现出一种“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伊斯兰势力发展如火如荼,宗教话语日渐成为无人敢于公开顶撞的“政治正确性”话语。因此,当前伊拉克媒体虽然已相当自由,但极少有媒体敢批评宗教或宗教机构。用伊拉克诗人哈兹·马吉德的话说,“伊拉克仍缺乏言论自由。我可以对政府发表任何(批评)意见,但一旦我批评政党或宗教,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注:Al-Sharq Al-Awsat(London),August 30,2004,转引自Nimrod Raphaeli,“Islamist Pressures in Iraq”,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September 29,2004.)这种伊斯兰化倾向在2005年的伊拉克大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就是传统色彩浓厚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尤其是“伊拉克团结联盟”中的什叶派宗教政党(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和“达瓦党”)。这些宗教政党以及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都曾表示,希望增加伊斯兰法在法律中的比重。(注:Juan Cole,“The Shiite Earthquake”,Tuesday 01 February 2005,truthout.com)加之伊拉克是什叶派的重要发祥地,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很可能使伊拉克的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因此有人就认为,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伊拉克的民主转型。(注:Nimrod Raphaeli,“Islamist Pressures in Iraq”,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September 29,2004.)有媒体甚至认为,什叶派伊斯兰分子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伊拉克。(注:Dan Murphy,“Shiite Islamists to shape new Iraq”,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4,2005.)这种“没有民主派的民主化”现象,既使美国处境尴尬,也使伊拉克民主化前景难料。
其次,互不信任的政治文化容易导致“政治返祖”。民主政治实际是一种集体游戏,因此基本一致、彼此信任是必要的且“游戏规则”极为重要。它有助于维系选举制度和权力分享机制,创造民主的政治氛围。可以说,社会信任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如知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认为,人际信任感是有效民主的先决条件。(注:[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民主制度如果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就会是一个难以运转的和脆弱的制度。(注:[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因此,如何看待政治对手、是否愿意分享权力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而对当前伊拉克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来说,至少应保证两点基本共识:一是民主化在世俗化基础上进行,不能搞神权政治;二是允许政治竞争,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民主政治涉及公开的权力竞争,没有一个团体有把握稳操胜券。因此,输家必须信守选举结果。同时,赢家必须了解他们并不能永远执政,必须一再竞争。”(注: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等编:《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等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57页。)实际上,在伊拉克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却很难做到这些。
“在构成成分极不相同的社会,每个公民对反对者的力量都心怀恐惧。”(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78页。)伊拉克三大种族、教派长期敌对,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因此,伊拉克人更倾向于忠于本种族、教派的“特殊信任”。阿拉伯逊尼派、阿拉伯什叶派、库尔德逊尼派构成了伊拉克分裂型政治文化的三大认同群体。在他们看来,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竞争完全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之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之所失。(注:Patrick Clawson,“Iraq for the Iraqis:How and When”,Middle East Quarterly,Spring 2004,Volume,XI:Number 2.)然而,他们越是依靠他们的密友和亲戚,就会越是按照‘我们’和‘他们’的标准来看待世界。他们不会信任“大多数人”。(注:[美]艾里克·M·乌斯拉纳:《民主与社会资本》,转自(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这样,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并非基于政治理念的先进与否,而是“自己人”数量的多寡。
目前伊拉克各派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基本上沿用萨达姆时代的老办法:重出身甚于重能力,重立场甚于重观点。因此,伊拉克的民主选举固然使民众可以自由表达意愿,但他们所表达出的不是民主、人权意识,而是维护种族、教派等原初认同的本能意识。无论是备战伊拉克大选,还是组建过渡政府,如何维护教派、种族利益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从政治发展角度看,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返祖现象”。历史已经表明,社会分歧越大,民主就越是脆弱。因此,在种族的或经济的亚群明显可分而且实质上已经定型的地方,发展、健全民主会遇到极大困难。(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78页。)
第三,缺乏个人权利意识极易导致“极权民主”。“自由”与“民主”彼此关联但又截然不同,因此,民主的发展未必会给民众带来自由和福祉。事实上,民主也有“好的民主”(即自由民主)和“坏的民主”(即极权民主)之分。对个人权利的充分保障,是自由民主展开的基本前提;而认为只要“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观念,则是通向极权民主的渊薮。阿克顿曾指出:“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注:[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35页。)因此,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只要赢得50.1%的选票就应掌握全部权力。
在当前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中,许多人却把民主理解得过于简单,不少人仍认为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就连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有将民主简单化的倾向。伊拉克解放之初,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发言人便曾坚决要求直选,并认为留出时间组建政党没有必要。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伊拉克没有足够的受过民主思想熏陶的民主派来维护民主制度。什叶派囊括了各路人马,但其中大部分倾向于教士统治。而属于少数派的逊尼派长期统治伊拉克,他们的领导人因不甘沦落为二等公民而拒绝民主原则。对库尔德人来说,他们已经相当成功地管理着他们的自治区,但他们更热衷于党派和部落忠诚,而不是代议制民主上的个人主义。(注:Edward N.Luttwak,“Iraq:The Logic of Dis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p.30.)
因此,在民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伊拉克民主进程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基于数量的民主”。尤其在伊拉克种族、教派隔阂很深情况下,基于人口优势的权力优势,便成了衡量自身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因此,伊拉克什叶派之所以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人口居多,选举可以使这种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进而有效维护自身利益。逊尼派这类少数者之所以对政治进程态度消极,同样是源于“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害怕失去权力后出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景象。说到底,这仍是个是否能保障少数种族个人权益的问题。
在此次伊拉克大选中,据说有10万基督徒被剥夺投票权。今后,亚述—迦勒底人等其它少数民族的权益是否能被承认仍是很大疑问。这种不良兆头对伊拉克民主化发展绝非福音,相反却很有可能将伊拉克引入“极权民主”的陷阱。“确定多数拥有将其意志强加于少数或各少数派的权利,等于是确定一种工作原则,从长远看它同它所标榜的原则相抵触。假如民主竞争中最初的获胜者把自己定为永远的获胜者。这样一来民主便不再有民主的前景,民主开始之时,便是民主寿终正寝之日。”(注:[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7页。)
余论
从发展的观点看,政治发展的环境、进程和内容都是可以逐步改变的。其中,尤其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当前的伊拉克政治重建中,伊拉克政治家和多数民众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耐心和勇气令人钦佩。2005年1月31日伊拉克大选的顺利举行表明,伊拉克民众通过自由投票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甘冒恐怖袭击的危险。许多学者把“竞争性的选举”视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就此而言,伊拉克已趋近民主政治的底线。在历史上,由少数精英人物移植,甚至由外国强加的民主化不乏成功的先例(如二战后的德国、日本)。可以说,由美国这个强大外力推动的伊拉克民主化也存在着成功的可能。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存在种种结构性难题的背景下,如何才能保障伊拉克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而不致重返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相继建立了民主政权,但当遇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时,许多民主政权就难以为继了。为什么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存在下来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为何高水平的民主化未必持久?《最新民主化历程》一书曾列出了民主存续的五大要件。(注:这些条件包括:1、具有正当性(包括地理正当性、宪法正当性、政治正当性);2、对游戏规则形成共识;3、限制获胜政党政策;4、贫穷阻碍民主巩固;5、种族、文化或宗教分裂限制民主发展。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等译,第656—658页。)据此衡量,伊拉克民主化能否在历经坎坷后继续生存,关键问题在于它能否在民众中建立起根深蒂固的文化依恋,(注:[美]马克·E·沃伦著,吴辉译:《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或者说能否以实际政绩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民主本不是万能的,民主选举(乃至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政府上台执政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同时为解决社会经济难题创造重要前提,却不能使种种现实问题自动解决(即不能解决“实质合法性”问题)。伊拉克政治进程亦复如此。而且,长期专制统治反而容易使民众对民主化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预期——“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政治选举同时实现制度创新和繁荣经济。对于刚刚破土而出的伊拉克民主幼苗来说,这一任务是如此之重,以致轰轰烈烈选出的新政府一旦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垮掉的将不仅是当权者,可能还有民主制本身。
标签:政治论文; 库尔德族论文; 什叶派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经济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逊尼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