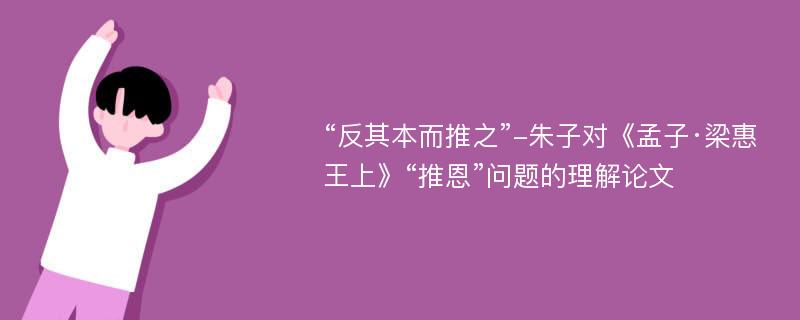
“反其本而推之” ——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
东方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推恩”问题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章。所谓“推恩”,简单地说,指的是行为者在面对某事物(或境况)时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心”会自然产生某种道德反应,并将此“心”所产生的道德反应推而广之,施加到其他相关事物或境况中去,以使该行为者在面对其他相关的事物或境况时也能作出相同的道德反应。“推恩”理论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本文所要处理的只是朱熹对“推恩”问题的解释。本文的基本主张是:西方学者的相关解释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相比之下,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尝试透过朱子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对孟子理论的“扭转”。
【关键词】 孟子 推恩 朱子 扩充 反本
“推恩”问题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以羊易牛”章。就现今学术视野看,对孟子“推恩”的解释,除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任继愈等之外,当今学人对此也已做了相当多的研究[注] 参阅刘清平:《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吴先伍:《“见牛未见羊也”——〈孟子〉中“见”的道德本性》,《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张丰君:《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管子学刊》2012年第2期;李凯:《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与出路》,《齐鲁学刊》2012年第5期等。 ;而英语学界对孟子“推恩”理论的解释则较为繁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推进和深入。[注] 在英语学界,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倪德卫(David S.Nivison)、信广来(Kwong-loi Shun)、黄百锐(David B.Wong)、艾文贺(P.J.Ivanhoe)、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任满说(Manyul Im)、田中孝治(Koji Tanaka)、井原敬(Craig Ihara)等皆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笔者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曾专门就西方汉学家(指英文世界而言,其余则由于语言能力所限,不能论及)对此的相关论述给予了梳理。由于该部分与本文相涉不是很大,故而我们在稍后只作为背景资料加以必要的说明。
正如论题所显示的,本文所要处理的只是围绕朱子对“推恩”问题的相关的解释以显示朱子立论的特色。
“推恩”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道德推扩问题,但若作深入的考察,其间亦可涉及许多复杂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今暂且撇开政治问题不论,即就概念语词及其蕴含而言,诸如何谓“推”?“推”是一种类比推论吗(analogical reasoning)?抑或是一种类逻辑的占有(para-logical occupation)?朱子为何将“推恩”直接理解为“扩充”?若“推恩”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类比推理,目的在寻求一致性原则(a principle of consistency),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理解朱子所说的“盖天地之性,人为贵”,与牛相比,人更值得同情?此外,什么是“恩”?假如把“恩”理解为一种道德感,就其作为类比逻辑“推”的对象又是如何可能的?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见牛之觳觫”的情境性引发与朱子所强调的“无那物时,便无此心乎”(《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之间的关系?
似乎可以说,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复杂的道德和心理理论的解释。此外,除对“推恩”本身的理解之外,假如我们把第七章孟子与齐宣王的整个对话结构一并纳入进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在孟子对齐宣王的劝说中,孟子劝宣王推其恩以行仁政似乎只是出于实现宣王之政治大欲的“目的—手段”的考虑,因此成为行动的理由,而仁政本身却不构成行动的理由。换句话说,在与宣王的对话脉络中,孟子似乎主要不在理论上证成(justify)仁政本身,而似乎在竭力为宣王给出行仁政的动机与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孟子》一书在理论本质与对话脉络中的意义蕴含之间出现解释上的“罅隙”与紧张。本文的基本主张是:西方学者对“推恩”的相关解释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相比之下,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尝试透过朱子对“推恩”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孟子理论的“扭转”。
周末,林露白接到前同事的电话,说看见魏舟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吃饭,举止亲密,还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才分手多久啊,他就有了新欢。”
一、 文本与概念解释
大致而言,孟子的整个理论立说是对礼崩乐坏的世界提出救治之方。孟子的理想是施王道,开出的良方是行仁政。仁政为什么能行?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仁政该如何实行?孟子认为,只要在位者推其不忍人之心及于其治下的百姓,便足以保四海、致太平。孟子因齐宣王不忍见一牛无罪而就死地之觳觫,认为其必能实行仁政,故孟子云:
1)过万学生的高校很多,学生的第二课堂事务信息量大,且涉及多个部门和人员,对各个学院、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协同工作要求很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据此,“推恩”的要义可以理解为“举斯心加诸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乃是通过具体的带有事例性意味的说法以说明推恩之义。故而,所谓“推恩”,简单地说,指的是行为者在面对某事件(或境况)时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心”会自然产生某种道德反应,并将此“心”所产生的道德反应施加到其他相关事件或境况中去,以使该行为者在面对其他相关的事件或境况时也能作出相同的道德反应。不过,要理解孟子此段所说的“推恩”,最好还是与孟子对齐宣王“以羊易牛”章的整个言说脉络联系起来。宣王有一统天下的政治欲望,孟子告之于保民而王,则莫之能御。宣王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孟子则通过“以羊易牛”的故事,认为宣王对无罪而就死地的牛尚且不忍其觳觫,可见若宣王发其不忍之心推恩泽于百姓便足可以统一天下,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说,宣王的不忍之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益,个中原因是什么呢?宣王不行仁政来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干,而不是不能干。由此观之,“推恩”问题在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脉络中首先是作为政治与社会哲学问题提出来的,是外王的问题,孟子正是由此脉络提出其推恩理论。[注] 冯友兰先生认为,依孟子,若齐宣王“因己之好货好色,即推而与百姓同之,即‘举斯心加诸彼’也。若实现此心于政事,则其政事即仁政矣。‘善推其所为’即仁也,即忠恕也。孔子讲仁及忠恕,多限于个人之修养方面。孟子则应用之于政治及社会哲学。孔子讲仁及忠恕,只及于‘内圣’;孟子则更及于‘外王’”。参阅氏著:《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33][47] 李贵州:《从美国国会议案看其南海问题态度及其根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122、126页。
明白了上述特征以后,我们再转过来讨论“推恩”问题。
如前所云,“推恩”是行为者在面对A事件(境况)(“吾老”)时其心会自然产生道德反应(“老”),并将此种道德反应推及到B事件(境况)(人之老)中去,使行为者在面对B事件(境况)时具有相同的道德反应。这是对“推恩”的原则性或本质性的说明。在此一说明中,的确在预设了A与B两种事件或境况的同时,用孟子“举斯心加诸彼”的话来解说“推恩”。“推”即是“举”,“恩”即是“心”,“推恩”当约略可了解为“举心”或“推心”。尚需说明的是,“恩”固然可以理解为恩德或恩惠等不同的含义,[注] 杨伯峻将“恩”理解为“好心好意”或“恩惠”。参阅氏著:《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19页。 但落在“以羊易牛”的脉络中,此“恩”指的是由此心所发的不忍、恻隐之情(或曰同情心,朱子常谓之恻隐之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德情感。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道德情感乃是根于心而发的,故孟子总是云“举斯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心足于王矣”。
在西方学者中,对于孟子“推恩”的解释,倪德卫首先问:“人们怎样去‘推’他们的爱、憎、同情心、潜在的自我尊重等,从而使他们‘充其类’,充分而有效地推动他们去做明白或该明白他们应该做的事?”[注]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倪氏注意到墨家的类比逻辑所使用的“推”的概念,亦即通过显示两个东西是相似的,迫使论辩对手把他们的赞成由这个东西推到那个东西。“孟子把‘推’的概念从辩论的逻辑扩展到对我的意志(原文为“dispositions”,当为“意向”较恰当)的自我控制。看到这个情形(case)(我在这个情形中有主动的同情)和那个情形(我在那个情形中没有主动的同情)的相似性,我把我的同情从这个情形推到那个情形。然后,我就能在那个情形中做(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做)我以前认识到应该做但又不愿做并且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做的事情。”[注]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第173页。参阅原文David S.Nivison, “Two Roots or One?”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 ed. Bryan Van Norden (Chicago: Open Court, 1996) 137.具体到第七章的解释,在倪氏看来,孟子通过指出宣王因被牛的痛苦所感动而赦免牛这一事件,正是试图让宣王认识到他应当对同样处于苦难中的他治下的百姓作出同样富有同情心的反应。倪氏因而提出,孟子在此处的劝说或论辩存在一种逻辑论证,亦即如果宣王赦免牛但又不去解除百姓的痛苦,便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注] 任满说对此认为,倪氏所理解的“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服模式”(a rhetorical mode of persuasion),或者说是一种“理性压力的策略”(rational pressure tactic)。Manyul Im, “Action, Emotion, and Inference in Menciu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9.2 (2002): 235.
类似的主张我们也可以在信广来的相关论说中看到。依信氏,在“以羊易牛”章中,孟子劝说宣王实行仁政的过程体现出孟子所采取的是一种类比推论的方式,借由这种方式使宣王认识到他有行仁政的能力(对牛之觳觫所表现的不忍之心),同时也让宣王认识到他治下的百姓正处于痛苦之中。如是,通过凸显宣王对牛的同情与对百姓的无情两者之间的不一致(inconsistence)以使宣王实行仁政。信氏认为,孟子将宣王对牛的反应和态度看作是道德的自我培养的起点,孟子使用“推”这个技术性的词汇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类比推理(analogical reasoning),亦即通过一种用于特定的自发(spontaneous)反应和态度作基础的类比推理,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应当在其他境况和对象上具有相似的反应和态度。[注] Kwong-loi Shun, “Moral Reasons in Confucian Ethic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6.3-4 (1989): 322.
不过,既言“推恩”,即推恩本身亦可作一个相对完整的问题来分析。如前所言,“推”本身则预设了两种事件或境况,“举斯心加诸彼”亦可分析得出“此”与“彼”的分别,而所“推”者则一。具体地说,在孟子的文本中,“推恩”问题涉及到三个相互关联的不同特征:其一是同类对象之间的差别。从“老吾老”推及到“人之老”等,这种同类对象之间的差别,在孟子那里同时也预设了“远近”、“厚薄”的不同。其二是不同类对象之间的难易。宣王对无罪就死之牛尚且有不忍之心,并见其觳觫而给予赦免,但宣王却对作为同类对象的其治下的百姓所遭遇到的苦难无动于衷。依常识而立,这种做法不合情理,也不可想象。依孟子,对不同类之对象施以同情已经较为困难,而对同类之对象施以恩泽则更为容易,因为人与人之间“同类相亲”,而人与禽兽之间则“同生而异类”。因而“推恩”所表现的亲亲、仁民、爱物之间不仅有远近、厚薄的差别,而且也有难易的不同。其三是“推恩”的范围问题。孟子论推恩在其言说脉络中常常由人己、远近、难易等概念指点而出,上述概念由于其具体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推恩所及范围的理解。就理上言,孟子的推恩原则上并无封限可说,“推恩足于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保四海”谓安天下,“天下”概念并不是具体的实指的封限概念。
以类比的逻辑推理来理解孟子的“推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显明推恩过程中由此及彼的关系,但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理解。任满说认为,孟子在此章中所采取的道德论辩不应理解为一种逻辑推理,孟子劝说齐宣王并非要宣王接受某种信念(beliefs),而是要宣王采取一种“关心的模式”(mode ofregarding )。[注] Manyul Im, “Action, Emotion, and Inference in Menciu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9.2 (2002): 221, 242.黄百锐则将已有的有关孟子“推恩”的解释划分为几种类型,如倪德卫、信广来的“逻辑的扩充”,万百安、井原敬、任满说的“情感的扩充”以及他自己的“发展的扩充”。[注] David B.Wong, “Reason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Mengzi,”Essay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engzi , eds. Xiusheng Liu, and Philip J.Ivanho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190-191.尽管艾文贺不同意倪德卫以逻辑推理来解释孟子的推恩,进而提出一种“类比共鸣”(analogical resonance)的观念[注] Philip J.Ivanhoe, “Confucian Self Cultivation and Mengzi’s Notion of Extension,”Essay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engzi , eds. Xiusheng Liu, and Philip J.Ivanho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234.,但在黄百锐看来,艾氏所谓的“类比共鸣”仍然是一种推理。[注] Ibid. David B.Wong (2002) 198-199.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学者对孟子的“推恩”是不是逻辑推理互有争论,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紧扣着事件以及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人物的道德心理反应进行各种深度的动机、理由的分析。黄百锐认为,孟子的推恩或扩充包含着对各种情感能力的养育美化、富有意义的改变和拓展,而这些变化并不能仅仅通过对逻辑一致性的认识而获得。[注] Ibid. David B.Wong (2002) 191. 在《〈孟子〉一书中存在理性与情感的区分吗?》一文中,黄氏认为,《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对宣王的劝说并不是一种逻辑论证,换言之,孟子并非试图指出宣王对牛的同情与对百姓的无情之间的不一致,并以改变这种不一致来获得道德行动的理由。假如孟子对宣王劝说的目的是要让宣王认识到他应该对百姓施于同情,而宣王没有这样的同情反倒是正常的,因为认识到应该有同情与实际上是否有同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依黄氏,孟子要向宣王确认,认识到牛的痛苦并由此而产生的同情心既是宣王赦免牛的动机,也是其行为成立的理由。故而面对理性认知与道德情感互斥的困难,黄氏认为,孟子的道德情感具有认知的面相,“同情(compassion)典型地包含着(至少隐含着)对以特定方式行动的理由的认识”。[注] David B.Wong,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Philosophy East &West 41.1 (1991): 32.可以说,黄氏的此一主张是试图为倪德卫的解释所遗留的问题做解答。不过,情感如何具有证成行动理由的功能?学者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注] Cf.Craig K.Ihara, “David Wong on Emotions in Menciu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1.1 (1991): 45-54.通常人们会认为,情感表达的是好恶,而认知表达的是对错,这当然只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主流看法,但若谓儒家传统不同于西方,故情感皆具有证成行动理由的功能,我们亦恐很难邃下断语。
二、 朱子的理解
以上我们简略地对孟子的“推恩”概念以及西方学者对此的相关看法作了介绍。必须说明的是,对西方学者的介绍只是就其观点的主要方面略作了陈述,不是全面呈现其主张。当我们的视线转向朱子对孟子“推恩”问题的理解时,我们会发现,与西方学者的看法和观点相比,朱子的诠释表现出颇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解释偏于分析哲学的路数,从认知、行动,情感、理性,到内在、外在,动机、理由等,无不辨识,但另一方面也给人一种析之既细、离之亦远的印象,而朱子的解释有其自己的立场,他能从孟子思想的整体出发,充分体现出儒家心性哲学的特色。
2013年,我国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全面变革,为谋求新路径,科学技术的使用成为解放劳动力、提高作业效率的关键。以小型无人机为例,借助无人机植保示范基地的建设,融合传统自动喷雾器,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农药喷洒效率。而要想保证无人机农业植保优势,则可在优化相关技术的前提,强化农户对现代科技的认知,辅之自动化机械设备知识的学习,逐步提高自动机械的需求量,为小型无人机的发展带来前景。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朱子“无那物时,便无此心乎”一说。“那物”指的是赤子入井、宣王见牛之觳觫。在这种说法中,“那物”与宣王所生的恻隐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了因果关系,有那物即有那情,无那物即无那情。如此一来,人的恻隐、不忍之情的产生似纯系乎偶发的“那物”,而真正生发人的恻隐、不忍之情的“生物之心”却不再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见此情以至见此心,人们只得被动地等待“那物”的出现,甚至“常妆个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可以看出,朱子之时,这种头足倒置、舍本逐末的为学现象已经出现,故朱子谆谆教诲学生“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触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而是无“那物”时,我心已在,必须就此已在之心上推扩。依朱子,“以羊易牛”章中因对牛的同情而发现自家本有的仁心并就此扩充以成就德行,原本只是孟子因机指点的方便说法,若学生执着于此,并以为是上手佳途,便不对了。为此,朱子乃反复叮咛,且累言之而不足:
如一场及时雨,我正求之不得呢。景花厂订单多了,现有人手忙不过来,我和阿花都在担心能不能如期交货呢。阿花说,水深水浅咱都要试试,阿坤你去,他林强信还能吃了你?
王见牛之觳觫而不忍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集注·梁惠王上)
(4)科学管理指标。科学管理指标主要用于对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定性调查,对矿山运营管理规范进行评估。对矿山开采企业而言应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实行生产责任制,定期对员工进行生产培训,实施人性化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
此处,朱子对“推”的理解明确指的是“扩充”,推恩就是扩充恻隐之心,朱子所谓“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明显是对着孟子“推恩足于保四海”而来的。而作为对“以羊易牛”章的总结,朱子同样把“推恩”了解为“扩充”,朱子云:“此章言人君当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齐王非无此心,而夺于功利之私,不能扩充以行仁政。”(集注·梁惠王上)
朱子在《集注》以外的说法也一样,如朱子云:
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这些子发了,又过却,明日这些子发了,又过却,都只是闲。若能扩充,于这一事发见,知得这是恻隐之心,是仁;于别底事便当将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这是本心,这是不忍处。若能充之于每事上,有害人之处便不可做,这也是充其恻隐。如齐宣王有爱牛之心,孟子谓“是乃仁术也”。若宣王能充着这心,看甚事不可做!(《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三《孟子三》)
如齐宣王因见牛而发不忍之心,此盖端绪也,便就此扩充,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方是。(《朱子语类》卷第十八《大学五》)
不过,如果我们把“推恩”问题放到第七章孟子与齐宣王的整个对话脉络中来理解,那么,其对话结构大体呈现这样的情形:
孺子入井之恻隐,爱牛之不忍,表达了相同的道德情感,扩充此情感则足于保四海。我们此前说过,推恩预设了A与B两种事件或境况,而且就理上言,推恩在原则上并无封限。这种说法既来自朱子,也印证了朱子的主张。上引所谓“于这一事发见”、“于别底事”即是两种事件由此推及于彼的表达,朱子只是将“推恩”的“推”理解为“充”或“扩充”,而扩充的结果并无封限,所以朱子云“使事事是仁”、“看甚事不可做”、“无一物不被其泽”。朱子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不采用墨家的“推”来理解孟子的“推恩”?由于未曾看到确切的文献,不敢断言。但朱子不用逻辑推理的概念,而用“扩充”的概念来了解“推”,当有其特定的用心,在义理上也更为周全,盖推理概念就其内涵规定而言指向的是理性的品格,而扩充概念就其内涵规定而言则偏向于意志的品格。若放在《孟子》的文本和思想系统中来了解,朱子的这种诠释无疑更为妥帖。
不过,朱子虽然在许多地方把推恩了解为扩充人的恻隐、不忍之心,但此恻隐、不忍之心,在朱子那里说的正是情,这与朱子对心、性、情的特定了解密切相关,如朱子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 (《集注·公孙丑上》)“如曰‘恻隐之心’,便是心上说情。”(《朱子语类》卷第四《性理一》)又云:“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见处。”(《朱子语类》卷第五《性理二》)正因为如此,学者将这种恻隐、不忍之心称为道德情感显然是有所据的。不过,若把朱子所理解的“推恩”直接了解为“推情”,却并不符合朱子的意思。在朱子那里,“推恩”的准确意思乃是扩充此心。
但是,有些学者如万百安[注] 万百安文请参阅“Kwong-loi Shun on Moral Reason in Menciu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4 (1991): 353-370.、井原敬、任满说等人则据此将孟子的“推恩”直接了解成“推情”,亦即“情感的扩充”(emotive extension)。他们的主张当然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孟子所言的推其不忍之心的确可以了解为推其道德情感,只是他们认为人的天生的情感能力已然自足,无需重要的改变、扩展和培养。[注] 主张“情感扩充”的学者虽然在主要方面有其相似的看法,但他们之间在具体观点上也各不相同。 暂且撇开他们在照应孟子的整体文本及义理上是否足够有效不论,“情感扩充”的主张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注] David B.Wong, “Reason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Mengzi,”Essay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engzi , eds. Xiusheng Liu, and Philip J.Ivanho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191.另一方面,情感如何扩充?单纯的情感本身是否可以给人的行动提供足够动力?这些问题在理论上似乎也并不是自明的。[注] 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如小张平时就喜好、也了解汽车,一日受同事之邀到销售汽车的4S店观看一部他早已了解、名声甚好的汽车,经由对样车的驾驶体验和销售员对该车的各种性能指标的详细讲解,发生了下述情况:1.小张知道了这是一部好车;2.小张从内心也喜欢这部车;3.小张也不缺钱购买这部车。但最后小张并没有购买这部车。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把它了解为情感在行为动机方面的失效。 而黄百锐则将自己的主张了解成“发展的扩充”(developmental extension)以区别于“逻辑的扩充”和“情感的扩充”。依黄氏,当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他的行为进行辩护时,他所诉诸的是他人的痛苦,而不是诉诸于他正好有解除他人痛苦的欲望。换言之,同情心既包含了解除他人痛苦的目的,也为解除这种痛苦的行为提供理由,但同情心却不包含对此一目的的欲望。[注] David B.Wong,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Philosophy East &West 41.1 (1991): 33.同情心包含了目的,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但同情心如何为行动提供证成的理由?一个出于同情的行为一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吗?朱子可能不会邃然同意,他明确指出:“恻隐羞恶,也有中节、不中节。若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便是不中节。”(《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三《孟子三》)又云:“四者(指四端之情——引者注)时时发动,特有正不正耳。”(《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三《孟子三》)由此看来,同情心并不具有行为规范的证成功能,不能一任同情心之发,“须有断制”,此断制即是此心所包含的仁与义,亦即理,故朱子云:“这仁与义,都在那恻隐羞恶之先,未有那恻隐底事时,已有那爱底心了;未有那羞恶底事时,已有那断制裁割底心了。”(《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三《孟子三》)
对防错系统检查可以发现故障,极大地提高可靠性。自检技术分为离线自检与在线自检。离线自检为定期对防错系统进行检查,发现固定性故障,只有无故障才可以开始工作。在线自检为边工作边自检,可以发现偶然性故障。每次开机后进行自检,自检方法有重复自检、再生输入自检、输出自检、校验自检与全信息自检[9]。通过上述措施来保证其在3个月内不发生故障。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思路。前面说过,朱子并不把“推恩”直接了解成“推情”,而是了解成扩充此心。依朱子,恻隐、不忍之情既为此心之发见处,那么,推此恻隐、不忍之情,严格说来当在推此心处用力,恻隐、不忍之情只是此心所发的表现,故而在根源意义上,扩充此恻隐、不忍之情当在扩充此心上下手,道德行动的理由和动机亦应当在此心(“心统性情”意义上的“心”)上寻找。所以,当孟子说宣王不行仁政,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乃折枝之类时,朱子对此注云:“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扩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难之有?”前面我们说过,当朱子把“推恩”了解成“扩充”,而“扩充”又偏向于意志的品格时,此意志则预设了一个道德主体,而这个道德主体正是朱子所说的“心”。如是,我们看到,在朱子的解释中,“推恩”似乎每每在不同的角度被了解为“推心”。如朱子云:“古之圣王所以博施济众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岂自外至哉。”(《孟子或问》卷一)“如爱牛,如赤子入井,这个便是真心。若理会得这个心了,都无事。”(《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四《陆氏》)又云:“心有何穷尽?只得此本然之体,推而应事接物皆是……盖此乃尽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则皆推得去无穷也。如‘见牛未见羊’说,苟见羊,则亦便是此心矣。”(《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孟子十》)依朱子,“推心”乃是“反本”的功夫,此前我们曾引朱子对孟子“是心足于王矣”的注释云:“王见牛之觳觫而不忍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此处所谓恻隐之心乃是仁心所发的端绪,“欲王察识于此”之“察识”在朱子乃是已发处的功夫,已发的察识功夫当然重要,但似乎不完整,察识的目的还要反本以见此心,并由此心推而扩充出去,“此心之发,固当密察存养而扩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几,乃存乎平日,所以涵养之厚薄,若曰必待其发见之已然,而后始用力焉,则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学者为无所用其力,可乎?”(《孟子或问》卷一)正因为此,在《集注》中,朱子常常强调“反本”来扩充此心,如朱子云:“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复萌,乃知此心不从外得,然犹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又云:“盖力求所欲,则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则所欲者不求而至。”《孟子或问》中的一段说法可以看作在某种意义上透露出了朱子对“情感扩充”论的批评和回应,朱子云:
范氏诸说皆善,伹以齐王不能推其所为,不能举斯心加诸彼,则孟子此言正谓推近及远者,发以明齐王能远遗近之失,欲其于此深识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爱物之心以及于仁民也。(《孟子或问》卷一)
此处所谓“爱物之心”指的是恻隐、不忍之情,乃此心之发见处。依朱子,孟子言“举斯心加诸彼”,即宣王对牛的不忍之情反其本以见此心(所谓“深识其本”),并就此扩充出去,而不是推已发不忍之情以仁民。依朱子,“斯心”与“此情”之间有一种“本根与枝叶”或“迹与本”的关系,我们不能重其“迹”而遗其“本”,而应该反其“本”而显其“迹”。假如我们将朱子此意与他把“推”理解为“扩充”,把“推恩”理解为“扩充此心”联系起来,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在朱子的心目中,宣王见牛之觳觫而生的不忍之情,只是一个“引子”。朱子真正教导我们的是,要透过这个“引子”让人反思到自家恻隐之仁心,此仁心深广不竭,不可胜用,惟就此扩充出去,方为究竟之法。
孟子告齐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执此,便不是。(《朱子语类》卷第一百《邵子之书》)
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触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时,此心何之?须常妆个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恻隐之心;无那物时,便无此心乎?”(《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训门人八》)
两组患者相较于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其中观察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国舞蹈的发展史反映了我国历代历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舞蹈文化也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特点以及越来越丰富的内涵,舞蹈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生活。
从文献资料上看,朱子对孟子“推恩”说的解释,除《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外,遍及《语类》、《或问》、《文集》等许多地方。理论上看,“推恩”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是人天生必有“恩”,此“恩”在上述的文本脉络中指的是恻隐之心,故朱子云:“人若无此,则不得谓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集注·公孙丑上》)推恩就是推此恻隐之心。但“推”究竟作何理解?如前所云,倪德卫和信广来等学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借用墨家“推”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将“推恩”了解成类比逻辑的推理。这种了解所遭遇到的理论难题是:无论是出于理性压力的策略(谓合理不合理),还是出于准逻辑的推论(谓一致不一致),推理能得出的只是知识,但却难以造就行动;何况就恻隐、同情之心作为道德情感来了解的话,其如何作为推理的对象也并非不待解而明的。而当我们转到朱子的理解时,我们注意到,在朱子的众多说法中,他并未将“推”与类比推理联系起来,而是直接把“推”理解为对恻隐之心的“扩充”。《集注》中,当宣王看到牛无罪就死之觳觫而心生不忍时,孟子指点曰“是心足以王矣”,朱子对此注云:
孟子指齐王爱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导之,非以为必如此然后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识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听其枝叶之自茂耶?(《朱子文集》卷七十三《杂著·胡子知言疑义》)
孟子此事,乃是一时间为齐王耳。今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程子门人》)
假如上述分析有其根据,则朱子对孟子“推恩”说的理解所体现的轻其枝叶、直落本根的方法,表现出与西方学者迥然不同的特色。按之于“以羊易牛”的案例,孟子的确指出了偶发的事件、情境的特殊事实,并就此事实中指点出不忍的道德情感。西方学者在诠释孟子“推恩”的过程中,无论持何种观点和主张,他们皆十分注重此偶发事件、情境,并就此事件、情境对人物所引发的各种可能的心理现象进行细密的分析。平心而论,这种努力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拓展和深化了儒家道德心理学的理论,应当得到重视和肯定。不过,如此一来,孟子的“推恩”理论所涉及到的更为基础性和本质性的问题反倒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方面,对偶发的事件、情境及其所引发的道德情感现象的分析得到了凸显与放大;另一方面,真正生发出此种道德情感的、不待外求的恻隐之仁心本身反而隐而不显。站在朱子的立场,这种了解方式毋宁说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依朱子,“推恩”问题主要不在注重这种由特定的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各种情感和态度,而是要人们由此已发的情感和态度反思到自家身上本有的恻隐之仁心,并就此栽培壅灌,涵养扩充,这才是掘井及泉的究竟一着。如果只是执着于此类偶发事件及其情感表现,则无异于舍本逐末,故朱子云:
知言问“以放心求心如何”,问得来好。他答不得,只举齐王见牛事。殊不知,只觉道我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见牛时方求得!……如终身不见此牛,不成此心便常不见!(《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孟子九》)
“因苗裔而识本根”、因那情而见那心并非全不对,却非为学成德的正确之方。学者当在本原处涵养理会,反其本而推之,即此心自然会触物便感,随感随应,随应随润,如是,则何须待那些子发见!
最后,孟子的“推恩”说在理论上还涉及到一个远近、难易和亲疏、厚薄的问题。依孟子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刑于寡妻,及于兄弟”,推恩的途径和方法即是由近及远,故朱子对此注云:“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当然,推恩所及的对象自非只止于同类之间,就仁心无封限而言,推恩必同时及于世间的每一物。如是,推恩就还有一个异类之间的推的问题。自己与骨肉之间“本同一气”,故爱由亲始;同类之间,虽有远近不同,但“同类而相亲”,故推恩容易;同类与异类之间,由于“同生而异类”,与人相隔亦远,推恩则较难。在“以羊易牛”章中,宣王对牛(作为异类之物)无罪就死而生不忍之情并给予赦免,但对其治下百姓的苦难却无动于衷,这是一种违背常识的做法,故朱子注曰:“盖天地之性,人为贵。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是以恻隐之发,则于民切而于物缓;推广仁术,则仁民易而爱物难。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则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为耳。”又云:“今王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是其爱物之心重且长,而仁民之心轻且短,失其当然之序而不自知也。”
围绕此一问题,学者争议较多的是其中涉及到的差等亲疏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但孟子同时又主张“爱有差等”。如是,推恩的普遍之爱与爱有差等两者之间便难以相容。基本上,孟子的推恩以恻隐之仁心为基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为路径,以“达之于天下”(《孟子·尽心上》)为目的,故而我们认为,推恩在原则上是一个无封限的概念,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称作普遍之爱。但孟子的思想中的确蕴含爱有差等,在孟子与夷子的辩论中,孟子认为,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却是二本,朱子对此注云:“孟子言人之爱其兄子与邻之子,本有差等。……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然而,在理论上,普遍之爱与差等之爱如何得到合理的说明呢?《孟子或问》的一段话可以给人启发,朱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运于掌,何也?曰: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爱必自亲始。为天下者诚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则虽天下之大而亲疏远迩无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岂不易哉。”(《孟子或问》卷一)普遍的爱是“理一”,差等的爱是“分殊”。因为是“理一”,所以普遍之爱有其必然;又因为世间万物各有不同,所以差等之爱有其必要;虽谓差等,但其爱则一,故而在朱子看来,“推恩”与“爱有差等”并不矛盾。
三、 对孟子的扭转?
就较为狭隘的意义上说,“推恩”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道德实践中的道德成就问题,而理解孟子的道德实践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或方式:其一是通过说明“四德”之实践所需要的人性论基础和修养功夫来呈现孟子道德实践理论的特征,即此而言,我们会认为,孟子的道德哲学倾向于动机论和义务论;其二是通过分析孟子与他人的对话或论辩,尤其是通过分析孟子试图借此对话和论辩以改变他人的道德思考、走上道德实践之路的事例来呈现孟子道德实践的特色。按理,上述两种进路所讨论的道德实践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但表现上却不尽相同:前者侧重于从道德实践的理论层面来表现孟子道德哲学的特色,它要求在理论上提供一套可证成、可委身的价值理想;后者则侧重于从道德实践的事实层面(如对话、论辩等)来表现孟子思想的特点。但由于后者明显地落在对话和论辩的脉络之中,因而显示出很强的“理由”、“效果”呈现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在对话脉络中可能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理论问题。
如前所述,“推恩”问题在第七章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脉络中首先是作为政治与社会哲学问题而提出的。政治当然要以道德作为基础,但政治问题与道德哲学问题却有不同的侧重:前者所关心的是“事”,所讲求的是“效果”;后者所关心的是“理”,所讲求的是价值的证成与委身。而我们通过朱子对孟子“推恩”理论的诠释,可以看到,朱子虽然紧扣着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对话、论辩脉络展开,但很明显,朱子是将孟子的“推恩”理论在较严格的意义上理解为一套道德哲学的术语(terms),解释为对“恻隐之仁心”的“扩充”,而扩充恻隐之仁心即落在道德成就或道德实现的层面。此一现象至少表示出朱子对孟子劝说齐宣王的对话更多的是站在成就道德的角度来理解的,而未将孟子如何从对话、劝说的角度“打动”(motivate)齐宣王施行仁政以统一天下的政治考量更多地纳入其中。在朱子看来,孟子的目的是意欲通过说服、劝导的方式让齐宣王完善和成就道德,而不是直接劝说他实行仁政。在朱子的理解中,孟子所取的宣王对牛的不忍,并就此所作的一整套包括“推恩”在内的道德劝说,只不过是孟子的一种方便说法而已,因为在朱子看来,齐宣王“人欲蔽固”(《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而要对这种人进行有效的道德劝说和引导,便只能“指其可取者言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否则便很难达到劝说的目的。依朱子,齐宣王只要依照孟子的劝说,由见牛所生的同情反其本,扩充其恻隐之仁心,即可成就道德。至于仁义政治和统一天下乃是顺此而有的不期然而然的结果。
通过对部分职业院校教师调查和分析,目前教师在教科研能力主要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认为自己只要上好课就行了,高不可攀的教科研与自己关系不大,有这种认识的大多数是普通专业教师;第二种倾向是想致力于提升自己教科研综合能力,但找不到交流合作培训的平台,持这种观点的教师基本都是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
1. 宣王志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2. 孟子说,只要实行仁政,保民而王,则可以实现其志向;
3. 所以宣王应该推恩以行仁政。
提问的艺术性中融合了创造力与智慧的果实,教师应注重提问方式的灵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答形式,结合文章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问答,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同时,实现课堂教学形式的灵活多变,促进师生思维方式的协调统一。问题的设置要最大化地彰显教师个性,促进提问语言的生动,提升其语言美感,从而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深度思考。
在此一对话结构中,孟子的中心关怀是仁义政治的施行,“推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正因为如此,在理解上述的对话结构时,我们充分地将齐宣王的政治目的纳入到孟子的劝说中来考虑。第七章一开头齐宣王即要求孟子讲述齐桓、晋文称霸诸侯之事,此已确然无疑地透露了宣王的心志,但孟子却劝说宣王要实行仁政,并通过“以羊易牛”的事例向宣王证明:1.宣王有能力实行仁政;2.同时,宣王通过孟子的劝说,也了解到其治下的百姓处于苦难之中,觉得自己应该对百姓推恩。但是,宣王却“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孟子认为宣王是不为而非不能。然而,为什么不为?宣王谓“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宣王之大欲即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不过,孟子除了认为依宣王那种做法根本不可能满足其愿望外,似乎自始至终皆没有对宣王之政治大欲的正当性问题给予必要的反省;同时,孟子似乎也没有就仁政本身在理上的自足性给予足够的说明。相反,在孟子的劝说脉络中,反而顺着宣王的心志,认为只要宣王施仁政便可竞其一统天下之功。换言之,孟子首先默认了宣王的政治大欲,只是认为如欲成就其政治大欲,当以推恩以行仁政为先,如是,“推恩”问题似乎成了成就宣王政治大欲的手段。[注] 此一对话结构的特色亦可见于第五章。
经研究表明,观察组中老年糖尿病合并脑梗塞患者检出率90.00%(阴性患者10例、百分比为10.00%;阳性患者90例、百分比为90.00%)高于对照组检出率8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将此对话结构表述为:
1. A有X欲望;
植物体内同化物的流动具有向库性,和植物具有向光性都是植物的特性。植物具有向光性,但如果没有光,植物的向光性就显示不出来。同样,植物体内的同化物,在没有库信号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停在原处不动。“小麦籽粒的干物质约有40%来源于旗叶,如果把正在灌浆的麦穗剪掉……结果同化物多以淀粉的形式积累于叶片中”[《植物生理学》(2016年7月第一版)(中国林业出版社)(第173页第25行)]。这个实验证实了同化物的移动与库信号相关联。
2. 行仁政可以实现和满足A的X欲望;
3. A应行仁政。
在上面的对话结构中,宣王所以行仁政(此仁政即包括推恩问题在内)乃是因为由此可以成就其政治大欲。如是,仁政之被实行并不是出于仁政本身,而是出于宣王之政治大欲。若就理论本身而言,孟子试图劝说宣王行仁政,其最大的理由当来自于仁政本身,可在上述对话结构中,孟子并未在这点上用心。相反,在孟子的对话中,仁政只是出于实现宣王之政治大欲的“目的—手段”的考虑,而成为行动的理由,而仁政本身却不构成行动的理由。
宣王没有行仁政,没有推其恩以泽其治下的百姓,“推恩”失败了,孟子说宣王是“不为”。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看,“推恩”的失败或宣王的“不为”涉及到对话者为何要“推”其“恩”以行仁政的动机或欲望问题。在上述对话脉络中,我们看到,宣王最大的欲望是莅中国而抚四夷,今假设经由孟子的劝说,宣王即便有了行仁政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也并不是由仁政本身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其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产生的。用休谟的话来说,这种欲望也只是“衍生”(derive)的,而不是“原生”(original)的欲望,因而宣王即便认识到行仁政的理由,此理由也只是工具性质的理由。孟子随顺宣王之政治大欲,以为行仁政即可无敌于天下,这种劝说在效果上的确足以让宣王动心。然而,无敌于天下是行仁政自然而有的结果,而不是为什么要行仁政的理由。如此看来,孟子对宣王的对话和劝说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证成仁义之政,而似乎在竭力为宣王给出行仁政的动机和理由。不过,这种劝说策略也潜藏着一些问题,给出人们去做某事(行仁政)的动机和理由,主要在情感和欲望上激发和“推动”人们去做某事,其重点并不落在某事(行仁政)本身是对的,并因为某事是对的而应该去做;相反,是因为劝说对象看到了做某事(行仁政)的好处,而这种好处又恰恰能够满足其最大的欲望(“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换言之,孟子的对话和劝说似乎是以效果论为道德实践寻找动机和理由,这在理论上便会有极大的风险[注] 有关孟子思想或其道德劝说是否具有效果论性质的问题,西方学者间或有所提出,可参阅顾立雅 (G.H.Creel,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ze -tung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86-87);倪德卫 (David S.Nivison,The Way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 ed. & Intro. Bryan W.Van Norden,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1996, p.106);信广来(Kwong-loi Shun, “Moral Reasons in Confucian Ethic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6, 1989, p.341.)等。中文学界较有代表性的是蔡信安,参阅氏著:《道德抉择理论》,台北:时英出版社,1993年,第150~154页。。盖从孟子道德哲学的理论上看,仁政本身便具有理由和动机的自足性,仁政也不需要依凭别的效果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或正当性。仁政之实行自然有其效果(如统天下于王道),但此效果不是用来证明仁政之正确,而是仁政之实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
如此看来,孟子的道德哲学理论与其通过对话和劝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理论特色之间似乎并不那么协调一致[注] 此处所谓“并不那么协调一致”乃基于两个假设的前提:一是假定对《孟子》一书可以有整体理论的把握和章节对话脉络的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读法;二是假定孟子的相关对话章节可以作为独立的文本加以分析。某一段落或章节是否可以作为独立文本加以分析,而不至于被认为断章取义,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该段落或章节论述的目的、宗旨清楚且确定;2.该段落或章节论证的过程完整而清晰。 ,前者可以被诠释为一套“义务论”,后者却具有“效果论”的意味。与此相应,“推恩”问题如果落在前者,其自身便是自足的[注] 朱子云:“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讨,反己自求。”(《语类》卷第十九《论语一·论孟纲领》) ;如果落在后者,“推恩”即可能成为某种手段或工具。
假如上述分析还有文本根据的话,则朱子本人是否意识到可以对《孟子》一书就有关对话、劝说的章节在结构上进行独立的理解和分析,我们目前尚未看到相关的文字。但可以确定的是,朱子将《孟子》的“梁惠王上”第七章理解为一套自足的心性论理论;同时,以朱子四十年如一日注释“四书”,他不可能不熟悉《孟子》一书的篇章和对话结构。剩下的可能解释是,朱子或者根本不认为第七章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在结构及此结构蕴含的意义理解上存在任何问题;或者朱子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将孟子与宣王的对话结构及其蕴含的意义理解从孟子的整体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把握。就目前来看,后一种解释无疑更符合朱子的理解方向。当然,指出《孟子》一书中整体理解上所表现的道德哲学的“义务论”特色与某些对话章节结构中所表现的“效果论”意味,或许是有些学者不愿看到的,但此一现象的确具有文本解读的根据。考虑到孟子的核心关怀是在政治上推行仁政,而其所使用的却是心性的道德的方法,故而在孟子与各诸侯的对话、劝说中,政事与道德之间不免会有夹杂、扞格,这似乎并不难理解。何况战国之时,各诸侯一心想的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孟子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若不从“效果”上打动他们,几乎连对话的可能都非常小。[注] 对话、劝说如要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在现场情境下切实“打动”对方;而面对满眼都是功利的诸侯而言,若不在“效果”上着手,则很难真正“打动”他们。这是从常识着眼的理解,却十分符合战国时期众多士人游说诸侯的策略。 由此观之,在孟子的整体理论特色与章节对话蕴含之间存在扞格和罅缝,毋宁说是合乎情理的。而相比之下,朱子的理解便显得更为纯粹,直以心性道德的语言和思路对孟子的“推恩”问题作出了融贯的说明。仁政王道的问题在朱子的理解中,不是作为目的问题而出现,而是作为“推恩”所表现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完成自然而有的结果。
在此并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朱子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对孟子的“扭转”。
四、 简短的结语
“推恩”问题在孟子的思想中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理论问题,涉及到政治、道德以及道德心理学的诸多方面,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相当的重视。而朱子对“推恩”问题的理解与他的整个心性理论协调一致、紧密相连,同时也表现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解颇为不同的理论特色。朱子把“推恩”的“推”理解为“扩充”,而所扩充的主要不是作为已发的恻隐、不忍的道德情感,而是此道德情感赖以生发的恻隐之仁心,故而朱子教导人们应在此未发的恻隐之仁心处涵养用力,而不应过分执着于因境而发的道德情感。推恩所涉及到的远近、难易、差等等问题,朱子则以其“理一分殊”的理论加以解释,表现出儒家传统智慧的特色。总体而言,朱子对“推恩”的理解自成一体,在理论的整全性和一致性上,有胜于西方学者的一面。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Extending Gratitude”
Dongfang Shuo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The notion oftui ’en 推恩, which literally means “extending gratitude,” appears inMencius 孟子.Tui ’en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phenomenon. If a certain thing or situation can give rise to a relevant kind of moral response in an agent’sxin 心 (heart/emotion)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then his or herxin will extend the same moral response to similar things or situations, so that the agent exhibits moral virtues in all circumstances. The phenomenon oftui ’en is connected to complex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moral problems. While many scholars in Chinese philosophy, especially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 have tried to give their own accounts oftui ’en , I will focus o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per. I try to argue that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tui ’en is better than most Western account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herence and unification, although the latter is not without merits. In the process, I have two aims in my mind. The first aim is, through articulating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to reply the mainstream account proposed by Western scholars. The second aim is to reveal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Zhu Xi’s philosophy, in particular, his “twisting” of Mencius.
Keywords :Mencius; extending gratitude; Zhu Xi; extend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mind
[作者简介] 东方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新编》”(项目批准号:17ZOA0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晓 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