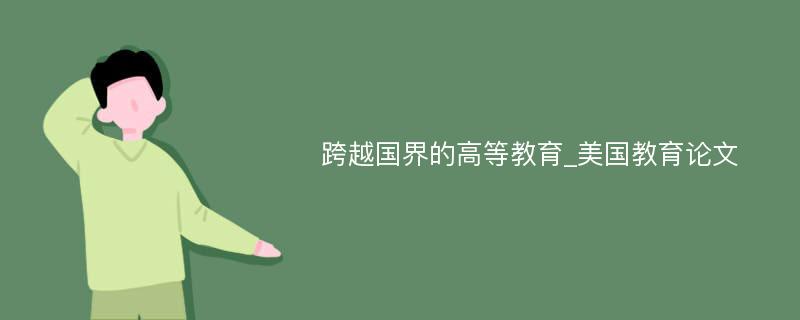
跨越国界的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国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00万离开自己国家到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最近的研究显示,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800万。由于各种原因,希望学生出国留学的国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呈增多趋势。工业化国家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让自己的学生出国学习,以增强全球化意识,从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例如,欧盟已经制定了政策,鼓励学生在欧盟内部跨国学习。随着欧盟的扩大和“博洛尼亚计划”(Bologna initiatives)的实施,欧盟国家的学术结构将更趋和谐,跨国学生的数量也将大大增加。
另外,在一些国家,中等后教育的容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入学要求。总体而言,世界范围内学生的流向是由南向北,即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北方富裕国家。目前,全世界接受中等后教育的学生有超过一半在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比例还将增加。这些人口高增长国家常常不能满足国内的教育需求,于是它们将越来越多的学生送到海外学习。北方富裕国家的中等后教育机构有较大的教育容量,而且由于在课程和科学话语(scientific discourse)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们在当代学术市场上享有不可置疑的声誉和实力。
对于那些留学生输入国而言,国际高等教育堪称一笔大买卖。例如,外国学生每年能为美国带来12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其学习费用由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支付)。在当前美国经济紧缩的大环境下,这部分学生非常受欢迎。而且,外国留学生不仅仅是来占据教育空间的,他们还为一些关键领域增加了高素质人才的数量,从而提升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在一些研究生专业中(例如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外国学生甚至在博士生中占据了大多数。
目前,美国共有586,000名外国留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使其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入国。美国吸引的留学生数量超过了三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英国、德国和法国)所吸引留学生数量的总和。赴美留学生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中有55%来自亚洲(排名前五位的留学生输出国和地区分别是印度、中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
然而,随着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对美留学生输出国的情况也发生着变化。例如,伊朗曾经是最大的对美留学生输出国之一,但自从巴列维国王政权垮台后,就再也没有伊朗学生到美国求学。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最近陷入困境,再加上由9·11事件引发的一些问题,该国向美国输出的留学生在去年一年中减少了10%。同一时期,与美国素有较强学术联系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向美国输出的留学生减少了2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美国输出的留学生减少了16%。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的亚洲输出国——尤其是印度(该国在2001~2002年度取代中国成为最大的对美留学生输出国)和韩国,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留学生数量的减少。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清楚2002~2003年的数字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模式还是只是短期的调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2001~2002年度赴美留学人员的数量还是增长了6.4%),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统治地位已不再无可置疑。
“推”与“拉”
很多国家对学生的跨国流动颇有兴趣,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学生是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推”到别的国家去的。由于教育容量不足以及有时入学要求过于严苛,许多学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却无法进入当地的大学。这类学生常常发现,进入外国的优秀大学反而比进入本地大学容易一些。很多最优秀的学生寻求留学海外是因为“世界级”的大学非常之少,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这样高质量的大学。还有一些学生出国留学是因为在国内无法学到想学的专业,在研究生层次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硕士和博士层次提供的学习机会极为有限,而且所能提供的学习计划也极少具有国际竞争力。
一些社会和政治因素也会将学生“推”离自己的国家。在一些情况下,歧视性的招生政策(例如马来西亚针对华裔学生而专门给予马来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会使学生不得不求学他国。学生出国学习或者是为了躲避国内的政治压迫及其他方面的压迫,或者是为了追求学术自由。还有一些学生出国是为了逃离不堪学生运动、教师罢工、政府施压之重负的学术系统。
由于众多原因,大多数出国求学的学生被“拉”到了美国。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术体系。一些学生认为,外国学位(特别是美国学位)所带给个人的荣耀要高于本国的学位。同时,很多学生发现不选择生源的美国高校其入学难度要低于本国学校,因此,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被吸引到一些声望较差的四年制大学和较好的社区学院。这样,美国学术体系的各部分都对外国学生形成了“拉”力。不仅如此,这个国家本身也是一种吸引力——这里不仅有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其文化更是遍播全球。
相当一部分学生留学海外是为了在留学国谋求职业并定居。美国是这类留学生的首选目标,因为美国有着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系,雇主们愿意雇用合格的外国人,而且包括学术在内的很多领域能够提供可观的薪水。但是要想量化这部分留学动机则比较困难,因为极少有人会承认他们赴美留学的目的是为了移民,尽管来自一些国家的留学生的不返回率(non-return rates)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据估计,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留在美国的比例分别介于66%~92%和77%~88%之间。
9·11事件及其启示
9·11事件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的学术和研究体系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各国学生仍然视美国为留学首选地。美国的巨大容量和多样性仍然是使其具有特别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然而,变化也是存在的——一些显而易见,一些模糊难辨,还有一些尚未显现。在全球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的总趋势下,2002~2003年度赴美留学生的数量却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所接纳留学生的数量则获得了大幅增加。这些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上越来越商业化的国家正享受着美国日益不友好的留学环境为它们创造的利益机会。现在,赴美留学之路已变得障碍重重,留学生们已经对美国政府严格、多变、刚愎,甚至有时反复无常的政策(如签证规定、向政府部门报告等)提高了警惕。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实施的学生与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以及新增的收费项目更是加重了外国学生的负担。更为糟糕的是,关于这些困难的各种传闻也起到了与事实同样大的破坏作用。很多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听到这些传闻后,将美国排出在选择范围之外。
最近的调查显示,有留学意向的学生认为美国目前的安全程度要低于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但由于9·11之后美国没有再发生较大的恐怖袭击,关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并不十分突出。尽管美国的留学生事务官员注意到,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但目前已经身在美国的外国学生却反映感觉相当安全。这说明,担心主要来自外部。9·11事件发生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外国学生离美回国,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又返回美国继续学习。
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绝非一池静水。主要的竞争者们都愈来愈重视吸引留学生到本国大学学习,它们把美国给外国学生设置的障碍视为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澳大利亚现已成为一个锋芒日盛的留学生吸收国,英国和新西兰紧随其后。这几个国家都把吸引外国学生前来留学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们都制定了积极的留学生教育政策以图减轻地方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
“博洛尼亚行动”在欧洲引起的变化虽然朝向另一个方向,但同样不可忽视。更多的欧洲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在欧盟内部留学,因为这里学费相对较低,而且欧盟的“共同学术空间”(common academic space)使跨国学习变得较为容易。一旦在五、六年后全面运作起来,欧盟很可能会转向欧洲之外去吸引非成员国学生到其成员国留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实现其外交政策。
美国人在海外
到海外留学的美国人也呈增加趋势,但增加速度较为缓慢。2001~2002年度,留学海外的美国人为161,000人,这一数字比2000~2001年增加了4.4%。这种增加趋势已经持续有10年左右。长久以来,美国高校(特别是那些享有较高声望者)一直宣称,要在本科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如果可能,还要为学生提供出国经历。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学生有必要对整个世界有一定的认识。尽管如此,四年制高校本科生中到国外学习的学生比例仅为0.2%。
赴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的行为不同于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绝大多数是本科生,他们几乎从不在国外拿学位。相反,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多为研究生和专业学生(Drofessional student),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在美国获得学位。一般而言,美国学生大多在大学三年级到其他国家去经历“文化体验”,接受语言训练,而非学习学术知识。近年来,美国学生到海外学习的平均时间已经缩短到了一个夏季甚至更少;许多批评者同时指出,这些学习计划的学术标准也在降低。与此相反,到美国留学的外国人极为注重学术和专业训练,他们追求的正是美国学位的知识与声望价值。
长期以来,出国学习的美国人乐于选择的国家很少变化。大多数美国人选择去富裕国家(在最受青睐的9个国家里,只有墨西哥是非工业化国家)。其中,62%选择欧洲作为目的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集中了一半美国学生,其他一些与美国有移民或其他联系的国家(例如希腊和以色列)也吸引着一部分美国学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1~2002年度只有不到3%的美国学生去了非洲。
美国高校也主动采取措施促进学校的国际化,例如招收外国学生、建立合作交流项目以加强大学之间的联系等。这些措施增进了跨国界的学生流动。尽管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庞大,但在美国四年制高校本科生总数中,他们只占2.7%;在研究生中,他们的比例也只有1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其他主要的留学生输入国中外国研究生的比例。
新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
高等教育机构也加入到了跨国流动的行列之中。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高等教育跨国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分支,不同国家的大学合作实施学术项目,高等教育经由远程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方面的发展将影响到学生的跨国流动。
与学生流相同,跨国学术与教育项目的动向也是由南至北。就课程、学术方向以及师资等方面而言,这些合作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由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学术与教育机构主导。即使合作项目所在国的教学语言并非英语,教学语言往往是主导机构所在国的语言(多为英语)。通常,合作项目所在国很少作出努力去使来自发达国家的模式适应该国的需要或传统,它们只是原封不动地引进这些项目和计划。举个非学术界的例子,尽管马来西亚的汉堡包必须使用伊斯兰教的合法牛肉以满足该教的宗教要求,但马来西亚的麦当劳汉堡包与芝加哥的麦当劳汉堡包毫无区别。
在跨国高等教育方面,澳大利亚和英国一直是先驱,美国只是最近才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一支主要力量。在跨国高等教育合作中,既有中等后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有教育机构与有意进军这项新教育产业的公司或企业家的合作。例如,澳大利亚一些大学已经与马来西亚、南非和越南的学术机构和私人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而可以在这些国家颁发澳大利亚学位。一个学生可以无需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就获得澳大利亚的学位。此外,根据一些特许协议,在颁发本校学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院校可以使用发达国家大学的教学计划。各国政府都把跨国教育视为增加高等教育收入的一条途径,各院校也是如此。国际合作计划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尽管这类学校目前为数不多。毫无疑问,许多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或开办跨国项目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尽管美国的学术机构并没有在跨国教育中占据显要位置,但它们在这一领域中存在已久。一些美国大学,例如波土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和韦德纳大学(Wide ner University),很早就在海外开设了分校,为美国人(包括美国驻外武装力量中的工作人员)和外国客户提供服务。还有一些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借美国认证和赞助之名得以运营,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十几所美国大学在日本开设分校,希望能从当时繁荣的日本经济和学术市场中获利。但除一两所之外,这些学校绝大多数都不是美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因此日本教育界并不十分认同它们的分校。当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些分校也随之遭遇了严重的经济与生源危机。现在,它们中只有一所仍能幸存。这一案例说明,高等教育的海外扩张是一项风险事业。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更成熟的路子来进行全球扩张。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商学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设有一所分校,该分校可颁发芝加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其课程中安排有一段时间在芝加哥大学校本部进行学习。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正在新加坡建立分校。在保加利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美国大学正在帮助建立越来越多名为“……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的高等学校。这些学校能够得到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
在一些情况下,美国高等教育的海外扩张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商业性质。几年前,以色列开放了其教育市场。为满足当地需求,一些美国高校与以色列企业家合作,在教师教育领域和一些其他领域开设了学习计划。这些美国学校的声望都比较差,有些甚至质量低劣,它们急需从海外生源身上获得资金来源。不久,出于对教育质量低劣以及主办机构监督松懈的担忧,以色列有关部门紧缩了国际合作办学的渠道。盈利性高等教育提供商西尔文学习公司(Sylvan Learning Systems)正走出一条高等教育海外扩张的创新之路。该公司已经在墨西哥、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买下了几所学校。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学校将与美国学校进行合作还是将在美国获得认证。毫无疑问,美国的高等教育出口将获得增长,并将对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产生难以预计的重要影响。
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的实施,在全球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开办贸易,可能会增加跨国教育的机会,但同时可能带来诸多相关问题。如果得以实施,服务贸易总协定将解除一些对跨国高等教育的限制,这将有利于美国学术机构和公司在海外开办学习计划和建立分支机构。但是目前还无法预见这些变化将给国际学生流动以及美国大学的具体政策带来何种影响。
代表政府立场的美国商务部和盈利性的私人高等教育提供商对服务贸易总协定表示欢迎,而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等组织及学术界则普遍对此协定表示反对。它们主要担心,由服务贸易总协定带来的竞争与市场化倾向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不能像钢铁或香蕉一样作为商品在国际市场中进行交易。高等教育界还有人担心,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后,发展中国家将丧失对高等教育进口的控制能力,从而使其自身的高等教育自治权遭到损害。种种争论仍在继续,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可能影响也仍旧复杂莫测。
远程教育也是跨国教育的一部分。目前,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尚小,但其学生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学生规模将持续扩大。远程教育学位在全球工作市场中能得到承认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会不会有大量的学生不愿再跨越国界,而是选择通过因特网进行学习?这些问题的提出将有助于确定日益发展的远程教育技术对跨国学生流可能产生的影响。
结论
在迅速扩大的国际学习市场中,美国正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竞争者们拥有一些显著的优势。它们制定有与国际学习和跨国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和计划。这些国家早已设定目标,实施政策,并且鼓励学术机构吸引外国学生。相比之下,美国却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国际高等教育政策,联邦政府也极少提供足够的支持。现在,美国的确有了全国性的政策,但它们全都是负面的——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外国学生和学者的赴美之路变得困难重重。作为美国政府政策的执行者,美国驻各国使馆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则向有意留美的学生传达着最具负面影响的信息。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提供给海外学生的联邦奖学金的数量在去年出现了下滑。传统上负责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州已经变得不再关心甚至敌视外国留学生,尽管这些学生为地方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并且为公立大学提供了廉价助教与助研人员的来源。因此,在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很可能不会出台鼓励国际交流的公共政策。
国际学生流动已形成这样一幅画面:全球学生数量显著增加,主要留学生输入国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技术对学术计划的实施影响日增,但这种影响仍不明晰。由于其容量、重要性及其学术体系的优越质量,美国仍将在所有这些发展变化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美国是否仍能保持其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则另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