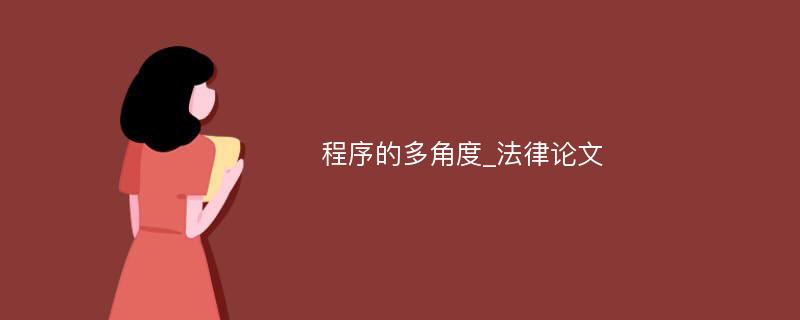
程序的多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学者对程序的误读
程序源于人的存在和交往,最初是自然性质的,受习惯法的约束和支持。随着人类控 制社会能力的提高,社会秩序被理性化,程序也被理性化,程序具有了人为的构造性意 义和工具理性功能。程序主义并不限于纯法律问题,它是超越法学范畴的、多学科性的 社会理论。至少我们会发现:罗尔斯、哈贝马斯、卢曼的程序理论是兼具哲学性质的, 有着根深蒂固的民主和宪政思想渊源。
在中国,真正从抽象的哲学层面探讨程序问题,肇始于季卫东先生1993年发表的《法 律程序的意义》一文。身居国外的他与国内学者的程序观是否也有思维层面的根本性差 异甚至冲突值得探讨,国内学者的程序语境与季先生的程序语境也可能是不同的。大体 说来,国内学者关于程序的探讨是一种注释性的概念阐释思维方式,高度关注具体化的 、形式化的法律技术,没有将法律程序话语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 学和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中国学界对法律程序的切入是在法治国家建构的浪潮下开始 的,因此不可避免地突出了程序的法治特征,尤其是形式性和工具性。但是,程序主义 体现为一个变迁性过程,它的主题已经从关注法治的形式性切换到关注民主和人权的主 体性、经济的效益性上来了,从程序的普遍遵守视角转到利害关系人对争议的参加、论 证和同意上来了。抱着不敢苟同的态度,我认为,中国学者对程序的误读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正当程序的思想谱系是否起源于13世纪?
对程序理论的时空定位主要依据是对英美法制正当程序渊源的解释。(注:1215年英国 《大宪章》第39条:“除依据法定判决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流 放及其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Magna Carta,1215,Article39.No freemen shall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disseized or exiled or in any waydestroyed,nor will we go upon him nor send upon him,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法令规定: “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 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No man of what state orcondition he be,shall be put out of his lands or tenements nor taken,nor disinherited,nor put to death,without he be brought to answer by due process of law;美国宪法第5、14条修正案均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 的生命、自由和财产。”nor be deprived of life,liberty,or property,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但是,按照正当程序规则的具体内容分析,程序理念发现的时间 可能要向前推进。博登海默就认为,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法和平等观念的人道主义思想 促进了罗马帝国的法律改革,尤其是对奴隶制产生了影响,哈德良皇帝(公元118—138 年)曾经规定,“禁止奴隶主不经过地方法官的判决就处死其奴隶”、“禁止在没有事 实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情况下对奴隶刑讯逼供。”(注:[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 《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但是,这还不是正当程序最早 的理论雏形和具体实践的开始,正当程序至少可以被溯及到公元前6世纪的早期。爱尔 兰法学家凯利认为,古希腊语中虽然没有与今天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对应的术语, 但在希腊社会,若一个人未经审判或定罪而被处死就是一种暴行,有诸多的希腊作品对 未经审判或有罪判决而进行惩罚的现象进行谴责,这表明“在雅典至少存在着一种强烈 的,即便并不专业的支持有序的、无偏的司法程序的情感。”并且,雅典“法律宣布对 一个人就同样行为只能提起一次诉讼。”(注:[爱尔兰]M.凯利著,王笑红译:《西方 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在文化的视角里,正当程序的渊源 可以追溯得更远,听取相对方意见的程序原则可能缘起于伊甸园的“原罪裁判”——上 帝在处罚亚当与夏娃之前倾听过他们的意见。
(二)“中国人重实体、轻程序”是正确的结论吗?
其实,中国自古就不缺少程序(中国语境里的“程序”),只是缺少正当性的、能够保 障人权、抑制公共权力滥用的程序(西方语境里的“程序”)。如果中国人真心真意地重 视实体法上的权利保护,社会和政府就会想到程序安排的重要性。只能说因为没有真正 重视人权和民主,中国才缺少基于程序视角的人权和民主保障机制。程序的工具理性功 能既源于实体正义的内在要求,又可以独立地保障权利实现。
(三)程序是否是法治主义的产物?
实际上,程序与法治是并列关系和相互独立的范畴,程序主义先于法治主义产生,二 者并非包容关系。例如,从结构上说,社会契约、法治和正当程序是美国宪法设定的约 束权力的三种独立方式。(注:[美]埃尔金、索乌坦著,周叶谦译:《新宪政论》,三 联书店1997年版,第182页。)程序并非法治的从属物,也不能仅仅从法治视角来狭隘地 诠释程序。
(四)中国学者对程序进行诠释的视角是否需要改变?
仅仅从法治的视角诠释程序,可能导向纯粹形式主义,最后程序亦变成压制性工具。 我们是否忽视了主权在民原则的理念力量和制度建构?程序理念和制度是否需要揉进民 主和人权的成份?程序法是否只是“仆法”或“手段”,程序权利是否可以或者正在创 制、修正和颠覆实体权利?这些诘问表明:中国对程序的研究语境应该是开放性的,对 程序应该有多视角的解读,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效益都是诠释程序的相互独立的视 角,并且不能采取相互定义、“概念乱伦”的方式解释人权、法治、民主、宪政、程序 诸概念的涵义。
二、从人权视角诠释程序
姑且沿袭已有定论,把13世纪欧美关于正当程序的立宪定位为程序主义的历史源头。 但是,英美程序主义的最初切入点与中国今天的程序观有所不同。正当程序最初被置于 政府——公民二元架构之下,即政府和公民两造对抗之间,它首先是一种批判性制度, 起初与刑事性的司法公正审判联系在一起,后来被扩展到福利权领域。(注:英美法的 正当程序从刑事程序开始,渐至行政程序,再到实体法的正当性。我国台湾省“大胆的 将所谓正当程序条款,扩张至立法程序,甚至是修宪程序中,这是在英美法的发展中所 无的。”“在移植这个正当程序的概念时,附加了台湾自己的特色。”吴景钦:《张君 劢与英国大宪章》,http://www.libertas2000.net/gallery/zgxz/wuJQ.htm.)“正当 程序建立在政府不得专横、任性地行事的原则之上。它意味着政府只能按法律确立的方 式和法律为保护个人权利对政府施加的限制进行活动。”(注:[美]伦斯特洛姆编,贺 卫方等译:《美国法律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正当程序包 括程序性的正当程序和实体性的正当程序两种。其中,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目的在于限制 公共权力和保护人权,并且它们是以自然正义和契约同意理论为基点和轴心向外辐射的 ,(注:[美]施瓦茨著,徐炳译:《美国法律史》,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5页。 )这是关键之点。也就是说,程序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权,设定程序是用以批判和检验 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正当程序一词一般喻指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状况、确立行 使权力者与权力对象之间互动秩序、体现某种正义理念的程序性或实质性评价标准。” (注:郑成良、杨云彪:《关于正当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9年第3期,第7页。)程序性的正当程序主要是指通知、评论和听证权不能被剥夺 。不难看出,西方语境里的程序与中国语境里的程序,首先在调整对象和客体指向上存 在分歧:正当程序是个人主义和原子论的,而非公共秩序的视角,尤其不是政府的视角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正当”的涵义,也无法诉诸人权或者自 然法的其他价值来批判和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在英美法律中,正当程序是一项独立的 人权保障根本原则,程序正义尤其指向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注:[日]古口安平著 ,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 页。)人权保障这一价值理念是正当程序的逻辑起点。与之相反,中国的程序主义最初 起源于压制性的官僚法,诠释程序的视角自然而然地指向权力主体的管理秩序,与人权 无涉。例如,“三纲五常”作为乡土中国典型的伦理法律制度,主张“君为臣纲、父为 子纲、夫为妇纲”,这样的实体性规则必然要求非人道的程序主义和象征仪式。
三、从法治视角诠释程序
中国学者对程序主义的本土践行并不陌生,但我们对程序的法哲学性研究相当之晚, 大约始于1993年。程序主义在中国本土切入的背景,正是法治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年代, 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均对法治的工具功能充满了幻想,“法治”被作为基本范畴和终极价 值目标用以阐释社会众多现象。例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即程序”、“ 依法治x”等结论随处可见。不可否认,法治理想的张扬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 ,法治主义的膨胀也足以影响程序的本真面目,程序主义在法治浪潮下已经被“去真存 伪”。一定意义上,人们不是在探讨法律程序固有的、内在的、独立的品质和价值,而 是在探讨程序内涵如何包容法治的全部价值。至此,程序主义在中国本土化时已经完全 丧失了自己原始的语境和话语权,它被塞进许许多多“陌生的”的东西。
人权语境下的程序与法治语境下的程序,它们的侧重点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尽管人们 对法治的理解颇多争议,但是,“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 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 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 人事物。”(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7年版,第73页。)也就是说,法治首先表现为规则的普遍性,即形式性。法治并 不必然带来正义,法治可能专注于自己的形式性和工具理性价值,反而因此压制了人权 ,掩盖了正义的本来面目。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的概念,即有规则地和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在适用法 律时,就成为法治。”(注: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 出版社1996年版,第620页。此文的译法与何包钢的译法有很大的差异。何文是:“形 式正义的观念和有规则的、公平的行政管理的公共规则被运用到法律制度时,它们就成 为法律规则。”参见[美]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8节,第225页。)法治主义和程序主义有相同的一面, 都强调秩序、普遍性、稳定性与逻辑一致性,即强调形式合理性,将所有的人都视为无 差别的、中立性的“客体”。黑格尔对司法程序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他认为“法律程 序使当事人有机会主张他们的证据方法和法律理由,并使法官得以洞悉案情。这些步骤 本身就是权利。”但由于程序权利“步骤分裂”、“零星”且“无一定界限”,“原来 是一种手段的法律程序,就成为某种外部东西而与它的目的相背。当事人有权从头至尾 穷历这些繁琐的手续,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种形式主义也可能变成恶事,甚至 于成为制造不法的工具。”(注:[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页。)
“形式法治决不能等同于程序法制建设。”(注:姚建宗:《法治的多重视界》,《法 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1期,第11页。)我认为,迄今为止,西方程序主义经历了三个 发展阶段:压制型法的程序、自治型法的程序和回应型法的程序。季卫东先生虽然没有 论述自治型法的程序与回应型法的程序有何不同,但他极富意义地指出:诺内特和塞尔 兹尼克主要从形式主义的侧面来理解程序,从而把程序性规则视为次要规则,“其实, 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程序体系还原为形式范畴,程序正义也并不等同于形式正义。调整 价值纠纷需要论证规则,其基础只能是程序性安排……。”(注:[美]诺内特、塞尔兹 尼克著,张志铭译:《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季卫东 代译序,第10-11页。)在“自治型法的程序”阶段,程序主义强调规则的普遍性和形式 主义,程序被简单地视为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性和工具性规范。在“回应型法的程序 ”阶段,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对法治主义产生了冲击,规则的形式主义、法治的普遍性 和自治性遭到侵蚀,程序主义转而强调目的性法律推理和论证方法形成公共决策的重要 性。
四、从民主视角诠释程序
如前所述,法治化的程序可以是非人道的,并不必然带来正义和“好结果效能”。在 本质上,程序不是使主体客体化的流水线,相反,程序是参加者角色互动、意见对话与 整合的场所,程序不能被扭曲为“走过场”。程序主义的基本要件是参加和论证话语的 交往和沟通,现代程序已经逾越了纯粹形式主义和仪式性特征阶段,转向开放性、角色 参与性、对话性和论证性阶段。参与性、透明性、话语论证性、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理解的一致性)已经构成程序的基本范畴。程序理性受沟通伦 理指引,认为法律规范只有在论证话语中得到相关者的合作与赞同才能获得有效性。( 注: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实际上,程序既吸纳了民主和人权的价值( 主体性),又吸纳了法治的价值(形式性和工具性),既是一个统合了民主和法治价值的 独立范畴,也是一种兼备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实践理性、反思理性,无论法律程序本 身的合法性还是程序交换内容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受约束者的同意和认可。中国主流的法 律程序观念正滑向极端形式主义,把人置于客体化背景之下。我们不仅要从法治角度理 解程序,而且必须从主体性、契约共识性和民主性角度来理解程序。以法治主义全部吸 纳程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法治和程序的误读。
“民主”并非政治哲学独霸的范畴和话语结构,在集合体的日常伦理中,“民主”就 是自己做主,个人是集合体的主宰。民主视角的程序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程序的控制 权process control”(注: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 98年版,序言,第17页。)的归属和分配,程序价值的首要内容是“参与性统治(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注: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 程序价值”理论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98)第1卷第1辑,第187页。)程序的民主 性是通过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程序对话和参与机制表达出来的。
(一)司法过程的“参加命题”
程序正义的一个基本要件是“参加命题”。“参加命题”是富勒提出的概念,谷口安 平在反思程序正义时,强调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程序的趋势和重要意义。他认为:“ 在实体的正义被相对化、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当代社会中,以利害关系人的 参加和程序保障为中心内容的程序正义观念在其固有的重要意义基础上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程序的理由。”(注:[日]古口安平著,王亚新、 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2页。)恰当 的告知和意见听取是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要求。日本民事诉讼的“第三 波理论”强调把“对当事者主体性、自律性的尊重置于优先地位的角度”,(注:[日] 古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版,第17页。)要求重新考察法官介入程度与人们正义实现之间的关系。英美法的社会 学研究表明:“人们对程序的控制权越大,人们对这一程序所引导的结果的接受程度就 越高。”古口安平也发现:“在日本,当事人的‘参与’程度与案件的接受程度也成正 比。但是,日本人的‘参与’不像美国人所要求的那样是‘对抗性’的,而是‘被动的 ’,也即当事人有机会观察整个过程则心满意足了。”(注:宋冰编:《程序、正义与 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代译序,第17页。)司法过程的“参加命题 ”直指法院实现正义的方式,即法官家长式的纠问制与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哪一个更 能导致司法公正。黑格尔将司法权列入市民社会范畴之中,他也思索过现代人正在遭遇 的难题——“应在如何程度上责成作为正式法律机关的法院对事实问题和对法律问题作 出判断”,在评价陪审法院的功能时,黑格尔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事实构成 只能单独由专职法官来认定,因为这是每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而不只是 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事。”(注:[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 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5页。)
当事人的司法过程“参与命题”主张两种价值目标。第一种价值目标与事实的真理性 相关。当事人和法官通过透明和可视性的程序结构,就各自主张和证据进行认真的对话 和信息博弈,可以逐渐获致问题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法官对于摆在他面前的这桩案子 而言,仅是一个陌生人,当事人最了解案情。当事人的参与能使法官的决定比当事人不 参与‘更’正确。”(注: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 8年版,第373页。)“被听取的机会”作为程序主义的最基本要义,也正迎合了“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中国古律。第二种价值目标与当事 人的主体性相关。当事人对司法决定的承认和服从,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程序能否反映当 事人的道德主体性。法律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参与司法决定过程会使当事人感觉 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而且直接参加与间接参加(代理制度)的效果也不一样。法官过 多介入程序,实际上把当事人边缘化了,剥夺了他固有的主体感。但是,弱者也许并不 希望自己做主,宁愿法官过多地干预案件以主持公道,强者可能更希望通过律师来主持 公道。
(二)行政程序的听证过程
现代行政程序趋向于采纳司法程序,行政程序是准司法性质的,集中表现为行政立法 的参与和协商机制、行政决定程序的说明理由和听证制度。中国行政法正在转型,行政 程序立法也被提上日程。但是,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定位不能不令人充满忧虑:大 多数学者仍然津津乐道于正当过程或者正当法律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对参与原则的探讨 尤显不足,行政法治实践亦未真正普遍推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制度。参与是实现程序正 义和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行政法的激励机制迫切需要的是经过理论改造后的正当程序 ,即对话性的理性过程。(注: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6 -527页。)而且,行政程序的私人参加是不以实体权利为存在前提的具有独立的法价值 之物。在现代议会民主“形骸化”之后,只有参加程序才会使行政民主获得正当性。( 注:朱芒:《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日本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及其启示》,《外国 法译评》1997年第1期。)由于听证程序的切入,中国行政程序法的范式也发生了变化: 从法治视角转向民主视角,从客体化的主体返回真实性的主体。听证机制不但改变了传 统行政决策模式而且确立了新的公正和正义识别标准,即正义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意 见交涉和规则共识。法治原则也不再是行政法的唯一主导原则,在行政决策中“可接受 性原则”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注:于立深、周丽:《论行政法的可接受性原则》,《 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2期。)
(三)民主政治的程序理论
民主政治是以程序正义为基础的,强调参与性统治、充分讨论和多数表决。无论选举 程序、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行政程序还是纳税程序,都可以从当事人的主体性和主体 意识角度加以解释。在民主社会,“参与性统治”是法律程序的首要价值,它既可以确 保公民不同程度地进行自主性的自决,也可以使程序本身获得正统性以及“更可能产生 好的边际效果和附带效果。”(注: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 序价值”理论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98)第1卷第1辑,第187-194页。)事实上, 西方程序主义一直重复着一个相同的主题:程序可以推动思想竞争并因此使结论获得广 泛接受。譬如,卢曼认为程序“不但有利于决定的形成,而且同时也有利于对反对意见 的吸收。”(注:[德]赫费著,庞学铨、李张林译:《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 判哲学之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泰勒认为:“一个民主政府在 进行决策之前与各社团进行商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为了选定最受欢迎的政策 ,也是为了缓和与那些受损失者之间的磨擦,因为这些受损者至少会认为,他们的意见 曾被且将会再被政府听取。”(注:[英]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编:《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安守廉认为:“立法性听证, 行政性通报和评议,它们旨在推进思想和意见市场上的竞争,而由此产生出来的法律和 法规将规制我们各种产品和服务市场。这样做既为推动市场制定良法,又通过鼓励那些 其观点没有被采纳的人们去尊重根据已采纳的意见制定的法规,来加强人们对市场经济 的信任。这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已经在相关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并 且仍将在将来得到公正的对待。”(注:[美]安守廉著,唐应茂等译:《论法律程序在 美国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第126页。)
民主政治程序理论的典型代表当属哈贝马斯和考夫曼。哈贝马斯高举批判与解放大旗 ,推崇程序理性,他的程序在两个视角(哲学和法学)和两个层次上(思维和制度)相继展 开:
1.话语论证程序,即思维程序(认识程序)。哈贝马斯独创了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 ),(注:哈贝马斯的众多哲学术语转译成中文时,字面含义已经相当混乱。
Diskursethik(英文是Discourse)已有中文译法包括:话语伦理学、言语行为理论、讨 论理论、对话理论、论辩理论、辨谈原则和商谈理论。本文在使用Diskursethik一词时 ,交叉使用了上述不同的中文译法。)主张超越传统哲学的主体—客体图式,认为可以 从纯形式(程序—话语形式规则)中获得内容,真理得自于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或者 同意。按照沟通(交往)哲学的逻辑,交往是任何存在的基本方式,交往的具体表现就是 对话(Discourse),对话是在已在与未在之间的不断转换。交往理性要求主体以语言为 中介,进入互动状态。在理想的对话情境下,“所有论辩参与者机会均等、言论自由、 没有特权、真诚、不受强迫。”(注:[德]考夫曼著,米健译:《后现代法哲学》,法 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 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对话不限于一问一答,它是两个以 上的对话伙伴之间进行的一种交谈,通过质疑、指令和否定的话语方式,谈话各方共同 致力于意义制造。“互动性的对话是一个建立共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每个人在冲突当中 寻找自我肯定的语言途径的过程,包含着主观成分。”(注:[法]海然热著,张祖建译 :《语言人》,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0页。)“程序主义的话语伦理学”立足于程序 理性,“论证的程序让参与者自己去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注:章国锋:《关于一 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 01年版,第153页。)
2.制度性程序,即决策程序和法律程序。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公正程序由三部分构成: 话语论证的程序、决策程序和法律程序。话语伦理学被运用到法律领域,核心原则是: “只有得到作为理性话语参与者的所有相关赞同的行为规范,才可要求有效性。”(注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即任何法律规范和决定的有效性必须通过充分 的话语论证,得到民主程序的普遍共识。
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的程序理论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交往)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为中心 的。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程序理论主要有两种模式:契约模式(Vertragsmodell)和论 辩模式(Diskursmodell)。契约模式由美国法哲学家罗尔斯代表,论辩模式由德国哲学 家哈贝马斯代表,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合意被视为关键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标准 。”(注:[德]考夫曼著,米健译:《后现代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
哈贝马斯的程序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和全然的“乌托邦主义”。以民主的视角观察,话 语论证的思维程序,当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A Fireside Chat)最为典型 ,藉此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独特的说话方式、治国理念和社会契约情结。在微观层面上 ,形式意义上的对话所展现的辩证推理方法,最早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采用,“辩证法 ”在希腊语中意为“谈话”或“对话”,这种发现真理的对话艺术被罗马法学家转化为 判决技艺,影响了近代欧洲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注:[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 《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7页。)哈贝马斯的真理合 意理论和程序性论证原则,也是“议论法学”的组成部分,由此揭示了西方法律解释的 真谛。(注:季卫东:《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民主政治的制度程序则体现为“论坛国家”模式,英国学者芬纳认为,政府有四个类 型,继“贵族政体”、“教会政体”、“宫廷政体”之后,人类社会20世纪后期主要的 政体形式是“论坛政体”,“论坛政体的主要原则是可解释性,即进行劝说,而不是强 制实施它的主要措施。”(注:[英]《经济学家》(Economist)周刊:《世界是如何被统 治的——评芬纳<政府发展通史>》,鹰子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 4期,第55页。)如果权力拥有者乐于以使他们看来有权的方法去思考问题,未必能增加 他们的效益。(注:[美]麦克尼尔著,雷喜宁、潘勤译:《新社会契约论》,法律出版 社1994年版,第126页。)
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有效地解释了民主的立法程序、公正的司法程序和后民族主义国 家的构成。他认为:
现代法律的巨大教化成就恰恰表现在,它规定策略性行为领域(如为了获取个人财富或 政治权力而实施的行为)必须以共识的方式得到规范,即涉及这类行为的规范必须得到 所有国家公民的预先赞同。这不但适用于市场体制调节的私法实践,而且也适用于党派 竞争或政治权力行使的公法限制。法律规范只有在制定这些规范的程序被认为是合法的 而得到广泛承认时,才能始终具有强制的有效性。而交往行为的重要作用便体现在这种 承认之中:它在法律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即在民主意志的形成和政治立法的层面显现出 来。(注:[德]哈贝马斯、哈勒著,章国锋译:《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 贝马斯对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陈弘毅先生进一步揭示了哈贝马斯的程序理论,认为: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体系“需要 透过公共讨论和对话来阐释和塑造,权利体系的内容不是不证自明、一成不变的。”“ 权利体系中一个核心权利便是平等参与导致民意、公意和法律形成的公共讨论和对话的 权利。”“他们都是在解释、塑造和阐明那个同时体证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权利体系 。”(注: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51页。)法律(立法)和司法裁决的正当性、有效性取决于它们的程序是否是对话、商 谈或沟通性的。在立法过程(规范的证成)中,“每位参与者都是规范的‘作者’——他 们都平等地参与规范的创造,而他们之所以收到最后被创造出来的规范的约束,正是由 于他们是规范的作者,规范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在这种对话中,每位参与者想象自己是 有关规范的约束‘对象’(addressee),它们不但从自己的角度想象规范的适用性,也 要从他人的角度看同一问题,把自己代入他人的位置,所以参与者的位置的互换性是关 于规范的证成的对话的基本原则。”(注: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为什么说司法过程也是一个对话过程呢?原因 在于,法官只是适用法律,这种法律是所有诉讼主体的立法过程中已经同意了的规范。 在民主政治领域,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正被他用来建构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欧洲民主社会 :欧洲宪政化需要“制度话语过程和制度决策过程与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过程(依靠的是 大众传媒)在公共交往层面上的相互作用。”(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欧洲 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读书》2002年第5期,第89页。)
五、从经济视角诠释程序
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政治、道德、经济或者法律角度加以思考。政治思维重 在利与弊的权衡,道德思维重在善与恶的评价,法律思维着眼于合法性分析,经济思维 注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注: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6页。)西方功利主义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对程序的观察, 都是以经济效益作为分析线索的。公正和效率作为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它们 之间既可以是正相的兼容关系,也可以是负相的相斥关系。法律程序能否兼备公正与效 率的价值,取决于程序设计在多大程度上是价值中立的,多大程度上是与实体权利的重 要程度相关的。(注:程序正义的最常见隐喻莫过于罗尔斯的“切蛋糕”,但是,中国 经济学者观察到的东西方人“打篮球”的不同习惯规则,更有助于说明程序在公平与效 率之间的作用。参见张宇燕:《打篮球》,《读书》2000年第5期,第91-92页。)
在正相关意义上讲,良好而有实效的法律程序可以实现三种经济价值目标:
降低社会安全成本。和平性是程序固有的一项品质,它以秩序理性为价值目标,可以 避免暴力和革命性的公开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当民主作为一种实体性权利时,宪政程序 和法律程序可以通过合理的角色分配和组织关系来保障民主以最小成本的方式得以实现 。民主程序包括选举程序、表达自由程序、立法程序以及司法主导的权利救济程序。在 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里,民主的涵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亨廷顿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注:刘军宁:《民主与 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9页。)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带给人 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是:实体性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必须通过程序性的民主权利加以落实和 保障,这样做既可以消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安全成本,又可以最大化的优化人力资源 和物力资源。
降低社会经济成本。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体系有两大经济目标:一是减少决策的错 误成本,二是减少程序体系运行的直接成本,听取意见的程序(听证会)可以预期地降低 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从而增进效率。(注:[美]柏士纳著,唐豫民译:《法律之经济 分析》,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7-398页。)无论司法程序、行政程序还是立法 程序,都可能因为程序正义而降低决策成本、运行成本和外在成本。
降低个人成本。程序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它以规则普遍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程序缘起 于人类的基本矛盾:有序和无序、自治和他治是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现象。程序就像一 个承上启下的活塞儿,对不同主体的不同欲望和价值观进行梳理和整合,由此不仅产生 秩序而且产生公正和效率,为主体带来合理预期,从而提高个人的生活效率,降低生活 成本。
在负相关意义上讲,法律程序也可能与效率目标背道而驰,原因在于:
所设计的程序缺乏科学性。程序必须具备客观性品质,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立 性的技术性规则,只有信息充分、决策过程反复博弈,才可能制定出高效率的程序规则 。
所设计的程序缺乏民主性。开放性也是程序的内在品质,现代法律程序已经开始修正 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图式,尝试通过利害关系人的 参加程序来弥补公共决策和决策执行的割裂关系。屡屡被规避的法律肯定是低效率的。
所设计的程序过分关注人性价值目标。程序正义不否认程序本身的客观性、中立性, 但是,人权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相对繁琐的程序规则,程序经常在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 目标上发生冲突。例如,“辩诉交易”明显背离程序正义目标,这是由抗辩式诉讼程序 缓慢且花费昂贵现象造成的,若不采用“辨诉交易”,美国的刑事审判就会陷于瘫痪。 (注:[美]埃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 80页。)任何程序都面临着资源有限性问题——时间、金钱、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 程序效率低下同样也会影响公正,“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注:宋冰编:《 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简易程序也是一种 程序选择,它既可能带来效率,也可能带来公正。
总之,理解程序需要全面的观察视角。法律程序理论的崛起至少带给我们两个认识变 化:
一是对权利性质认识的变化。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误读,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我们 有关权利的思维是分裂性的。权利本是连贯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好比一条绳索,一头 拴着实体法,一头拴着程序法。程序不仅使价值化的权利(法律文本上的权利)最终走向 实证化的权利(程序过程的权利),而且使实体权利相对化,实体法只是权利的开始,程 序法才是权利的结束。
二是对程序地位认识的变化。程序有其内在的、独立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一种制度性 伦理,既不可以从个体伦理视角加以否认,也不可以从实体——程序二分视角加以否定 。我们不仅要从正相关角度判断实体与程序的关系,而且要从负相关角度判断二者的真 实关系。程序本位主义也潜藏着危险性,即实体权利可能被虚拟化,程序权利可能分割 实体权利的完整性和客观性,程序正义是相对的。因此,要倡导健康的程序观念:“既 应当准确认识程序的必要性或优点,又应该看到程序的不足,并对程序弊端予以宽容对 待。”(注: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怎样给行政行为设计正当的程序 》,《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