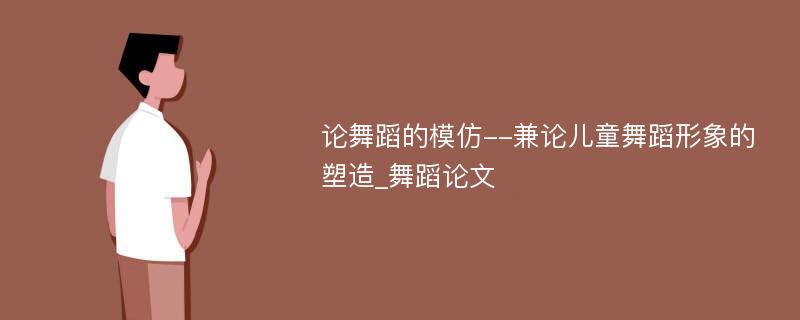
论舞蹈的摹拟性——兼谈儿童舞形象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形象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On Dance's Imitation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艺术,大体上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例如绘画、雕塑、戏剧、小说……属于再现艺术,再现艺术主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像绘画艺术,它的对象是一些客观事物,对这些有形的物体,画家通过颜料,可以在平面上再现得惟妙惟肖,达到一种虚拟的立体,使观者在视觉上产生逼真的效果。任何一幅好的绘画作品,都能体现着“形”与“神”的完美统一,做到神形皆备。
表现艺术有音乐、舞蹈……,它们主要抒发内心的情感。如果说音乐、舞蹈在再现有形物体方面远不如绘画,那么在表现内在思想感情方面,绘画则难望其项背了。
绘画、雕刻、戏剧、小说、工艺、建筑、音乐、舞蹈、电影……虽然分属于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但每一种艺术都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表现与再现的统一,只不过不同门类的艺术偏重不同而已,再现艺术中以再现为主,表现属于次要地位;表现艺术中则表现成份多些,再现次之。
音乐、舞蹈区别于绘画等其它艺术,就在于它们在客观生活中没有现存的摹拟对象,而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动态总以一定生活中的人或事为蓝本,“以墨形天地万物”,再现的成份多些。而舞蹈动作却不尽然,它不只是机械的节奏、动律,连造型也没有现存的蓝本可以参照、模仿。音乐、舞蹈艺术的存在不仅是摹拟现实生活,更主要的是通过连绵不断的声音动作,在表达主体感受的同时,给欣赏者以一定的审美情趣。因此,“情”就成了音乐、舞蹈的主流。
中国的三大抒情艺术——诗、乐、舞可谓三位一体。汉代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话的意思是说诗歌是由情志所表达的,蕴蓄在心中是人的情志,表达出来就成为诗,当人们的内心产生了某种思想感情,就要用语言来表达;当语言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就要咏叹,当咏叹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就要放声歌唱;当歌唱仍不足以充分表达内心情感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可是,当人的情感不能以诗、歌来表达时,而舞蹈则是最恰当、最充分的宣泄。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说舞》中阐述:“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是节奏的动,或更准确点,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所以它是生命机能的表演……它是真正全体生命机能的总动员……”(闻一多:《说舞》《闻一多选集》第一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们无论从汉代人的解释中,还是闻一多先生的阐述中,都不难领会到三个基本要点:第一,表现艺术的产生都是情感所至,有感而发,所谓“情动于中”,而舞蹈则表现得“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舞蹈动作的美总要带着饱满的情绪而表现出来,无论是舞者,还是观者,更多地受情绪的感染而从中得到满足,这也是舞蹈艺术的特征之一——抒情性;第二,舞蹈是时间的节奏艺术,具体地说,是有意识地在时空中美化自己节律,以流动、持续的形体来表达情绪的起伏,无论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还是“舞便是节奏的动”,都是如此,这就是舞蹈的第二个特点——节奏性;第三,舞蹈是动态艺术,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而“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是节奏的动”。动作性是舞蹈的第三个特点。
舞蹈动作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程式化和摹拟化两种。程式化主要的是一种抽象化,其舞蹈动作并不根据任何自然的原型,在生活中找不到所依据的蓝本。程式化、抽象化是舞蹈的主流,但是,舞蹈并不排斥摹拟化,作为表现艺术的舞蹈,由于侧重点不同,表现中也可以存在着再现的成份,这种再现就是摹拟。本文着重探讨舞蹈中的摹拟性。
摹拟化舞蹈古已有之,在原始社会最为突出,原始人类首先摹仿大自然中的鸟兽情态,因为这些鸟兽与人们朝夕相处,是人类最熟悉的,因此,摹拟也非常逼真。澳洲的摹拟性舞蹈有蛇舞、袋鼠舞、野狗舞、青蛙舞、蝴蝶舞;北美印第安人有水熊舞、水牛舞;巴西印第安人有鱼舞、蝙蝠舞;印度有象舞……舞者通常是青年男子,裸着上半身或裸体,有时候很古怪地穿着动物皮做的裤子,或是海豹皮或是鹿皮,头上戴着羽毛,着颜色的布,他们表演种种摹拟野兽的滑稽形状,动作是由击响鼓唱歌曲伴奏的,这种摹拟舞的逼真程度,往往成为儿童成长的早期教育。儿童在舞蹈中学会了怎样抓青蛙,用工具捕鱼,怎样打猎……曼台曾经说,看了这些舞者的跳跃竞争就会觉得不能再有比这更神妙更成功的摹拟。埃尔看了维多利亚湖上的袋鼠舞之后说:“他们表演得这样令人叹美,如果在欧洲剧场里演出,定然彩声雷动。”(〈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摹拟实在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摹拟舞蹈也丰富多彩,在原始社会,人们狩猎、采摘果子、打磨石器等劳动实践,使他们的舞蹈内容与大自然极为贴近,所谓“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这正是人们狩猎生活的生动摹拟。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墓地发掘了一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陶盆,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不但创造了自娱性的群舞形式,而且舞蹈性质是摹拟式的,陶盆上的舞人,身后都拖了一个小尾巴,这大概是扮鸟兽的装束吧!
中国古代的摹拟舞,除摹拟鸟兽等以外,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如表示战阵生活的舞蹈,《刑天氏之乐》,又如反映宗教活动的祭祀舞蹈《大夏》,舞者摹拟劳动者的装束,头戴皮帽,上半身裸露,下半身穿素白裙,通过摹拟治水的劳动动作,用比较朴实的舞蹈语汇,歌颂禹为民治水的功绩,以及先民们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敢顽强精神。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舞蹈的摹拟内容更为丰富,白居易《西凉伎》中相当生动真实地描写了《狮子舞》诗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从诗中我们了解到人们披着缀毛的假狮皮,用木头刻成狮子的头的形状,用丝线做成尾巴,在眼睛上涂上金粉,牙齿上涂上银粉,表演狮子俯仰驯狎的各种情态。
清代还有许多描写儿童摹拟舞的诗篇,如《松风阁诗抄》:“太平鼓,声咚咚,白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环中,广场骈集四方客,曼衍鱼龙闹元夕,姹女弄竿竿百尺,惊鸿宛转凌风翼,今夜金吾铁锁开,铜街踏月人不归。”这里描写了广场上孩子们在咚咚的太平鼓声中,跳绳游戏,鱼龙曼衍(各种拟兽舞)百戏杂陈,踏月游玩的人群留连忘返的情景。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朝鲜族、瑶族、傣族等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舞蹈《灯舞》、《盅碗舞》,藏族的《锅庄舞》,其中许多舞蹈动作是摹拟动物的形状的,如“猛虎下山”“雄鹰盘旋”“孔雀开屏”“野兽戏耍”等,苗族的《镕鹆舞》,傣族的《孔雀舞》,壮族的《扁担舞》,高山族的《杵舞》等,哈萨克族的《虎舞》、《熊舞》、《马舞》,这些舞蹈或摹拟鸟兽跳跃,或摹拟生活动作,例如云南彝族人民中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形式《烟盒舞》,又名三步弦,舞者摹拟先民,在没有弓箭之前,披着兽皮,学着野兽动作,悄悄接近兽群,然后出其不意地捕捉它们。这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舞蹈的再现性。
随意舞蹈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舞蹈术语特别是戏曲舞蹈和武术术语也代代相传,其中不乏以摹拟动物情态来命名的,如打鸳鸯场、雁翘儿、龟背儿、双飞燕、大鹏展翅、虎跳、扑虎、乌龙搅柱、商羊腿、蝎子步、金鸡独立、鹞子翻身、白蛇吐信……
摹拟动作在远古时期是直接再现生活的,人们在摹拟的冲动中得到满足。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舞蹈中的摹仿因素逐渐淡化,但是,这种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特别在儿童世界中仍然得到充分的表现。
在儿童的艺术天地里,可说是摹拟舞一统天下,儿童们在舞蹈中喜欢摹拟世界上一切可摹拟的东西,例如摹拟吃饭、穿衣、洗澡、荡秋千、打乒乓等生活动作,或摹拟擦桌子、洗手绢、开火车、摘果子等劳动动作;或摹拟小鸟儿、小企鹅、小鸭子小树、小花等鸟兽草木;或摹拟弹钢琴、吹笛子、打鼓等演奏动作;或摹拟机器人、火箭等,真是花样繁多,五彩缤纷。如上海小荧星艺术团的编导胡蕴琪创编的《劳动最光荣》,通过一群孩子利用休息日来到军属奶奶家帮助打扫卫生,表现孩子们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的好品德,在舞蹈中孩子们穿着劳动背带裤,有的扛着拖把、拎着水桶,有的拿着扫把,有的拿着抹布到军属老奶奶家劳动,有的孩子扫地,有的擦窗,有的抹桌子,这些摹拟生活的劳动动作结合霹雳舞风格,新颖、恰当而具有现代化气息,其中一个小淘气戴上老奶奶的黑边老花眼镜,摹仿老奶奶的动作,那惟妙惟肖的动作,使其他孩子认为老奶奶真的来了,都躲了起来,一个小小的“恶作剧”把孩子的童心充分地表现出来,并把舞蹈推向高潮,观众无不被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的表演所深深地打动。平凡的劳动动作,经过艺术的夸张和美化,孩子的表演使舞者和观众都沉醉其间。
另一位舞蹈编导郭子徽创编的《小小变奏曲》寓意更深刻,舞蹈内容直接反映当前存在于孩子中的现实问题。孩子的家长望子成龙,不顾孩子的喜好,强迫孩子弹钢琴,而孩子却愿意成为一个羽毛球运动员,为国争光。舞蹈首先从孩子弹钢琴开始,编导的钢琴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他让七个孩子穿上黑白两种不同裤腿的紧身衣,七个孩子成为钢琴上C、D、E、F、G、A、B七个键,当孩子们平躺在舞台上,一条腿弯曲,成九十度时,就成了黑键,白色裤腿的脚伸平,则成了白键,观众无不为此设计拍案叫绝,舞蹈的第二部分,是孩子偷着练习打羽毛球,摹拟动作结合高技巧动作,这时孩子梦想着自己夺得冠军,为国争光时,舞台天幕上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孩子站在领奖台上激动万分,“七个钢琴键”送上了鲜花,为他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戴上了冠军的奖牌,围着他载歌载舞。
孩子们对这些摹拟动作做得如此逼真而自然,并带着激情,我们不禁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成人世界可以熟视无睹的事物,儿童却在摹拟的天地里乐此不疲呢?那么,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
儿童的大脑发育较快,兴奋过程强于抑制过程,他们好动,好摹仿,充满童情稚气。他们对五彩缤纷的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对什么都要跃跃欲试,好奇使他们产生摹仿的愿望,并付诸行动。儿童在不断的好奇和摹仿中体验生活、认识世界,如果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儿童的摹拟在好奇的作用下会发出熠熠的光辉。
儿童的好动是一种天性,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成人所羡慕的蓬勃的生命力,这就如种子欲破土而出般顽强。好动使他们对摹拟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精力充沛,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摹拟舞正适应了他们的身心特点,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是节奏的动……”儿童在动中体现着活力,体现着蓬勃的生命的机能。儿童舞蹈的绝大多数都是节奏欢快,就像舞蹈《泥娃娃》一样,孩子们玩着泥巴,捏着泥人,一会儿泥娃娃活了,摹拟着木偶动作,屈臂,走路一步一顿,显得僵硬、机械,充满了童趣,孩子们进一步生发幻想,用泥巴捏出一个个机器人,用舞台干冰创造了云雾弥漫的太空场景,机器人带着他们到太空遨游,那缓慢的太空步,如身临其境,充满动感。这种富有幻想性的摹拟舞,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上海普陀区少年宫的舞蹈《唐老鸭扭秧歌》就受到中外观众的一致好评,鸭子的形象是儿童喜闻乐见的,鸭子胖胖的身体,肥肥的翘屁股,摇摇摆摆的走路姿态和儿童有着相似之处,要儿童摹拟鸭子的形象,可谓适得其所,稍加学习,便能驾轻就熟,唐老鸭的基本形象是两腿弯曲,半蹲,两手臂屈肘压腕于腰侧,翘臀并用钟摆步,使其形象显得憨厚而又可爱,舞蹈还摹拟唐老鸭喝水后高兴的动作,一腿单跪,另一腿膝盖伸直,蹦脚背点地,一手压腕,屈肘于腰侧,一手用指并拢,虎口分开,手背向上,齐头屈肘于右斜方,摹拟鸭头,喝完水后鸭头前后伸缩。此外,唐老鸭扭秧歌的动作,是舞蹈中最频繁出现的动作,扭秧歌的动作要求双手横八字摆动,由于儿童手短,改为两臂前后摆动,但收到了成人秧歌舞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虽然说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成人的教育和儿童的摹仿,但是,儿童对成长的行为的摹仿是能动的再造,而不是机械的描摹,他们还融进了主体的想象,进行改进,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夸张变形;二、简约反复。儿童想象分为无意想象和再造想象,这种想象多与现实不完全一致,儿童们是用自己的心灵来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
我们创编儿童舞,特别是情节舞,有时会碰到一些小小的麻烦。例如要表现一群孩子听故事,捉螃蟹,点鞭炮等舞蹈中的一些类似散板性段落时,成人往往不能夸张而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即使煞费苦心地“经营”结果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从成人的眼中所看到的事物,与儿童眼中的事物是有差别的,因此儿童摹拟性的舞蹈动作如果一味按照成人的编排,儿童跳舞时会显得呆板而无生气。因此我们用启发性的语言,充分利用儿童的再造想象,让孩子们来处理,编导只要稍加整理和调度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斗蟋蟀》的编舞可算是聪明的了。舞蹈中有个小情节,一只蟋蟀跳进了一个孩子衣服里后,需要一段找、摸、逮蟋蟀的情景,首先是蟋蟀不见了,孩子们满地找蟋蟀,当蟋蟀跳到一个孩子身后时,按照常人的编法是转身,下蹲,双手会合拢,扑蟋蟀,但是这个孩子却是两腿分开,直立,双手撑地,从裤裆中把头探出,那高高翘起的屁股,夸张的动作,在舞蹈中是如此真实而富有情趣,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当我们讨论了摹拟在古今中外的舞蹈、特别是儿童舞蹈中的重要性以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舞蹈的摹拟不是机械地摹仿生活,它必须服从一定的动律、节奏,并具有艺术性。这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埃尔在《澳洲人跳舞记》中写道:“看到他的拍子如何严正不苟以及舞者的动作和音乐的抑扬如何精确一致,实足令人惊叹。”同时,我们从朱立人所译《勒布丛书·疏善选集》(英文版)第五卷中,也看到人们是如何评价一位好的演员的:“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有正确的节奏,美丽、均匀、和谐、统一……最主要的是表现感情要富有人性。”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舞蹈演员应具备的三个条件——节奏、动律、表情,这就是舞蹈的三要素。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不论是程式化、抽象化的舞蹈,还是摹拟化、再现性的舞蹈,都必须体现这一点。
我们舞蹈工作者在创编摹拟舞,特别是儿童摹拟舞的时候,一定要使摹拟动作和程式节律统一起来,使生活的具象和艺术的抽象统一起来,把具体的摹拟动作融化在时间的动律之中,融化在时间的动律之中,融化在流动的节奏之中,这样,才能使舞蹈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