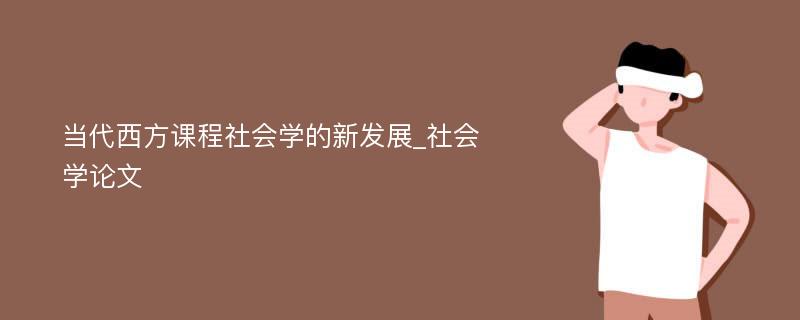
当代西方课程社会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新发展论文,当代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1971年,由英国学者扬(M.F.D.Young)主编,伯恩斯坦(B.Bernstein)以及法国学者布迪厄(P.Bourdieu)等人参与编写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Knowledge and Control: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出版,标志着英国以及西方教育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方向,史称“新”教育社会学,即课程社会学研究。尽管80年代以后,“新”教育社会学有偃旗息鼓之势,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回归“正统”的现象,但是,“新”教育社会学的课程研究一直未停止,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得以双向深入开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末,西方课程社会学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得以双向深入开展,并且有整合趋向。
就微观层面而言,教室(课堂)层面上的关于课程的经验性研究得以深入开展。例如,英国教育社会学学会1981年年会的主题是“课程实践的社会学”,会上及会后不少学者提交的论文和后续的研究,都是在微观层次(课堂层面)上所做的经验性探讨,其实证细节的丰富、方法论的出新等都是令人瞩目的。后来的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伯恩斯坦、惠蒂(G.Whitty)等学者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佐证。① 正如哈格里夫斯指出的那样,课程社会学在课堂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即对诸如学科的设置、考试体系的研究,将使我们检视和发展对于课程实践的更加理论化的解释;对此,社会学学者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如在意识形态、霸权、文化资本等概念的创造使用与研究上。哈格里夫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试图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引入教师对情境的定义,将微观与宏观社会学融合在一起,即把社会与课堂上的互动联系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供一种将结构问题与相互作用问题联系起来的框架”。② 他认为,教师“怎样”组织教学,“怎样”评价学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为此,他提出了“复制策略”的概念。所谓复制策略是“根据一套在战术上被人接受并深信不疑的有关教育、儿童和学习的假设”制定出来的,“围绕着复制策略概念制定的模式的实质就是,所有行动者……要按照他们的经历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即教师的教学方式要受到限制,只有当教学方式能够成功地复制(教师曾经)体验过的约束因素时,它才能产生和延续。这就是说,教师具有创造性,但他们受到自己体验过的约束因素的制约。这种约束因素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教育制度的相互矛盾的目标和教育意识形态。这样,哈格里夫斯就以其实证研究确立了由社会的方式建构而成的社会与个别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为久负盛名的学者,伯恩斯坦在长达30年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课程社会学的探讨,其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执着地进行着,业已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综合化的具有“伯氏特色”的课程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欧美诸国同领域的学者,而且也影响了一些非英美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成为激励他们在此领域不断探索的一面“旗帜”。
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伯恩斯坦在微观领域作了新的探讨,取得了新的发展,提出了“教学法实践”(pedagogic practice)的概念。③ 他指出,教学法实践是文化的“中转站”(relay), 有必要从“什么”和“怎样”这两个角度具体考察学校里教学的内容和过程。教学法实践的理论既揭示了一系列的规则——界定知识传递过程的内在逻辑的规则,又探讨了这些规则如何影响被传递的内容,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如何有选择地作用于那些能成功地获取知识的人”。伯恩斯坦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中转站”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因此,他具体和细微地考察了教育知识传递的过程及其中的构架规则,他甚至把这些规则看得很重,“当我提到教学法实践的内在逻辑时,我指的是一套规则,这些规则优先于传递的内容”。他试图通过对这些规则的研究, 探讨蕴涵于其中的社会阶级的前提(social-class assumption)以及它所反映的秩序和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有三个基本的规则决定着教学法实践的内在逻辑:等级制规则(rules of hierachy)、顺序性和速度性规则(rules of sequencing and pacing)、 标准性规则(rules of criteria)。等级制规则规定了传递者(教师)和接受者(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决定了“社会秩序的原则、特征、行为模式的获得方式”;顺序性和速度性规则规定了知识传递的进展顺序和学生希望学习的速度;标准性规则则让学生领悟什么是教育过程中合法的和非法的事情。三种规则又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显性等级制规则下,权力关系是被清晰地规定的,对学生来讲一目了然;而在隐性等级制规则下,传递和接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被传递的策略所隐藏或遮盖”的关系。显性的顺序性和速度性规则的典型例子是课程标准,它清晰地规定了师生“怎样”、“何时”开展教学活动的界限,而当这个规则是隐性时,只有教师知道怎样做;在显性标准性规则下,学生们知道他们被希望怎样做,而在隐性情况下,学生们则有较多的自由去创造他们个人的评价标准,这种情况下,标准性规则是多样的和散漫的,教师承担了“助长员”的角色,而不是传递者的角色。不同的规则与不同的“构架”相配,形成教学法实践的不同模式,主要有显性的、清晰的教学法实践和隐性的、暗含的教学法实践两大模式。
就宏观层面而言,课程改革的研究成为课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突出亮点。扬、阿普尔(M.W.Apple)等人都有突出成果。曾经作为课程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扬在80年代后期一度转向教育的政治学分析,而在90年代又重新回到知识与课程,尤其是课程改革的社会学分析上。他认为,课程形式与内容的选择反映了统治阶层的立场或利益,课程改革实质上就是课程文化资源的配置活动,其背后是权力的运作,社会权力结构对课程知识或资源的选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④ 如在哪些知识最有价值并可能成为课程知识上,他认为,有人认为专门知识最有价值并进入了课程,就是因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掌握着权力,这样一来,知识的客观性就受到了挑战。过去,扬曾经否认过知识的客观性,显然他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因此在后期,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社会现实主义”的知识与课程理论。⑤ 该理论主张,任何知识都是建立在社会网络或共同体之上,但并未否定知识的客观性,而是既承认课程知识的社会历史本质,也承认它们超越其特殊社会起源的客观性。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焦点将是知识的生产和获得公共规则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普尔从7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展开课程社会学研究,集中于“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的探讨。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代表作《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1990年再版)、《教育与权力》(Education and Power)等,对课程改革的本质及在学校中实施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入研究。1992年,他应我国华东师范大学之约,撰写了“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State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Knowledge)一文,发展了他的课程改革理论。
他认为,课程改革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和文化利益的分配活动。课程作为一种事实,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并体现了某些利益,这些利益均是支配群体与从属群体相互之间及其内部不断斗争的结果。⑥ 一般而言,课程知识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利益,由国家进行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对课程进行控制的方式。但是,社会不同群体在改革中,会通过社会运动和社会群体的冲突、妥协及联盟对课程产生影响;课程通常是不一致的,其本身体现了各种矛盾的倾向,即经济与文化上的权力群体与希望课程更能反映自身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普通阶级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研究的阵容、地域、规模以及内容都有所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课程社会学的研究队伍有所壮大,研究地域不断扩展,研究规模逐渐扩大,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深化,跨国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更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人,如美国学者大卫·李·史蒂文森和大卫·贝克(David Lee Stevenson & David P.Baker)等所做的跨国的比较研究都是令人欣喜的成果。史蒂文森和贝克的一项跨国实证研究表明,⑦ 即使是数理学科(如数学),在相同的教科书或相同的课程指导方针下,教育体制不同,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两位学者研究了15种教育体制下的2200堂数学课,结果发现,国家控制的教育体制与省或当地政府控制的教育体制相比,其教师更可能教授相同的内容,并且,所教的内容量一般与教师或学生的性格没有什么关系。这表明,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所选择的内容与教育体制、社会控制具有明显的关系,在集权制下,教师的教学自由度比较低,而在分权制下,自由度则较高。像这样大规模的跨国研究是当今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美国纽约爱德斐大学教育学院学者阿兰·萨多夫尼克(Alan R.Sadovnik)深受伯恩斯坦的影响,在90年代成为在课程社会学研究上颇有名气的学者。他曾编辑过伯恩斯坦的文集,并运用伯氏的教学法实践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不同学校之间以及教育实践中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教学法差异。他的研究基于实地观察和对纽约市区、郊区十几所学校的数百位教师所作的访谈,因此具有很强的实证性。他认为,美国绝大多数课程及教学法的实证研究集中在“结果”而不是“课程和教学法的社会建构”上。对于后者,他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分别为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学生设置的)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学校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以及他们的教学法、课程实践方面,特别是他们的等级制规则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团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特别是在低年级,尽管教学法是显性的,等级制规则却更加隐蔽;团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等级制关系越明显,越显示出权力主义的特征。在中学,团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具有自生的显性教学法;团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有可能具有市场取向的显性教学法。当然,关于采取何种教学法实践,不同教育实践和不同学者之间有争论。阿兰·萨多夫尼克运用伯氏理论考察了伴随着美国自60年代以来20多年的教育改革的历史所产生的教学法实践的变化。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非英美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在课程社会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反映了西方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如澳大利亚学者R.哈克(R.Hacker)就研究了执政党的变化对课程政策的影响。他指出,1983年澳大利亚工党在赢得大选后的一个月里,就成立了西澳大利亚教育咨询委员会,并于1984年出版了研究报告,导致了澳大利亚初中科学课程的显著变化,即把原来作为4个核心课程之一的学科变成含有7个组成部分的课程之一,而且,这一部分被命名为“科学和技术”,包含计算机学科、技术学科、电子学和科学。新课程被称为“单元课程”(unit curriculum),这一变化反映了科学学科平衡发展的要求。⑨
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如智利天主教大学的麦坚索(A.Magendzo)、韩国汉阳大学教育系的车允卿(Yun-Kyung Cha)博士等所做的有关课程编制以及现代外语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就是很有水平的成果。麦坚索在危地马拉的实证研究表明,⑩ 学校和当地社会之间存在着强构架和强分类:在家里,教导或社会化过程、学习社会文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在学校里则是一个强迫学习学校文化的过程;在家里,孩子们承担不同的角色而没有任何的反抗,而在学校里则被强迫适应不习惯的角色;家庭与学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使学生们真正学有所长,课程编制应当有所转向,即从文化变量(cultural variables)入手,再到文化常量(cultural invariants)。套用伯恩斯坦的概念,首先是从局限编码入手(局限编码是在最初的环境如家庭、同辈团体、地方环境中产生的),然后再到精制编码:从集权制到分权制;从文化同质到文化异质。这样,课程编制就必须摒弃“共同文化观”(在麦坚索看来,强调共同文化易于成为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的借口),充分考虑亚文化的贡献,考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
车允卿博士则运用“全球体系”的分析模式对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全球体系结构性的变化对课程中语言学科的涨落情况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11) “全球体系”是当代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的新概念,它以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局势的变化,超越了单个国家的局部分析,以期从整体上动态地把握世界发展的态势。应当说,这样大规模的研究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研究实力,与史蒂文森等人的研究相得益彰。车允卿的研究表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和国际霸权的重新排序对国家教育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外语类型具有重大影响,古典语言学科(拉丁语和希腊语)急速消亡,强调促进国家语言发展的课程和现代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教学迅速增长。
此外,受西方课程社会学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及大陆学者分别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涉足该领域。可以预言,随着21世纪我国课程改革力度的加大,课程社会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果。
另外,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对于课程的探讨拓展了课程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女性主义社会学指责所谓的社会学只不过是“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社会学,女性长期被忽视。女性主义对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挑战在于,社会学必须彻底反省学科的全部内容和方法论,社会学也必须从女性的视角看社会,因为过去的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主,并隐含了男性话语霸权,漠视女性切身的领域和议题,将男性样本的研究推及总体。就课程研究而言,(12) 课程开发已经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基本问题,她们试图通过课程改革来提高女性团体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其研究多集中在课程决策的性别不平等、学科选择的性别偏见、教科书中的性别歧视、课堂互动的性别差异等。这些研究的确为课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新的观察方式及重心、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
三、课程社会学研究上的“制度性区分”正在得到弥合
由于传统课程研究和教育社会学研究存在“制度性区分”,两者对课程的研究视角、内容、方法论、研究技术等都有所区别;而课程社会学研究在传统上属于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势力范围”,未得到正统课程论学者的关注;即使有课程论学者的参与,他们要么是被认定为具有“社会学”特征的学者,如阿普尔(从阿普尔的学习经历、所属机构来看是典型的课程论学者,但被认为和经典的课程专家泰勒等有着重大区别);要么就是偶尔为之,未形成体系。因此,教育社会学和课程论在课程的社会学研究上也存在着“制度性区分”。
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课程论专家也尝试着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课程知识,如英国经典的课程论专家劳顿就曾借鉴社会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来探讨“课程编制模式”、“课程决策”等课题,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味的观点:“课程在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实际上,作为世界学术界公认的“课程论”专家,劳顿在课程设计(编制)上所倡导的“文化分析模式”就很具有社会学意味,这一研究成果已成为英国课程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对欧美诸国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智利的麦坚索以及澳大利亚的一些课程论学者也都试图整合社会学、课程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以期形成新的理论并为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而一些教育社会学学者也注重吸收劳顿的课程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对课程进行实证观察的成果。(13) 实际上,美国学者阿普尔可以被视为弥合这种“制度性区分”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既努力消除传统课程论忽视社会性的“工艺学”研究的局限,又努力避免结构主义简单决定论的狭隘,试图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一套辩证的分析模式。正如阿普尔自己所言:“我们不赞成文化或意识是由经济结构机械地决定的观点。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知觉,从历史和实证两方面来了解文化控制、分配与政治经济阶层化的辩证关系的发展问题……就方法论而言,就是能作相关性和结构性的思考。”(14)
此外,美国权威的《教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Education)、《课程研究杂志》(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在80年代后期都曾刊载过有关课程社会学研究的论文,反映出两大学科在课程研究上的整合趋向。
注释:
① 转引自Whitty,G.,1985,pp.39~52.
② [英]布莱克莱吉等,1989。
③ Sadovnik,A.R.,1991,pp.48~61.
④ Young,M.F.D.,1998.
⑤ 扬,2003,pp.1~5。
⑥ 阿普尔,1992,pp.1~6。
⑦ Stevenson & Baker,1991.
⑧ Sadovnik,A.R.,1991,pp.48~61.
⑨ Hacker,R.,1990,pp.40~45.
⑩ Magendzo,A.,1988,pp.23~33.
(11) Cha,Yun-Kyung,1991,pp.19~31.
(12) Donn,G.,1997.
(13) 转引自Whitty,G.,1985,pp.73~75。
(14) Apple,M.W.,1990,p.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