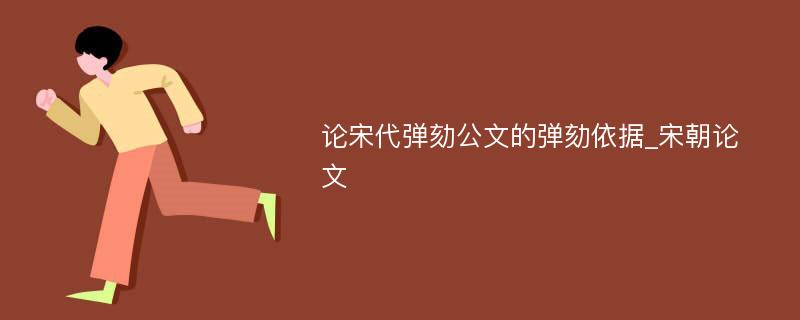
论宋代“弹劾公文”的弹劾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5.2
凡批评缺点,检举他人行为,揭发罪状,或者导致他人最终被定罪的行为称“弹劾”。而承担弹劾职责的文书则统称为“弹劾公文”。宋代的弹劾公文由于写作群体繁杂,个人文法各异,因而文本的个体差异较大,但其弹劾依据依然出现类别化特征,主要与工作、品德、政治等因素有关。
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工作热情
宋代作为封建文明的成熟时期,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生产关系由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赁制转化,经济形态、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微妙变化,各项政治体制也在远承汉唐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开拓,表现之一便是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大力发展。
当然这也与宋太祖个人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在“陈桥兵变”之后便对武将势力心有余悸,同时也看到了文官势力的易于掌控。故在“杯酒释兵权”之后便定下“以儒立国”、“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严格控制武将势力,大力提升文官地位。在官员的选拔中,充分发挥科举的导向性作用,将选官的杠杆向知识分子倾斜,同时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和途径,并创设“糊名”、“誊录”等制度来保证科举取士的公平公正性。大批寒门学士通过科举顺利进入官僚体系,以读书为业的“士”与官僚在宋代完成合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一词从此便成为文人官僚的带义语①。士大夫阶层的突然崛起对原本的贵族势力形成打压之势,并最终成为政坛的中坚力量影响朝政。自此正式宣告了自秦代形成的“皇权——吏员”体制的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可以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宋神宗与枢密使文彦博的一段对话为证,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②
在这种文官体制的确立下,传闻宋太祖又立下“不杀言官”的条令且被历代相袭,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③此碑虽争议颇大,但宋代不轻杀士大夫确实属实。经历过五代腥风血雨的士大夫,突然在宋代被推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宋代士大夫显得格外珍惜这样一种参政资格的获取,政治热情得到空前高涨,从此不再唯皇命是从,反之“以天下为己任”,开始用一种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士大夫们在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中,自觉承担起对封建政权的维护职责,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这样一股参政热情下出现的弹劾公文大都秉着相对客观的依据,从人事角度出发进行监察纠合,凡有出现滥恩过赏、无功受禄、才不服众、败坏纲纪、外戚涉权、影响局势等情况,立即进行积极干预,以此来实践士大夫个人的治国理念。
1.劳浅赏重。皇帝对某臣恩宠过厚,多次行赏或是过快提拔,皆会引起朝廷士风骚动,士大夫屡上章奏加以制止,认为皇恩偏袒过于明显,赏罚皆因适可而止。杨绘在《上神宗论向傅范除知郓州》④340这篇奏折中指出向傅范作为“后族”外戚而以防御使身份兼一路安抚使,属于不次之恩,有违近制。皇帝今日偏袒“后族”,明日“母族”必会仿照今日之例,后日“祖母族”再仿效之,对于皇恩而言,“其源一开,攀援其例者,数十年犹泛滥而不可止矣”。为长久之计,必须“谨其源,塞其例”,向傅范切不可以知郓州。杨绘从长远利益出发,指出恩命偏袒之后出现的各类弊端,论断确实有理。殿中侍御史吕悔的《上仁宗岂罢内臣暗转官例》(嘉祐五年十一月)④476中,“(内臣)或因监督工作一切小劳,便理绩效;得圣旨画下,则超资躐等,谓之暗转。”内臣暗转途径便捷,暗转之后俸禄增倍,甚至“如前班武臣更历外任,及沿边立显功着效者,未有酬赏若是之速也。”皇帝对内臣的偏袒显失公正而显得过于私腻,挫伤文武官员积极性。本着对朝廷纲要负责的态度,必须对这样一种欠合理的“暗转”制度加以修正,将其纳入正常合理的官员升迁体制之内。监察御史裹行傅尧俞《上仁宗论赵继宠不合越次勾当天章阁》④680一文中提到,仁宗念赵继宠久侍淑妃董氏,先已不顾内臣补阙资辈之先后顺序,将延福宫之阙差与继宠,现又使其勾当天章阁,“仍指挥在勾当使臣之上”,恩宠过于隆重乃至不顾旧法。所谓“事不均平,人用嗟怨”,也是为一区区内臣破坏传统,实在有失皇帝英明,台谏大臣对皇帝所作的不合理决策承担起一定的职责,并适时进行劝导和阻止,是其对理想政治环境的维护。
2.无功受禄。相对于滥恩过赏,无功受禄显得更加有失公允难以服众,弹劾时一旦举到这一点,贤明的君王都会迫于士论而收回成命,罢黜所弹纠的官员。杨畋在《上仁宗论李殉刘永年无功除授》④337一奏中,直截了当指出李殉、刘永年“无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实在令大批镇守边疆的将士不服,以后一旦有灭寇立功者更不知再以何官赏之。范镇对此事也有论列,李殉、刘永年最终未能得以除授。吕悔在嘉祐三年十一月的《上仁宗岂罢内臣暗转官例》④676中,同样针对内臣刘保信、王保宁、鄧保寿、王世宁四人以“暗转无名之例”,竟与功臣秦翰恩赏相同。内臣的无功进秩,必然消磨武将斗志而影响叛乱的平定,边关的镇守,如此以私害公对于国家实在没有任何好处可言。宋代士大夫对于宦官势力一直多有提防,除了固有的阶层矛盾因素之外,更多的还是对国家安危的关注。
3.才不服众。在士大夫眼中,官员占其位就应效其忠,尽其职,如果才能不足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必然会给朝政带来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将领的任命中显得尤为重要。钱彦遠《上仁宗论不可令李璋管军》④331中一句“人才懦弱,别无勋劳,委之师旅,未协公议”直逼要害,认为李璋其人既无韬略,又无边防经验,令其管理军队实在让人担忧,不如罢黜其职,以恩礼相代。军队将领的选择不同于其他,必须以能者任之,皇帝要以大局为重,用军衔来表示恩宠实在有百害而无一益。余靖的《上仁宗论狄青不可独挡一路》④721更为典型,“泾原”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故先前由范仲淹、韩琦共同经略,以张亢知渭州,以狄青为一路部署,今却逐步移除其他三人,而已狄青一人兼领三人职权。余靖认为狄青一介武夫,性情“率暴鄙吝,偏裨不伏”,缺乏独挡一路,全领泾原路兵马的能力,才干不足以承担起镇守要塞的职责,需另派奇才与之共事,方可安军民之心。此奏是对狄青能力的质疑,也是士大夫心系边疆安危,积极参奏干预朝政的表现。
4.内侍越职。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历来相互对立,两者矛盾始终无法调和,宋代也不例外。宦官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内廷机构,原本只是侍从机构,除了负责皇帝衣食起居之外,负责一部分文书工作,但由于皇帝的信任往往会委以他职以示恩宠,另一方面也可用来牵制其他势力。但是宦官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对于朝廷大事多缺乏正确的处断能力,史上宦官专权的教训已让士大夫深恶痛疾。鉴于各种原因,一旦出现宦官势力超出职权范围之事,士大夫立马会对其进行激烈地攻击,以规劝皇帝以史为训,防微而杜渐。
侍御史赵瞻的《上英宗论差中官为陕西钤辖》④686即是如此,“招讨”、“经略”、“安抚”、“总管”四路责权重大,历来都选取文武贤明之臣掌其权柄,如今却以内臣王昭明四人各当一路,实在尚无前例。兵权旁落,统帅不安,为此赵瞻多次上奏规劝宋英宗应以唐代为鉴,及早罢黜内臣军衔。权御史中丞孙抃《上仁宗论王守忠不当除节度使》④673一奏中,对于内臣王守中除节度使一事“惊骇未信”,宦官势力侵入军政,已不合常理,还委以如此重任实在让人无法心安。当然,宋代的宦官监军,仅是作为皇帝的亲信起到监察作用,并没有实际控制军队,但是士大夫们对其越职行为如此之敏感,可见提防之重。
5.有违礼法。宋代的政治体制都是在前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是前代经验的积累,加上“尚古”心理的影响,宋人都习惯以先人法制为本位。道统需要遵从,先例不可乱开,一旦出现不符祖宗法制的官员任免,便争议不断。陈襄《上神宗论大臣皆以利进》④497,对于韩绛除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一事,才望上无可争议,但是加上之前的王安石、陈升之,三者领枢密院事都为“兴利之谋”,自此“中书选任大臣皆以利进,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兴利”之事本不足以取,大臣的选任历来更重视道德经术的修养,如今三位大臣通过“兴利”得到升迁,已违祖宗选官之制,如不及时罢免韩绛参知政事一职,恐要侵害王政。且不论陈襄是否具有先进的历史远见,此处确实是其本着维护士风的责任,对原来选官标准的努力维护。何郯的《上仁宗论王守忠预紫宸殿上宴》④670也比较典型,王守忠以“带两使留后”的身份,却依照正宫例在紫宸殿预宴,已破坏尊卑上下之分,加上祖宗典章中不曾有内臣殿上预宴之例。礼法关系着朝廷纲纪,不可以随意破坏,对于这种不可常理之事的积极弹奏是士大夫维持王朝正统的方式之一。谏议大夫范祖禹所作的《上哲宗乞罢韩忠彦政事》④344也是对当朝法典的维护,在韩琦子弟中,韩嘉彦已授驸马都尉,其兄韩忠彦又为左丞相,实为对外戚干政的默许,所谓“非祖宗故事”,法制一坏,祸害匪浅。外戚一直是权力斗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稍有纵容即成蔓延之势,对其及时打压十分重要,并且在士大夫维护皇帝利益的旗帜下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二、以儒家道德为信念的立身准则
自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术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延续千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仁义”、“礼乐”、“孝悌”、“诚信”、“中庸”的价值观念,都对广大仕子的道德标准、处世准则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军阀割据的唐末五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其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⑤冯道其人,先后侍奉唐、晋、汉、周、契丹五朝十一帝,毫无忠君气节可言,却是当世人推崇的榜样,正是整个时代对原本忠君爱国思想的摒弃和正统价值观念的扭曲,又客观上加剧了朝政的动荡与不安。
赵宋皇朝的统治者深刻体悟到武力政治的不稳定和士风沦丧的弊端,恰如其分地抓住儒家思想中“德治”和“仁政”对笼络人心、巩固政治的作用,大力提拔优秀儒生,以文官血液为主导对政治力量进行重新洗牌。除了打压武将势力外,利用整个儒生群体的力量,将儒家思想推广而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从张希清先生《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一文中统计的科举取士人数以及宋太祖赵匡胤对当时武成王庙中的“七十二贤”的重新删定⑥,可以看出赵匡胤的思想倾向和对是非善恶标准的重新审视,杀妻求将、母死不归的吴起,以报仇为终极目的的孙膑,有勇无谋的廉颇,背信弃义的韩信都因未能符合儒家的忠孝仁义而统统被贬出“七十二贤”。
在统治者颇有用心的道德重塑行为的推动下,儒学作为一种强劲的学术力量迅速发展,社会风气一改五代颓败之貌,开始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随之而来的是士子价值取向的变化。历代士子毕生所推崇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到了宋代开始“由汉唐时代士大夫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立功、立言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⑦王安石一句“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⑧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写照。《论语·先进》中论述的“以道事君”成为大部分士大夫毕生的政治追求,如果说“道”是其内在一直默默坚持的处世准则,那么外在即可表现为对个人品行道德的重视。在这种类型的弹劾公文中,其被弹劾的原因可能会与上文提到的有所接近,但是最出彩的地方确是在对人品的论证上。在以儒家道义为准则而兼济天下的文人士大夫心中,人的品性出问题是最无法容忍的硬伤,对其的指责也更具有直接的攻击力。如果以儒家道义中的“忠孝仁义理智性”的角度来审视,可以归出如下几类。
1.易纲不智。王安石争谋杀刑名之时,刘述认为不可,后率御史刘琦、钱顗联名上疏,认为王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害天下大公”。不仅没有遵从尧舜之道,还“奸诈专权,刚狠自任”。弹劾的依据本来可以属于客观的就事论事,但却突然论及王安石人品,可谓整此大类的特色所在,以客观的政治立场为背景,却主要依靠主观的品德人性来作为主要的弹劾依据。上疏者认为刚狠专权主人,首先在品性上不属上乘,不宜处之庙堂之上,其所作的改革仅为管仲、商鞅权诈之术,擅自改动朝纲,其一没有看到古法传承至今而不朽背后的大智,其二实为朝廷祸乱之源。⑨
2.为臣不忠。侍御史陈瓘,于元符三年九月的《上徽宗论蔡京交结外戚》④350中,论蔡京勾结外戚势力向宗良,大肆宣扬禁中传闻,且撰写制命,无中生有,又自我邀功,反而陷宣仁(皇太后)于不利之地,如此举止“止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对朝廷而言是有害无益。“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国体,为千万年长久之虑。”蔡京之徒利用朝廷之名,“示私门之好恶,反而使天下众议纷纷,其所为并不像先前的范仲淹、范纯仁有“尊主不贰之心”,反而轻君误国,绝对不是为社稷考虑。
3.惑君不义。“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君子对道义的重视要超过对于富贵的追求,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丧失分辨善恶的能力,便是大不义。任伯雨《上徽宗论郝随特许复官》④703一奏中,论到郝随其人,以蛊惑人主大兴土木为业,“穷奢极侈,殚工尽巧,”随意取财,擅自支费,丝毫没有体恤皇帝“恭俭恤物之意”,相反为了满足自身的恩宠,不惜巧言取宠,劳财害命,陷皇帝于不义之中。这样的人即使有巧思,善营造,也不应重新起用,实应祖宗恭俭之德不可弃。
另天禧年间,朱能献《乾祐天书》,孙爽立即上疏规劝,一句“朱能者,奸憸小人妄言祥瑞”开门见山,朱能以邪说“惑左道”,“紊政经”,若真有“民心用离,变起仓卒”,区区祥瑞宝符又怎可平定灾难。像朱能之人,无非想蛊惑圣听,以求富贵,无义之小人实不可信。⑨896
4.性奸不仁。奸邪之人列居高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祸害,虽然在弹劾文书中时常以“奸”字笼统概括被弹劾之人的品性,但是仔细揣摩文本所论述到的仅有“一恶”,真正大奸之人往往劣迹斑斑,罪状集中且不可胜数,故此类弹劾文本多以列罪的形式,一一加以陈述。例如司马光于治平元年八月所上奏疏《上英宗论任守忠十罪》④683中,证据确凿列出奸邪事迹:阿谀求悦、徇私任情、资性贪婪、结党营私、诬告皇子、弃长立幼、离间百官、无端造事、谗告太后、取悦皇后,毫无一点儒家道义可言。这十大罪状中任何一项便罪不可赦,何况“事类繁多,不可胜言”,其人奸诈之极,严重破坏了儒家王道之术的现实运用,这样的国贼已无品德可言,对其的弹劾合情合理。
三、以趋利性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虽然我国古代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但是宋代异常活跃的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异常深远,延时千年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彻底打破,整个社会的风气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宋都东京之繁华程度,足以证明当时商业之活跃。
在这股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世人的价值观念变化巨大,表现之一便是社会趋利性的增强,掌控社会舆论阶层的士大夫一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开始为“农本工商末”中的“商”寻求合理的地位。北宋范仲淹即有诗曰:“(商者)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⑩,到了南宋这种以商为末业的思想彻底受到冲击,朱熹一句“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为世人“逐利”之举给出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宋代人的趋利性表现在经济生活中,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对经商的高度热情,当时的市场“呈现出一种皇室日益靠近和走进市场、官僚吏员迷恋市场、禁军士卒被迫走进市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以及中小商人活跃于市场的情况。”(11)社会低下的商人涉足政坛谋求政治地位,生活清贫的吏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士商相互渗透,“义”和“利”在宋代士大夫身上逐步结合,从而也加剧了政坛中逐利思想的蔓延。宋人趋利性表现在政治生活中,便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本位,抓住各种机会攻击政敌。虽然在王安石变法中,关于义利之辩中有大批士大夫激烈反对,然而即使广大士大夫在道义上无法承认“逐利”的合理性,但是无可否认,宋代经济对世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其本身对自身利益的极力维护和对政敌不惜一切的攻击手段,便是这种趋利性在人性上的外在表现。在宋代的弹劾公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利性的文本体现。
富弼于熙宁二年《上神宗论内外大小臣不和由君子小人并处》④134一奏,用古今例子论述君臣之道,所谓“执政者和与不和,实系乎天下之乱之本,存亡之机”,而“不和”的原因,“止由乎君子小人并处其位也”。然而,何为君子,何为小人,却并未有客观定性。熙宁二年正是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之时,从奏折中所引《周易》一句“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也”,可见其矛头直指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虽然这篇奏折写法比较含蓄,没有直接点名道姓,但其实质却是对王安石所推荐的年轻官员的一概贬斥。就其缘由无非在于政见不和,却冠以士大夫最不齿的“小人”之名加以攻击,并成功在道义上占据上风。作为前朝元老的富弼,一方面年事已高保守主义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更是与变法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王安石变法是以侵害旧贵族势力为代价的“开源”之举,富弼作为这个阶层的代表,对变法派的打击根本上还是对自身集团利益的极力维护,所谓的“君子”“小人”不过是利益相争背后的托词。
再如熙宁四年杨绘的《上神宗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④897,摘录王安石杂说数条,所谓其文如其人,王安石身为人臣却不以维护君臣之道为己任,大放厥词,“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等不合常理的言论。如果说王安石本人的处世理念甚至其“尚利”性质的变法本身,就体现着宋代政治为适应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趋利性调整,那么杨绘此文又何尝不可谓是捕风捉影,抓住一些颇具争议的事情,断章取义反复渲染,以此来打击与之利益相悖者。王安石诗文众多,忧国忧民忧天下之作更不在少数,杨绘偏偏截敢如此几段,用意已不甚明了。即使从整段历史来看,王安石一生清贫,个人操守并无问题,变法是为了缓解北宋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目的也是在于富国,杨绘的异志之说在现在来看显得有些牵强和可笑。谦卑懦弱的语气背后是显在的敌对意识和“为我所用”的攻击手法,而这无非也来自于执政理念的不同,像这类以“利”为上的政治表现发展到后来直接导致承担着特殊功能的弹劾公文,逐步丧失客观的评判标准,反之以个人立场、喜好为出发点,以攻击政敌为主要目的,形成一股相互倾轧之风,宋代党争政治的形成与世人这种求利。
注释:
①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8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④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卷三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⑤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9页。
⑥王瑞明.宋儒风采[M].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页。
⑦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44卷第2期:第59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78页。
⑨脱脱.宋史[M].卷321列传80.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民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页。
(11)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J].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第29卷:第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