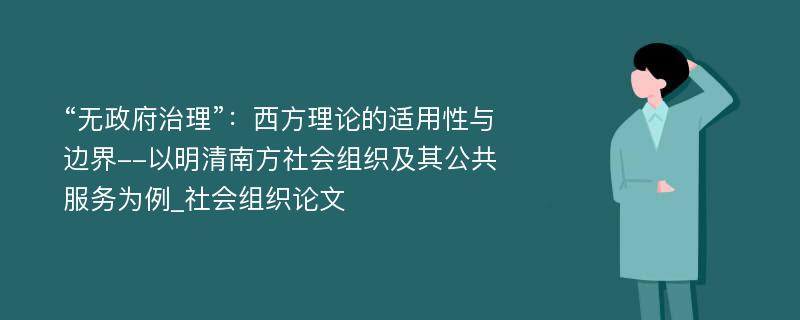
“没有政府的治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及其边界——以明清时期的南方社会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用性论文,为例论文,明清论文,边界论文,公共服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概念与解释体系的发现与重塑,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核心命题是,在一个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或政府权力应当扮演怎样一种角色,不应当做什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应当如何清理,社会组织能否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否具有传统的基础?现有的解释大多从西方研究中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概念与理论加以阐释,那么,它有多大的解释力,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有怎样的不同?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南方社会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为例,论证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条件与解释边界。 没有政府的治理:问题的提出 “没有政府的治理”,像近代以来的其他命题一样,具有浓烈而清晰的西方学术背景,是几种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合流的中国因应。首先,作为明确提出者,罗西瑙主编的专题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讨论超越权威性统治的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去除强制服从关系,建构协作、参与和互动的模式。其次,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理论的兴起,尤其是企业化的政府改造及政府再造理论等理论的推动,强调市场与国家的分立,政府应当向企业学习,建设企业型效率政府。进而,在公共管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形成了多中心治道理论,强调NGO(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或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合作功能。最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或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大行其道,公共领域或社群社区成为不同学者的关注中心。这些围绕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共同建构起“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宏观分析框架。 “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激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回应,以两种面貌盛行于两个研究领域,以期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与“公民社会”的政治发展。首先,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下的晚清社会史研究。继“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西方命题中国因应之后,史学界自1990年代初就开始热烈讨论“晚清以来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西方汉学家或支持或反对地提出国家与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汉口研究”两部曲,他从大量史料出发深描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生活状态,认为至19世纪末,中国城市社会已如同西方,渐渐发展出欧洲资产阶级初期所特有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之下,大量研究者将家族、会馆、行会、寺庙道观等社会组织放置于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框架下加以审视,晚清民国时期俨然形成了类西方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但是,史家注重描述的学科本能也使他们展现出较多的清醒与谨慎,引起了一场将西方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解释力争论。 其次,因应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没有政府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分析框架与政策议程。第一,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演进看,国内学界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的演变,政府角色也由统治型、全能型向服务型、治理型转变。第二,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主流,NGO(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以补充政府服务之不足,多中心治道理论得到阐发。第三,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强调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而非对抗竞争的法团主义成为主导性分析框架,共青团与工会等人民团体研究得到启发,枢纽性社会组织成为官方社团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然而,让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者纠结的是,中国的社会组织或社会领域却始终无法获得它们在西方社会中的那种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研究者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与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研究一直处于既爱又恨的矛盾状态中。 无论是史学家严谨的警惕,还是社会科学家的纠结,都反映了中西话语的“同床异梦”,同一概念之下,中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社会所体现的组织结构。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研究更像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或者说学界的现实期待与理想愿景。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必须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地方性历史经验的限制,而否认“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命题所具有的普适价值。“没有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一个中西方共同面对的元问题:能否在政府直接治理之外形成一种自发而有效的社会自治,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换言之,“没有政府治理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生活是否可能”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历史文化与地域经验的交织之下,充满着颉颃与冲突,故此我们需要剥除历史与地域因素之后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涵及自治的含义 没有政府的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 所谓“没有政府的治理”,并不是全然的政府缺位与社会独大,而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相对分治,各自在所属的领域内发挥治理功能,整体上又构成合作共治。“没有政府的治理”可以从三层意思上理解:第一,国家与社会的共时存在以及相互规制,它们之间不是竞争与替代的关系,既不能“去国家化”,也不能“去社会化”,它们是合作共治的格局;第二,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或管理机构等形式对社会组织形态加以规制,但是,国家并不安排或决定社会组织的领袖,也不直接提供社会组织运行的经费,国家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第三,社会组织的领袖与经费皆由社会组织自行产生,社会组织的根本任务是服务特定的社会群体,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如果国家权力不但通过法律制度与管理机构实行对社会的规制,而且直接控制社会组织的领袖产生与经费来源,那么,该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称之为国家主义的;如果国家仅仅通过法律制度与管理机构实行对社会的规制,但却不控制社会组织的领袖与经费来源,那么,该共同体的社会便具有了独立性或自主性,可以称之为社会自治。此种社会自治也有两种情形。通常,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明确的,社会组织并无监督或限制国家权力的意图。但是,也有社会组织逾越了社会服务功能,并主张国家权力由社会(个体与组织)产生进而国家权力应当受到社会组织的监督与制约,这样的社会组织被称为政治性社会组织(例如现代政党)或者具有了政治指向(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组织及20世纪多元主义所主张的社会组织)。所以,“没有政府的自治”分作两种:社会性社会自治与政治性社会自治。 “没有政府的自治”,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而实现。社会组织的建构目的及其功能效果决定着它的兴立存废与历史形态,社会组织的自身再生产决定着它的维系延续与解体转型,而社会组织及其公共服务共同构成“社会领域”,并与国家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列于国家权力。 从发生学上说,社会组织皆为功能性组织,即因为某种社会目标而建构,它有特定的服务人群,当然也有组织所必需的领袖、结构、行动等惯常因素。社会目标与服务对象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性质,社会生活的单一或复杂决定着社会组织的类别与多元化程度,就传统中国而言,大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生老病死教育救济等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的建制目标因此而生。进而,传统中国的群体划分主要由两种方式界定:第一,基于血缘伦理的差序格局;第二,基于职业分途的四民社会。这两种方式因为社会个体的迁徙流动而划分为归属于宗法秩序之内或者脱离于宗法秩序之外,由此形成传统中国的三类社会群体:第一,完全镶嵌于宗法秩序之内,在宗族内生活,表现为士农群体;第二,虽然有迁徙流动进入新地域,但是仍未脱离宗法秩序,或者通由宗法秩序而构建新地理空间的社会组织,表现为士人与工商群体;第三,因为贫困、战争等原因脱离了宗法秩序或行业归属而无所皈依的贫人或流浪人口。对应上面的三种社会群体,传统中国形成了三类社会组织:第一,完全归属于宗法秩序者的士人农民,由宗族保障其生老病死教育救济(族内救济);第二,进入新地域或行业而未脱嵌宗法秩序者,由同乡会馆或行会公所保障其生老病死教育救济;第三,脱嵌了宗法秩序与行业归属而无所皈依的贫穷者与流动人口,则由寺院庙观宗教组织或乡村士绅组建的善会加以救济(族外救济)。 上述社会组织的结构状态,反映了人众生活的自我建构与自我治理。就社会组织本身而言,其自治状态的长久维系需要价值信仰、物质生产、冲突协调、互助救济等运行机制的再生产。第一,具有支撑集体生活记忆的信仰再生产,如传统中国的谱牒、祭祀、祠堂、墓地,这是社会组织的文化基础;第二,具有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如土地、资本、空间,这是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第三,具有利益冲突时的自我协调与调适,如裁判规制、裁判者、裁判权威,这是社会组织的利益协调机制;第四,具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如生活困顿、自然灾害、战争兵乱时的自我救助与互助,这是社会组织在非常态下的自我调适。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社会组织便是自组织,相对独立于国家,在国家资源之外,能够自成体系,自我治理与自我生存。 最后,还应当从方法上赘言几句。传统中国并不是恒定之物,相反,它时刻都在发生内在变化,我们以明清的南方作为观察对象。首先,之所以以明清为研究时限,是因为通常我们认为明清时期国家与政府权力极度膨胀,甚至发展出专制主义的权力特征,然而,就社会组织最为重要的社会救济而言,汉唐时期以自发的佛教寺院为主,宋元时期的国家慈善占了主导,明清虽则接续了宋元的国家救济政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由乡村士绅加以救济。何以在皇权帝制如此专制的境况下,社会救济却由乡村士绅自发成行,二者并行不悖?以“极端”的明清时代为对象有助于我们分析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次,之所以以南方(华南、江南)而不是北方作为分析地域,是因为宋代以降,南方商品经济、城市化程度已经远超于北方,附着于经济社会网络之上的社会组织也以南方为盛。吕思勉曾指出:“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南方的祠堂比北方多,宗族公共产业的种类与数量也比北方多,族谱也比北方完整,如冯尔康、杜赞奇、杨懋春、黄宗智、乔志强、从翰香、张思、周大鸣等均指出,北方宗族发展不及南方,宗族组织的影响亦远不及南方。就现有研究来说,南方尤其是华南宗族等社会组织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并且形成了成熟的代际研究范式。而且江南由于财力雄厚,民间慈善、社会救济事业也远较北方发达。至于晚清民初,由于中西遭遇,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外来商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尽可能不涉及 故而,我们的分析重点以明清时期的南方为中心,以三层关系为展开:第一,社会组织的功能旨趣或文化信仰;第二,社会组织所映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第三,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功能自治。 人伦皈依、血缘组织与宗族自治 汉唐以降,士族没落,宋明理学建构起家国同构的国家制度,它内生于“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外辅以地主官僚为核心的家族制度。家国同构,一方面建构起忠孝互释,移孝作忠的政权合法性维护;另一方面借以减少政府的治理成本,给宗族以自治空间。有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规定作为族产的祠堂可以永久继承,但是政府并未直接介入祠堂建造的具体事务,建造主体是地方乡绅或商人,建造资金来自族众捐资而非朝廷拨款。国家甚至宁享其自治,纳粮税契之事也交由祠堂办理,“官府把纳粮税契事交给祠堂,祠堂按房支征收,缴纳官府,官府不自费力。祠堂对于各支派家户之经济情形知之甚审,所以征收赋税有所标准,各无怨言。”这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中国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整体重叠或覆盖,相反,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分离,各自独立。皇权国家只在资源汲取或维护统治的时候与民间发生关系,例如收税与征兵,而在日常生活中,国家政治权力(以皇帝以及官僚体系为代表)并不深涉民间生活,这可以从王朝初期的繁荣鼎盛往往与“休养生息”政策相关看得出来,国家政治权力的消极参与或权力管束(不扰民)往往是王朝鼎盛的前提,只要不涉及政治挑战,社会层面的结社自由还是相当大的。 家国同构为宗族自主提供了文化空间,但并不否认在基层社会,“村落有两套平衡并列的社会组织系统:按地域划分的政权组织,如都、保、甲;按血缘关系划分的家族组织,如族、房、家。”保甲制度最初是军事管理制度,王安石变法后演变成户籍管理、征派差役为主的乡村政治制度,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接通国家政策并维护地方事务,也称为乡里制度或里甲制度。明代里甲制度规定,保长或甲长并不由国家直接委派,通常里老由耆老族长或解甲官僚充任,而且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使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不外是家族组织的代名词,强化了家族组织。因此,保甲(里甲)制度与宗族自治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故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创者之一的傅衣凌先生提出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公”与“私”两大系统、“乡族的理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认为乡族不仅是一个血缘性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地缘性组织,乡族组织是官僚政治的补充,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宗族与村落高度重合而成“宗族乡村”。 宗族在传统中国的演化趋势是由大变小,化繁为简,但是并未散逸,聚合实质也未变化。先秦行贵族,汉唐行门阀士族,宋代在五代十国的士族崩解之后构建出更为紧凑的家族,还制定出乡规民约作为家族治理的自治章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安土重迁的居住特征、差序格局的社会秩序、忠孝互构的文化信仰,塑造了宗族组织的封闭性与有机性。宋明时期形成的普及型、以地主官僚为主体的家族,已经摆脱了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关涉(门阀政治、世袭士族)。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单位越来越小、政治地位也越来越下行,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族自治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宗族制的要旨在于养民、教民,家族首先是一个教化组织,敬祖归宗,惩恶扬善。家族的稳固,固然依赖于儒家文化的支撑,其特有的文化载体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谱牒制度就是实现家族信仰与集体记忆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与宗族制度的高度发达,仕宦、乡绅等宗族精英分子积极参与,宗族商人则以丰厚商业利润反哺,徽州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族谱编纂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族谱的功能从先前敬祖归宗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谱法劝惩”的教化文本。陈瑞通过对族谱凡例、血缘谱系纯洁性、联宗收族等内容的考察,认为,族谱能够实现惩恶扬善、劝惩教化与族内控制的社会功能。此外,家族信仰也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与地理空间——祠堂与墓地,并且按照固定的仪礼与时间通过仪式象征强化家族信仰与集体记忆。墓碑上的谱系记录着家族世系,墓地的空间布局遵循世系排列而昭穆有序,墓地祭祀活动制度化并形成“房社会”等组织,从不同层面强化宗族的凝聚力。此外,还有家族义学,资助族人子弟的读书向学行为。 为了充实道德教化的物质基础,家族也形成了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与分配制度,以及困境灾荒时的族内自救与互助系统。宋代范仲淹的义庄按照平均主义的精神,计口供给同族各房的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办理族内义学等公共事务,“家族自宋以来一直是保障其成员各种福利的重要制度。”明清时期福建义田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出功能多、来源广、规模大和影响深的趋向,它时常发挥着族田的作用,义田除了赈贫恤孤外,亦可发挥祭田的作用,赡族仍然是义田的基本内容,其来源有官捐、义民捐助、商捐、诸生捐、僧捐等形式。明清时期的徽州,由于人口膨胀,人地矛盾恶化,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使宗族内部始终存在着一个规模较为庞大的贫困阶层,为了实现族内互助救济,设置有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物质性救济手段。当然这些物质救济有其限制甚至惩罚性条件,诸如年龄、品德、素质、生存状况、赈济数量、操作办法等在族内救济时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特别重视族人的道德品质、血缘状况等条件限制,如“继子不合例,不给”、“男妇素行有亏,曾经祠厅革退者,虽合条规亦不给”,这些规定具有较强的劝惩功能,对族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控制力。 宗族还是族人利益冲突的协调与调适主体,兼具治安、司法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自宋代开始不再教条地以血缘脉络认定宗子,而改以官僚地主承继宗子之职,族长便有了管理的特权。一方面,族长通过一套完善而高效的规制教养着族人的行为,例如文字条例的“乡规”“民约”,文字与口头并呈的“家训”“家范”。这些族规乡约几乎涵盖族人个体生活的全部内容,从音容举止到饮食服饰,从男女异序到邻里关系,从宗族祭祀到族长之威,无一不备。另一方面,倘若发生个体间利益表达的纠纷冲突,族长具有裁断的权力。昆陵陈氏规定:“族中倘有因事失和,致起争端,务须极力排解,勿令涉讼,以免贻笑外人!”宗族就此代理实行了部分的司法权,将族人之间的争斗消灭于宗族内部,故而,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是“无讼的文化”。 显然,宗族独立的信仰基础(祖先崇拜)、组织形态(血缘纽带)、教化基础(私塾教育)、组织主体(族长、父亲)与经济基础(大户及同族),承担着村落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家庭利益的表达。在一个宗族内,个人消费品的生产,以及读书、教育、祭祀、防卫、婚嫁、救火、冲突解决等公共产品都由家族自治实现,遇到饥荒或某个家庭困难,整个宗族还能守望相助实现自助与自救。传统中国由此形成了以宗族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相对独立、与政治国家无涉的民间社会 移民群体、类血缘组织及其公共服务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但是,四民社会之“工匠”“商人”则要向社会讨生活,士人也要到各地走马上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移民运动的高涨是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流动的个体始终有进入新地域或新行当的陌生世界之虞,为此,传统中国形成了两种类血缘或拟宗族的社会组织。一种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馆,一种是以业缘为基础的行会公所。这些拟血缘组织事实上是血缘家族差序格局向社会空间的延伸,它以族人近邻等熟人社会原则建构起陌生人组成的“移民社会”。 尽管有学者将会馆追溯到汉代的邸舍,但是,其官设性质使学者更愿意将纯粹民间性质的会馆视为明清两代的特产。如王日根的历史考察认为,会馆初创于明代中叶,主要是官绅阶层的娱乐场所与志同道合者的汇聚之所,从明中叶到清咸、同年间这一段时间是会馆的兴盛期,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也日益复杂,譬如在京师就有官绅会馆、试馆、商业会馆等类型,清末以来则是会馆衰微蜕变的阶段。 会馆首先是同乡组织,是人们进入陌生城市之后寻求帮助的首要选择,其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一般而言,以一个府为范围建立的会馆,称之为郡馆,会馆的主体建筑以宫、殿、堂、庙、祠等命名,每所会馆均供奉原籍习惯尊奉的神祇或先贤。明清时期,稳定的科举制度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为谋求本地人官数的增多,人们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会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融“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宗亲或神灵祭祀形成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为外乡人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义举则不仅为生者在身处逆境时由此解脱,给予社会救济,更注重给死者创造暂厝、归葬的条件,而公约则要求会员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会馆有时也发挥解决纠纷,编户齐民,辅助治化的功能。以上种种对于本地人来说,尽可在宗族之中解决,但是外乡人到该地,人生地疏,人少势弱,便有团结同乡以互相扶持之必要,故有会馆之设。总之,会馆发挥着类似乡村宗族的社会功能,构成了地理空间转移后的类宗族网络,是一个基于乡谊的自治、自助与自救的组织。因此,会馆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命名,如芜湖会馆、山陕甘会馆等。 会馆本是地域性同乡组织,然而它一旦被工商业者利用,便有了竞争色彩,是团结同乡竞争异域商人的经济社会性组织,从而构成了明清时期工商业系统中的地域性商帮,一所会馆也可以是由一个地域的几个行业的帮派共同组成。商帮(地域性组织)与行业(行业性组织)结合形成了行帮,清初景德镇的行帮便是按照地域与行业自然结合的社会势力,如都帮(都昌人)主要是窑帮,徽帮主要是商帮,构成了一种同乡同业的民间社会组织。但是,严格来说,行帮偏重于地域性而非行业性,其会馆也不是行业性会馆,在明清的苏州绸商行业内就有钱江会馆、武安会馆、济宁会馆、元宁会馆等。故而在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之后,商业帮派会馆的衰落与同业公所的兴起便是接续的事情了。 在行业生产与市场规范方面提供公共服务的,是拟家族化的同业公所等社会组织。传统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专门化的经济管理部门,社会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的规范和约束主要靠民间约定俗成的习俗,而实行这种规范的社会组织是同业公所。同业公所模仿家族制度,以商业资本共同体为中心,其组织方式是以父系家长制为特点的经理专制并行共食制。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如同亲属,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业公所供奉的是本行业的祖师神,如纱缎业公所供奉的是传说中的黄帝,瓦木业公所供奉的是鲁班,把祖师看作行业的祖先。行会将个体化、流动的异乡生产者者组织了起来,罗威廉认为,超过100万的汉口城市流动人口就是“依照籍贯和行业原则建立起来的行会公所”组织起来的,“这种城市自治在日益正式化的、遍及整个城市的主要商业行会的联合过程中,逐步得到了制度化的表现方式。”斯特兰德(Strand)则发现,“没有政府的城市并不一定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至少中国的情形是如此,市民习惯性地围绕在实际上发挥着准政府功能的地方精英周围。” 同业公所的最主要职能是规范行业生产与市场秩序:第一、集体决议、厘定同业生产的行规。如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乾隆五十年(1785)《公议杂货行规碑记》制定的行规业律: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合外分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沿路会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人家店内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栈房门口树立招牌,只写某店栈房,如违者罚银五十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俱有齐备,如有违者不许开行;要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第二,调解、平息同人纠纷和冲突。凡有纠纷者均由会馆先行调解,判别是非,确有赏罚,亏理者有的认茶水账,有的罚以摆酒或鸣鞭爆赔礼,一般纠纷亦能合理解决,非不得已,不进官府。第三,社会化福利事业及扶危济困作用。给同业失业者介绍职业,给同业流浪者给予落脚地,葬殓死者,拟设同业子弟的学堂,解决同乡读书问题,此外还设有义渡、育婴堂、养病所等救济设施,完成修桥补路、施棺材等各种公益事业。 晚清中西遭遇,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西方化生产方式带来急剧的职业变化与地域流动,随着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会馆、公所、行帮等传统社会组织也逐渐发生变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义仓、社仓、祠庙、栖流所、民信局等传统社会组织逐渐衰落,农会、教育社、报馆以及借钱局、洗心局、迁善局、济良所之类的新型慈善组织在长江周边尤其是江南地区首先出现,公馆、公所、行帮等社会组织则逐渐改变形态,走向更为纯粹的经济性商会,义学私塾等教育组织也走向更为新式学堂或学校,慈善观念与机构职能也都发生了变化。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会馆、行帮、公所等社会组织更多在社会、经济等领域发挥作用,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权力,也较少开展政治活动。日本学者清水盛光认为,“中国行会的特征是政治势力的脆弱性和其活动范围只限于经济生活”。会馆、行帮、公所的纯然经济性与社会性,使之明显区别于近代西方的政治抗争性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丰富且发达的城市并未像西方近代一样成为“暴乱与反抗活动的中心”(罗威廉语)。 脱序人口、寺院庙观与乡绅善会的社会救济 扶危济困的社会慈善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于宋代以前的中国言,扶危济困的标准不是物质上的匮乏与贫穷,而是社会人伦上的依靠与相助,贫困与无依是同义词。因此,“古书中不见将纯粹生活困苦的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类别来讨论,而将鳏寡孤独这四种在人伦上有缺憾的人等同为贫人”。宗族家族、公馆公所都是按照社会人伦提供着相应的扶危济困服务,无法被编织进宗族家族、公馆公所或行帮的人,则需要另外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寺院庙观宗教组织和士绅主持的善会。就社会救济的主体变迁而言,汉唐之间,佛道等宗教组织是最初的救济提供者;唐宋之际,政府主导了社会救济事业;明清时期,地方精英取代政府成为社会救济的主体。 6世纪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轮廓逐渐清晰,主要是含有强烈行善观念的大乘佛教,此后行善成为中国佛教信仰的基本活动。大乘佛教要救济的,不限于信徒或僧侣,还包括一切贫病者以至动物。佛教宣扬福田思想,认为行善有如农民播种于田,必有秋收之获,多行善事于前,将会受诸报于后,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收获福德,功德的“福报”。因此,人伦无依者在汉唐之间的扶危济困更多由佛教寺院实践。但是,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其强盛和本土儒家造成冲突,甚至在政治势力上威胁到朝廷,以至于传统中国有过四次灭佛运动。明代虽然重建了了大量寺庙,甚至在数量上远超前朝,但是在制度控制上却更加严格,政府对寺庙的一个控制手段是明确规定府州县的寺庙数量、寺庙的寺僧名额以及每年的度牒人数,中央政府甚至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作了细致的规定,不准随便混淆,清代对于僧寺的管理,在制度上沿袭了前明旧制,僧官制度仍基本沿袭明制。 明代以来官方政策有意弱化佛教的社会影响力,遂使明清佛教在社会救济事业上未能发挥如唐宋以前那般积极自主且极具规模的影响力,明清时期甚至有些宗族的祠堂设在寺院中,寺僧流为宗族的附庸。但是,佛教的行善活动,继承旧制,仍很广泛。第一,公共卫生方面,佛寺设置悲田养病坊的经验记忆使其仍然担任着鳏寡孤独者的疾病诊治与收容救助,在此背景下,很多僧侣成为职业医生,担任“瞻病僧”等职岗。第二,佛教寺院还主持或修建各种公共工程。桥梁是僧人最乐意参与修筑的,因为它具有现世中普度众生的寓意,僧人中很多桥梁专家,除此之外,僧人还投身于筑路建塔、开凿义井、设置“茶亭”、“茶庵”等公益工程,有的寺院设有义学,为乡民提供教育场地和经费,甚至为朝廷提供科考考场(暂借寺院),读书人也有寄读于寺庙的传统。第三,收殓死者、救治狱囚。寺院僧人积极收集遗骸,集中安葬,以体现“慎终追远”的义理。对于狱囚群体,寺院以常视之,在狱中设立观音堂行精神救治。清人林云铭被囚候官县狱时,所著《狱中观音堂忏文》载有其事:“狱中有观音堂,环堵不逾丈,内供养观音大士金身小像,余瞻礼毕,遂寝息其中。堂后粪秽充积,腥臭困馒,群囚往来拜祷,垢腻嘈杂,夜巡击柝声,达曙不辍。”第四,佛寺也是赈灾救灾的主要社会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最直接的施粥施粮,容留与庇护乞丐难民,这一传统一直保存到近代;其次是以工代赈,灾荒年份寺院招募流民,兴建土木工程而使双方受益,寺院以低廉价格完成了计划修建的工程,流民也因此获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免于流离失所。再次,独立主持济贫机构,创建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等,贫困流浪者帮助寺院做些舂米、做饭之类的杂活,寺院则提供饭菜、睡觉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政府宗教政策的严厉,乡绅士大夫替代宗教寺庙成为民间族外救济的主要力量。明清政府继承了宋元的政府救济政策,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有救济机构,例如明代继承了宋代“惠民药局”和“养济院”的制度,基本实现了一县一所养济院,也有一县两所,甚至一县三所的,福建的普及程度更高,以《福建通志》统计,福建有十府二州共62县(包括台湾府),计有养济院75所;清代养济院的救济功能逐渐衰微,与之并存的普济堂收养对象与养济院趋同,甚至合一,而且清代创造性地普遍设立了育婴堂,并以绅商民间力量为主体。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经费的进展、官员的不重视与吏治腐败,制度条文并未走向能动主义的现实生活,政府留下的空白便有乡绅的民间救济充任。 夫马进、梁其姿等学者曾经对善会的源流与发展做过研究,万历十八年(1590)在河南虞城县出现了最早的同善会组织,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江南地区。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江南的武进、无锡、嘉善、太仓、昆山等地先后创立了同善会。研究者也指出了江南善会与北方的不同,虞城杨东明所创建的善会具有两方面的性格,它既是地方名士借之联络感情的亲睦会,又是施行救济的社会福祉团体,而江南地区的善会,抛弃了前者,对后者则加以承续并强化,并且除了贫穷这一物质标准外,还对救济对象提出了严格的精神方面的要求,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道德取向,体现出强烈的教化倾向。同善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捐赠,也有大户乡绅置办或捐献不动产——土地、房屋,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以乡绅土大夫为主体的民间救济,往往假手僧人及寺院,例如乡绅造桥往往请托僧人做督工,乡绅赈灾往往借助佛寺空间,并请僧人做协助者,这也是因为佛寺拥有成熟的人力、精湛的技术、空大的场所与完善的组织渠道。 明末善会“不似宋代的救济组织,处处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官领导,而以地方上无官职而有名望的人为领袖,同时被救济的人的资格并不受官方机构所订的注籍所限制”。从江南各地善会的情况来看,其创立者一般都具有进士、举人或者生员的功名身份,有些人有过为官的经历。他们往往结成团体,利用群体的力量从事社会福祉活动如无锡同善会的创立者高攀龙、陈幼学等都是东林书院的骨干,高攀龙不仅是进士,且官至都御史;嘉善同善会的陈龙正、周丕显都是举人,魏学濂是生员;太仓同善会的主要人物顾士琏是生员,而且同善会组织与太仓知州以及复社领袖张采也有密切关系。 主题与变奏 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按照人伦亲疏而建构,在血缘人伦群体中建构起宗族家族、会馆公所等独立自主、自循环再生产的社会组织,而在非血缘人伦的群体中则由寺院庙观与乡绅善会发挥着社会救济、赈灾救灾的慈善公益功能。传统中国的这些社会组织都围绕儒家/理学信仰而建构,独立而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保障了它的自主性,有效调解群体内的利益冲突凸显了它的功能,而在个体困境或自然灾害等非常状态中能够厉行自救、互助则表明其完善。因此,断言传统中国具有一个区别于国家、相对独立、自洽运作的社会领域当是公允之论。国家与社会的分治与共治是传统中国的重要特征。 从共性上看,近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的“没有政府的治理”,都揭示了一个现象,即在政府直接治理之外形成了一种自发而有效的社会自治,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没有政府治理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生活是可能的;进而言之,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或管理机构等形式加强社会组织的规制,但是,国家并不安排或决定社会组织的领袖,也不直接提供社会组织运行的经费,社会组织的领袖与经费皆由社会组织自行产生,国家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社会组织的任务是服务特定的社会群体,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总之,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各自所属的领域内发挥治理功能,整体上又构成分工共治。 然而,这个“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社会却不是西方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首先,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合作与共治关系,社会组织是社会与经济性的,它没有政治抗争或限制政治权力的企图与行动,而近现代西方的国家与社会是一种竞争与替代关系,社会组织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因此,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尽管内部形成了发达的分工与合作,也有程序正义与资源开放,但却都是“向内用力”(梁漱溟语),具有绝对的内敛性,并没有形成竞争性利益表达的民主诉求。这种“内向封闭”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治理,应和了儒家文化民生政治和谐共融的信仰。进而,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向内用力”的组织建构必然使传统中国的群体间关系走向道德伦理而不是契约法律。也因为如此,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在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状态,并未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或社团,没有成为斗争性力量。而在中西遭遇之后的近代,在西方商品化与城市化的逼迫下,行会组织已经在谋求行业间联合或地域甚至全国的联合。李约瑟就敏锐观察到,“中国的商会也是社会上的一部分团结力量,只是它不像欧洲的商会那样具有政治上的重要作用。”一句话说,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性、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这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兴起的政治与社会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欧洲,是君主专制的绝对主义封建制国家,拒绝任何社会势力或社会组织分享权力,奉行单纯的血缘传递与军事暴力原则,与此同时社会则由于资本与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而信仰契约关系、法律规制与权力分享,因此,掌握新技术与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建构了谋求“革君主命”的政治性市民社会,它表现为社会组织的监督或限制国家权力的意图与行动。在启蒙思想家与20世纪上半叶的多元主权论者看来,国家起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民众首先建构起社会领域,主权属于人民或者主权应当由所有社会组织分享(而不仅仅是国家独享);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人民主权的宪政规制与分权政制,又为社会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性组织,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了法理依据。西方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在政党与利益集团中表现为最为明显。故而,从形态和某些功能看,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有相似性,但其性质却大异其趣。 其次,传统中国与近现代西方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来源不同。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取决于它与国家政治的距离。宗族家族与皇权国家是同构的,会馆公所的组织原则也是类家族的血缘制,它们都是血缘组织的社会性扩展,共享着由血缘人伦建构起来的儒家文化,与国家权力并无本质性冲突,因此,它们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然而,在非血缘人伦群体的组织上,国家权力与佛教寺院之间的紧张就相对明显,宋代之前,佛教寺院受到四次灭顶之灾,佛教被取缔,寺院被焚毁,僧人被还俗。宋代儒释道三宗合流,佛教被融合为新儒学的理学之后,才最终被国家所认可,成为纯粹的社会救济力量。故而,明清时期才出现国家与社会之间体现出互赖和谐、平衡互助的合作式治理局面。 而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组织的独立自主生存空间取决于其独立传统与法律信仰,尤其是中世纪封建制时期的权力分立传统。欧洲封建制的特征是“经济庄园-军事城堡-政治领主”三位一体的权力割据,比君主地位更彰显统一与高贵属性的是基督教与法律信仰,君主并没有决然超越贵族的统一权力,相反,君主的形式性中央权力——例如征税——必须得到贵族的支持。1215年滥觞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充分体现了贵族以法律传统抗争并限制英国王室的权力。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正是来自传统贵族分立权力以及法律信仰的合法性遗传,故而有英国所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议会斗争,也有法国第三等级的议会反抗。也正是在贵族或地域性抗争的传统下,尽管近代君主取得了专制性权力,建构了利维坦国家,但是替代传统贵族的“市民社会”再次挑战君主的绝对王权,并不惜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胜利后用“公民社会”巩固分权与制衡的权力格局。因此,构成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西方社会组织是具有抗争君主或国家权力的独立自主传统的。 最后,传统中国“没有政府的治理”所昭示的社会组织,取决于安土重迁的静滞性或封闭性农业社会结构。商业化与快速流动将打破熟人社会的组织黏性,血缘人伦的人际纽带无法结纳快速流动的陌生人。马克思很睿智,他在1853年说:“与外界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晚清以降,伴随着列强入侵,商品资本化、城市化与人口快速流动已经使传统社会组织快速消亡、衰败或转型,利益表达性或类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日渐生发。这使我们不能轻言“公民社会”仍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也不能轻率地拥抱“公民社会”。重温传统中国的经验是有益的:面对几乎同样的贫困无依成为社会问题与移民社会的陌生感,近代西方通过国家救济与法律信仰而发展出福利国家模式,明清时期则在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中走向乡绅善会的社会救济模式。显然,明清以上大夫为主体的社会救济传统能够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政治想象力。标签:社会组织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明清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祠堂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