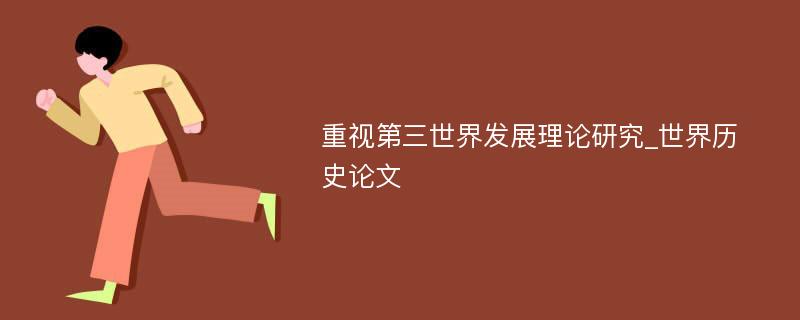
重视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视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格局和历史变革中的地位,一再重申,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在世界各国所有政党中,我们党是唯一提出自己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科学理论的政党。这一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同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几次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英明而富有远见,给我们开辟了道路,对于团结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和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80—90年代,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家的安全和主权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东西南北四个字,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等等。这些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尤其在第三世界的现实和当前国际关系的演变中,愈来愈勃发出真理的力量。
随着苏联剧变和解体,南北问题更加突出,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研究尤其显示出紧迫的、重大的意义。
第三世界发展是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内容的非常广阔的领域。即以经济而论,其发展不能离开政治和思想文化;在其内部,为着区别增长和发展这样两个概念,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付出沉重代价,出现了几十部甚至更多的专门著作,何况仅仅对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的认识也还仍然存在许多不甚了然的环节。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一些特别突出的问题,亟待提上日程。
首先是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第三世界的地位和面临的新情况。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全球经济增长了,但是南北差距却在继续扩大。按照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提供的材料,第一世界同第三世界人均收入的差距,1500年为3∶1,1850年为5∶1,1900年为6∶1,1960年为10∶1。联合国1992年版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从1960—1990年,世界总人口中20%的最富裕的人的收入同20%的最贫困的人的收入的差距,从30倍增加到60倍。联合国1996年版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这种差距已经达到61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达到创记录的13亿,358名亿万富翁的财富超过占世界总人口45%的低收入国家年收入的总和。联合国关于1997年世界社会情况的报告承认,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西部地区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于80年代;非洲在目前人均收入倒退20年以上的总共71个国家中占33个,人均负债460美元,外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80%。世界的发展不会要求不同民族采取同一步调。但是世界的发展无论从社会生产力本身的要求还是从道德上,都应该是人类的总体的发展,而不应该是牺牲占世界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人民利益、以第三世界的不发展和反发展为代价的西方少数大国的发展,不应该是这种不公正秩序的永世长存。这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及其理论界,要么力图掩盖令人不快的现实,要么用似是而非的教条说服第三世界人民在它的阴影中一味忍耐和等待。此外,人们还到处看到忧虑和无奈。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的一个庄严使命,就是从深层揭示这一悲剧进程的原因,寻找使第三世界摆脱困境、真正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政策。这种政策,使得上述不公正秩序得以产生、巩固下来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它最初表现为赤裸裸的抢劫、杀戮、攻城掠地、贩卖黑奴、灭绝种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大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独立国家的产生,则代之以承认政治独立前提下的经济控制、不平等贸易、封锁和禁运。随着苏联剧变和解体,有两个动向值得严重关注。一个是“重新殖民化”。英国《卫报》1991年1月29日刊出评述海湾战争的《一场殖民战争中的为害者和受害者》,说这场针对第三世界人民、捍卫西方利益的战争,采用21世纪的技术,但却是“典型的19世纪的旧式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干涉的政治和推翻不顺眼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已形成一种臭名昭著的模式:我们不喜欢格林纳达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巴拿马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伊拉克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这就是美国要求我们欢迎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11月11日发表《再见吧,莫伊先生》,公开主张“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另一个动向,是利用现代技术、知识产权和跨国公司强制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有研究者把这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指出其宗旨在由物的掠夺、劳动及其成果的掠夺转到精神的改造,以彻底摧毁第三世界人民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意识和历史创造主动精神,实现灵魂的奴隶化和附庸化。这种政策的核心,它的演变过程和趋势,理应在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中占有自己的分量。
第三,南北关系和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前,可以说全部属于经济落后或比较落后的国家。前引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一书,有专门章节分析苏联东欧地位,指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以后,东欧首先落入第三世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也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先属于第三世界,应该不会引出歧异。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首先使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且在这一前提下取得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这一历史进程要求对两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性回答。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为第三世界发展,做出了哪些前所未有或者在其他社会制度下不曾做出的新的贡献。即使未必赞同社会主义但却努力保持严谨科学态度的西方学者,一般地也承认,社会主义的突出成就,在于实现独立和主权,在于比较公正地处理分配、教育、医疗等涉及国内不同群体关系的问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1970年)中指出,“共产主义政权最初受到普遍欢迎,这可以从共产主义革命的效果看到,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第一次给了人民一个不腐败的政权。”仅仅这些贡献,已经使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接着出现的问题是,怎样解释苏联的易帜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继续巨人般地巍然屹立。邓小平同志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为第三世界发展开辟和继续开辟着一条成功的道路。这是一条立足于第三世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包括,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其内部矛盾达到成熟、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然后实行革命并产生新的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主义;这种发展道路又不同于第三世界的其他发展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决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第三世界之外和第三世界之上的现象以及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属于第三世界和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等等。
第四,西方发展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出现专门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比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等。这些理论著作在第三世界广有市场,80年代以来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不仅是译介和传播,而且以第三世界发展的实践检验这些理论,对它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仍然是繁重的任务。西方发展学的历史功绩在于开始确立以第三世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西方发展学的不可逾越的困境在于它同西方利益、同国际资本垄断统治秩序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它同第三世界发展实践之间的深刻鸿沟。它提出了自己无法完成却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课题。被列入发展经济学先驱的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谈到,西方富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上的兴趣”,导致发展学和它的种种偏见的产生;“由于所有研究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进行的,由其政府、基金会、大学和行业提供资金,实在没有道理不指望研究和开发工作将对他们自己有利。”正是在这里,一些西方研究者如果说远不是清晰地认识至少可以说多少感觉到了西方发展学的某些根本性缺陷。尽管相当一些中国读者至今保持着对西方发展学的新鲜感觉,但是西方学者包括西方发展学学者甚至从60年代就已经在谈论西方发展学的贫乏、危机、衰落问题了。受世界银行委托,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该书跋文《发展的两分法》引述的两个看法是耐人寻味的。第一,把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归因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面夹攻(虽然不是协调一致的进攻)。前者责备它因背离新古典原则而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当,后者责备它为依附和剥削进行辩护。第二,早期发展理论的许多错误,就在于把一个地区的假设和关系,生搬硬套到它们不适合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北方的经济学原本不适用于不同的南方社会。跋文认为,说发展经济学已经衰亡固然过于夸大,但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却需要吸取教训。它开列出七条教训。不过七年以后,我们又在美国《国际发展比较研究》1991年夏季号读到K·曼佐的《现代主义学说与发展理论的危机》,再一次对西方发展学进行系统清算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一书两主编之一杰拉伍德·M·迈耶在该书导言中承认,“那些开始对不发达国家作理论研究的人多半是发达国家的公民”,接着引用了冈纳·缪尔达尔的热情洋溢和寄予深切期望的呼吁:
在这伟大的觉醒时代,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可悲的。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妨碍那些国家的学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对不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学术创见更充耳不闻。
我但愿他们有勇气抛弃那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想。
我们把包括主要由西方学者和接受西方教育的学者推行的,以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却又主要依据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理论和一套范畴、术语的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等等,概括地称为西方发展学。拉美学者C·F·博尔达在《今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展望》(美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80年第1期)中,痛切地谈到“学术上的殖民主义”问题:“我们受到外国同行的束缚,为他们的思想所支配。……我们不能指责外国人只按他们的利益行事,因为,如果我们迷惑于他们的公式、数字和金钱,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了。”对于第三世界来说,现在尤其需要的,是创立和不断完善符合第三世界实际情况的、反映和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第三世界发展学。
所谓反映第三世界实际情况,就是要从第三世界的实际出发,特别是要认真总结第三世界自身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西方发展学的丰富思想资料当然有其可资借鉴和利用的价值。但是陷入盲从和抛弃分析的态度,那就势必极大地降低研究的科学性。仅以数字而论,《世界贫困的挑战》就承认,统计材料“是一个政治统治至上的领域”,尖锐地批评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DAC)提供的、被作为权威到处引用的统计资料之不可相信,说那里的“行为不道德的靠领薪水吃饭的专家”在“遵照老板即政府的意图行事”,此外还有“惯常的草率”。同一作者1974年出版的《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也以相当篇幅揭露了西方“乱造数据”的情形,干脆指出“发达国家所发表的有关援助的统计数字一直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已”。关于西方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数字,这里谈到几种情况:不考虑物价不断上涨的因素;把贷款和赠与混为一谈;贷款和赠与以购买“援助国”出口货物为条件;政治因素,比如“在算作对外援助的总额中,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纯粹是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提供给美国控制的南越地区和在越南战争中帮美国忙的该地区少数几个卫星国”;“纯由私人提供援助”的统计数字,很多“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类业务往来,那是根本不会算作援助或帮助的”,——美国弄虚作假的程度尤为严重,如果如实计算真正属于援助的数额,官方数字就要减少一半以上。坦率地说,第三世界发展学没有理由以这类东西作为依据。第三世界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第三世界人民为自己的发展曾经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但是极富创造性的探索和奋斗。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有严格事实作为基础的理论的概括和总结,都应该在人类历史创造的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世界发展学,应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发展学。人民的发展,包括从民族压迫、社会压迫下的解放,也包括从自身愚昧、狭隘、贫困和陈腐习惯势力下的解放,包括物的解放,也包括人的、精神的解放。因此,第三世界的发展,是第三世界最大多数人民参与而又为着实现第三世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第三世界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接受外面或“上面”恩赐的事业。在这里,第三世界人民的实践高于一切,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马克思研究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的发展问题,也有两个伟大发现。第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代现象,因此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第二,这种发展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两个伟大发现已经不再是只作为科学的预言,而是深深融铸于我们时代亿万人民的实践了。第三世界长期被迫以自己的不发展、反发展支撑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它的发展却必然地包含着双重内容:同第一世界的民族压迫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同时开放大度地吸取其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文化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避免它在取得这些成果的过程中付出的痛苦代价。根本的问题恰恰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能不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秩序而又必须为摆脱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进行不屈斗争,不能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存在而又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在自己的大地上植根,使自己从对方发展的客体转化为自己发展的主体。这是新的历史创造的过程。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自觉或不自觉,第三世界人民都在以自己的实践同马克思对话,都在执行他的遗嘱和努力实现他提出的历史任务。人类的历史创造,本来就不是满地鲜花、酒香四溢的宴席和呢喃着爱的呓语的轻歌曼舞。无论经历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论在闪耀过一个时期的辉煌之后又怎样再度坠入黑暗、仿佛前功尽弃、还需要从当初起步的地方重新开头,无论有些事情事后看来怎样地幼稚可笑,无论还有多少茫然无知的领域和面临怎样的困境、多大的艰难,第三世界的发展都将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