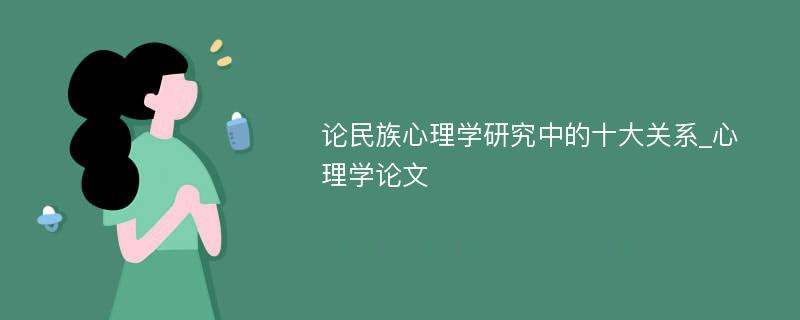
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十种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种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1-0044-07 2015年,对于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2015年3月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2015年6月8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在中国人民大学挂牌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学术研究讨会;2015年7月3日,中国心理学会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这三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高调地进入了政府、研究者和民众的视野。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早在19世纪后期,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W.Wundt,1832-1920)在创建了个体心理学之后,又花了20年的时间,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然而,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个体心理学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的同时,民族心理学由于其鲜明的人文倾向却发展缓慢,始终未进入心理学的主流。在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发展亦举步维艰。民国时期只出现了少量的民族心理学论著;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心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90年代,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1]、高觉敷[2]、荆其诚[3]、张厚粲[4]、刘兆吉[5]、李伯黍[6]、林仲贤[7]、陈永明[8]、燕国材[9]、彭聃龄[10]、杨金鑫[11]、左梦兰[12]、张世富[13]、傅金芝[14]、沙毓英[15]等人在汉族心理和少数民族心理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民族心理学还十分孱弱,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后,大批研究者为之所吸引,民族心理学研究进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尽管如此,仍然有一批研究者在继续努力。例如,李静出版了《民族心理学》[16],万明钢等人开展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研究[17],郑雪与陈中永考察了我国不同民族的认知操作、认知方式与生态文化的关系[18],蔡笑岳开展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智力与文化适应的研究[19],周爱保考察了回族大学生自我参照中的阿訇参照效应[20],植凤英等人探讨了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实现质与量的整合[21],李杰等人研究了蒙古族双语者的语言表征与加工特点[22],尹可丽等人考察了景颇族初中生的民族社会化觉察及其特征[23]。至于我本人,开始时是由于对东巴文感兴趣而进入了民族心理学研究领域,从2004年起,我们课题组先后对纳西族[24—33]、摩梭人[34—39]、藏族[40—41]、彝族和白族[42—44]、羌族[45]、傣族[46—47]、基诺族[48]、鄂伦春族[49]、傈僳族和普米族[50]的心理了进行研究。2012年,我受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杨玉芳研究员和《心理科学进展》主编隋南研究员的委托,在《心理科学进展》上主持了“民族心理学专栏”,共发表了13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广泛的注意[51]。同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与蔡笑岳共同主持了首届民族心理学论坛。在2014年北京全国心理学大会和2015年天津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又与七十三、高兵、尹可丽等人组织和主持了民族心理学论坛。今年,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我主持了“民族心理学专栏”,分期发表民族心理学论文,目前已经发表了15篇。这些工作均属于推动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发展之努力。本专栏亦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是,它的一些元科学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均有过很多讨论,却均无定论。这种状况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这不是因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缺乏智慧,而是因为民族心理学是一个与方方面面都有着极其错综复杂关系的学科。余以为,在当前,中国民族心理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十种关系。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必须正确处理的十种关系 (一)民族学研究取向与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关系 在民族心理学发展史上,一直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民族学研究取向与心理学研究取向。心理学研究取向是冯特开创的,许多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麦独孤(W.McDougall,1871-1938)和勒庞(G.Le Bon,1841-1931)为之做出了贡献。民族学研究取向是与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列维-布留尔(L.Lvy-Bruhl,1857-1939)、博厄斯(F.Boas,1858-1942)及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R.Benedict,1887-1948)和米德(M.Mead,1901-1978)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52]。心理学研究取向不仅推进了民族心理学的发展,还催生了两门相邻的学科——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民族学研究取向亦催生了两门相邻的学科——文化人类学与心理人类学。由于民族心理学是跨人类学、民族学与心理学两大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与综合学科,因此,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在我国,心理学取向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者大多分布在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和科研院所,民族学取向的研究者大多分布在民族类院校、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机构。过去,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是互不联系、互不沟通的。为了使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能够健康发展,一方面,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切莫相互轻视;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尽早结束目前存在着的“各说各话”的局面。两种研究取向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令人欣喜的是,无论是隶属于中国心理学会的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还是隶属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目前都由两种研究取向的人员组成,这无疑有助于两种研究取向的学者的交流与整合。 (二)质的研究范式与量的研究范式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范式不同:民族学研究取向的研究者一般采用质的研究范式,主要从事定性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国外的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53]、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54],国内的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55]、严汝娴和宋兆麟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度》[56]。心理学研究取向的研究者一般采用量的研究范式,主要从事定量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国内的如左梦兰与卢濬的《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57]、陈中永的《中国多民族认知活动方式的跨文化研究》[58]、蔡笑岳的《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智力发展与教育》[59]、张海钟的《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60]、张积家的《纳西族—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研究》[61]、植凤英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和谐及教育对策研究》[62],等等。当然,也有整合两种研究取向的研究,如韩忠太的《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63]、李静的《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64]。在研究方法层面,民族学研究取向的研究者大多采用田野调查、文献分析、谱系调查、案例分析等质性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更多地采用心理测量等量化的研究方法。近年来,采用实验法研究民族心理的论著有了显著增加[65]。我们课题组的民族心理研究大多采用实验法。实验法能够方便地操纵自变量,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精准地测量因变量,可以做因果关系推论,因而能够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精确性,也有利于提升民族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发表层次。那种认为民族心理研究不适合采用实验法的看法是片面的,也为大量的研究范例所证伪[66]。在分别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也在探寻民族心理学自身的研究方法,例如,李静提出了“田野实验法”。田野实验法是指在田野场景中研究民族心理,其核心是参与观察与深度体验,以影响民族心理的主客观因素为自变量,以民族心理和行为为因变量。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因果关系明显,故有实验法的特点;又由于研究变量是在田野中发生的,而且不由实验者来设定和操控,研究人员只是利用现成的条件,因而减少了人为的操控,因此可以获得真实的材料和较高的效度。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或一个地域均是开放的实验室,生活与居住于其中的“人”可以视为研究对象。田野实验法遵循“在一起”的原则,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67]。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在研究初期可以通过质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去发现问题,然后设计实验去揭示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与行为反应的因果关系[21]。 (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解释学的文化观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而心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在心理学领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则盛行着解释学、现象学的文化观[52]。根据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世界是以统一的、有层次的方式组织的,科学是以还原论为特征的,人类的心理是以生理和生物的结构和过程为基础的,不同民族的心理具有共性,心理规律独立于文化与情境。根据解释学和现象学的文化观,人类的心理高度依赖于所处的文化与情境,心理规律是文化特异的。研究者应该深入到民族文化中去,研究在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特点,并且从文化与情境对行为的影响中去寻求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这两种观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何兼顾,需要研究者的深思熟虑。总的看法是:在研究中,既应该坚持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努力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实证性,又要重视社会与文化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在提出研究假设和解释研究结果时,应该以该民族特有的历史与文化作为基础。 (四)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反映。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民族和谐与民族冲突均是历史地产生的。因此,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不仅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而且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特征,就要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且设身处地地用这个民族成员的眼光去看世界,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民族的心理特点,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才有可能。德国解释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认为,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差异性。历史涵盖了主客观关系:历史不是客观的,因为历史是入的一部分,人不能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认识历史,必须在历史之内认识历史;历史又不是主观的,因为它先于人的反思,预先决定了反思的对象和方向。伽达默尔将这种涵盖了主客观关系的历史叫“效果历史”。他还提出“理解界域”的概念,认为理解是理解界域和理解处境的互动,处境是历史的产物,人始终处在处境之中,并在处境中理解。处境是人的理解范围的界限,这种界限叫界域;界域是理解在其中悠游并随着理解而移动的生成变化的过程。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模式,也是一种创造过程。语言是理解的媒介,它表达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人总以语言的方式去拥有世界,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因此,承认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承认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伽达默尔的这些观点对民族心理学研究者把握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心理学以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狭义的民族心理学仅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心理学史上,民国时期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主要以汉民族心理为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大多以少数民族心理为研究对象。在少数民族心理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毋庸置疑,民族心理学研究要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是,少数民族同胞亦有追求现代化的权利。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与现代化之间有时会形成矛盾与冲突。少数民族同胞多分布在祖国的边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来内地求学与谋生,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异文化之中;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发展,大量的内地人群涌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异文化,特别是现代化的异文化,这些现代化的异文化会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不小的冲击。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汉族的传统文化,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例如,对亲属词空间隐喻的研究表明,汉族亲属制度虽然是父系制,但汉族被试对待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的空间隐喻已经无明显区分,他们均属于汉族人的“圈内人”;由于独生子女占优势,当代汉族大学生对不同辈分的亲属词有上下空间意象图式,即他们具有“尊老”意识,但他们对同辈亲属却无左右空间意象图式,即他们并没有“敬长”意识。他们能够接受“孝”的行为准则,却难以接受“悌”(敬兄长)的行为准则。摩梭人在传统上不知父或不亲父,但是,当代摩梭中学生却对父系亲属(爸爸、爷爷、奶奶等)存在内外空间意象图式,他们将父系亲属(如爷爷、奶奶、伯伯等)视为“圈内人”,这显然是由于文化变迁的缘故[36]。 (六)人类共同心理特征与民族特异心理特征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要研究民族的心理特征,这一类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共有的,对民族成员而言,它们是心理的共性;但是,对全人类而言,它们又是民族特异的、文化特异的,是心理的个性。一方面,作为类存在物,不同民族的人的心理具有共性,即古人所说的“心同此心,理同此理”。例如,亲属之间具有高亲密度,亲属之间血缘关系越近,亲密度就越高,个体就越容易做出利他行为。另一方面,当这种共同性运用到具体民族时,就要受社会和文化制约。例如,在我国,汉族亲属制度属于父系制,摩梭人的亲属制度属于母系制。对汉族人而言,父亲与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比个体与舅舅之间的血缘关系更近,因而父亲比舅舅更亲;而对摩梭人而言,由于舅舅承担教养外甥的责任,个体与舅舅生活在一起,因而舅舅反而比父亲更亲,摩梭人即使知父也不亲父,这就是民族特异心理特征。再如,汉族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摩梭人实行走访制,汉族人的夫妻之间是亲属,摩梭人的阿注之间是朋友[37]。这也是民族特异心理特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认为,语言是世界观的体现,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的表现形式,不同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自我显现的结果。根据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1884-1939)和沃尔夫(B.L.Whorf,1898-1941)提出的语言关联性假设,语言影响人的思考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以不同方式来思考[68]。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因而也有不同的心理特点。然而,不同民族之间毕竟有许多心理特征是相同的,否则,不同民族之间就难以沟通和理解。因此,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既要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也要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特异性。人类心理如果没有共同性,心理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不同民族的心理如果没有特异性,民族心理学也就无立足之地。 (七)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是与个体心理学相对应的。个体心理学以个体为单位,民族心理学以群体为单位,民族心理学研究不同民族的心理规律与心理特点。然而,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时,研究者所接触的仍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体。这些个体来自于不同的群体,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群体的烙印,他们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体,而不是中性的个体。然而,个别人的心理特点就能够代表整个群体?不一定。例如,能否因为出现了基地组织和IS,就说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具有恐怖分子的心理特点,显然不能。在与不同民族的成员相处时,最忌讳受刻板印象影响,而刻板印象的形成与观察者或研究者以个体替代群体有关。因此,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特别应当防止受“知觉的类别效应”(perception categorical effect)影响。知觉类别效应是指概念(词)对知觉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事物如果被贴上相同的标签,人们随后就更容易等同地对待它们。Goldstone发现,分类学习会导致人们对有关维度敏感化。而类别一旦形成,类别内会发生紧缩效应,人们会有意无意地缩小或忽略类别内成员之间的差异;类别间会发生扩展效应,人们会扩大类别间成员之间的差异[69]。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切忌给不同民族贴上不同的标签,特别是负性标签,要防止以偏概全,以局部来代替整体。 (八)内隐与外显的关系 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往往要涉及不同民族对不同事物的态度,如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对本民族与他民族的文化的态度。这些不同态度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这些不同态度,研究者往往通过不同的心理测量工具和调查问卷来获得。然而,研究表明,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如果你询问美国白人是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态度,他会肯定地回答“没有”,但是,如果你让他选地段买房子,一个区域完全由白人居住,一个区域多数由有色人种居住,对方如果毫不犹豫地选择完全由白人居住的区域,就说明他具有种族歧视的态度。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进行外显自尊测试,回族被试(没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得分显著高于苗族被试(有本民族的语言但很少或不使用苗文)和汉族被试(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然而,如果进行内隐自尊测试,回族被试的得分却显著低于苗族被试和汉族被试。因此,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只有将被试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够把握被试的真实态度。 (九)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不等同于行为。态度只是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是否产生与态度一致的行为还取决于许多主客观因素,如能力与情境因素。正好像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一样,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经常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民族语言教育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在许多场合都呼吁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将自己或亲属的子女送到汉语学校中,因为这样会使其子女或亲属将来在高考和社会竞争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又如,许多干部和名人对美国颇多微词,甚至竭力批判,颇有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之豪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却积极地申请美国绿卡或赴美国生子。在美国,有研究者让一对华人夫妇游历美国,事先咨询了100多家宾馆和酒店,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待这对夫妇,结果均表示不愿意,然而,事实上,当这一对华人夫妇去入住时,只有两家酒店拒绝。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对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有足够的重视,应该审慎地对待各种态度调查得来的结果。 (十)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民族”在我国的语境下属于政治的范畴。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例如,汉代与唐代的“和亲”,清代的满蒙联姻。甚至在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与义渠王私通的目的也与政治有扯不清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秦统一以后,在国家政权中均设有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秦朝设典客,汉代改为大行令、大鸿胪,隋、唐、宋、明设鸿胪寺,清代设理藩院,民国时期设蒙藏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设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民族心理研究必须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无论何时,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都应该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学术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稳定。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心理学研究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要努力当好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工作的智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民族心理学所以要处理好如此复杂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心理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民族心理学的交叉性、综合性。有鉴于此,那种单一的、非此即彼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可能不适用于民族心理学研究,一种综合的、包容的、折衷的、交叉的与整合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更有利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