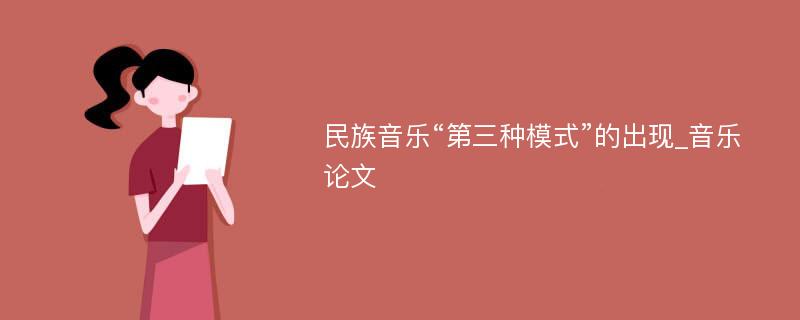
民族音乐出现“第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音乐论文,第三种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以独奏、重奏为主要演奏形式、突出经典传统曲目和个人演奏技巧的小型民族乐团,目前表现活跃。它既不同于“彭修文模式”,也不同于谭盾、叶小钢等人领衔的“新潮音乐”,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种模式。本文试图描述其生成原因及发展轨迹。
像“华韵九芳”这种以独奏、重奏为主要演奏形式、突出经典传统曲目和个人演奏技巧的小型民族乐团,目前在国内出现且表现活跃,这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界的一种潮流和现实,即重新认识中国民间音乐固有的美学传统和艺术传统,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音乐领域里所有“改革”的成败。这是和从五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主要以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古典音乐”的和声学、配器法、乐器制作标准和西方管弦乐队编制为楷模的大乐队(即“彭修文模式”),和从八十年代兴起的、以西方现代、后现代的音乐思维和“反传统”为旗帜的“新潮音乐”模式不同的另一种追求,我姑且名之为“第三种模式”。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不以对古典艺术精神的追索与张扬开始一样,“第三种模式”所追求的,也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层次的挖掘。可以认为“第三种模式”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明确背弃的,主要是那种追求民族乐队“高、大、全”的“彭修文模式”和认为“新即美”的流行音乐思潮。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过去几十年里,那种在艺术上不加选择地强调“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的思想,那种基于民族乐器和民族乐队“音不准”、“音色太刺耳”、“音域太窄”、“转调不方便”的思路而在竹笛上加键、在二胡上加指板、把阮或马头琴放大后当成大提琴立在地上拉。按照西方管弦乐队的编制和规模组建中国民族乐队的“改革者”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应该说,过去许多的乐器改革包括民族大乐队的建立,都有其历史的功绩,在那样一种时代,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在目前,彭修文模式的民族乐队也还是“一枝花”。问题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改革”,是以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为背景的。在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历史重压下,这些“改革者”们的爱国心,以及他们出众的才华和想象力,不得不用在了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模仿上,他们虔诚地相信只要把我们的民族乐器和民族乐队“改革”成西方乐器和乐队的样子,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就能摆脱“落后”的局面,他们不屑于深挖自己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意无意地割裂了传统(如不去挖掘仍在中国民间流行的类似“五调朝元”的固有转调方式,不去向那些能用指法和“口风”在一支竹笛上转五个调的老艺人学习,而宁可牺牲民族韵味去追求“十二平均律”的“音准”)。其思想的深处,其实还是一种隐蔽着的民族自卑感——认为我们的乐器和乐队不如西方的乐器、乐队“科学”;我们的混合律制,不如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科学”。其实,艺术有时并不一定是科学,在艺术领域,也本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同的民族,只有不同的美感和不同的审美习惯。一个受西方音乐教育的耳朵可能认为西北民间音乐中的“fa”不“fa”、“si”不“si”,觉得那个被西北农民世世代代称作“苦音”的音阶中比本位“fa”高、但又比升“fa”低的音“不准”,但正是这个起码已有了两、三千年甚至更长历史的音现象,不可替代地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西北诸民族共同的、长期的审美习惯和音阶体系。同理,在西方,“强势文化”进入我国之前的数千年里,欣赏“中庸之道”、喜欢“中和之声”、讲究不同音色的对比和在旋律的横向进行中体现多声思维,有着从北方的“笙管乐”到南方的“十番鼓”、“江南丝竹”等几十种合奏形式的中国人,也从没有觉得我们传统的乐队组合中一定要加上什么“低音声部”、一定要用三度叠置的和声才好。
而另一方面,“新潮音乐”虽然在破除我国近五十年形成的“新传统观念”和破除音乐思维定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在国内外赢得了一批以青年专业人员为主体的听众群,但始终因为“脚步太快”而难逃“脱离群众”之讥,并被某些“新传统观念”的卫道士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怪胎”,处于“曲高和寡”的尴尬状态。我个人认为,“新潮音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但不是卫道士们的狙击,甚至也不是听众的多少和舆论的毁誉。“新潮音乐”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自己,即“新潮音乐”的作曲家们如何超越自己的问题。在近十多年里,以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郭文景为代表的“新潮音乐”,在中国和世界的乐坛上掀起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新闻热点,展现了一个个在时间的纵坐标上与前人不同、在空间的横坐标上与他人不同的艺术境界,尤其是把中国乐坛搅得波翻浪卷后又在世界乐坛上叱咤风云,仅从振聋发聩、摧枯拉朽和使广义的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意义上来说,便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们既不被外在的传统所囿,也不被内在的局限所困;既不迷信别人,也不崇拜自己;把追求自己的个性与追求人类的共性结合起来,为这个民族、为这个世界,创作出一批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能流传几代的经典作品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种模式”即新古典主义的出现便成了一种必然,人们希望有一种直接根植在传统之上但又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音乐出现,希望艺术家们能在传统韵味与现代气息之间找到一种契合点,希望能在西方“强势文化”和“流行音乐”大潮的双重冲击下,听到直接从我们血脉的源头传来的声音,听到那种地地道道、不折不扣但又新鲜活泼的民族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