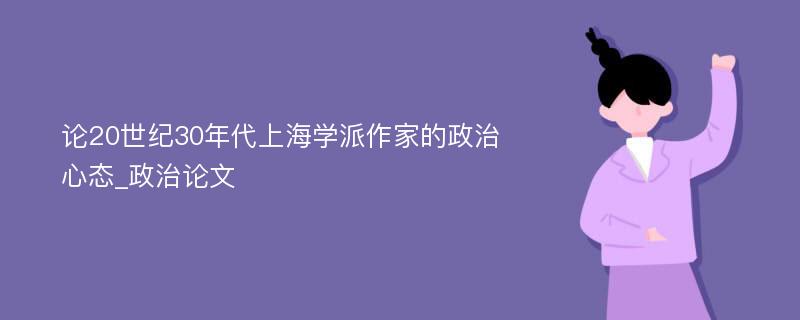
无根的飘荡——论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的政治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心态论文,作家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3-124-06
在20世纪30年代(注:中国文学史意义上的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1927年至1937年这一段时期。可参看李欧梵《三十年代文学(1927-1937)》:“(三十)‘年代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从1927-1937年这10年间的作品。”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海派作家的政治心态呈现出不断转变的迹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热潮中,海派作家一度表现出趋附左翼的政治热情,但在国民党右翼采取政治、军事上的高压政策后,海派作家迅即脱离了左翼政治,转向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试图“远离”与“规避”政治。本文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杜衡等为代表,考察了30年代海派作家政治心态的嬗变,力图揭示出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心理深层的政治倾向性。
一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世界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大力倡导下,中国文坛进入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期。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热潮影响下,30年代海派作家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倾向。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海派作家都曾一度热衷于政治,表现出政治上的“左”的倾向。施蛰存、杜衡等人曾加入过共青团和国民党,他们参加的是国民党左派,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他们都曾到共青团团部开过会,散发过革命传单,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在文艺领域,刘呐鸥、施蛰存等还创办了“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列著作《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编辑具有进步倾向的《无轨列车》半月刊和《新文艺》月刊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杜衡等30年代海派作家还都创作出了有“左”的倾向的“普罗小说”,如施蛰存的《阿秀》、《花》、《追》,杜衡的《机器沉默的时候》、《墙》,穆时英的《黑旋风》、《南北极》等。
30年代海派作家的一系列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与文学活动,似乎显示出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靠拢的所谓“转向”,当时的左翼文坛为此曾予以高度评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钱杏邨这样评价穆时英的小说:“作者的表现力量是够的,他能以发掘这一类人物的内心,用一种能适应的艺术的手法强烈的从阶级对比的描写上,把他们活生生地烘托出来。文字技术方面,作者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份子所不熟习的语汇。”[1]穆时英的小说在当时“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2]然而,我们不应该被30年代海派作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的“转向”,他们一度所呈现出的明显的“左”的倾向,并非出自他们内心对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和文学的认同,而是源于他们的趋时心态,源于他们政治认识上的幼稚。
30年代海派作家与“五四”作家不同,他们把目光直接投向了当时世界文学流行思潮,试图作一种文学的横向移植。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世界文学的新迹象,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坛上兴起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30年代海派作家所向往、所谈论的往往是新潮的、流行的话语,施蛰存曾说:“刘灿波喜欢文学和电影。文学方面,他喜欢的是所谓‘新兴文学’,‘尖端文学’。新兴文学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兴起的苏联文学。尖端文学的意义似乎广一点,除了苏联文学之外,还有新流派的资产阶级文学。他高兴谈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理论,也高兴谈佛洛伊德的性心理文艺分析。看电影,就谈德美苏三国电影导演的新手法。总之,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他每天都会滔滔不绝地谈一阵,我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2]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思潮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思潮,左翼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热烈响应,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如苏联、德国、奥地利、美国、英国、日本等,都有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世界各国的左翼文化团体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以便互相促进,进一步开展左翼文化运动。中国同样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流行思潮的影响。30年代,虽然有国民党右翼的政治高压,“左”倾话语还是成为权威话语和流行话语。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进步的左翼文艺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审美需要。一位研究者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30年代文学受众的迫切需求,认为30年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广大的读者层,由此形成30年代普遍的阅读心理”,即对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的关注、期待,“读者的普遍政治心理,在30年代的文学阅读中起了一种支配性的作用,这大大便利了左翼革命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造成了左翼革命文学的盛行”。由于读者对被查禁的革命文学有着旺盛的阅读要求,进步的左翼文学成为30年代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甚至“出现了盗印、翻版被禁革命文学书籍非常盛行的现象”。[3]对于30年代海派作家而言,“左翼”同样是流行思潮中的一种,是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支,正如施蛰存所说:“在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全世界研究苏联文学的人,都把它当作Modernist中间的一个LeftWing(左翼)。”[4](P180)海派作家更多地把“左翼”归入30年代的流行思潮,而不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比较左派的理论和苏联文学,我们不是用政治的观点看。而是把它当一种新的流派看。”[4](P179)因此,海派作家的“转向”,绝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是为了作品的畅销,这恰恰是其趋时心态的反映。《新文艺》就完全是受革命文学潮流的影响而转变办刊方向的,《新文艺》“介绍、创作新风格文学,颇获好评。出至第七期,革命文学声势逼人,同人不甘‘落伍’,遂宣告‘转向’,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4](P210-211)穆时英也曾对自己有“左”的倾向的小说作出过说明:“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5]也许施蛰存的陈述更有说服力:“为了实践文艺思想的‘转向’,我发表了《凤阳女》、《阿秀》、《花》,这几篇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但是,自己看一遍,也知道是失败了。从此,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还不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穆时英写的最初几篇小说,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尖子。但是,到后来就看出来了,他连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没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生活体验。”[2]这表明,他们的“转向”,只不过是为了新潮,为了趋时,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而已。
另一方面,30年代初期的海派作家还是具有浪漫主义理想色彩的青年,他们对政治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对政治还更多地抱有一种理想化的期待。30年代海派作家与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普遍对政治抱有幻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特别是国民党右翼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海派作家才意识到革命并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1927年3月,戴望舒、杜衡因参加团小组会议而被法捕房便衣逮捕,差点被军阀枪毙,后通过关系疏通,才得以释放。几天之后,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然而,“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4](P122)。施蛰存、戴望舒、杜衡都是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右派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他们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便都撤离学校,暂时隐避。施蛰存回到松江,戴望舒和杜衡也暂时回到杭州老家。不久,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扩大反共,戴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的危险,也赶到施蛰存家庭所在地松江来暂避风头。正是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种国民党的军事大屠杀,使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等人认识到了“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同时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而且“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4](P129)因此,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便脱离了党的关系,退出了实际的政治活动领域,虽然冯雪峰曾劝他们恢复党的关系也无济于事。施蛰存后来曾说过:“‘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葛利尔恰尔曾经说:‘所谓政党,是指大多数人牺牲,少数人掌权享受。’十八世纪的话,到今天仍然是真理。从此我不再搞政治。戴望舒、杜衡和我都是独生子,我们都不能牺牲的,所以我们都不搞政治了。”[4](P171)施蛰存、杜衡等人脱离政治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政治认识上的极端幼稚。
然而,这一段时期,军阀们忙于军事混战,还无暇顾及文化界的左翼倾向,所以国民党对左翼文艺并没有采取全面查禁的高压政策,对左翼作家还没有采取绑架、暗杀等卑劣手段。海派作家虽然由于对政治的恐惧不再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左翼文艺,当然,这可能更多地归因于海派作家的趋时心态,归因于他们把左翼也当作“现代派”中的一种来看待,正如上文所述,海派作家继续从事着左翼文艺活动,他们先后创办过《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等刊物,译介了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学书籍和文章,并创作了一批具有“普罗”倾向的文学,他们还创办了明显具有进步倾向的“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等。但是,到了1931年前后,国民党右派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左翼文艺的“危害性”,开始残酷镇压左翼文艺:“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左翼运动在知识界和学生界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国民党忽然意识到它的巨大的力量及影响,就认真镇压起来……为了杀一儆百,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在上海处决了胡也频和其他五位左联很有前途的年轻成员……。一九三二年,一个法西斯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文化剿匪战’,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政治警察和蓝衣社的秘密恐怖分子来执行。”[9]当然,从20年代末,国民党右翼就已经开始了对左翼文艺的查禁,如施蛰存等人创办的刊物、书店都先后遭到查禁、封闭:《文学工场》还没出版,即告流产;“第一线书店”因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国民党警察局一纸公文即告取消;《无轨列车》、《新文艺》都仅仅出版8期,因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查禁。但此时国民党右翼对文艺界的查禁还没有达到残酷镇压的程度,他们一旦意识到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便开始了对非右翼文艺的残酷压迫。正是因为国民党对左翼政治和左翼文艺的血腥镇压,海派作家出于对政治的担心和恐惧,最终走向规避政治:“从此以后,刘灿波不想再干文艺事业,他转而去从事电影,和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戴望舒回杭州去,筹划出国。杜衡住在上海,闭门译书。雪峰、蓬子都已迁居,暂时不通消息。徐霞村回北平去了。我回松江,仍旧当中学教师。”[2]穆时英、刘呐鸥、黑婴等海派作家“对革命变革失掉信心而转入悲观绝望”,“从左翼背叛出来”。[6]穆时英曾说:“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里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跑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7](P615-616)这意味着穆时英对左翼政治的怀疑,以至于背叛,从此,穆时英“闭口不谈政治,甚至对关于‘第三种人’那样的文艺论争,他也不感兴趣”。[8]
二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开始蒙受政治高压后,海派作家出于对政治的恐惧便有意规避了政治,特别是淡化了对左翼政治的趋附,而转向了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自由主义。
1932年,施蛰存开始筹编《现代》,明显走的是当时被称为“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道路。《现代》创办之时,3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使《现代》不得不具备“中间路线”的先天性,正如施蛰存所说: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看重了我。因为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办文艺刊物的经验。这就是我所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先天性,它不能不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文艺刊物。”[4](P27)在这种情况之下,《现代》不可能办成一个有鲜明的共同倾向的同人杂志。《现代》1932年5月1日创刊时,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宣称: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这种非同人性质的宣言,表明了编者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宽容的文化心态。施蛰存后来曾说:“《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4](P181)《现代》上所载文章,既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第三种人”的作品、京派作家的作品,因此,施蛰存主编的各期杂志,基本上体现了他在《创刊宣言》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精神。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海派作家大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论争,他们旗帜鲜明地在文艺领域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胡秋原在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一文,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胡秋原明确打出了“自由人”的旗帜,他声称:“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9]苏汶有感于左翼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种种限制,他在1932年7月《现代》1卷3期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表达了对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左翼作家的不满,提出了“第三种人”的概念。之后,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等30年代海派作家大多表明了对“第三种人”立场的认同。(注:关于30年代海派作家对“第三种人”立场的认同,可参看拙文《论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自由主义在三百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哲学自由主义。因此,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运动等。[10](P13-27)30年代海派作家所提出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概念虽然表面上是针对文艺领域的,要求文艺摆脱政治的束缚而自由发展,如胡秋原《真理之檄》、《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勿侵略文艺》,杜衡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等都是针对文艺的不自由而发的,但是,“所谓‘自由人’或‘第三种人’这种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的界分,而非‘文学性’的界分。”[11]在当时国民党右翼文艺和无产阶级左翼文艺的对峙中,大多数论争者都偏离了胡秋原、苏汶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原意。“自由人”、“第三种人”成为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作家的代名词,甚至苏汶本人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有时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无疑,“自由人”、“第三种人”成为30年代海派作家自由主义立场的载体。海派作家虽然一直都没有在政治领域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概念,但其自由主义立场却是不言而喻的。施蛰存后来曾谈及一部分海派作家的“组合型”思想模式,他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左派,但是左翼作家不承认我们。我们几个人,是把政治和文学分开的。文学上我们是自由主义。所以后来杜衡和左翼作家吵架,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论。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4](P181)虽然,我们承认这种“组合型”思想的存在,但是,以施蛰存、杜衡等为代表的30年代海派作家似乎还不能划到左翼作家的行列,他们仅仅是曾经一度热衷于左翼,其基本政治立场在30年代初无疑是自由主义。施蛰存、杜衡曾悲痛地说过,“人类用无量数的生命去换来的自由,现在又从新被剥夺了去”,然而,他们坚信,“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文学发展的绝对而且唯一的保障”,而“不相信独裁政治是世界必然的趋向”,他们甚至把自由主义精神作为“一切发展之基础”。对于美国,他们认为,“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以“指示出一个新文化的建设所必需的条件来”。[12]
出于对政治的恐惧,30年代海派作家不得不选择“远离”政治和“规避”政治。但“远离”政治和“规避”政治之后,他们必然要寻求另一种言说立场,以表达他们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意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知识分子肩负着无可推卸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使命,政治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命题,他们也就注定无法真正的远离政治,正如詹姆森所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13](P240)因此,30年代海派作家在当时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不可能真正地远离和规避政治,表面上与“左”倾政治和“右”倾政治无涉的自由主义便成为海派作家“远离”政治和“规避”政治之后的最好的选择。然而,自由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思潮,30年代海派作家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地脱离政治。
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并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思潮、制度或运动,基本上一直处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自由主义成为“五四”时代的中心话语之一。然而,当历史迈进革命的、“红色的”30年代时,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自由主义伴随着左翼作家对“五四”的清算和批判而日益暗淡。当时的文人桀犬所谓“自由主义在哭”的形容极为形象,也真切地表达了自由主义在30年代无地自由的尴尬处境。他认为,“今天还提起自由主义,这似乎会受人非笑的。在这世界上正有力地发展着的两端,那一边都不要这种空泛的口号,它已经和理想主义唯美主义一样被唾弃了”,“自由主义的确似乎走到末运的晚年”,所以,“自由主义躲在墙角里吞声哭”。[14]应该说,30年代海派作家在“远离”和“规避”政治(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转向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精神危机和非主流,注定了他们的落寞和动摇。“自由主义居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中间。它构建理想社会,批评现实制度,似乎永远不满足现状。但另一方面,它对渐进的改变比对激进的改变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如果现状在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自由主义往往会有较大的号召力。如果现实是令人沮丧,甚至令人憎恶的,自由主义往往会缺乏吸引力,无法与激进主义竞争。”[10](P261-262)而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经济衰败,社会现状是让人极端沮丧与绝望的,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两极对立,注定会成为总体现状难以令人满意的30年代的社会主题,所以,倡导激进革命的集体主义在30年代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强劲的吸引力,主张渐进变革的自由主义在30年代只能遭遇冷落,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慰藉。而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紧张及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更进一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海派作家也日益分化。随着杜衡1933年后与国民党右翼建立了密切关系、穆时英1934年加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事件的发生,大部分海派作家在30年代后期抛弃了岌岌可危的自由主义,而转向右翼。抗战爆发后,刘呐鸥、穆时英等海派作家竟至投靠汪精卫汉奸政府,(注:关于穆时英抗战时期的身份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汉奸,一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可参看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0页。)更无从谈起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仅仅成为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曾经披过的一件绚丽的衣衫。
总之,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倾向性,他们热衷过左翼,也钟情过自由主义,甚至迫于政治的高压而转向右翼。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一贯的主义,呈现出在无根中飘荡的政治心态特征。
标签:政治论文; 施蛰存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