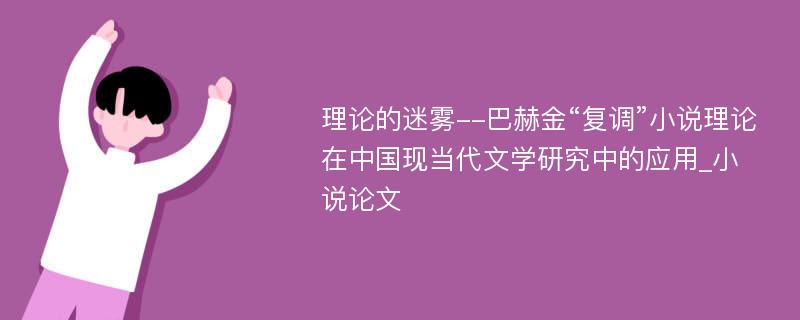
理论的迷雾——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理论论文,迷雾论文,中国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本只研究一位作家的书中,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概念:“复调”小说。阅读这本书,会让人想起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关于“经典何为”的言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①在现今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时时处处会与“复调”一词相遇。翻阅期刊杂志和研究专著,经常可以看到人们用“复调”来形容某位作家的创作特色,用“复调”来界说某部作品的艺术品格。这些论文著作中,有些作者明示自己是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运用,也就是说,他是在巴赫金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复调”一词的;有的作者则只是使用了“复调”一词,而没有明示该词的来源。在前一种情况中,很多文章虽然是在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但往往存在着理解的错位,存在着非创造性的误读。后一种情况则会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知名度甚高,对于读者来说,很容易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此一“复调”应该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有所关联,甚至会为它们划上等号。而这些没有明示“复调”一词来源的文章,却大多不是在巴赫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种情况应该属于理论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它同样造成对原理论的扭曲和误解。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形成了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复调”概念的迷雾。作为“身在此山中”之人,笔者显然也有着“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可能,但还是拟通过本文表达自己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一些理解②,同时就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运用问题做一点思考。 每一个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一个词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意思,但不可能包罗万象。而一个理论词汇,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相对更加固定了。所谓“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③,“是由观点、立论、推断等组成学说、知识体系”④。也许有人会说,理论的价值不正在它的涵盖力、它的丰富性、它的极大的思想容量吗?的确如此。但我们所说的理论的这些特性,都应该包容在特定理论的具体内涵体系中。理论是思想的高度精炼和浓缩,好比一块糖,溶解在水中还该有甜味。可如果投入的水太多,则让人感觉不到甜的味道,那么也就感觉不到糖的存在和意义了。理论是不可泛化的。如果一个理论概念什么都能包容,什么都能与之沾边,那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也许还有人会说,不是常有“理论的更新”这种说法吗?没错,深刻的理论能够激发人的思维,人们可以在一种理论的启发下引申出其他的光辉思想。但这变形了、更新了的思想必然要拥有一个新的概念来指称,不然就要引起理解的混乱了。 所谓文学研究中“复调”概念的泛化,是指一篇研究论文在比较宽泛和简单的意思上使用“复调”这个概念,用“复调”来指称与巴赫金界定过的“复调小说”不同的其他文学现象。“复调”作为一个舶来的文论词汇,若对它进行一番溯源可以发现,除了巴赫金,昆德拉和热奈特也曾在各自的文论中使用过这一概念。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将文体的复合以及同一主题下不同故事的并置称作“复调”⑤。热奈特则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从叙事视角的角度解读了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复调式”叙事⑥。他认为,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有着不同聚焦方式或者说是不同叙事视角的成功共存。应当说,在热奈特和昆德拉那里,“复调”一说是作者在其主要论述中伸出的一个小小的枝节,它的内涵实际上较为简单,不具有成体系的独立意义,也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赋予“复调”一词理论生命的是巴赫金。巴赫金不单先于昆德拉和热奈特从音乐术语中借用了“复调”一词,而且将其发展成一套拥有复杂、深邃的组成细部的理论学说(具体含义下文详述)。也就是说,在昆德拉和热奈特的笔下,“复调”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在巴赫金那里,“复调”早已“由隐喻增生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⑦了。 对“复调”一词在文学研究中的出现进行上述溯源后,热奈特、昆德拉似乎成了“复调”概念泛化的“始作俑者”。严格地说,这里面涉及翻译用词的问题,是译者都采用了中文“复调”来翻译原文中的对应物。笔者不通俄文和法文,无法考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小说的艺术》这三部著作中的“复调”原词本义为何。显然,巴赫金、热奈特和昆德拉的“复调”所指不同。巴赫金的“复调”要比热奈特、昆德拉的“复调”复杂、系统得多。然而,且不论翻译中的用词问题,在中国,自巴赫金的理论被介绍进来后,“复调”一词已成为一个经典化的理论概念。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收录的“复”字打头的七十八个词语中,没有和“复调”相关的词语⑧。一般性综合词典如《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该词,《现代汉语大词典》和1989年版的《辞海》开始收录“复调音乐”一词,1999年版的《辞海》增加了“复调小说”的条目⑨。专科词典如《世界诗学大辞典》、《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美学大辞典》、《西方文论关键词》⑩等则都收有“复调”这一词条。可见“复调”没有独立的日常用法,它是一个艺术领域的理论概念。且以上提及的所有“复调”条目的综合性或专科性词典中,编纂者都明确显示了巴赫金对这一概念的“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凡将某篇作品是“复调小说”作为主题论点的文章,都应该在巴赫金所界说的意义上使用“复调”概念。因为,再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复调”一词,会导致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独特意义被遮蔽和扭曲,使得“复调”一词的理论价值逐渐流失。再者,在巴赫金已经赋予“复调”一词在文学研究中棱角分明的理论站位之后,所有不在巴赫金的意思上使用“复调”概念的研究都容易被误解。这里举一个例子。严家炎著有《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文章认为,决定鲁迅小说成为复调小说的几个因素,是思想的复杂性、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叙事角度的自由变化这三个方面(11)。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他对“复调小说”下的定义。我们暂且不谈这定义本身是否过于宽泛,只先确定这是一个不同于巴赫金笔下“复调”的新定义。严教授没有声称自己是在巴赫金的意义上使用“复调”的概念,那么从道理上说,我们不能称其为误用。但是却有其他的研究者把这篇文章中的“复调”理解为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比如,吴晓东著有《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一文,是在巴赫金的意义上讨论“复调”话题的。文章开头即以严家炎的文章作为前人典例示出,将其置于自己的研究理路中(12)。这很容易带给人误解,以为严家炎的文章也是在巴赫金意义上使用“复调”概念的。不过,严家炎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确实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的影响,也提到了巴赫金的名字。把“复调”的渊源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并未在巴赫金评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上使用“复调”这个概念,这就不免让其他研究者眼花缭乱了。 在文学研究中,“复调”在巴赫金处已获得了经典性的理论意义。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轻易为某部作品或者某位作家贴上“复调”的标签。严格来说,当我们使用“复调”一词作为文章的主题论点时,除非有令人信服的新的界说,我们都应该在巴赫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而话又说回来,若真有新的想法,为防止概念的混乱,在“复调”一词已很大程度上成为巴赫金的“专利”之后,最好还是使用其他词汇来命名自己的论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绝大部分使用“复调”概念的研究者都通过对巴赫金相关理论的摘引和概括,直示自己是在巴赫金的意义上使用“复调”一词的。要证明一些研究者泛用、误用了巴赫金的概念,无疑需要说清楚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本来内涵。 这个问题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在各大词典中,这一术语已有了固定的释义。但是,人们对“复调”的理解和接受存有一定偏误。在众多的研究文章和词典条目中,学者们常常引用的是原著中这样一些语段(13):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14)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15)复调的任务,同一般类型小说里思想的单一性,是互不相容的。(16) 由这些语段,可以概括出“复调”一词比较宏观的意思。它是指作品中有不同声音的存在,且每一种声音具有同样充分的展示权利,这带来了作品思想的复杂性。然而,仅仅满足了上述条件,就能称一部小说为“复调小说”吗?那么,一部表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作品(假设作者赋予每个人物鲜明的特色、表现了每个人物人性的复杂)、一篇拥有不同叙事视角的小说(且作者赋予每个视角一样的展示权利)、一位富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的作家,都能与“复调”挂钩吗?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层层迈进地框定了“复调”的含义,在以上宏观性的较为抽象的界说之外,还有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论说: 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地反驳出自别人之口的对他们个人所作的类似定论。他们都深切感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17) 他总是让这些主人公与他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产生对话式的接触。在一部小说中,每一个表现出来的他人“真理”,必定又要被纳入到小说中所有其他主要主人公的对话式的视野之中。(18)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一切人一切物都应该互相熟识,互相了解,应该互相交往,面对面走到一起,并且要互相搭话。一切均应通过对话关系相互投射,相互辉映。(19)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别人对他的感知为背景。“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因此,主人公谈及自己的语言,是受到他人议论他的语言的不断影响才形成的。(20) 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具体描述还有很多,此处不可能全部摘引罗列。这里做一点概括和分析。 我认为,在巴赫金那里,作家如何表现人物是判定“复调”与否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人物的描写,不论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还是使用全知全能的视角,都必须把人物的内心所想全面、充沛地展示出来。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复调小说的核心。但不要以为只要表现了人物的自我意识就可以了。这种“自我意识”必须是多层次的:它包含人物对自己的了解、对他人的了解、对他人关于自己印象的了解这些层面。这种“自我意识”还应该是全盘“对话化”了的。因为每个人物的“自我意识”都包含了对他人意识的洞悉,所有人就处在了一种对话关系中,每一种“自我意识”就都处在与“他人意识”的论辩之中。人物预想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猜测这种评价的语调和涵义,从而做出应答。“复调”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人物“自我意识”的复调,人物间对话关系的复调性。很多作家虽然也表现人物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表现自我所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意识,不表现这种自我意识和他人对自己的意识之间的交流。那么,这种“自我意识”本质上还是单一的、封闭的、隔绝的,用巴赫金的话说,是被“客体化”了的。而复调型的艺术则不仅表现人物的自我意识,还表现不同人物的自我意识之间的交流,甚至人物意识和作者意识的交流——“主人公反对文学中把人看死的完成性”(21)。一个主人公心里所想的话题会出现在另一个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中,形成互相的激发与应答。这是复调小说的重要表征。 在复调小说中,“对话”是又一个核心。“自我意识”是容器,“对话”是其中的盛载物,同时还是各容器间的联通道。这里的“对话”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情节上的对话,不是在文本层面表现出来的戏剧性对话台词,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具有交谈沟通意向的存在。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因为人物的“自我意识”包蕴了众多的内容,甚至作者的叙述也作为众多“意识”中的一种而存在,整个小说于是呈现为一个对话的大舞台。“他把现实中完全分割开来的互不相通的那些思想和世界观,聚拢到一起并让它们互相争论。”(22)即使是写到人物内心独白的地方,对话的声音依然存在:“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一场交谈,尽管只有一个人在说话。还觉得出两个人谈得很激烈,因为每个对语都全力以赴地在应对无形的交谈者,暗示在自身之外存在一个没有说出的他人的对语。”(23)“对话渗透到每个词句中,激起两种声音的斗争和交替。”(24)如果我们对小说进行改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内心言说几乎都可以改为两个人甚至多个人的对话(巴赫金即做过这种工作)。人物说出其他人说过的话语,但为之加进了自己的情感态度。这就是巴赫金所定义的“双声语”(或者叫“双重声音”)。微小的“双声语”(比如人物的某一句话)就是一种“微型对话”,它们是“大型对话”的回声,和“大型对话”共同构成小说的“复调”形式。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建造的不是统一在作者意识下的相互绝缘的各人物意识,而是一些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即“大型对话”的展开。小说展现了人们的思考是如何包含着对自我的认识、对他人的认识以及对他人之于我的认识的回应。作者将这一复调性的过程描写出来,把这种思考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赋予了艺术的形式。在不同的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不同涵义的终极话题,揭示纷繁复杂的人性困境,但“对话”几乎是贯穿其所有小说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把以这种形式表达的思想提取、综合在一起,这思想的内容或许没有变化,但失去了“对话”的交锋,就失去了形式的美感,在巴赫金看来,就不是复调型的作品了。 从以上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复调小说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也许还未达到眉目清晰的地步,但应该是棱角分明的,它已足够为我们守住复调小说的准入底线了。简单地说,评价一部作品是不是复调小说,要看在这部小说出场的人物中,是否存在人物A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他/她对人物B的认识;是否存在人物A对人物B之于自己想法(作者在写人物B时写到)的洞悉以及他/她对人物B想法的回应。同样,人物B也是如此,处于同人物A或其他人物的“对话”之中。如果还需更严格一层,那么,小说中必须如巴赫金所说,存在“思想的人”。“他须是自己道理的载体,他须持有具有价值的(表现思想观点的)立场。如果一种感受或行为不求具有价值(赞同或反对),而仅求具有真实性(评价),那么,只能有最微弱的对话关系。”(25)对照着这样的描述,中国现当代小说中那些被研究者称为“复调”的作品,如鲁迅的《在酒楼上》等小说、莫言的《酒国》、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等等,就都失去复调小说的资格准入权了。 “复调”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个性的高度概括与界定。他无比妥帖、精妙地定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特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篇成功的作家作品论的论文。既然“复调”一词是巴赫金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量身订做的,我们动辄为其他作家穿上“复调”的外衣恐怕实在是不大合适。当然,这绝不是说“复调”理论就不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被高高在上地供奉着,也就失去了活力。比较合适的做法或许是从某一理论的某一点或某几点上生发自己的思考。一个含蕴丰富的理论是由众多启人思考的细部组成的。“思想的人”、“双声语”、“独白实体”、“隐性对话”等等这些就是“复调”理论的关键词,也是组成它的细部。文学的花园里不可能存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与巴赫金的“复调”之说全然吻合的小说,但某些在局部采用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手法的作品还是可能存在的。研究者从自己的审美体验出发,可以借用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某些细部来深化自己对作品的感悟。比如,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一文,就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巴赫金“双声语”的说法,对阿来的小说进行了不错的解读。黄书泉没有为《尘埃落定》贴上“复调”的标签,只说这部小说带有“复调小说的艺术风格”(26)。这样的做法是比较谨慎、恰切的。 不少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复调”正名,我认为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国内研究者眼中,“复调”已经从一个对某种艺术形式进行命名的指称上升为一种价值判断。有研究者说,“巴赫金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因此出现诸如“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反思我国当代小说”的说法,甚至出现“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的疑问(27)。这种“复调崇拜”本质上还是对“复调”理论的误解。这误解的“归罪”还不能都算在中国读者头上,巴赫金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处处隐含着巴赫金对现实意识形态的批判,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复调理论是对苏联这场悲剧的深刻反思,是对独白社会权威话语的有力抗争”(28)。在全书的不少地方,巴赫金抛开具体的小说文本不论,进行一些抽象的评说,借此表达逸出了文学理论范围的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看法。这就使全书洋溢着一种价值判定的激情,使论说处处染上了褒贬的色彩。比如,他在论述狂欢化体裁的特征时,用“狂欢处世态度”来形容这种体裁的精神。巴赫金认为,狂欢处世态度的意义正在于它对片面的严肃性、单一意义和教条主义的削弱。这样的论断使“复调”理论的建构从一种事实陈述滑向一种价值判断。本来,巴赫金是从“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29)的角度建构“复调”理论的。在“结束语”中,他也说道,“复调小说的出现,并不能取消也丝毫不会限制独白小说(包括自传体小说、历史小说、风习小说及史诗小说等等)进一步的卓有成效的发展”(30)。在理性上,巴赫金应该是知道“艺术形式”、“艺术思维”和“艺术态度”、“艺术立场”的区别的。他所倡导的是复调式、对话式的艺术创作态度,而独白形式的小说并不意味着作者的艺术态度也是独白的,只有“独白的艺术态度”才是被完全否定的。但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独白形式的小说即反映了作者的独白式艺术态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形式的小说才是一种复调式艺术态度的反映。在某些部分,巴赫金几乎在艺术形式与艺术态度、艺术立场之间划上了等号。例如他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新的艺术立场上。是这种立场使他拓展了艺术视觉的视野,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艺术视角来观察人。”(31)“总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32)而事实上,采用独白方式结构作品的作家,他们的艺术态度、艺术立场也可以是复调的、对话的。每一位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作家在写作之时必然都经历了各种思想的碰撞交锋,也都采取了一种对话的态度。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确定的视角、独白的形式来编织作品,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对话式的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作品的全部内容上。只能说,在众多具有复调式艺术态度的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赋予这种对话式的艺术思维一种表现形式,使之得以人格化、戏剧化。 巴赫金在论说中的偶尔偏激和越界,被中国的一些研究者附上了理解的重音。人们很容易忽视“复调”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名称,没有注意到“复调小说”首先是一个中立的事实判断,而把着眼点放在巴赫金激情洋溢的价值论说上。这样一来,就误解了“复调”一词的真正属性,把理解的重心放在了艺术态度、思想倾向的层面。所以,国内的一些文学研究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复杂性”、“多元化”、“多样性”等意义层面使用“复调”一词——这些词代表的都是优秀小说的普遍特质——而忽视、排挤了“复调”在形式上的具体意义。相对于“独白”,“复调”拥有了绝对的价值优势,被打上“复调”印记的作品被认为是好的作品。其实,在文学创作中,作品形式是独白还是复调,并不构成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独白形式的小说也有它富有成果的表现。“复调”并非一个优秀作品应该具有的标准,它只是众多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中的一种。“复调”当然具有对世界存在和人类思想的多元性的肯定这样的意义,但这样的意义内容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艺术表现方式展现出来。 “诗学”谈论的是一种“建筑术”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艺术创作的方法和规律问题,侧重的是作品的形式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开篇“作者的话”中,巴赫金即明确地说过他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拥有的“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所开创的新的“艺术形式”称作“复调”的。形式和内容不可截然二分,形式当然具有内容的意义。但同样的思想内容,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形式也具有独立于思想内容的自身的意义。就拿“复调”来说,它所具有的形式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方面,不妨从法国学者托多洛夫的解析中获得启示。他认为,巴赫金全部思想的统一性在于“坚定地相信人际是构成人的要素”(33)。巴赫金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揭开人际秘密上的重要意义。“人的实现只能来自外部,通过别人的眼睛完成。”(34)我的意识无法从内部了解我的生我的死我的身体整体。这时候,他人就是自我的必要补充。他人成为自己的构成要素,是“自我之镜”。“‘超人’的确存在——但不是尼采意义上的高于别人。我是他人的超人,就像他人是我的超人一样:我处于他的外部(我的‘外在地位’),所以我有把他看作整体的优越。但同时,我不能为所欲为仿佛没有其他人的存在:知道他人也能够看见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的地位。”(35)这种人际的存在也就是一种对话的存在。 在巴赫金看来,世界的本质是对话的,一个人,只要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他的所思所想就附着他人的意识,包含着对外部世界刺激的回应。自我的树立是以他人为参照的。这种对人际的理解具有生成形式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把这种人际的关系赋予了一种艺术形式,也就是“复调小说”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几乎没有不紧张地盯着他人话语察言观色的语言。”(36)“没有单纯判断的语言,没有只讲客体的语言,没有背靠背的单纯指物的语言;只有交际中的语言,与他人语言接触对话的语言,谈论别人话语的语言,发向他人话语的语言。”(37)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采用的这种复调形式对表现“人的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38)具有突出的效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不论人物之间的显在对话和人物自我意识的内在对话表达了对世界何样的理解,也不论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和塑造的人物具有何种主题内蕴,作家所采用的复调式的表现形式首先就具有发现人际秘密的意义——它表现了人和人之间的语言和意识是怎样发生相互的碰撞、激发和回应的。这就是“复调”这一形式本身的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雏形本出版于1929年,经作者长期增补、修改,才以现在的样貌在1963年问世。1961年,巴赫金写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这篇修改提纲,其中说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些发现在形式方面的蕴涵,比具体易变的思想内容要更深刻、更凝炼、更具普遍性。各个平等意识的内容会变化,思想要变换,对话的内容要更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发现的艺术地认识人类世界的新形式却依然不变”(39)。这就更加明确了“复调”理论的本质属性。就像意识流小说提供了一种表现人类变化多端、稍纵即逝的内心想法的艺术模式,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是将自我同他人意识的人际交互、将思维感知的对话特征铸型为“复调小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并不鲜见的研究倾向是,对主题内蕴的分析总是多于对作品形式的分析,对作品内容的关注总是处于对创作方法的关注之上。即便不少文章也关注到创作手法、叙事方式这些形式方面的话题,但对艺术形式的分析总是作为揭示思想意义的准备而存在的。这就轻视了审美形式本身具有的意义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理应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发。但惯有思维方式的存在,还是造成了我们对这一理论的宽泛领会和使用偏误。研究者生搬硬套和肆意延展理论概念的现象并不鲜见。而“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40)。在文学研究中,既存理论的价值在于对思维方式的训练。我们不该直接将之拿来当工具使用,而是应通过理论对思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提高对作品的品鉴、解析能力,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其实,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诞生也是源自研究者对常识问题的细致思考与概括提炼。巴赫金说:“我们生活中的实际语言,充满了他人的话。有的话,我们把它完全同自己的语言融合到一起,已经忘记是出自谁口了。有的话,我们认为有权威性,拿来补充自己语言的不足。最后还有一种他人语言,我们要附加给它我们自己的意图——不同的或敌对的意图。”(41)巴赫金由日常生活中各种“旁敲侧击”的话语、“话里带刺”的语言联想到它们在文学中的存在,由此提炼出“双声语”的概念,又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细致阅读中结合了对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人的思维方式特点的思考,由此发明了“复调小说”的理论。可见,理论是来自生活的,文学理论来自对作品的深切感悟,这感悟同时也浸透着评论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我们不必怀有过深的“理论焦虑”,换句话说,每一篇融入了自己独特理解和深刻思考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具备理论的质素。 ①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我们都是经由汉译本理解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某种程度上而言,每一个靠译本来讨论这一理论的人都很难谈得上是该理论的真正理解者。不过既然平台相同,对汉译本中“复调”概念的理解还是可以讨论的。在阅读中,笔者比较了大陆主要的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巴赫金全集》中收录的即是此版)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这两个译本在具体字句上虽有所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文学研究界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误用与译本差异没有关系。 ③《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 ④《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7页。 ⑤详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6页。 ⑥详见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45页。 ⑦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⑧《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3—344页。 ⑨分别见《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页“復”字条和第九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複”字条;《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第1354页;《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248页。 ⑩分别见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页;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145页。 (11)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148页。 (12)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3)如张炜婷《论董启章〈体育时期〉的复调小说精神》,载《长城》2012年第4期;王西强《复调叙事和叙事解构:〈酒国〉里的虚实》,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杨贤稳《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两种复调小说比较——以鲁迅的〈孤独者〉和余华的〈兄弟〉为例》,载《安徽文学》2007年第6期;李遇春《对话与交响——论长篇小说〈秦腔〉的复调特征》,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等。这些论文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至少一条本注释后摘录的三句原文。 (14)(15)(16)(17)(18)(19)(20)(21)(22)(23)(24)(29)(30)(31)(32)(36)(37)(38)(4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0页,第29页,第120页,第97页,第116页,第247页,第284页,第96、97页,第137页,第271页,第118页,第24页,第364页,第363页,第103页,第279页,第324页,第363页,第268页。 (25)(39)《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第374页。 (26)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7)张晓玥:《复调诗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28)缑广飞:《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哲学意蕴》,载《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 (33)(34)(35)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7页,第88页,第90页。 (40)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