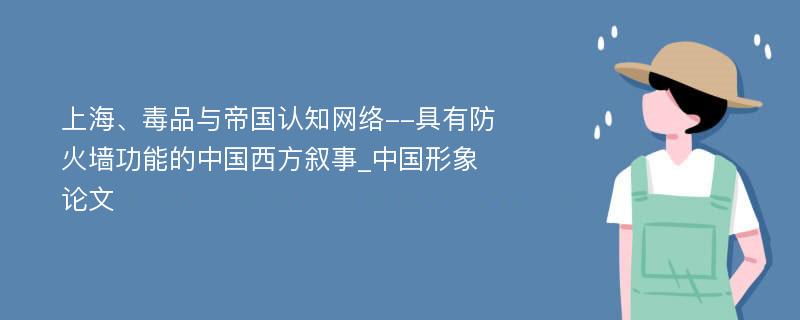
Shanghai、毒品与帝国认知网络——带有防火墙功能的西方之中国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毒品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防火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0)03-0097-12
一、Shanghai、毒品、中国城:诱惑与恐惧
(一)Shanghai:神秘而恐怖的东方都市
Shanghai,我们在此标示的首先是“动词”的含义,其中隐含的又是作为“地域名词”的两个主要文化意象。
在俚语中,Shanghai①可作为动词用,表示:(1)用麻醉剂或烈性酒使(男子)失去知觉后,将男子绑架去当水手,如be Shanghaied onto a foreign ship,即表示“被劫持到外国船上当水手”;(2)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强行拘留,诱骗或强迫某人做某事,如Shanghai sb.into doing sth.
与之相关连的名词“Shanghai”,展示的意象亦有两个:(1)神秘(美国水手跑进酒吧间——诱惑);(2)恐惧(大街小巷被人抓住,服毒迷昏或绑架到船上——不安全感)。
“Shanghai”(上海)的这两种文化意象正好展示出西方世界(尤其是殖民帝国时期)对东方中国的认知印象:既向往(神秘的东方,诱惑无处不在),又恐慌(无理性、罪恶的、阴暗的东方)。此乃赛义德东方主义式的“东方”,西方殖民文化语境中的东方(Orient)。
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存在着两个世界:洋人的租界,这是西方人的上海;中国人的弄堂世界,这是产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环境。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弄堂世界,就是欧美世界或好莱坞电影里的Chinatown(中国城)——神秘莫测、诱惑不断、毒品遍布、绑架不绝,总之罪恶丛生、糟糕异常。西方殖民者相信,上海的这两个世界不可沟通,租界是租界,弄堂是弄堂。上海的公园即曾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此带有极端殖民主义色彩的牌子在1928年被打了下来,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影视剧里看到当时的情景。外国人的生活活动范围仅限于对他们来说安全的租界;而身处弄堂世界里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倒是想光顾法租界的咖啡馆,英租界的书店、电影院。
上海是一个神秘而恐怖的东方都市,这是不少西方作家笔下的上海形象。在此,我们试以两位作家为例,一个是对上海不甚了解的法国作家马尔罗,一个是童年时代生长在上海的英国作家巴拉德。
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小说《人类的境遇》(1933),出版后在读者群中产生过轰动的震撼力,获得过当年度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被评论界称为“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上海。所谓“人类的境遇”,就是人在地狱中的境遇或命运,这个地狱就在“中国上海”。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一小撮革命党正在进行谋杀活动,遭到政府的无情镇压。上海的景象是世上最黑暗的,是一座地狱:天空总是阴云密布,贫困、肮脏、混乱、疯狂、恐怖、仇恨、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一只只乌黑的笼子里装着砍下来的头颅,头发上还滴着雨水。我们找不到材料证明马尔罗到过1927年的上海②。他表现的是在他自己所能想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即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描述的那样:“一大群人戴着锁链,他们每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外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类命运的图景。”③
马尔罗在《人类的境遇》中,无论是关于地理参照还是小说人物描写,其所使用的中国的真实材料是比较贫乏的。正如一个研究马尔罗的法国学者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所说的那样,马尔罗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人造中国,他通过一些贫乏且陈旧的异国情调的符号,“创造了中国景象的一个概貌、范型”,“中国街巷的声音背景也是由一些尤其老套的符号立体构成的,……清脆的骨牌声,街巷上极有特色的木屐木鞋声,汽车喇叭、鞭炮、锣鼓、钹、二胡或笛声构成的喧嚣——还有‘永垂不朽的蚊虫’的或调节风扇的嗡嗡声,这些作为必需的声音,构成了马尔罗对中国夜晚的描写中的景象和伪真实。”同样,马尔罗在关于中国人的品性描写方面,也基本上遵循了西方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那套陈词滥调,以至于可以通过这本小说,编一部真正的关于中国的“成见大词典”④。把马尔罗介绍给我们的中国学者更清晰地指出:“必须承认,马尔罗写中国革命的小说几乎没有写出一个真实的革命者,也没有写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他笔下的中国革命者和中国人民的形象与实际生活相距实在很远。”⑤
马尔罗如此展示他的人造中国场景,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缺乏对中国的直观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部小说中最想构建的不是关于1927年中国真实场景的重现(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从地理层面上),而是一种关于人类悲剧处境的气氛。因此,《人类的境遇》中的中国上海具有相当的讽喻意义⑥。
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中国革命,对于马尔罗来说,是人对抗生存荒诞性的最好例证,因而将地狱的地点选择在东方中国上海,上海则成为他想象的一个恐怖区域。马尔罗借此展示他关于人类生存荒诞性的思考,这样,所有中国的革命,只不过是供他思考人类在地狱中境遇的一个题材。根据后殖民批评理论,中国上海只不过是马尔罗心目中的一个他者形象。这样一个他者是西方的对立面,甚至构成了西方的异端⑦。
与马尔罗想象性的上海经验不同,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的童年时代是在中国上海度过的,他对现实中国有着清晰的感知⑧。他以其在上海生活的童年记忆写成自传小说《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1984),获英国文学之最高奖项布克奖提名,被誉为“英国描写战争最好的小说”,最终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小说以一个住在上海英租界的英国男孩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男孩吉姆和他的父母失散并流落街头,后又被关入日军拘留营,历经磨难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在战争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对巴拉德来说,他曾经生活过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在他心目中是神秘而充满诱惑力的。“上海这个荒淫无耻、魅力十足的城市比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城市都令人兴奋刺激。”它能吸引包容一切,即便是战争,也“总是给上海带来活力。”当然,《太阳帝国》中对上海的描述,主要不是一幅幅乌托邦(Utopia)式的虚构空间,更多的是地狱般的恐慌,展示出西方人心目中如福柯所说的那种异托邦(Hetero-topia)场景。
马尔罗《人类的境遇》也是异托邦想象模式的极致表现,书中所描绘的20年代中国上海,因贫困肮脏、疯狂仇恨,俨然呈现一片片人间地狱场景。巴拉德笔下的上海描述,其异托邦思维模式异常突出。这座三四十年代东方都市繁华景象背后的丑陋,一如《人类的境遇》所描述的地狱场景,令人战栗厌恶、心生恐怖:满街游荡的酒吧女郎,沿街而坐的要饭叫化子,露出的伤口和畸形的肢体惨不忍睹;夜总会、赌场一字排开,地痞匪徒充塞其间,流氓阿飞当街斗殴,影院门口站着200多个穿中世纪服装的驼背;背着大小包裹难民的涌入,无数的苦力、人力车夫,愈发使街道拥挤不堪,还有乡下女人发出的阵阵汗臭,街上为非作歹的巡捕;以及外滩悬首示众的血淋淋的人头,站台现场上演的国民党密探的砍头示众,鲜血四溅,恐怖非常。
黄埔江边的情景同样恐怖。穷得无钱埋葬亲人的中国人,在棺材上堆上纸花,从送葬码头丢到江中任其漂流。这些棺材连带尸体落潮时被带走,涨潮时又漂回到江边。肿胀的尸体和聚积在码头油污斑斑木桩周围的纸花,及丢弃的垃圾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恐怖的“水上花园”。
战时的上海愈发恐怖,街头死尸遍地,断臂残腿隐现于废墟之中。江上船只的残骸夹杂着漂浮的死尸。上海周围乡下的场景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俨然一场无尽的噩梦。中国士兵的尸体横躺路边或漂浮在运河里,战壕里成百上千死去的士兵挨个坐着。战场外荒地中遍布隆起的坟堆,腐烂的棺材横埂在路旁,发黄的骷髅任凭雨水冲刷。干涸的稻田一片沉寂,乡下人的逃难使上海近郊的村落杳无人烟。而俘虏营因微薄的口粮竟吸引了中国叫化子盘踞门口,甚至有些人铤而走险爬入营房。国民党军队攻打共产党盘踞的村庄时炮弹横飞,尸体像劈柴一样堆积。苍蝇蚊子群飞臭气熏天,死人的血液流入运河滋润稻田。这是一个异常恐怖的世界,上海成了“一颗承担着中国死亡脉搏的丑陋心脏。”⑨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指出贯穿于巴拉德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是“混乱不堪的生活,饥荒,骚乱和死亡”。小说的中心意象“非常凄惨”,而且“小说是以儿童死亡的意象开始和结尾的,描写的是父母把装着他们孩子的小棺材抛到江浪中。吉姆原先在远距离外看到的这一意象,后来突然变成了对他自身生命的威胁。”⑩所以史景迁认为巴拉德属于那类对中国甚感悲观的作家。
巴拉德在《太阳帝国》中对中国人思想和性格的描述基本上遵循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固有成见,据此也可以编一本关于中国的“成见大词典”。他对并无多少了解的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大发议论,重复着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作者对三四十年代上海场景的描写有其真实处,但着重渲染可怕时代的恐怖场景,正反映了作者看待中国时的异托邦思维模式。这种认识中国的观念程式不时迎合着西方人关于上海的主导意象:神秘而恐怖。
(二)中华帝国:毒品——鸦片
被称为帝国主义诗人的英国人吉卜林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相交。”赛义德《东方学》等表明: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把“真实”的东方(East——地理概念)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Orient——文化概念,是西方人的虚构,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
这样用新奇和偏见的眼光看东方的极端时代,是在19世纪。就在这个世纪里,东、西方的差异完全成了优劣等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是理性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大地,似乎所有的愚昧与苦难都是为了等待西方殖民者的最后到来,西方殖民者想象自己是上帝一样的拯救者,“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西方带来了理性与文明,照亮了匍匐在黑暗大地上的无数可怜的扭曲的面孔,以及他们在历史深处拖长了的身影。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偏见中,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傲慢(11)。
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19世纪代表东方本质的,是中华帝国,而中华帝国的核心象征便是鸦片。鸦片凝聚着所有的东方特性、道德堕落与感官诱惑、邪恶而残酷、神秘而怪异的体验,令人向往又令人恐惧,可能给人天堂般的幸福感,也可能成为死神的使者引你堕入地狱。”(12)在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德·昆西(1785-1859)的忏悔录《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中,描述同时让他幸福也使他痛苦的鸦片吸食经历时,他也是在描述他对东方与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吸食鸦片给德·昆西带来的痛苦,有时是由一些稀奇古怪和可怕的噩梦构成的,噩梦的来源则是东方和东方人(一个马来人)。在德·昆西眼里,中国是一个无生命力的国度,中国人是非常低能的民族,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他声称“我宁愿同疯子或野兽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在中国生活。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极具成见和偏见的英国作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正是忠实地展现英帝国殖民心态的自白书。德·昆西的儿子霍拉蒂奥参加侵华英军,1842年8月27日死于中国(13)。
可以说19世纪,在西方有关中国人的种种恶习中,对他们印象尤深的是中国人嗜吸鸦片成瘾。那些描写中国城的作品中,都会刻意描写一个狭小、昏暗、窒息的房间内,许多中国人或蹲或躺,神志恍惚吸食鸦片的场景。狄更斯《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儒勒·凡尔纳《环球八十天》以及马克·吐温《苦行记》里的中国人,就都被描写成吸毒成瘾,完全被毒品搞昏头的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城首要的罪恶就是吸食鸦片。
(三)中国城与中国城小说
在那些怀有种族偏见的西方人眼里,毒品虽然就是东方中国,但毕竟离自己遥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臆想里的恐怖。可是,与自己同处一个城市的华人群体,他们倒是危险的。中国城(Chinatown)是毒品的集散地、罪恶的滋生处,危害着(殖民)帝国的安全,冲击着白人世界(文明世界)的道德底线与秩序规范。于是西方作家(尤其是英、美、澳作家)通过变幻莫测又千篇一律的中国叙事——尤其是“中国城小说”,呈现着这样的恐惧与不安。同时通过这种虚幻的中国叙事,更是有意识维护着西方殖民帝国的认知网络,任何一种危害帝国安全的因素,都被想象夸大在各式各样的中国叙事之中,通过文本及影视艺术、舞台剧,不断提醒、刺激、强化着帝国居民(白人)的神经,形成坚固的防火墙,阻挡来自异域的危及帝国认知网络安全的“病毒”。时至今日,这堵防火墙(尽管是想象性的)依然存在,不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制造障碍,制造跨文化交往的恐慌与不安,即所谓“中国威胁论”。
一般所谓“中国城”小说,多描写犯罪与历险故事,作品中总会出现一些中国恶棍,试图绑架侮辱白人妇女、诱惑白人男性,甚至征服全世界。最后,白人英雄出现,化险为夷,消灭了中国歹徒。恐怖解除,世界重见光明。此类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偏见。
居住在英国伦敦的中国人集中在莱姆豪斯(Limehouse)。莱姆豪斯是英格兰伦敦东区陶尔哈姆莱茨自治市邻近的一个地区。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以水手旅店、教堂和酒店众多为地方特色,散布着不少华人餐馆。那儿也是伦敦最大的华人聚居地,流动性也最大,就像纽约和旧金山的中国城。因此,莱姆豪斯后来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诸如北京、南京、广州、明街之类的街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里的华人区曾遭受毁灭性的轰炸,破坏严重,但莱姆豪斯依然能在英国人心中勾起生动的形象,并始终在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笔下以一种奇异的构思方式存在着,如关于鸦片馆和点煤气的神话等。
有一位伦敦的中学校长罗宾逊小姐,就曾两次指控莱姆豪斯地区的中国佬勾引英国未成年少女,激起了不少人的公愤。“莱姆豪斯的引诱”成了华人区罪恶的代名词。一名曾在莱姆豪斯里当过三年警察的侦探被派往那里展开调查,事后他认为,“中国佬要是与一位英国姑娘亲近上的话,就不会引诱她卖淫,只会娶她,待她好”。1920年,一位《新闻晚报》的记者经过调查也下结论说,做华人的妻子是一种好逸恶劳的生活,许多白人姑娘正是因此被引诱到中国城去的,因为伦敦东区的妇女没有一个像“中国佬张三的妻子或管家”那么悠闲的,丈夫甚至亲自下厨房。当时嫁给华人的大多数是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来自外省的、“声名狼藉的”英国姑娘,出身较好的妇女宁愿自己的丈夫是白人。由此可见,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认为中国人属于劣等人的看法(14)。
一般人认为是伦敦东区的华人提供了鸦片或其他毒品。同样,一些人也把白人在“中国城”里闲逛看成是东方的罪恶把白人给迷住了。毒品的魔力也波及到伦敦演艺界,由此大英帝国臣民笼罩于一片毒品恐惧之中。1918-1922年发生了一系列大肆渲染的毒品恐慌案。几个夜总会舞女和合唱团成员的死亡,均与毒品有关。据当时的小报报道,这些死亡都是白人女性在受了黑人和黄种人的诱惑之后服用毒品和纵欲的结果。这些小报还宣称,这些事件绝非偶然,而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在羞辱白人女性并进一步瓦解大英帝国权力中心的道德和现实统治。在这一时间中,一个狡诈的“中国人”一手操纵了鸦片和可卡因的走私组织。他被冠以“卓越的张”的称号。他在1924年被捕,以私藏毒品罪遣送回中国,但张并未就此消失。据说他在船只到达中国之前跳海逃亡,并在欧洲其他地方重操旧业。人们认为张应对数十年来全欧的毒品死亡负责。有一位作家如此描述张:“张具有一种诡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有人说是催眠术),这种力量能使妇女吸可卡因。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黄种人想败坏白人女性。”一些作家,如我们在下文要论及的萨克斯·罗默,创造了一些像“卓越的张”一样狡诈的中国罪犯傅满楚。他们不只是在英国阴谋经营毒品,而且还将上流社会的贵族女士、女演员和那些柔弱的男性诱骗到邪恶的毒品世界中(15)。欧美作家通过不断书写觉醒的亚洲对于白人男子、白人女子气质的种种威胁,延续及强化着这一焦虑。而这种带有历史与现实感的焦虑,正是试图维护帝国认知网络安全运行的心理渴求。
二、帝国认知网络的建构与运行
(一)西方殖民帝国关于中国认知网络的建构与维护
在西方殖民帝国对中国的认知网络上,中国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沉溺于鸦片梦幻中的最具有东方性的非现实的国度,野蛮而残酷,堕落又愚昧,诱人且恐怖。这就是关于中国的一般知识,也是一种话语权力结构,构成了帝国殖民体系的认识论基础。
大英帝国的战略家们(由传教士、驻华商务、教育和外交机构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企图创造一整套与虚构作品(如中国城故事)一致的特定事实,并依靠对于整体知识的幻觉(假作真时真亦假)来维系它们。而来自中国的真实的知识混杂其中,会引发对网络信息质量的质疑,其结果是污染甚或颠覆大英帝国的认知网络,最终可能使帝国殖民体系难于幸免。于是,制止这种“污染”(展示出的也是对文化、种族混杂的焦虑与隐忧),对维系帝国认知网络的统一性(健康运转)至为重要。整个19世纪中后期,就在大英帝国将中国操控于股掌之中时,种族混杂(华人移民大量增加)、中国复仇(16),以及俄国在东亚的大战略(与大英帝国争夺亚洲),都像鬼魂般威胁侵扰着英国的在华利益,并为流行小说中“卓越的张”和傅满楚等“东方幽灵”式的噩梦提供了想象的基础(17)。
与之相连的另一问题是帝国认知网络的空间分布。为了使帝国殖民意识更广泛地传播,让所有阶层的人都“了如指掌”,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实属必要。于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新期刊、附有插图的报纸与儿童读物、电影胶片、戏剧舞台等,传播着以帝国意识为主题的小说,也包括中国城小说。
1907年,英国作家尼姆(L.E.Neame)发表《英殖民地面临的亚洲危险》(The Asiatic Danger in the Colonies)一书,这是一本讨论亚洲人可能侵吞整个英国殖民地的专著(18)。他在书里忧心忡忡地预言:“任何国家一旦把大门对着东方敞开,一旦大批接受亚洲人,其所承受的包袱只会越来越沉重。”这样一种对东方亚洲人的忧心与恐慌在当时以“黄祸”恐惧最为典型。
在一些欧洲思想家看来,皮肤的颜色与智力和道德水准有关系,“肤色愈深,智力愈差”。康德就认为东方人不具有道德和审美能力,而与之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奥格斯特·施罗泽则明确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笨的民族。这样一种带有种族偏见的理论当时在欧洲很有市场。在他们眼中,中国的愚昧落后、道德低劣,要依靠欧洲文明才能获得教化与救助,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人掌握了欧洲技术的秘密与武器装备之后,在与白人的战争中,黄种人残忍、冷漠,对死亡无动于衷的性格就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于是来自“黄祸”的恐惧与日俱增。
“黄祸”恐惧与种族主义偏见紧密相连。这种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比较典型地呈现在英澳作家,如盖伊·布思比(Guy Boothby,1867-1905)、威廉·卡尔顿·道(William Carlton Dawe)、玛丽·冈特(Mary Gaunt,1861-1942)等人的笔下。
这几位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作品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偏见,东方主义特征比比皆是。那些身处中国土地上的英国人或西方人均无所不能,而中国人则是些难以同化的他者或异类,凡是投合西方文化标准道德规范的、肯与西方合作的就受到颂扬,否则就是不能接受的异类。
这种以消极方式处理中国人形象的做法反映出不少作家持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们在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下,将中国和中国人边缘化并降低到一种劣等地位,以衬托英国人或西方人的“英雄”形象。这种故事模式得以风行,也是为了投合英国民众的阅读期待。比如,玛丽·冈特在中国旅行过,她所看到的并不都是中国人恶劣的一面。不过丑化中国人,贬低有色人种为时尚所趋,而她的写作目标是瞄准英国市场。把中国人写得很糟糕,会迎合一些读者的兴趣,借此赚钱恐怕不难,她自己对此并不讳言:“我写作就是为了挣钱。”正因有此大众心理为基础,黄祸恐怖与种族偏见得以充斥每一个角落,甚至形成某种文化心理积淀,在不同时期都会听到它的回声。
(二)萨克斯·罗默笔下的恶魔式中国佬形象(19)
玛丽·冈特为投合英国民众的阅读期待而塑造丑恶中国人的写作策略,与英美作家萨克斯·罗默创造傅满楚这样一个恶魔式中国佬形象相似。
傅满楚形象之所以被塑造成“黄祸”的化身,因为他符合当时通行的中国观以及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但是这一形象并不能代表罗默自己关于中国人的真正看法。在1938年的一次采访中,罗默泄漏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反驳布勒·哈特创造的阿新形象(20)。他说“我完全不同意布勒·哈特的结论……中国人是个诚实的民族,这就是西方人认为他神秘的原因……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拥有平衡、和谐,这正是我们日渐失去的东西”(21)。采访中罗默还谈到了另一个神秘、高贵的中国人Fong Wah,也许他才是傅满楚的真正原型。Fong Wah在唐人街开餐馆和杂货铺,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和爱戴。很多年以后罗默才知道他也是一名堂会的官员。Fong Wah待罗默非常友善,他经常向罗默讲述自己早年的生活。Fong Wah的宠物——獴,也立刻让我们联想到了傅满楚的獴,它们都是神秘而诡异的,瞪着圆圆的眼睛,匍匐在主人的身旁。在Fong Wah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某天,他送给罗默一把精致的匕首后,突然消失了……
罗默心目中的中国人是诚信的、友善的,而傅满楚形象的主调却是邪恶与恐惧。如果说这仅仅是罗默的艺术想象,那么这样的傅满楚形象为什么会在西方社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一个人的想象只能写成一本书,大众共同的想象才能使一本书变成畅销书。因而,傅满楚是迎合大众想象的创作结果,是那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际遇使得中国人形象被如此的妖魔化、丑恶化。
20世纪初,傅满楚这样一个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人知的恶魔典型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人作为“黄祸”的形象,已经在西方的文学想象中逐渐固定下来。如果说义和团是本土中国人代表的“黄祸”,那傅满楚则是西方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可以说后者是西方文学中对中国人形象最大也是最坏的“贡献”。这些傅满楚式的野蛮的中国佬,在西方人看来,丑陋肮脏、阴险狡猾、麻木残忍:“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可见这是中国“黄祸”威胁西方文明的象征。
罗默在首部小说《狡诈的傅满楚博士》里把傅满楚描述为亚洲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代表人物。他将东方所有“邪恶”的智慧全部集中在傅满楚一人身上,并让他随心所欲地调动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而且,傅满楚的长相也可谓东西合璧:西方莎士比亚的额头,象征着才能超群者的智慧;想象中撒旦的面孔,暗指邪恶狰狞而又法力无穷;猫一样的细长眼,这是西方人对东方人外貌特征的典型想象,见出傅满楚这个人物本身所被赋予的丰富的隐喻含义。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既带有本土特征,又具有异国情调的形象,是黄祸观念具体化的一幅心像,迎合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20年风行一时的排华之风。
在罗默笔下,傅满楚首先是一个残忍、狡诈的恶魔。他领导着东方民族的秘密组织,杀人、绑票、贩毒、吸毒、赌博、斗殴无恶不作,意在“打破世界均衡”, “梦想建立全世界的黄色帝国”,他们是来自东方的梦魇,来自地狱的恶魔,“黄色的威胁笼罩在伦敦的上空,笼罩在大英帝国的上空,笼罩在文明世界的上空”(22)。
为了实现他的“邪恶目标”,即征服白人世界,建立黄色帝国,傅满楚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敌手。任何阻碍这一伟大进程的人都会被毫不留情地除去。大英帝国派驻远东的殖民官、著名的旅行家、熟悉远东的牧师甚至是美国总统,“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对傅满楚不利的资讯,只有奇迹可以帮助其逃脱死亡的命运”(23)。他杀害泄密者,谋害对抗者,祸及无辜者,凡是对抗、妨碍傅满楚计划的人都会落得凄惨的下场。皮特里认为傅满楚的残忍完全来自他的民族和种族。“在傅满楚的民族,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会把成百上千的不想要的女婴随手扔到枯井里。傅满楚正是这个冷漠、残忍的民族刺激下的犯罪天才。”(24)
傅满楚既是危险邪恶的,也是法力无边的。他的强大更来自于那不可思议的天才。在罗默笔下,傅满楚可谓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知全能的天才,而且已经成功地入侵大英帝国的中心伦敦,使得英国人很少有安全感。尽管史密斯、皮特里痛恨他、仇视他,立志消灭他,但根本无计可施。他们无奈地承认傅满洲是“撒旦式的天才”、“恶魔天使长”(25)。傅满楚“拥有三个天才的大脑,是已知世界的最邪恶的、最可怕的存在……他熟练地掌握一切大学可以教授的所有科学与技能,同时又熟知所有大学无从知晓的科学与技能”(26),傅满楚的武器库里品种繁多,威力无穷。不仅有蝎子、蜘蛛、毒蛇等颇具东方色彩的武器,更有西方生物学、病理学、化学等最新发展而衍生的高科技武器。两者结合使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成为那片神秘土地——中国所产生的最不可捉摸的人物。傅满楚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并在其中进行大量的科学试验,研制毒品和新的杀人机器。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中国是最遥远的东方,也是最神秘的东方。那儿有难以计数的财富,又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威胁。从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西方人就开始勾勒一个怪诞、奇异、阴森恐怖的东方。傅满楚来自古老中国最神秘的地方——思藩(Si-Fan)(27),自然弥漫着最神秘的气息。伴随傅满楚出现的是阴森的场景,若有若无的黄雾,浓郁神秘的东方气息。他如幽灵似的无所不在,从伦敦到加勒比海,从纽约到缅甸,他的足迹遍布世界,但很少有人能够觅其行踪,窥其真容。在伦敦、在纽约,他隐匿在中国城里。那是一个黑暗、幽闭的世界,是在西方文明、法制管辖外的另一个独立的世界。傅满楚就藏匿在这样神秘、黑暗的中国城里,这儿没有西方世界的力量和秩序,有的只是华人的统治以及衍生其中的各种神秘、邪恶而见不得人的勾当。赌博、抽鸦片、绑架、杀人,这就是神秘、恐怖的东方的缩影。在这儿傅满楚策划、发动所有的袭击。
因此,傅满楚成了笼罩在西方社会的不散的阴云。傅满楚及其领导的庞大的犯罪组织对整个白人种族和文明世界带来了巨大威胁。他们身上都带有不可更改的东方性。他们相貌丑陋,衣饰古怪,匿藏、滋长于阴森、杂乱,见不得光的黑暗角落,过着腐朽、堕落的生活。男人们沉迷堕落,流连于地下赌馆、酒馆、鸦片馆。女人们妖冶、放荡,既让人向往,又使人恐惧。傅满楚神秘、恐怖,狡猾而又残忍,是来自神秘东方的最大威胁。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力大无穷、野蛮残忍,带着先天的嗜血性,残忍的执行谋杀、绑架等犯罪行为。
与傅满楚对抗的是大英帝国驻缅甸的殖民官、著名的侦探奈兰德·史密斯。他瘦高、坚毅,有着古铜色的肌肤与铁一样冷峻的目光,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责任感。一出场他就庄严地宣称: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我千里迢迢从缅甸赶回伦敦,绝不仅仅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白色种族的利益。我相信我们种族能否生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这次的行动能否成功。”(28)
对于史密斯来说,与傅满楚的对抗从来不是简单的中英对抗,而是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较量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种族和文明的存亡。在系列小说中,傅满楚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心脏地带,阴谋策划一次次的袭击,他的计划一次比一次周全,手段一次比一次诡异,但总在最后关头被史密斯粉碎。罗默既提醒着西方社会来自东方的威胁,又坚信“高人一等”的西方社会一定能够战胜“黄祸”,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且,在罗默笔下,傅满楚不只是“黄祸的化身”,他还体现了为数众多的黄种人、黑人,以及棕色皮肤人蜂拥入西方后,对整个白人种族和文明世界所带来的威胁。这一形象比较复杂。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他颓废堕落、鸦片成瘾、狡诈残忍、老于世故、傲慢、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也无动于衷;同时,又聪明、勤劳、有教养、风度翩翩、言而有信、超然离群。但是,傅满楚又和传统的中国统治阶级以及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通晓现代西方科技,又掌握着隐秘的东方知识,这两者结合使他有着超自然的能力, “是那片神秘土地——中国——所产生的最不可捉摸的人物”。正是这种东西方的组合使傅满楚比欧洲人幻想中的东方野蛮人入侵更可怕,也比廉价的华工在欧美的泛滥更有威胁力,因为这种东西方知识的融合蕴涵着极大能量,它使推翻西方、破坏帝国结构乃至全球白人统治成为可能。
(三)西方殖民帝国认知网络的运行:形象的传播与再创作
萨克斯·罗默创造的傅满楚形象,典型地展现出西方关于东方中国的那种神秘而恐怖的心理状态,而这一形象的多元化传播也体现出西方殖民心态下关于中国的认知网络的运行轨迹。
傅满楚形象的独特性吸引大众媒体的广泛参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均加入了傅满楚形象的传播与再创作,范围之广、形式之多样,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令人惊讶的。傅满楚系列作品问世之初主要以报纸、杂志连载的方式在西方世界进行广泛传播,《柯立叶》(Collier)、《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新杂志》(The New Magazine)等三十余种杂志相继刊载了傅满楚系列故事。一部傅满楚小说往往被分为几十个故事,每周一期,持续刊载半年到一年。在那个年代,不接触傅满楚系列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借助大众媒体的广泛参与,傅满楚形象从一个文学形象变成了一个媒体形象,更加无所不在。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传播方式出现以后,傅满楚的形象更加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西方观众眼前。
傅满楚广播剧的制作和播出单位都是世界著名的媒体集团,听众遍及全国甚至欧美。傅满楚广播剧多安排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且多次重播,收听人群非常庞大,傅满楚形象产生的广泛影响可想而知。傅满楚形象最早出现在荧屏上是1923年,那还是默片时代。英国Stoll电影公司拍摄了首部傅满楚系列电影《傅满楚博士的秘密》,一年后,Stoll公司又摄制了《傅满楚博士的秘密Ⅱ》,均非常轰动。当时伦敦的每一个地铁站都张贴着巨大的傅满楚电影海报。在大笨钟的上空,天气阴霾,乌云密布,隐约中透出一个中国人的脸。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露出不怀好意、阴森森的笑。电影剧照还被印成了系列卡片,广泛派发。此后,好莱坞电影公司相继出品的傅满楚系列作品使得傅满楚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恶魔形象。1929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拍摄了首部有声的傅满楚系列电影《神秘的傅满楚博士》,随后两年间又相继出品了《傅满楚博士的归来》(1930)、《龙的女儿》(1931)。傅满楚成了侦探电影中最为著名的角色。1930年,在派拉蒙电影公司影展上,电影公司还特意设计了一个短剧,由两位著名的侦探福尔摩斯侦探和费洛·范斯(Philo Vance)侦探联手对付傅满楚(2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梅高美电影公司(MGM)先后拍摄了《傅满楚的面具》、《傅满楚的鼓》和《傅满楚的反攻》等三部电影。由于好莱坞的“世界电影工厂”的广泛影响力,傅满楚系列电影在英、法、德、意、西等主要西方国家公映,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1942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抗议,好莱坞暂停傅满楚系列电影的拍摄。但傅满楚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抹灭。
新中国建立后,伴随着“红色威胁论”(30)的兴起,西方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拍摄傅满楚系列作品的热潮。194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率先制作了两部电视短剧——“红桃皇后”和“恐怖的咳嗽”(取材自《傅满楚博士的归来》)。1952年Herles公司拍摄了《扎亚的吻》(选自《神秘的傅满楚博士》)。1955-1956年,好莱坞电视公司拍摄了一系列十三集的傅满楚电视短剧,在美国全国播放,仅1956年间就在纽约重播三次。1965-1969年,英国Harry Alan Towers电影公司连续推出了五部电影《傅满楚的脸》、《傅满楚的新娘》、《傅满楚的报复》、《傅满楚的血》和《傅满楚的城堡》。关于傅满楚题材的电影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1980年最后一部《傅满楚的奸计》中,家喻户晓的傅满楚才被电影安排“死去”。但傅满楚形象始终深藏在西方人的心里。当1999年土生土长于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间谍时,一家美国报纸所用的标题就叫做“傅满楚复活”。
傅满楚形象自诞生以来,至少在几十部影视作品中出现,在欧美世界反复公映,受众面非常广。电影、电视以其声、光、电合一的独特魅力,形象再现了那个身穿长袍、面似骷髅、目光如炬的傅满楚形象。在阴森的气氛里,在恐怖的音乐中,傅满楚一次次地伸出了留着长指甲的枯爪,一次次将观众拉入死一般幻境。在恐惧、挣扎、反抗之间,观众经历了一场生与死、善与恶的搏斗。在与傅满楚的较量中,深切地感受到致命的威胁以及危机过后的酣畅淋漓,在幻想的世界里成就了白种人的英雄史诗。傅满楚恶魔形象是如此的深入人心。2000年,西班牙导演亚历斯·艾格列斯还曾计划开拍千禧版本的《傅满楚》电影,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型。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傅满楚形象的受众面。借助新媒体形式特有的生动性、形象性,更加渲染、强化了观众业已形成的傅满楚形象。傅满楚形象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形象。
总之,经过一系列广播系列剧和好莱坞影片等多媒体的传播,傅满楚很快变成了一个在西方家喻户晓的名字,并把一整套关于中国人的严刑、无情、狡诈和凶恶的陈腐框框传遍了大半个世界。无知的英美儿童也从关于傅满楚的电影和故事中获得了关于华人品性的概念。拿好莱坞制片宣传材料中的话来讲,傅满楚“手指的每一次挑动都具有威胁,眉毛的每一次挑动都预示着凶兆,每一刹那的斜眼都阴含着恐怖”(31)。在傅满楚系列电影的宣传海报上,也总是傅满楚的人像高高矗立,白人男女主角被傅满楚的巨影吓得缩成一团。傅满楚令西方世界憎恨不已而又防不胜防。他如此邪恶,以至于不得不定期地被杀死;而又具有如此神秘的异乎寻常的能力,以至于他总是奇迹般地得以在下一集的时候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西方人看来,傅满楚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的罪恶。
在欧美世界妇孺皆知的傅满楚形象,甚至也波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以傅满楚形象为原型的茶壶、笔筒、火柴、糖果种类繁多,一种罕见的兰科植物因为垂着类似傅满楚胡须的枝条而被命名为傅满楚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苏格兰等地甚至还有傅满楚主题餐厅、傅满楚研究会。傅满楚形象极大地影响着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傅满楚这个精心打造的脸谱化形象,成为好莱坞刻画东方恶人的原型人物。这个“中国恶魔”的隐秘、诡诈,他活动的帮会特征,以及作恶手段的离奇古怪,都被好莱坞反复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楚博士”这个原型人物,鲜有偏离和创造(32)。
三、知识与权力:维护帝国秩序的防火墙
萨克斯·罗默臆想中塑造的傅满楚形象,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从传播学角度讲,极好地承担着传播西方殖民帝国意识的作用。这样一种关于中国的叙事,包括文本与影像资料,是一种关于中国的知识,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关于中国的话语权力。
20世纪法国大哲学家、思想家福柯通过阐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消解了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纯洁性”。在“五月风暴”之后,他开始关注知识的话语与社会的机制尤其是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权力与话语的不可分离。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展示权力。这样看来,西方之中国叙事的东方主义话语,首先确定了中国作为西方的对立面“他者”的形象。而构筑文化他者的真正意义是把握与控制他者,这个把握包括知识上的理解和解释,以及权力意义上的控制与征服(33)。
可以说西方文化正是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凭借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构筑了中国这一他者形象。照赛义德的说法,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34)。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正是永恒的他者。无论西方文化感到得意或是失意,需要自我批判或自我确认的时候,中国形象这一“他者”都会自然浮现出来,帮助西方文化找到自我。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无所谓真实或虚构。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在中国形象的延续和变化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现实中国的变化,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力量关系的变化。
那种丑陋、狡猾、残忍、爱报复的“中国形象原型”,反复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里,诗人、哲学家、传教士、商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背景,有不同的动机与方法,但他们表现的中国人形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特定的中国人形象并不是某个文本的发明,而是该时代社会文化内在结构的产物,体现并维护着那个时代的权力关系。任何个别表述都受制于这个整体,这是所谓的话语的非主体化力量,任何一个人,哪怕再有想象力、个性与独特的思考都无法摆脱这种话语的控制,只能作为一个侧面重新安排已有素材,参与既定话语的生产(35)。中国人形象已经变成一种话语,除非你不涉及它,只要你参与表述,就一定得在既定的话语体制和策略下进行。
比较历史话语中的中国人形象与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楚形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话语的中国形象的强大规训力。正如罗默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的:傅满楚的狡猾是整个东方民族狡猾的总和,傅满楚的残忍来自其惯于杀害女婴的民族,傅满楚的嗜食鸦片来自其奇怪的民族性。作者一再地暗示我们,傅满楚形象、傅满楚集团中的中国人形象并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独特创造,而是承袭了由来已久的“中国形象”原形。在傅满楚的长袍、秃脑袋、长指甲、猪辫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以叶名琛为代表的满大人的影子,在唐人街的赌场里我们立刻可以找到鸦片瘾君子、赌徒以及形形色色卑鄙下流的中国人,在傅满楚的犯罪计划里,我们又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狡猾与残忍。总之,罗默笔下的傅满楚形象是对已有的“中国形象原型”的继承,即使有些许的调整,也只能在傅满楚性格的某些侧面加入个人的理解,罗默无力颠覆传统的中国人形象。
因此,西方的中国叙事,既展示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观,同时也在制造或维护着西方的中国认知,这是一道维护帝国秩序正常运转的防火墙,维护着西方的帝国心态与观念视角。任何试图冲击西方帝国秩序的外来知识档案(来自东方的真实的知识信息),均被其规避、解码、重新编码,以增强帝国认知网络系统的免疫力。免疫力之强,西方殖民帝国时代的中国叙事“功莫大焉”。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文化语境中,这道“防火墙”成了阻碍东西方跨文化交往的障碍之“墙”。这堵“墙”能否拆除,拆除到什么程度,以近年来的国际形势、外交关系,以及文化交流情形观之,尚难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与预测。2006年3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BBC国际台)曾公布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中国明显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因为它有杰出的经济成就,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经济成功的势头。其中,对中国看法最消极的国家是日本,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军力增长的国家也是日本。从受访者年龄层次上看,年轻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对中国发展持积极态度,从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上看,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积极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受较少教育的人则对中国发展持负面看法。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也公布了一项全球民意调查,亦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敬重的前五个国家之一。在26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获得的正面评价率为42%,负面评价率为32%。对中国评价最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对中国持负面评价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在9个接受调查的欧洲国家中,有6个国家认为中国形象负面。
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其本身也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文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态和核心的价值观。过多负面的国家形象,也说明那堵“防火墙”仍在不断发挥作用。在这方面,通过持续开展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这堵阻碍东西方正常交往的“防火墙”,以实现人类平等、自由、进步的良好愿望。
注释:
①与此相关的有一个名词:Shanghaier,即源出于19世纪时使用强迫手段裹挟水手远航东方尤指上海。
②根据相关传记材料,马尔罗在写作《人类的境遇》期间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极短。他在印度支那居住期间曾于1925年4月到香港去了几天;后来在其环球旅途中,于1931年9月在上海和广州待了几天。正是在这第二次到达中国期间,马尔罗产生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构思及小说的题目。参见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马尔罗〈人类境遇〉中的“中国式”和中国性》,载《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③马尔罗在哲学思想上受帕斯卡尔、尼采、施本格勒等人的影响,认为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将要死亡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境遇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马尔罗自己就是一个不断地行动的人。
④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马尔罗〈人类境遇〉中的“中国式”和中国性》,载《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主编),第151-153页。
⑤柳鸣九:《马尔罗研究》(编选者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⑥然而,法国读者相信1927年的中国只可能像马尔罗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在他们眼中,马尔罗是中国革命的知情人。马尔罗在《人类的境遇》中对上海的描述,看上去更像是西贡,后者是他所更了解的区域。
⑦对此,澳大利亚史学家杰弗里·布雷尼教授谈及历史上澳大利亚对中国人的态度时,曾指出“即便没有中国人,澳大利亚人也会把他们发明出来。每个社会都需要替罪羊,需要打击的对象。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几乎把中国人作为衡量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之下,他们觉得自己还挺不错。”转引自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⑧1930年在中国上海出生的英国作家巴拉德是当时英国驻上海外交官之子,1942-45年间被日军拘禁在龙华,后于1946年才回到英国。他的自传性短篇故事《死亡时代》(the Dead Time,1977),自传性小说《太阳帝国》及其续篇自传体故事集《妇女的仁慈》(The Kindness of Women,1991)均以其少年时代中国上海的生活及战时经历为素材。
⑨J.G.Ballard:the Kindness of Women,1991,p328.
⑩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7-128页。
(11)(12)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99页。
(13)葛桂录:《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眼里的中国形象》,载《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4)[英]潘琳:《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陈定平、陈广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98-99页。
(15)[美]何伟亚:《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楚》(The Archive State and the Fear of Pollution:From the Opium Wars to Fu-Manchu),何鲤译,载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一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7-88页。笔者写作本文,受到该文启发,谨致谢忱。
(16)根据种族中心主义的“投射”理论,一个民族会利用“妄想狂的投射”方式,把本民族不能接受的欲望归罪于其他民族或他者。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遭人仇视,被视为不可接受的他者。在他们的臆想中,中国人在中国曾受到西方人的虐待,因此要以恐怖行为对白人实行报复。傅满楚就是如影子一样尾随西方人的报复典型。这种对中国人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直到新千年,还不断在“中国威胁论”里得到呈现。
(17)[美]何伟亚:《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楚》载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一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0-102页。
(18)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坛,也曾出现过一批以中国人侵略澳大利亚为主题的“侵略小说”,如《黄种还是白种?公元1908年的种族大战》(1888)、《黄潮》(1895)等。这些小说既是“东方主义”思维观念的产物,也表现了澳大利亚政治话语中的恐外症或恐华症。参见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1-43页。
(19)本部分对萨克斯·罗默笔下傅满楚形象的阐释,笔者指导的研究生刘艳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提供了初步的解读文字。
(20)阿新是19世纪下半叶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国人形象。1870年,美国作家布勒·哈特创作了这个狡猾、贪财的中国人形象。
(21)Pipe Dreams:The Birth of Fu Manchu,The Manchester Empire News,Sunday January 30,1938.
(22)Sax Rohmer,The Hand of Fu Manchu,From Four Complete Classics by Sax Rohmer,Castle,1983,p1、p9、p40.
(23)The Return of DR.Fu Manchu,From Four Complete Classics by Sax Rohmer,Castle,1983,p135.
(24)The Return of DR.Fu Manchu,From Four Complete Classics by Sax Rohmer,Castle,1983,p174.
(25)The Return of DR.Fu Manchu,From Four Complete Classics by Sax Rohmer,Castle ,1983,p93、 p103.
(26)The Insidious DR.Fu Manchu,New York:Mcbride,Nast,1913,ChapterⅡ,p9.
(27)思藩即西藏,也有人称之为香格里拉,是西方社会了解得最少、最神秘的地方。
(28)Sax Rohmer,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NewYork:Mcbride,Nast,1913,Chapter I,p2.
(29)费洛·范斯(Philo Vance),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人物。许多专家学者论及美国推理文学黄金时期的兴起之议题时,必定会追溯至1926年的《The Benson Murder Case》。这本由范斯出马破奇案的作品,销售成绩之好让人诧异,据说该书还帮助出版商Scribners渡过经济大萧条的难关,免于负债的窘况。
(30)“红色威胁”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观臆想。受到传统中国形象以及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社会总是担心中国会发动对其的毁灭性打击。
(31)哈罗德·伊萨克斯(H.R.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32)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楚形象》(刘艳著,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7年),对这一形象在欧美世界产生轰动的原因,作了较详细的分析。
(33)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34)[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页。
(35)[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相关观点见“绪论”与“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