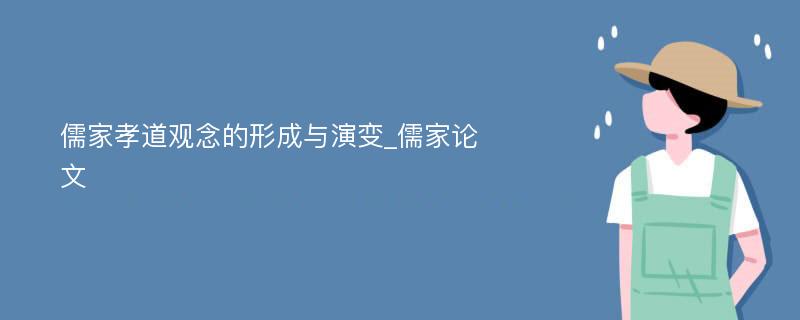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孝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历来有注重孝道的传统。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孝道仍然得到了全世界华人的认同,被视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质。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孝道的演进就不难发现,孝道与人类其他道德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正因为儒家孝道观是一种反映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具有生命的,不断流转变化的学说,所以它也一定能适应今天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一、古代宗法宗族社会与祖先崇拜
远古的宗法宗族社会里,初民的爱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儒家经典《礼记·郊特牲》解释敬祖的意义时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祖先的开拓之功。《礼记·坊记》:“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当时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孝道,但尊敬、爱戴、崇拜本族长者、老者的情感已经发生。在宗族社会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的传统宗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崇拜统一的祖先,是使某一血缘团体保持一致,共同对外的基础。有了本氏族内部的团结,才能联络其他氏族团体,结成巩固联盟。
关于夏王朝的宗教生活,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黻冕。”(《论语·泰伯》)众所周知,孔子对鬼神的存在持存疑态度。但是他对大禹崇敬祖先,自己菲食恶衣,却隆重丰盈地大搞祭祀活动大加赞美。研究殷墟的甲骨卜辞,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宗教祭祀活动的发达。殷人心目中的最高神是“上帝”,上帝左右着世间的风雨云雷,生死祸福。殷王几乎是事无巨细,样样贞问于上帝。但是根据陈梦家的研究,“卜辞中并无明显的祭祀上帝的记录”(《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7页),因为殷人认为凡人不能直接与上帝交通。殷王死后“宾于帝”,灵魂随侍于帝廷,时王只能通过祭祖这条唯一渠道沟通上帝,所以殷王祭祖虔诚、隆重、频繁。殷代宗教祭祀祖先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以活人作为牺牲,其野蛮性令人发指。《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通观夏、殷两代的宗教,显然还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处处带有原始宗教的痕迹。殷人虔信鬼神,祭祀频繁,重鬼治而轻人治,尚未形成“孝道”的宗教伦理。对民众单纯依靠鬼神的威慑力量来增加统治者的尊严。在宗法体系中,突出了人际关系中上下等级“尊尊”的一面,而忽视了血缘关系中“亲亲”的一面。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以周代殷,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不止是王朝的替代,而是社会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自西周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宗法分封制度。配合政治制度的变革,周公在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使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向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为之增加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指出:德与孝是周代统治阶级的道德纲领,“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是周代伦理的特色。(《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从周代开始,明确提出了孝的观念。最为可靠的证据是出土的周代金文,在西周的青铜器中,孝字已经大量出现。《三代吉金文存》中孝字共104见,《西周金文大系考释》中36见。除去两书中重复的部分,共有讲孝的铭文112则。(查国昌:《西周“孝”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二期)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尚书》、《周易》以及稍后的《诗经》,其中关于孝的论述,更是比比旨是。可见孝道在周代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了。
在西周金文中,与孝字连用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追”字和“享”字。如:“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锡永寿。”(《邿遗殷》)“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匄眉寿。”(《王孙逸者钟》)“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诸老,用祈匄眉寿”。(《殳季良父壶》)“显孝于神”。(《克鼎》)从“享孝”、“追孝”等字的用法看,金文中的孝字,主要还是针对故去的祖先的。但是在大力提倡祖先崇拜的同时,周人的孝道观也增加了生活伦理的内容,即在颂扬祖先功德,祈求祖灵佑护的同时,孝道中也出现了“孝养”的观念。《尚书·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这段话是周公对殷族遗民的训诫之词,要求他们自食其力,专心农事,农事之余则牵着牛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以便孝敬、赡养自己的父母兄长。
二、宗法家族社会的出现与儒家孝道观的形成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社会剧烈的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自三代以来一直作为唯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法性宗教开始土崩瓦解了,并严重影响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孝道,出现了儿子杀老子,臣子杀国君的现象,《左传》中有很多记载,说明西周时期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若想使其保存下去,并能规范社会上下层的行动,必须对它进行新的论证。
在重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的过程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后世,儒家的孝道伦理,才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儒家孝道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孝道根据的转变——从宗教到哲学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传统宗教瓦解的时代,重建道德伦理,必须首先重建人们的信仰。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并且“约礼入仁”用仁学的观点重新解释了西周的“礼”。他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果离开了仁爱之心,礼就会成为单纯的“钟鼓”、“玉帛”之类的虚文。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怎么才能做到“爱人”呢?“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此原则来看到孝道,那么孝敬父母就不再是因为社会的外在压力,鬼神的约束,而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要求和道德自觉。例如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己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期可已矣。”孔子回答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的依据不再是对祖先灵魂的畏惧或者祈求,而是对父母抚育之恩的怀念。幼儿三年方可脱离父母之怀衽,因此也要用守孝三年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曾参是孔子学生中最早彻悟“忠恕之道”的人,也是孝道伦理最忠诚的实践者。他用“忠恕之道”作为孝道的哲学基础,指出:“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同上)人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人若想在自己晚年时得到子女的孝养,就必须孝养自己的父母。所以他又说:“善必自内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只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孝道,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尽心竭力,和颜悦色,无微不至。他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曾子不只是把孝道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义务,而是当做不断自我反思的精神修炼过程。
在儒家后学中,思孟学派以继承发扬孔子学说“内圣”的一面而著称。在孝道观上,子思、孟子进行了人性论的证明。子思在《中庸》里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具体表现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也就是说,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孝敬自己,首先要孝敬自己的父亲;要想使臣下忠于自己,首先要忠于长上。孝道不仅出于血缘亲情,也符合于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逻辑。在这里,儒家使孝道完成了从天国到人间的转化,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自我意识进行反思的人生哲学。
(二)孝道内容的转变——从追孝到养孝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作为生活伦理的孝行,作了系统的论证。孔子指出,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爱亲。春秋以后,个体家庭相对独立,养亲逐渐成为孝道的主要内容。孔子对应如何养亲作了细致的说明。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人应当努力地劳作,竭尽全力使父母过上好的生活。“孟懿子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父母关心着每一个子女的健康,要让他们少操心。“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子女也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为政》)除了要对父母尽各种孝养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父母有敬爱之心。“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子,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同上)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孝子养亲,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发自至情至爱,应毕恭毕敬,和颜悦色。
儒家的亚圣孟子活动于战国中期,他对孝道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如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幸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不仅要养亲,还要尊亲,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这种尊敬,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爱慕,“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同上)孝亲还必须守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为了保证家族香火不断,祭祀有时,孟子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除了祭祀祖先,怀念祖先,更重要的是把祖先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上述论述,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孝道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奠定了基础。
《礼记》是产生于战国后期的一本儒家礼书,对中国宗法社会通行的各种礼仪进行了详备的记述。《礼记·祭统》说:“是故孝子事亲有三事,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礼记》各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说明了孝子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父母所尽的礼仪。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父母,如:“凡为人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不争。”(《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不言老。”(同上)“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同上)与父母交往要和颜悦色,“孝子之有深爱也,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礼记·祭义》)除了在生活上关怀,更重要的是对待父母要有敬爱之情。“子曰:‘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礼记·坊记》)《礼记·内则》又引曾子的话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孝养父母的关键是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愉悦,人格得到尊重,心情保持愉快。
三、封建专制社会与“以孝治天下”
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相对稳定,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反思,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只有儒家学说最适合为宗法家族制度服务。因此,儒家的孝道观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最核心的统治思想。汉代的统治者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国家设立一个官职“孝廉”,由有孝行的人担任。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成书于汉初的《孝经》,集中论证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如果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较,《孝经》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孝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从“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义——“以孝治天下”。《孝经》的绝大多数章节,不是讲“事于亲”,而是讲“事于君”的。在不足二千的文字中,“治”字出现了11次,“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孝治章》说:“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套用《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其中贯穿的精神,则是《天子章》中以爱敬之心治天下的原则。《圣治章》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儒家理想的圣人之治,是将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统治者以爱子女之心爱护百姓,而百姓则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长上。即使长上对下民有些严厉的措施,那也不过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出发点还是一片爱心。对于君主专制社会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候,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统统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了。
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之间既存在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也存在着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压迫。在这两方面,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孝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亲亲”率“尊尊”,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孝道,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哲学,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例如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了论证“天下没有不是的君”,就说出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最后竟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
四、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孝道观的复归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地加速了中国宗法家族社会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也必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历史地讲,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孝道观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当时有些提法和口号过激,考虑到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和最终取得的巨大效果,我们今天都应当给予宽容的评价。但是问题是:儒家的孝道观真的就是糟粕一团,一无可取之处吗?历史的回答显然不是如此,这主要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家庭本身在当代是不可取代和消亡的。近代以来,不少激进的思想家提出过消灭家庭的口号。如康有为曾提出:“去家界为天民”;辛亥革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搞过消灭家庭的实验。可经过了各种试验及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终于发现,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婚姻,在当代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还必须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所具有的生育功能、生活互助功能、培养教育功能、精神慰藉功能是不能由其他社会组织代替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思想界对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因而西方社会流行的亲情淡薄、家庭破裂、老人晚景凄凉、青少年犯罪率高的问题也多发于我国。如何治疗这一顽固的世纪病?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更是应当认真地检讨前圣先哲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资源,发现儒家孝道观中的普世性价值,将其发扬光大。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首先,儒家的孝道,反映了人类世代繁演过程中家庭“抚幼养老”的自然属性。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非常特型化的生命属性,即个体在其幼年时期和晚年时期,都是十分脆弱的,需要群体的呵护。当出现了家庭以后,养老的任务就逐渐成为家庭的责任。人类的这种“反哺”行为,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灵。知恩报恩作为生命历程中不同阶级的互补性,也就成了孝道伦理最为深刻的社会依据。儒家经典《诗经》中保留了许多感念父母抚育之恩的诗篇。“父兮生我,母兮掬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小雅·蓼莪》)这里“报”的概念,可以说是人类个体生命自我保护的伦理表现,只有通过这种代际之间的“反哺”、“报恩”,人类的种群才能够继续繁演。从这种意义上讲,孝道是可以与人类共始终的。
其次,儒家的孝道反映了人类家庭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方面的作用。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以父子关系为基轴的链式家庭,已经让位给了以夫妻关系为基轴的核心家庭。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使“抚幼养老”的许多工作可以转移到社会的方面。但是,幼儿园再完善的生活、教育设备,也代替不了父爱和母爱,自幼缺乏家庭温暖的孩子将会在一生中留下不可弥补的性格缺陷。同样,老年人可以通过养老金、社会保险解决生活的经济需求,通过雇保姆、进养老院解决送终的问题。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老年人晚年的孤独和凄凉。唯一化解的方法是通过子女经常的探望和交流,以亲情来抚慰父母的心灵。1999年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一首文辞朴实,曲调悠扬的流行歌曲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关注,歌名叫做“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群众对孝道的理解,在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以后,老人更看重精神的慰藉。而儒家孝道中不是有大量关于“孝敬”,“色难”的文化资源可供借鉴吗?
再次,儒家的孝道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和子女的培养。在现代家庭中提倡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可以增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感,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同时,成年人孝敬自己的父母,就是对自己未成年子女最好的言教。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现代社会结构虽然与古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皆出于父母怀衽这一点是不变的。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敬爱的人,很难相信他会爱祖国、爱人民。家庭是子女的第一课堂,对子女进行一些孝道教育,有利于他们将来在社会上接受其他道德规范。
最后,弘扬儒家的孝道观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儒家一向认为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长幼顺而上下治。近代以来,儒家这些维持社会稳定的思想一直是受批判的。然而,当封建社会已经被推翻,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全心全意维持社会的稳定,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明确了时代的特性以后再看孔子的思想,那么孝道中维持社会稳定的观念就完全可以阐释出新意。
总之,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人类还以家庭的形式繁衍生息,儒家的孝道伦理就不会完全过时,儒家文化一定会成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厚的文化资源。
标签:儒家论文; 孝道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天下父母论文; 论语·为政论文; 孝经论文; 家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