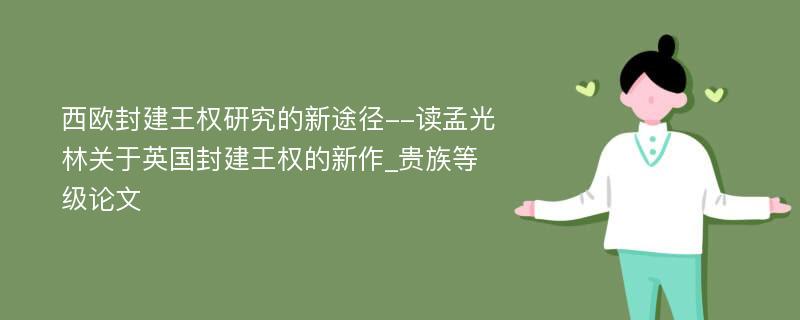
研究西欧封建王权的新理路——读孟广林新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封建论文,西欧论文,理路论文,新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东西封建政治史上,9—13世纪的西欧封建王权,可谓是非常晦暗而复杂的一个问题。由于奠基在日耳曼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西方式”的封建制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上,西欧封建王权的属性、地位及其政治基础并不明朗,各国王权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诠释难度很大,且存在着学理上的差异与纷争。同时,西欧封建王权也是一个富有学术与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将大大深化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有力推动对西欧封建政治史之特殊历史规律与东西方封建政治史之共同规律的求索。新近问世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一书,展示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所作出的可贵尝试。
翻开《论稿》的第一章,就看到作者对一百多年来西方学者有关西欧、特别是英国中世纪王权研究的学术史的全面展示和评述,给人以引人入胜之感。首先是19世纪晚期以斯塔布斯为首的“牛津学派”开创的把中世纪王权描述为近代“自由民主宪政”先驱的“宪政主义”。作者指出:“这种以近代政治图景为样本去裁量中古政治的史学观点,虽然在本世纪(20世纪)日趋消沉,但它的思想底蕴仍不时产生其特有的学术效应,它所包纳的‘王在法下’、契约平等、主权分割之类的基调,也就不同程度地成为西方学术界解释西欧封建王权的理论参照坐标”(第7页)。接着是19世纪末在法、美、德等国中世纪学者中形成的强调西欧封建贵族各自为政、王权形同虚设的“封建政治分裂割据”学理模式,其中有的学者强调土地分封基础上的国王与封臣之间的封建等级关系,是国王权威被分割的主要根源;有的强调封君封臣之间只存在“私法”意义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并无“公法”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对此,作者指出:“自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学理模式在西方开始受到怀疑乃至局部修正,但总的说来它至今仍然盛行和支配着西方史坛,对法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也有很大影响”(第14页)。然后是德国学者F.科恩对“分裂割据”模式提出局部修正的基于日耳曼“法律”的“有限王权”论。他强调契约关系本是作为中世纪“祖宗之法”的古日耳曼“法律”中的一部分内容,不能视之为中世纪特有的封建关系的主导原则。他强调“王从属于法”才是中古西欧王权的主要特征;那种法律是“私法和公法”的统一,它的“王从属于法”的原则决定了西欧封建王权是一种“有限王权”,国王仅仅是臣民选举出来的“公共首领”,他的权力也仅是同其他个人权利没有什么不同的“私人权利”。作者指出,“科恩这一学说对所谓封建‘契约’的政治效应的批驳,是对‘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之学理模式的有力挑战”;但是他从古日耳曼“法律”引申出一个所谓“客观法律秩序”,从而“演绎出一个适应于整个封建西欧的‘有限王权’类型与中古西欧的所谓‘王在法下’、‘王从属于法’的君主政治图景,这无疑是‘牛津学派’的宪政主义史学观点的理论翻版”(第17页)。最后,作者展示了对“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学理模式的另一种修正论说:布洛克等人倡导的强调西欧封建君权至上的“权威”论。他们竭力否认封建制度必然分裂割据而与统一王权互不相容的陈见,认为国王恰恰是利用封建制度逐步加强王权对封建贵族的控制,并利用基督教会涂油加冕等手段确立君权神授地位,逐步树立起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作者认为,这种修正对于纠正“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的传统学理模式的偏见颇有建树,但缺陷在于未能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本质上阐明封建王权逐步强化的必然趋势和根本原因(第26页)。
以上,《论稿》作者一共展示了4个学理模式。其中,“宪政主义”模式和“分裂割据”模式主要是19世纪初创的,“有限王权”论和“君权至上权威”论则是20世纪出现的对先前模式加以修正的模式。这就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西方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王权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溯了西方学者在涉及英国封建王权不同于其他西欧王权的特点时所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并对其是非得失作了精要的评点。这就使《论稿》的学术史追溯更加丰满。
如此丰满的学术史追溯功底,既使作者有可能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避免重复前人误蹈过的沟沟坎坎,在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学术理路对西欧封建王权研究作出新贡献。
二
在13世纪以前的西欧封建政治史领域中,我国史学界涉猎不多,研究也十分薄弱。《论稿》全书共7章近33万字,在仔细辨析西方诸学理模式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这一个多世纪的有关英国封建王权的重要问题,如封建王权的形成、王权的政治与思想基础、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等主要问题。作为中国学者在该领域中所撰写的第一部重要学术专著,我觉得《论稿》在英国封建王权——并进而涉及整个西欧封建王权——研究上的突出学术贡献,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力地纠正了长期流传的谬见,而且立论以丰厚的史料、史实为依据(所用英文参考文献、著作多达160余种),刻意求真求实,这就使作者能够站在学术创新的前沿,作出更富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一,分权统治论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论”——我们简称为分权统治论——视王权形同虚设,把封建贵族的分裂割据夸张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似乎带有近代“民主”色调的分权统治。这种学理模式在20世纪虽已遭到“有限王权论”和王权至上“权威”论的修正和否定,但是修正者自身又带着新的缺陷。而分裂割据论仍然继续得到不少人的认同。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中国和西方学者中都有人相信,西方封建制度之所以解体较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政治上的分权分治,使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较多的缝隙争得较大的发展空间,不像中国秦汉时期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严重窒息着商品经济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观点不能成立(注:参见拙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但它却表明“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论影响有多么深远。
“分权统治论”的基本论点之一,是认为封君封臣制度决定了封建贵族的离心倾向必然胜过其向心倾向。《论稿》作者则认为,贵族对王权是向心还是离心,不是由封建制度的原则决定的,而是根据他们的切身利害关系作出相应的抉择。如在分析诺曼王朝时期部分诺曼贵族反叛王权的基本动因时,作者既揭示了封建制的负面效应,也剖析了王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大量数据统计与贵族复杂心态的分析,认为在英格兰与诺曼底联结一体的政治格局下,王位之争是直接促成一些贵族反叛王权的主要原因。作者指出,威廉一世临终前让其忠诚的次子鲁弗斯为王(威廉二世),而让其与法国国王有勾结的长子罗伯特为诺曼底公爵。这一安排所造成的当时英王国“英、诺分治”、两权并立的局面,即使国王失去了大贵族专一不二的忠诚,更使大贵族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效忠任何一方以反对另一方,都意味着其在英格兰或诺曼底的政治、经济特权与地产被剥夺,但又必须在这两难中冒险作一抉择。从身家利益考虑,部分大贵族选择了支持罗伯特的道路(第132—133页)。而在论及斯蒂芬王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时,作者既描述了一些大贵族乘内战之机为私家权益投靠“安茹”派以对抗王权、甚至进行私战,同时也分析了大多数贵族反对分裂割据与社会动荡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特别是大贵族之间缔结和平盟约的措施及其意义,从而揭示了贵族的政治“离心”与“向心”倾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变化趋势。作者指出,贵族的“无政府状态”固然体现了其封建离心倾向,但却是他们对严重内战形势的本能反应:“既然王位的最后归属尚难确定,既然封建王权逐渐失去了王国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政治权威的实际意义,政治‘离心’和封建割据就成为不少大贵族确保和扩大私家权益的最佳选择”(第151—152页)。不过这样的贵族却是少数,大多数贵族只是整饬一方,以待时变,并随着国王军队的胜利而“逐渐向王权这个王国的政治统治‘中心’归附”(第153页)。这样的分析,的确是富有说服力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封建贵族之所以终归要归附王权,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注:指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统治阶级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的领导之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71页。)(第371—372页)。
第二,领主—附庸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契约关系。
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西欧中古领主和附庸或封君和封臣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契约关系,将封建贵族看作是“民主”“平等”权利的载体;一些教会史家则把基督教会看作是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从而将他们都视为封建王权的天然对立物,片面地强调贵族、教会与封建王权的对立与斗争。针对这些观点,《论稿》作者既探讨了贵族、教会与王权的矛盾斗争,又分析了教、俗贵族朝臣、官僚参与国家的管理以及在动荡与内战中支持王权、基督教神权的“王权神授”理想与王权的神化等诸多史实,说明了王权与贵族、教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与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虽有权益冲突与纷争,但密切的政治合作却始终是其相互关系的主流;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决非“平等者”之间按照“契约”关系实行合作,而是“主”、“仆”之间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各尽其责的不平等的合作。“平等契约”论者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在英国集中体现在国王的加冕誓词。新国王加冕时,为获得教、俗贵族支持,就在誓词中承诺要维护教会与臣民的利益和安宁,遵守先王的旧制良法,废苛政恶习,行仁德之政;进而将誓词中的承诺转化为赐予贵族的特权赐予状。“平等契约”论者认为,这样就“置国王于法律之下”,“国王就被自己对臣民的义务束缚起来”(第35—36页)。对此,《论稿》作者反驳道:“事实上,君主即位加冕时……许诺推行‘仁政’、‘德政’,乃是东西方封建政治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皇帝在登基之时也要发布诏书,其中也有类似的要推行‘仁政’、‘德政’的许诺。……将这类誓词看作是‘法’或‘契约’对君主的限制,难免有臆断之嫌”;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那样的许诺本是国王的权宜之计,是“朦胧的与无效的”;有的学者还指出,那样的誓词完全是国王身边的几个主教构想出来的,“从理想与形式”上看都是教会的产品(第381—382页)。
第三,中古西欧并不存在所谓“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
如前所述,19世纪的“宪政主义”模式论者、“分裂割据”模式论者和20世纪的诸多“修正”论者都强调中古西欧政治理念和实践中贯穿着“王在法下”的原则,强调国王必须服从“客观法律秩序”(包括所谓的“自然法”、“习惯法”)和上帝的“神法”。《论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这一理念与史实不符。他承认这一理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源头,那就是,“中古西欧的封建社会直接从原始社会中产生”,因此“国王在立法时,常常要派人去搜集”世代相传的习惯、惯例,并同贵族一起加以整理、认定,由此产生了法律先于并且高于国王的观念。蛮族国王接受基督教以后,又必须服从上帝的“神法”。这使“王在法下”观念进一步加深。这些因素确实对西欧中古王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王权的日益崛起,这种限制的力度也就相应递减”(第377页)。而且,封建王权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并非西欧独有现象,东方的封建王权也是如此。例如,“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有类似的‘王在法下’的情况,所谓的‘天命’、‘民心’、所谓的‘祖宗之法’、‘先王成制’与‘圣人礼教’”之类的东西,与西方的自然法、神法和习惯的含义虽不尽一致,但大体还可对应,都被看作是高于并支配着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法’。因此,一个‘合法’的君主应当也必须要‘奉天法祖’、‘以民为本’与‘尊圣崇礼’。主导文化领域的儒家,更是将‘民心’与‘天道’交融起来,构成了一个比西方的‘法’更具有威力的‘天命’法则。君主如果违背这一神圣的法则,‘天’就可以改变其作为‘天之元子’的地位而废黜他,民众可以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将其作为‘独夫’而诛之,‘汤武革命’也就伴随着‘天命’转移而必然出现。这些无疑都对君主形成了某种限制。故征诸史籍,我们发现,不仅君主‘敬天保民’的承诺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的肺腑之言”(第379—380页)。相比之下,西欧的封建君主在这方面受到的威胁反而还要小一些。作者引用一些著名神学家的权威观点证明了这一点。如圣伊西多尔强调,上帝任命暴君或仁君的决定是根据一个国家人民的情况而作出的。“如果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上帝就给与他们一个仁德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是邪恶的人民,上帝就将让一个苛暴的统治者来对其统治”。圣格里哥利除了坚持这种看法外,还特别强调,“好的臣民甚至不应当粗暴地批评一个苛暴的君主的行为,因为抵抗或冒犯一个统治者,就是冒犯将这个君主置于他们头上的上帝”(第183页)。作者还引用中世纪英国乃至整个西欧最有名的神权政治思想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话说,即使是应当诛杀的暴君,也不能由臣民去诛杀,因为“暴君仍然被称为上帝的神命之君,他虽然推行暴政,却未丧失一个国王的荣耀。因为上帝的恐惧折磨所有人,以至于民众将他尊崇为上帝的大臣,尊崇为有点具有上帝影像的人”(第207页)。有的西方史家也指出,“中世纪的王权被理论限制,但却不被制度所限制。即便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决心去废黜其统治者,他们也没有任何合法的道路去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很少的例外”(第377页)。这样看来,是否更有理由说中国才是“皇在法下”呢?或者,按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就可以断言“皇在民下”呢?显然谁都不会那样断言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 相信西方有“王在法下”的法制传统呢?实际上,正像在中国不可能“皇在法下”,在 西欧王权的实际运作中也不可能真正实行“王在法下”。正如作者指出:“君主权力与 ‘法律’影响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是由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内 涵决定的,相反‘法律’本身倒是由这种对比决定的”(第378页)。作者还指出:“‘ 法’之所以限制不了王权,是因为……社会政治的运作与等级秩序的维持最终仍然要靠 国王依据社会统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制定的实体法来保障,国王成了实体法的制定者, 高踞于实体法之上并将之作为巩固与发展王权的有力工具”。有一个生动的实例证明这 一点。1040年,波西米亚人抱怨德王亨利三世打破了他与其前辈订立的“协定”,亨利 三世反驳道:任何国王都增设新的法律;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不能被法律支配,因为法律 只有一个“蜡鼻子”,而国王有一只长的“铁手”,可以拔掉“蜡鼻子”(第377页)。 在这里,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中古西欧是否存在着国家政治“主权”的问题,强调不应 以近代国家政治“主权”的标准来衡量西欧的封建王国。西欧的封建君主有无“主权” ,封建国王是否位于“法”下,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观念或法理问题,因此考察这 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西欧封建政治的实际。史实证明,在11—13世纪的英、法等国家, “封建君主在王国内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最后命令的权力’”,对此不一定用“主权 ”一词名之,“但起码可以认为中古西欧也存在着‘朕即国家’的现象。”封建王权固 然受到各种限制,其中包括“王在法下”的观念所带来的限制,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 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梳理上与法理范畴的辨析上,也不应援引“中世纪人的理想” 来证明,因为“中世纪法学家的有关‘王在法下’的主张常常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不 应当将其作为研判王权的地位与性质的主要依据”(第374、379页)。
《论稿》作者不但以翔实的史实证明了上述“三论”不能成立,而且还深入剖析了倡言“三论”及其相关的学理模式的西方学者的文化心态,指出:“他们对西欧封建王权的研究,常常寄托着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同时也深寓着一种‘西方文明优越’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心态。在他们的视野中,早在中世纪西欧社会,日耳曼的民主政治文化传统或封建的契约关系就为西方播下了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种子,从那个时代起,西方的‘权利’社会或‘契约’社会开始在西方人反对国王暴政与专制的斗争中孕育与成长起来,而西方人崇尚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思想与实践,正是后来西方超胜东方并制约东方的历史根源”(第46页)。
在此,《论稿》作者提醒人们切莫轻信那些带有“西方文明优越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偏见。“实际上,不管西欧中古社会有何特点,它与东方的封建社会一样,都是以‘人蹬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在从事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时,尤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第46—47页)。这些论说,无疑都很中肯。
三
《论稿》作者依据丰厚的史实,对西方史坛在西欧封建王权研究中长期流传的“封建分权统治”论、“平等契约”论和“王在法下”论进行了精辟的驳正,进而揭示了中西封建社会“人的依附关系”的同一本质及其对封建君权之共同基本特征上的影响。但是,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到,尽管《论稿》是一部研讨英国封建王权而不是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专著,但它在第六章中所附带的中西比较考察却多少存在着一些不足,那就是在突出“共性”的同时,多少有些忽略“个性”。例如,西欧封建社会虽然不存在“分裂割据”模式论者强调的那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分权统治”,但毕竟在中古初期确实存在过恩格斯说的那种“贵族民主制”现象,如贵族会议“选举”国王,各大贵族领地俨然自成一个个小独立王国的局面;中古中期存在过等级代表会议或封建国会;中古晚期存在过专制君主制。这与中国秦汉以后存在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天子—子民”统治制度毕竟有很大差别。西欧封建社会固然不可能有基于近代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平等契约关系”(附庸依附于领主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双方的地位不可能平等),但是那里的领主和附庸之间确实存在着具有双向制约作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毕竟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君臣父子”之间那样的“宗法制”或“准宗法制”的原则上的单向服从关系。西欧封建时代固然不存在所谓“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但是西欧封建君主所受的各种法律、制度和诸如封建国会之类的机构的制约毕竟比中国皇帝所受制约更多。
西欧封建王权具有的这些特点当然不能用西方具有什么民主、法治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但却需要从当时西方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特点处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页。)。
日耳曼人从长期迁徙不定、征战不停的游牧、游耕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和“亲兵制度”对西欧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国家结构特点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
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和“亲兵制度”同古希腊人、罗马人的“军事民主制”,和“亲兵制度”本是同根同源的:都是来源于离不开征战和迁徙的游牧、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马克思论及古希腊人的“军事民主制”时指出:“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的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一种军事民主制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2页。)。恩格斯补充说:“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论断,至今还没有被后世的研究所超越。如格兰特和基振格1988年编辑出版的《古地中海文明》一书中述及古希腊的巴赛勒斯及其“亲兵队”时提到,由于定居以前的希腊人经常处于迁徙、征战之中,国王自然同时就是军事首领。或者说,只有军事首领才能当上国王。但是,要成为军事首领,必须拥有自己的亲兵。首领与亲兵之间的连接纽带,不是宗法血缘关系,而是“伙伴”关系:亲兵由于钦佩首领的英勇和仁义而甘愿为首领效命;首领则以胜利的荣耀和战利品来凝聚亲兵。首领靠着亲兵的拥戴得以臣服群雄而为共同体之王;一旦失去亲兵拥戴,就不再是军事首领和国王(注:M.Grant & R.Kizinger(ed.),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Greece and Rome,vol.1.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98,pp.4,8-9.)。另一位古希腊史专家托马斯在1998年发表的《追寻历史上的荷马》一文中,论及那时的王(巴赛勒斯)的地位时,也指出,他们的地位主要靠两方面的品质和能力来保证:一是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二是富有智慧,能对别人提出中肯劝告,能够在辩论和主持会议中说服众人。一旦不能表现出这样的品质和能力,就会失去王的地位(注:C.Thomas,Searching for the Historical Homer,1998.http://www.bib-arch.org/aopi98/homer.html,8-12.)。这些描述与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及其亲兵的描述交相辉映,同马克思、恩格斯概括的“军事民主制”也凿枘相应。
不幸的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人们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理解为一切民族从野蛮向文明过渡时期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的制度,以致把中国先秦古籍中提到的黄帝、尧、舜、禹等人物说成是相当于古希腊的巴赛勒斯那样的“军事民主制”的首领。这就抹煞了中西古代文明发轫期就存在的一个重大差别。实际上,黄帝、尧、舜、禹等人物同“军事民主制”中的巴赛勒斯毫不相干。如据《易·系辞》和《世本·作篇》等文献所记,黄帝的主要功绩是穿井、作杵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养蚕缫丝、制衣裳;还造文字、占日月、作甲子、发明算数、音乐、医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大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奉献。又如禹,按孟子所说,他为人民创造生产生活条件所作的奉献似乎比黄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注:《孟子·滕文公上》。)黄帝、尧、舜、禹等人物虽然也有打仗的事迹,如黄帝战炎帝、斩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等战事。但这些征伐与西方“军事民主制”下的“酋帅王”们的征伐有两个根本的区别:一是他们不像后者那样以夺取包括奴隶在内的战利品为目的,而是像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那样,以排除“无道”、“无德”之君,维护王道秩序为目的;二是,他们不是率领按个人意愿对自己效忠并且要同自己分享战利品的“亲兵”出征,而主要是按照血缘或准血缘的同盟关系征兵出征。种种事实表明,中国从未出现过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有过的那种军事民主制。这是因为,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的中华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和龙山文化时代就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域进入了定居农耕文明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掌握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只有简陋的木石工具,显然主要是依靠血缘或准血缘纽带组织集体协作,才创造了定居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这种以血缘或准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定居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权力组织,正是黄帝、尧、舜、禹那样的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指挥者的权力组织,而不是西方那种“军事民主制”和以征战为首要职守的“酋帅王权”。
西欧中世纪的国王与封臣之间的领主—附庸关系,显然就是直接从“军事民主制”的首领和亲兵关系演变而来的。马克·布洛克对此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日耳曼人那种亲兵制度的基本形式和价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中保持了许多世纪。克尔特人社会也是如此(注:M.Bloch,Feudal Society,Translated by L.A.Many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1,p.154.)。“罗马军团到来之前,没有一个高卢酋帅身边没有一群随从,无论是农民还是武士。”(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49.)而且,罗马帝国崩溃后,职业化的步兵团从此消逝了。“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整个形势越来越需要招募职业武士,也就是那些受过传统团队训练的人,特别是骑手。为国王服骑兵兵役的人,虽然直到9世纪末在理论上还是从家产足以支撑武备的所有自由人中征召,但是,这些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惟一可能有高效率的部队——的核心,自然就是那些早就充当国王和显赫人物的武装侍从的那些人”(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4.)。gasindus这个称呼在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整个蛮族世界都还在使用,用来指私家武装人员或家臣(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5.),但是逐渐被源自克尔特语vassus,vassallus的‘vassal(附庸)’一词代替,其原意为‘servant(侍从)’,指的是一度当过武装侍从而社会出身又比传统的gasindi地位低的人。但是,往昔的亲兵队的基本理念并未消逝:“显贵甚至国王蓄养的‘thugs(暴徒们)’尽管原来的社会地位卑微,从此以后却越来越有权势。把这些战斗伙伴与他们的首领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一种忠诚契约,那是适合于上流社会人们自由缔结的契约。王室近卫军的称呼,很值得品味,叫做‘trustis’,也就是‘效忠队’(fealty)。这支队伍新招募的成员要发誓表示忠诚,国王也要答应‘向他提供援助’。这些都是一切‘奖赏’(commendation)的原则。权势人物和他们的gasindi或附庸之间无疑也 交换着类似的承诺”(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6.)。
布洛克的论述充分证明,西欧封建时代的领主—附庸制度及其中包含的“契约”式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直接从古日耳曼人的亲兵制发展演变过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兵制或军事民主制之类的制度就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明传统。任何往昔的制度都必然要随着时过境迁而遭到改变,甚至失去继续存在的余地。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世人继承,取决于后世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与先辈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联系。实际上西欧封建国王与荷马时代的巴赛列斯或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已经有了本质区别。马克思嘲笑那些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的“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0页。)。只是因为欧洲封建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各小共同体不可能融合成为中国那样的具有大协作生产功能的大统一体,彼此之间继续存在着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那些小共同体——王国或王公领地——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具有昔日那种“军事共同体”或“军队组织”(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476页。)的特征。而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生存条件又促使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处于人的依附关系之中。于是,原有的“军事民主制”、“亲兵制”及其中包含的某些“民主”、“契约”因素就被沿袭下来,成为具有全新内涵的制度的外观形式。必须注意的是,无论野蛮时代的“军事民主制”、“亲兵制”,还是封建时代的“领主—附庸制”,其中包含的“民主”或“契约”因素,都是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前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民主、自由、契约等等观念和制度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其中也有某些历史联系,那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上古和中古时代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充满“竞争”特性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连续性或相似之处,而所谓民主、自由、契约等等观念和制度,正是为竞争性生产生活方式服务的。
标签:贵族等级论文; 王权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治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新著论文; 法律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