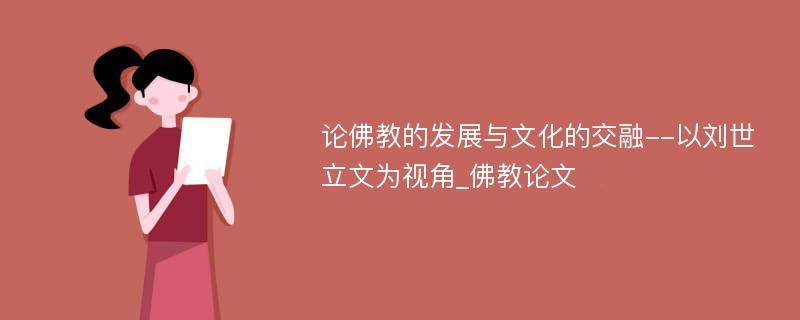
试论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论文,礼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1-0037-06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形态都是历史现象,其发展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也是如此。文化发展的过程犹如滔滔的长江,从巴颜喀拉山麓发源,到崇明岛入海,一路上吸纳百川,浩浩向前。那么什么叫长江?是它发源地的清清溪流?是在横断山脉间怒号的金沙江?是伴着三峡的猿啼滚滚向东的巨浪?还是在肥沃的东部平原上缓缓徜徉的洪波?同样,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日本等东亚各国,乃至近代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营养,依据不同的条件,变幻着自己的形态。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日本“批判佛教”的倡导者那样,因为佛教吸收了别的文化营养,改变了形态,从而否认它是佛教;也不能如教内某些法师,忽视佛教吸收别的文化营养自己的事实,忽视活动于不同时空的佛教出现形态差别的必然性,追求回归原始佛教。本文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佛教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受到什么因素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
从上述立场出发,从古代印度传入,在古代中国成长、发育的中国佛教,理所当然地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但问题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印度、在中亚,在这些佛教经典的原产地,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文化,对佛教经典的形成和发展,是否也产生过影响?
宗教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在流通。事实上,文化的流通从来都具有双向性,并非单行道。那么,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也影响印度,并作用于印度佛教呢?上述问题或者可以改换一个提问方式:当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传到中国、传遍整个亚洲的同时,中亚文化、中国文化、亚洲其他文化是怎样介入佛教这一文化形态,并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对其施加影响?
中国道教对印度佛教密教的影响,已经引起研究者注意。有研究者主张在印度佛教的净土信仰中,可以看到有伊朗文化的因素。《大集经》中出现中国的十二生肖,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① 笔者在此想以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刘师礼文》为切入点,对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问题作若干考察。
《刘师礼文》,保存在英国图书馆斯坦因特藏的一个写卷中,该写卷编号为斯4494号。斯4494号,首残尾全,现存文献如下(文献名称除注明为拟名外,均为原名):
(一)《方广经典忏悔文》(拟)②
(二)《请观音咒》
(三)《除度毒陀罗尼咒》
(四)《除睡眼陀罗尼》
(五)《观世音菩萨陀罗尼》
(六)《咒眼陀罗尼》
(七)《法华咒 药王菩萨咒》
(八)《勇施菩萨咒》
(九)《毗沙门天王咒》
(十一)《持国天王咒》
(十二)《十罗刹女咒》
(十三)《普贤菩萨咒》
(十四)《法数释》(拟)③
(十五)《刘师礼文》
(十六)《受八关斋文》
(十七)《施食咒愿文》
卷尾有题记:“大统十一年乙丑岁(545)五月廿九日写乞(讫),平南寺道养许。”④ 由此可知,该卷乃平南寺僧人道养个人持有之写卷,故定名为“道养文本”,为南北朝西魏写卷。
除英国翟理斯之《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对该号有著录外,至今未见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⑤。该《道养文本》抄写了将近十多个文献,本身是否一个完整的整体,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的一种仪轨形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第十五个文献《刘师礼文》,先录文如下:
刘师礼文
正月廿四日,平旦寅时,向东北。丑地,礼八拜,除罪廿一。
二月九日,鸡鸣丑时,向东南辰地,礼十拜,除罪卅一。
三月廿六日,人定亥时,向正南午地,礼四拜,除罪四百。
四月七日,夜半子时,向正北子地,礼四拜,除罪四万。
五月六日,黄昏戌时,向西北未(?)地,礼六拜,除罪一千八百。
六月三日,食时辰时,向南午地,礼六拜,除罪一千四百。
七月四日,甫时申时,向东南已地,礼四拜,除罪二千八百。
八月八日,日出卯时,向正南午地,礼九拜,除罪六千。
九月十日,食[时]辰时,向东南已地,礼九拜,除罪一千八。
十月十一日,吴(午)中已时,向正南仵(午)地,礼九拜,除罪六千。
十一月十一日,日入酉时,向正西酉地,礼九拜,除罪六千。
十二月二日,黄昏戌时,向正东卯地,礼卅拜,除罪卅万。
玄始十一岁次己卯⑥,刘师唯法,教化后生,除罪礼拜。若有信者,能如不失时节,礼拜满三年,即得道。所愿随意,不违心。欲生向处,随意求愿。欲生弥勒佛国,愿人求毕,不违心意。住生西方妙乐国土,亦得住生。生卅三天上,亦得如是。礼敬礼尽,更如法界诸佛,并及得道沙门。
文献的标题作“刘师礼文”,其后的流通功德文中又有“玄始十一岁次己卯,刘师唯法,教化后生,除罪礼拜”云云,故知道养于西魏大统年间(435~451)抄写这个文献时,社会上认为该《刘师礼文》是由一个叫“刘师”的人在北凉玄始年间(412~427)流布的。那么,这个刘师究竟是谁?笔者认为,这个“刘师”,应是早期中国信仰性佛教的代表人物——刘萨诃。
刘萨诃,梁慧皎《高僧传》有传,列为兴福门正传第一人。唐道宣《续高僧传》亦有传,列为感通门正传第三名。此外,道宣的《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以及与道宣同时道世的《法苑珠林》亦均有记载。早期记载还可见《出三藏记集》、《冥祥记》、《佛记》、《梁书·诸夷传》等。敦煌遗书及莫高窟壁画中也保存不少以刘萨诃为主题的资料。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刘萨诃其人,大体应活动于东晋。但其后事迹日益被增益、神话,以至有关他的传说岐杂,资料矛盾⑦。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曾将不同人物的故事,归并在一起,构成刘萨诃纷繁岐杂的经历。本文不打算介绍、梳理有关刘萨诃的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料以及其中记录的身世、事迹。只是指出,依据道宣的实地考察,从南北朝晚期直到初唐,刘萨诃在民间深受崇奉,“图像严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1] 卷50(p.645)因此,把斯4494号中的这个“刘师”,判定为当时民间佛教信仰中甚为崇仰的刘萨诃,当无大差。
考察《刘师礼文》,它的形态其实很简单,仅仅要求修持者在特定月份的某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辰,向某个特定的方向,礼拜特定的次数。认为这样的礼拜,均可减除特定的罪孽;坚持三年,则能得道,所得遂愿。
在此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这种礼拜法,是否符合印度佛教的传统?佛教大藏经中收有《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传统列为小乘经典,《大正藏》将它收入《阿含部》。该经有三种异译本:《长阿含经·善生经》(后秦译出)、《善生子经》(西晋译出)、《中阿含经·善生经》(东晋译出)。即使从译出年代,也可以肯定该经确为印度佛教中时代较早的经典。上述四部经典叙述虽有差异,内容大体相同,谓尸迦罗越的父亲要求尸迦罗越每天要向东南西北及天地等六方礼拜。释迦牟尼询问原因,尸迦罗越回答是遵循父亲的教诲。释迦牟尼说:“父教汝使六向拜,不以身拜。”[1] 卷1(p.250)然后讲述了应该如何处理父母子女、师傅弟子、夫妻、亲朋、主奴、在家人出家人等相互关系的一套伦理规范。成为我们研究小乘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
《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中释迦牟尼所说“父教汝使六向拜,不以身拜”,这句话,在相应的异译本中,是这样的:
《长阿含经·善生经》:“尔时,世尊告善生曰:‘长者子,有此方名耳,非为不有。然我贤圣法中,非礼此六方以为恭敬。’”[1] 卷1(p.70)
《善生子经》:“众佑报曰:‘居士子,父所言者非此六方也。旦而晞坐六面之欲,如有四面垢恶之行不能悔者,则是身死,精神当生恶道地狱之中。’”[1] 卷1(p.252)
《中阿含经·善生经》:“世尊闻已,告曰:‘居士子,我说有六方,不说无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别六方,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彼于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1] 卷1(p.639)
文字表述不同,基本意思相通。释迦牟尼并不赞同这种六方礼拜法。在初期佛教,乃至早期部派佛教中,也没有发现曾经流行这种礼拜法。
那么,《刘师礼文》提倡的这种礼拜法,缘于何处呢?如果翻阅《白虎通义》,看看王充《论衡》及早期的道教经典,就可以明白,这种将某一特定方向,赋予某种神秘含义的思想,正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
再考察时辰问题。
《刘师礼文》要求在特定月份的某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辰进行礼拜,这在印度佛教中是否可以找到根据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先,就日期而言,印度虽然朔望为界,将每月分为白月、黑月,但没有赋予神秘的宗教含义。如下述《佛说四天王经》中的六斋日,就平均分配在白月、黑月中,各有三个斋日。而《刘师礼文》中十二月礼拜,除了正月、三月选择在后半月之廿四日、廿六日外,其余十个月均安排在前半月。中国传统认为,前半月为阳月,后半月为阴月,阳月礼拜,功德更大。由此可知,《刘师礼文》中每月礼拜日的选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其次,《佛说四天王经》这样说:“须弥山上即第二忉利天,天帝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镇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龙鬼蜎蜚蚑行蠕动之类,心念口言身行善恶。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复下。二十九日太子复下。三十日四王复自下。四王下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其中诸天佥然俱下。”[1] 卷15(p.118)
亦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四天王会派遣使者、太子乃至亲自巡察天下。经中说,巡察时,如果见众生行善,会“具分别之,以启帝释。……释敕伺命,增寿益算;遣诸善神,营护其身。”[1] 卷15(p.118)否则,“即令日月无光,星宿失度,风雨违时,以现世人。欲其改往修来,洗心斋肃。”[1] 卷15(p.118)
这部经以佛经的面目出现。且按照经录记载,它是南北朝刘宋凉州沙门智严共宝云译。但是,其中反映的却是天神伺察思想。封为善者,它的奖赏是“增寿益算”;对作恶者,它的惩罚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下地狱,而是中国文化主张的天人感应,敦促自省。那么,它是真正的印度佛教经典吗?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当然不能说古代印度没有天神伺察思想,其实早在吠陀典籍中,就载有天神伺察的思想。但是,早期印度佛教的确没有类似的论述,起码我们在现在公认的早期印度佛教典籍中没有发现这类论述⑧。撇开天神伺察暂且不讲,仅从《四天王经》宣扬天人感应来说,说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应该可以成立。
《四天王经》既然是翻译典籍,何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涉及到笔者近年来非常关注的问题,即佛教的发展,并非印度文化单纯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具体到《四天王经》,很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传入西域、传入印度,与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这一文化汇流的产物又回传中国,被翻译成汉文。因此,笔者曾经撰文说:“佛教的产生虽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也就是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结果中,也体现在历史的过程中。”⑨
类似的例子,还有《净度三昧经》。
《净度三昧经》,也是南北朝刘宋宝云翻译,原本一直收入大藏流通。8世纪智昇撰写《开元释教录》时对它产生怀疑,但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于是把《净度三昧经》作为附录附于“入藏录”末尾,称:
《净度经》下十部十五卷,并是古旧录中疑伪之经。《周录》虽编入正,文理并涉人谋。故此录中,除之不载。[1] 卷55(p.699)
智昇的这段话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自该经翻译出来之后,从来没有人怀疑它的身份。我曾经撰文考订,它的确是一部翻译出来的经典,参见拙作《净度三味经的目录学考察》[2],此不赘述。但是,也必须指出,《净度三味经》中的确有着浓重的中国文化气息,如:
神明听察,疏记罪福,不问尊卑。一月六奏,一岁四覆。四覆之日皆八王日。八王日者,天王案比诸天、人民、杂类之属,考校功最。有福增寿,有罪减寿夺算。
天地浩浩,黎庶无数。诸天、地狱、五道大王、司命、都录、五官、都督、四镇王使者、承天、大将军等,春秋冬夏承天统摄,禁察非法。总持众生名籍,制命长短,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不知天地五官所记。不能自知生所从来,死至何所。不能自知命之长短。不知为五官所收录。不知豫作善求安,不知豫作功德救罪。亦不晓依附三尊,求后世救。不晓求守戒明经道士,从求度世道。如牛老败不中用,大家言:“此牛老败不中用。烦劳牧养,久已无益我家。但当早杀。可得肉食之,亦可除烦劳。”人亦如是。不奉持戒禁,亦不作功德,如牛烦劳大家甚多。不益大家,又不能自活。人依道生,道气养之。不肯奉道,亦不能自度。为五官所收,死付地狱,尽属三十王所治如是。
难怪当年智升将这部经典判为伪经。
提到伪经,这里要提及百年来学术界纠缠不清的两部经典,一部是《大乘起信论》、一部是《仁王般若经》。不少人指出这两部佛典,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倾向,不可能是翻译入华的印度佛教典籍,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但是,根据最新的佛教文献学研究成果,这两部经典的确是翻译的。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此必须正视中国文化西传,与中亚文化、印度文化汇流,共同创造新的佛教形态,而又回传到中国的问题。
中国文化西传,可以分为流传到狭义的西域与广义的西域两种情况。所谓狭义的西域,亦即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这里从来是多种文化荟萃的地方。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汉文化在这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里又是一大批大乘经典产生、传流、贮藏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佛教、这里产生的佛教典籍,必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新疆地区呢?
首先是汉文化对当地居民的直接影响。敦煌遗书与吐鲁番文书都反映出敦煌及西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许多非汉族居民的生活,已经受到汉文化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既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也可以熟练地使用汉语文从事各种活动。如统治高昌的麴氏王朝,统治于阗的李氏王朝,都是典型的例子。最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这里不一一介绍。
其次是汉族移民的影响。也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但专门的研究论著还较少。在此以佛教僧人法海为例,略作说明。
在北图藏BD03339号(雨39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末尾有这么一段译场列位,共罗列18位参加义净译场的僧人:
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
翻经沙门婆罗门三藏宝思惟正梵义;
请翻经沙门天宫寺明晓,
转经沙门北庭龙兴寺都维那法海,
弘建勘定。
在敦煌遗书伯3532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上文讲到安西有两所汉人住持的佛教寺院,其中一所名为“龙兴寺”,由一个名叫“法海”的僧人任寺主。这个法海,虽然是汉人,却出生在安西。
长安三年是公元703年,而慧超于开元十五年(727)到北庭安西。从上面两条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法海生于西域,在西域出家,后到长安参学。长安三年(703),曾以北庭龙兴寺都维那的身份参与义净译场,后又回到西域,727年左右任龙兴寺寺主。慧超称他“学识人风,不殊华夏”,想必与他的这种经历有关。法海的这种经历,对我们研究当时西域移民文化的形态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再次是汉文佛典的影响。
敦煌遗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文,其次是藏文,此外还包括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诸多文字的各种文献。其中有用藏文音译的汉文文献,也有原典为汉文,但已经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文献。比如翻译成回鹘文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翻译成粟特文的《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
这里特别想谈一下《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这是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佛经,是典型的“伪经”。它所反映的是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思想,或者说经过中国文化改造的佛教思想。中国古代经录虽有著录,由于是伪经,故没有收入大藏经,因而亡佚。敦煌遗书中除了保存有粟特文译本残卷外⑩,还有五个汉文原本,分别保存在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及三井文库。保存在英国的粟特文残卷虽然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始终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经。1933年,法国戴密微(P.Demieville)根据收入在《大正藏》第85卷的汉文残本,比定出该粟特文本就是《佛为心王菩萨所说经》。其后日本学者依吹敦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学习粟特文,并将这个残卷还译为汉文。
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凡明确是中国人撰写的,一律是“伪经”;凡明确按照域外底本翻译的,都确定为“真经”;无法断定翻译还是撰写的,暂且作“疑经”处理。假设该《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在历代经录中没有被著录(属于伪经,而历代经录未予著录者,数量不少),假设该经的所有汉文原本都没有被保存(这种例子,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举出不少),假设依吹敦先生是古人,他发现了这个粟特文本,并将它翻译成汉文;他的翻译活动被古代的经录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这部经典呢?上面的问题虽然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但它显然并非一个“伪问题”。
总之,包括印度文化、汉文化在内的诸种文化在西域汇流,不可能不对流行于西域的佛教产生影响,不可能不对部分产生于西域的佛教典籍产生影响。这些典籍传回中原,与中国文化产生进一步的互动。这是我们在佛教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考察诸种文化在狭义西域地区的汇流对其对佛教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非一篇论文可以讲得清楚的。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认真研究的问题。这显然可以成为我们佛教研究中的又一个制高点。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疑伪经,以及学术界认定的一批所谓“疑伪经”,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所谓广义的西域,在本文中主要是南亚次大陆,亦即古代印度。由于古代印度缺乏详尽的历史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即使从汉文典籍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曾有大批商人、使节、僧人往返两地。他们都是文化的载体,承担了传播文化的功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中国来传播佛教,然后返回印度的印度僧人;以及到印度去求法,留在印度没有返回的中国僧人。义净诗称:
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别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辈马(焉)知前者难。
雪岭崎岖侵骨冷,流沙波浪彻心寒。
后流不辩当时事,往往将经容易看。
“去人成百归无十”,其中固然有在路途死亡的,也有不少留在印度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即使那些求法回国的僧人,他们在印度的活动,同样打上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比如,与古印度诸国分立的政治局面相适应,印度佛教从部派分裂开始,就再没有统一过。印度人倾向于认为,无数相互对立的集团与派别、各种异质东西的同时并存是一种正常现象。部派佛教时期的印度僧人说:一个金手杖虽然断为十八截,但每截都是真金的,由此论证当时分裂的诸多部派都属于佛教正统,都是合理的存在。出于这种思想方式,他们自然无意于从事统一各种各派的工作。中国的情况则不相同。从历史上看,从古到今,中国基本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即使国家暂短分裂,有关国家或自诩正统,以统一为己任;或奉别国正朔,自居于藩属。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应,在意识文化领域,中国人总是力图会融各种矛盾因素,致力于建立一个圆融和谐的体系。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的判教就是中国人这种思想方法的反映。唐代中国僧人玄奘到印度后撰写《会宗论》,企图融会印度佛教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敦煌遗书斯06884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末尾有这样一条题记:
敬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十卷。/右,已上写经功德,并用庄严/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伺命伺录、/土府水官、行病鬼王、并役使、府君诸郎君/及善知识,胡使录公、使者、检部历官舅母、/关官、保人可韩、及新二使、风伯雨师等,伏/愿哀垂,纳受功德,乞延年益寿。/
该《金光明最胜王经》抄写于敦煌归义军时期,约9到10世纪。如果将该题记与翻译于南北朝《净度三味经》相比,可以看到有许多共同之处。它提示我们,对文化的汇流,除了正式的、经典的、精英的文化形态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信仰性的、民间的、民俗的文化形态。但这个问题很大,拟另文叙述。
注释:
①除了将虎改为狮子,十二个动物的名称、次序、乃至所代表的方位完全与中国的十二生肖相同。
②原卷首残,第一个文献的名称不详。从内容看,应为礼佛忏悔文一类。行文中有“复行方广经典忏悔”云云,故拟名作“方广经典忏悔文”。
③解释“八不净”、“十不净肉”、“三十六物不净”、“十四音”等四个法数,故拟此名。
④除了尾题中的“道养许”外,文中另有两处“养许”。一处在《请观音咒》下,一处在《刘师礼文》下。“许”,在此即“所有”之意。
⑤法国苏鸣远在《敦煌写本中的地藏十斋日》中,注意到与《地藏十斋日》抄写在一起的《十二月礼佛文》,并提到斯2565号、伯3588号、伯3809号等,但并未对该《十二月礼佛文》展开研究,也没有涉及斯4494号。
⑥玄始为北凉年号,十一年为公元422年,干支应为壬戌,与“岁次己卯”不合。
⑦可参见史苇湘、孙修身、陈祚龙、魏晋贤(Helene Vetch)、饶宗颐等诸位的论文。
⑧《增壹阿含经》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杂阿含经》(1117),均有类似的文字。但前者虽然题为东晋翻译,现在的传本,实为南北朝定本;后者为南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两部经典的时代均与《四天王经》译出时代相同。
⑨《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前言》,载《蒙古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该遗书的完整编号为:B.M.Or.8212(160)/Stein Ch00353号。" B.M.Or.8212" 是英国博物馆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文物给予的编号,而“Ch”为“千佛洞”音写首字,表示该遗书为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得到。从编号看,该遗书应为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所得。
我们知道,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到敦煌时,藏经洞剩余遗书已经调运北京。斯坦因搞到的敦煌遗书是王道士私自藏匿的,约500多卷。此外他还从新疆等地发掘到不少古文献。
从斯坦因、伯希和的有关记录可知,由于王道士只懂汉文,对其他文字的典籍不甚重视。所以王道士最后藏匿的这批东西,只能是他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汉文文献。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则该粟特文本《佛为心王菩萨所说经》是否从王道士手中得到,大可怀疑。这里有两种可能:一、该遗书可能是斯坦因从千佛洞其它洞窟所得;二、也可能该遗书并非敦煌遗书,此编号有误。
标签:佛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张骞通西域论文; 金光明最胜王经论文; 读书论文; 法海论文; 西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