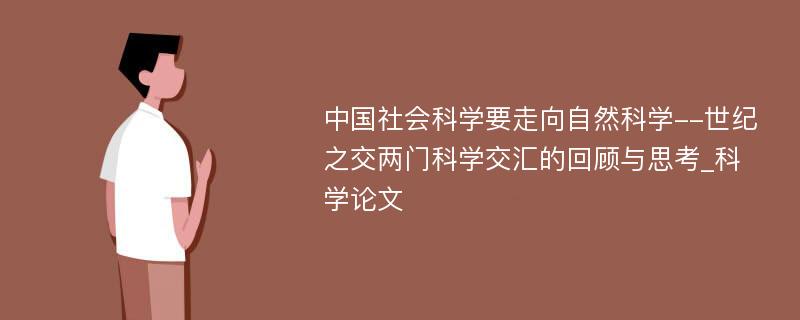
中国的社会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世纪之交两大科学合流的回眸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两大论文,中国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改变着人类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代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显然,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正面临着自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而言,囿于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从根本上缺乏现代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那种执着和科学追求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故在两大科学“合流”的撞击中,不时地暴露出固有的弱点或陋习。人类正处于世纪的转折点,21世纪的曙光即将降临。不言而喻,我们的社会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
分久必合:当代两大科学的“合流”
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在《对科学的挑战》等论著中曾经指出:从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世纪,科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发展,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处于自伽利略、牛顿以来另一个重要的科学革命时期,近几百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有一个古老的同盟;但是随着经典科学的建立,人与自然的同盟破裂了,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种科学,两类文化。现代科学就是要重新把二者统一起来,建立人和自然的新的同盟。在《结构、耗散和生命》这篇耗散结构论的主要代表作中,普利高津开宗明义地写道:“生物学与理论物理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提出耗散结构论的目的在于:“能够使生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的鸿沟缩小”,并进而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缩小。
本世纪初,列宁就曾指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在上个世纪,马克思也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20世纪科学发展的历程,完全印证了这些远见卓识。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趋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
首先,数学一马当先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使社会科学染上“数量化”的色彩。如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都已先后应用定量分析。甚至在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两极的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交叉学科——数学语言学。据统计,1900-1965年间,全世界社会科学共有62项重大进展,其中定量研究约占三分之一,尤其在1930年以后,这个比例高达六分之五。1969年第一次设立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时,两位欧洲经济学家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对各种假设的证明成了可能”,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代表诺贝尔委员会为这一决定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对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反映并认可了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一种经济观,一种崇尚数学、图表、定量分析和数学公式的经济观。
其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正在相互移植和吸收。如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电子学中“阈”的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用来研究社会变革;人们还把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引入社会学和思维科学等等;自然科学中惯用的数学方法、模拟方法、计量方法、元素分析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等,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样,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模糊集合”、“目的的假定”等,已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所吸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愈来愈考虑到它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比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的那部不朽著作,其书名为《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三,人类一些综合性的难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爆炸以及城市、交通等问题,都必须依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通力协作研究,“立体作战”才能解决。并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一些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如像试管婴儿、器官移植、遗传工程、克隆技术、安乐死等等,都需要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协助来共同解决。这些都是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科学攻克的难题。
第四,伴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或相互渗透,综合性(交叉性)研究方法和综合性科学(交叉科学)应运而生。本世纪中叶崛起的三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就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贯通起来的“横断科学”。“三论”(老三论)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被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泛应用。有人指出: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上述“横断科学”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界的思维方式。”1977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年鉴》中写道:“突变论使人类有了战胜愚昧无知的珍奇武器,获得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的深奥见解”。
第五,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人——机的组合是人脑的延伸,它把人类大脑功能大大提高,开创了人类思维的新纪元。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尽管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人的思维,但它对人的认知,对揭示人类认识之迷,都具有重要意义。就目前来说,它无疑是人类思维信息加工处理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电脑的普及,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形成,标志着人类信息处理及应用进入了新的时代。
本世纪的一些卓越科学家都在致力于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话,探寻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然和思维两个世界自己展现出的那种崇高和令人惊奇的秩序”。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在《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一书中指出:“在西方文明史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裂至少可上溯二百年。可是,现在从关于进化过程的科学中产生的崭新的知识已经超越了这种分裂,因此这就为建立统一的、宏大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相互交叉:科学综合的历史契机
20世纪勃兴的两大科学的交叉、合流,是历史的必然,是科学发展自身所作出的选择。考察一下科学发生学,便会发现:人类先哲认识事物,乃是从总体的联系上来把握对象,这是一种原始的“整体式”的研究方式。尽管这种认识尚处于混沌状态,或不配科学的美称,但它不失为一种“综合”探讨的方略。
若追溯到古代,我们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乃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且不说宗教文化、神学渊远流长,尽管它们与现代科学风牛马不相及,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像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都是从其中分离出来、上升为科学的;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如诗)、艺术(绘画)等,都一直在人类认识史上占重要的、领先的地位。当然,数学、天文学也是两门古老的科学,但在古代和中世纪,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远不及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那样“发达”。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狂飚运动(14-16世纪),就被称谓“文艺复兴”。
尽管宗教神学残酷迫害了塞尔维特、布鲁诺、伽利略等自然科学家,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科学、艺术与宗教神学同出一辙,人类原始思维起源于巫术礼仪。恩格斯就曾指出:“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3页。),“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也曾指出:“从历史上说,一切(或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的确,人类如果没有占星术,很难设想会有今天的天文学。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终究与宗教神学分道扬镳,这样,占星术也就绝不可与天文学相提并论了。
应当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无情地冲击了宗教神学,但整个人文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解放”,似乎不及这一冲击波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之深。从哥白尼开始,近代自然科学以天文学、物理学为先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不言而喻,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已把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抛到了后面。看来,要推进两大科学的交叉或“合流”,社会科学首先还得需要自然科学的“提携”。据说,国外一些极有名望的学者,如库恩、波普尔、贝尔纳等科学学巨匠,都曾说过社会科学尚处于“前科学”时期,马克思就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注:拉法格:《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如果说,从哥白尼开始的近代科学直至19世纪上半叶,人类科学研究就总体而言是以分析为主,那么,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已并驾齐驱。进入本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综合化和整体化的势头突飞猛进。50至70年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横断科学”的异军突起,则标志着整个科学王国正从以“分析”为主的阶段,跨入了以“综合”为主的阶段。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学科的迅速分化,同时也孕育着更大的综合。经验的自然科学用分析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实证知识材料,这些知识不断聚集,为科学的系统综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粗略地考察一下本世纪的科学发展过程,便能证实这一点。科学史向我们揭示,科学的分化和综合是辨证统一的。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即是当代科学学科高度综合的契机,又是高度分化的最主要的“发祥地”。两大科学的渗透合流,呼吁着各学科的通力合作,和多层次的“立体作战”。而这一切,正标志着人类科学系统综合发展时期的到来。
总之,当代科学正处于大综合、大交叉的时期。交叉科学犹如雨后春笋,迅速生长,聚然形成了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三大科学群的崭新的科学体系。交叉科学的异军突起,使整个科学世界的图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统计,目前仅自然科学总量就已超过2600门,它们通过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等构成了网络。这将有力地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交叉合流,也将是人类献给21世纪的一幅壮丽的科学画卷。
彼此融通:科学发展的逻辑
协同论给我们启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从表面上看,支配着各门学科的现象和理论虽不相同,但深入地考察和研究表明,由完全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的系统,在宏观结构上所产生的质变行为(如从旧结构转变为新结构的机理)则是相同的。即,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不断发展、“不断革命”的。现代科学(泛指两大科学)正进入了总体革命的状态。科学理论框架的总体变革,它把以往的科学学科“整编”为现代科学母系统的一个个子系统。现代科学革命(以自然科学为先导),不仅重新描绘出全新的科学世界图景,同时,科学理论结构重建的秘密也第一次被真正揭示:科学不再是被描述为某种终极真理或规律,而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过程。
比如,近三百年间,牛顿经典力学及其科学观一直被人们奉为科学的圣经,人们笃信科学真理一定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绝对性。这是一种建立在机械决定论之上的科学观。到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及在此前提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严重地打击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科学观。随之建立起新的科学观:相对性、历史性和主体实践性。尤其是,本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建,对旧的科学理论框架从总体上、根本上予以否定。而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创立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横断科学”,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和科学本身的新的本质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的手段。
相对于以自然科学和“横断科学”为前沿的科学总体的发展和革命,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是缓慢的。面临着科学总体革命狂飚的无情冲击和挑战,当代社会科学如果不急起直追,这个差距将越拉越大。因而,在西方,无论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无不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其科学方法和学习其科学精神。稍回顾一下历史,便可发现,近代以后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借自然科学尤其是其“带头学科”之东风而扬帆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尾随自然科学步伐的历史。甚至可以认为,与其说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是从宗教文化这个“大摇蓝”中演化而来,倒不如说它是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前进的。科学史向我们展示:自从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脱颖而出,昂首走上人类认识的舞台,也便拉开了社会科学步其后尘的序幕。如,哥白尼“日心说”的创立,不仅标志着自然科学率先冲破宗教神学,而且给人类带来了崭新的宇宙观。而此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严格地讲,它们尚处于萌芽时期)还在“地心说”的摇蓝曲催眠下睡大觉哩!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问世,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又一次辉煌胜利,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且由洛克、斯密等人将这种科学观运用于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斯密由此而得到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桂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建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的诞生,既是自然科学的划时代进步,又带来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就是这“三大发现”。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影响之深,更是空前的。
当然,在西方,自然科学家同样也很关注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据说,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就对康德、休谟、马赫的哲学著作有过钻研,他的相对论的创建,与此不无联系。顺便指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哩!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本世纪以来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纷纷表现出强烈的哲学探索精神。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本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科学家具有哲学头脑,而今天的物理学家几乎全是哲学家。”在恩格斯看来:“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页。)
另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念,就是把科学家想象成没有艺术修养、毫无人情味的“机器人”。其实不然,美国科学家莫里斯·戈兰博士在《科学与反科学》一书中批驳了这一近乎神话的观点。作者用了大量事实说明科学家不仅喜欢艺术,而且还直接从事艺术创作,不少的科学家本身就是艺术家、文学家,他们中间有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记得恩格斯在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就曾列举到:“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页。)20世纪数学物理学家沃伦·韦弗总结了科学家的艺术爱好,他说:“科学基本上是一项艺术事业,好奇心、训练有素的想象、合理的自信心以及美好安宁的环境则是成功的阶梯。”
各自为政:中国学者的反差
我们的祖先曾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近代以后,“四大发明”的故乡却在世界科技竞赛中落伍了。当代世界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和人才的竞争,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学者必须放眼世界,反思自我,寻找差距,奋起直追。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或合流,是大势所趋,日本著名学者玉野井芳教授甚至认为:“自然科学可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可见,试图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永远截然分开,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互不买帐,凡是有这种头脑的人,是决不会站到历史的高度来全方位地俯瞰科学总体的发展图景的。那种自我封闭的“亲本研究”,如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格局下仍遗留的小生产作坊式的手工个体劳动一样,“老牛拉破车”,是上不了当今世界科学高速公路的。而类似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被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批评过了的,他指出:“这种做法(指近代科学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形态的研究——引者注)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1页、83页、60页。)
如果说伽利略时代是科学家“个人奋斗”的时代,是一位科学家、一间实验室的研究模式,那么,牛顿则是“站在巨人肩上”进行综合创造的时代,牛顿曾提出了一条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原则:所有的研究者都可以自由地采用前人的技术。而到了20世纪,科学研究则进入了协同攻关,联合战斗的阶段,有的甚至必须大兵团作战。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曾指出:“科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前辈的工作……科学家不是依靠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依靠几千人凝聚的智慧”。1942年,著名的美国“曼哈顿工程”动员了15万名科技人员,耗资20亿美元,历时三年,研制出了第一批原子弹。1961年美国又组织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发射火箭“土星-5”,有560万个零部件,飞船也有300万个零部件。为了这项研究,前后有400万人次参加,最多的一次则动员了42万人。参加研制的有200家公司,120所大学,花去300亿美元。1969年人类终于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在我们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人们相互之间缺乏普遍的联系。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彼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至于知识分子,更是“文人相轻”。从古到今,我们的科学家们都喜欢埋头照料他们自己的小花园,很少向相邻学科的园地里张望。正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关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呼声日趋高涨,但具体却尚未真正落到实处,为什么两大科学相互奔向、相互交叉渗透如此步履艰难?这全然不是一个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个与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我国,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已经开始迈出了实验室,开始奔向社会、奔向社会科学,有的学者甚至“下了海”;而奇怪的是,面临着这种挑战,我们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却姗姗来迟。人们往往还看见,正是社会科学界(包括哲学、人文科学)一些人士,总是在那里指手划脚,洋洋得意地指责:这里是“技术(科学)决定论”,那里是“做数学游戏”。不错,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不能单凭用数学公式去模拟便能解决的。然而,必须明确:“数量化”、“精密化”等不等于“机械论”,就像合乎逻辑的“定性分析”决不是“伪科学”一样。再说,即便自然科学真正渗透、“打进”了社会科学,会不会“没了社会科学”呢?不会的。现代科学是平等相处的,两大科学的交叉、合流,决不会“谁吃掉谁”。比如,当今世界,数学方法,统计方法(概率论)以及“老三论”,“新三论”等科学方法已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而在我国,传统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却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的确,对于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正面临着自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如果说现代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而显得“先天不足”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那么,生活在长期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总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尽管吸取了现代西方文明尤其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营养,但总的说来,人们对迎接现代科学总体革命狂飚的思想准备并不充分。显然,现代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和批判的理性精神,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拍打着中国的海岸。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央电视台科技节目《科技之光》栏目主编、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科技投入,不拿出足够的经费进行科学普及,就等于在21世纪的人才智力战面前进行单方面的裁军”。自然科学的突破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自然科学的勃兴又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所以,要振兴我国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固然重任在肩,同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也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跳出怪圈:寻求新的思维方式
应该看到,在我国,影响和防碍两大科学交叉、合流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很清楚:它与传统思维模式不无关系。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痼疾,就是具有封闭性、保守性、排他性和单向性,并由此构筑成一个壁垒森严的怪圈。这种严重的思维定势,与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思维方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主体的认识能力是受其思维方式制约的。自我封闭、作茧自缚、拘谨保守、排他排外的习惯性思维(这是一种陋习!),又怎能适应当代两大科学交叉、合流的汹涌澎湃的潮流呢?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且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传统”,即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僵化理解,并以此作为价值尺度去衡量一切。于光远先生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科学是与宗教和法律截然不同的:法律是使人服从的,宗教是供人膜拜的,而科学则是让人研究、批评、发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和世界观,本来是开放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可人们把它视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永恒教条,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把它神化了。过去,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我国不是打倒了许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吗?当然,现在,关于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争论不多见了,但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领域,将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恐怕也是影响、防碍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和两大科学交叉、合流的一个屏障。
顺便指出,探讨科学,坚持真理,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环境。发生类似烧死布鲁诺、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固然是人类历史的不幸,但这些血的教训,也揭示人类追求真理必须塑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否则,即便不再重演科学的悲剧,恐怕也难免出现像美国物理学家塞姆·K·艾利森所说的现象:“第一流的科学家就会转向研究蝴蝶翅膀的颜色去了”。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指出:“有史以来,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他发现,“既然西方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而且事实上,中国同西方发生接触的头一个后果便是加强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贝尔纳认为,“不过从中国已有的成绩可以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的确,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这位科学家的创始人的上述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的确,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保守性,长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在这种传统下,中国的学者们也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习惯:躲进小屋成一统,在“象牙塔”中做学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崇尚经典,述而不作,祖宗之法不可变等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探寻精神不相容的。
当然,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并非都是一无是处,比如,贝尔纳所归纳的“细心、踏实和分寸感”等,的确就属于“良好的基础”,看来任何传统和传统思维模式都有它存在的合理因素,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替。这里就存在一个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也就是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在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现在,事实上已不可能指出人类活动中,有哪一个领域不是人(社会)的自然的相互结合或相互渗透。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1页、83页、60页。)因而,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合流,也就不再是一个“需要不需要”和“可能不可能”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所在,恐怕是:怎样去促进二者的交叉、合流?这种交叉、合流的前景如何?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两大科学交叉、合流的浪潮中,需要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
面临着现代科学总体革命的挑战,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出路何在?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先验地给它订一个去向和取舍标准。但是,我们有必要寻求把握顺乎世界科学潮流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方向和趋势的途径。每一个关心科学发展前景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责任来共同探索这一途径。如果说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封闭式”的,那么,构建新的、“开放式”的思维模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这种“开放思维”,从宏观角度看,也正是符合当代世界开放潮流的。当然,它也是顺应当代两大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大趋势的。
英国作家肖伯纳有一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前苏联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凯德洛夫也曾指出:“两个不同的科学认识领域可以经由把它们引入相互联系的途径,而达到互相补充,从而同时把它们共同的本质揭示出来”。这些闪耀着真知灼见的论述,从各个方面一语道破了开放思维和科学互补效应的天机。
中国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员李醒民先生曾经谈到:“当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流的趋势锐不可挡,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很难设想,一个对当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的人能谈论好时间和空间、认识的详细过程、思维的本性等问题,更不必说去发展、创造了。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科学一窃不通或一知半解的所谓的‘伟大哲学家’会越来越少,而伟大的科学家却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总之,正是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和互补,才形成了交叉科学大量涌现的蔚为壮观的局面。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带来了整个科学王国的繁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展望科学发展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科学理论之花,将在两大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开放思维、综合研究及其实践的土壤中盛开。面临着两大科学的合流,我们的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21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它昭示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去迎接新的纪元,去“拥抱科学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