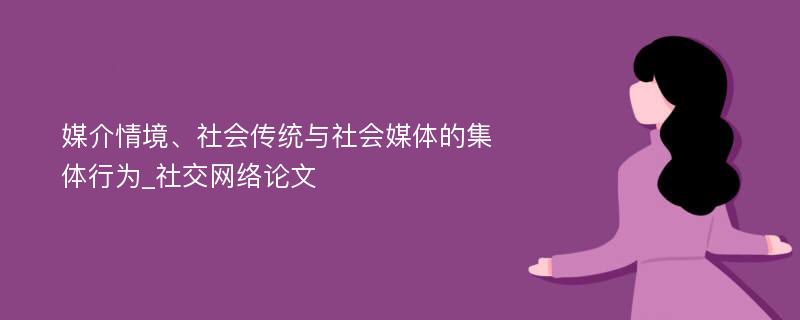
媒介情境、社会传统与社交媒体集合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媒介论文,社交论文,传统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拉伯之春的出现,绝非孤立的事件。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几乎都成功地瓦解了传统政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变,民众并不买账。皮尤的一项调查显示,埃及民众对现有政府的不满已经回到骚乱前的水平了①。回顾阿拉伯地区的社会变革,社会事件成为引爆公众情绪的导火索。看起来很偶然的社会小事件,却带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正好印证了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科技的威力无远弗届,并且在信息扩散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警惕唯科技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社交媒体虽然风靡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但因此带来的集合行为,后果却是极其不同。
一、社交媒体的革命性
社交媒体是信息传播科技的一个重要创举。社交媒体指的是网络使用者在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网络中生产、分享、交换信息和思想的交互行为,其技术基础是web2.0的互动,其思想基础是使用者生产内容。②社交媒体在信息质量③、到达率、可用性、直接性和持久性④方面都超越了传统媒体。相对于传统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秩序而言,社交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流通,强化了使用者的主动权。传统媒介的生产,大都是专业媒介机构的工作,它们掌握着信息的采集和加工。社交媒体开创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守门人的新时代,传统的社会信息管理秩序也面临极大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秩序已经被彻底重构。
在重构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秩序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大大不同于往昔。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构建自己的交流圈,主要目的有三:实现社会声望、寻找工作机会和赚取收益⑤。这三个目标,在全球任何一个社交网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可以被称为是社交网络的基本目标。不同的是,在有些国家,社交媒体的使用,变成了积聚社会力量的工具。阿拉伯地区的骚乱和最后的政权更迭,就是社交媒体积聚社会力量产生的强大后果。这也就是说,同样的媒介情境,并不一定制造了相同的社会趋向。在讨论社交媒体对人造成的后果时,不能单纯就社交媒体进行考量,而应该载入一些其他变量。因此不仅要分析媒介情境,而且要考察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传统不同的结果,本文的目标是引入这两个变量,试图解释社交媒体在不同国家的影响。
二、分析工具
1.媒介情境
本文所言媒介情境是基于麦克卢汉和梅洛维茨的媒介观念。媒介情境指的是通过媒介接触,使用者感受到的生活环境。媒介塑造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媒介功能的应有之义。不同的媒介给使用者带来不同的体验,而习惯于某一稳定媒介情境的人,在遇到不同情境时,就会出现迷失和错乱。这个概念最初的提出者是梅洛维茨,它的基础有三:即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和高夫曼的社会情境论。麦克卢汉(1976)指出,每种媒介都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媒介通过并按摩了人的中枢神经。鉴于这种效果是可以累积的⑥,媒介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不同媒介作用于人们的感知系统的方式不一样,会生产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譬如,报刊和书籍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当人们有了报刊阅读习惯时,严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就形成了。广播是主要刺激人的听觉系统,不需要识字能力,广播使传统的价值迅速消褪,造成了非理性思维的活跃。在麦克卢汉生活的年代,多媒体尚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不难理解,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的媒介,不断地交互,其作用于人的结果,最大的影响力不在于媒介内容的陈词滥调,而在于媒介形式开创了人的生活新方式。套用麦克卢汉的观点,就是创造了人类生活的新经验。
既然媒介形式如此重要,媒介形式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重组。梅洛维茨观念的另一个来源是英尼斯的媒介偏倚理论。英尼斯认为,媒介类型造成了媒介偏倚的不同趋向。因为不同媒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表现不同,帝国秩序的存废也有了空间感⑦。梅洛维茨继续了英尼斯的观念,他认为(1985),比起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其中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令人瞩目,因为它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和削弱自然环境及物质“场所”间一贯密切的联系⑧。梅洛维茨认为,在组织社会环境方面,媒介成就了空间。不同的媒介空间联系着人们的行动。人们的行动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特定媒介的独特性。对广播的媒介情境,梅洛维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解释。在其指认的广播媒介情境基础上,我们得以通过历史资料去推论报刊的媒介情境。同样,我们对普遍使用的媒介现状,也可以进行分析。而对于新媒体的媒介情境,目前为止尚未达成独特和精髓的看法,它是社会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五大趋势之一⑨。梅洛维茨在吸收了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将媒介创造的生活方式,纳入社会交往的结构中,从结构与功能论的观念出发,指出了媒介的社会影响。
媒介情境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性要素,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的。在平面媒介时代,人们可以体验的媒介情境相对单一,也即是,社会个体的生活比较稳定。电子媒介时代到来后,人们遇到多种传播情境,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会发现社会秩序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很容易产生出“社会正在堕落”的观念。同样的道理,习惯于大众传播的个体,在新媒体的人际交流中,就容易产生恐惧。人们总是无法保持高度协调的比例,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媒介情境。大部分情况下,社会人必然要面对的是,情境的分离和重组。梅洛维茨指出,不同情境的重叠或混淆会引起行为的错乱,因此,真正不同的行为需要对应着不同的情境。重要的是,在web2.0中形成的社会网络,看起来虽然易碎,却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像Facebook和YouTube,逐渐地蚕食着传统媒体的权威。美国人通过Facebook或者YouTube,张贴自己选择的信息,满足了个体传播社会新闻和政治新闻的需要,正在改变人们的集体记忆。⑩
2.社会传统
如果媒介情境的解释力是足够的,那么,我们就有信心通过媒介情境去分析集合行为。我们注意到,此理论从媒介的结构出发,发现了多重情境的社会影响。但是,把社会行为归结为由媒介所创造,有些过分乐观。因为,如果媒介情境的解释力足够,那就意味着接触了同样媒介的人们,会在日常活动中显示出一样的行为来。同样,接触了大众传播情境,加入人际传播,人们的反应也应该一样。如此就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囹圄了。
就社会历史的进展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不尽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都与技术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历史的撰写方法,是以技术为标志的,很容易让人们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社会的进展,都源于技术的创造。诚然,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极为关键,但是社会历史习惯对工具和技术的效果形成也具有加速或阻滞的作用。比如,古代的驿政或者驿站制度是个很好的创造。无论是在古罗马时期,还是中国的汉唐及以前,对驿站都相当重视。历史学家认为,“在从北部海岸到意大利南部的罗马之路(Roman Long Road)上,每隔30公里就有一个类似的驿站”(11)。驿站的设立,不仅是为战时之需,更重要的是联系百姓出行。正因为这种做法,才有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反观中国的驿站,就少了为百姓服务的功能。它们通常只是为了传递情报,或者在信件、情报到达以后,为情报员提供休息或者马匹更换。同样的创新,不同的结果。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必然混合着社会的逻辑。之所以在中国驿站功能单一,与中国早期的通信历史有关系。中国社会通常把驿站制度,表述为邮驿制度。“邮”字,语出《孟子·公孙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里所谓的“邮”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传送情报,更核心的业务是传送政令。从春秋、左传等书,可知当时通信之方式有三种:一是“传”,为车递;二是“邮”,为步递;三是“驿”,为马递,综称“传遽”,后因车递费用太大,渐不使用,只剩步递及马递,故改称为“邮驿”站。汉朝许慎著作《说文解字》指出:“邮者,境上传书舍也”,“邮”即是传送命令之站,古设“驿站”及“邮亭”。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邮驿制度,基本上只是官方专享的,它排除了民间用途。这大概可以说,“并非条条道路通长安”吧。
显然,看起来一样的事物,在服务对象和内容上却有很大差异。这就不得不说到社会传统的差异,社会传统的差异不是社会制度问题。在过去,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中世纪在制度层面有着比较广泛的相似性,但相似的制度之下,对待科技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个广为大家引用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中国我们把它变成了娱乐手段,在西方却成为社会转型和开启民智的车轮,这里的差异,其实就是社会传统的差异。古希腊时期,就有着辩论和公开演讲的说法。希腊的城邦制,加强了君主统治的开明。再想想古罗马的《每日纪闻》,这份古代报纸是凯撒大帝与元老院长老对抗的工具之一。当信息被扩散出去,社会意见就会形成压力。反观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平民阶层,统治者试图将信息局限在某些空间内。国王或皇帝,要么就是控制一切,要么就是受皇室大臣和外戚控制。这样的传统,对媒介创造的情境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西方备受震动的事件,在中国也许什么影响都没有。
所以,媒介情境的解释力,需要一个新的参照指标,以便更好地解释媒介影响,这个指标体系就是社会传统。事实上,梅洛维茨的媒介理论在作者自己看来,也是有必要修正的,他在《全球本土化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了虽然我们越来越全球化,但事实上我们的经验都是在地性的(12)。在地性经验离不开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传统所扮演的作用,帕特南在《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了意大利民主的南北差异。虽然有批评家指出帕特南未能准确地描述意大利南方曾经是殖民地的历史(13),但该书仍然证明了社会传统扮演着关键角色(14)。除了政治学研究的进展外,经济学、诸如制度变迁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传统的价值。制度变迁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诺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的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15)。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效,取决于社会传统和人们的对技术创新的期望。社会传统既有可能保障制度的存在,也有可能构成威胁。在社会传统与技术创新的方向一致时,就会大大推动科技创新;相反,就会形成阻碍。社会传统是维持社会连续性的工具,一个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传统力量的强弱,因为制度能不能推行,关键要看社会传统有没有转移方向的动力。
三、社交媒介之前的集合行为理论
在确认了媒介情境和社会传统后,我们来看集合行为理论的研究。勒庞撰写的《乌合之众》(16),大概是集合行为理论最早成型的著作。勒庞研究了群体心理,他认为,群体心理很容易受到群体统一律和群体成员的感染,从而造成大规模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社会理论通常做如下假设:作为社会个体,其行动在参照他人的信息基础上,形成个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通常,在没有交换信息的时候,个体的行动是千差万别的。在群体行为中,个体成员会在瞬间感受到周边气氛,并依据“越是公开表达的,越可能被认为是优势意见”的逻辑,作出与其他人一起行动的决定。勒庞的群体心理认为社会成员以群体无意识为心理依赖,多数人所做的行为,未必会受到惩罚,从而增加了非理性的社会冲突。“在群体性事件中,个人的力量湮灭于群体中,个人的身份也隐藏于群体之中,行为的匿名性和情绪的传染性致使群体性中的个人会呈现出急剧的狂热状态,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17)。需要指出的是,勒庞的感染理论在充分考察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对媒介环境进行了质性考察。勒庞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心理形式和城邦政权的环境限制,社会传统只能影响后来者,不能逆反。意即新的情境不能用来解释新情境出现之前的活动(18)。在以报刊为情境的社会秩序里,等级体系是坚定的。勒庞之所以发出悲叹,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来被剥夺社会资源分享的人群开始要求分享社会资源。社会个体在旧有的秩序中,是无法享用这些社会产品的。现在随着无声电影和广播的出现,社会信息逐渐从精英阶层的垄断中扩散到社会一般群众。虽然只是萌芽的状态,但体现了追逐分享的权利要求。贵族阶层的权利在受到普通群众影响时,他们容易出现对普通群众的肆意贬低。
感染理论重在推测群众情绪的转变,模仿理论是对感染理论的发展,重在讨论社会行动的生产机制。20世纪60年代,斯梅尔塞提出了集合行为的基本条件论(又称价值附加理论),认为集合行为是以下要素组合——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诱发因素、行为动员、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社会控制能力——造成的社会集体行动(19)。社会条件论,指出了多元因素的存在,认为集合行为与集体行动关联在一起(20)。同时期的集合理论还有紧急规范理论。研究者认为,突发事件出现时,人们之间通过互动会产生一种“紧急规范”,以此形成社会压力,迫使其他人去仿效和遵从,从而产生集合行为(21)。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都是有理性的。在集合行为中,盲目追随怎么可能出现呢?在此情境下,有人用匿名性来分析。匿名理论是指人处在一种没有明确的群体或个人标志状态下。该理论认为,在集合行为中个体之所以做出他平时很少出现甚至根本没有做过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在匿名状态之中。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他也不必担心承担破坏规范的后果。匿名心态的参与者,即便没有领导,也能形成集合行动,因为这些参与者,相信其他人跟自己一样,都是匿名做出非理性的行动(22)。
从感染理论、模仿理论、紧急规范论、匿名理论来看,它们共享的集合行为总体上接近于发生在大众或群集人群的社会行为。骚乱、乌合之众、大众歇斯底里、时尚或狂热、流言及公共舆论都是集合行为的重要表现。理论试图探讨的是参与其中的人们,如何放弃了个体性和道德判断,服从于权力领袖的意志。然而,斯梅尔塞认为,集合行为是“基于社会信念重塑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它包含能够引起巨大能量的信念和对追随信念指引所导致社会行动成功与否的评估。集合行为不是体制内的。”(23)因此,集合行为是非建制的,存在非理性的一面。集合行为表现为社会动员,在虚拟的社交网络中,集体动员与集合行为联合起来。
四、社会网络的发现和社交媒体的集合行为
研究者在经历了长期的观察后,对上述几种集合行为理论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与社会科学对网络的发现紧紧关联。社会网络,就是由社会行动者组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24)社会网络,打破了以往集合行为研究认为人们是一盘散沙,是原子状存在。社会网络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社会整体研究的清晰架构。研究者发现,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门槛(25),在社会网络中,人们的关系被重新建构。格拉诺维特指出,社会网络中的弱连接,与人们的职业追求有着密切关系(26)。我们不仅生活在社会网络中,而且生活在虚拟的互联网络中。互联网加剧了虚拟社会关系取向(27),社交媒体是更加真实的虚拟关系网络。
社交媒体虚拟关系网络,是一种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28)。共同体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可感知类似个体的集合,传统的共同体往往通过面对面互动形成。社交媒体是整合的、公开的、公共的信息交流平台,在信息传播中形成情感和思想的集体。社交媒体制造了非对称的社会信息交流网络,将私人信息转变为公共信息,不仅是工具性需要,也是情感性表达。负载情感信息的内容传播,增加了共同体的凝聚力。社交媒体创造的共同体,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增加凝聚力:首先媒介情境方面,社交媒体虽然可以成就大众传播情境和人际传播情境,但占主体地位的系统刺激是视觉器官,通过以视觉刺激为主的多情境融合,越来越多的个体加入到社交网络中,形成复杂和公共的信息传播网。如梅洛维茨指出的,电子媒介使原来的私人情境并入公共情境。社交平台的代码非常简单,能够迅速地集合不同经验的人群,并且顺着社会关系的渠道,循环往复,有如病毒传播一样,将不同经验的人群迅速集结起来。在私人的活动被公之于天下后,表意性的、情感性的表达,加速了媒介内容的倾向性。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的和私人的经历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很多私人的活动和情感表达能够在短时间内演化为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社交网络中是透明的。我们所做的各种活动,都在公众观察视野中。
其次,传播网的出现和非对称的社区关系。在传播活动中,为获取被关注的可能,个体需要不断生产可被人们感知的内容,甚至某些个体不惜代价,制造虚假事件,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社交媒体提供社会网络关系后,使用者需要维系已有的网络,同时尽可能扩大追随者人群,才能形成个体中心位置。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创造的关系网,通过熟悉关系,连接了陌生人。同时,社交媒体提供了多种包括图像的、文字的、视频信息的分享,促进了受众群关系的重新组合,相对于社会现实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泾渭分明,社交媒体关系网中,人们的关系很难用“差序格局”来分析。
在微博中,熟人和陌生人的界限不明显,追随者和被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有不少追随者都是默不作声或者是间歇性的发言,互动频率较低。一项研究指出,与传统的高频度互动的双向交流相比,微博的互动是J型曲线,但也创造了彼此之间的链接(29)。在一项以个人网为中心的研究中,研究者证实了跟随“Wellman 3034”的使用者,在虚拟的关系组合中,有明确的身份特征,他们可以按照需求进行整合,他们有着共享的情感关联。所以,社交媒体创造了虚拟空间的“共同体”。它不仅扩大了多种媒介情境同时出现的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文字或者图像(视频)为主的媒介情境,在融入人际交流情境后,以人际交流情境替代大众传播情境,并且将人际交流的情境转变为公共领域探视的对象。
以人际传播情境的存在形态进行大众传播的工作,是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微博传播的人际情境,一旦转变为大众传播的情境,有可能将社会个体的隐私和个人事务发展为公共空间的讨论对象。判断一个事件或者个体隐私能否成为公共讨论的问题,需要查看其是否具有社会意义。如果有社会意义,就可以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正是这一点,有效解决了既往社会学无法作答的问题,因为通过传统程序,了解事件的社会意义,需要既耗时又靡费大量财富的投票(30)。社交媒体通过追随和转发,避免了耗时和靡费财富的投票程序。节省成本和关系网的特点,为集合行为创造了便利条件。复杂适应性网络和聚合理论开始了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集合行为的局面。不像传统集合行为理论所认定的,参与集合行为的个体因为受到情绪感染,经常表现出非理性行为,复杂网络理论和聚合理论认定社会个体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目标。这两个新的理论体系是前后衔接的,聚合理论指出了集合行为中主体具有明确目标,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则指出了集合行为之所以产生能量的原因。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在理解人们如何形成群体,然后怎么实施行为的路径依赖方面和在解释快速变化的细节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31)聚合理论指出,尽管参与集合行动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相像,但是他们在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尽一致。
五、社交媒体集合行为的再解释
诚然,在不同的媒介时代,集合行为表现不尽一致。一定时期的媒介供应会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中,这源于不同媒介时代,信息的供给和人们的观念的差异。同时,因为社会传统的差异,集合行为的后果也不一样。尽管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社会结构性的压力都差不多。
社交媒体使得集合行为的情境扩大化。如今社交媒体风行,信息供给和社会个体的需要随之发生重大改观,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相对稳定的角色体系,已经转变得越来越模糊(32)。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交媒体的这个特性,大大增加了传播情境的复杂性。社交媒体使人际传播情境扩大为大众传播情境,个体的信息分享成为社会公共活动。社交媒体首先通过个体网络,快速传播信息,从特定地区扩散到全球;同时,因其可以被转发,信息超越传统的社会关系网,从熟悉人群扩散到陌生人群。如此一来,社交媒体增加了参与者的交往机会,迅速将信息连接到全球,这因此导致了社交网络的虚拟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交往的一部分。信息的瞬间全球化,增加了传播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越是不确定的,或者熵值高的信息,意味着传播的可能性越大。信息传播越多,越助长社会风险,在信息未能被多数人感知的情况下,网络讨论未能形成理性的传播流,就已经出现了集合行为。
社交媒体通过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通过连接集体行动,形成公共讨论,助长了集合行为。虽然集合行为是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确是理性的。然而,非理性集合行为借着集体行动的外衣,或者通过融合集体行动,大大增加了集合行为的破坏力。集体行动是一种基于共享理念的社会行为。蒂利指出,集体行动通过分享共同的社会观念(33),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集体行动往往与公共利益联结在一起(34),通过社交媒体,集体行动与社交媒体传播网络结合起来,能够发动更大范围的、更具有凝聚力的人群。社交媒体将社会信息和私人信息公开出来,提供了迅速暴露社会问题的空间,这些信息在朋友和更多的链接中分享,形成公开讨论。不同于以往的公共讨论内容,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从社会个体相关的信息开始的,私人内容在高度曝光后,只有极少数会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即便只有极少数信息能成为社会公共问题,这些信息,往往具有结构性特点,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关联。譬如“宜黄强拆事件”,经过当事人的爆料,迅速演变为社会问题。最初与当地管理部门和开发商的冲突,最后演变为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行动。
社交媒体上的私人信息传播,已经超越了私人特点,成为公共传播。达尔讨论说,网络内容的分享,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虚拟网络,他们的犬儒主义式表达加速了私人问题的传播(35)。私人问题在社交网络中广泛分享,传播的性质因之而发生转变,或公或私的传播、公私混合的传播都变成了公共传播。这些传播类型,在实现社会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方面,形成两种不同渠道。私人利益的扩展与虚拟网络关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称其为基于个人目标的社会实现方式;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在互惠的行为逻辑中,在参与他人的社会目标创造的镜像中实现个体利益。在个体有明确认知的时候,需要动员其关系网,以便扩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力。通过社交媒体,个体网络就像病毒的自我繁殖一样,不断扩大。在个体目标不明显时,就会以其所能接受到的他人目标为参考,通过感情支援,形成集体行动的压力。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通过广泛分享,人们形成了互惠的可能。在传统社会压力比较高的国家,这种社会动员的能力十分强大,以突尼斯和埃及来看,就是期望互惠能够为社会成员带来整体的收益。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把社会传统强调一下。集合行为的扩散如果是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区域出现,社会抗争就会非常剧烈;相反,在一个国家体系内,部分区域遭受殖民统治的,内部冲突造成的对抗激烈程度就会小很多。在那些曾经作为殖民地统治国的国家体系内,尽管冲突会很激烈,但是不会形成政治变局。社会传统不同,现实的政治制度也不同,那些完全被殖民化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外壳,但政策的执行者大部分情况下未能将其落实到位。相反,那些内生制度,或者保持了较多传统制度的国家,就会较少的受到外在信息的冲击。
在社交媒体信息扩散逻辑的影响下,集合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结构条件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集合行为的社会结构条件,深受社会传统影响。一般地说,如果传统渠道畅通,社会性压力不会发展并形成社会冲突。因为社会问题如果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就不会积聚社会压力。反之,当社会结构性压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特别是不能成为国家政治议题时,就会持续累积。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北非地区,积聚的社会压力让社会成员的日常生存受到威胁,遗憾的是,当局却不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去解决社会问题,结果越积越多,出现了政治骚乱。在这里,我们发现,社交媒体只不过是将社会事件不断放大。媒介情境提供了社会信息扩散的途径,这些信息扩散方式,都有着一些关系密度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在传播信息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关系密度较小的节点,一旦达到高密度节点需求的信息,借助那些节点,也能迅速传播信息。信息是否可以传播,关键要看个体事件与结构性压力的吻合程度,吻合程度越高,就越能出现快速增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控制能力的高低。国家制度是内生的或者外予的,对结构性压力的控制能力不同。在外予性的制度体系内,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压力,譬如失业、社会不公,甚至包括自然灾害,都可能酿成足以导致政治变革的冲突。
社交媒体增加了社会动员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呢?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具有多重的传播情境,有私人的、有公共的;有人际传播的,也有大众传播的,不同的社会情境,会让接受者不知所措。不同传播方式的交织,对接受者而言,容易造成日常生活冲突的常态化。冲突常态化,伴随着情感的传播,增长了信息的导向。社交媒体不仅是获取资源的工具,而且是表达情感的平台。在社交媒体上,社会个体发布的信息会负载更多的感情表达,大部分容易上升到社会公正问题。一旦被赋予社会公正的意义,集体行动就能迅速被动员起来。通过社交网络,这些冲突性的信息容易被放大。除了情感表达外,社交网络也会涉及到工具性表达。工具性表达,不仅仅是单一追求资源的行为,它附带有社会动员的情感。情感表达介入社会事件,就会增进极化意见的出现和扩散。反过来,极化意见强化了社交网络群体的极化水平。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有的某种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根据这种理论,原来群体支持的意见,讨论后会变得更为支持;而原来群体反对的意见,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会变得更强,最终使群体的意见出现极端化。极化意见形成社会力量,就会加剧社会紧张。
六、结语
传统媒介分析一般是从媒介创造的可能性上去探索,对于社会传统重视不够。帕特南在研究民主运作时,发掘了长久以来被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所忽视的指标。本文尝试用这两个指标重新探索社交媒体时代的集合行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情境,从本质上将风险社会的特征不断扩大,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极有可能发酵为社会混乱。我们发现,社交媒介提供了社会关系建立的新途径,在虚拟网络中,个体性事件经过社交网络传播,能够演化为公共议题。纵览全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不少集合行为,但是集合行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区域却是独特的。从颜色革命到中东变革,这些冲突仍旧在持续。社交媒体加速了集合行为和集体行动融合的步伐,使得社会事件的冲击力持续扩大。在结构性压力存在的地方,社会历史传统扮演着复杂的助推或阻滞作用。在社交网络情境中,公共议题在其关系网络中不断扩大影响力,考虑到社会传统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的交叉,最终构造了社会变革的多元方向和全球社会秩序的非整齐划一。
注释:
①Egyptians Increasingly Glum:Not Optimistic about Economy or Certain They Are Better Off Post-Mubarak,http://www.pewglobal.org/2013/05/16/egyptians-increasingly-glum/.
②Kaplan Andreas M.,Haenlein Michael (2010).Users of the world,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Business Horizons,Vol.53,Issue l.
③Agichtein,Eugene; Carlos Castillo.Debora Donato,Aristides Gionis,Gilad Mishne(2008)."Finding high-quality content in social media".WSDM08-Proceedings of 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183-193.
④Nigel Morgan,Graham Jones,Ant Hodges."Social Media".The Complete Guide to Social Media From The Social Media Guys.Retrieved 12 December 2012.
⑤Tang,Qian; Gu,Bin; Whinston,Andrew B.(2012)."Content Contribution for Revenue Sharing and Reputation in Social Media:A Dynamic Structural Model".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9:41-75.
⑥McLuhan & Fiore,1967,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An Inventory of Effects,Bantam books.
⑦Innis,Harold(2007).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Toronto:Dundurn Press,p.23.
⑧Meyrowitz,Joshua(1985).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Valkenburg,P.,Peter J.(2013).Five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of Media-Effects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7:197-215.
⑩Motti Neiger,Oren Meyers and Eyal Zandberg.On Media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
(11)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两千年前古罗马驿站,北方网,http://tech.enorth.com.cn/system/2004/12/07/000919732.shtml。
(12)Meyrowitz,J.(2004).The Rise of Glocality In:Nyiri,Kristof(2005),A Sense of Place: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Mobile Communication.Passagen,Communic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P21-30.
(13)Tarrow S.(1996).Making social science work across space and time: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0(2),P389-397.
(14)Putnam R.(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ee Chapter 1.
(15)卢栎仁:《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导刊》2010年第1期。
(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秦强、郭星华:《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8)Le Bon G.(1898).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P56.
(19)Smelser N(1967).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Free Press.P23-46.
(20)Scherer CW,Cho H.(2003).A social network contagion theory of risk perception.Risk Analysis.23(2):261-267.
(21)Mariel M,Arthur L.(2013).Emergent Norm Theory.In Ryan JM.The Wiley-Blackwell Er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John Wiley and Sons,Inc.
(22)Cadwalladr,Carole(September 8,2012)."Anonymous:behind the masks of the cyber insurgents".The Guardian.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May 2,2013.Retrieved May 2,2013.
(23)Smelser N.(1963).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Inc.P8.
(24)Stanley W.,Katherine F.(1994)."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27.
(25)Valente TW.(1996).Social network threshold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Social Networks.18(1).P69-89.
(26)Granovetter M.(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6).P1360-1380.
(27)Laser D.,Pentland A.etc,(2009).Life in the network:the coming ag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cience.2009 February 6; 323(5915):721-723.
(28)(29)Gruzd A.,Wellman B.,Takhteyev Y.(2011).Imagining Twitter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utist 55:1294.
(30)Savage N.(2009).Twitter as Medium and Message.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54(3).P18-20.
(31)Ginneken JV.(2003).Collective behavior and public opinion,Mahwah,NJ:Edbaum.
(32)[美]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郭镇之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3)Tilly R.(1986).The Contentious French: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8.
(34)Olson M.(1971).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P16.
(35)Dahlgrena P.(2005).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22(2).P147-162.
标签:社交网络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交平台论文; 网络行为论文; 社交媒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