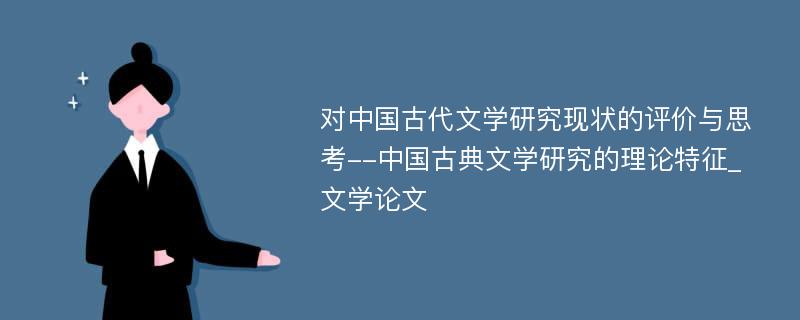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中国古典论文,现状论文,理论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人们从总体上比较国内近20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要低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这种理论品格的悬殊,是前此以往所未见的。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囫囵吞枣式地“西为中用”的躁动以后,已经渐渐恢复平静的心态,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崭新的方法理论、批评话语和操作规程。而与此同时,古典文学研究却一直深深地沉迷于“理论的困惑”之中,茫然无措,难以自拔。
我认为,近20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理论的困惑”,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伪理论形态、准理论形态和非理论形态。
所谓“伪理论形态”,指的是盲目地进口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生搬硬套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中,伪饰出种种莫测高深的“理论”和百试不爽的“方法”。有的研究者陶醉于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证,为西方的某种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或哲学理论作注解,从而证明这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有的研究者满足于以西方某种理论为工具,来剖析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削足适履或伤筋动骨,也置若罔闻,视若无睹。有的研究者则醉心于把西方某种理论作为望远镜或显微镜,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藏中寻找契合于这种理论的残瓦碎片,从而说明这种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明代文学家徐渭曾批评“以艰深文浅陋”的戏曲语言说:“锦糊灯笼,玉镶刀口,非不好看,讨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处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误入野狐作娇冶也。”(《徐文长佚草》卷二《题昆仑奴杂剧后》)这正可以移用来作这种伪理论形态的评语。
所谓“准理论形态”,指的是依傍于某种口口相传、人云亦云的现成理论,即所谓“学术界普遍公认”的理论,不加思索、不讲条件地教条演绎,依样画瓢。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吗?那么在探讨某一文学现象的成因时,有人便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发掘这一现象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是说“文学是人学”吗?那么在描述历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变迁时,有人便全神贯注地揭示不同时代人性的“进化”,解释新出现的各种文学形式是如何更为切近人性、便于表达人情的。不是说“知人论世”吗?那么在阐释某部文学作品时,有人便一劳永逸地将对作者或对社会的先验理解直接用于对作品的解读,寻求作品与作者、与社会之间直观的对应关系或简单的因果关系。殊不知,未经反思、无可证伪的所谓“理论”,归根结底只是某种准理论或前理论。当人们只是在证明或演绎一些似乎无须证明的理论时,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思维又从何谈起?
所谓“非理论形态”,指的是既把西方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各种理论,也把文学研究中所有一切理论思维,统统都视为“邪魔外道”、“野狐禅”,对之深恶痛绝,从而自觉地消解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从80年代末以来,有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者“发思古之幽情”,对博大精深的“国学”表现出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拜之情。他们对清代的乾、嘉考据之学“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提倡“回到乾、嘉学派去”,把古典文学研究里的事实缕述和细节考索看作是真正的、唯一的学问,把史料之学和考据之学看作是真正的、唯一的方法,殚精竭虑,乐此不疲。在他们看来,所谓古典文学研究,理应远离现实人生,理应步入象牙塔里,理应是一种学者的高深的智力游戏,理应是对古人古文的破译。因此,他们要么热中于穷追不舍地考证某某作家的绵远家世,要么热中于捕风捉影地附会某某作品的历史本事,要么皓首穷经于枝节末微之事,或者津津乐道于繁琐细屑之趣。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像鲁迅先生曾批评过的那样:“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小品文的危机》)。缺乏理论发掘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实现量的积累,而不能达到质的突破。
以上三种表现形态,貌似相离相反、实则相合相因,它们殊途同归地导致了古典文学研究理论品格的低下。这三种表现形态之所以盛行一时,究其原因,盖有两端:其一曰研究者的理论修养不足,其二曰研究界的学术风气不正。
出生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方面,虽然沐浴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是就其个人素质而言,“国学”根柢深厚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人的“国学”修养远逊于世纪初那些叱咤风云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更无法望乾、嘉考据大师的项背了。另一方面、他们几乎与生俱来地就受到了现代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的熏陶,因此也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西方现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然而由于缺乏扎实而系统的理论思维的训练,这种熏陶往往是不自觉的,这种根基也往往是不牢固的。宋哲朱熹曾有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子年谱》)。而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者却是:“旧学荒疏加浅薄,新知研习转迷茫。”若有若无,似深似浅,载沉载浮,——以如此这般的理论修养,投身于古典文学研究,又岂能不要么饥不择食地拿来理论就用,要么生吞活剥地照着葫芦画瓢,要么因噎废食地鄙弃一切理论?
近十几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日常生活困境的逼迫下,在功名利禄追求的驱动下,学术界浮躁之风极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假冒伪劣,剽窃抄袭,人弃我取,溜须拍马,自我推销,等等,各种各样的“短期行为”、“轰动效应”,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学术风气里,因急进心理而大量炮制伪理论,因从众心理而盲目兜销准理论,或者因逆反心理而自我标榜非理论,本为应运而生,实在不足为奇。
那么,如何拨乱反正,重铸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呢?
我认为,所谓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并不是外加于、粘贴在具体研究对象之上的,而是内蕴于、包含在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之中的,是学术研究者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的自然升华和必然归趋。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必须、也只有以具体研究对象为根基。因此,对古典文学研究来说,理论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文学现象,而绝不是某种悬想臆造、现成抄袭或进口倒卖的理论。研究者首先应沉潜于文学史料的宝藏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将他们的发现、思考与解决,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因此,我提倡“走向具体”,主张“小题大作”,而不赞成“假、大、空”式的所谓“宏观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可谓最为传统、毫不新潮的方法,然而却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这里,至为关键的是研究者对思维方式的自省与自觉,是研究者应具的思维的敏捷性和理论的判断力。
多年来,有不少脚踏实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此作过艰苦的探索。他们有的偏重于历史思维,选择古典文学传承嬗变的历史过程中某些重要环节,进行历时性的理性思考;有的擅长于逻辑思维,抽取古典文学中某些错综复杂的特殊现象,进行共时性的理论阐发;有的则综合运用历史思维与逻辑思维,竭力考察某一时代、某一作家、某一文体或某一风格的演变进程的逻辑脉络和文化根源。他们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葛晓音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相当精辟地概括道:进入“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首先在评价性方面有了进展,其后逐渐向认知性转变。我认为,无论是评价性还是认知性,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这就是阐释性,即建立在对文学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基础上的审美阐释。偏重评价,可以发掘古典文学的文化底蕴;偏重认知,可以勾勒古典文学的历史状貌;偏重阐释,可以阐发古典文学的审美意味。但是,研究者的个人的兴趣固然可以有所偏好,而研究的过程却不能不兼顾三方。如果要在整体上重铸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就有必要对评价性、认知性和阐释性,在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上进行整合,力求做到以认知性为基础,以阐释性为途径,以评价性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