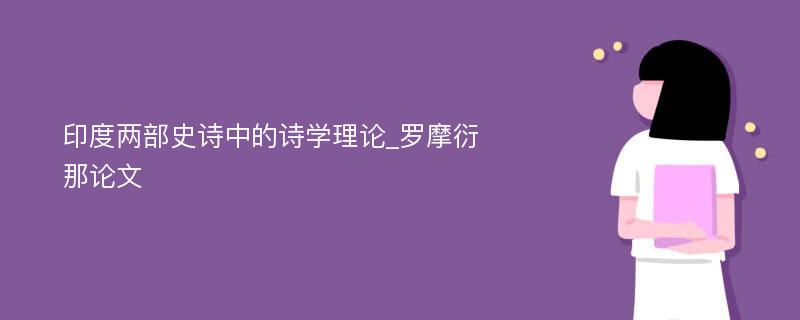
印度两大史诗中的诗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两大论文,的诗论文,学理论论文,史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是吠陀诗和奥义书诗歌后突起的两座奇峰,是印度原始诗歌向成熟诗歌转折标志。它们既保留着原始诗歌的基本特点,又表现出诗人创作的某些新趋势。由于两大史诗是“最初的诗”和“历史传说”,因此它们以丰富深邃的思想和完整美妙的韵律、以细腻的叙述和炽烈的情感表现,奠定了后世印度诗歌的美学特征。
一、史诗象征观念的审美表现
象征思维是用某种感性的形象或符号来表达主体所意会到的观念。象征既可以意指具体的事物,又可以意指某些看不见的抽象观念。换一种说法,象征就是“主体把某种观念意义寄寓在一种感性符号中”。[①]因此,象征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象征同艺术重合在一起了。更直截了当地说,象征思维也就是艺术思维,象征的表现方法也就是艺术表现方法的一种。
黑格尔把东方艺术确定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类型,即象征型艺术,并且把印度艺术作为东方象征型艺术的代表。为什么古代东方人要运用象征这一思维形式呢?黑格尔认为:“因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的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他们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他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这里的表现,即感性事物或形象,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②]这就是说,象征性符号同表象的区别在于它有两种意义,它作为事物的符号而具有表面意义以及它被主体所赋予的意义即隐蔽的意义。而只有后一种意义才构成象征物的真正意义。因此,象征思维中的符号及其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借喻和隐喻的关系。象征的本质是借此而言彼,形象与事件表面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现象、事件的表面意义去洞察内在的、更隐秘的含义。按现代术语来说,象征就是要透过语句和语义层面,透过形象符号的外部形式揭示出它内在的隐义层面。象征思维是原始时代的重要的、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原始人总是在心里呈现现实映象的同时,呈现出另一幻想的神秘意象,史前的象征思维就是物象和观念、映象和幻象的无意识的互渗。正如麦克斯·缪勒所指出的那样:印度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透过有限事物的形式去追寻其中的无限——神的本体。原始的象征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被印度审美思维保留和传承下来。这在吠陀诗歌和奥义书及两大史诗中得到确凿的证明。就两大史诗而言,它们总体上就是把遥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加以象征化理解和表现的结果。这种表现的目的在于传达出宗教的、人生哲学的、超验哲学的、伦理的、世情的等方面的根本观念——达磨,并努力去描述那不可描述之物——永恒的神或宇宙的绝对本体。
印度学者苏克坦卡尔指出:《摩诃婆罗多》的象征意义在于表现:“两个理想中的集体,一个是道德的集体,天神们参加其中,以英雄与正直的个人面目出现,另一个是邪恶的,或者说非道德的集体,它是前者摧毁的对象。”[③]《罗摩衍那》的象征含义是通过毗湿奴化身的坚持正法而历尽人世艰险痛苦的英雄罗摩同各种非正法的邪恶势力的斗争,维护了社会和宇宙的合谐平衡。这种冲突仅仅是宇宙无限存在中的一个瞬间的、不合谐的过程,通过这冲突争斗,又使宇宙恢复原有的平衡态。根据这一象征原则,两大史诗中充满了各种象征意蕴。
就俱卢大战所发生的地点来说,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从名称看,俱卢之野就是“正法之野”(直译为“达磨之地”),也就是远古时代的“普五”;“在第二与第三由伽(时代)之间,卓越的执武器者(持斧)罗摩为仇恨所激,不止一次杀戮了刹帝利五族。他暴烈似火,以自己的力量消灭了刹帝利,在普五地方造成了五座血池。他怒火攻心,在这些血池之间向祖先献祭。……那些血池一带地方从此名为福地‘普五’。在第三与(第四)迦利由伽(时代)之间,在普五地方发生了俱卢族和般度族的两军大战。”[④]这就意味着这一地方正是演示世界从创造到毁灭,又从毁灭到新的和谐的舞台。此外,又象征“发生在人自身内部的精神冲突在普遍的历史背景上映射出来的一幅图形。……在《薄伽梵歌》的数论——瑜珈术语中,俱卢之野的野字正是身体的专名:这身体被人称作‘原野’。”[⑤]也就是说,俱卢之野上的大战象征人体内部物欲、权势、邪恶的力量同正法、善良等正义力量之间的冲突搏斗。通过俱卢之地的大战,人获得了新生,宇宙秩序得到了恢复。因此,奥义书中把俱卢之野又称作“不离地”,即神仙和凡人常聚之所。在印度的传说中,凡在该地逝世的人,必然得到解脱,死后由湿婆神救度到永恒境界。这地方是湿婆不离弃的地方,因此名为“不离地”,是为圣地,这种信仰至今不衰。[⑥]
就史诗的人物而论,他们是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和坏蛋,但在宗教哲学的象征意义上,他们都是某种抽象观念的象征表达,是概念的人物化或形象化。
例如,罗摩就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象征正义、善良和秩序;他的妻子悉多是大地之女,象征生命与美;他们的结合与离别则象征天地之分合。以罗波那为首的罗刹,象征破坏与非正法、丑与邪恶。《摩诃婆罗多》以树的形体象征俱卢族和般度族所分别代表的善恶美丑、正法与非正法、创造与毁灭的两大株系:“难敌是一株忿恨构成的大树,迦尔纳是树干,沙恭尼是其枝柯,难降是茂盛的花果,根是昏聩的老王持国。坚战是正法构成的大树,阿周那是树干,怖军是其枝柯,玛德利之子(无种和偕天)是茂盛的花果,根是黑天、梵、婆罗门。”[⑦]在这两大株系总的象征意义中,每个人又有具体的象征含义:
坚战被象征为正法。他的称号是正法之王,是法神(法的抽象概念)的儿子,梵文叫达磨苏多或达磨苏奴。他是法神的肉体化身。他整个生命是按照正法的性状铸成的。英勇扫敌的毗摩是风神的化身。阿周那是因陀罗之子,又被象征为克利希纳(黑天)的现实物质生命。黑公主是火神之女,象征祭火的神圣与纯洁。
俱卢族兄弟被象征为天神的死敌阿修罗的化身。难敌就是最邪恶的魔鬼迦里。沙恭尼是迦里形影不离的帮手陀伐婆罗。瞎眼国王持国是不幸、恶运、祸患、预示灾难的不祥之兆之神阿利斯德的一个儿子享斯的化身。
黑天是宇宙最高神毗湿奴或者克利希纳的肉身形式。他是包容了创造与毁灭的绝对的“一”,因此,大战前难敌和阿周那都希望得到黑天的同情和支持。《备战篇》有一个插话说明了正法的阿周那和非正法的难敌对黑天的各取所需的态度:难敌和阿周那同一天到达黑天所住的多门岛,都请求黑天的支持。黑天答应一视同仁地支持双方:他可以把军队去支持一方,他自己可以为另一方亲自参战。难敌选择了军队,阿周那选择了黑天本人。一方选择了物质力量和实利,另一方选择了荣誉、声名和精神思维。
在超验哲学的意义上,史诗暗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人的内心中进行的善与恶、现实物欲和精神解脱这两种倾向的不断的冲突。黑天和阿周那就象征为一身体中的二重灵魂:人的灵魂和神的灵魂,或者说是存在于同一肉体中的经验的自我和先验的自我(神我)。这个象征在《奥义书》中表现为人的身体是车,个人的心灵是乘车的人,而觉(智慧)是驾车的驭者;在《薄伽梵歌》中,个人的身体是车,个人的心灵是乘车的人,驾驭车的是最高的自我——黑天。苏克坦卡尔指出:“创作史诗的诗人们自始至终把大神黑天看成是最高的自我,而把阿周那看成生命的自我。”这场大战实际上表现了每个人内心中都存在的痛苦搏斗:“一场人与自己的卑下的自我,经验的自我,以及它的帮手:情欲、冲动、贪婪、忌妒和怨尤进行的战斗。”[⑧]对此,在《薄伽梵歌》如是说:“如果自我克制自我,自我便是自我之友,倘若不能克制自我,自我如敌而结怨仇。”[⑨]所以,在黑天精神的感召下,阿周那才能够超越了现实的血缘关系的束缚,站在替天行道的立场去进行战斗。阿周那同黑天的辩论,黑天大篇的说教都是象征个人内心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过程。这一过程象征了个人在前往天路中的不断净化和自我提升的历程。
在超验哲学的象征意义上,黑天、阿周那、坚战等象征着最高的自我生命的自我;而持国显然代表了经验的自我,代表了卑下的、变幻无常的人性,由于自私和愚蠢变得盲目;持国的百子代表了经验的、物欲世界的自我。总之,象征着人类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中,从不断的毁弃与净化中得到升华。正如苏克坦卡尔所说的那样:“俱卢之野同时就是人内心深处各种不同感情和欲念的战场,即人的高尚的品格相互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大战的战场。……史诗的作者把一场发生在人的高级的自我与低级自我之间的大战搬上了舞台,那个堂家族便是象征。”[⑩]
正是这种总体上和个别的象征意蕴表现了史诗时代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艺术美学的“情味”理论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史诗中的象征有一种奇特的表现方式,这就是把抽象的概念人物化、形象化。这一种方法在后来《小泥车》、《觉月初升》等戏剧中有更为明确的运用。
在《罗摩衍那》中,有不少人物就是为了表达概念而命名、而活动的。例如:罗摩流放去森林时,母亲祝福罗摩说:“记忆、坚定和达磨,儿啊!愿他们都保佑你!”这里的“记忆”、“坚定”、“达磨”都是抽象的普遍观念,也都是人格化的神。记忆是达磨和弥陀所生之女;坚定则是达磨之妻;达磨是法王。在《摩诃婆罗多》中,正法神的十位妻子是:声名、吉祥、坚定、知识、丰足、忠信、法事、觉慧、羞耻、思想。她们实际上是正法神所拥有的不可或缺的品性,但是,作者把这些概念人物化了、肉身化了。正法大神的三个儿子是平静、爱欲、快乐;而爱欲的妻子是情欲;平静的妻子是成就;快乐的妻子是欢喜等等。非法的妻子是尼梨蒂,他们所生的三个儿子是恐怖、大恐怖、死亡。(11)这就是概念的人物化的滥觞或雏形。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概念的人物化是观念的直接呈露,它已不完全符合象征的本质规定了,也就是说超越了艺术的定性而倾向哲学的抽象表述了。因此,黑格尔指出:“这种表现方式也还不能称为真正象征的。因为真正的象征应使它所运用的确定形象保持它原有的确定状态,它并不是要在形象里按照意义的普遍性而直接显出那意义,而只是用形象的某些相关联的性质去暗示那意义。”
二、在原始思维的完整性特征制导下的诗歌表现
此前说过,原始人类在表达对象时受完整性思维的制约,即原始人类有一种冲动,要求完全彻底、细致周详毫无遗漏地把所要表达的对象全部描述出来或表现出来。如果不这样完整地表现,他们就会认为不真实,而不真实就不能完全地认知和把握对象,就必然产生惶惑感,哪怕事实上难以真实也要用想象的方式去弥补它、完善它。正是这种强烈的认知冲动,才促成原始人类去熟悉对象、认真地观察对象,把对象予以详细分类、比较、排列组合并纳入某种秩序中去。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它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12)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原始人类在认知对象和再现对象时,就非常准确、细致、详尽、全面。这种思维定势反映在绘画中,就是正面律、散点透视和无遮扫原则;反映在雕塑中就是突出特征和注意细节表现;在原始诗歌和叙事作品中,就是追求绝对的真实(最完全地符合事实)的叙述、重复和过分繁琐的交待、非善即恶和以绝对美和绝对坏的方式塑造人物、环中环(即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方式等。
史诗追求以绝对的真实来表现事件、人物和环境等。因此,史诗就把真实性当作诗学的第一要义。在《罗摩衍那·童年篇》第二章中,当诗人蚁垤咏唱出了他真情流露的小诗后,大梵天来到诗人身边,授意他“来编写篡述罗摩故事全传。”大梵天嘱咐诗人:“你就把这勇士的故事叙述,象从那罗陀嘴里听到的那样。……聪明的罗摩的奇遇,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有关罗什曼那和罗刹的,你都要一一加以论叙。有关毗提诃公主的事(指悉多——译者),不管公开的还是秘密,有的你已经有所了解,有的你可能还不知悉。在你的诗篇里面,不要有任何不真实。”(13)从大梵天的神谕中,表明了这几层文学理论思想:第一,尊重传说故事原型,保持传说中的历史真实;第二,把英雄及妻子和恶魔的事迹要详尽叙述;第三,要真实地表现,知道的要表现,“不知悉”的或秘密的也要表现;至于如何表现“不知悉”的和“秘密的”则没有发挥意见。可以认为最后一点要求,既包含着故事事实本身,也包括人物的真实情感,因为个人情感总是显得隐秘的。正是这一最重要的诗学理论,决定了史诗在艺术表现方式和思想倾向上的基本特点。
首先,就叙事方式来说,两大史诗在介绍基本事实方面可谓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其目的就是为了最真实地再现传说。
史诗非常详尽地介绍所触及到的每一个家族的谱系,并在叙述中把每一个著名成员及所涉及到的其他人的故事又详细地讲述。在《摩诃婆罗多》中,不仅把俱卢族的远祖到大战发生时的家谱都毫无遗漏地介绍,而且把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的名字都罗列出来。在叙述蛇祭的缘起和祭祀过程时,把这事件的来源从头到尾地讲述一遍,并把百种以上的蛇按不同的种类和名称加以详尽地罗列,同样,叙述国王豆扇陀非常勇武,杀死了许多老虎,就把国王所使用的全部武器种类、杀死老虎的种种杀戮方式及各种老虎的名称、色泽都细细道来,并形成了介绍任何一个人或物的故事,都要介绍他的家族谱系及祖辈的故事,然后才慢慢讲述到眼前的事件来的叙事模式。如谈到湿婆四面脸,马上就抛开故事去讲这四面脸的由来,在介绍般度五子得到了他们的半个王国时,除详细地进述了此地的风景外,还一一罗列了其中各种树的名称等,这种叙事模式就是原始思维的完整性所制导下的叙事产物。这种叙事方式的内在动因除开因祖先崇拜而注重血缘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要求完整无遗漏地认知对象和把握对象的思维定势。列维·布留尔说:原始语言的一个最触目的特征是它“特别注意表现那些为我们的语言所省略或者不予表现的具体细节。”(14)博厄斯指出:“多数原始叙事文学的特点是不厌其烦地交待过程,列举细节,一笔不漏”。(15)正因此,史诗的叙述显得格外繁复琐细,并形成了故事中套故事这种环中环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模式在所有的古代史诗中都存在,例如《天方夜谭》也是如此,但不能说这是由哪个民族影响别的民族,而是一种人类思维共性的反映。不仅如此,而且史诗中很多地方的诗句在一节结束的地方重复同样的话语,这也是原始诗歌所遗留下来的特征,如《罗摩衍那》中,罗摩将被流放到森林中去,悉多执意要跟随丈夫前往,罗摩不愿意让悉多跟随自己去遭受森林中的苦难生活,便劝阻悉多。这第二十五章中,每一节诗的结束句都是:“森林本身就是苦恼”和“森林里面真苦恼”。这种为了追求完整全面的真实表现而采取的繁琐详尽的铺陈方式,在同时期佛教堵坡围栏的雕塑造型上也表现出来:重重叠叠的人物与植物枝蔓的繁复刻划而不留空白和空间,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其次,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由于这种完整性思维的制导作用,史诗把英雄都加以最完美的赞美和表现:好人都完美无缺,毫无瑕疵;而坏人则都一坏到底,丑恶之极;这就是原始思维所采取集中概括人物种类特征并加以抽象化后的缺少个性的类型人物或扁平人物。例如《阿逾陀篇》中叙述罗摩之美在尽其所有方面都加以最高赞美之后说:“具有人类的最优秀的品质,他具有那大地容忍一切的禀性,他在三界为所有神所重视,在智慧方面他赶得上祈祷主,在精神方面,他媲美纯洁主子。”塑造国王豆扇陀之完美形象则是:“有一身神奇的伟力,坚如金刚,风华正茂,有河流密林的曼陀罗山,他能用两臂举起来搬走,弯弓射箭,抡杵大战,挥刀舞剑的格斗厮杀,骑象打仗,纵马沙场,各种武艺他都十分娴熟,他具有毗湿奴的臂力,有太阳似的璀璨光辉,如同海洋一般深沉,像大地一样度量宽广”。(16)所以《罗摩衍那》中谈到阿逾陀城中的人或事物都完美无缺:“凡是完美的人,都具有一切妙相。”这种完整性思维是不能理解辩证思维支配下所用的好中有坏,恶中有善,美中有丑,丑中有美的塑造人物的方法的,这种人物对史诗时代的作者和听众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
三、史诗中比喻方式的运用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性同造型艺术的形象性有本质的差别。造型艺术的形象是视觉直观的形象,是有一定的空间体积、面积及线条、轮廓、色彩的固定形象。文学艺术的形象性本质上只是一种通过想象而构成的内心表象,即心象、意象。这种形象固然来自现实生活与自然,但是在传达方式上,它们受到了根本的阻隔:即他们不能拥有二维或三维的空间形式和物质特征,所以,就诗的形象本身而言是不能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形象的,正因此苏格拉底才问道“看不见的东西能够模仿吗?”(17)可见,心象、意象是不可直观的,不可能以物质形象的方式来表现,只能借助想象来促成心象、意象,只能采取比喻的方式来唤起近似的想象和相同的情绪感受。
史诗在这一方面正是充分地表现了文学表现的比喻方式,大量地以自然形象来比喻、来传达心象和意象。例如,《罗摩衍那》中,当罗摩被立为太子时,民众非常高兴:“他们伸出了合捧的双手,好象一朵一朵的莲花。”写罗摩宫殿的欢乐气氛时是:“罗摩的宫殿闪耀辉煌,象是飞满了狂乐的小鸟、布满了盛开的荷花的池塘。”小王后吉迦伊的驼背女仆曼他罗非常丑陋,但是当她给吉迦伊出了坏主意后,吉伽伊这样赞美她:“有许多弯腰的驼背,样子丑怪,性情乖张。可你却象那风折荷花,看上去那样地漂亮。”曼他罗刺激吉迦伊的盲目高兴时说:“你那幸福真容易破碎,就好象夏天河流里的细流。”罗摩母亲听到了罗摩失去王位并将放逐森林时就“象芭蕉一样往下倒。”罗摩将去森林,他的母亲宁可放弃王后身分要跟随罗摩去森林中,她说:“自己的牛犊子走了,母牛怎能不在后面跟?”“我失掉了你,就象母牛失去了牛犊。”她的“眼中流出了眼泪,好象河流新涨雨水流出。”悉多要跟随罗摩去森林,高声地又哭又喊,“控制住的眼泪流了出来,象是钻木冒出了火焰。她那痛苦产生的泪水,象水晶地光华,从她两眼里流出来,有如水珠溅上了荷花。”十车王死去,宫中的妇女们“她们浑身发抖,……她们好象是草叶子,在逆风中摇摆不己。”(18)在《摩诃婆罗多》中描写俱卢族的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都迅速长大时说:“他们全都长大起来了,犹如湖水中的朵朵莲花。”写罗刹女爱上怖军时说她“宛若一株羞怯的藤萝。”(19)类似的描写在诗中比比皆是,成为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这种比喻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整个印度文学创作。我们在迦梨陀婆和泰戈尔的作品中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史诗比喻手法的影响。
四、万物有情与情味理论
在原始万物有生观、万物有灵观、轮回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印度思想往往把人、兽、物等同看待,统统把它们归纳为“有生类”,并竭力抹杀人、兽、物之间的界线,把人叫做“prana”(气息、呼吸)、“pranin”(生物、复数为众生);把人或万物都叫做“bhuta”(万物、万有)、“sattva”(生灵、存在)或者“jivaloka”(有生界)。梵文中尽管也有“人类”的一些词汇,但更习惯的用法则是“有生类”这类词汇。例如,佛教徒把释迦牟尼称为“两足尊”,人同其他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足的多少而已。可见,印度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等,都是“有生界”的一种,其共同性的基础是生命的存在。因此,达磨之法适用于任何有生物,是一切众生的生存关系准则。《奥义书》和佛经《法句经》也宣扬“人兽等同”论,“一切有生类都爱惜生命”之类的话比比皆是。在《奥义书》《摩奴法论》和其他教派的典籍中,都把有生类的区别按照出生的方式分为:胎生、卵生、湿生(有湿气产生的生物,如蚊、虱子)、芽生(植物)等。万物有生命,万物有思想感情,因此人、物相相同通,故印度宗教都宣扬不杀生。所以一切有生类也叫“有情”。人与动植物之间可以沟通、互渗、互变,因为都是五种大原素和细微元素组成,只是表面形态不同而已,这就形成了“万物有情观”。
正是这种万物有情观决定了两大史诗和后来的印度文学打通了人与动植物的界线,把一切有情物都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来渲染情感。例如,《罗摩衍那》中,罗摩为了忠孝而被迫离开阿逾陀城去森林中流放时,亲友和民众都极度悲愤伤心,史诗为了加强情感表现的力度,把一切“有情”之物的情感都加以描写:
连那一些大树也都枯萎,
带着花朵、嫩枝和蓓蕾,
都为罗摩受难而伤悲。
爬行的动物不再爬,
野兽都不再游行;
大树也为罗摩担忧,
现在变得寂静无声。
在那多泥的水里,
荷花叶子都已隐去;
荷花池中荷花干枯,
再也没有飞鸟和游鱼。
长在水里的鲜花,
长在陆上的花朵,
今天不再芬芳灿烂,
不象从前飘香结果。
悉多被罗刹罗波那劫持后,罗摩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到处找寻悉多,罗摩悲伤地询问胡椒树,问无忧树,问多罗树,问大山,问河流,问小鹿、大象、老虎等“有情物”是否看见了悉多,这就把万物的同情和罗摩缠绵悱恻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史诗的作者看来,山亦有情,水亦有情:“有一条珠贝河流向婆薮王的都城。有灵性的噪鸣山出于爱慕之情,把她半路拦住了。婆薮王朝那座山踢了一脚,珠贝河便从那个踢开的缺口(山谷)穿流而过了。噪鸣山与珠贝河生下了一双儿女,河流随之获得了自由。河流女身十分高兴,把一双儿女送给了国王。那一个男儿,……婆薮让他当了军队的统帅,成了镇伏敌人的英雄;而那个少女,名唤山娘,国王娶了他做爱妻。”(20)这说明万物之间没有任何阻隔。这就大大扩展了表现有情世界的范围。
不仅如此,在万物有情观的制约下,史诗时期的人们相信人、兽、物之间的交感互渗、互变、人与动物之间不存在感情和思想上的界线。这在两大史诗中表现为人与动植物的互变、互渗上。例如,在《摩诃婆罗多》中,有一个仙人名叫千足,因为被婆罗们诅咒而变成了大蜥蜴;一位名叫紧陀摩的仙人和一头母鹿结为配偶,变成了一头公鹿,和许多麋鹿一起优游在林莽深处。当他正同母鹿交配时,被般度王射杀;蛇王多刹迦变成裸体的出家人偷走了优腾迦的耳环;行落的母亲肚子里正怀着行落时被变形为野猪的罗刹驮走,他母亲受了惊吓而生了行落。在《罗摩衍那》中,一个叫做挢尸吉的女人变成了挢尸吉河;天女兰跋变成了一只迷人的杜鹃,后来又变成了百灵鸟;喜马拉雅山生下两个女儿;恒河和优摩,她们的母亲是须弥山;在《阿逾陀篇》中,一条牛向国王诉苦:“我自己的两个儿子受苦,我看在眼里不禁心酸,看到它俩消瘦痛苦,受熬煎在阳光下。….这两头牛被农民用鞭子痛打。它俩是我所生,现在负重受艰辛;我看了心里难过,谁也比不上儿子亲。”(21)
万物有情正是一切生命体的自然本性,是达磨这一宇宙精神本质的显现。人情、世情的自然流露中显现出梵性,这也就是万物皆梵的道理。符合达磨、顺其自然就是要尊重自然物的生命和情感,在人与万物的和睦相处中,在人与物的交感互渗中就体现出了梵的合谐本性,即梵本质的“一”与万物之多的统一与和谐。史诗中这一基本思想决定了其美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决定“物感”的自然审美观及其表现方法。
第二,决定了印度美学情味理论的雏形。
万物有灵有情,情可动人,形可愉人,这是印度自然美感产生的基本要素。
在《摩诃婆罗多》中,般度王无意中射杀了正在交配中的雄鹿,雄鹿乃是仙人紧陀摩所变形,他死时诅咒般度王:他将死在同妻子交配之时。从此,般度就严格恪守不与妻子交配的禁忌。然而,当般度王带着几个王后在百峰山上隐居修炼之际,正值“盛春时节,树木枝头鲜花烂漫,一切众生都为之心迷神乱。一天,般度王偕同妻子在森林中漫游。林中的波罗莎树,体罗迦树,芒果树,赡波迦树,波利跋陀罗迦树,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树木,果实累累,鲜花吐艳扬芬。又有形状不一的湖泊,红莲灼灼的一处处莲池,森林中风光旖旎。般度王观赏着森林,心中油然生出一片春情。他心情怡悦,……当时,只有玛德利追随左右,身穿一件艳丽的衣裙。他看见玛德利正当青春妙龄,薄裙裹身,他的情欲猛然勃发,犹如林中野火蓦地燃烧起来。……般度王情欲迷心,竟然忘记了那一诅咒,他依据交合之正法,几乎是强迫玛德利。这位俱卢的子孙,在情爱的控制下,走向生命的尽头。……终于落入了死神正法的控制下。”(22)同样,在《罗摩衍那》中,罗摩因流放来到了荒无人迹的大森林中,见到了各种动物自由自在的安静生活和植物勃勃的生机,“他也心旷神怡。从城里流放出来,忧愁为之一洗。”(23)自然事物和风景之美使人的生命同万物的生命交感交融在一起,使人心旷神怡,情绪激荡,获得了最大的审美愉悦,这就是自然美何以为美的原因。审美的愉悦起源于“物感”,起源于人的个体生命同大自然的博大生命的融汇之中。人与自然的最大程度的合谐就是美。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印度美学思想最重要和最根本之处。这一美学思想同中国古典美学的“物感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歌创作的审美激情和原动力时也说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陆机在《文赋》中也说道,大自然不同气候和自然景物的生命形式,激发起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产生不同的人生感受。在两大史诗中,拥有许多对大自然景物的富有生命力的细致描写,这些表现大自然的画面直接反映了自然——宇宙这一伟大生命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存在,这一生命在我们周围以强大而有力的脉搏跳动着,人类一旦感受到了这强大的脉搏,便领悟出自己的生命不过是另一个更加伟大的生命的一部分,在人与大自然生命的崇高的交感中,领略到深邃的、充满人性和生命哲理的意义。
史诗通过“物感”这一审美心理的描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在于:人对大自然生命的感受和交融是诗歌创作激情和灵感的来源。
《罗摩衍那·童年篇》第二章描写诗人蚁垤听过仙人那罗陀叙述的罗摩传说后,进入神仙世界呆了半响,然后来到离恒河不远的多摩娑河岸,他看到河岸清洁无泥,感到清洁的河水真可爱,就象善人的心灵,他便沉浸在水中洗澡。清清的河水促使他依然在思索和领悟罗摩的故事,所以洗完澡后,他徜徉在无变的树林中。这时他看见“有一对麻鹬安然地、静悄悄地愉快交欢。他忽然抬眼看到,一个凶狠的尼沙陀把那公麻鹬杀死,……那只母麻鹬看到,公的被杀血满身,在地上来回翻滚,她悲鸣凄惨动人。这位仙人看到了,尼少陀杀死的麻鹬,……动了怜悯之意。为了安慰痛哭的母麻鹬,又说出了下面这一些话:“你永远也不会,尼沙陀!享有盛名获得善果;一双麻鹬耽乐交欢,你竟杀死其中一个。‘”他情不自禁地说出来的话,居然是一首小诗。诗人自己也不解:“我为那母麻鹬伤心,究竟说了些什么?”他认为“我的话都是诗,音节均等,可以配上笛子,曼声歌咏,因为它产生于我的输迦(悲痛),就叫输洛加(体),不叫别名。”这说明了诗人“非常同情这只母麻鹬,他心情沉重愁绪满怀,他真难过得支撑不住,吟出这一首输洛加来。”正在这种动物的悲惨情状的刺激下,他获取了灵感并掌握了诗的奥秘,在梵天的鼓励下开始创作《罗摩衍那》这部大诗作。这证明了交欢中的麻鹬的死亡和生离死别的悲哀之情是创作史诗的最初冲动和契机。这正如中国的《诗大序》中说的那样:“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激情的迸发,物感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是诗美的核心。
“物感”之审美思想的确立,促成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象征、比喻、借喻方法的大量运用,以动物植物的形象互渗,来充分地表现人与物的情感互感、交流,表达大千世界最丰富多采的情感和姿态。这种表现方法在印度神话中就早已存在,如在《月的一分》(许地山的中译本改名为《二十夜间》)中如此说创造女人的经过:“在天地开辟时代,大匠(创造生物的神)到了要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发现在创造男子的时候已把所有的材料用完,一点实质也没有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时间,他入了很深的禅定,到出定以后,他就照下面这样做了:他取月的圆,藤的曲,蔓的攀缘,草的颤动,芦苇的纤弱,花蕊的艳丽,叶的轻浮,象鼻的尖细,鹿眼的瞻视,蜂的丛集,日光的炫耀,层云的悲恸,飘风的变动,兔的畏怯,孔雀的浮华,鹦鹉颔下的柔软,金刚石的坚硬,蜜的甘甜,虎的残忍,火的炽热,雪的寒冷,鹊的噪,鹃的啼,鹤的虚伪,鸳鸯的忠贞,把这些性质混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将他送给男人。”(24)在史诗中,也以同样的比喻来表达人休美:例如,在人体美的表现上,两大史诗充分地把动植物的色彩、形态及力的表现来表达人体之美和对这种美的情感倾向。如比喻女性人体之美就以“眼如莲花瓣的女郎”,“她的大腿象芭蕉似的白净”,“她的身形真是花枝招展”,“面如莲花”,“口如相思果”,“鹿眼女郎”,“眼睛象鱼鳞般闪烁”,“象黄莺般宛转的细语”,“手如绵柳一样的柔软”,“大腿象象鼻一样地柔软”,“她象娇嫩的枝条那般模样”,“她的乳房象熟透的多罗果”,“她的双臂柔软就象那嫩树枝”,“她的脸庞象满月”等来表现;男性人体之美则是“身如狮胸”,牛眼的英雄”,“山峰般地挺立”等。《在摩诃婆罗多》中,美妙的爱神迦摩(又名门摩陀)所持的引发生物情欲的神弓是:以蜜蜂为弓,以鲜花为箭。
这种意象的比喻方式在同时期的《伐致呵利三百咏》中也得到同样的表现:倒如,“面容如明月,俊眼笑莲花,颜色胜黄金,黑蜂让秀发,两乳欺象颊,美臀如重压,言语含温柔,天然妆饰女儿家。”(25)这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如对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等人,也对后来视觉艺术的造型和表现方式如绘画和雕塑、舞蹈都有深刻的影响。只要注意一下同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就可以看到史诗所描写的人体美特征,都在造型艺术中得到完全的表现。后来印度绘画的“画经”中的人物都以动植物的基本形态来有表现人体之美。直到芨多王朝时期的绘画和雕塑,“在表现身体的各部分的比例时,它不用希腊人的几何标准来度量,而是采取了在大自然中所发现的活的曲线——采自花枝生长的习性和在毛皮下动物的形体的灵活流动时所呈现的曲线,面部现在成为椭圆的卵形,而到了孟加拉的波罗王朝式的艺术中,则用了枸酱(Betal)叶子状的更为神经质的线条;在眉发间的前额要如拉开的弓形;眼眉也要象弯弓或楝树(Neem)叶子,女子的眼睛在急瞥时如脊翎,温柔时如小鹿,诸神之眼睛则比之莲花;女人的鼻子要象胡麻子花;润软、鲜红的唇则与红相思果相比;下颏比作芒果核;颈上横纹比作贝壳;身躯的柔软如母牛的口鼻;而英雄的胸膛则如雄狮的肢体;肩部与前臂要弯曲得似象鼻,前臂应象橡树干;手指的丰满如豆荚;腿的腓部要隆起象产卵的鱼;手与足则为两瓣莲花。”“这种对模仿花朵及动物曲线的研究,并使男女的姿式,相辅相依,也象并蒂的花枝一样,给印度美学的典型,注入新的生命。……从整体看起来,形成一种温柔的轮廓线,唇吻手指和乳房,都仿佛是在青春的躯干上所生长的花朵与蓓蕾一般,这样遂产生一种浑成、柔韧、朴素而且和谐的艺术,为芨多时代唤发了光彩。”(26)应该说,这种在后世文学和造型艺术所形成的定型表现方式的审美思维之根,在两大史诗时代就奠定了它的雏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季羡林指出:“真正对自然美十分敏感并且以饱满的激情加以描绘的自《罗摩衍那》始。《新梵语文学史》的作者(支坦尼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在《罗摩衍那》里看到一种对自然美的敏感性的光辉灿烂的发展’”。(27)
万物有灵、万物有情的生命观念影响了印度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情味”理论的形成。
所谓“情味”是指诗歌和其他艺术中“味”的审美特征。“味”(滋味)这一概念在印度生活与诗歌中存在很久远。在最早的吠陀诗篇中,“味”(rasa)一词是仅指植物的汁,后也用作水、奶、味,这都是引申义。在奥义书中,味一词往往被用为事物的本质、精华:如“万物的精华(rasa)是地,地的精华是水,水的精华是植物,植物的精华是人,人的精华是语言,语言的精华是梨俱,梨俱的精华是娑摩,娑摩的精华是歌唱”(《歌者奥义书》第Ⅰ,1,2)。但是直到古典时期婆罗多在《舞论》中才明确把生理意义上的“滋味”升华为核心的美学范畴,并予以具体的界定。
由于《罗摩衍那》在印度被认为是“最初的诗”,因此味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它的胚胎形式被认为在这史诗中首先出现。在《罗摩衍那·童年篇》第四章中,诗人指出:“这部诗具备有各种情绪:快乐、爱情、怜悯、忿怒、勇武、恐怖、还有厌恶”。被罗摩遗弃的两个儿子俱舍和罗婆在森林中演唱给仙人们听时,“两个人进入了情绪,就合起来纵声高歌,甜蜜、激昂又优美,音调均匀又很柔和。”“啊!这部诗歌多么美呀!特别是那些输洛迦诗篇。这些事虽然发生已很久,却象是在我们眼前一样。”(28)这里的情绪就是味。可见,情味一词本质上是主情,是情中之味。中文翻译中,有的翻译家翻译为情绪、情感,有的直接翻译为味;英文翻译也译为sentiment,即感情或情绪。那么印度美学家为什么不直接说“情”而用“味”呢?这就涉及到情味之间的关系了。
首先,就情与味的共同方面而言,可以看出,当时的印度审美观念已把生理的快感同精神的愉悦加以区分。由于精神的愉悦很难言说,很难表达出来,所以就把对生理快感的体味来比喻精神上所获得的那种特殊的审美愉悦。因此尽管用“味”一词来表达审美快感,但它已不是直接的生理需要满足后的快感了。
其次,味这一概念含有事物内在的精华、本质的意思,它所要表达的情感就是人类心理中最典型、最深切、最包容着普遍性的情感,最具有感梁性的情,而不是通常的浮泛之情。由于人类情感的表达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如动作、眼神、姿态、面容来表现,并且感情又很难确切表达,使人难以捉摸,因此,传情达意和领情会意之间,往往就需要心领神会和细细领悟,这就同生理的品味过程非常相似,因此,表情达意就被嫁接到“味”这一概念上来。这就是说,味这一概念,包容着一定的情感力度和深切幽远的意思。因此,用“味”来表“情”,正是符合印度思想中对词性要求通过表面义而领悟它的“暗示义”的思维定势。
最后,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感染、交流共鸣是一种有极大冲击力的精神活动,因此,就情绪感染方面说,味所表达之情,是康德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感情,不是那种无法引起共同感受的、共鸣的怪异乘戾之情,正如怪味是人们无从表达和交流的那样。因此,《罗摩衍那》中所表达的“悲悯”情味,及史诗中提及的其他情味,象大海之波一样,都是能充分地引起共鸣和理解,能引起人们情绪激荡的情感。这种情感情绪才能够称得上“味”。
只有在以上这几种意义上来把握“味”才能够真正深切地领悟和感受史诗所表达出来的回肠荡气的人类最普遍的最美的感情。
注释:
① 李景源:《史前认识论》,第30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8页、1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⑤⑧⑩ 《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第218、233、227—228、250、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 ⑦ (11) (16) (19) (22) 《摩诃婆罗多》,第一卷第35—36、25、190、192—194、203、348、401、117、348—3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 《五十奥义书》,第998页,徐梵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 《薄伽梵歌》,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①②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3) (18) (21) (23) (28) 《罗摩衍那》第一卷,第23—24页、第二卷第18、37、47、118、112、179、64、350、374、422—423、321、3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4)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5) 博厄斯:《原始艺术》,第29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7) 参阅鲍桑葵:《美学史》,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4)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122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
(25) 《伐致呵利三百咏》,第42页、第90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6) 常任侠:《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第27页、3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29) 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第123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标签:罗摩衍那论文; 罗摩论文; 阿周那论文; 摩诃婆罗多论文; 史诗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文化论文; 奥义书论文; 薄伽梵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