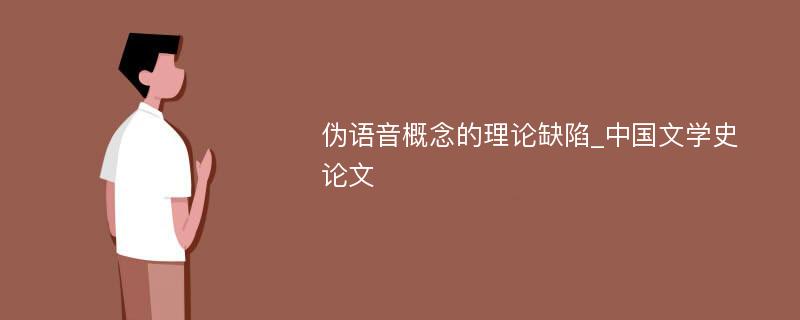
拟话本概念的理论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缺失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拟话本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一个小说文体概念,它的定义与指称对象,60年代编写的两种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做过这样的解释:“由于受到宋、元时期流行的讲述故事风气的影响,到了明代便出现了大量文人模拟这种故事形式而编写的作品,现在一般叫做‘拟话本’。”①“话本在明代,因群众的爱好,书商的大量刊行,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他们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模拟话本写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通常称为拟话本。”②拟话本就是明清时期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我们仔细考察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发现拟话本是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且不能说明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本质特征的概念。
拟话本这一概念最早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十三篇的标题为“宋元之拟话本”,该篇论列了《青琐高议》、《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宋元作品。《青琐高议》“文辞虽拙俗,然尚非话本,而文题之下,已各系以七言……皆一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末之题目与正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及文章”③。《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及《大宋宣和遗事》,“皆首尾与诗相始终,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词句多俚,顾与话本又不同,近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④。因而将它们称之为“拟话本”。鲁迅最初提出拟话本,并不是作为一个文体概念使用的,而是用以说明宋元时期的一些著作与话本的关系,“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⑤。就和“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清之拟晋唐小说”一样,是对不同时期小说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后人并没有将“拟宋市人小说”和“拟晋唐小说”作为文体概念使用。
明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鲁迅称之为“拟宋市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标题为“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该篇论列了“三言”、《拍案惊奇》、《西湖二集》、《醉醒石》等白话短篇小说。他这样解释将这些白话短篇小说称之为拟宋市人小说的理由:“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并没有用“拟话本”和“拟宋市人小说”指称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马廉称“三言”、“二拍”为“白话短篇小说”⑦。郑振铎则将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叫做“平话”⑧。最早用拟话本称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孙楷第,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一文中说:“明末人作短篇小说,是学宋元话本的。因此,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从体裁上看,与现存的宋元话本相去甚微。但论造作的动机,则明末人作短篇小说,与宋元人编话本不同,宋元人编话本,是预备讲唱的。明末人作短篇小说,并不预备讲唱,而是供给人看。所以,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称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为‘拟话本’,不称话本,甚有道理。”⑨孙楷第用拟话本指称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并没有进行严密论证,只是说是鲁迅提出来的,而事实上鲁迅并没有将拟话本作为一个文体概念使用过,更没有用以指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我们不认为孙楷第是有意曲解鲁迅原意,很可能是孙楷第记忆失误所致。此后,人们以讹传讹,误认为这一概念经过鲁迅的科学论证,可以放心地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警世通言》的“出版说明”云:“所谓‘话本’和‘拟话本’,其实都是短篇小说。‘话本’起源于宋代(特别是南宋)‘说话人’(即说书人)所用的底本,更确切地说,是专说‘小说’的‘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拟话本’则是后代(主要是明代)文人摹拟‘小说’话本的体制,继承‘小说’话本的传统而写出来的作品。”⑩范宁为《话本选》所作序言中说:宋元时期,“出现了一些不能讲唱的小说,鲁迅先生曾称这种小说叫做‘拟话本’。”又说:“宋元人编‘话本’,目的是预备讲唱用的,但到后来有些人模仿话本的形式做起小说来,不预备讲唱用,只供人们阅读。这些‘拟话本’有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照世杯》、《幻影》、《豆棚闲话》等。”(11)从表述语言可以看出,范宁的解释明显源于孙楷第。直到现在,拟话本概念还经常出现在一些文学史、小说史的论著中,内涵与外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拟话本概念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是否可以进行补充论证后继续使用呢?也就是说,拟话本是否具备存在和使用的依据和价值?回答是否定的。
作为文体概念的拟话本是建立在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底本的基础上的。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将话本解释为说话艺人的底本本身就不科学。
在现存文献中,“话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载: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12)到元代,“话本”出现在白话小说中,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叶结尾处有:“话本说彻,权做散场。”(13)
明代嘉靖刊本《六十家小说》残本(即《清平山堂话本》)中,《简帖和尚》结尾有:“话本说彻,且作散场。”《合同文字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末尾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明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中,大量出现“话本”一词,如:“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14)“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15)。“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你道这话本出在哪里?”(16)“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后精灵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的话本。”(17)“上述“话本”的使用来看,话本与白话短篇小说关系最为密切。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话本作为一个文体概念,用以指《新编五代史平话》和《京本通俗小说》中所收白话小说,该书第十二篇标题为“宋之话本”,并对话本作了这样的解释:“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事生发,而仍有底本作为凭据,是为话本。”(18)这一解释,为现代小说研究者所广泛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内地学者编撰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都把话本释为说话艺人或者说话艺术的底本。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19)胡士莹说:“话本,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来,应该是、并且仅仅是说话艺人的底本。”(20)这些论著所论列的话本包括《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等讲史话本和《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小说选集中保存的小说话本。
1965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发表了《论“话本”一词的定义》,对鲁迅关于话本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他说,话本一词,“从字面来看是‘说话之本’或者是‘说话人之本’的意思,这个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解释,谁也不至于怀疑。但是再详细考察它的惯例用法时,我们发现‘话本’有‘故事’,但是却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他列举大量例证来证明,“‘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在清平山堂的《简帖和尚》、《合同文字》、《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白话小说的末尾有:‘话本说彻,且作散场。’(或者‘话本说彻,权作散场’)的话(另外,熊龙峰四种小说的《张生彩鸾灯传》末尾也有同样的话)。这儿用的‘话本’一词,怎么说也跟‘说话人的底本’之意有所不同。如把‘话本说彻’解释为‘据底本全部讲完’未免不通,如把‘话本’解释为故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故事说到此为止’,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可以接受。”(21)增田涉的论文在海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内地学术界与海外很少交流,增田涉的论文直到80年代才介绍到中国内地,并引发学术界的讨论。这一问题与拟话本关系密切,“话本”一词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还是故事的意思?说话艺人是否有底本?
“话本”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尤其在白话小说中,应该是故事的意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话本说彻,且作散场。”只有作故事解才通畅。“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22)“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你道这话本出在哪里?”(23)“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后精灵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的话本。”(24)这几处“话本”,前面都有“说”、“宣”等动词,就是讲的意思,只能是讲故事,而不能是讲底本。“从来说鬼神难欺,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25)“这个话本好听,看官容小子慢慢敷衍。”(26)这两处将“话本”与“听”搭配,也只能是听故事,而不会是听说话艺人的底本。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所说的“话本”,联系上下文看,“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大抵多虚少实”,“大抵真假相半”,显然是指傀儡戏、影戏所表演的故事。
说话艺人是否有底本?因人而异。王秋桂《论“话本”一词的定义校后记》云:“近来的田野调查说书人之间有用所谓秘本者。秘本记载师承,故事主角的姓名字号,人物赞,武器的描述和其他包括对话的套语等;这些记载并没有什么连贯性。另有所谓脚本,只记载故事大纲、高潮或插科打诨处及韵文的套语等。这些记载和实际的演出相差很远。”(27)周兆新《“话本”释义》云:“说书艺人主要用口传心授的方法带徒弟。徒弟未说书之前必须听书,并且接受师傅的指点。不识字的徒弟无法作笔记,全凭脑子记忆。识字的徒弟在听书之后,把师傅所讲的内容扼要地记下来,作为秘本保存。师傅也往往把自己的秘本传给徒弟。如果我们认为说书艺人有底本,那么这种秘本就是底本。秘本的内容大致包括两部分,一是某一书目的故事梗概,二是常用的诗词赋赞或其他参考资料。”(28)宋元说话艺人也是如此,不识字的艺人和盲艺人不可能有底本,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29)这位负鼓盲翁只能凭大脑记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九云:“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以后踪迹,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30)这位内侍纲是先搜集素材编写小说,再根据小说为皇帝讲述,他所编写的小说可以称之为底本。负鼓盲翁和内侍纲情况特殊,应该是少数,多数艺人只有记载故事梗概和诗词赋赞的秘本。
既然话本不能释为说话艺人的底本,拟话本概念的根基也随之动摇。话本是故事的意思,拟话本即模拟故事,模拟故事仍旧是故事,拟话本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说话艺人的底本只是记载故事梗概和诗词赋赞的秘本,没有阅读欣赏价值,文人作家写小说也就不可能模仿说话艺人的底本。
如果一定要说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对某种艺术形式的模拟,那也不是模拟说话艺人的底本,而是模拟说话艺术。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最鲜明的文体特征就是有入话,入话包括开篇的诗词、议论和头回。关于入话的产生及其作用,郑振铎指出:“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么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肃静场面,怡悦听众的。”(31)所以,当明代文人与书坊开始记录整理艺人讲述的故事以供案头阅读时,大多将入话删除。以《清平山堂话本》为例,该书流传话本二十九篇,残七篇,全篇传世的共二十二篇,这些话本只有《简帖和尚》、《刎颈鸳鸯会》和残篇《李元吴江救朱蛇》有头回。《刎颈鸳鸯会》、《李元吴江救朱蛇》有议论。《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有很短的两句议论。其他话本均无议论和头回。如果说明清文人创作话本是模拟所谓说话艺人的底本,那么明清话本就应该和这些所谓说话艺人的底本一样,不写入话,尤其是议论和头回,而事实是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大多有入话,包括议论和头回。“三言”、“二拍”、《石点头》都是如此。这说明明清文人创作话本,不是模拟所谓说话艺人的底本,而是模拟说话艺术,文人作家为了还原瓦舍勾栏说话的真实情境,大多编写了入话,尽管入话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说话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方式是有说有唱,以说为主,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开篇和末尾的诗词,正话中描写环境与人物肖像的韵文,说话艺人作场时显然是要唱的。这种说唱结合的表演方式不仅可以丰富艺人的表现手段,活跃场上气氛,也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一段或紧张、或惊险、或刺激的故事之后,来一段音乐演唱,舒缓紧张情绪。这种适应观众场上欣赏需求的演唱,在案头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失去意义,文人作家在写小说时完全可以不写韵文,而我们看到的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仍然有大量的诗词韵文,翻开“二拍”、《石点头》、《西湖二集》等文人创作的话本集,篇篇都有诗词韵文。这也是文人作家模仿说话艺术的有力的证据。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就是作家扮演说话人向观众讲故事,这一特点,几乎不需要多加论证,随便翻开一部话本集,便可以找到作者以说话人的身份与拟想观众对话的段落。《拍案惊奇》卷一:“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32)《拍案惊奇》卷一○:“说话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难道一个个为官不成?俗语说得好:‘赊得不如现得。’何如把女儿嫁了一个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有所不知,就是会择婿的,也都要跟着命走。”(33)“说话的”与“看官”的虚拟对话,实际上就是模拟瓦舍勾栏说话艺人与观众的对话。
话本作家以说话人自居,向拟想听众讲述故事,他就必须遵守说话规则。说话人在瓦舍勾栏向观众讲述故事时一说即逝,观众不可能像读者阅读小说那样可以掩卷沉思,甚至翻回去重读。因此,说话人就得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把故事讲得清楚明白,听众可能不懂的地方,说话人还要加以解释。作家创作话本小说时,对一些生疏的名物、制度、习俗和读者可能产生疑问的情节,亦如说话人一样,出面加以解释和说明。《拍案惊奇》卷五写元宵节观灯,贵族人家捧着帷幕。这是什么东西?有何用处?读者可能不明白。作者解释道:“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幕?盖因官宦人家女眷,恐怕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体面,所以或用布匹等类,扯着长圈围着,只要隔绝外边人,他在里头走的人,原自四边看得见的。晋时叫他做步障,故有紫丝步障、锦步障之称。这是大人家规范如此。”(34)凌濛初解释“帷幕”,主要是为了方便市民读者阅读,而在讲述故事中穿插解释的方法,明显是源于说话艺术。
综上所述,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不是模拟所谓说话艺人底本的话本,而是模拟说话艺术,因此,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也就不能称之为拟话本。
作为文体概念的拟话本缺乏科学依据,理应弃用。弃用拟话本,我们用什么术语来指称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文人话本。而宋元时期说话艺人讲述、文人记录整理的白话短篇小说可以称之为艺人话本。
话本一词尽管在古人的笔下不是一个文体概念,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还是代指某一个故事,在《红白蜘蛛》中,“话本说彻,且做散场”,这里的话本就是指这篇小说所讲的故事。“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你道这话本出在哪里?”(35)凌濛初说得很清楚,这里的话本指包龙图智赚合同文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在古代的白话小说中,话本既可以指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也可以指文人作家编写的故事。在话本的前面加上限定词,艺人话本用来指称说话艺人讲述、文人记录整理的故事,文人话本则用来指称文人模拟说话艺术创作的案头读物。这样既可表明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是话本,又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作者身份与创作方式不同。
文人话本这一概念揭示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要特性,即文人性。明清话本作家都是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十几岁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科场屡战屡败之后,转而选择编刻话本作为谋生的手段之一。这种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使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满怀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即使不能走上仕途,一样关注国计民生,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国难当头,世风日下,官贪吏虐,民不聊生,这些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作家,希望用他们的小说来警醒世人,改变现状。冯梦龙将自己编纂的三本话本小说集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要用文学唤醒沉醉的世人。席浪仙的《石点头》用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来说明自己的良苦用心。陆人龙的《型世言》书名三字就有两字与“三言”书名相同。薇园主人的《清夜钟》“将以鸣忠孝之铎,唤醒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36)。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命名意图也非常明确。笔炼阁主人撰《五色石》以补“天道之阙”(37)。尽管这些文人作家略显迂腐,但他们对世道的关注、对现实的忧虑,表现出文人作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文人作家模仿说话艺术编写小说的时候,更多的只能是形式上的模仿,而题材和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小说中描写文人的生活,表现文人的思想感情。科举作为明清文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被作家写进话本中,“三言”中唯一能断定出自冯梦龙之手的《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卷一八)便写这一题材。冯梦龙作这篇小说的本意是要用鲜于同成功的事例来抨击贱老爱少的试官,小说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官场上进士官与科贡官的不平等,考场上试官的有眼无珠,老秀才考科举的辛酸遭遇等等,客观上是对科举制度的揭露与批判。《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源“怀才不遇,蹭蹬厄穷”(38),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认识非常深刻,在《巧妓佐夫成名》(《西湖二集》卷二○)中,作者通过不学无术的吴尔知中进士的故事揭示了明代科场贿赂公行、有钱通神的黑暗现实。在明清话本中出现了众多的文人形象,他们满腹经纶、怀才不遇、蔑视权贵、桀骜不驯,小说家笔下的李白才华横溢、诗酒风流,到长安应试,被杨国忠、高力士当面侮辱,唐朝接到番使国书,只有李白能够翻译、回复,李白让杨国忠捧砚磨墨、高力士脱靴结袜。在文人与官吏的冲突中,文人成了赢家(39)。“卢学诗酒傲王侯”,作者有意识将高雅脱俗、轻世傲物卢柟作为“王侯”的对立面来处理的,贪婪鄙俗、附庸风雅的汪知县成了卢柟的陪衬人(40)。这些形象不妨看作文人的自画像。
文人创作的话本在艺术形式上也渗透了文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化素养,话本的题目,从冯梦龙编纂“三言”开始,都用工整的对偶命名,有的两个题目一联,如“三言”、《石点头》、《欢喜冤家》、《西湖二集》、《无声戏》等话本集中的小说。有的则采用每篇小说一联的命题方式,如“二拍”、《型世言》、《醉醒石》、《娱目醒心编》等话本集中的小说。文人话本的语言已失去了艺人话本的朴实与自然,趋于典雅。明清文人从小习八股,读诗文,对骈俪文非常熟悉,这种阅读和写作习惯也影响到他们的话本创作。在李渔的话本中,经常可以读到近似骈文的语句,如《十二楼》第一篇话本《合影楼》正话开篇对人物的介绍,便有这样一段:“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管提举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41)这段文字每两句的字数、结构相同,内容前后对照,和骈文相似,只是用白话,偶有词语相同。还有一些话本语言有如优美的散文一般,《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卷四)、《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都有大段的景物描写,语言典雅华美,和历代文人所写的山水游记没什么区别,作者完全陶醉在自己创造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似乎忘记了市民读者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文人话本这一概念其实就是前人对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进行描述的简称,胡士莹说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的书面文学”(42)。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为“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53)。文人话本不用解释,人们都会明白它的指称对象。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64页。
②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4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④⑤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19页,第119页,第197页。
⑦马廉:《关于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⑧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⑩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11)范宁:《话本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0页。
(12)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13)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页。
(14)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页。
(15)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16)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3页。
(17)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12页。
(19)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第144页。
(20)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页。
(21)增田涉:《论“话本”一词的定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三,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50-52页。
(22)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第3页。
(23)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三,第583页。
(2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第124页。
(25)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一四,第239页。
(26)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七,第466页。
(27)王秋桂:《论“话本”一词的定义校后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三,第65页。
(28)周兆新:《“话本”释义》,《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9)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3页。
(3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丙,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版,第246页。
(31)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32)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一,第2页。
(33)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一○,第161页。
(3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五,第102页。
(35)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三,第583页。
(36)薇园主人:《清夜钟序》,《京本通俗小说等五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37)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五色石》,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38)湖海士:《西湖二集序》,《西湖二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39)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九。
(4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九。
(41)李渔:《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399页。
(43)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4页。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文学论文; 二刻拍案惊奇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清平山堂话本论文; 读书论文; 警世通言论文; 拍案惊奇论文; 冯梦龙论文; 石点头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