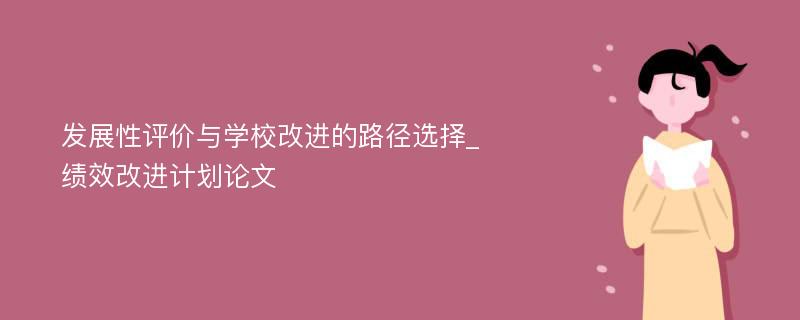
发展性评估与学校改进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性论文,路径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权力下移”和“赋权承责”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发展个性”和“提升质量”教育目标潮流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场以有效学校、开放学校、多元智能学校、跃进学校、成功学校、丰富性学校和学习型学校等优质学校建设项目为特征的“学校重建”运动。随着教育权力的分散和下放,一方面,学校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学校;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也越来越想了解学校是否得到改进、达到优质,在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学校问责制度。应该说,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与强化对学校的评估是“学校重建改革运动”这枚硬币的两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一、发展性学校评估的概念意含
近年来,随着学校发展、学校改进等概念在学术界的被认同和在实践界的流行,发展性学校评估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1]但对什么是发展性评估,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四年前,笔者曾经为发展性评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发展性评估是‘为了发展的评估’,即以学校实际发展和自主发展能力的形成为目的;是‘关于发展的评估’,即以评价学校发展的过程,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学生、教师和校长的发展为重点;是‘在发展中的评估’,即以学校现场中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和学习生活为手段。”[2]虽然在总体方向上这个定义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概念还是显得过于抽象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还是存在许多困惑。而解决这些困惑的过程就是深入理解学校发展性评估概念的过程。所以,笔者愿意把在实践过程中学校遇到的困惑提出来,加以辨析,以便形成更为清晰的学校发展性评估的概念。
困惑之一:发展性学校评估就是学校为了改进和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评估?
发展性学校评估首先是一种学校的自我评估,因为发展性评估理论相信:(1)每所学校都是独特的,它的历史、文化以及面临的学校环境都是不同的,期望外部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多样化的学校,可能会泯灭学校的办学特色,扼杀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2)只有在校内形成积极向上的专业力量,才能真正对学校发展有影响力。因为只有局内人才真正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即使存在着“当局者迷”的情况,局外人只能指点迷津,要走出迷局还必须依靠局内人自身。(3)促进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改善需要三种力量:一是动力系统的情意力量,即乐于改进和变革;二是能力系统的智慧力量,即有好的改进与变革想法;三是行动系统的执行力量,即能创造性地把好的改进与变革想法变成实践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性评估是以校内力量为主体的评估,学校自我评估必须动员全校教职员工的集体参与,以激发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评估对被评对象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怎样让校内评估成为校长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机制和学校改进机制,而不是外部强制和威胁的手段,让校内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到校内评估团中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做会使每位教师都有体验评估的机会,使他们了解自己学校的教育背景,把评估当作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使评估常规化而不是专职化,使评估过程成为学校成员间相互学习、激发创新热情的过程。
学校内部评估可以有效地履行形成性评估的功能,没有内部评估就不可能形成学校对评估的积极态度。但是,发展性评估不等于校内评估,片面地强调校内评估可能导致学校逃避社会责任。外部评估的适时介入是发展性评估的重要内容,运用得好,它同样是动员校内力量发现问题、厘清思路、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改进与发展的动力。因此,这里存在一个校内评估与校外评估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校内评估与校外评估是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一种鉴定关系,否则校外评估就会强化学校的自我防卫行为,而不是发展与改进的行为。这恰如内伏教授所说的:“不是用内部评估来代替外部评估,而是要将内部评估放在比有效的外部评估可以优先发展的位置上。”[3]
困惑之二:发展性学校评估的目的就是实现学校教育成果或效果的增值?
近年来,“发展就是增值”的观念渐入人心。因此人们逻辑推演出“发展性评估就是增值评估”的结论。从理念上看,它看到了学校原有起点的差异,重视学校自身的纵向自我比较,即在原有水平上的“进步度”或“增加值”,鼓励学校追求自己的发展目标、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塑造自己的学校文化。应当说,从横向比较的意义上看,增值性评估是比较公平的,它关注了学校的努力程度和进步幅度,而不是教育成果和效果的绝对值。
但从本质意义上讲,增值性评估并不是一种自我改进式的评估,实际上,它是一种变形了的横向比较评估,只不过这种比较的对象是进步度罢了。笔者认为,增值性评估强化的是一种绩效结果,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强化了“学业成绩”,学校效能就等于学校在标准测验中所测量到的学业成就。在增值性评估的倡导者看来,“考试分数体现着学校的内在价值,在标准测验中获得高分数的学校理所当然地成为有效学校……有效学校就是使学生获得比入学时的期望分数更高的学校。”[4]这种增值性评估使得“绩效责任”、“绩效标准”、“学业成绩”、“高风险测验”等成为社会关注的主流话语,使绩效责任制成为学校管理的主要方式。而驱动绩效责任制的是三个原则:学校应为高标准的绩效负责;要提高学校向社会传达自我改进状况的能力;学校要重视绩效结果的提升,尤其是学生成绩的数量和质量。[5]实践中,增值性评估成了简单的测验运动,在美国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是对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无理由的干扰”。甚至有人指出,“这些测验过程没有提高多少学业成绩,所产生的变化就是教学生学会了考试,训练了学生应付测验之类的项目的能力,排除了学生在测验过程中取得进步的可能,增加了学生的辍学率。”[6]
在中国,“应试”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积弊。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渐渐觉悟到应试教育的弊端,开始探索素质教育的新路,并实施了以素质教育为理念的课程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就就是打破了单纯以考试成绩评定学生、评价学校的藩篱,而现如今,我们又简单地视国外的增值评价为先进,并套以发展性评估的新外表,这是比较可怕的。笔者认为,发展性评估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绩效论评估,而是一种变革论评估。“绩效论”认为学校发展就是在一定的教育输入背景下实现教育输出(即实现所期望目标)最大化,或者学校由原有水平状态向较高水平状态跃进与增值。这种线性思维指导下的学校评价设计,最终指向的往往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而“变革论”则认为学校发展并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机制的转换、能力的成长和价值的提升,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所以,发展性评估是素质教育导向的评估,而不是单纯追求学业成绩和升学率的评估,学校的发展或效能应该体现在校长的管理能力、教师的教育能力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上。
二、发展性学校评估的目的:学校的持续改进
在发展性评估的理念中,评估本身不是目的,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学校的持续改进。发展性评估的发展观,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但是,发展不是一切都推倒重来,而应是在学校原有基础上的持续不断改进。
那么,如何判断一所学校是发展性学校,是一所不断改进的学校呢?从根本上说,就是能让每一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全面、和谐、自由、充分与持续的发展,使他们有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健全的心理品质、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强健的运动体魄、更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开放的思想观念、更高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这样的学校才是发展性学校。学校改进不仅表现为一种结果,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一种过程、一种能力、机制和精神,学校改进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理想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标准指引或引导学校不断改进、追求卓越呢?概括来说,有三个层次:一是价值观;二是能力;三是绩效。
第一,学校成员价值观的持续改进。
学校价值观是学校所秉承的哲学、理念、信仰、假定、态度和期待等精神思想体系,它既是学校发展的内源动力,也是学校发展的方向指引。学校价值观念的积极转变与提升不仅是学校发展的应有内涵,而且是学校最根本的发展。学校价值观是一个内隐的概念,它指向的是学校各种外显制度、规范、行为和器物背后的一整套“假设和信念”。如果这种价值观念能被学校成员共同分享、集体信守,渗透并体现在学校日常生活与存在方式之中,那么它就变成了学校的独特文化。学校的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学校校长和教师等所持的学生观、教育目的观、人才观、课程观和教师观等方面,是学校成员的信念体系。笔者的课题组有一所实验学校——PY小学。这是一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薄弱学校,区领导不重视这所学校,而校长却真心希望学校能有所发展。记得第一次给这所学校教师进行培训时,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我们学校的生源太差,没有办法跟人家比,怎么发展呀?”为了改变教师们这种片面的学生观,笔者给教师们讲了一只老鹰和小鸡的寓言故事:
一只小鹰在鹰妈妈出外觅食时不慎从巢中掉了出来,刚巧被鸡妈妈看到,便捡回去和一群小鸡放在一起喂养。
随着时光流逝,小鹰一天天大长大了,也习惯了鸡的生活,并且鸡们也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同类,它也像其它鸡一样外出寻食,从来没试过要飞向高空。
一天,在小鹰外出觅食时,忽然遇到鹰妈妈,鹰妈妈见到小鹰惊喜极了,对它说:“小鹰,你怎么在这里,随我一起去飞向高空吧!”
小鹰说:“我不是小鹰,我是小鸡呀,我可不会飞,天那么高,怎么飞得上去呀?”
鹰妈妈对小鹰有些生气,但她还是大声地鼓励它说:“小鹰,你不是小鸡,你是一只搏击蓝天的雄鹰呀!不信!咱们到悬崖边,我教你高飞。”
于是,小鹰将信将疑地随着鹰妈妈来到悬崖边,紧张得浑身发抖。鹰妈妈耐心地说:“孩子,不要怕。你看我怎么飞,学我的样子,用力,用力。”小鹰战战兢兢,在鹰妈妈的带动下终于飞向了蓝天。
通过这则故事,笔者想传达给教师的思想是,只要是雄鹰,它总会展翅飞翔的,教师要对学生有信心。可当讲完故事时,一位教师立即站起来说:“雄鹰当然是可以飞翔的,关键我们的学生都是鸡怎么办呢?”教师们的提问让我很震惊。说到底,这是一个教师是否相信学生具有成才潜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学生观的问题。经过全体教师的讨论,这所学校最终定位于探索建立一所多元智能的学校,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观就是相信学生各有不同的潜能,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的学生。在具体的教育生活中,我们通过对教师行为背后所持的学生观的评估,让他们的观念发生由明白到相信的转变,从而引导学校的不断改进。
第二,学校主体能力的全面提升。
学校的主体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管理群体;二是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育教学群体;三是以学生为代表的学习发展群体。能力建设过程就是学校在什么方面花大资金、花大气力和精力的过程,就是学校选择战略重点的过程。当一所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盖大楼、挣大钱上时,学校进行的是物力建设和财力建设,而不是能力建设。投资于人,投资于人的品德、知识、智慧和健康,才是能力建设。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一种现象,即凡是能力建设比较强的学校,其办学质量也就比较高,凡是比较薄弱的学校,其能力建设也就比较差。这是一个经验观察,需要实证研究去证明,但笔者相信这是一个能够被证实的命题。
首先是以校长为代表的领导管理能力。现在学术界已经越来越认同校长是一个专业,那么作为专业人士的校长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呢?根据研究经验,以下几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学校发展规划的能力。规划的核心是为学校设计一个建立在现实条件基础上的、可信的、诱人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前景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步骤及行动策略。设计学校发展规划时,要学会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参与,要学会使用科学的规划方法。二是资源组织运筹的能力。学校要想实现大家共同设定的愿景目标,就必须动员和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与社会和社区建立友好的发展关系,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习型团队建设,有“从外部学习”和“从内部反省”的态度与习惯。三是人际关系协调的能力。人际关系是学校的重要生产力,人际关系和谐,可使组织发展成为真正的团队,可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和工作活力;人际关系紧张,会产生离散力,会让每个人的最佳能力减半。
其次是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师的专业能力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必须调动教师本人的学习动力,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这一点非常关键,否则教师能力建设就会落入形式化。教师专业能力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学习研究能力。每一个走上教师工作岗位的人,都具备了基本教师素养,但这最多只能称之为合格教师,只是教师专业发展历程的第一步。持续地钻研与学习能力是专业人员的必需能力。教师不爱学习、不爱研究,对新知识没有积极情感,他就绝对不可能有创新的教育行动。二是智慧实践能力。教育实践是情境性的、特殊的,优秀的教师会知道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如何去做,在与学生相处时会根据临场情境展开创造性活动,其教育判断、选择和决定具有意向性,体现出“实践之知”、“实践之美”和“实践之善”。[7]三是团队合作能力。长期以来,教师的教育活动一直被认为是个体化的行为,教师专业化也日益被分割化。莫兰指出,“事实上超级专业化阻止看到整体的东西和根本的东西”。“科学的科学性的发展不只是带来了劳动分工的优点,它也带来了超级专业化以及知识的分割和隔离的弊病;它不只是产生了知识和明了,它也产生了无知和盲目。”[8]所以,教师团队合作能力已经成为学校教育能力能否得到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再次是以学生为代表的学习发展能力。学校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不只学生要学习发展,学校中的每个人都要学习和发展。仅就学生的学习而言,应着重加强建设以下能力:一是策略学习的能力。二是探究学习的能力。三是团队学习的能力。
第三,学校全面绩效的综合提高。
学校改进不排斥结果和绩效,作为学校教育的“产出”,它应该是学校能力的综合体现,更是学校价值观的展现。这里的关键是要看学校的全面绩效。什么是全面绩效呢?从学业成绩上说,不只是看个别优秀学生的成绩,还要看学习困难学生的成绩,要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而不是少数学生的发展;从身心发展上说,不只是看学业成绩,还要看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看学生对学习的动机、兴趣、归属感和幸福感,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从个性成长上说,不只是要看学生的当前的发展,还要看学生的潜能开发、个性自由和今后发展的持续性与后劲,要关注学生的自由性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规范性发展。
三、学校持续改进的路径选择:从改变行动开始
那么,如何通过发展性的学校评估来推动学校的持续改进呢?厄斯金—卡林指出,要启动学校的变革工程,必须在学校内先凝聚一定的启动力量。[9]时下,对于学校变革启动点的选择大多人认为要从变革教师的观念开始。人们相信,观念决定行为。记得2006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学时,笔者曾与北美著名现象学、教育学专家范梅南教授谈起中国新课程改革,并告诉他:改革中有人主张新课程改革要从更新教师的观念开始,因为观念决定行为。对此,范梅南教授提出了一个令笔者至今难忘的问题,他问:“观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可能是由另外一个观念决定的,那另外一个观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从原初的意义上说,是行为决定观念的,是人们行为的客观效果决定人们是否相信某一观念的。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学校改进首先是人自身的积极变化,那么是先变人的行为还是先变人的观念,则是一个学校改进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现实的学校变革中,我们发现许多学校花了大笔的教师培训经费,虽然从应然的意义上说教师的观念产生了改变,但从实然上看教师们依然如故地沿袭着传统的教育教学行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早期有关态度的实证研究认为,人们所持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两者之间存在着线性的A-B关系(A为态度Attitude,B为行为Behavior,即A决定B)。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列昂·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感受到两种或多种态度之间不一致,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和谐时,便会感到不舒服,因此,个体会努力减少这种不协调或不舒服。个体减少失调的愿望通常是由下面三个因素决定的:造成失调之要素的重要程度;个体相信自己受到这些要素控制的程度;个体在失调状态下的受益程度。也就是说,如果考虑一些调节变量,如态度的重要性、态度的具体性、态度的可提取性、是否存在社会压力、个体对态度是否有直接经验等,态度可以有力地预测未来的行为。[10]
但是,达里奥·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认为,态度不是在行动之前指导行动的工具,人们只是在事实发生之后使用态度使已经发生的事实具有意义。当问到一个人对某事的态度时,个体会回忆他们与这种事物有关的行为,然后从他们过去的行为中推断出对该事物的态度。因此,态度只不过是一种很随意的言语陈述,人们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听起来合理的答案。因此,在许多情况下,B-A关系可能比A-B关系更有力。[11]
美国变革理论大师科特和科恩也认为,要想在组织变革中取得真正的成功,首要条件就是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而人们行为的背后则是文化。在那些比较成功的组织中,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改变他们的感受。科特教授认为“目睹—感受—变革”机制不是常见的,而“分析—思考—改变”(更不是“命令—接受—改变”)机制才是改变行为的最佳方式,直观印象所激起的情感比理论分析更能引导变革的发生。心(情感)常常比头脑(思维)更重要。[12]因此,在学校改进的行动选择上,我们非常赞同香港优质学校计划所采取“以点带面、保旧立新、循序渐进”策略,即先从个别层面展开改革的序幕;先从考试压力较轻的年级试行新的教学模式;先组织较活跃的教师进行共同备课、协作教学、观摩示范等教学活动;累积新教学模式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享及表扬新教学模式下学生所展示的转变;尽量在行政及资源上配合新教学模式的推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