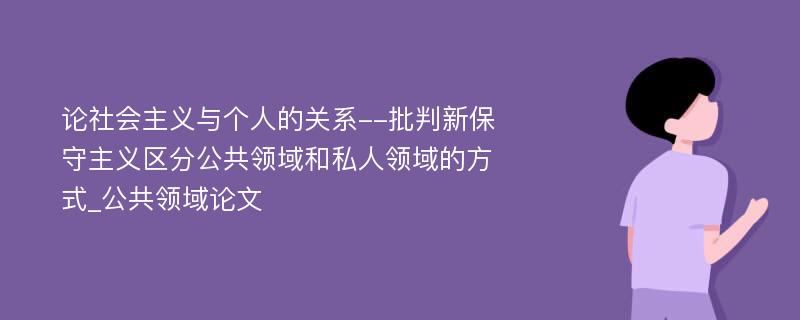
论社会主义与个体的关系——兼批评新保守主义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域论文,保守主义论文,个体论文,批评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掘社会主义个体概念对社会主义的复活极为重复,因为近年来右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将自己打扮成自由和自我发展惟一的捍卫者,独占了自由、自决和个体等话语。最近十年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此方面已有所努力,但还缺少发展自我创造性个体的社会的论述。
新保守主义话语中的个体与共同体
新右派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宣称利己主义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真正基础。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主要论点如下:个人是最基本的真实存在;他们是理性存在,能够制定自己的生命规划;社会作为个人利益的总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在总体上是不可知的;除了为个人追求利益保留最大空间,不存在其他社会利益;因之,任何有关全体社会利益的论断都是个别利益的具体化;最后,任何以全体利益为出发点重新组织社会的尝试,都会对自由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自由是对私人利益的私人追求,而社会过于复杂,不能由任何中心管理)。
新右派宣称,无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还是改良的社会主义,都违反了上述每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家长式的扩张,破坏了个性,这种公共领域的扩张使个人的原创精神从属于集体平等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
我们以20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大师哈耶克为例。哈耶克的核心论点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对个人行为的目的不存在强加的全体一致。任何导致国家对私人领域进行干预的政治压力都很容易使社会走向极权主义。因为私人领域里的国家干预与极权主义具有共同的前提条件:两者都设定,围绕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存在着一个共识。但是,这种设定既是虚假的又是有害的。只有个人才具有目的,而国家将集体目的强加于个人的行为阻挠了个人目的的实现。社会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结构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的无目的产物。这样,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小心谨慎就连贯起来了。与柏克的态度相似,哈耶克认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那些历经许多时代而保留下来的制度。由此,设计社会制度的工具理性只能起到有限的从属的作用。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中变量的数目之巨大,使得任何对公平制度和公平动力的精心设计都成为不可能。
然而,哈耶克与柏克还有不同。哈耶克认为,个人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传统最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生产率。他认为,英国所表现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最优秀,因为只有这一传统领会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别的必要性。政治自由建立起来,并由受到法制保证的私人领域来维持,在这种私人领域里,个人创造性可以发展起来。这种创造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企业家。只有一个强大的企业家阶级才能创造生机勃勃的经济,而只有在法律确认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独立自主时,强健的经济才成为可能。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生产率反过来又证明了自由的价值。这样,自由与社会财富互相增强,互相合法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增强了社会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而社会稳定反过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施行高压措施的必要性。当特殊的目的被具体化,被表现为普遍的社会目的时,灾难就开始了。私人领域的自由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财富都极为重要;当政治企图以某些所谓普遍利益特别是实质平等为基础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构时,私人领域的自由就会遭受致命伤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社会群体影响政策是有可能的。群体的集体私利能够将政策从维持形式平等推向实质平等,而这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公共领域从个人手里攫取资源并向社会群体进行再分配,任何公共领域的扩张都违反了个人主义的核心信条。哈耶克说:“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把人尊重为人,这就是说,在个人自己的领域里,承认他自己的观点和兴趣是最重要……这肇始自文艺复兴,并发展为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
但是,自由主义所说的人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这种思想不是主张所有人的自由,而是反对对私人领域进行民主干预。这一主张掩盖了资本主义用以限制多数公民的自由的机制。资本主义使人们在发掘、培养和追求他们的天资和禀性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从属于过度的保障利润的需求。这种思想还模糊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特性,因为它只主张数学意义上每个人的平等。通过这种抽象,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对立就建立起来了。
尽管哈耶克重新建立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但今天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起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对新左派的回应。新左派刺激了新右派作出道德上的反应。同时美国政府采纳的经济政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激发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评。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以新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保守主义道德特色便出现了综合。哈耶克战争年代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被重新用于和平年代,并被解释成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既是经济批判,也是政治批判。新保守主义认为,它们反对的运动不仅是正常健全的财经管理的敌人,也是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等等)传统的敌人。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对美国是一个白人的、清教徒的、田园的、稳定的、平等主义的社会这一神话提出了挑战。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只能是消极的和代表制的;对这种民主制的局限进行激进的质疑不会产生更加强健的民主制文化,只会导致混乱;民主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权威和惩戒的崩溃,而权威和惩戒对自由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对保守主义者而言,60年代的民众运动力图改变平等的含义,迫使国家转变角色。机会的平等变成为由国家倡导并支持的结果的平等。当集体权利由一个范围广阔、代价昂贵的公共领域强迫推行时,个人权利就受到侵害。丹尼尔·贝尔1972年写道,为实质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不是由理性纲领驱动的,不是要改变基本的不平等,而是受到非理性欲望的驱动,即经济上低水平阶层对高水平阶层的无名怨愤所致。
但是,为什么这种对大多数人有害的纲领现在会受到如此多的支持呢?因为这些纲领包含了正确的因素,如贫穷问题不能靠福利解决;另外,新右派从左派那里成功霸占了对国家的批评。新保守主义者很愿意提出个人自由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无论是改良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都缺少类似的话语,左派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现实意义。但新保守主义涉及自由的观点的正确性被它对资本主义的支持损害了。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它必须将大多数人仅仅当作“人力资源”,就是说作为他人实现目的时加以利用的资源。因此新保守主义是极为反民主的。
左派的反思和批判
新右派对国家膨胀进行的成功批评刺激了左派重新思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左派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完全依赖官僚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增加边缘群体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对公民社会实行民主化。这种主张是由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引发的。若检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国家的规模缩小了,但是国家的强制权力并没有缩小。对福利国家的破坏增加了人口的生存压力,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社会紧张不断增加,这必然又会导致采取高压措施。因此,新保守主义对待国家扩展的反应是自相矛盾的。随着与国家干涉相关的被称为“威胁自由”的政策的终结,所有在社会公正方面所获得的成果也都将终结。很明显,新保守主义要保守的并不是强健的个人主义自由,而是那些拥有大量经济资源并要保持和扩大其财富的人的自由。那些生活受到有害影响的多数人民则越来越多地受到监视和攻击。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低,越会遭受更野蛮的镇压措施。民主被确认是保持公司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一旦民主制成为平民的、公共的和积极的(也就是说,民主制一旦成为民主的),那么它就会被谴责为极权主义。新左派的回应是希望重新定位对国家主义的批评,以使这种批评增强而不是损害被边缘化的和受压迫的人们的地位。
我所指称的新左派可能可以回溯到1985年,那一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了他们颇富争议的著作《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他们核心的政治观点是:严格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已经结束;新社会运动是左派的重要力量;政治和文化要求必须摆在激进思想的前列;社会主义(他们仅仅将之作为一种经济观点)必须被重新定位为左派众多话语和实践中的一种;最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内容之间建立亲善关系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和环保主义者等以认同为划分基础的群体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伟大的自由主义斗争,可以深入推进社会的转化。
拉克劳和墨菲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政治运动和经济要求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他们并不想抛弃社会主义目标;他们希望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激进运动的目标之一,与其他政治目标或文化目标具有同样价值。社会主义不再被理解为激进的民主运动,而是激进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对社会主义进行价值收缩的观点是危险的,当人们转移重心并探索激进民主和为自由的公民社会而斗争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危险尤其明显,因为他们只含糊其辞地说“各领域的最大程度的自治”。
经济活动属于公共领域
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同时代左派的批判,它们的理论前提都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明确区分。然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在作出这一区分时都没有正确理解私人领域。左派和右派都将经济关系这一也许是所有关系中最具有公共性的关系归入私人领域,这样就将经济与民主转化隔离开来。由此,社会经济因素对公民的实际私人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这一问题的中心是民主和对公共财富的控制之间的关系。200年前,政治权利得到保障是自由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今天,拥有权利不再是健全民主的保证。正如埃伦·迈克辛·伍德在她的最新著作《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中所说:“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资本主义中政治品贬值了。政治品的地位注定要因为资本主义剥削从直接的强制权力中独立出来而降低。”这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对资源的控制并不直接与他的政治地位相关联(在封建制度下则直接关联),那么一个人对政治权利的占有本身并不保证他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这样,就一个人的实际发展范围和可能性来说,公民身份这一权利的意义日益缩小。
这并不是说公民权利就没有意义了。这里的意思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自由社会而言不再是根本的。对人类自由来说,关键的是能力的运用,而不是法律保证。但能力在表达出来之前总是抽象的,而它们的表达需要获取资源。新保守主义扩大了权利和现实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增加了人民和有意义的自我行为、自我创造所必需的公共资源之间的距离,这表明今天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伍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此问题时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以都是公民,但是这种公民权与我们每天怎样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想一想那些民主制下公民权范围之外的生活领域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劳动和资源的配置,时间本身的组织……全部都在公民权之外。”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我们工作的质量;孩子的日托服务、社区活动中心、溜冰场和公园;解决吸毒和失业问题的方案;体面的住房;生机勃勃的艺术社群;易于获得的教育和医疗保障——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资源,自由公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公民社会的界限不是民主确定的,而是由独自掌握开展任何生产活动或者协会活动所必需的资源的阶级决定的。
但在上述提到的所有方面,政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削减。而公民却没有权利将这些领域的基金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没有上述公共领域(这是过去民主斗争的产物),就谈不上个体,因为个体是通过他们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能力的发现和运用取决于是否可以获得资源。获得资源是个体发展的根本原则。没有公共领域,就没有真正的个体,至少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如此。对公共领域的进攻不仅仅是要消减该领域的开支,而且还要使过去几个世纪争得的民主成就倒退回去,并增加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惩戒压力。
如果左派接受新保守主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那么左派就不可能对新保守主义作出真正的激进反应。经济关系绝对是公共的,因为经济关系决定了社会中的每个人获取资源的水平。而认为否定经济关系的私人性就会导致对整个私人领域的否定或者会危害自由公民社会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相反,对经济关系私人性的否定是充分的自由公民社会的条件。
本文的结论有如下含义。第一,激进左派必须回到一条已被遗忘的原则: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控制经济;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社会、民主的方式控制经济。左派需要抵制将资本主义市场与效率和理性等同起来这一错误公式。资本主义市场既不等于效率,也不等于理性。第二,左派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关系。新左派的巨大创见就是揭示了后两种斗争形式对民主社会事业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认同政治的模式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斗争使人们之间的差别具体化,另外,也阻碍了斗争中的联合。第三,我们需要开始思考今天在实践中使政治斗争和社会经济斗争联系的战略。例如,使工会要求重新政治化,开展斗争加强工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增加业余时间;或者社区对新企业施加压力,使它们改善所在地的社会基础设施;还可以发展社区委员会,将该地区不同的认同群体召集到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培养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相互了解,消除对他人的恐惧,并为更为广泛和激进的政治运动提供舞台。
标签:公共领域论文; 政治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