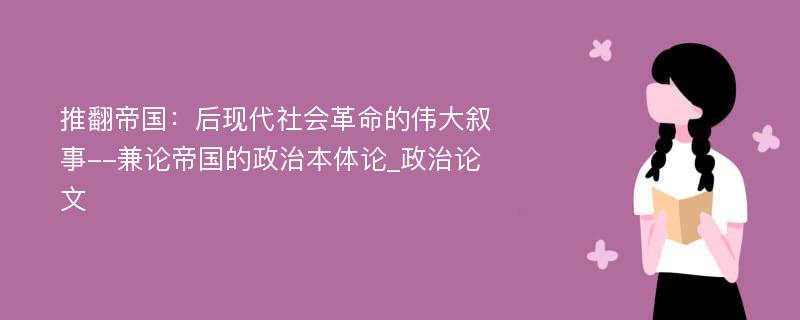
推翻帝国:后现代社会革命的宏大叙事——兼论《帝国》的政治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本体论论文,后现代论文,宏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11-06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在论及他们合著的《帝国》的理论旨趣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将帝国主权确立为自己的敌人,探寻合适的途径将其颠覆。”[1]212可见,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秩序进行研究,不是站在控制的立场上为了统治秩序的巩固,而是站在反抗和斗争的立场上意在推翻现存的帝国统治。暂且不论其理论逻辑的严密性与政治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单就其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而言,在当今革命低迷的情势下实属难能可贵。可见,对其革命理论进行研究,不仅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试从政治本体论的视角,对他们的革命理论予以简要探析。 一、本质腐败:推翻帝国之必要 在对帝国进行深入探讨时,哈特和奈格里充分肯定了帝国替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的进步意义: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促进了解放潜能的增长。[1]44他们同时强调,这一进步性又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这是因为,它并没有消除剥削,只不过是对剥削进行了重新定义;它在摧毁旧有的、以等级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同时,又建立起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非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型的权力关系和剥削关系比旧有关系更残暴、更野蛮:一方面,随着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今天的贫富分化更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关系向全球的扩展,今天几乎全人类都被挟裹进帝国的剥削网络。他们据此断言,帝国仍是“自在的善”(good in itself),而远非“自为的善”(good for itself)。鉴于此,他们提出了推翻帝国,消除善的自在性,实现作为“自为的善”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政治要求。[1]384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将帝国之“善”的自在性归于其所具有的腐败本质。他们断言:在帝国之生态政治空间中,“欲望显现为生产性空间,显现为历史构建中人类合作的事实。”[1]387然而,帝国为了维护其统治,着力于控制并阻止欲望之生产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打破了欲望之链,中断了欲望在生产之生态政治范围内的伸展。它建构起民众(multitude)生活中的黑洞与本体论真空。”[1]389他们将帝国对欲望的消极作用名之为“腐败”(corruption)。在他们看来,“腐败与欲望相对,不是本体论的原动力,而纯粹是存在的生态政治实践之本体论基础的缺乏。”[1]389他们同时强调,正是由于帝国中充斥着“腐败”,以至于在其中发生了权力与价值的割裂,进而导致了存在的缺失;而生态政治世界中的知识与存在无一不体现于价值的生产中,致使这种帝国之存在缺乏的现象“显现为一种伤口、一种社会之死亡愿望、一种存在之于世界的剥离。”[1]390 在他们那里,与“腐败”相对的是“繁育”(generation)。“繁育”就是指一种“欲望性生产,或者劳动的超溢和一种被融入到既是其起因又是其结果的独特本质的集体运动之中的力量的积累。”[1]387-388“一种集体的机制或欲望的工具”[1]388。鉴于作为“欲望性生产”的繁育对帝国构建及其秩序稳固的重大作用,“为了使之得以发生,政治不得不让位于作为生态政治之基本力量的爱和欲望,也就是让位于生命政治生产的基本力量。”[1]388这一基本力量无疑就是怀有各种冲动欲望、从而从事着“繁育”的民众。 他们认为,作为欲望之载体,民众不可避免地遭受腐败的侵袭。通过对腐败的深入考察和探究,就会“发现所有形式的腐败基部都有一种破坏对民众之独特本质定义和实现的本体论的失效的活动。民众必须被统合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这就是民众不得不遭受的腐败。”[1]391他们强调,从民众的视角看,“腐败纯粹是监控的行使。它通过其强制的统合和(或)残酷的分割成为走向毁灭民众之独特性的监控。”[1]391-392同时,从这一角度看,繁育与腐败的对立尤为突出和明显:“生态政治的繁育直接将民众之身体改造成……一种受到智力性和合作性的力量滋养的业已混杂起来的身体;而腐败不但显现为以其权力对抗着受到滋养的身体的疾病、挫折和缺失,而且还表现为分裂独特身体之共同体以及生产性生命政治共同体、并且阻碍其行动及生命的精神病、麻醉剂、焦虑和无聊。”[1]392这样,帝国的腐败性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悖论:“在合作中的身体生产的越多,在共同体中的身体享受的就越多;但是,帝国为了不被其摧毁,就不得不阻碍和控制这一合作的自主性,就不得不以其腐败在活动中阻滞群体中的身体出现……‘超越于标准’(beyond measure)的情况。”[1]391而且,这一悖论不可化解,“世界越富有,以这一富有为基础的帝国就越加否定财富生产的条件。”[1]392可见,尽管帝国的生存有赖于繁育,但为了免于灭顶之灾,就不得不付诸与繁育相对的腐败。而腐败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将民众统合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以避免民众之身体力量出现独特的普遍化。事实上,正是帝国这种对繁育与民众活力既依赖又压制的两面性,为对其实现政治替代提供了可能。 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自在性的观点深受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欲望政治学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作为他分析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德勒兹将欲望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德勒兹在吸收了尼采把欲望作为一种主动和积极的力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把欲望定义为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欲望。[2]德勒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不仅各种欲望流动而构成的“欲望流”被符码化(coding),而且这些“欲望流”所呈现于其上的各种社会场域也被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资本主义的进步在于对各种“欲望流”和社会场域的去符码化(decoding)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资本主义在对过去的符码和疆域予以消解的同时,重又根据自己的标准对欲望施加了“再符码化”和“再疆域化”。 哈特和奈格里借鉴了德勒兹的欲望、符码化和疆域化等概念,进而认为帝国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对被资本主义再符码化和再疆域化的欲望和社会场域进行了“再去符码化”和“再去疆域化”,由此导致了各种界域分界趋于模糊的“平滑空间”。然而,由于帝国中腐败的存在,因而其出现并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地对欲望进行去符码化和去疆域化;因而,要使欲望和社会场域彻底地去符码化和去疆域化,就必须消除腐败、推翻帝国。在这一问题上,哈特和奈格里与德勒兹出现了分歧。德勒兹认为资本主义在其自身体制内,能够通过对欲望和社会场域的不停地去符码化和去疆域化而趋于完美。这样,他就没有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构设出全球性的政治变革,而是“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3]30就此而言,哈特和奈格里要比德勒兹更为激进。 二、本体缺乏:帝国灭亡之宿命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源自其自身本体的缺乏。[1]361他们断言:“就在帝国建构超国家形象时,权力似乎丧失了承载它的地基。更确切地说,它丧失了推动个它前进的动力。”[1]17之所以帝国权力能够无所不在,是因为“为其发挥纽带作用的虚拟性(virtuality)和可能性无所不在。”[1]361他们据此断言:相对于民众的虚拟性,帝国政府显现为“一个空壳或寄生的机器。”[1]359这就是说,帝国的寄主是民众,它依赖于对民众之虚拟性的吸吮而生存。 据其在帝国建构中所发挥作用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将民众的虚拟性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非现实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是指由民众所从事的非物质劳动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智能化而引发的虚拟性。在他们看来,在帝国政治现实的构建中,这种虚拟性的作用仅限于提供诸多可能性。而真正能够将可能性和现实性连接起来的是民众之独特的虚拟性,因为这种虚拟性手中握有两张对帝国秩序而言具有颠覆性的王牌:其一是作为一种毁灭性武器的外在于标准(outside measure);其二是作为构建性力量的超越于标准。[1]369换言之,正是民众之外在于标准的虚拟性和超越于标准的虚拟性,为对帝国进行政治替代提供了可能。 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民众之外在于标准的虚拟性,就是指来自于劳动的非物质化所发展起来的对自由流动的渴望以及对统治体制的抵抗的虚拟性。面对这些渴望和抵抗,帝国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一种宪政力量,帝国必须对这些不稳定因素予以压制和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帝国自身呈现为一个消极的现实,其控制“纯粹是否定和被动。”[1]351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依赖于民众之活力而生存的寄生性存在,帝国又必须将其对民众流动和抵制的压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确保自己的营养供应;鉴于此,他们断言:“帝国之规范性和压制性手段的有效性最终必须溯及虚拟性的建构性的民众行动。”[1]361帝国这种对民众之自由流动与抵制既爱又怕的复杂态度,充分暴露了其腐朽寄生的消极本性和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他们强调,从帝国建构的视角看,民众之外在于标准的虚拟性不过是一种毁灭性武器,它对固定标准的冲击和摧毁不过是为政治的多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虚无地带(non-palace)”。而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还有赖于民众之虚拟性借助一定的手段对可能事物的边界施加压力,使之触及真实的事物,……”[1]356他们将这种建构性的虚拟性名之为“超越于标准”的虚拟性,一种“在外在于标准所积累的虚拟性的基础上,现实地构建起帝国全球化之整个生态政治网络的一种虚拟性。”[1]357 在他们看来,与民众之外在于标准的活动所采取的形式——抵制和反抗——不同,超越于标准则主要通过作为可能性手段的活劳动来建构起帝国大厦。在帝国中处于霸权地位的非物质劳动,不再是一种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且尤其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一种“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所激活的社会力量。”[1]356可见,非物质劳动对帝国的建构不仅发生于形式上,而且还现实地实现于生命政治的层面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将非物质劳动称作生命政治劳动。)由此,劳动力就变成了一种兼具智力性和肉体性的生产性能力,一种生产出社会网络、共同体形式和生物能量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建设性能力。 通俗一点讲,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引发了外在于标准的虚拟性,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则激发了超越于标准的虚拟性。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日趋稳固,这两种虚拟性日益累积,实现对帝国政治替代的潜能在增长。归结起来,非物质劳动霸权引发的革命潜能增长的因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导致了帝国结构的脆弱性。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环境日益促成了帝国的脆弱结构。一方面,促成了一个网状结构。随着社会生命政治化的不断加深,对帝国控制的抵抗不断地在帝国之全球性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并贯穿于帝国整体发展与重组的每个阶段。[1]384这样,任何一个对抗与冲突,其效应都会波及全球,从而构成对帝国体制的普遍性攻击。另一方面,促成了一个平面结构。生命政治的内在性与差异化消解了社会结构的内外之分,并引导着帝国的横向发展,从而呈现出一个平面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任何一点遭受攻击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鉴于此,当今对抗帝国的斗争没有也无需横向联合,只需纵向跃起就能“直击帝国的核心。”[1]358 其二,促进了后现代政治主体队伍的锻造。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环境中,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日渐巩固,一个新的后现代政治主体日益形成。这是因为,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的非物质化使得一些传统无产阶级的附属阶层都成为非物质劳动者,并使各种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减少。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劳动的生命政治性使得劳动和生活的时间和场所等不再明确可分;资本以其“生命权力”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控制也不再限于特定时间和场所,而且还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监控与规制。这样就促使作为被剥削者采取与之相对的策略,通过“生命政治”而形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这样,一个由“其劳动直接或间接遭受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1]52组成的全球劳动阶级得以形成。 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的逻辑是,由于帝国中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日趋巩固,导致了自身结构的脆弱性,锻造了成熟的后现代的政治主体,从而致使革命的潜能在增长。可见,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延续了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相关理论,是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进行改造而成的。[4]可见,哈特和奈格里提出非物质劳动理论,与马克思考察工业劳动的初衷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以期在生产劳动的领域探寻革命的可能性。[5] 三、“斗士”锻造:推翻帝国之路径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为了推翻帝国进而实现“自为的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当今的生命政治环境与差异政治条件下,传统的横向联合式有组织化的斗争形式已不再适用。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斗争之间毫不关联、各自为战。民众要真正承担起推翻帝国的重任,还有赖于一套统一的斗争方案的组织和指导,借以将自身锻造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主体——后现代的“斗士”。他们强调,为了做到这一点,民众的斗争应围绕着以下三个权利而展开。 首先,争取全球公民权。如上所述,鉴于帝国的本体缺乏,民众单凭积极流动——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进行的流动——就能抽空帝国,就足以致使帝国因营养缺乏而衰败。[1]397-400因而,帝国自然不会容忍民众的这种流动,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对其予以阻止和限制。与之相对,为了有效地抗击帝国,民众必须借由积极流动来打破帝国所施加的地域局限,使纯粹的可被穿越的客观空间变成被主观流动和抵抗所激活的生活空间。他们还强调,鉴于帝国控制机制的全球性,对它进行替代的政治方案也必须在相应的全球规模上被推出。因而,民众应努力争取全球流动的自主权,以及在其所居住和工作的国家拥有公民权。他们将这种权利命名为“全球公民权”。借由这种权利,民众不仅能够“指认新地方”、“建立新处所”、“夺取新空间”,而且还能够促成一种“新人类”——“一个有着无限力量的多种肤色的奥菲士”[1]361。鉴于此,他们将争取“全球公民权”确立为抗击帝国的首要任务。 显而易见,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观点是对德勒兹游牧政治学的借鉴与转译。根据他们对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的解读,德勒兹所指认的当今时代的政治主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有鲜明层级化、组织化特征的分子主体,而是后现代的分子主体——精神分裂者和游牧者;新型主体借由自己肯定性和主动性的力,对各种“流”进行着“解码”或“解辖域化”,进而形成“新地球”和“新人类”。在他们的理论中,他们将德勒兹意义上的分子主体转译为民众,将“解码”或“解辖域化”转译成民众的抵抗——“民众对约束的反抗——对归属于一个国家、一种身份和一个民族的奴役进行反抗的斗争。”[1]360一种旨在消除主权施加于民众之上限制的抵抗。这样,他们就将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改造成了流动政治学。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他们的流动政治学的有效性已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正是作为后现代政治主体的流浪者通过其积极而自由地流动,不仅移除了施加于其上的地域限制和种族隔离,消解了“第三世界”;而且还通过全球性的肉体的出逃或混种,“新地球”和“新人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1]362-363 其二,争取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他们认为,在当今的生态政治环境下,一切超验的想象都转为内在的领域,“价值和标准之所有超验的决定因素已丧失了连贯性”[1]34,从而用以衡量事物价值的恒定而同一的标准已不复存在。同时,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日趋巩固,生产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彻底浸透,致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不再清晰可分,从而导致了剥削和支配对象的改变——由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转变为一般性的生产能力,即社会活动及其包容一切的力量。鉴于此,哈特和奈格里主张:“所有为资本的生产所必需的活动都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以使社会酬劳真正成为受保障的收入。一旦公民权扩展到所有的人,我们可以将这种受保障的收入称作公民权的收入,即每个作为社会成员所应得的收入。”[1]403简言之,所有的人在全部时间内都应获得报酬。 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主张,无疑是与他们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立场相一致的。他们推崇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之超验标准的进攻,响应他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号召,盛赞民众对规训体制的各种拒绝“是一种尼采称之为‘价值重估’的创造过程。”[1]274当然,他们所谓的“价值重估”与尼采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尼采的价值重估强调标准的内在化,主张价值标准应由外在于人的超验存在转向人自己的生命世界;而哈特和奈格里的价值重估强调标准的多元化,主张价值的衡量不再单以客观的、经济的因素为尺度,还要虑及社会、文化等非经济方面,尤其注重主观方面。 其三,争取再占有的权利。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再占有的权利是指“民众真正地自我控制和自主地自我生产的权利。”[1]407。在他们看来,“后现代的民众不仅使用机器来生产,而且随着生产方式不断地融入民众的大脑和身体,民众自身愈加变得机器化(更加异化)。”[1]407鉴于此,他们主张新型民众应着力于争取“再占有生产方式的权利”[1]407。同时,随着对语言意蕴、意义以及交际网络的控制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新的无产阶级“都要参加到语言意蕴上的斗争以及反抗资本对社会交际殖民化的斗争中去。”[1]404这就是说,新的无产阶级还应争取拥有对知识、信息、交流和情感再占有的权利。 他们强调,民众争取再占有的权利,就是要在空间意义上的出逃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形变——形成一部完全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和工厂纪律并能创造出新生活的新躯体。[1]216进而由这些新躯体组成一个他们名之为占有力(posse)的组织,“一个社会工人和非物质劳动的组织,一个作为由民众管理、组织和指导的生态政治统一体之生产性、政治性的组织。”[1]410借由这一组织作用的发挥,“作为政治主体和占有力的民众出现在世界舞台上。”[1]410-411至此,流动的民众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主体,成长为后现代的“斗士”。 在这里,他们将实现一种人类学形变作为最终的政治目标,无疑受到了发端于尼采并在德勒兹那里得以丰富和发展的身体哲学的影响。德勒兹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意识哲学;甚至马克思也是在意识和身体的哲学双轨中跋涉。[6]58然而,尼采打破了这一传统,将肉体视为生命唯一的居所,并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7]178口号。德勒兹继承并发展了尼采的理论,认为意识性的人已转变成不再受意识的支配的“无器管身体”。哈特和奈格里继承了德勒兹的身体哲学,并将之应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将一种特定身体的形成直接等同于政治目标的实现。 纵观《帝国》,哈特和奈格里从对非物质劳动霸权及其所引发的生命政治环境的分析出发,在确认帝国之善的自在性和本体缺乏的基础上,通过对革命方案的具体考察,发展出了一个较为完备而视角独具的后现代的革命理论。然而,由于他们固守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法和理论立场,以至于存在诸多悖谬之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非物质劳动问题。究其实质,他们所谓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不过是他们对劳动形式新变化的经验总结,而远非他们所坚称的一种本体性和虚拟性。同时,他们所确认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也是极有问题的。就现实状况而言,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领域,非物质劳动在总量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而且也远未能对生产领域产生决定性影响。 其二,生命政治和欲望问题。哈特和奈格里强调生命政治的内在性,以及对欲望和肉体之力量的确认,不过是延续了旧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的思想传统,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任何积极性的新东西。[8]相反,他们对欲望之本体性与生产性的确认,还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将物质资料的生产指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观点相对立,从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 其三,民众问题。不可否认,在利益日趋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当今无产阶级的某些方面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界定确实需要予以适当调整。然而,哈特和奈格里所发展出的民众概念,其内涵是如此的含糊,以至于没有规定任何实质性内容;其外延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这一新的无产阶级甚至包括了拥有巨大私有资产的资产者,从而隐匿了阶级差别进而消解了剥削与斗争本身;事实上,鉴于在当今分工依然强劲存在的现实,革命主体必然仍旧是作为一个“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9]230的无产阶级。 其四,斗争方案问题。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致使斗争策略显得纸上谈兵和不切实际,可操作性令人怀疑。而且,争取三个权利的观点内容空洞而缺乏新意。其中平等的公民权和公平的报酬权等观点,不过是自由主义正义哲学的老调新弹。[5]而争取再占有的权利不过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且是一个与前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的要求。[10]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上述种种理论缺陷与逻辑硬伤,但毕竟开启了后现代社会革命的宏大叙事。[5]从而仍不失为我们开展社会探讨和理论研究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