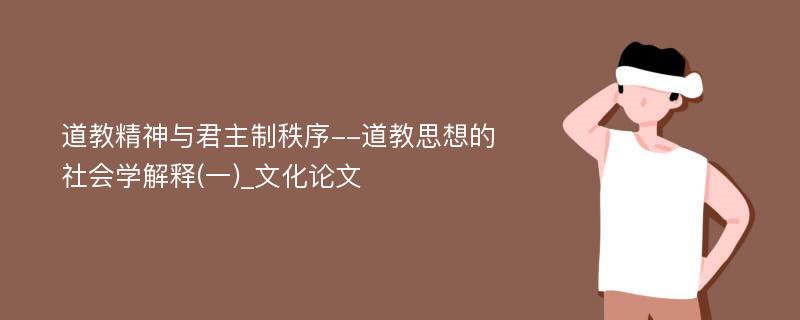
道学精神与君主秩序——对道学思想的一种社会学解释(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君主论文,社会学论文,秩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学精神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以“天秩”为基础而构造“人秩”,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人道应效法天道,即社会生活中应贯彻“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道学精神的内核。它深深地植入于中国人的生活,与君主秩序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郑杭生,男,193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陈劲松,男,196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在职博士生。
一、道学精神及其社会支柱
道学精神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以“天秩”为基础而构造“人秩”。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人道应效法天道,即社会生活中应贯彻“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道学精神的内核。
(一)道学精神的渊源和规定
一种精神总是在正面直视一种问题时才被显现出来。道学精神就是老子(老聃)正面直视历史、社会、人性的一个独特视角。一部五千言之《道德经》,抒解了老子对社会问题的忧患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其中流溢出道学精神的精髓并最终确定了道学精神延续的内在规定性。老子说,
“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三宝”正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即针对“有为”和“无为”这一对矛盾,要敢于“不敢为天下先”,针对“有欲”和“无欲”这一对矛盾,要认识到“治人事莫而啬”(59章);针对“刚柔”(强弱、动静)这一对矛盾,要胸怀慈惠。这“三宝”是老子解决社会问题、构筑新型社会秩序的三把钥匙,它们共同体现了道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首先,把“人道”纳入“天道”。“人道”即人类社会的秩序,它的构建和运行都应效法天之道,与道为一。他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
这是告诉人们,人事(社会)受自然而然的法则所支配,人类的社会秩序也应效法于此。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老子建立社会秩序的最高公理。
自然秩序的最根本法则是什么呢?老子认为,自然“无为”,天道“无为”,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罔恢恢,疏而不失。(73章)
天之道,即自然的法则,它是不必争斗即可致胜,无声胜有声,一切无须召唤就会自动到来,宽缓似乎善于谋划,自然之道是如此恢宏广大,疏而不漏。这个“天之道”即人类社会应效仿的法则,便是无为,即不争、不言、不召。
其次,消解社会动乱的根源即“有欲”。老子认为,一切社会冲突和纠纷都是因为人们的欲望。他看到社会伦理规范是对人们欲望的制约,但它自身又是社会动乱以后的产物,老子希望能至纯素古朴的社会,因此他通过对社会伦理规范的批判来直接消解动乱之根即“欲”。他说,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
又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
这是说,自然无为的“大道”被破坏了,人们用“礼义”来制约社会行为;因为“六亲”之间关系不和谐,所以用“孝慈”来整合;国家动乱不定,因此人们希望有“忠臣”保国安民。所谓的“礼”,是因为人们的忠信之义几乎殆尽之故,它成为各种动乱的罪魁祸首了。
仁义、孝慈、忠信、礼等都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一方面它们是动乱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动乱的结果。作为动乱的结果,它们是“有欲”、“多欲”的产物,这样,老子把社会动乱的原因直接归结为“有欲”,这正是老子的魅力所在。因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冲突、矛盾,即“有欲”和“无欲”的冲突和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源,又是个人生活的根据。
解决社会秩序混乱的第一步在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9章)即首先要抛弃智、仁、义、孝、慈、利,使民不知这些社会规范之为何物。第二步在于要使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9章)。做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实其腹”(3章)。老子看到了“欲”与“乱”的关系:“民心”乱,则社会乱;而“心”乱在于“见可欲”;因此老子要求人们“寡欲”。“寡欲”并不是“灭欲”,更不是“无欲”,可见老子看到了欲望对于社会存在的必要性,这和后来的宋明道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有着很大区别。“寡欲”的标准是什么呢?即“虚心”和“实腹”。
再次,控制社会的策略,在老子看来,“人道”应法“天道”,而天道是“自然无为”,人类社会毕竟只是“效法”,并不能达到真正的“无为状态”。这里的“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心灵对社会秩序社会规则的一种背叛,一种对自然的回归,这种背叛和回归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无为”并不是人类心灵的寂灭,而是心灵自身力量的憩息地,是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束缚的一种抒解;因此老子在这里给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一席之地。既然真正的“无为”不可达到,因此老子主张从“有为”逼近“无为”,以至于“无为而无不为”。效法“无为”而至“无不为”的具体方法,可以归结为贵柔、谦下、宽容、见微等等。
(1)贵柔。老子说,“柔弱胜刚强”(26章), “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43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是说,大道自然无为,可以通过相反相成来得以实现;弱者,无为,它却能至强,至有为,几乎能表现大道“自然无为”的功用。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驰骋天下之最坚强的东西,柔弱能胜过刚强。老子告诉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柔弱”的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刚强),这种“柔弱”的方法几近于“天道”化育万物所用“无为”之方法。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战术: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36章)
(2)谦下宽容。老子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 发现若要成自然之主,或社会之王,都要有谦下和宽容的精神。谦下和宽容是“贵柔”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66章)圣人当效法于此。他说,“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由此处理国家和国家之关系时也取法于此,他说,“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 ”(61章)
“谦下”必将以“宽容”为怀。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要做到“无弃人”,“无弃物”,应该具有“报怨以德”(63章),“执左契,而不责于人”(79章)的宽阔胸怀,唯其如此,方可成就“百谷王”之业。
(3)见微知著。真正做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防乱于末然, 还必须培养一种“见微知著”的素质。他告诫人们,“合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4章)。又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3章)对于治和乱的关系,他说,“其安易持,其末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章)
最后,老子提示了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图景。老子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死不相往来。 (80章)
(二)道学精神的社会支柱
精神或思想要占有真实的生活,必须找到执行这种思想的社会阶级。一方面,道学固有的内在性格通过道学主要社会支柱的社会阶级,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依其社会地位影响并最终限定了道学的发展。我们把道学精神的社会支柱简要分为封建君主阶层、封建官僚阶层、封建社会下层民众、道教领袖和道士阶层及道学知识分子等五种类型。
有必要指出,道学思想在中国发展有一个从纯道学向道教的演化过程:在道学宗教化的过程中又有一个从下层民间宗教向上层道教转化的过程。道学演化出道教标志着道学理论寻找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柱。
(1)封建君主阶层。封建君主对道学、 道教的解释和应用可分成几种类型,即攀附型、务实型、延命型等。
攀附型。借此以提高自己身份,使臣僚百姓确信自己出身高贵。如战国时期齐之威王,攀附黄帝为自己祖先,借以使人确信“田氏代齐”的合法性。再如,李唐王朝推翻隋炀帝统治后,为了确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密派他人传授天意,说自己是老子世孙(老子姓李,名聃)等。
务实型。老子强调“清静天下自正”,那些起于民不聊生的开国之君往往为寻求天下安宁,民心归正,而找到了老子。最典型的有汉初黄老之治、唐初贞观之治等。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接受了大臣陆贾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其后继者惠帝、吕氏、文帝、景帝延而用之。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近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繁荣了,出现了“文景盛世”。唐王朝开国之初,出现“贞观之治”亦与李世民善于吸收运用道家学说,以“贵静”为治国之策略不无相关。
延命型。人生短暂,尘世可恋,帝王君主在玩天下于股掌之后,往往最恐惧的(尤其是晚年)便是死亡,道学、道教中养生术、巫术因素为延命型皇帝提供了精神支柱。如秦王赢政一统六国后,最大渴求便是“与仙有缘”,多次派方士下海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以通神成仙而封禅。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服食金丹求长生的外丹术在统治者中间盛行,唐代不少君主皆热衷于炼丹服丹,唐太宗、唐武宗、唐宣宗等皆服食金丹中毒而死。
(2)官僚、士大夫阶层。官僚、士大夫阶层对道学、 道教的应用和发挥往往和封建君主对道学、道教的态度分不开。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表现为后者对前者道学认识的采纳和奉行(合理化建议),或者表现为前者对后者所奉行政策的执行。如,为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提出新的治国方略,高祖刘邦指示陆贾著《新语》一书。陆贾《新语》每成一篇,即呈奏刘邦过目,“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这表明刘邦接受了陆贾的政治主张。陆贾《新语》有儒道兼备的特色,但崇尚“无为而治”是它的核心。《新语·无为》篇曰:“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而天下治。”曹参任齐相时,即聘黄老学者盖公为师,“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刘国安集(宁也),大称贤相”。后来肖何死曹参升任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死后百姓歌曰:“肖何为法,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在此之前,作为政治家的管子(有散篇于《管子》中)、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积极地改造和利用了道家精神。
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道学之集大成者,其辅佐梁武帝取得政权,却不愿为官,但朝中大事总要听取他的意见,被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
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建设唐初政权的魏征,先当过道士。当他辅佐李世民时,常常也是把道家的“无为而治”作为理政的目标。魏征在一次上书中说:“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铖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嘉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资治通鉴》128页,中华书局1956 版)“十思”集中体现了要求君主清虚自守的道家风范。
这些说明官僚、士大夫以积极的态度发挥和运用道家的精神,辅佐朝政,往往都会取得与民生息、天下泰平,经济繁荣的政治局面。但是也有些执左道之官僚、士大夫取道教之未流如神仙巫术类来取媚于君,导致王朝的衰落、灭亡,其例子可谓历历可数。例如,唐玄宗治政后期,奸相李林甫受宠得势就与神仙道术有较大联系。李氏本人即是一个嘉好道术之人,改自己的住宅为道观,“以祝圣寿”,常以仙药道术迎合玄宗。左宰相陈希烈同样以道术作为获庞的手段,“以讲《老》、《庄》得也,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直接促成唐王朝的衰落。北宋末年朝政的腐败与蔡京、蔡攸父子乱政有着重要的联系,蔡京父子是道教神学的迷信者。身为宰相,蔡京借道教来迎合和讨好徽宗,并向徽宗推荐许多道士,最终使宋徽宗溺信于道,加速靖康之祸的到来。
(3)下层民众。下层民众很少有机会接受道学的教育, 但道学中许多重要思想却在下层民众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归于道教。正如上层统治者希求“神道设教”来进行思想统治一样,下层民众也有寻求解救的心理需求。简言之,道家通过道教这个中间层次而获得了作为广泛的社会支柱的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眼中的道学或道教主要是做为一种神学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对宇宙的本质、人生的真谛、彼岸的世界的存在以及达到彼岸世界的途径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回答。道家宗教化过程主要在两汉之际,其主要经典有《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想尔注》把《老子》的“道”人格化和神格化,阐扬长生成仙说,论证彼岸世界的存在。《太平经》还试图创立神仙系统,并且强调“内以至寿,外以治理”,以“学道”和“得道”为人生之终极目的。把儒家一些社会行为伦理规范纳入了道学之中,从而真正地控制着人们的世俗行为,这也是道学或道教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转折。“学道”之人,首先要做到忠君,敬师、事亲以积德。“学问何者为急?……寿孝为急”,“寿者长生,与天同精;孝者下承顺其上,与地同声”,“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尊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不穷之业也。此三者,道德之门户也”,“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其次,要守一以养身。再其次,食气服药。
道教一产生,就和下层民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其社会作用不仅表现在平时它左右、制约着世俗社会行为,而且表现在社会动乱时代,它对下层民众起着一种组织和号召的作用。历次大的农民起义都有道教力量的存在。东汉末期的“黄巾大起义”、魏晋时代的石冰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宋时的“方腊起义”,元后期的明教等等便是。这又表明道学、道教具有一定的抗拒现实社会的力量,有着破坏既存秩序的力量。
(4)道教领袖和道士阶层。 道教领袖和道士阶层是道学生存的重要支柱。正是通过这个中介层次,帝王君主和下层民众才和道学直接相关。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于道学,道士的前身是方士。道教领袖和道士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极力捍卫道教的优等地位,从而直接延续了道学的发展。从儒、释、道的相互指责中,便可见道教领袖和道士阶层是道学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东汉时期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等传说。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化胡经》增益此说,谓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以佛为道教弟子,是道教论证“道先佛后”,“道优佛劣”的主要根据。
魏太武帝自称太平真君,成为第一位道教皇帝,其国号亦改为太平真君,道教成为国教。梁武帝萧衍在陶弘景帮助下取代南齐政权,陶虽不愿出山为官,但朝中大事总要听取他的意见,被时人称作“山中宰相。”隋文帝的开皇年号来自道经,隋文帝将擅长辟谷之术的道士徐则等人留在宫中,并向茅山派道士王远知请教神仙之事且亲执弟子之礼。唐李渊的起兵更是得力于道士和谶语;由于在亡隋风潮中道士的巨大贡献,高祖武德八年,亲临国学,正式下诏宣布三教先后,道先、儒次,释再次;至玄宗二十九年,设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考试合格者,与贡举及第者同等待遇,从而在科举中首次开创了道举。宋徽宗期间,道士也受到特殊礼遇。为了整肃和培养道士队伍,在全国范围内促进人们学习、研究道教经典,徽宗特令各地选派道士赴京,于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命令各地州县依儒学的样式设立道学,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并通过每年按考试成绩分别授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号;徽宗还热哀于道教经典的收集、编写,政和年间编成了《政和万寿道藏》,并亲注《道德经》等;授意臣下“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从此他拥有兼天神、人君、教主于一身的神圣身份。总之,朝庭尊崇道教,道士享有殊荣,尤其当君主或自加道号(这便是最大的道教领袖)或有意识把道教作为神教来统治黎民百姓时,道学地位就相应提高,道学经典也被颂读,甚至被视作考试经典。
(5)道学知识分子阶层。老子强调人道应效法天道,人道有为, 天道无为。“效法天道”即应是有为逼真于无为,因为人类必然要生存,不可能真正的介入“无为”状态,因此这里老子的“无为”其实可以看作是人类心灵对一切社会秩序、社会规则(有为)的一种背叛,一种对自然的回归,即心的回归。这种背叛和回归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无为”并不是人类心灵的寂灭,而是心灵自身力量的憩息地,是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束缚的一种抒解,是心灵的奔放和自由。因此,老子《道德经》为象庄子这种纯粹为自己精神而生活的文人留下了一片天空,也为那些官场失意、儒途沧桑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块心灵的慰籍地。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称得上完全不愿和世俗政权同流合污的典型。即使《道德经》的作者老聃也曾为西周小吏。庄子生活十分穷困,但《史记》本传谓楚王遣使臣请他去楚国为相,被他拒绝了。他在《庄子》里酣畅淋漓地把老子思想发挥至极致。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演父》、《盗跖》、《祛箧》,以诋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思想和老子思想有许多区别,但《庄子》却是从《老子》中引申出一种飘然若仙的人生画卷,从此规范出中国古代文人一种向往。《庄子》把“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最后根源,直接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思想;肯定道不离物,使老子的“道可道”具象化;其最显著的还在于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发挥至相对主义的“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等,这往往被视作庄子比老子更消极无为的根据,其实这是人类心灵深处的独白,表现出人类心灵在面对“万物”、“是非”、“物我”等矛盾时的痛苦与超越,也是老子“天大、地大、我亦大”观点的挥扬。
文人墨客既受道家意识影响,又传播着道家精神,唐代文坛最能表现出这一点。道教被视为唐王朝的国教,与此同时道家学说广泛传播,道学意识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文人学士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唐道士司马承祯的“仙宗十友”都是当时文坛名人,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贺知章等。有“谪仙”、“诗仙”之称的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等诗表现出诗人和道家的精神联系。今天,翻开唐代诗文,字里行间,常常可以看见道家思想的烙印。信仰道学的艺术家(文人墨客)本身就是道学的脊梁。在中国大凡有成就的文人墨客都与道学有着很深的精神之恋,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可以避开世俗纷扰的、真正的心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吸取并丰富着道学之精神、道学之博大。
(末完待续)
